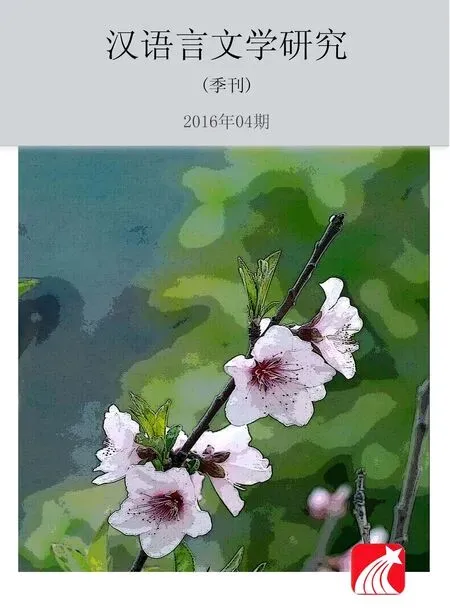地方性、民族形式与国家想象
2016-12-29季剑青
季剑青
地方性、民族形式与国家想象
季剑青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往往被视为一种美学风格,相关的讨论经常只停留在形式层面。李松睿的新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却注意到,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的笔下,地方性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地方性的关切,显然已经突破了形式和技法的范围,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因而,尽管这部著作仍以小说文本的分析为主体,但分析过程本身却包含了自觉的理论视角和问题意识,从而使得全书获得了一般小说研究著作所不具备的分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研究之外的历史学领域,就会发现地方的视角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的编纂和研究之中。且不说源远流长且延续至今的地方志的编撰传统,近代以来兴起的新史学也非常重视地方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地方史的研究。当代历史学者更是在域外理论的刺激下,在“国家/社会”“中心/边缘”等框架下挖掘地方视角的潜力。无论是在王朝国家的大一统格局下,还是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地方的意义往往是在与中央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参照和互动下凸显的。在这样的视野下,20世纪40年代的特殊性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和国民政府的内迁,政治权力一体化运作的空间不复存在,中国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央的失坠使得地方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抗战时期地方性成为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界和知识界讨论的核心话题。
作者显然注意到了抗战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于地方性问题的意义,正是抗战所造成的生活境遇的改变,“使得地方风光、地域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带有地方性特征的事物,真正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作家、批评家的生活之中”①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尤为重要的是,抗战在打破旧的权力中心的同时,也在召唤新的国家想象。从这个角度,作者对“民族形式”论争这一老问题,以及民族形式与地方性问题的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书中数次引用黄芝岗《论民族形式》中那段著名的话:“抗日的内容是火”,地方性的“旧形式”则是“薪炭”;而“‘民族的形式’则是烈火锻炼成的”,因此“薪炭”的作用就在于“使内容的火燃烧得更其猛烈”。②同上,第10、33、102页。地方性为民族形式的锻造提供了材料,而民族形式又关涉着“抗战建国”的构想:“在文艺‘民族形式’论争背后,隐藏着的是不同的对于民族国家未来的构想与理解”。③同上,第92页。
发生在国统区文坛的“民族形式”论争,不仅展开了对地方性与民族形式之间关系的讨论,更进一步延伸出民族形式如何获得“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如果说只有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民族形式,那么也只有通过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形式,中国的文学艺术才能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一席之地。这就是萧三那句著名的“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④同上,第107页。背后的逻辑,也是胡风强调五四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的真正用心所在。作者敏锐地指出,地方性与民族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两组概念实际上处于同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地方—民族—世界’的递进关系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被反复确认,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基本共识”①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第103页。。也许可以补充的是,这种递进关系包含着反向的辩证运动。正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关切,使得地方性的材料和叙述上升为全民族的寓言,获得了某种普遍性,这在作者专章分析的老舍40年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样,也正是4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家自觉的国际主义视野,正是他们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地位的强烈关切,赋予民族形式以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也把他们所呼唤的民族形式与晚清以来建立在对传统的体认的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30年代国民党官方的民族主义运动,鲜明地区分了开来。
民族形式问题在解放区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与国统区文艺界经由与地方形式的接触而展开民族形式的讨论这一路径有所不同,解放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通过民族形式加以本土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在毛泽东这里,由马克思主义来保证的普遍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通过民族形式来取得本土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受到国统区的影响,追求的是借助地方性特征来获得“世界性”和“普遍性”,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这种追求会在受到1942年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批评后突然中断。③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第110页。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改造自己的阶级立场,写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作品。《讲话》没有专门讨论民族形式和地方性的问题,贯穿其中的始终是阶级性这一普遍的尺度。然而当像周立波这样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努力按照《讲话》的要求去表现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时,他的作品却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来,其中特别显眼的便是他对方言土语的自觉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放区文艺中的地方性特征乃是阶级话语支配的结果,“阶级性成了衡量文学的地方性特征的价值尺度”④同上,第113页。。
有趣的是,周立波的这种努力却并未受到解放区文艺理论家的认可,他作品中的地方色彩不仅没有为他赢得荣誉,反而成为他未能真正改造自己获得“无产阶级立场”,从而思想感情方面存在缺陷的标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赵树理,这位后来被追认为山西“山药蛋派”鼻祖的小说家,当时备受解放区文艺理论界的推崇,却从没有人强调他作品中的地方性色彩。为了解释这种意味深长的现象,作者巧妙地引入认知“装置”的概念,非常精彩地分析了解放区批评家如何在这种认知“装置”的支配下,“自动地把这位作家(按:指赵树理)笔下的方言土语‘过滤’为‘群众的语言’或‘人民的语言’”⑤同上,第200—201页。。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赵树理的小说也不像老舍的小说那样提供了具有民俗学意味的标本,而是刻画了以整体形象出现的“人民大众”。⑥同上,第232页。赵树理小说中地方性的“隐退”,确实是作者的独到发现,对于理解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是具有症候性意义的。这表现出作者锐利的眼光,他基于文本细读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的分析,也令人拍案叫绝。
概括地说,主导40年代解放区文艺理论界的主要是阶级性的观念,其次是民族性,地方性即便有所表现,也往往是批评的对象。在解放区的话语体系中,民族性是在和阶级性的纠缠中,而不是通过对地方性的提升来呈现的。贺桂梅曾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构想中,“新的民族形式必须在两个纬度上展开,一是相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普遍话语的民族性,一是相对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话语的阶级性”①贺桂梅:《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为了调和阶级话语的普遍性与抗战中建立 “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之间的紧张,毛泽东把由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界定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6页。,使其在具备阶级代表性的同时,也获得了代表全民族的资格。正是着眼于“人民大众”在中华民族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给延安根据地的抗日敌后斗争,赋予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历史任务。他批评有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因为对延安生活不熟悉而生出“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想要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以为这样才有 “全国意义”。毛泽东告诫这些作家,大后方的读者也希望读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这句话很像“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可实际上讨论的是延安这一特定环境的“地方性”如何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毛泽东的逻辑不是从地方性本身提升到民族性,而是强调延安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内在地就体现了“全国性”和“民族性”,因为“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③同上,第876-877页。。这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对新的国家的想象。它将是一个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而非简单地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民族国家。
与作者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讨论相比,书中关于沦陷区作家对地方性的认知和处理的讨论稍显薄弱。在作者看来,由于沦陷区高压的政治氛围,“沦陷区文艺理论家对乡土文学的大力倡导、对地方色彩的反复强调,其最终目的在于让作家真实地写出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生活”,“借助于意义略显含混的地方性特征,使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战争年代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在言论动辄得咎的沦陷区,或许已经是那些正直的文艺理论家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④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第126页。作者以东北沦陷区作家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例,具体分析了小说中东北地方风物描写,如何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不允许直接表达的诸多意义。这样的论述自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展开的空间:在这种复杂暧昧的政治气候下,民族和国家议题是不是有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呈现?如果是的话,这种呈现方式与地方性又是怎样的关系?
这里不妨以书中没有涉及的周作人作一点提示性的探讨。1945年7月,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谈胡俗》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北京的少数民族习俗。考虑到北京历史上曾多次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都城,而在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北京,民族关系又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周作人撰写此文的用心颇值得玩味。他在文中提出北京的所谓“胡俗”不过是北方一地的风俗,“我们翻阅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点心有萨齐玛是满洲制法。此外也还多是古俗留遗,不大有什么特殊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并没有什么,虽然有些与别处不同的生活习惯,只是风土之偶异而已”。⑤周作人:《谈胡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6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用“风土之偶异”造成的地方性特征,来淡化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所带来的创伤体验,消解种族对立的意味,隐隐有为自己沦陷时期的附逆辩解的用心。周作人煞费苦心的表述提醒我们,沦陷区作家的地方性书写,是不是也隐含着化解民族认同危机的心理动机呢?在伪满洲国和华北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作家,借由地方风物的描写,是不是也在曲折地表达某种民族意识和国家想象呢?
当然,我们不必要求作者在一本以“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为主题的著作中,充分地讨论甚至解决地方性、民族形式与国家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包含的诸多问题。重要的是,这部既有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又不乏深刻见地的出色论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地方性的概念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理论潜力,如果加以充分地开掘,将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怎样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说《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一书开辟了一个新的问题域亦不为过。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该书将激发更多研究者去思考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地方性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