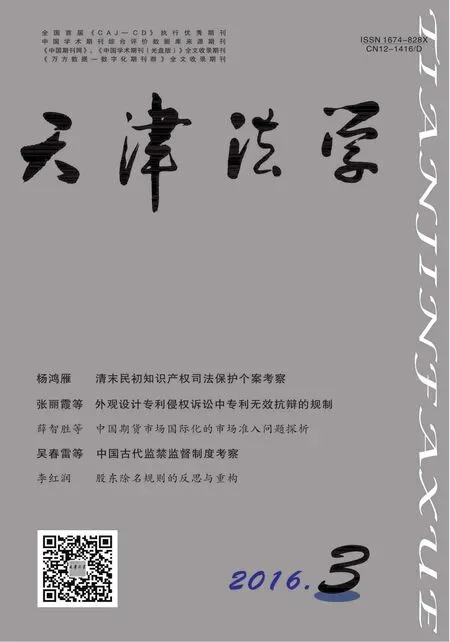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与双边投资协定的解释问题探析
2016-12-19张建
张建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国际法研究·
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与双边投资协定的解释问题探析
张建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现代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主体已经由传统的国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并伴生了专门针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仲裁程序。与传统的商事仲裁不同,以ICSID为基础的投资条约仲裁不要求严格意义的仲裁条款,而是以“书面同意提交”为前提,这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合意解释留出了可裁量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在向外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将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由原本的征收与国有化补偿问题开放到所有投资事项,因而有必要充分理解ICSID仲裁的管辖权要件。此外,对投资协定中的关键条款进行把握也关系到投资仲裁的程序正当性,如公正公平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保护伞条款。
国际投资仲裁;书面同意提交;最惠国待遇条款
一、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的主体转型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际法的开端,其不仅确立了领土主权及主权平等的原则,也使得国籍概念取得了独立于宗教的法律内涵。与此相呼应的是,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突显了国家的主体功能,即投资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与投资者母国的属人管辖权[1]。这种国家本位观念具体体现为:其一,投资东道国有权要求先行“用尽当地救济”,原因在于外国投资者既然选择前往东道国实施投资行为,其便负有义务遵循当地法律并受行为地国法院的属地管辖权制约;其二,投资者母国实施的外交保护权,即居所或财产位于东道国的事实并不使投资者丧失其国籍,当本国国民在境外遭遇他国国家不法行为侵害时,母国有权在投资者穷尽当地救济仍未解决争议的基础上,以国家名义出面解决争端[2]。尽管这两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却相互依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第14条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从习惯国际法层面确立实定法条款,为外交保护权的行使预设了前提,而第15条则为该原则的适用设定了例外。不过,总体来看,外交保护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议解决升格为国家间争端,政治色彩浓于法律色彩:一方面,有些国家基于政治考量不愿行使外交保护权,致使投资者权益保护被无端架空;另一方面,利益真正受损的外国投资者本人因母国的介入而丧失了直接诉因,因而产生了针对法律性的争议解决机制的需求。实践中,1840年之后大约设立了60多个国家间混合求偿仲裁庭专门解决此类投资争端,尤其在1945年至1980年期间,伴随民族国家争取主权独立,针对外国人财产实施国有化或征收措施致使各类利益矛盾纠葛,海外私人投资者对直接索赔权的吁求愈发强烈。
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议解决机制(简称ISDS)的改革因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的实施而得以成为现实。该公约设立调解与仲裁两套机制,旨在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直接针对投资东道国的救济,并力图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重平衡。尤其是《华盛顿公约》项下的仲裁,以投资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作为“同意”中心受理案件的基础,在约定此类仲裁的同时意味着投资者放弃了寻求母国外交保护的权利[3]。根据该公约,投资者享有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在仲裁或调解的法律程序中对抗东道国国家的争议解决请求权,而不复附属于其母国外交保护权或代位求偿权,摆脱了非独立法律救济权的束缚。以此为标志,ISDS机制由国家为主体的阶段向投资者个人为主体的阶段实现转型,这不仅是尊重私权救济独立性的产物,也是投资争端解决发展进程中人本性复苏的征兆。
二、海外投资者对争议解决自由同意的扩张性解读
《华盛顿公约》项下的投资仲裁所管辖的案件有特定的范围,这不仅体现在其第二章当中,也受公约本身的适用范围影响,意即只有以国际法上条约义务之违反为基础而引发的“条约诉求”方可纳入中心受案范围,而单纯的合同义务违反所引发的“合同诉求”不属于公约范畴之内,不过对两类诉求的理论区分却面临诸多实践困境,“一刀切式”的标准在处理事实各异的个案时失灵的状况时有发生。正如某些仲裁庭所指出的:东道国所实施的某项特定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对投资合同与国际法的违反,但如果仅仅是对合同义务的违约却并不当然构成对条约义务的违反,逻辑上讲,两类诉求不完全是相互排他的,毋宁仅作为区分义务违反的标准系双重违反抑或单一违反而已[4]。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特指仲裁请求权的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均源自国际条约授予,就中心管辖的法律基础而言,《华盛顿公约》从性质上属于典型的程序性公约,但并不能构成实体投资待遇与投资权利的来源,而国家同意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通常体现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当中。尤其自1959年阿巴斯—肖克罗斯境外投资公约草案及1967年经合组织(OECD)外国人财产保护公约草案之后,诸多国家纷纷订立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有利于外国投资与外国投资者的保护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早期《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新发展。
需要明确的是,在符合了程序性的《华盛顿公约》的适用范围并且构成对实体条约法上投资权利违反的基础上,还需充分满足公约第25条的管辖权行使要件。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公约对争议双方将纠纷提交中心管辖的约定并未采用惯常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而是采用了“书面同意提交”的措辞。这意味着,海外投资者与东道国就争议解决的约定,尤其是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的“同意”,既可以同时在同一文件中表达出来,也可以在不同时间于不同文件中表达出来。尤其在后一类情形下,通常先有缔约东道国的国内立法或其作为缔约方的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中单方面表示出将特定类型的争端诉诸中心仲裁,然后于争端发生后外国投资者径行向中心提出仲裁申请,便构成了双方争端解决的一致同意[5]。可见,从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入手来解决投资仲裁的管辖权问题至关重要,例如Brierley教授所提出的对角线条款理论即为典型(如图1所示)。该理论提出,应当允许投资者依据投资东道国所缔结的条约直接提出仲裁诉求,例如瑞士与斯里兰卡于1981年签订的BIT中即采用此种条款,从而将国家间关于争端解决约定的效力延伸至投资者,从而赋予投资者以直接索赔权。

图1:国际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的对角线理论示例
当然,BIT中的核心条款主要涵盖关于实体投资待遇的内容,诸如公正公平待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征收与国有化等,但相关的协定通常会明确违反上述协定中的哪些条款可以提交仲裁,以厘定可仲裁事项的范围。美国、加拿大即采取此类方式,将可提交仲裁的范围取决于是否符合特定实体待遇条件。相比而言,美国稍显宽泛,协定中规定只要存在违反透明度要求的,投资者即有权提交仲裁,而加拿大则明确排除[6]。因此,同意提交ISDS机制的可仲裁事项范围往往体现于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当中。这意味着,在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与签订过程中,缔约国就要对以后可能会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范围尽可能作出明确而清楚的限定。从效力上讲,这个同意的范围一旦做出以后,不得通过单方面予以撤销,因此需要结合本国所处的国际投资格局进行慎重把握。事实上,我国在签订BIT的过程中,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接受度与提交国际仲裁事项的范围经历了从无至有、由窄至宽的演变。
三、中国对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接受范围的演变
如前所述,ISDS式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在整个国际经贸领域尚属新兴形式,但提交世界银行体系下的ICSID仲裁并非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争议的唯一选项,尤其对于非《华盛顿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在签订BIT时往往允许投资者在其他国际仲裁机构中进行选择。尽管投资仲裁与典型的国际商事仲裁差异显著,但一些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伦敦国际仲裁院等,并不排除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其他的类似机构还有法兰克福、维也纳、开罗、吉隆坡、香港等地的仲裁中心,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程序中多根据BIT或投资协议的约定援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简称《UNCITRAL仲裁规则》)或《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简称《ICC仲裁规则》)。因此,投资争议仲裁对国际性仲裁机构与国际仲裁从业者而言亦不失为新的增长点。
颇值得一提的是,对我国而言,尽管早在1982年我国就与瑞典缔结了第一份双边投资条约,但却迟至1990年2月才签署《华盛顿公约》,并于1993年1月对公约予以批准。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尽管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向外国投资者传达出政府吸引外资的诚意与决心,但公约本身的部分条款未必符合我国所处的国际立场或彰显我国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例如公约在准据法选择上使用并未被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国际法”来纠正东道国的国内法、对征收及国有化的概念做相对宽泛的解释、片面强调投资者权益以致双方保护失衡,因而我国不得不在充分研究、慎重考虑后方成为公约缔约国[7]。此外,《华盛顿公约》第25条明确规定,对公约缔约国而言,加入公约本身并不意味着自动接收了ICSID仲裁管辖权,而需要以前文所述及的“书面同意提交”为前提,而在投资争端仲裁方面,我国所签订的BIT基本上奉行相对保守甚至非常严格的态度,仅约定将征收及国有化补偿数额的有关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但自从1998年中国与巴巴多斯缔结的BIT中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把与投资有关的所有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以后,投资保护协定的内容较原来主要解决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丰富,可仲裁事项的范围扩张至概括性的全面同意,这既彰显出中国对自身投资环境和国际仲裁机制的信心,也符合国际投资争议解决领域的一般化趋势。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这种全面接受国际仲裁管辖权的趋势愈发凸显。据统计,我国所订立的现行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至少有104项,在入世之后或新增或修订,一改以往的态度,允许将投资争端提交仲裁事项的态度全面放开。这意味着,投资条约所使用的措辞是任何争议都可以提交国际仲裁,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往往落在外国投资者手中。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中国当下居于投资地位转型期,即我国既是“引进来战略”下的资本输入大国,又是“走出去战略”下的资本输出大国的混同身份。将可允许提交仲裁的事项放开,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改良了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同时为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在外国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风险提供来自条约项下保护,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当下所开展的“一带一路”投资战略就愈发必要。截至2016年5月,公开报道与我国有关的投资条约仲裁案件共有6起:谢叶琛诉秘鲁案、黑龙江国际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共和国案、Ekran Berhad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共和国案和Ansung Housing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国家与企业所遭遇的投资争端仲裁会更为频繁,因而对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问题的关注具备迫切的现实意义。
四、ICSID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的法定要件剖析
根据ICSID公约第25条,中心行使管辖权须同时满足四方面法定要件:
(一)主观要件
在主观要件上,必须存在争端双方将其特定争端提交中心的书面同意,这意味着中心在管辖权行使时奉行的是自愿管辖的原则而非推行强制管辖权。问题是,既然《公约》同时提供了调解和仲裁两种方法,是否要求双方的书面同意必须明确到是仲裁还是调解?例证表明,《公约》任何条款皆未规定同意中心管辖时必须明确到具体是仲裁还是调解,只要认可中心的管辖,选择权便落到率先启动程序的一方当事人身上。此外,“书面同意”的表现方式有三类基本框架:一是东道国法律的授权;二是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所签投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三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缔结或共同加入的国际投资协定(前文已有阐述,此处不再详加论证)。
(二)客体要件
在客体要件上,从对物管辖权的角度分析,争端本身必须是直接因外国投资而产生的法律性质的争议。对于争议本身的界定,通常用以指称有关当事人各方对于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有不同的主张,而争议的产生归结为利益冲突和认识分歧,其既包括有分歧的争论、意志冲突,也涵盖未解决的关系、互有冲突的观点。而争端的法律性要求,意在将对物管辖限定在涉及法律权利或义务的存在与否或范围大小,或涉及因违背法律义务而产生的赔偿的性质或范围,用以与纯粹的政治或经济争端区分开来。不过,客体上最难以判定的是如何确定争议是否围绕一个合法的、适格的、受实体投资条约保护的“直接投资”而展开,而对“直接投资”的界定首先要受制于对“投资”的定义。各类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通常会就“投资”作出相对宽泛的定义,既有采取抽象概括方式者,也不乏具体列举方式者,更有二者的结合运用。
(三)主体要件
在主体要件上,从对人管辖权的角度分析,争端一方必须是《公约》缔约国的国民,且同时争端对方是《公约》的另一缔约国。
1.关于投资东道国,其必须是缔约国,以确保该国在同意中心管辖后受公约规定的约束与保护。同时,东道国既包括缔约国政府,也包括该国的“组成部分或机构”。根据《公约》第25条第1款,每一缔约国得自由把特定的自认为合格的公共实体指派到中心作为中心程序当事人,此种指派可构成这类实体具备“组成部分或机构”地位的证据和这些实体能够有效作出接受中心管辖同意的一个前提条件。不过,实践中难判定的是,缔约国下的哪些组成部分有权享有BIT的保护,例如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即为典型,其自身能否作为主体而享有ICSID仲裁中的当事人资格。在香港尚未回归祖国之前,英国已经将香港作为英联邦的组成部分指派到ICSID中心,但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国却迄今尚未将其作为组成部分派到中心,不过从理论上探讨是完全可以进行指派的,因为现在香港和大陆之间在双边投资条约方面存在两套体系。一方面,香港作为拥有一定立法自主权的特别行政区,自身可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另一方面,大陆作为国家的身份也可以签订协定。目前香港已经同其它国家签订了十余项双边投资协定,但同时香港作为中国的组成部分,亦有权在ICSID框架内以缔约国组成部分的身份参与仲裁,该问题在“谢叶深案”中尤其突出。
2.关于外国投资者,之所以将其资格限定为另一缔约国国民,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首先,要确保投资者受第27条约束,不得就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已经确定向中心提交解决的争端请求外交保护;其次,要使投资者受第54条第1款的约束,对不利于本国投资者的中心裁决,母国作为缔约国仍然负有承认与执行的义务。对于自然人投资者的认定,向来以国籍为关键标准;而法人投资者的认定,则兼采国籍标准与控制标准。所谓“控制标准”,主要是考量到如下情形的可能性:某些投资者虽然缔约东道国的国籍,如果单纯采取国籍标准,则此类投资者属于东道国“国内投资者”而非“外国投资者”,无权援用公约框架;但与此同时,该法人是由外国人所控制的(控制的方式包括股权与非股权的控制),那在此类情况下是否应当让它作为另一缔约国国民的身份来参加仲裁的问题,就取决于双边投资协议的规定。当然,公约同时明确规定,如果双方缔约国同意为了公约的目的,他可以把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但是受外国控制的法人也视作是外国投资者,则此类受控外国公司有权援用公约项下的仲裁机制进行争议解决。
(四)时间要件
最后,要符合属时管辖权的前提,即涉案相关条约及协定必须在争端所涉事实发生及争端解决的相关时间点上是可适用的。如前所述,存在一项可适用的实体投资条约是投资者能够寻求国际投资仲裁的前提,也是形成仲裁请求权的实体要件。一项BIT的属时效力往往规定在协定的最后条款部分,包括生效日期、有效期、协定的延展及对在终止生效之前的投资保护;同时,也有些BIT在投资的定义中或以专门条款规定条约惠及生效之前所进行的投资[8]。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BIT生效之前的投资能否援用BIT寻求保护和救济?早期的实践倾向于仅仅保护BIT生效之后所进行的投资,即“新的投资”,但新近缔约实践的立场是,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形下,先前的投资同样可以受到保护,例如阿根廷与美国所签订的BIT规定,该协定既适用于协定生效之前即已存在的投资,也适用于其后进行或获得的新投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比利时王国投资条约仲裁案属于这方面的典型仲裁例证。在该案中,争议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及《议定书》(2005年6月6日签订,2009年12月1日生效,简称“新约”)生效前,申请人平安于2012年9月亦即新约生效后提起仲裁。平安在管辖权问题上依赖于2009年新约,在实体问题上则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及《议定书》(1984年6月4日签订,1986年10月5日生效,简称“旧约”)。被申请人比利时主张仲裁庭对新约生效前发生的争议不具有管辖权,此一异议为仲裁庭接受,最终仲裁庭以没有以管辖权为由驳回平安的诉求。
五、双边投资协定关键条款的解释与适用
(一)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标准有待实践澄清
如前所述,某争议事项能够向国际投资仲裁庭主张管辖权的基础首先是相关仲裁请求属于“条约诉求”而非单纯的“合同诉求”,因此就作为管辖权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关键条款进行准确理解与适用就同时影响到管辖权问题与实体审理。近年来,国内外对BIT中关键条款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扩张适用于仲裁程序性问题;保护伞条款的理念与实践。
公平公正待遇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如今世界上大多BIT都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给予了此类待遇标准。不过,早期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作为投资条约中的条文,更多的是体现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一个态度,缔约国通过条约声明,缔约一方将要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及投资者以保障,通过这种原则性的规定,统领其他具体的待遇标准,并弥补具体待遇标准之不足。不过,对于这类待遇究竟应如何来解释、怎么定义、范围何在、包括哪些因素等问题,条约中从来没有细化规定。而BIT中的公正公平待遇,尽管仍然留有模糊性,但却正是这种模糊性恰恰有利于灵活应对BIT所未予规定的留白事项,使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东道国始终享受非歧视待遇。实践中,最早根据公平公正待遇之违反提请投资仲裁的,尤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第十一章是目前为止对投资者权利提供最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约,堪称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第十一章所确立的ISDS也是目前为止所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领域最新且最为大胆的保护投资者权利的制度设计,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NAFTA项下的仲裁制度颇为独特,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商事仲裁制度体系中独立出来:
1.传统的商事仲裁以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为前提,NAFTA项下的投资仲裁则不需要;
2.传统的商事仲裁需要双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而NAFTA项下的投资仲裁则可以由投资者单方启动仲裁程序;
3.传统的商事仲裁在法律适用问题上以意思自治为核心,而NAFTA项下的投资仲裁则明确规定只能适用NAFTA的规定及其他可适用的国际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此前美国已经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签订了BIT,但NAFTA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间签订的,这意味着,作为NAFTA的拟定主体及投资仲裁制度设计的总舵手,美国需要同时面临其与另一发达国家及其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身份混同”地位颇有启发性。原本美国仅需重点考虑如何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者,却未曾料想自身也会作为投资东道国受到投资者的异议和仲裁请求。自NAFTA成立后,有多起案件是投资者针对美国或加拿大所提起的,而其中的仲裁诉因恰恰以东道国的某些措施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为争议焦点。而这些措施按照传统的实践解释,属于东道国正当行使管理性的规制权的举措,如环保、人权、劳工等问题,如今却被NAFTA仲裁庭定性为间接征收或违法公平公正待遇,尽管被诉的东道国多宣称此类举措并非出于经济考量,而是为了遵守多边环境协定或单纯的东道国国内环境法,该类抗辩却鲜被支持,而是被判定为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9]。非但如此,NAFTA的仲裁实践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ICSID的裁判。鉴于此,美加墨三国曾于2001年进行谈判,通过NAFTA自由贸易委员会发布了针对NAFTA第1105条第1款的解释,将“公平与公正待遇”及“充分的保护与安全”限于国际习惯法关于外国人的最低待遇标准,并规定对NAFTA其他条款或其他独立国际协定的违反不构成对该条的违反。部分仲裁庭在裁决中主张,最低标准的内容不应僵硬地加以解释,而应反映演进中的国际习惯法。如此一来,若是对演进中的国际习惯法有不同理解,那么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解释和适用仍将存在不确定因素。
由于公正公平待遇的模糊性造就了它的灵活性,因而成为投资仲裁实践中最容易获得索赔的一个根据。反倒是运用投资条约中传统的直接征收条款进行成功索赔的比例大大减少,现在更多的是国家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环保等非经济性管理措施[10]。换言之,国家在采取管制措施时仍然可能损及外国投资的利益,但外观表征发生了转变,并不必然采取剥夺财产所有权的方式,只要对投资者财产权利的行使构成减损即可能引发投资争端[11]。最典型例证莫过于阿根廷在爆发金融危机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20世纪90年代末,为吸引外资,传统上坚持卡尔沃主义的阿根廷开始推行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包括加入1965年《华盛顿公约》并签订大量BIT。在这些BIT中,阿根廷普遍承诺给予外国投资以高标准的保护,并同意将有关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2001年阿根廷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元与比索的比值变动剧烈,致使阿根廷不得不改变对投资者作出的承诺,采取紧急措施以解决国内危机并避免损失扩大。由于阿根廷的举措客观上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各国投资者纷纷将阿根廷诉至国际仲裁庭,至2006年以阿根廷为被申请人的ICSID仲裁案件已达40起。2005年,ICSID首次针对系列案件作出首份实体裁决,在CMS天然气运输公司诉阿根廷一案中裁定阿根廷败诉,这如同首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映[12]。其中,多数案件中阿根廷的败诉要点之一都在于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而其解释的要素往往以大陆法系中的善意原则作为辅助。根据善意的要求:第一,东道国要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商业环境、法律构架;第二,东道国要尊重投资者合理的预期;第三,违反公正公平待遇并不以恶意为条件,即不要求有恶意。一旦东道国违反了善意原则,也就同时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原则,致使此类争议频发。与此同时,公正公平待遇的解释标准也引发一定分歧,美国为了反对善意原则的适用,一度提出应依据传统的习惯国际法为标准,传统的习惯国际法要严格一些,但是现行的一些仲裁庭的案例基本上都不认同这一点。我国近年来所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现在也都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其解释空间与解释标准尚有待进一步澄清。
(二)最惠国待遇条款在仲裁程序问题上的可适用性
BIT中对外资实施保护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体现为,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待遇不低于东道国(即“国民待遇原则”)或任何其他国家(即“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国民和公司在同等情况下所享有的优惠。这类保护标准不同于以“公平公正待遇”、“最低待遇”为内容的绝对待遇标准,由于是相对于给予其他投资的待遇,而被统称为相对待遇标准。传统上,最惠国条款以实体权利为基础,例如投资东道国在石油行业给予法国投资者以税收优惠,则英国投资者可以依据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主张享有与法国人同等的优惠,被东道国拒绝时也可以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向仲裁庭主张因歧视而遭受的损害赔偿。但是在投资仲裁实践中,却出现了将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张适用于程序事项以规避BIT中要求在东道国当地救济等待期的案例,1997年ICSID受理的Maffezini诉西班牙案即为典例[13]。
中国在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过程中面临着两个难题:其一,正如Maffezin仲裁案所显现出来的,外国投资者能否将最惠国条款扩展适用于程序性事项,将原本不应由ICSID仲裁管辖的案件交付ICSID仲裁?其二,有些双边投资条约将由ICSID仲裁的事项限定为涉及征收和国有化而引起的补偿款额争端,那么外国投资者可否依据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来扩展ICSID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事实上,为了明确缔约时的意图,英国缔结的部分双边投资条约中已经对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了相当具体而明确的限定,如1996年英国与阿尔巴尼亚BIT第3条:“为免生疑义起见,缔约双方确认,本条第1、2款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本协定第1至11条的规定。”这种方式可以使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不至于成为“脱缰的野马”而无限扩张,也令当事人规避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设定了限度。据学者考察并统计,在Maffezin案之后的西门子案中,ICSID仲裁庭亦支持了德国西门子公司将最惠国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中的请求。但在Plama案中,ICSID仲裁庭对最惠国条款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性事项上的态度可谓峰回路转,该案的仲裁庭认为,保加利亚——塞浦路斯BIT第4条规定的用尽当地救济要求,是两国间特别谈判设定的将争端交付国际仲裁庭的限制性条件,且除非缔约双方有明确的、不含糊的约定,否则基础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不能经由最惠国条款为第三方条约中的其他争端解决机制所替代。无疑,由于ICSID投资仲裁中不适用“遵循先例”的传统,对该问题也并未形成裁决结果的一致性。不过,这却对BIT缔约国提出了要求,即应当尽可能将其意思表示进行明确化,以避免投资争端解决事项范围的不确定性。
(三)保护伞条款扩张管辖权功能的解释趋向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责任并不会单纯因东道国违反投资合同而产生,但BIT中的“保护伞条款”却具有此种功能。这类投资条款往往规定,要求缔约国遵守它对投资者作出的任何承担法律义务的承诺,即缔约国在投资条约中承诺它将承担或者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任何的承诺或者是义务。投资条约中的该类承诺即被称为“保护伞条款”,其功能在于把东道国的投资者通过国内法的形式或者投资协议的形式作出的承诺上升到条约层面,以提供给外国投资及外国投资者以全面的保护。
但实践中对该类条款的解释趋向却颇有争议:一种意见主张,应采取限缩性解释,部分仲裁庭即指出,即使BIT中存在保护伞条款,违反国内的合同或者协议也并不等于就违反条约,以避免将所有合同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庭;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应采用从宽解释、扩张性解释,认为违反国内合同的同时即已违反了条约,可以提交国际仲裁进行管辖;近几年还有观点提出,应当就国家所签订的投资合同进行分类,“保护伞条款”应当仅适用于东道国政府干预“国家合同”而不应当包含“商事合同”[14]。所以在这方面现存的国际案例,观点亦有所分歧。国际法院更是指出,“保护伞条款”的存在实际上创造了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国家责任一般来讲是彼此分离的例外情况[15]。不过从ICSID的实践上来考察,绝大多数仲裁庭借由此类条款的适用来扩大对投资者的保护,扩张ICSID国际仲裁的管辖权,反倒不太注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维系,以致于今后无论是在国内立法、条约缔结,抑或在投资条约的解释与适用,尤其在仲裁过程中,如何平衡投资者和保护东道国的权益,成为一项颇具挑战性的问题。
[1]石慧.投资条约仲裁机制的批判与重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
[2]James Crawford.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611-612.
[3]John Shijian Mo.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M]. Beijing:Lexis Nexis and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2004.697.
[4]Christoph H.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79.
[5]陈安.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08.
[6]黄洁.美国双边投资新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环球法律评论,2013,(4):156.
[7]魏艳茹.ICSID仲裁撤销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30.
[8]杨卫东.双边投资条约研究—中国的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73.
[9]韩秀丽.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国际投资法视角[M].法律出版社,2013.93-114.
[10]蔡从燕,李尊然.国际投资法上的间接征收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2-23.
[11]M.Sornarajah.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367.
[12]刘京莲.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法理与实践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4.
[13]朱明新.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表象与实质[J].法商研究,2015,(3):171-183.
[14]徐崇利.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之争与我国的对策[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4):49.
[15](尼)苏里亚·P·苏贝迪.国际投资法:政策与原则的协调[M].张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07.
Research on Jurisdiction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ZHANG J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The subjec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has converted from nations to persons,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rbitration procedure for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the investor and the host country.Different form tradi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the investment treaty-based arbitration does not require strict arbitration agreement but require"consent in writing to submit",which leaves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ent between investors and the host country.Recently,in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China makes the matters to be submitted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pen to all in vestment matters from the original expropri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compensation issues,so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CSID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What's more,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ome critical clauses in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also concerns the legitimacy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rocedure,such as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clause,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as well as umbrella clau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consent in writing to submit;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D997.4
A
1674-828X(2016)03-0075-07
2016-04-27
2015年度北京仲裁委员会科研基金项目“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的制定与适用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10;2015年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项目“国际私法著作精读”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JPXC06。
张 建,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5级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商事仲裁法研究。
(责任编辑:杜爱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