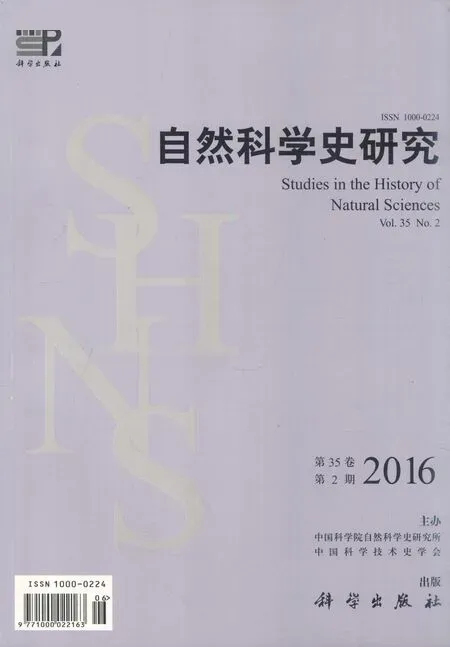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及影响
2016-12-16王涛
王 涛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浙江 金华 321004)
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及影响
王 涛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浙江 金华 321004)
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地图上已经展示出香港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大屿山岛和担杆列岛。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水文专家达尔林普尔等人利用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新的香港地图,首次展示出香港岛西部海岸以及部分岛屿。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买海军组织人力物力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与测绘,将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与西方先进测量技术和绘图理论相结合,不断改进地图中的缺失,体现了中西地理知识的融合。随着测绘成果的推广应用,英人认识到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由此将这里发展成为鸦片走私的巢穴,并成为蓄谋吞并的目标。
英国东印度公司 中国船民 香港 地图测绘
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和离岛四部分及水面组成。这里港阔水深,拥有天然良港,而且邻近广州,与澳门也仅一水之隔。优越的地理条件使香港自18世纪中叶以来就成为中西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大量船只由此通过,往来于澳门和广州的贸易航线上。它的地理状况也引起了西方人探索的兴趣,尤其是英人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查和测绘,将香港比较准确地刻画在地图上,这增进了英人的地理认知,也影响到中英之间贸易和军事关系的发展演变。
以往研究表明,18世纪英人只测绘了香港部分地区,其中1760年英国航海地图首次标出香港岛西部海岸;1780年乔治·海特(George Hayter)的航海地图首次记录下Hong Kong这一地名。①关于18世纪英人测绘香港的研究,详见(英)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Henry D. Talbot, A British Maritime Chart of 1780 Showing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10, 1970).19世纪英人测绘次数更多,涉及范围更广。1806至1819年詹姆斯·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连续多年在中国沿海进行测绘,后来他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多处提到香港水域的情况;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也对香港进行了全面的调查;182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动用船只专门对香港水域进行测绘。[1]
随着地图测绘的展开,英人获取了香港水域的地理资讯,认识到港口的价值和功能。自19世纪20年代起,英人开始大规模进入香港,并以此为据点,向中国沿海非法走私鸦片。他们“自道光元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门,九月后仍回零丁洋。”[2]将新界与大屿山岛之间的急水门海峡发展为鸦片走私的渊薮,此后扩展到维多利亚港等地。到1841年,英人利用鸦片战争的机会,派兵船强行侵占香港岛。*关于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的活动,详见丁又《香港初期史话》(三联书店,1958年);金应熙《香港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蜀永《简明香港史》(三联书店,1998年);余绳武、刘存宽《19世纪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萧致治:《鸦片战争与香港割让》,《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可以说,英人的地图测绘为鸦片走私贸易以及侵占香港提供了丰富的地理资讯。
以往研究,将地图测绘作为鸦片战争前夕英人入侵香港的一种形式,进行了年表式的介绍,所用资料十分有限,对测绘的历史脉络、英人测绘的前因后果、清政府对地图测绘的反应、中国船民在测绘中发挥的作用缺乏具体论述。有鉴于此,本文利用英文航海地图、航海指南、航海游记等资料,考察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发掘英人对香港的地理认知,分析地图测绘所产生的影响。
1 海上贸易航线与香港的地图测绘
清初开放海禁后,清廷在东南沿海设置四处海关,开始允许欧洲船只停泊贸易,此后广州和澳门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18世纪中叶,每年到达广州的欧洲船只就有20艘左右。([3],310页)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规定多数欧洲人限于广州贸易,葡萄牙在澳门贸易。至此,来华欧洲船只的贸易地点基本固定下来,清廷也确立起以广州口岸为中心的“广州贸易体系”。
尽管香港邻近澳门和广州,它们之间也有水路和陆路可通,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只是偶尔经过香港水域,对这一地区的地理认知十分有限。1721年英人乔治·谢尔沃克(George Shelvocke)在广东沿海航行时就发现:“用任何地图,我们都不能全面认识珠江口尤其是大屿山岛(Pulo Lantoon)以东的沿海地区,地图上存在许多错误,令我感到十分震惊。这里被描绘成绵延20里格以上的一系列岛屿,地理学家们对此毫无察觉,我曾遇到的航海家们对此也一无所知。”[4]大屿山岛位于香港的西南部,而此处以东的香港大部分地区没有在欧洲地图上准确地展示出来。这也反映出,当时欧洲人对香港水域的地理认知局限于大屿山岛等局部地区。
1735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达普莱·德·曼纳维耶特(Jean Baptiste D’ Après de Mannevillette)在前往广州的时候,测量了他所经过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1745年他将绘制的地图编为一册,取名为《东方海神》(LeNeptuneOriental),被认为是当时最准确的航海地图集。[5]《东方海神》共有25幅地图,第23幅名为《柬埔寨海岸、交趾支那、东京湾、部分中国海岸和菲律宾群岛地图》,包括对广东海岸和岛屿的描述,详见图1。

图1 柬埔寨海岸、交趾支那、东京湾、部分中国海岸和菲律宾群岛地图(局部)[6]
图1明确标出了广州和澳门,但错误地刻画了香港海岸,也没有标出香港任何地名,其周边水域只有担杆列岛标出了地名I. de Leme,可见欧洲地图缺少有关香港的地理资讯。对此达普莱《东印度和中国航海指南》(RoutierdesctesdesIndesorientalesetdelaChine)提出,欧洲船只来到广东海岸后,一般由老万山岛也就是图中的La grande Ladrone前往澳门,再由澳门前往广州,而香港与中西交通的主要航线仍有一定距离。中国古籍也记载了这条航线,1751年成书的《澳门记略》指出老万山于“岁五六月,西南风至,洋舶争望之而趋,至则相庆。”[7]《澳门图说》也写道:“凡番舶入广,望老万山为会归,西洋夷舶由老万山而西,至香山十字门入口;诸番国夷舶由老万山以东,由东莞县虎门入口,泊于省城之黄埔。”[8]由于航海地图主要记录航线所经过的地区,所以广州、澳门和老万山被标在地图上。
实际上,只有个别欧洲船只从菲律宾群岛或台湾南部来到广东,才会经过香港水域前往澳门和广州。据达普莱叙述“由此向西南,不久就能看到担杆列岛,这些岛屿之间有一条优良的水道通向澳门。”而且“担杆列岛以北是大屿山岛”。[9]由于这条航线通过担杆列岛和大屿山岛,所以达普莱地图对香港水域的刻画,主要是集中在其南部的许多岛屿,也就是今天属于珠海的担杆列岛以及香港离岛大屿山。
1758年,《东方海神》被英国人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翻译成英文出版,并更名为《新东印度指南》(ANewDirectoryfortheEastIndies),其后1759年、1767年、1776年、1780年、1791年、1806年又多次再版,以致这部著作成为18世纪欧洲人编制航海指南的主要参考资料。《新东印度指南》第1版收录了《准确的中国海地图:包括占婆海岸、交趾支那、东京湾、部分中国海岸》(A correct chart of the China Sea containing the coasts of Tsiompa, Cochin China the Gulf of Tonquin, part of the coast of China),这幅图对香港水域的刻画与《东方海神》相吻合,标出了名为Lantao的大屿山和名为I Leme的担杆列岛。([10],23页)另一幅名为《东印度最东部地图》(A Chart of the Eastermos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也按照《东方海神》刻画香港海岸和岛屿,但没有标出香港地名。([10],11页)
欧洲人通过广东沿海航线前往澳门或广州时,有机会接触担杆列岛和大屿山岛,因此,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游记中,留下了关于这些岛屿的记录。更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中叶以前许多欧洲地图已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担杆列岛和大屿山岛的轮廓,并标上了Leme以及Lantao或Lantoan的地名,但在这些地图上,香港水域其他地方普遍缺失或存在错误,也缺少相应的地名。*18世纪中叶以前部分欧洲地图绘出了担杆列岛和大屿山岛,如荷兰地图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 et Insulae Adiacentes;Paskaerte Zynde t’Oosterdeel Van Oost Indien;Nieuwe Pascaert van Oost Indien.另外,英国地图A Chart of the Eastermos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and China;A Chart of the Coast of China from Cambodia to Nanquam with part of Japan.以及法国地图集Nouvel Alt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这其中《东方海神》和《新东印度指南》所附带的地图,精确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可见,当时欧洲人对香港水域的地理认知十分有限,更遑论对整个水域进行准确的地图测绘了。
2 18世纪后期英人对香港的地图测绘
18世纪60年代以后,前往广州贸易的欧美船只数量增多,从每年20余艘发展到18世纪末的50余艘。([3],310~313页)英国船只更是从每年10余艘增加到20余艘,占有较大优势。这一时期,欧美船只开始使用许多新航线往返于广州,尤其是1759年英人威尔逊(William Wilson)发现“东路航线”(Eastern Passage),此后大量英国船只由印度的港口出发,横穿印度尼西亚群岛所在的低纬度海域,再沿着菲律宾群岛东西海岸来到澳门和广州,返航时也采用这些迂回航线,从而使英商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广州之间的“三角贸易”格局基本形成。据范岱克(Paul Van Dyke)研究,18世纪广州的新航线包括西菲律宾航线、东菲律宾航线、太平洋航线等。[11]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与应用,它们很快成为欧洲人调查测绘的重点,而且这些航线都通过香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另一方面,18世纪8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聘用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担任水文专家(Hydrographer),陆续投注专门人员、设备用于海洋地图的测绘,并重视水文信息的整理与出版。[12]与此同时,英人在航海仪器与航海地图制作方面有了引以为傲的发明或改良,包括麦肯齐(Murdoch Mackenzie)倡导以科学方法绘制地图、哈里森(John Harrison)发明了专为海上测量经度的“精密定时器(chronometer)”等。这些仪器制造与绘图理论的改良皆有利于东印度公司测绘调查的进行。
由于上述进展,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水文专家通过对香港实地调查,在欧洲地图上初步标出了香港岛以及周边一些岛屿,并且将这里的岛屿海岸刻画得更加准确。值得注意的是,英人在香港调查测绘时,许多中国船民参与其中。英人绘制的地图,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反映了中西地理知识的融合。
2.1 中国船民对香港的地理认知
中国船民很早就在香港水域进行航海活动,如明代《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为现存最早的航海地图,已明确标出蒲胎山、东姜山、佛堂门、官富寨、大奚山、小奚山等香港地名。[13]此航线也载于《东西洋考》“西洋针路”:
大星尖,属广州东莞县,其内为大鹏所,洪武间筑城守之。大星尖赤石甚尖,故名。内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针,七更,过东姜山;东姜山,对开,打水四十五托。其前为弓鞋山;弓鞋山,山如弓鞋样,对开,打水四十九托。内外俱可过船。其前为南亭门。[14]
“大星尖”指今广东惠东县东南小星山岛对面突出之海角[15]。“东姜山”指今香港蒲台群岛中的宋岗岛,广东话“姜”与“岗”同音;“弓鞋山”也称作“翁鞋山”或“翁鞋”,指三门列岛中的隘洲。[16]南亭门一说是老万山[17],一说是大屿山水道南部的大蜘洲岛[18]。所以“西洋针路”这段位于香港南部的岛屿之间。16世纪成书的《顺风相送》也记载了这条航线,“大星尖,洋中有大星尖,内过打水二十五托,外过打水四十五托。”“东姜山,对开打水四十五托。广东前船澳港口有南亭门,打水十九托,泥沙地。”“弓鞋山,似弓鞋样,对开四十九托水,北低一角,七箇高山合做一箇山,南边高近大山,内十九托水,泥地。”([19],32页)《顺风相送》进一步刻画出岛屿形状、海洋底质和海神信仰。
清代的航海著作中,对香港一带海上航线的记述更为丰富。至迟18世纪初成书的《指南正法》,包括“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这条航线经过福建头、樑头门至赤安庙:
福建头,内是南风澳,好抛船,出入在福建头屿上门出入,内门夹小,下有荔枝屿;樑头门,入门是妈祖庙前好抛船。入去小急水,九龙澳后好抛船。入出是大急水门,流水急深无礁。北边大山是传门澳,好抛船;赤安庙,抛船东边北边鼻头有徒,内有大屿二个。船出入在屿外,有小屿无礙也。([19],157页)
据雍正八年(1703)陈伦炯写成的《海国闻见录》之《沿海全图》,“福建头”和“荔枝屿”位于香港佛堂门海峡以东。[20]另据向达注释,“樑头门”为香港西北的急水门。“赤安庙”为今深圳赤湾天后宫,或是《沿海全图》所记的“赤湾”,据屈大均所说“其在新安之赤湾者,舟行必告,是曰辞沙,以祠在零丁洋沙上也。”[21]此处位于以内伶仃岛为中心的伶仃洋海域。换言之,“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记述了由佛堂门海峡经过维多利亚港和急水门进入伶仃洋的航线。总之,明清时期中国船民已经频繁地在香港水域进行航海活动,他们完全熟悉这一地区的山形水势,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
2.2 中国船民与英人的地图测绘
由于地理知识存在差异,欧美船只到达香港水域时,离不开中国船民为其领航。据范岱克研究,对于欧美船员来说,他们来到中国海岸后先到澳门,再进入虎门停泊于广州的外港黄埔,这一段航程是异常险要的,非有本地船民作“引水人”不可。[22]引水人大多以捕鱼为生,懂一点英语、葡萄牙语,对欧美船只起帆、收帆、起锚、放锚等相关术语也了如指掌,能熟练地与外国人打交道。[23]18世纪后期英人在香港水域进行地图测绘时,引水人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地理资讯。
1759年至1764年,达尔林普尔跟随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来到广州,他曾在引水人协助下对广东沿海进行调查,据此绘制的地图融入了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成为欧洲人绘制广东海岸的新蓝本。达尔林普尔指出:“1760年,名为Yafou的广州引水人将一幅大屿山岛以及中国沿海部分岛屿的地图赠予我,尽管很不准确,而且在我看来这幅图不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而是利用其他船民的描述绘制而成,但大致充分的标出了这里的岛屿。”([24],33页)后来这幅地图被译成英文,取名为《大屿山岛东南部的中国沿海诸岛图》(SketchoftheIslandstotheSEofLantaoontheCoastofChina),详见图2。这幅地图利用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绘制而成,勾勒出香港水域大部分岛屿、海岸、水道的地理状况。
1764年,达尔林普尔在Yafou地图和其他引水人指引下,对香港水域进行了地图测绘。他首先从蒲台岛即Yafou地图中的Pootoy出发,沿着《东西洋考》和《顺风相送》记载的航线到达南丫岛(Lamma),然后调转方向前往急水门,再沿《指南正法》“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从“樑头门”到“赤安庙”。([24],34~46页)根据这些测绘成果,1771年达尔林普尔出版了《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AChartofpartoftheCoastofChinaandtheadjacentIslands),详见图3。

图2 大屿山岛东南部的中国沿海诸岛图[25]

图3 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局部)[26]
《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列举的香港地名可分为三类:其一,以往欧洲地图已经明确标出的地名,包括老万山LANTAO ISLAND、担杆岛GR LEMA、外伶仃岛LING TING等。其二,从Yafou地图上直接音译或意译过来的地名,包括北九针岛(Nine-pin)、大东门(Tat-hong-moon)、横澜岛(Waglaang)、宋岗岛(Song-keo)、蒲台岛(Poo-toy)、螺洲(Lo-chow)、南丫岛(Lamma)、长洲(Chang-chow)、坪洲(Taipak)、小交椅洲(Sinpak)、交椅洲(Psang-chow)、青洲(Taipak-how)、索罟洲(Socko-chow)等。这类地名占大多数。其三,Yafou地图上没有出现,属于新增地名,包括昂船洲(FANCHIN CHOW)、青衣岛(CHINFALO)、马湾(COWHEE)。这类地名为数甚少。可见达尔林普尔主要参照Yafou地图,并结合实地考察,利用欧洲先进的绘图理论,绘制出《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
由于达尔林普尔使用西法对香港水域进行测绘,使他的地图比Yafou地图更准确,这也是欧洲地图中第一次绘出香港岛西部海岸,并以FANCHIN CHOW即“昂船洲”命名了香港岛。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达尔林普尔同行的阿尔维斯船长(Captain Walter Alves)在航海日志中写下:“下午五点,船在青衣岛西南角向东南东方向行驶,下午六点到达Heong-Kong岛以北,因为潮流太大,船只能在水深6寻处抛锚,这里距离Heong-Kong约1英里,位于大屿山岛西偏南8°。”[27]阿尔维斯指出Heong-Kong就是Fanchin-chow,这是西方文献中首次以Heong-Kong命名香港岛。
达尔林普尔地图在欧洲流传甚广。1775年达普莱将《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译成法文,置于《东方海神》第2版中刊出。[28]当时英国地图出版业占垄断地位的塞耶和班尼特(Sayer & Bennett)以及劳里和惠特尔(Laurie & Whittle)也将达尔林普尔地图加以翻印,1778和1794年多个版本的《中国海地图》(AChartoftheChinaSea)对香港水域的刻画都是以达尔林普尔地图作为蓝本,只是将香港岛的名称改为“FAN-CHIN-CHEOW or HE-ONG-KONG”。*英国地图商塞耶和班尼特、劳里和惠特尔都曾出版发行《中国海地图》,详见1778年Robert Sayer and John Bennett地图集The Oriental Pilot第69幅地图,以及1794年Robert Laurie and James Whittle出版的地图 A Chart of the China Sea。所以18世纪后期,在中西地理知识融合的基础上制作的《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已成为欧洲人认识香港地理状况的主要素材。
3 19世纪初英人对香港的地图测绘
3.1 丹尼尔·罗斯对香港测绘的起因
随着达尔林普尔地图的传播与利用,许多来华船只配备了《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使地图的实用性和准确性得到检验。1779年戈尔(Captain John Gore)船长率领“决心号”(Resolution)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就发现“达尔林普尔先生的地图比例尺太小,用它为我们指引方向起不到太大用处。”[29]范西塔特号(VanSittart)大副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也认为:“达尔林普尔先生的地图当中,担杆列岛和蒲台岛等非常准确,但这幅地图的纬度偏北太多。”[30]可见《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的地理位置不准确,因此这幅地图仅具有参考价值,更多情况下欧美船只仍利用中国船民的经验知识为其引航。
尽管达尔林普尔绘制的地图仍存在各种问题,但它向欧美船长们敞开了一扇认识香港的窗口,从而指引着欧美船只来到香港停泊。1791年美国人肯德瑞克(John Kendrick)率领“华盛顿夫人号”(LadyWashington)运载毛皮到广州贸易,返航时一度进入今香港岛的香港仔避风,并将这一港口称为“独立港”(Port Independence)。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款待,1793年“华盛顿夫人号”再次到广州时,仍到香港仔停泊。次年肯德瑞克在夏威夷去世,但他留下的航海日志中记载了有关香港的地理资讯,后来这部航海日志被达尔林普尔发现,为绘制香港地图提供了依据。( [31],33~48页)
19世纪初,每年到广州的欧美船只已达到70余艘。然而第四次英荷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波及亚洲水域,英国船只时常遭到敌军劫掠,与此同时“华南海盗”日益猖獗也对英国船只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英国兵船以保护航运为名时常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命令“孟买海军”(Bombay Marine)下属船只对中国和东南亚水域进行大规模调查测绘,以增进航行安全。1806年“孟买海军”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船长率领“羚羊号”(Antelope)来到澳门,不久穆罕(Philip Maughan)和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也加入调查的行列。他们以澳门为基地,对中国和东南亚水域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820年,前后长达15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水文专家,也是孟买海军测绘调查的策划者,达尔林普尔将大批航海资料交给“孟买海军”的调查人员,以供测绘之用,其中就包括肯德瑞克的航海日志。([31],45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罗斯船长对香港的关注,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3.2 丹尼尔·罗斯的《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
1806年罗斯船长到达澳门,他首先对电白港与担杆列岛之间的广东海岸进行调查。[32]对此清廷管理澳门及广州一带海防的澳门同知对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表示抗议,命令“羚羊号”和另一艘“玛丽亚号”(Maria)离开。[33]但罗斯认为清廷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可以不加理会。令人遗憾的是,广州和澳门的官员并未意识到地图测绘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
1807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出版了罗斯船长绘制的《对部分中国南部海岸的调查》(SurveyofPartoftheSouthCoastofChina)、《电白港》(ThienSienHarbour)、《海陵山港》(HinLingSanHarbour)、《南澳港》(NamoHarbour)、《从磨刀门到澳门西部地图》(PlanoftheBroadwaytotheWestwardofMacao)、《从内伶仃岛到虎门航线图》(PlanoftheChannelfromLintintotheBoccaTigris)。([34],610~611页)1810年,东印度公司又出版了罗斯的《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ThisChartofthedifferentPassagesleadingtoMacaoRoads),详见图4。

图4 《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局部)[35]
据图4,香港海岸和周边一些岛屿已经准确地绘制出来,并用中英两种文字将地名标在图上,这种地名的标注方法也见于《对部分中国南部海岸的调查》等地图。与《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相比,《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的地名更详细,并且所有英文地名都是直接由中文地名音译过来,就连达尔林普尔所取的一些英文地名,罗斯也更换为相应的地名音译,如《部分中国海岸及邻近岛屿地图》中的香港岛FANCHIN CHOW、青衣岛CHINFALO、马湾COWHEE,罗斯将它们改为HONG KONG、Chuengyu、Mahwan,甚至欧洲地图上早已明确标出的大屿山LANTAO,这里也标为LANTAO by Europeans OR TYHO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TYHO对应的是中文“大澳”。*地名TYHO或“大澳”,来自大屿山岛西部的大澳渔村,罗斯曾到此汲水。上述英文地名与中文地名更加吻合,所以后来香港地名的英文翻译大部分只是直接的音译。
由此可见,《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包括大量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实际上,罗斯在香港水域进行调查时,不止一次地访问广东沿海的引水人和当地居民,在此基础上,他首次标出了香港一带的居民点。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会发生冲突,如在南丫岛就遭到当地人抵制。[36]不过,罗斯通过访问常年生活于此的中国船民,并利用西方先进的仪器与绘图理论,这才将香港较为准确的呈现在地图上。
《通往澳门水道各种航线地图》展现了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在罗斯船长的推荐下,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使团船队选择香港岛作短暂停留。当时东印度公司命令罗斯率领“发现号”(Disocvery)和穆罕率领“调查者号”(Investigator)与使团一起北上,同时使团副使之一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斯当东。由于阿美士德担心会在广州被拦截,所以没有直接前往广州,而是要求罗斯和斯当东等人先期乘船到广东海面与使团会合。为此罗斯选择了今香港仔的瀑布湾作为会合地点。([31],45页)使团停留香港期间,博物学家阿贝尔(Clarke Abel)等人登岛进行了全面的调查。[37]而且这次与香港的接触,给使团成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其中副使埃利斯(Henry Ellis)就说:“这个海湾里以前可能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么多的欧洲船只,从岸上看去,整个景色极其富有生气。到了晚上,为数众多的渔船点亮了盏盏渔灯,就像灯火通明的伦敦街道”。[38]阿美士德使团的经历及其成员的赞誉,使香港声名鹊起。
4 地图测绘成果的更新及影响
4.1 霍斯伯格与地图测绘成果的更新
1810年,詹姆斯·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接替达尔林普尔成为东印度公司水文专家,他于1809年和1811年出版两卷本的《往返东印度、中国、新荷兰、好望角和途中各港口航海指南》。1817年,霍斯伯格将该书更名为《印度航海指南》(TheIndiaDirectory),并于1826~1827、1836、1843、1852年再版,使内容持续更新,而且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美流传,由此这部著作成为东方航海的标准参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东西海上交通指明了方向。
霍斯伯格利用罗斯的测绘资料,记录下香港及周边岛屿、港口和水道的地理位置、水深、礁石、居民村落等。随着测绘成果的不断出现,他对香港的记载更加详细。1811年《往返东印度、中国、新荷兰、好望角和途中各港口航海指南》只提到担杆岛(GREAT LEMA ISLAND)、大屿山岛(LANTOA or TY-OA)、香港大潭湾(HEONG-KONG-OA)等少数几个岛屿和港口。[39]1817年《印度航海指南》第2版又增加了长洲(CHUNG-CHOW)、南丫岛(LAMMA ISLAND)、香港岛(HONG-KONG ISLAND)、螺洲(LO-CHOW)、双四门(SINGSHEE-MOON),反映当时英人关注的仍是香港南部的港口和航线,即明代航海著作《顺风相送》和《东西洋考》所记载的地区。有鉴于此,霍斯伯格认为,可以将香港的大潭湾和瀑布湾发展为供英国船只停泊的两处良港。
1820年代以后,中英关系出现重大转变,首先是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数量大增。这一时期,英国散商的鸦片走私船开始季节性地到香港水域停泊,并以此为据点将鸦片输往沿海其他地区。它们“自道光元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门,九月后仍回零丁洋。”与此同时,英人加快了“北部开港运动”的步伐,企图冲破贸易壁垒,在广州以北开辟更多商埠。[40]到182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也转到香港一带停泊。当时由于行商拖欠英商债款问题,英商强行索欠,导致中英之间一次较大的冲突。为处理这次贸易纠纷,东印度公司大班采取强硬手段,命令英国货船全部停泊在澳门外洋,拒绝进口贸易,而且决定到广州和澳门以外另找可以停船的港口。这时东印度公司参考以往调查测绘的成果,终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并派布拉克利(W. R. Blakely)再次进行调查,试图将香港发展为英国船只停泊的口岸。([41],212~213)
1830年,霍斯伯格刊出了布拉克利绘制的地图《通向鲤鱼门的航线》(PassagesLeadingtotheLymoon(Hong-kong),continuedfromCapt.D.Ross,SurveybyWm.R.Blakelyandothers)。([34],584页)1836年,霍斯伯格《印度航海指南》第4版收录了布拉克利的调查成果,增加了对“南丫岛、鲤鱼门和急水门航线”以及“急水门航线”的介绍。这就意味着,布拉克利主要调查了香港岛北岸的维多利亚港和西北部的急水门,相当于《指南正法》“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所述的航线。布拉克利认为维多利亚港“有许多安全的锚地,可以在东北季风期为船只提供庇护,但是除了香港以外,其他地方不容易提供淡水。”急水门也适合停船,“马湾以北的海峡非常开阔,拥有良好的锚地,潮汐也有规律,并且在东北季风期具有迎风而行的优势。”[42]
至此,英人全面认识了香港水域的地理状况。所以1829年冬,东印度公司“大部分的委员,在十二月初命令六艘商船去停泊在香港港内,并任命林德赛先生为船上的货物管理人,又命令两艘泊在急水门,任命克拉卡先生为船上货物管理人。”([41],214页)这时东印度公司已选中香港为船只的停泊处,并试图在此建立贸易基地。
4.2 地图测绘成果的影响
通过达尔林普尔、丹尼尔·罗斯以及布拉克利对香港的地图测绘,英人掌握了香港水域的地理状况。他们的测绘成果被霍斯伯格汇集起来,编入《印度航海指南》,在欧美船员中广为流传。随着测绘成果的推广应用,欧美船员们认识到香港水域优越的地理条件,此后大量船只开始进入这一水域。
1833年乔治·贝内特(George Bennett)在香港一带航行时,叙述了测绘新进展对英人地理认知的影响,指出:“船上的中国引水人毫无用处,船长对岛屿、水深等方面的地理知识令他感到震惊,后来才发现,这些知识来自地图和霍斯伯格的航海指南。”[43]英国地理学家穆瑞(Hugh Murray)也认为,船只在香港岛与担杆列岛之间的水道航行时,“假如遇到恶劣天气,而且没有引水人的情况下,即使初来乍到者也可以凭借罗斯船长和霍斯伯格先生令人钦佩的航海指南安全通过。”[44]可见航海指南和地图的推广应用,使英人利用最新测绘成果,而不依赖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就可以在香港水域航行与停泊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图和航海指南的指引下,大批鸦片走私船肆无忌惮地侵入香港。19世纪30年代,维多利亚港的尖沙咀发展成为鸦片走私的据点,多数鸦片走私船云集于此。英人又以保护鸦片船为名,派兵船入侵香港。鸦片战争期间,他们更是凭借坚船利炮强行将香港占领。这期间,地图测绘成果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时,英军“康威号”(Conway)船长贝休恩(Capt. Drinkwater Bethune)由广州前往香港时指出:“整个航程全部利用霍斯伯格地图而不是引水人来领航,我们只用地图,就可以沿番禺的水道顺流而下,并穿过了急水门。”[45]“复仇女神号”(Nemesis)船员班纳特(W. D. Bernard)提出:“最近中国新港口开放和占领香港,使这一水域受到重视,由这些地方通过的英人和其他外国人,无不感激霍斯伯格航海指南令他们能安全地航行。”[46]不难发现,英人的鸦片走私船和兵船之所以能在香港自由进出,取决于测绘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1843年《印度航海指南》第5版对香港的记述没有太大变动,这是因为达尔林普尔、罗斯和布拉克利等人对香港的调查,提供了充足的地理资讯。直到鸦片战争期间,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r)率“硫磺号”(Sulphur)在香港岛登陆,并强行占领该岛,才再次对香港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测。[47]在此基础上,英人绘制了新的地图,其测量结果也被记录到1852年《印度航海指南》第6版中。由于《印度航海指南》是中国和东南亚海域航海知识最权威的著作,一直被欧美船员奉为圭臬,所以该书为英人在香港的活动提供了指引,而且东印度公司地图和霍斯伯格航海指南广泛传播,使香港优越的地理条件被欧美船员所了解,也使其成为英人蓄谋吞并的目标。
5 结 语
以往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前英人一直妄图在中国沿海夺占海岛作为通商据点,他们的首要目标定在浙江舟山。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数量大增,香港成为鸦片走私的据点,因而,要求占领香港的呼声日益高涨。鸦片战争后,英人最终放弃了舟山,而占领香港岛。*关于鸦片战争中英人放弃舟山转而侵占香港岛,详见刘存宽:《香港、舟山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对华战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郭卫东:《从舟山到香港:英国在华殖民战略的调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王和平:《英国侵占舟山与香港的缘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转变固然与舟山的条件,以及清廷和英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但英人吞并香港实属蓄谋已久,他们对香港的地理认知,是在18世纪以来历次地图测绘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对香港的侵占,也依靠地图测绘的成果作为指引。可以说,鸦片战争前英人对香港的地图测绘在这一时期英国对华的贸易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其意义不容小觑。
实际上,欧洲人对香港水域的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常年生活于此的中国船民和当地居民,最早开发利用香港的港口和航线,他们拥有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只不过这些经验性知识长期湮没无闻,或是口耳相授地传承下来。所以英人在香港测绘时,往往需要中国船民和沿海居民的协助。达尔林普尔、罗斯、布拉克利和霍斯伯格等人正是将中国传统的地理知识与欧洲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理论相结合,才绘制出准确的香港地图,反映了中西方地理知识的融合。
另一方面,清廷也注意到英人在香港的测绘,并对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表示抗议,遗憾的是,在缺乏“海权”观念的时代,广州和澳门的中国官员并未将测量船只驱逐出境,而是任由其窥探中国海域的情形。由于没有来自清廷的干扰,英人才顺利完成了调查和测绘,他们制作的地图更加详细准确,并记录下这一地区的地理状况,随着测绘资料的传播和利用,英人认识到香港优越的地理条件,最终将其变为鸦片走私的巢穴,并成为他们蓄谋吞并的目标。
1 Sayer G R.HongKong1841—1862:Birth,AdolescenceandComingofAge[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21~33.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G].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29.
3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G].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Shelvocke G.AVoyageRoundtheWorldbytheWayoftheGreatSouthSea[M]. London: J. Senex, 1726. 441.
5 Suarez T.EarlyMappingofSoutheastAsia[M]. Hong Kong: Periplus Editions Ltd, 1999. 238.
6 D’Après de Mannevillette.CarteplatequicomprendlesCostesdeTsiompa,delaCochinchine,legolfedeTunquin,unepartiedescostesdelaChineavecunepartiedel’ArchipeldesIslesPhilippines[M]. Paris: Jean François Robustel, 1745.
7 印光任, 张汝霖. 澳门纪略[M]//中山文献.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22.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G].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08.
9 D’Après de Mannevillette.RoutierdesctesdesIndesorientalesetdelaChine[M]. Paris: Chez CH. J. B. Delespine, 1745. 236.
10 Herbert W.ANewDirectoryfortheEastIndies[M]. London, 1758.
11 范岱克. 18世纪广州的新航线与中国政府海上贸易的失控[C]//全球史评论.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98~323.
12 游博清.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水文调查(1779~1833)[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1):61~73.
13 向达. 郑和航海图[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9.
14 张燮. 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2.
15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34.
16 郭声波,鲁延召. 明清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名实研究[M]//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253~255.
17 韩振华.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40.
18 章巽. 章巽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125.
19 向达. 两种海道针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 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188.
21 欧初,王贵枕. 屈大均全集[M].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41.
22 Dyke P A V.TheCantonTrade,LifeandEnterpriseontheChinaCoast, 1700—1845[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50.
23 程美宝. 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J]. 学术研究,2010,(4):114~121.
24 Alexander D.MemoiroftheChartofpartoftheCoastofChinaandtheadjacentIslandsneartheentranceofCantonRiver[M]. London: George Bigg, 1786.
25 Dalrymple A.SketchoftheIslandstotheS.E.ofLantaoonthecoastofChina[M]. London: Act of Parliament by Alexander Dalrymple, 1786.
26 Dalrymple A.AChartofpartoftheCoastofChina,andtheadjacentIslandsfromPedroBlancototheMizen[M]. London: Act of Parliament by Alexander Dalrymple, 1771.
27 Alexander D.JournaloftheSchoonerCuddalore,Oct. 1759.ontheCoastofChina[M]. London: George Bigg, 1786. 17.
28 D’Après de Mannevillette.Carted’unepartiesdesCtesdeLaChineetdesIslesadjacentes[M]//LeNeptuneOriental. Paris: Chez Demonville, Imprimeur-Libraire de I’ Academie Françoise, 1775. 53.
29 Cook J,King J.AVoyagetothePacificOcean;UndertakenbyCommandofhisMajesty,formakingdiscoveriesintheNorthernHemisphere,PerformedundertheDirectionofCaptainCook,ClerkeandGore,intheYears1776, 1777, 1778, 1779, 1780[M]. Vol.4. London: Champante and Whitrow, 1793. 222~223.
30 Robertson G.MemoirofaChartoftheChinaSea[M], London: Messrs. Gilbert Wright and Hooke, 1795.11.
31 Davies S. American Ships, Macao, and the Bombay Marine, 1806—1817[C]//AmericansandMacao:Trade,SmugglingandDiplomacyontheSouthChinaCoa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32 Low C R.HistoryoftheIndianNavy(1613—1863)[M]. Vol.1. London: Richard Bentley and Son, 1877. 394~395.
33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M] .第3卷.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160.
34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ACatalogueofManuscriptandPrintedReports,FieldBooks,Memoirs,Maps,etc,oftheIndianSurveys[M]. London: W. H. Allen & Co., 1878.
35 Ross D, Maughan P.ThisChartofthedifferentpassagesleadingtoMacaoRoads[M]. London: Engraved by J. Bateman, 1810.
36 Horsburgh J.IndiaDirectory,orDirectionsforSailingtoandfromtheEastIndies,China,NewHolland,CapeofGoodHope,andtheinterjacentPorts[M]. Vol.2. London, 1817.268~283.
37 Abel C.NarrativeofaJourneyintheinteriorofChinaandofavoyagetoandfromthatcountryintheyears1816and1817[M].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60~63.
38 埃利斯. 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3.
39 Horsburgh J.DirectionsforSailingtoandfromtheEastIndies,China,NewHolland,CapeofGoodHope,andtheinterjacentPorts[M]. Vol.2. London, 1811. 263~268.
40 郭卫东.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进行的“北部开港运动”[J].广东社会科学,2003,(3):80~88.
41 Morse H B.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M]. Vol.4.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42 Horsburgh J.IndiaDirectory,orDirectionsforSailingtoandfromtheEastIndies,China,Australia,CapeofGoodHope,BrazilandtheinterjacentPorts[M]. Vol.2. London: W. H. Allen and Co., Bookshellers to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1836. 355.
43 Bennett G.WanderingsinNewSouthWales,Batavia,PedirCoast,SingaporeandChina[M]. Vol.2.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34. 20.
44 Murray H.AnHistoricalandDescriptiveAccountofChina[M]. Vol.3. Edinburgh: Oliver & Boyd, Tweeddale Court, 1836. 154.
45 Becher A B.TheNauticalMagazineandNavalChronicle,for1842[M].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42. 221.
46 Bernard W D.NarrativeoftheVoyagesandServicesoftheNemesisfrom1840to1843[M]. Vol. 1 London: Henry Cloburn, 1844. 169.
47 Belcher E.Narrativeofavoyageroundtheworld[M].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Publisher, 1843. 147.
British Mapping of Hong Kong before the Opium War
WANG Tao
(DepartmentofHistory,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321004,China)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European maps had shown parts of Hong Kong, mainly Lantao and Lema islands.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East India Company hydrographer Alexander Dalrymple use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Chinese boat people to draw a new map, for the first time portraying the west coast of Hong Kong and some islands. Lat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Bombay Marine organized several expeditions to the region to carry out surveys, combining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Chinese boat people with wester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o improve map quality, embodying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creasing use of maps, the British realized the superior location of Hong Kong, so they made the place a nest of opium smugglers and the target of occupation plan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Chinese boat people, Hong Kong, Map surveying
2016- 03- 17;
2016- 05- 23
王涛,1983年生,山东淄博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地图测绘史。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中叶英国在南海的地图测绘及其影响研究(1780—1820)”(项目编号:15CZS015)
N092∶P2- 092
A
1000- 0224(2016)02- 0199-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