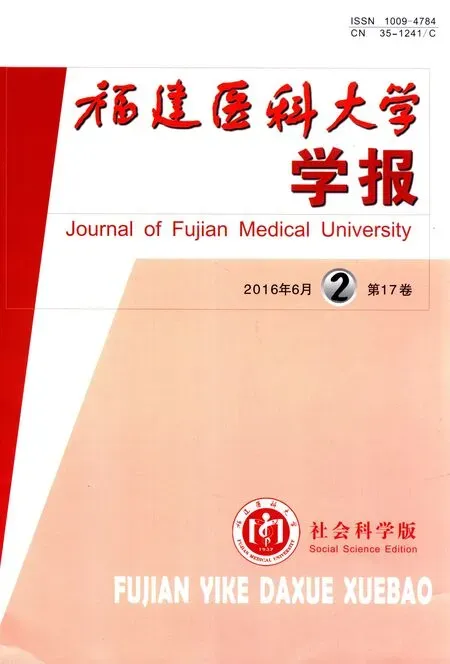运动亲反社会行为: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展望
2016-12-16陈华东高松龄翁慧婷
陈华东,高松龄,翁慧婷,王 栋
(1.福建医科大学体育教研部,福建福州350108;2.宁德师范学院体育系,福建宁德,352100;3.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运动亲反社会行为: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展望
陈华东1,高松龄1,翁慧婷2,王 栋3
(1.福建医科大学体育教研部,福建福州350108;2.宁德师范学院体育系,福建宁德,352100;3.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分析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研究进展,探讨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提出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应加强丰富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研究范畴、强化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纵向研究、完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和加大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干预等未来研究方向。
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体育道德;运动员
体育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强健人们的体魄为更好地生存提供物质基础,也能塑造人的道德品质为全面发展提供心智基础。在古代中国,体育运动不仅是一种健身活动,更蕴含着古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1],几乎所有的体育活动都有道德方面的要求;现代西方文化的摇篮地——古希腊同样十分重视体育运动,这除了与体育的健体功能有关外,还与体育运动能够对其公民进行道德教育有重要关系[2]。体育运动对人的影响可谓深远,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借助高效的传播媒介,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运动对人的影响力也得到了放大,体育运动所蕴含的精神,如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在每一次赛事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运动员的人格魅力从赛场一直延伸到世界各处,并长时间的影响世人,这正是体育运动贡献给人类的益处。然而,随着竞技水平的不断攀高,运动员体育道德水平较过去似乎有滑坡之现象,近些年来,体育伦理道德的失范诸如兴奋剂、消极比赛、球场暴力、假球等运动员反社会行为不断涌现,这些反社会行为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损坏了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声誉,制约了体育运动的良好发展。因此,运动员亲反社会行为问题研究愈发迫切,笔者通过梳理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为学者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内涵与测量
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内涵可以追溯到Eisenberg等提出的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概念[3]。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表现出对他人有利的行为,反社会行为指的是对他人不利的行为。体育学者Kavussanu等将此概念引入到运动中,根据行为结果对他人的影响将运动道德行为区分为运动亲社会行为和运动反社会行为两个维度[4]。在运动中,运动亲社会行为是指运动员个体表现出的帮助他人或使他人受益的行为,如帮助受伤的运动员等;运动反社会行为则是指运动员个体表现出伤害他人或使他人不利的行为,如伤害对手等[5]。以上概念的提出都是从行为上对道德以及运动道德进行解释。而从伦理学对于道德行为的定义,可以推理出运动道德行为是在体育运动这一特定情境中,运动者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有利于或者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不同学者所界定的概念其侧重点有所区别。近年来,随着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兴起[6],体坛中各种不道德事件频繁发生,个体行为的结果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重视。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已然成为运动道德领域研究的热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在运动亲反社会行为测量方面,由Kavussanu等编制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量表(PABSS)最受研究者青睐[7]。量表包含队友和对手的亲反社会行为四个分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Llikert 5点记分(“从来没有”到“非常多”)。该量表分别对两组运动员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的适配拟合良好,可以用来测量运动中的亲反社会行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国内学者祝大鹏对PABSS进行了检验、修订(包含4个维度,23个条目),结果表明该量表亦可适用于我国运动员,其信度和效度是可靠的[8]。运动亲反社会行为量表的理论基础是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从以往的测量工具来看,研究者过于倾向运用反社会行为,忽略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性;并且大部分调查都是以对手为指向,以队友为指向的测量相对较少,测量工具的不一致,使得量表应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因此,在研究国外相关测量工具的同时应积极开展一些探索性的、本土化的应用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实证研究。
二、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从已有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看,性别、运动项目等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性别方面,Kavussanu等研究发现,男性运动员与女性运动员相比更易做出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但在男女性别上并无差异;在运动项目方面,与篮球运动员相比,足球、曲棍球和橄榄球运动员表现出了更高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对手);足球运动员表现出了更高的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和运动亲社会行为(对手)以及低的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壁球运动员表现出了更低的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以及高的运动亲社会行为(对手);橄榄球运动员表现出了更低的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和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7]。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项目类型不同,运动员之间的互动性及接触性不同所致。虽然Kavussanu等的研究从实证角度对性别和运动项目进行了研究,但性别和运动项目还尚未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如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移情水平、道德认同水平等存在着差异,这很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也表现出差异。因此,将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验证性别和运动项目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二)个体特征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在现有的研究中,除了对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探究外,学者们也探究了某些个体特征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如道德推脱、道德意识、目标定向等。在道德推脱方面,早期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手方面,近期研究指出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同样也会发生在队友的身上[9]。从已有实证研究看,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反社会行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运动道德推脱可以正向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然而在与运动亲社会行为方面则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学者Kavussanut等研究发现,运动道德推脱可以负向影响运动亲社会行为(对手),但不能负向影响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团队内存在“合作”的关系所致,“合作”消弱了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之间的关系[7]。另一方面,Hodge等的研究则指出,运动道德推脱并不能负向预测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和对手)[10]。显然,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还尚不明确,有待更多研究者的实证检验。在道德意识方面,王栋等对运动员道德意识、道德推脱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道德意识会对反社会行为产生负向影响,道德推脱会对反社会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同时运动道德推脱在运动道德意识与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11]。然而,虽然其研究证实了道德意识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方面,研究所选取的样本量较少,这或许会对研究结论造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其研究未检验道德意识对运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效应,而运动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有益行为则更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目标定向是影响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另一重要变量,尤受运动道德领域研究者的青睐。从现有研究看,有关目标定向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如有研究指出任务定向虽然不能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但可以正向预测运动亲社会行为。也有研究指出,任务定向可以负向预测反社会行为。显然,目标定向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同时,从目标定向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已有的实证研究看,运动员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多指向于对手,有关队友为指向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还尚未被揭示,队友作为运动员最为重要的同辈,往往会对运动员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当在验证前人研究结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目标定向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队友)的关系。此外,从国内相关研究看,有关目标定向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关系研究还尚未出现,但有关其他运动道德行为则被一些学者所关注,如张璐斐等研究了目标定向对篮球运动员道德行为的影响,发现自我取向的人更倾向于在比赛中做不道德行为,任务取向的人则较少有采取不道德手段的意向[12]。贺亮锋在关于体育非道德行为与目标定向关系研究的综述文章中指出,除了任务—目标定向外,社会目标定向也会影响体育非道德行为,且存在性别差异[13]。因此,未来研究除可验证国外研究结论以及揭示目标定向与以队友为指向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关系外,还可以探究其他目标定向变量,如社会目标定向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等,这同样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方向。
除上述个体特征变量外,动机变量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Hodge等研究发现,自主动机可以正向预测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受控动机可以负向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和对手)[10]。然而,有关动机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较为少见,而且国内也尚未发现动机与我国运动员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探究。我国运动员的动机水平能否预测运动亲反社会行为,预测效应如何,预测效应是否会在队友和对手之间存在差异等问题都有待回答。另外,从生活领域的相关研究看,一些其他的个体特征变量(如道德推理、道德认同和移情等)也应当引起运动领域学者们的瞩目,如吴鹏等人进行的元分析研究发现,道德推理与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与不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14];王兴超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道德认同可以负向影响大学生攻击性行为[15]。然而,从运动领域的实证研究看,道德推理、道德认同和移情等变量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还尚未引起关注,将来的研究应当探究这些变量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影响运动员运动道德行为的发生,为将来运动员职业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三)社会情境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社会情境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练风格和动机氛围两个变量。在教练风格方面,Hodge等发现,自主型教练风格可以显著正向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负向显著预测与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和对手)[10]。Hodge等对兴奋剂态度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16]。在动机氛围方面,Boardley等研究发现,掌握氛围与运动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与运动反社会行为(队友)显著负相关,与运动反社会行为(对手)相关不显著;表现氛围与运动反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与运动亲社会行为(队友)显著负相关,与运动亲社会行为(对手)相关不显著[17]。然而,虽然上述几项研究分别探究了教练风格、动机氛围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但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仍旧较为缺乏,其研究结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而且其研究结论能否适用我国运动员也有待探究,因此,将来的研究应当在我国文化背景下验证教练风格和动机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情境变量对运动员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此外,一些其他的社会情境变量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父母教养方式、队友创造的动机氛围等等。
三、问题与展望
(一)丰富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研究范畴
现有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研究以运动员反社会行为研究为主,较少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这可能与反社会行为比起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得到媒体注意,并得以广泛传播有一定关系。然而,运动反社会行为虽然重要,积极的运动亲社会行为也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考虑到体育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发展人类优良品性之功效,人们应当更加关注思考运动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以期从中发现亲社会行为形成的有效方式,积极开发体育运动对促进社会积极风气的作用。另外,以往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研究以对手为指向的较多,迄今为止国内还缺乏以队友为指向的研究结果。因此,未来研究应当在进一步加大运动亲反社会行为队友指向的研究,这对于提高运动队团结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强化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纵向研究
已有的关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与年龄关系的研究较少且皆为横断面研究。研究表明,年龄对个体道德发展存在重要影响,那么年龄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也必然存在一些关系。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考虑从实证角度采取纵向研究的范式揭示年龄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性别、运动项目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仍有待明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控制性别和运动项目等因素后探究年龄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完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影响变量的研究中目标定向探讨较多,其他影响变量如动机、情绪、需要等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研究较少,未来应当加大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此外,当前研究多探讨单一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缺少多变量交互影响研究,如将个体特征变量与社会情境变量结合影响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研究。运动员始终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特定的社会情境将对其价值观、社会观等产生影响,这也将影响到他的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研究社会情境变量对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个体特征变量与社会情境变量之间交互作用,这同样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方向。
(四)加大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干预研究
在诸多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研究文献中,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干预研究十分少见。研究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揭示一些现象,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未来加大干预研究十分必要。归因可以影响道德情绪,道德情绪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考虑到归因与道德情绪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以及归因对未来行为的有效影响,可以推测归因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也可能存在重要关联。有效的归因训练可以改善不良归因模式从而对受训者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研究者可以考虑将归因作为运动员运动亲反社会行为干预研究切入点,探讨归因与运动亲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建构我国运动员运动亲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模型以及增加干预手段的新思考。
[1]梁 婷.中国古代体育蕴含着道德精神[EB/OL].(2012-11-27)[2016-04-18].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1/27/c_124007908.htm.
[2]马晓云.德性之维中的古希腊体育道德[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30(2):187-189.
[3]Eisenberg N,Fabes R A.Prosocial development[M].NY:Wiley.1998.
[4]Kavussanu M.Motivational predictors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football[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2006,24(6):575-588.
[5]Kavussanu M. Moral behaviour in spor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2008,1(2):124-138.
[6]陈作松,王 栋. 运动道德推脱的研究评述[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4):9-13.
[7]Kavussanu M,Boardley I D.The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scale[J].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09,31(1):97-117.
[8]祝大鹏.运动员体育道德: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展望[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8(7):64-70.
[9]Boardley I D,Kavussanu M.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sport scale[J].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07,29(5):608-628.
[10]Hodge K, Lonsdale C.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The role of coaching style,autonmons vs controlled motivation,and moral disengagement[J].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11,33(4):527-547.
[11]王 栋,陈华东,翁滢渌,等.运动员道德意识与运动反社会行为:运动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30(4):364-368.
[12]张璐斐,张华光,施小菊.青少年运动员的目的取向与体育道德关系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2):190-191.
[13]贺亮锋.体育运动中的非道德行为与运动员目标定向关系研究综述[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7,26(3):42-44.
[14]吴 鹏,刘华山.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学报,2014,46(8):1192-1207.
[15]王兴超,杨继平,刘 丽,等.道德推脱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3):532-538.
[16]Hodge K,Hargreaves E A,Gerrard D,et al.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doping attitudes in sport: Motiv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13,35(4):419-432.
[17]Boardley I D,Kavussanu M.The influence of social variable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s in field hockey and netball[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2009,27(8):843-854.
(编辑:常志卫)
2016-04-18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5YJC890003)
陈华东(1986-),男,讲师,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高松龄,Email:1578325223@qq.com
G804.8
A
1009-4784(2016)02-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