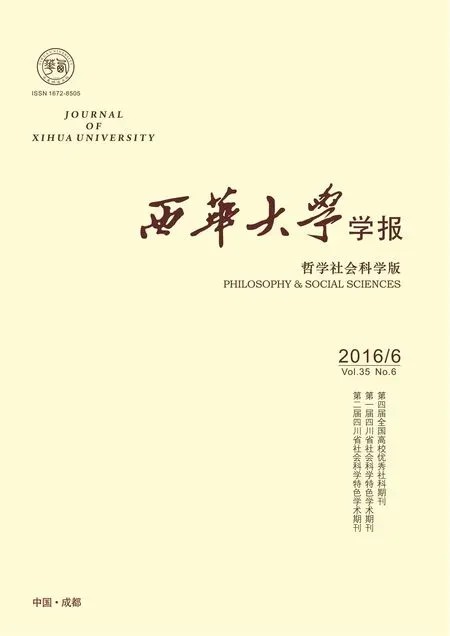试论苏轼诗歌的比喻艺术
2016-12-15商拓
商 拓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756)
·蜀学研究·
试论苏轼诗歌的比喻艺术
商 拓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756)
苏轼的诗歌善用比喻艺术。其诗歌的比喻,具有广泛性——不受时空限制,不受题材拘牵,亦不受体裁束缚;同时,又形式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曲喻、讽喻,也有博喻、联合比喻等;苏诗的比喻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准确贴切、恰到好处,真实亲切、具体生动,新颖奇特、变化多端,幽默诙谐、精警深刻。
苏轼;诗歌;比喻;广泛性;形式多样;艺术效果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4即用某种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明的事物,即人们常说的打比方,或称比喻。它不仅是汉语修辞格上的辞格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刘勰所谓“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2]202,即指此修辞手法。苏轼的诗歌创作就常用比喻手法。苏轼现存诗二千七百余首,其中大部分诗歌都程度不同地使用了比喻。对此前人早有评论,(清)施补华就说:“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不尽,重加形容。”[3]990可见苏轼是运用比喻进行诗歌创作的典型代表。对此本文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苏轼诗歌中的比喻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从他早年到晚年,由家乡至海南,无论何时何地;或刺时议政,或写景言情,无论何种题材;是五言七言,还是古体今体,无论何种体裁——比喻这种艺术手法,在苏轼的诗歌中都是随处可见,运用十分广泛普遍。
首先,苏诗运用比喻是一贯的,不受时空的限制。苏轼早年未出川时在家所写的《郭纶》一诗中,“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指出人们只看见郭纶所骑骢马瘦弱,却不知他使用的铁矛大如屋椽,就用比喻写出了郭纶“屡有战功,不赏”而“贫不能归”[4]5的窘况,对郭纶表示了赞扬与同情。而《咏怪石》一诗,则以物写人,全篇用比,颇多寄托。其中“初来若奇鬼,肩股何孱颜。渐闻声,久乃辨其言”[4]2605,就将奇石比作能说话的“奇鬼”以向世人倾诉自己的大才未被时用,既新颖奇特,又寓意深厚,“奇人”或是诗人的自喻亦未可知。其在出蜀离家途中所作《舟中听大人弹琴》一诗就将“残缺”的古琴比作“老仙”,阅尽历史的兴亡。又用“风松瀑布”“玉珮声琅珰”“浮脆如笙簧”[4]13等不同的物体声响来刻画琴声的变化,亦颇精彩而不乏新意。他在凤翔任官时所作《凤翔八观》八首几乎首首用比。其《东湖》云,“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而岐山地区却“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但不料往东南数步看见了湖潭,“入门便清奥,怳如梦西南”[4]112,仿佛梦中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西南”一样。用对比、比喻将自己的愉快心情明白地表现了出来,平淡而自然。熙丰变法时期,苏轼先自请通判杭州,后又调密州,改知徐州、湖州,最后因“乌台诗案”被判黄州,虽仕途上迭遭挫折,而其诗歌创作却更趋成熟,比喻手法的运用更加繁密熟练。如描写杭州西湖风景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4]430头两句既写西湖的“水光”“山色”,亦写西湖晴姿雨态,实中含虚,暗寓“淡妆”“浓抹”。后两句由实入虚,把西湖比作春秋时越国的美人西施,与前两句呼应,说她无论“淡妆浓抹”都难掩天生丽质。比喻贴切新奇,富有神韵。苏轼本人对此比喻亦颇满意,故在自己的诗中多次使用:“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次韵刘景文登介亭》)[4]1700;“祇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次前韵答马忠玉》)[4]1761;“西湖虽小亦西子,縈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4]1878。从此西湖便有了“西子湖”的美称,这一比喻“遂成为西湖定评”。再如苏轼在黄州时所作《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4]1033;《次韵前篇》又云,“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4]1033——皆用比喻手法。前者刻画环境的幽静,后者指出时事难期,年华流逝,皆具体生动,形象鲜明。苏轼贬谪海南时期所作的诗更进入化境,运用比喻更为纯熟,《纵笔》诗其三云,“北船不到米如珠”[4]2328,就用比喻写出了当时因海运阻滞,海南缺粮,使得诗人陷入了“醉饱萧条半月无”[4]2328的困难窘境。他由海南回归时途经大庾岭遇一老翁,老翁知其是苏轼时说:“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4]2424,就用比喻的手法表明自己高洁的情怀。不难看出,在诗歌中使用比喻贯穿于苏轼一生的创作中,其是不分时地、不受约束的。

再次,苏诗运用比喻是不受体裁形式束缚的。苏轼最擅古体诗,七言古体如《吴中田妇叹》“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4]404,两句两比,直写倾泻如注的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的灾害,农具发霉,镰刀生锈,“出菌”“生衣”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奇,显示出苏轼独特的艺术才华。五言古诗如《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二开头两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4]1526,用“幽人”比竹,以“处女”比花,进一步突出竹与花的风韵,是诗人在此诗第一首中以“神似”论诗的最好说明,精当确切,生动形象。苏轼的律诗亦颇有特色,七言律诗如《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一开头两句“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4]579,写飞蝗成阵象弥天塞地的烟障自西天蜂拥而至,虽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洒落的迅猛密集,以比喻写蝗灾的严重,具体准确。苏轼的五言律诗不如古诗与七律,但在比喻的运用上亦不乏佳作,如《荆州十首》其八“江水深成窟,潜鱼大似犀。赤鳞如琥珀,老枕胜玻璃”[4]66,写荆州江中之鱼的情景,具体细致,使人一目了然。其绝句创作特别是七言绝句亦不乏佳作名篇,而比喻手法的运用更是随处可见,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几乎首首用比,其第二云“万人鼓噪慑吴侬,犹是浮江老阿童”[4]484,连用两比,描绘潮来的威势。前句写所闻:怒潮呼啸而来如万人鼓噪,使弄潮观潮的吴侬都为之震慑。后句写所见:怒潮之来仿佛当年王浚(小字阿童)率军沿江而下,一举攻下建业,势如破竹。想象丰富,用典精切,令人叫绝。再如描写西湖景色的诗歌就多用七绝,多用比喻,《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二云“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4]369,大雨过后,潮水平静,江海相连,浩如碧玉,只有远处一时电光闪耀,划过长空,就象时隐时现的紫金蛇。想象奇特,真不愧是赞美“壮观”的“好句”了。苏轼很少用五绝,沈德潜说他“短于五言”[3]544就是指五言绝句而言。
不难看出,苏轼的诗歌创作,不受时空限制,不受题材拘牵,也不被体裁约束,广泛地使用了比喻的艺术手法。
二
苏轼诗歌使用的比喻手法又具有形式多样的特点。苏诗的创作,既有明喻、暗喻、借喻等一般常见的形式,也有曲喻、讽喻等不太常见的形式,甚至还有博喻、联合比喻、喻中套喻等特殊形式。各种形式互相结合,变化多端。
明喻又称显比、直比、明比,是一种常用的、明显的比喻,它是本体、喻体、比喻词都要出现的比喻,且本体与喻体之间在形式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或相类)的关系,二者之间往往用象、如、似、若等喻词进行连接。苏轼诗中使用明比的地方随处可见,出现十分频繁。其中有本体、喻体均为具体事物者,如《过子忽出新意,出山芋作玉糁羹,……人间决无此味也》云:“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4]2317苏轼被贬海南时,生活十分艰苦,其长子苏过特用山芋为他制出了玉糁羹这种新食品,“色香味皆奇绝”,此用比喻赞其色香象上品龙涎仍浓白,味道像牛乳而“更全清”。王文诰谓“此即海外实录”,表现出诗人在艰难困苦中的开阔胸怀。《南堂》其五云“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4]1167,诗人在南堂扫地焚香闭阁而眠,竹席细密,波纹如水;纱帐轻软,如烟如雾。其悠然自得的情怀、旷达乐观的胸襟跃然而出。有本体、喻体皆为抽象者,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4]97这里的“飞鸿”并未指具体的飞鸟,而是用来比喻飘忽不定的人生。有本体、喻体一为抽象一为具体者,如《徐大正闲轩》诗云:“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4]1284闲是什么味道,谁也难以用语言说出,但苏轼却用“如眼不自睹”五字作比,说它就象眼睛不能自己看见自己一样,把闲味明白地揭示了出来。本体闲味的感受是抽象的,而喻体眼睛却是明白的、具体的。《寒食雨二首》云:“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4]1113诗人谪居的荒村小屋,在寒食的濛濛雨雾中,仿佛是苍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本体小屋是具体的,而喻体诗人孤独的心境却是抽象的。
隐喻,又称暗喻、隐比、暗比,是不露比喻痕迹的比喻。隐喻使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更密切,融为一体。其语言更精炼,语义更含蓄。隐喻的本体、喻体都出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相同、相等或相类的,比喻关系往往不用比喻词表示,而是暗含在句子的结构中。苏轼诗歌中的暗喻也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苏诗有时将比喻词隐去不用,从而使诗意更富曲折性和含蓄性,意蕴更深厚。如《新城道中》其一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4]436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上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圆形的一种乐器)。以絮喻云,取其轻软而色白;以钲喻日,取其形状之相似。皆以平常事物为喻体,平淡自然而又新鲜活泼,情趣盎然。《有美堂暴雨》云:“十分潋滟金尊凸,千杖敲铿羯鼓催。”[4]483暴雨如注,西湖水涨,仿佛象一只酒满将溢的金盏;雨点密集,击打湖面,铿锵澎湃,又好像羯鼓齐奏。以“金尊凸”和“羯鼓催”分别比喻雨势雨声,状形绘声,形象贴切,如闻如见。苏诗中的暗喻有时与用典结合起来,联想丰富,如上例中“十分潋滟金尊凸”就化用杜牧《羊栏夜宴》“酒凸觥心潋滟光”句,而“千杖敲铿羯鼓催”又反用唐代宋璟描述击鼓“手如白雨点”诗意,皆不着痕迹而有行云流水之妙。
借喻,又称借比,是本体、喻词都不出现,而把喻体直接当作本体来说的一种比喻。表面上只有喻体,不提本体,实际上是强调本体,以喻体代替本体,是一种相代的关系,被比喻事物和比喻事物的关系更为密切。使用借喻,能使诗句意在言外、话中有话、含蓄隽永、耐人寻味。苏轼常用借喻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曲,如《送杨杰》中“三韩王子西求法,凿齿弥天两劲敌”[4]1375,就以晋习凿齿和高僧弥天(释道安)分别借喻杨杰和高丽王弟僧统,以他们二人同登泰山、上泰华、游钱塘的情景,赞扬杨杰旷达、豪迈的情怀,对其“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表示了欣羡向往之情,含婉不露,颇有韵味。再如《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其一“尚书清节衣冠后,处士风流水石间”[4]584就以三国时的曹魏尚书仆射毛玠和唐代处士方干借指同游者毛国华县令和方武县尉。据《三国志·魏书·毛玠传》载,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受到曹操的称赞。此借以指毛国华乃毛玠之后,亦有颂美之意。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方干曾隐于会稽鉴湖之滨,终身不仕,此亦以方干借指县尉方武,赞其为“风云水石间”的“处士”。此两处借喻,不仅谐音其姓,而且称颂同游二人皆清流雅望之士,切人切事,恰切精当而又韵味无穷。再如《寄题刁景纯藏春坞》“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4]679,就以汉末时的徐元直(徐庶)比友人,以汉末襄阳岘山德高望重的庞德公喻刁景纯,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刁景纯的仰慕之情,引典为喻,恰切精当。
曲喻是一种隐晦曲折的比喻,即从喻体的某一方面转移、联想到另一方面,再通过转移、联想使喻体和本体产生相似关系,换言之,即由一个比喻生出另一个比喻。由于它采用转一个弯子来设喻,故名曲喻。如苏轼《和李太白》云:“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4]1232此由月光似水联想到要用月光洗涤自己的心胸,拟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原韵而自出机杼,难怪纪昀说:“非东坡不敢和太白,妙于各出手眼,绝不规模。”[4]1232胡仔也认为:“大率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8]215再如《守岁》诗:“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4]161开篇六句把旧岁比成一条向深壑中滑去的大蛇,蛇身已经溜走了,只剩下尾巴,它的去意已定,你使再大的劲,又怎能将其拽回呢!想象新奇,比喻绝妙。且这一比喻将喻体岁月坐实,让它有行为动作,生动具体。更重要的是,通过守岁的徒劳,让人们进一步体会到岁月的流逝,这就把诗人同时也是所有的人对于岁月的流逝乃至人生的不再等感慨深刻地表达了出来,喻意深刻,别开生面,不同凡响。
讽喻,通常是指在本意不便明说,或者用简单的语言、一般的方式不容易把事理讲清楚的情况下,借用其它故事(寓言、典故)、事物来寄托抒发作者的感情。讽喻具有深入浅出、言近意远、委婉含蓄、讽刺幽默、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苏轼的诗歌多用讽喻手法,也因此而常常遭到政敌的迫害。如他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4]2366纪昀评此诗说:“前半(指此四句——笔者注)纯是比体。如此措辞,自无痕迹。”[7]1564此诗是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自贬所海南岛返回内地时所作,心情自是不同。“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之景,“欲三更”是诗人对时间的判断。前两句既写景,也写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可见诗人的心境是开朗的。而在此之前,却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久雨不停谓之苦雨,终日刮的凄风称为终风。“也解晴”:也知道放晴了。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暗中终于看到了“参横斗转”、晴天将至,其惊喜之情,跃然而出。三四句进一步就“晴”而言:“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过雨住,“海色”也是“澄清”的。此四句虽写的是眼前之景,但排比直贯而下,写出了诗人艰辛苦楚的人生困境和宠辱不惊、泰然待物的坦荡心境,更深富政治更替、时事变化于其中。再如《儋耳》一诗首联“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4]2363,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分,诗人独自登高,凭栏远望的情景。霹雳,疾猛之雷,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写所见之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的去世,徽宗的继位,朝政将更新。“暮雨”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则表现了他对徽宗新朝的幻想。其时徽宗刚即位,欲清除朝廷党争,苏轼对此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次联“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更是借写眼前之景,喻指时局的变化。“雌霓”指政敌的失势,“雄风”指诏命的降临,皆讽喻时事,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方东树称之为“奇警”[9]447,颇有见地。此外,如《荔枝叹》中将荔枝比为祸害苍生的“尤物”,也不无讽谏之意。
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轼诗歌中的博喻。博喻又称复喻、联喻,是以许多喻体说明一个本体,列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喻体来说明某一相似点。这种比喻使语言的力量增强,意味深厚。苏轼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把博喻的运用推向了新的高峰。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穴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它象《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10]72诸如此类,在苏轼的诗中甚多,如《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一诗,从题目可知,诗人仿效了欧阳修的原作,为避俗套,亦“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与雪颜色相关的事物“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与雪相关“等字”[4]20,但诗中大量使用比喻却是毫无疑问的。本体是雪,而喻体甚多,有人亦有物,显示出苏轼运用语言文字的高超技能。再如《西湖寿星院此君轩》:“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苍立玉身。一舸鸱夷江海去,尚余君子六千人。”[4]1688首句从听觉上写竹,以“碎龙鳞”喻风吹竹的声音;次句从视觉上写竹,以“立玉身”喻翠竹之形状;末两句从品性上喻翠竹为君子。连设三喻,喻体虽不同,但本体却都是竹,三个喻体分别从三个不同方面突出本体的特性,共同说明本体,表现出深刻细致的艺术效果。
苏轼的诗歌还往往将各种比喻联合使用,互相补充,富于变化。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4]340此诗写望湖楼的景色,每句一景,四句三喻。首句写云,乌云骤起,象墨汁被掀翻一般;次句写雨,暴雨骤来,雨点象珍珠般跳到船上;三句写风,狂风骤至,象卷地一样吹散了云雨;末句写湖水,湖水骤平,望湖楼下水天一色。连设三喻,分别以云、雨、水为本体,以墨、珠、天为喻体。一二句为暗喻,末句为明喻,分别从四个不同方面将西湖盛夏降雨的特色刻画得淋漓尽致,十分传神。多种比喻的综合使用,使此诗“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3]544。再如《戏子由》一诗中“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用明喻,“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就用借喻、反喻,“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密”兼用明喻、讽喻,使此诗显得新颖别致,意味深厚。
此外,在苏轼的诗中还有一句数喻的短喻,如“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4]892(《百步洪》);数句一喻的长喻,如《守岁》“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4]161;倒喻,如形容西湖之美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4]430;奇喻,如形容借酒浇愁为“三杯忘万虑,醒后还皎皎。有如辘轳索,已脱重萦绕”[4]423(《正月九日有美堂……》)。还有引喻如《书焦山纶长老壁》:“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4]552先用“君看”二句比“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又用“譬如”以下数句比“君看”二句,比中套比,由前一比引出后一比。
综上所述,苏轼诗歌中所用的比喻不仅数量多,而且方法多、类型多,巧于变化,涉及面广,堪称典范。
三
苏轼诗歌中广博的比喻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古人所谓“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11]286,即指此。苏轼巧妙的比喻往往画龙点睛,将诗意升华,提高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性。
首先,苏诗的比喻准确贴切,恰到好处。《文心雕龙·比兴》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2]205-206刘勰认为比的方法没有一定,或比声音,或比形貌,或比心情,或比事物。虽然比喻的类型很多,但总以准确恰切最重要,如果把天鹅刻画成家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要准确贴切就必须要注意比喻运用的基本条件,即本体和喻体是属性不同的两种事物,但它们之间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如形态、特征、性状等)。惟其相似,才构成比喻;而惟有不同,比喻才有意义。苏轼的诗歌广比博喻,但每一个比喻都准确贴切,恰到好处,经得起人们的反复推敲与细心琢磨。如《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云:“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4]369这是诗人在熙宁五年八月监考贡举时登临望海楼所作。首句描写海面涛头涌来的雄伟奇观。站在凤凰山腰的望海楼上极目远望,潮头就像一条线似的滚滚而来。“一线来”的比喻恰切精当,十分准确。次句“雪成堆”不是指“卷起千堆雪”的白浪,而是比喻被潮头卷起的沙堆。刘禹锡有诗:“八月涛声吼地来,……卷起沙堆似雪堆。”[12]252此处苏轼亦以“雪堆”喻沙堆,很贴切准确。末句以“银山”喻海潮以突出其气势,亦颇精当。其二云“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4]369,写骤雨过后,钱塘江潮平,海天一色宛如碧玉,只有远处不时闪现的电光,就象时隐时现的紫金蛇一样。其实这种雨后闪电的奇妙景象在盛夏是随时可见的,并不稀罕,但诗人用“紫金蛇”三字将其写出,不仅形象逼真,富有生活气息,而且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十分准确。再如《舟中夜起》诗云:“舟人水鸟两同梦,大鱼惊窜如奔狐。……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4]942以“奔狐”来喻“惊窜”的“大鱼”,用“寒蚓”幽咽的声响来喻潮水渐漫沙滩的声息,皆以动写静,突出了月下湖面的平静;而“落月挂柳看悬蛛”更为奇特:远看落月挂在细密的柳枝上仿佛是悬在珠网上的蜘蛛一样。这既是茫茫湖面上见到的远景,也是月色微茫、细柳如丝所产生的幻觉,恰切准确,令人叫绝。
其次,苏轼诗歌的比喻真实亲切,具体生动。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诗歌创作要有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袁枚曾说:“目之所未瞻,身之所未到,勉强为之,有如茅檐曝背,高话金銮。”[13]74如果诗歌所写并非作者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那就好像两个穷汉脱光上身在茅檐下晒太阳,却高谈阔论京城中皇帝所住的金銮殿一样,完全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没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苏轼的诗歌所写皆其亲身经历,反映的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情景。诗中的比喻亦是从生活中提炼,故能真实亲切,具体生动。如苏轼《谪居三适三首》其一云:“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騣。”[4]2285这是诗人谪居海南儋州时所作。诗人将“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视为“三适”,而用沙尘满騣的服辕之马来喻写自己年轻时忙于朝谒之苦的情景以反衬今日从容理发的适意,抒写了自己虽历尽艰辛却自得其乐的旷达情怀,比喻具体亲切,若非亲身经历感受,决不至此。再如《自题金山画像》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4]2641诗人屡遭迫害,贬谪天涯,浪迹萍踪,以至年迈,壮志未酬,有才难展,面对自己的画像,辛酸沉痛的经历、身世沧桑的感慨都蕴含在“已灰之木”“不系之舟”这两个喻体之中,真实而又具体,生动而又传神。其《吴中田妇叹》云:“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4]404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而米价低贱就如同糠与碎米价一样,经过许多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其比喻具体真实,若非亲历亲见,决无如此真实的描写。再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云:“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4]2365,诗人翘首北望,广袤的天空与苍莽的原野相接,高飞远去的鹘鸟正消逝在天际,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青山犹如一丝纤发,那里正是中原故乡。“青山一发”既是实写之景——雄伟壮观的青山宛若地平线上露出的一丝起伏的头发,可见其遥远;也是抒发感情——远处青山若隐若现,宛若发丝的若有若无,它牵动着诗人的思乡情愫,归乡难期。这里以发丝来比喻天际的青山,新鲜别致,真实具体,若非亲历眼见,决不能作此奇想。
再次,苏轼诗歌的比喻新颖奇特,变化多端。苏轼主张写作诗词文章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4]2210-2211,在遵守创作规律的前提下力求创新出奇。由于苏轼阅历丰富、生活经验深厚,且学问渊博、知识面很广,故其诗歌创作,无论选题立意,还是材料取舍,往往能别出手眼,巧比妙喻层出不穷、清新隽永、不落俗套。苏轼常常在自己的诗中描写相同的本体,但却很少使用同样的喻体。如写山:径山是“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4]348;巫山是“孤超兀不让,直拔勇无畏”[4]34;庐山是“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帝遣银河一派重”[4]1210。虽同样以比喻写山,但喻体却各尽其态,绝不雷同。再如写水:长江是“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4]42;黔江是“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4]32;汉水是“偶似蜀江清,……游女俨如卿”[4]72。也是各有特点,并不陈陈相因。再如写花,“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4]1713(《赠刘景文》),此用擎雨无盖比喻荷败净尽,用傲霜独立之枝喻菊之挺拔劲节,皆曲笔传神。写红梅云,“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4]1107(《红梅三首》其一),以桃杏喻其颜色,以雪霜拟其身姿。写海棠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4]1186(《海棠》),以人喻花,想象丰富。这些比喻虽本体相同,都是花,但喻体却千姿百态,各有独至,并不相同。苏轼在描写具体事物时用比如此,而在抒写抽象的感情时,由于各自的情景不同,其所用喻体也不一样。如同样写岁月流逝、光阴不再,《守岁》云:“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4]161将岁月的流逝比作赴壑之蛇,难以拖住。而《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诗云“岁月翩翩下坂轮,归来杏子已生人”[4]931,又将岁月的逝去比喻成如坂走丸的下坡的车轮,速度很快。本体虽同,但喻体意义并不相同。再如,同样是表达人生的难以预知,身受世情羁绊难以自由,《次韵前篇》云,“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4]1033,喻世间之事就象花开花落一样不可预知,人生岁月的逝去就象酒一样禁不起倾倒,很快将尽;《迁居临皋亭》云“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4]1053,用蚁寄大磨,随磨旋转,不能自已,抒写自己对于人生不定的思索;《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云“此身如线自萦绕,左旋右转随缫车”[4]2148,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比作随缫车旋转的线一样,毫无定准;《送司勋子才丈赴梓州》云,“人生初甚乐,譬若枰上棋。纵横听汝手,聚散岂吾知”[4]2602,又把人生比作棋盘上的棋子,任人摆布,聚散难料。这些比喻的本体也都相同,都指人生,但喻体却各有特点,显得新颖奇特,并不前后相袭、互相模拟雷同。苏诗中也常用一个喻体比喻不同的本体,其比喻手法灵活多变,应用自如。如《与王朗昆仲及儿子迈……得“月明星稀”四字》其二云“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4]985,以君子比喻清风;《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云“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4]530,又以君子比喻茶之优良。苏轼诗中比喻的运用可谓千变万化,既出人意外,又常在情理之中,新颖奇特,鲜明生动。
最后,苏轼诗歌的比喻幽默诙谐,精警深刻。苏轼是一个幽默诙谐的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子瞻虽才高行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是以尤为士大夫所爱。”[15]42幽默诙谐使苏轼的人生闪耀出智慧的光彩和旷达的乐观精神,这在苏诗的比喻中也反映了出来。苏轼诗歌的巧比妙喻常常体现出幽默风趣的特色。如《戏子由》: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4]324
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初苏轼连续两次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新法,未获准允,为避锋芒,自请外任杭州,十一月到任杭州通判。前一年其弟苏辙亦因力诋新法,被黜为陈州教授,此诗是苏轼刚到杭州任时写给陈州其弟的。以“戏”为题,本身就显出幽默风趣的意味。(宋)朋九万《乌台诗案》认为此诗为讽刺新法之作。前半为戏子由语,连设三对比喻极诙谐地写出苏辙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首以苏辙身长如土丘,而学舍屋矮如小舟的比喻,言其才高官卑却不肯阿世取容而能安贫乐道,于同情安慰之中又流露出对其学官位卑却可免去新贵烦扰的羡慕之情。含讥带讽而不失幽默之趣,令人忍俊不禁。次用《汉书·东方朔传》和《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两个典故为喻:任凭别人耻笑自己象东方朔一样贫穷而不顾,却不肯象优旃那样屈己媚人在雨中站立。并称赞子由不以眼前得失、困难为怀,随缘而适的乐观豁达。比喻信手拈来,虽为戏言,却洒脱诙谐。“劝农冠盖”一对比喻,更是形象生动。“闹如云”把“劝农”的官员们到处“苛细生事,发摘官吏”的喧嚣纷扰揭露无余;“甘似密”又对“朝齑暮盐”、甘居清贫的学官赞颂有加。两个比喻形成鲜明的对比,语中带刺,幽默诙谐中寓含深厚的感情色彩。苏诗比喻的幽默诙谐并非只表现在讽刺之作中,在其它题材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如《叶教授和溽字韵诗,复次韵为戏,记龙井之游》中“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4]1705将功名比作千人追逐的一只兔子,新颖奇特,幽默风趣。《无锡道中赋水车》云“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4]558,喻水车转动时,一节节车斗象联翩衔尾的乌鸦,而停止转动时就象蜕皮剩骨的蛇,以两个比喻写水车动、静时的不同情状,具体生动,于幽默风趣中不乏喜悦称赞之情。《于潜女》云“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4]448,描写穿着青裙白衫的于潜农妇,光着一双如霜一般白的没有穿鞋的脚。光脚的农妇,理应是黑色的脚,苏轼却以霜作比,形容其白,于诙谐风趣的比喻中,真实地再现了于潜女的形象,鲜明活泼,真挚亲切。
综上所述,苏轼的诗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的典范,其中比喻手法的运用更是不胜枚举,丰富多彩,构成了宋诗之一大观,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1]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M].济南:齐鲁书社,1982.
[3] 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陈衍,评选,曹旭,校点.宋诗精华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6]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彙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 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1] 包恢.答曾子华论诗[M]//全宋文·31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 刘禹锡.刘禹锡集[M].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四[M]//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4]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M]//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 燕朝西]
On the Figurative Art in Su Shi’s Poems
SHANG Tuo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1756,China)
Su Shi is good at using figure of speech in his poems and in which the figurative expressions exist extensively, i.e. without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subject restriction and genre constraints; moreover, in which its various forms exist, i.e. simile, metaphor, trope, song yu, bo yu and joint metaphor, etc. The figurative expressions show artistic effects strongly in Su Shi’s poems, which are accurate, perfect, real, vivid, fresh, various, humorous and profound.
Su Shi; poems; metaphor; universality; diversity; artistic effect
2016-09-01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16DFWH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商拓(1963—),女,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I207.22
A
1672-8505(2016)06-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