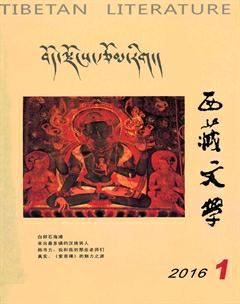韩书力:我和我的那些老师们
2016-12-08汪璐
汪璐
说到西藏的绘画,韩书力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一个文艺界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个推动藏地绘画的先行者。他的诸事似乎都透明在大众眼前,又被众多媒体推向了一个神秘的制高点——大家看得见,够不着。鉴于此,他被迫地成了~个大忙人,就像约定此次采访的时间,一不小心就从去年冬天跨入了今年的秋天。
9月10日下午,我如约来到韩书力位于文联的家中。书香、茶香、墨香混杂的居室里,他正接待着三位从浙江慕名前来拜访的画家。我在一旁边等候边听他们聊天。其中一位画家雪女士言谈特别激动,用今天的话说,她就是韩书力的“铁粉”。她不仅带来了自己的画集,还带来了几十年里她对韩书力的仰慕之情和终得一见的喜悦之情,她用了很多溢美之词来描述韩书力对她一生的影响和精神导师般的作用——虽然,他们只是第一次见。如同我,长久地“认识”着“韩老师”,今天也才第一次正式地面对面坐下说话,但毫无违和之感。
客人走了,韩书力认真地问我准备采访什么?这个问题我自己都想了很久。说实话,接这个写作任务我也很惶恐,因为关于介绍他的文字、影像不敢说铺天盖地,也可以说不计其数了。随手在网上输入“韩书力”三个字,有关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挖了个遍。于是,我的采访大纲也在等待他的九个月中一次次变化,期望找到一个全新的突破口。
巧的是,他最终把采访定在教师节。我忽然好奇,韩书力几乎被所有人尊为“韩老师”(上至领导、下至第一次见面的人),他自己是否也有一些难忘的老师呢?果然,和他一说这个主题,他顿觉轻松起来:“在教师节回忆我的老师,倒是件很欣慰的事情。我也一直记得他们,因为没有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没有今天的我。”
启蒙阶段,得到老师们的鼓励和点滴爱心
“就从启蒙老师说起吧……”韩书力捋着自己的思绪,“我读小学的时候,有几位启蒙老师,到现在我都不能忘怀。”韩书力说每次回北京休假时,他都会和同学骑车去原来南苑机场附近几位老师的旧址寻找,只是北京发展建设日新月异,那几位老师先后都搬家了,导致许久没有联系上。
韩书力首先提到一位叫张文的老师:“他是北京18中毕业的,毕业后就在我小学期间学习绘画的‘南苑少年之家当老师,所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张文老师那会只是辅导员,所以绘画才能并不是其最突出的,但韩书力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全中国人都很穷的年代,刚毕业的张老师带着学生到北海画舫斋看展览,还用自己微乎其微的工资给学生们买车票,天热时给大家买汽水……这些都是不能报销的。
“当时张文老师从自己可怜的饭碗里抠出来一点照顾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作为老师,他对自己学生的那份热情、鼓励和呵护。”正是张文老师一心一意为少年之家的学生铺路搭桥,一次次为他们创造学习、观摩的机会,启蒙了韩书力和他那些爱好美术的同学们。
说到启蒙老师,韩书力的记忆被完全打开:“后来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时,每隔两个礼拜就要到‘南苑少年之家上课。当时又来了一位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附中毕业的金声老师。金老师那会儿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就住在少年之家里。”当时韩书力的家离南苑“少年之家”十多公里,他在哥哥、姐姐休息的时候,他就借他们的自行车去少年之家上课,遇到哥哥姐姐加班就向家里要点钱坐车去……总之,能省就省。金声老师知道他的处境后,给他和另一个同学每人两块钱,让他们买了一张月票。“一个月内北京市里的公交车都可以坐!当时两块是很大的钱!可作为孩子,只觉得有了月票很方便,却没有想这个钱对老师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韩书力说正是那两块钱的月票和一个月正常学习时间的紧密相连,才让他完成了最初的学习。在金声老师的指导下,韩书力的绘画有了很大提高。“虽然如此,金声老师有时觉得自己修养不够、眼界不宽,还把他的艺术院校的老师请来指导我们画画。有时带着我们到农村、荒地里采野花,说自然生态的野花比城市花房里的花要好……”往事虽已久远,但在韩书力的讲诉里,一切仿佛历历在目,“还有一位张健老师。他是金声老师的同学,因为他就在我们家旁边的学校教美术,我经常去请教骚扰,对我的帮助也很大。”韩书力记得张建老师那会住在学校,平时喜欢音乐的他,闲时喜欢用风琴怡然自得地演奏“洪湖水,浪打浪……”。那是在1961年前后,所以直到现在,只要一听到这支曲子,便立刻会想到张健老师,当然也会回忆起当年饿肚子的滋味。
“我的这三位小学老师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关怀、很大的鼓舞,这种教诲至今难忘。”
让韩书力欣慰的是,在一位好心朋友的帮助下,他前几年找到了张文老师。张文老师由于受文革冲击,腰落下疾患,他把老师接到自己在北京的寓所,并送上自己的画册,算是向老师汇报自己这些年的成绩,更是解了多年的一种想念。
“他们对我的帮助很重要!”韩书力感激之余也很遗憾有的老师至今未曾找见。
得遇良师,更上一层楼
上初三时,韩书力就读的首都医学院附中分来了一位叫余友心的年轻美术教师。
“余友心老师毕竟是大学本科毕业,他的学术程度要比我的启蒙老师更高,他的毕业作品也发表在一些专辑上。那时我看到他,就像仰望很高的一座山。”韩书力说余友心的优秀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造诣,还因为他会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说到这,韩书力忍不住自我调侃了句:“我就没有这些优点,否则我也留在中央美院教书了。”韩书力把余友心的到来当做喜从天降,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纠缠”着余友心,零距离学习着学院派那套速写、素描的基础,让自己所学更规范了,通过近一年的强化,韩书力有了考入中央美院附中的愿望。
“余老师是我艺术人生的第三个馒头,启蒙老师给予我前两个馒头,没有之前的那点基础,余老师也不会理我。这就叫‘苍天有眼,给你送来一位老师!”
1965,韩书力如愿考上了美院附中,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之后虽照样招生,但学校的混乱状态导致不久生源就被退回去了,“这都是人生的坎,我还很幸运赶上了、留下了。”韩书力觉得能考进美院附中很不容易,所以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虽然这个学校4年有3年都在文革纷乱、嘈杂的环境中,但我真的没有浪费时间。作为一个工农子弟能考进这个名校,太不容易了。谁敢荒掷时光啊!”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被定性分类,韩书力既不是黑五类,也不是红五类,他的身份、社会关系只能做逍遥派。他无资格让自己极左或极右,所以在学校里大字报也要抄一抄,口号也要喊一喊。“我认识到这些不是我想要的。和我有同样认识的同学就约着一起到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画速写,那时给人画像也不会有人向你要钱。”他们因为带着中央美院附中的校徽,出入那些地方还算方便。
“在那种整个社会都很浮躁混乱的环境里面,我还保持着求学、上进的一颗心,现在看来是个可贵的心,也是个平常心。”想起那段时光,韩书力庆幸自己没有疯,没有跟着有些同学瞎起哄。他把那四年归纳为:一年基础课。三年“请教老师”。“其实也等于‘偷艺,因为老师不是在被批判就是被监视,没有谁敢教课。大家都在学校‘闹革命,只有吃饭的时候,我们才能想办法躲开工宣队、军宣队的目光,偷偷的找老师请教,去写生也是偷偷的。像做贼一样……”说到这里,韩书力忽然童心大发地站起来,把手放在身后给我比划当时的情景:“我们就这样,把画夹藏在背后的衣服里。校门口有值班的问‘你们干什么去?我们就说‘去清华看大字报,哈哈……”
那段时间,韩书力开始重点学习色彩,色调。虽然当时大多数老师不敢给学生讲解提点,但依然有老师冒大不韪给学生传授技艺。“我要必须说几个老师。著名的油画家孙滋溪老师,高亚光老师,高潮老师,赵友萍老师,李天祥老师,王文彬老师,杜健老师就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中敢于冒着风险小心翼翼给我们指点的人。”话锋一转,韩书力有点奇怪地说:“现在有的老师求着学生学习、学生却不爱学;有的老师忙着办自己的事情、顾不上学生,甚至学生毕业了,却还没见过他的教授呢……不像我们那时候,师生关系真的很单纯,就是传道解惑。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忘怀老师的恩德。”
与吴作人先生的师生情缘
1975年,已在西藏工作两年的韩书力无意中获得一本外文局主管出版的英法文版杂志《中国文学》,当时由杨宪益先生和他英籍夫人主编,“我和巴玛扎西有幸上过这个杂志,那一期恰好刊登了吴作人的新作品。”
韩书力说当时吴作人是中央美院院长,他作为吴作人先生的忠实粉丝,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向他学习,就是在附中就读时也不敢贸然去找院长。后来。因为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吴作人、李可染等几位当时还带着反动权威黑帮帽子的画家名家。被周总理亲自点名,集中到北京饭店,为外交部、外事单位、驻外使馆,画一批代表中国风貌、中国气象的美术作品,而韩书力看到的那一期《中国文学》,就刊有吴作人先生这一批里的作品。
“因为看惯了那种红光满面、口号性、标签性的画作,当时就感觉一股清新的艺术之风扑面而来。”韩书力坦言那种感染力让当时的自己十分喜欢,就一遍一遍的临摹,却不太得要领,当时还是西藏革命展览馆一名工作人员的韩书力,就壮着胆子贸然写了一封信给吴作人先生寄过去。
“隔了两个多月,我才收到吴先生托他的学生、当时任中央美院壁画系主任的李化吉老师,给我寄来一些先生当年去甘肃、四川康定等农牧区画的速写石印作品,让我学习、参考,连同先生新印发的作品,也签上名、盖上章,很郑重地一并寄来。”韩书力说之后李化吉老师到西藏还再次谈起过收信的事,说吴作人先生在文革时没少受红卫兵的罪,导致刚收到信时,怕韩书力是“红卫兵”似的学生,专门向美院附中的丁井文校长打听,丁校长只说有一个叫韩书力的学生,很用功……“由于文革没有结束,丁校长也没敢多介绍其它。但吴作人先生心里有了底,算是验明了正身,也就接纳了我这名‘私塾弟子。”
那之后,每次回到北京,韩书力都拿着自己的作业以及不太成熟的作品向吴作人先生请教,得到其悉心指导。
1979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指令韩书力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一张壁画,取名“喜马拉雅晨曦”。画完后,韩书力和罗伦张分别在宣纸上题写了汉文和藏文,领导审查时说汉文太弱,要求请书法更好的人来写。那时虽还没有“名家”的说法,但吴作人已是名满画坛,当时他是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既要创作又要兼顾各种公务,十分繁忙。“作为一个学生去麻烦他,我第一不敢想,第二不敢为。虽然那时我们交往有四五年了。后来我的恩师何溶先生从中帮忙给吴作人先生说了,没想到他很爽快的就叫我把这幅丈二匹的大画送去。他夫人萧淑芳先生接了,还替吴先生问我,是横写还是竖写?很当回事。”韩书力说吴作人先生那时也经常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来还专门去西藏厅看了那壁画和题字的效果,甚是认真。
遵从内心,回到西藏
1980年,已经在画坛有一定影响力的韩书力考回中央美院年画系,成为央美的头三届研究生。据他介绍,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丰同志创建了年画系,他去世以后,变成了研究所,后来又被并给壁画系。
“我的业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生导师贺友直教授,教我的时候已经快70了。当时贺老师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但他和我其他老师一样,为人相当质朴,直爽,简单,是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专业,性情、修养不允许他受社会上乌七八糟东西的侵染。”贺友直后来回到上海老家,韩书力还时常与其保持联系。西藏画家每次在上海开展活动,贺友直先生也自己打车前往捧场、指导。即使现在,93岁的贺老依然和韩书力保持着联系,这是韩书力内心又一段珍贵的师生情。
研究生毕业后,韩书力成绩优异被留校,“本来我该很庆幸,但呆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在那里我找不到在西藏自治区展览馆、在农牧区、农牧民以及寺院中的那种激情与亢奋了,我好像失去了磁场引力,找不到北了。”
韩书力明白,从理论上说,北京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中央美院是美术最高学府,在这里留校任教,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但他还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这样的内心独白:我可以骗别人,不能骗自己,我应该回到那片土地。
“尽管中央美院,从党委书记到系主任,都不理解我要回西藏的想法,但我还是决心回来。”难怪前年韩书力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的时候,当年的系主任杨先让教授在发言时说了一句:韩书力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个异类。
“用杨老师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央美院60多年。只见过多少人想办法、削尖脑袋要留在学校,没有见过有人想办法离开学校……但是,我个人认为杨老师最终认可了我,认为这不是简单地背叛学校、背叛系。因为他发现我还是能做一些实事、也做成了一些实事。”
几十年的实践,让杨教授、让韩书力都知道当初的抉择是正确的。
与“四又先生”余友心的君子之交
尽管质疑声很多,但那次重返西藏的决定,韩书力得到的第一份支持,却来自于他的初中老师、后来在北京画店工作的余友心老师。余友心毫不犹豫地肯定了韩书力的想法,也促成了这对师生之后的西藏情缘。
1981年,韩书力在西藏搞研究生毕业创作时,他频频写信告诉自己昔日的老师余友心,西藏如何的好……“受我的感染,受我的诱惑,余友心先生42岁也第一次来到了西藏,他一来就被西藏的高天厚土、原生态、朴素的民风民情所感染、所折服。这样,1982年,余先生也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余友心的到来,让这对师徒的许多经历都相依相伴。由于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们一起下乡写生,一起探讨西藏美……直到如今。“原来他住在文联大院时,我们一天见一、两次面,后来他搬到东郊,我们见得少了,但很多美术方面的活动,我们都会一起参加、一同出席,所以还是能常见到。”
关于这位特殊的老师,韩书力做了个有趣的总结:“余友心先生与我的关系,又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同行又是同事,等于是‘四又先生”。
韩书力说五十多年的交往,自己的作品里已经有了余友心的影子,余友心的作品里也有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就是重叠到这种程度!我们的路径、过程是一样的,那么结果也是不会距离太远。他和我的缘分是从初中一直延续到大学又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这种很纯的友谊就叫君子之交。半个世纪的因缘啊!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还壮心不已。活的越发年轻了!”老师晚年活得如此之好,韩书力由衷的欢喜着。
从“小韩”到“韩爷爷”依然在春蚕吐丝
韩书力现在有了很多学生,他学生的孩子都管他叫爷爷。对此,他颇为感慨,“一开始,我在展览馆时,大家都叫我小韩,同事的孩子都叫我叔叔;来到文联同事的孩子开始叫我伯伯……我‘赖在文联,‘赖到这个年龄,现在那些同事的孩子只能管我叫爷爷了。”
韩书力说前不久出国时,自己和另一位叫尼玛次仁的同志在出访团里年纪最大,吃饭、住宾馆大家都很照顾他们,上车还有人搀扶着……“后来觉得我在西藏也没有这样老啊,怎们出门在外时时被人家提醒,你老了,你老了?我不管他们,我真的没感觉自己老,因为状态还不算老嘛。只是融入社会,就自动归位,被强迫老了!”说起这件事,韩书力觉得既可笑又无奈,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在西藏呆太久了,成了别人眼里的老同志。
由于社会名望负累,韩书力现在的时间并不能完全由个人做主。他戏说自己作为“一个画匠”,还有许多蚕丝要吐。“这些蚕丝不是完全为我挣钱、出名。因为我的创作也不是我私人的东西,是属于西藏的东西,国家的东西。所以,有的事情让我也很纠结,我的时间都是被安排的,像蛋糕一样被切割了……春、夏、秋,事儿尤其多。所以我常给别人说冬天是我的蜜月,因为那会我可以安心呆着做自己的事、画自己的画。”
卸下了文联主席一职三年,韩书力还是被文联以及美协不断委以各种任务。看得出,韩书力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人。
阴差阳错,教师节成了“韩老师”生日
“是我的这些老师,让我相信老师是一个令人羡慕而崇高的职业,因为他们确实是传承社会文明非常重要的担当。”果然,谈着自己的恩师,韩书力心情十分愉悦,感激之情也屡屡溢于言表,时间也无声流走。难得一个轻松的下午!
韩书力还讲到一件趣事:“我83。年调到文联时,当时管档案的人粗心大意,把我的出生日期弄成了9月10日,那会儿还没有教师节,没想到84年9月10日就成了教师节……虽然生日提前了两个月,我现在也认了,今天,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和学生的祝福。”说到这里,韩书力还特意从上衣口袋拿出身份证给我看,上面清楚地写着他的出生日期为:1948年9月10日。
在西藏的几十年间,由韩书力牵头,穿针引线。多次把西藏美术介绍到北京、上海、巴黎、柏林、纽约、多伦多、悉尼、里约热内卢……让西藏中青代画家在世界艺坛“骚动”起来,让雪域绘画变成了一池活水,他几十年的无怨无悔的付出更被吴作人先生比作“嫁给西藏的人”。
“我非常愿意看到他们的成绩里面有我的一份心血,看到他们的成绩比看到我多画一张画,多得一个奖,多挣一份钱还要由衷的高兴。这是真话!”被许许多多的人尊为“韩老师”的韩书力认真地说。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