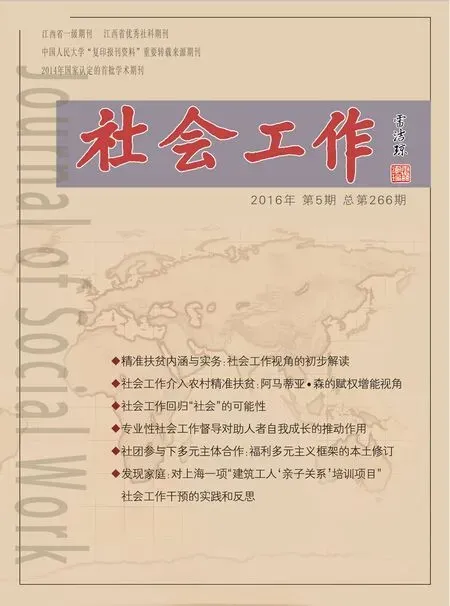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
2016-12-07郑广怀
郑广怀 向 羽
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
郑广怀 向 羽
“政府主导的购买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模式。从政府到民间、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几乎都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不能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基于对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历史进程的回顾,本文指出,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是社会工作转向“社会导向”的必要条件。本文呼吁大陆借鉴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在专业化的同时推动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
台湾社会工作 党政主导 社会导向 社会性
郑广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 430079);向羽,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社会学系,讲师(珠海 519085)。
导言
自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①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呈现全面发展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得益于国家层面对社会工作发展做出的整体规划和制度安排(王婴,2013)。例如,中组部、民政部等十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②2011年11月8日,中组部、民政部、财政部等18部委、社团联合会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参见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shgz/201111/20111100197275.shtml,同时倡导“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③2012年11月27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这是第一个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全国性制度安排。参见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211/20121100383464.shtml,并以此作为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手段。从各地的发展经验来看,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社会工作发展都有政府“强力主导”的特征,政府制度化地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已成为主要模式(王婴,2013;张和清、向羽,2013;曾伟玲、叶仕华,2014)。
对于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大陆社会工作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既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认为,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嵌入性发展”以及“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社会工作互构性演化”。王思斌(2011)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要嵌入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和管理中,推动自身发展,并预设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由边缘化向核心化、由浅层嵌入向深度嵌入、由依附性嵌入向自主性嵌的发展道路。类似的,史柏年(2013)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同于西方“自然生成”的路径,而是“政府强势建构”。简言之,大陆社会工作研究者的观点倾向于,在现实处境下,依靠政府或结合既有体制来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王思斌,2006;王思斌,2013;徐永祥,2000;李迎生,2008;史柏年,2006;史柏年,2013)。
在“社会工作的春天来了”一片欢呼声中,少数学者对社会工作依靠政府强力推动的“嵌入式发展”道路提出了质疑。朱健刚、陈安娜(2013)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和内部治理官僚化等问题,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失去影响力。郑广怀、王小姬(2014)的研究则发现,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嵌入”过程是被既有体制“同化”、“吸纳”的过程。社会工作不仅失去影响力,而且关键的是追求社会正义的使命被扭曲。因此,这些反思与社会工作发展所处的具体政治和社会条件密不可分。笔者并非反对“政府主导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也并非反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而疑虑的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侵蚀社会工作的本质①关于社会工作的本质,笔者认同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以下简称IFSW)的观点。IFSW在其网站(http://ifsw.org/)公布了2014年修订的社会工作的全球定义,该定义指出,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考虑到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于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正义的本质。Wakefield(1988)指出,每个专业都倾向于推动并实现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以促进人类福祉。专业的关键不在于技能和知识本身,而在于如何使用技能。他认为,社会工作的组织价值就是推动社会正义,推动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本质。,社会工作是否面临被塑造成专业化的“政府工作”?换言之,笔者主张,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不应以放弃其“社会性”②关于社会工作的“社会性”,Kam(2012)认为包括六个维度,即社会关注与意识、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优先、社会情境、社会建构、社会变迁和社会平等。我们认为,社会运动、社会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等都应属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范畴。为代价。笔者关注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和专业化是否构成中国大陆的独特经验,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政府主导对社会工作本质的扭曲和损害?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原来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专业化重新回归社会导向?这种回归需要具备怎样的社会基础和体制革新?
本文试图以台湾地区社会工作(以下简称“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为例来探讨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首先,将简要回顾台湾社会工作从“党政主导”到“社会导向”的发展历程。然后,我们将探讨促进台湾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最后,我们试图提出台湾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对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选择台湾地区为例探讨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并非强调台湾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已经达到较理想的状态。时至今日,台湾社会工作界内部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不足仍然多有批判。本文主要聚焦于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外部条件,有关台湾社工界内部对社会工作丧失“社会性”的批判涉及专业自主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需要另文讨论①例如,陶蕃瀛(2005)对国家机器对社会福利及社会工作服务的渗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社会工作专业处于“活命”和“使命”的两难处境之中。一方面,社会工作作为助人专业,希望在国家机器之外帮助别人,这是社会工作的使命;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自主力量不强,只好接受国家的控制,先让自己能够“活命”。类似的,王行(2013)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通过推动社会福利民营化,投入大量资源,采取项目委托、官办民营等方式,将原有政府执行的各项社会服务业务委托给民间机构执行,形成了民间社会工作的人力执行政府的社会政策,处理政府设定的社会问题的局面,导致民间社会福利机构被官僚体系的作业程序所规范,甚至沦为完成当局意志的工具。。
一、从“党政主导”到“社会导向”
1.社会工作产生——党政催生
如果说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由民间部门自下而上奋斗的结果,那么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可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政府建构过程。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地区一直处于“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ism regime)②按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将政治体制划分为极权体制、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威权体制是指统治者通过暴力手段取得政权后,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它有别于极权体制,有些民主成分,它又不同于民主体制,它是集权强制的(于建嵘,2008)。统治之下,台湾社会工作并非像英美等国通过民间部门自发性组织而形成,而是通过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和政府当局的精英决策而形成,随之全面性地展开(郑怡世,2006:101)。林万亿(2002)认为,台湾社会工作的一大源头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发展出来的社会工作,它由来华的美国社会工作者所传播的理念而形成,以社会救济和民众组织训练为主。台湾光复,特别是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考虑到台湾的状况并结合自身的统治需要,国民政府建构起一套社会工作制度。
2.目的与内容——为党政服务
(一)“党政主导”下的台湾社会工作
“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处于“党政主导”阶段。林万亿(2002)认为1945年至1970年的台湾社会工作处于“党国社会工作”阶段,“社会事业党政化”,社会工作不过是“党政工作的传续”。此时,台湾社会工作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二战”后台湾社会工作的目的与工作内容与台湾地区的政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当时台湾地区的政治因素,日本殖民时代留下的社会事业被视为“社会遗毒”(王卓圣,2004)。据台湾省社会处科长徐正一(1948)记录,国民政府在1945年接管台湾后,认为日据时代所办理的“保邻馆”③日本在占据台湾期间,引入了现代社会事业,推行感化教育,“保邻馆”就是用来帮扶贫苦、教化穷人的机构和场所。一类的社会事业是散播毒素的地方,必须矫正(转引自,林万亿,2002:11)。因此,当时的台湾社会工作专业被国民政府视为铲除殖民地遗毒、宣扬“三民主义”的工具(王卓圣,2004;林万亿,2002:11)。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社会工作更被夸张当作“革命工作”(杜章甫,1952:8)。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迁往台湾,但国民政府仍然视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叛乱团体,将当局政治定位为“动乱戡乱”的内战持续状态。当局一再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要“反攻大陆”。在“以党治国”的理念之下,社会工作自然受到这种特殊政治环境的形塑,其专业目标被定位于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前述的神圣任务(许君武,1952)。因而,“党国社会工作”是促使“国家统治”合法化的工具(王卓圣,2004)。换言之,当时台湾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协助当局控制、改造社会,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社会工作的实质就是“社会控制”工作。
就社会工作的内容而言,“二战”以后台湾当局所认识的社会工作其实就是行政工作,即以中国传统的德政观为基础,以巩固政权、安定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服务,通过官僚化的组织,如社会司、社会处、社会局来贯彻执行社会服务(郑怡世,2006:254)。尽管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工作的内容上也体现出某些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特征,但主要服务于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的目标。
3.专业地位的建立——体制内主导
在“党政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阶段,社会工作专业地位的建立,不是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如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制度、社会工作职业制度或社会工作考评等级等制度的建立来获得,而是通过政府体制内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来获得的①台湾社会工作界呼吁“纳编”,原因当然不仅仅只是获得专业认可或是专业地位的需要,也有纳入编制内的社会工作者薪资保障相对较高、较稳定的缘故。。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启动源于“政府约聘社会工作员实验”(林万亿,2002:17)。换言之,社会工作专业地位的建立以政府体制内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为主导,社会工作成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表1)。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各级政府为建构体制内社会工作制度制定了大量政策措施,基本做法就是在政府系统内设置社会工作岗位,聘用社会工作人员从事福利服务工作。詹火生(2007)认为,在威权时代,社会工作既是政府“社会控制”的工具,也是政府“解决贫穷”的手段。社会工作专业几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及可能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依附于现有体制,并由其一手打造。

表1 台湾地区体制内社会工作制度的发展历程

1976年在社会救助类第五项“建立社会工作员制度改进办法”中,提出制定有关法令确认社会工作员资格并纳入编制。1976年预计从1980年起,5年内每年选用社区社会工作员40人,5年内共计200人。1977年选择台北县、台中县、云林县、高雄市为实验示范县市。1979年增加桃园县、新竹县、基隆市、台南市等县市加入实验计划。1979年在30个山地(原住民)乡设置社会工作员54人。1979年1979年“内政部”颁布《当前社会福利服务与社会救助业务改进方案》《“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社会工作员设置运用计划》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设置社会工作员实验计划》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设置社会工作员实验计划纲要》颁布《“台湾省”加速改善偏远地区居民生活设置山地社会工作员实验计划》颁布“台湾省政府社会处”《“台湾省”社会工作员制度计划》颁布1979年“台北市政府”1980年1980年《“台北市社区发展推进办法”》颁布“行政院”颁布《“中华民国台湾经济建设十年计划”》1980年“内政部”设置社会工作室,负责全省社会工作员制度的拟定,以及社会工作员甄选训练、行政督导考核等工作。社工员制度推广至宜兰县、彰化县、嘉义县及台南县,全省推广社会工作员制度的县市已达17个。甄选社会工作员40人。其中14人成立团体工作组,从事人民团体辅导工作及劳工福利服务;26人以两人一组的方式,至台北比较偏远的13个社区从事服务工作。任用社会工作员投入社区发展工作。在社会福利部分的计划中,第四项第二条规定: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协助国民解决问题。拟定社会福利中长期计划,计划逐步建立社会工作员专业制度,促使社会工作专业化。1980年“台北市政府”晋用社会工作员40人,其中36人加入社区工作。1981年国民党通过“贯彻复兴基地民生主义社会经济建设”案1982年“台北市政府”1981年1983年在社会建设措施中的第四项“扩大社会保险,强化社会福利”中,有“健全社会工作员制度”的相关论述。将社会工作员集中于社会福利中心办公,同时将“社区社工员”更名为“社会工作员”,统筹社会局社会工作室督导考核,工作重点在于扩展个案服务。1984年正式接受委托,并于1988年将“儿童保护服务”列为各地“家扶”中心必办项目。自此,儿童保护工作成为台湾社会工作重要的部分。社区理事会置总干事一人,必须使用社会工作员,辅助社区推动各项业务。1983年1984年全省除澎湖县之外,所有市县都设置了社会工作员。1986年《“台湾省政府”委托“家扶”中心试办“儿童寄养服务”方案》“行政院”颁布《社区发展工作纲要》“内政部”研拟《建立社会工作员制度实施方案》“台湾省政府”“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社区发展后续发展第二期五年计划”

(资料来源:根据郑怡世(2006)、林万亿(2001)及邱汝娜、李明德(2005)相关文章内容整理而成。)
(二)“社会导向”下的台湾社会工作
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从政治威权到社会民主”,政策决策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过程(詹火生,2007)。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逐步兴起,关注新兴社会议题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1980)、原住民权益促进会(1984)、劳工运动支援会(1984)、农民权益促进会(1987)、妇女新知基金会(1987)及残障联盟(1989),开启了多元福利发展的机会之窗(林万亿、沈诗涵,2008)。此时,社会立法从数量、规模以及修法频率都大大超越以往几十年的发展(参见表2)。这一时期,更新的社会工作议题开始出现,如早期疗育、老人虐待、性侵害、外籍新娘等。西方新兴的“多元文化”观点也被引入台湾地区社会工作界(林万亿,沈诗涵,2008)。高涨的社会福利运动、多元化的社会关怀团体加上多样化的社会议题与需求,推动台湾社会工作从“党政主导”下的“政治工作”逐步转向具有“社会性”的专业社会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工作呈现出“社会导向”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表2 1980至1990年代台湾主要的社会立法
1.社会工作回应广泛、多元的社会需求
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台湾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老人、身心障碍及儿童三个领域,而90年代以后则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并在社会立法进程充分体现。从立法、修法频率上来看,在80年代以前只有覆盖老人、身心障碍及儿童的3部法律,90年代社会立法数量大为增加,福利涵盖范围、领域扩大,同时修法的频率也大为增加。从服务人群来看,社会工作服务开始扩展到老年农民、原住民、家庭暴力、特殊境遇妇女、性侵害者、外籍新娘、外籍劳工等群体。从服务内容来看,社会工作服务从最初的贫困救济扩展至社会福利、社区发展、志愿服务甚至社会保险(详见表2)。
2.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工作服务
台湾社会工作“社会导向”的发展趋势还体现在不断壮大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上。这些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背景,充分体现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工作发展的特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救济服务多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仅存在少量跨国的、具有教会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如世界展望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从事社会服务的机构数量大增,机构背景日趋多元。这其中既有公立的服务机构,又有公设民营的机构,还有民间自主办理的机构。就机构背景来说,既有政府背景的,又有民间性质的。民间机构又可划分成宗教背景及非宗教背景的。宗教背景的社会工作机构,又有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佛教、道教等不同背景。例如。在中国大陆开展服务的慈济基金会就属于佛教背景。以老人长期照顾和赡养机构为例,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全台湾地区老人长期照顾及赡养机构计有1,064所,其中以免办财团法人登记,不对外募捐、不接受补助及不享受租税减免的小型民营老人机构最多,占86.00%,其他依次为财团法人机构110所、公立机构23所、公设民营16所①台湾“内政部”统计处:《“内政统计通报”——“100年底我国老人长期照顾及安养机构概况 ”》,http://statis.moi. 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
3.社会工作发展中社会资金大量涌现
目前,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来源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如政府补贴、资助的服务项目,既有临时性的资助方案,又有长期委托方案。第二类是接受民间捐赠,如企业、民众、教会、寺庙、道观、跨国组织捐赠等。第三类则是自我开发的收费性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机构对资金来源单一化的倾向一直保持相当的警惕。新竹某天主教背景的机构负责人就对笔者坦言,如果机构超过30%的资金来自政府,则机构的发展和运作就有可能失去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存在与台湾地区民间社会较为发达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多数的台湾社会工作机构都接受政府委托或外包的项目,但机构与政府之间保持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和价值追求并不受太多威胁。笔者比较熟悉的“财团法人台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新竹分事务所”(以下简称“家扶中心”)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接受政府委托的儿童保护服务项目,但委托资金只占机构服务资金来源的小部分。机构负责人坦言,是否要与政府合作下去,是否要继续承接委托项目,主要取决于机构自身对合作项目的评估,看其是否符合机构价值理念,而不在于政府是否出钱或出多少钱。由此可见,强调机构资金来源多元化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并非让政府“撒手不管”或“袖手旁观”,而是要政府在承担责任(如经费投入)的同时必须“让渡空间”,让社会力量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4.社会工作发展中广泛的社会参与
“社会导向”下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参与的主体既包括体制内的社会工作者,也包括体制外(民间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更包括其他的社会群体。在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机构往往都会吸纳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工作服务,多数机构都有自己的义工组织,参与义工组织的人群是多样化的,有公务员、大学教授、私企老板、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大学生、中学生、家庭主妇等,他们组成专门的义工队服务特定人群。台湾清华大学(新竹)的学生就组成专门的送餐义工队,为附近社区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新竹“家扶”每年暑期针对小学生的营队活动几乎都是由大学里的学生社团配合完成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工作发展还表现为各种自主的社会行动。台湾社会工作迈向多元化的道路离不开不同社群的参与,他们在争取自身福利保障的过程中,无论是街头抗议还是立法游说,都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凝聚了社会共识。他们使用记者会、公听会及座谈会等“和平诉求”的行动策略,吸引公众的注意,进而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林国明、萧新煌,2001:14)。
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湾社会工作发展处于“党政主导”之下,80年代以后则呈现出“社会导向”的态势,两个阶段在主导者、服务目的、服务人群、服务内容、资金来源、与政府的关系及专业自主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详见表3)。

表3 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党政主导”阶段和“社会导向”阶段对比
二、从“党政主导”到“社会导向”何以可能
(一)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为转向“社会导向”创造条件
1980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威权体制”逐步松动,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对台湾社会福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直接为不同的弱势群体争取社会福利的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和合法性基础。社会福利运动的发展直接带动了社会工作转向“社会导向”。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二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
1.政治体制变革开辟社会空间
萧新煌、孙志慧(2001)认为,台湾政治体系的变革创造了新的机会,进而影响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发展。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通过“解除戒严令”及“开放党禁”两项新议题。1987年时任“总统”的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正式开放党禁报禁。1988年,台湾当局制定了“《国家安全法》”,同时修订“《非常时期人民社团法》”,从法理上恢复民众自由结社权,民众可以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人民团体法》”和“《集会游行法》”的立法,开放了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渠道,降低了政府的压制能力和倾向,进而促进社会福利运动的形成(萧新煌、孙志慧,2001)。换言之,逐步开放的政治氛围促进了民众争取自身福利的“街头抗争”运动。
省级政府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现行法律对省级政府的立法权限没有明确列举式的限制,但省级政府的立法权是有边界的,确定其边界的向度是在立足其自身行政管理职责的前提下,需要从纵横维度去认识和处理省级政府与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及其关系,尽量避免越权、重复、冲突和失职,以确保省级政府立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社会开始由“硬性威权体制”开始向“软性威权体制”转变,即国家机关对民间社会的支配性角色以及对政治经济资源的主导性角色已经较蒋介石时代松动(郑怡世,2006:194)。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多党竞争体制形成,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选举政治在推动福利多元化和不同弱势群体福利改善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萧新煌、孙志慧(2001)认为,选举政治的日趋重要,使得推动福利议题的社会团体,借由选举的过程,和政党及个别政治精英有了新的机会建立联盟关系,推动社会福利的改善。
1992年,台湾“国会”全面改选,终结了“万年国会”,“立法委员”、“民意代表”开始真正为普通民众的利益代言。台湾地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局面,逐步向着“一党主导、多党制衡”的方向演进(孙俐俐,2009)。伴随着多党竞争局面的出现,各个政党为了取信于选民,纷纷提出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施政纲领,其中就包括社会福利政见。1991年的社会权倡议、1992年的福利国辩论以及老年年金提议,都显示出社会福利政见已经成为各党派竞相提出的主张(林万亿,2001)。从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福利政见不仅可以作为执政当局用以继续执政取得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同时它也是反对党全力争取选举支持的有力武器(古允文,2000)。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民进党与时任“行政院长”郝伯村就“福利国家”和“老人年金”等议题进行辩论,民进党“立法委员”苏焕智等提出“国民年金”草案,促使国民党政府回应人民需求(王卓圣,2004)。同时,“国会”的全面改选使得“立法院”的政治角色发生转变,不但影响制度化政治结构的开放程度及社会团体与政治精英结盟的方式,更促进了社会福利运动从街头抗争向“立法院”游说转变。可以说,政治氛围的改变为多样化福利需求的表达提供了条件,也为社会工作向“社会导向”转变提供了制度空间。
2.当局变革社会政策
政治氛围的改变使得原有“党国”体制为巩固统治基础,在施政中不得不重视民众需求,进而出台或是改变一系列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政策,这实质上推动了社会工作向“社会导向”的发展。黄煌雄、赵昌平、吕溪木(2002)认为“社会福利三法的通过系70年代末期中坜①1977年底在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中,执政党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中做票,引发民众愤怒,上千群众包围中坜市警察局,烧毁了警察局。、美丽岛②《美丽岛》本来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一本批判性政论杂志,其领袖多为“党外”政治精英,他们以“社务委员”的方式联络各地精英,试图组织“政党”。这在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是大忌。1979年该杂志在高雄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活动,引发群众与军警冲突,后被查封,共计37名党外政治精英被捕。后此事被称为“美丽岛事件”。等重大政治事件造成台湾社会的震撼,当局为消弭与转移社会抗争的结果”。林国明、萧新煌(2001)在总结台湾社会福利运动的成果时认为,某些为特定目标群体带来新利益的政策变迁并非抗争性的社会福利运动所造成,而是外源因素与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老人福利法”的修正过程就有行政官僚的主动性影响。
(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造就“社会性”回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威权体制的松动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加快并非偶然,也不是当政者一时良心发现,而是社会不断参与的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起,台湾社会开始浮现一些政治革新力量,这些力量逐步展开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③“党外”一词主要针对当时国民党“一党执政”而言,它是非国民党籍的政治人物参加政治选举时共同的标志。,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以及现有政治体制的变革。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地区也存在一定数量的社会服务组织,但均是一些教会背景的国际组织,如“家扶中心”、世界展望会等。80年代以来,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争取社会福利的过程中,不断成立与之相关的社会福利组织。在这些社会福利组织中,有些是福利抗争运动的组织主导者,有些则在抗争过程中走向联合,有些则是以保护抗争结果的形式出现。例如,残障者福利运动,早期分为智障者家长运动、残障者福利运动以及植物人安养三个分支,他们在推动残障者福利改善以及残障福利法修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联合,进而成立了“残障联盟”。组成联盟并持续发展的好处在于,残障福利运动并没有因为制度化或是既有诉求的达成而逐渐消失,反而持续成长并发掘新的议题和诉求。再如,台湾地区的妇女运动最初是以争取福利权益为组织目标的,在政策立法完成之后就有意识地转向草根服务,“是希望借此将政策的诉求目标具体地落实在生活世界,透过地方组织网络的发展,厚植基层改造的力量”(林国明、萧新煌,2001:14)。
需要特别指出是,此时为不同弱势群体争取社会福利的“街头抗争”运动,并没有因为运动结束而消亡,多数的社会抗争团体转型成为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于是,以民间力量为依托的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机构涌现出来,直接造就了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机构今天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促成了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
四、对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社会性”回归
考察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有两种力量始终贯穿其中。一种是“自下而上”来自社会的抗争力量,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动革新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福利运动、社会福利政策立法及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建立彰显了“自上而下”的力量的强大。同时,台湾地区社会福利的发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制度化,也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动革新。这既包括在政治层面“解除戒严”、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及形成稳定的“多党竞争格局”,也包括在社会层面颁布“公益劝募条例”、“志愿服务法”等法律释放民间力量。正如林国明、萧新煌(2001)所指出的,某些社会福利的改善既有社会参与的结果,也有选举效应与政党竞争逻辑的影响,更有行政官僚的主动性。
大陆社会工作要迈向“社会导向”,进而回归“社会性”,“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相结合也许是可行的道路。首先,政府要“自上而下”地推动变革,努力创造民主、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建立社会工作“社会性”回归的政治基础。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在释放社会力量、推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发文,试图突破原有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双重管理”体制①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粤发〔2011〕17号)明确提出要“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办法,探索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工商经济类等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制,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和资源参与社会建设”。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粤发〔2012〕7号)指出,“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2012年7月1日起,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均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应该自信的是,这样的主动改革不再局限于广东一地,而是可以上升到更高层面。最近,社会各界围绕新通过的《慈善法》的争议,也反映出既有立法思路与社会组织期待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的消弭,显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动变革。
其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不可或缺。“自下而上”的参与是要促使民众充分利用法律或其他社会认可的途径,和平理性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凝聚促进政府变革的社会共识。就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现状而言,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供给和弱势群体的服务需求构成了“杯水车薪”的巨大反差,社会工作服务不仅覆盖面不够,亦不能满足服务使用者的首要需求。例如,对于广大的进城农民工子弟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平等的入学机会和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而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多是“四点半”学堂等课外辅导。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社会工作者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服务使用者、专业社团、政治人物和其他专业群体(如律师、记者)建立联盟关系,设定新的社会议程(Dominelli,1999),以促进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影响政府决策。
(二)研究者和实践者合力推动“社会性”回归
在台湾社会工作迈向“社会导向”发展的道路上,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既包括大学里的社会工作专家,也包括机构中的草根领袖。虽然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为社会政策决策的公共参与提供了可能性,但决策结构对公众而言仍然相对封闭(林国明,2001)。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学者往往就扮演起不同群体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比如,20世纪80年代为不同弱势群体争取社会福利、发动抗争运动的领袖,大多是来自大学的学者,他们通过研究提出新的社会论述,奠定了社会工作“社会性”回归的理论基础,也正是他们敢于担当,四处奔走,与民众并肩战斗,台湾社会工作才有今日之局面。
笔者认为,掌握着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话语权的学者需要知晓自身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朝向何方、政府与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都可能与其论述密切相关。在党政主导社会工作发展的情况下,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可能扭曲社会工作使命之时,社会工作研究者应当时刻反思行业现状,不能将眼光局限于某条单一发展路径之上,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批判和学术研究,为社会工作发展开辟多样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实践者不仅要将自己视为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士,更要将自己视为推动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正如Singh&Cowden(2009)所指出,尽管社会工作实践者直接或间接地被国家雇佣,但同时也可以运用知识在实践和政治之间建立起持续而动态的联结,在服务使用者、学界和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盟。社会工作者还应具备开放、多元和批判的心智,勇于开拓社会工作服务的新领域,探索社会工作“社会性”回归的发展路径。
五、余论
Abramovitz(1998)指出,行动主义(activism)是社会工作历史发展中的优良传统,社会工作具备满足个人需求和参与社会变迁的可能性①例如,20世纪早期的睦邻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就旨在推动社会变迁,认为贫困源于穷人无法控制的不利的社会条件,主张通过社区服务和组织动员来消除社会苦难(Abramovitz,1998)。,但专业化限制了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变迁的努力。Olson(2007)进一步指出,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社会正义和专业化两大事业,社会正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工作者改变不公正的社会条件,减少不平等。专业化则要求社会工作与其他专业竞争,以获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合法性及赢得尊重。尽管社会正义被宣称为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但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对专业化追求超越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社会正义沦为了专业化的修辞和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目前遭遇的专业化对“社会性”的侵蚀并非独特现象,而是贯穿全球社会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聚焦于本土智慧,还需要放眼全球性挑战,从而为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做出贡献。
[1]蔡明砡,2005,《我国社会立法历程》,《社区发展季刊》第109期。
[2]杜章甫,1952,《反攻大陆后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月刊)》第1期。
[3]古允文,2000,《龙之跃—中港台三地社会发展比较》,台北:人文科学出版社。
[4]黄煌雄、赵昌平、吕木溪,2002,《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总体检调报告》,“台湾检察院”。
[5]李迎生,2008,《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策略》,《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6]林万亿,2002,《台湾社会工作之历史发展》,吕宝静主编,《社会工作与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
[7]林万亿,2001,《社会抗争、政治权力资源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1980年代以来的台湾经验》,萧新煌、林国明主编《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图书。
[8]林万亿、沈诗涵,2008,《19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学术的发展》,《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第12卷,第1期。
[9]林万亿,2005,《1990年以来台湾社会福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社区发展季刊》109期。
[10]林国明、萧新煌,2001,《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导论》,萧新煌、林国明主编,《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图书。
[11]林国明,2001,《民主化与社会政策的公共参与:全民健保的政策形成》,萧新煌、林国明主编,《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图书。
[12]彭淑华,2001,《台湾社会福利法制分析》,詹火生,古允文主编《社会福利政策的新思维—社会福利篇》,台北:桂冠图书。
[13]邱汝娜、李明德,2005,《政府社会工作员制度的起初:参与者的回顾》,《社区发展季刊》第109期。
[14]史柏年,2013,《教师领办服务机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理想选择》,《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
[15]史柏年,2006,《体制因素与专业认同——兼谈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策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4期。
[16]孙俐俐,2009,《台湾地区政党体制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17]陶蕃瀛,2005,《走在国家体制与公民自主的钢索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9期。
[18]王卓圣,2004,《台湾与香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比较分析》,《台大社工学刊》第9期。
[19]王国庆,2005,《我国老人福利政策的历史制度论分析》,《社区发展季刊》第109期。
[20]王婴,201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2]王思斌,2006,《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
[23]王思斌,2011,《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24]王思斌,2013,《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河北学刊》第33卷第6期。
[25]王行,2013,《走调的音符:台湾少数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发声、行动与期盼》,《台湾社会研究》第91期。
[26]萧新煌、孙志慧,2001,《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福利运动的发展:演变与传承》,林国明、萧新煌主编,《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台北:巨流图书。
[27]徐永祥,2000,《试论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第4期.
[28]许君武,1952,《社会工作的时代任务》,《社会工作(月刊)》第1期。
[29]于建嵘,2008,《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与出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4期。
[30]曾伟玲、叶仕华,2014,《深圳社会工作发展报告》,罗观翠主编,《广东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2]詹火生,2007,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经验与展望,《社区发展季刊》120期。
[33]张和清、向羽,2013,《广东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及其经验反思》,王杰秀、邹开文主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4]郑广怀、王小姬,2014,《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博弈——以A市工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李昺伟主编,《专业的良心——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守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5]郑怡世,2006,《台湾战后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分析——1949—1982》年,暨南国际大学博士论文
[36]朱健刚、陈安娜,2013,《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37]Abramovitz,M.(1998)Social Work and Social Reform:An Arena of Struggle.Social Work,43(6),512-526.
[38]Dominelli,L.(1999)Neo-liberalism,social exclusion and welfare clients in a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8,14-22.
[39]Kam,P.K.(2012)Back to the'social'of social work: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October 5,1-25.
[40]Olson,J.J.(2007)Social Work’s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Justice Projects:Discourses in Conflict.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18(1),45-69.
[41]Singh,G.&S.Cowden(2009)The social worker as intellectual.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12(4),479-493.
[42]Wakefield,J.C.(1988)Psychotherapy,Distributive Justice,and Social Work:Part 1:Distributive Justice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ocial Work.Social Service Review,62(2),187-210.
编辑/程激清
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户籍限制放开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研究”(编号:13JZD018)。
C916
A
1672-4828(2016)05-0030-13
10.3969/j.issn.1672-4828.2016.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