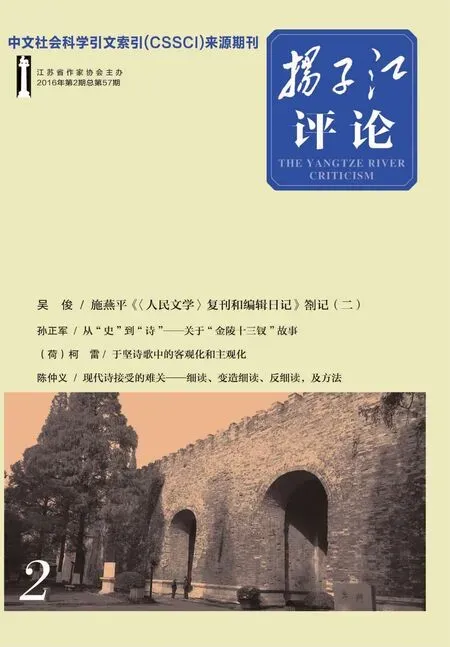于坚诗歌中的客观化和主观化
2016-12-07柯雷MaghielvanCrevel
(荷)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于坚诗歌中的客观化和主观化
(荷)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自80年代初以来,“口语化”诗潮向先锋诗歌之至尊朦胧诗发起挑战,于坚①是其中的两大诗人之一,另一个是韩东。与“口语诗”相关的作品最初载于《他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于坚、韩东和其他几位诗人被命名为“口语诗人”。但“口语”只是他们艺术的一个方面,这种命名难免有简单化之嫌。另外,评论界已经注意到,于坚的诗主要关注“普通人”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具体而琐碎;在表达方式上,有时严肃,有时片面,也有时幽默风趣。陈仲义把于坚写作的这个特征称为“日常主义”。②再者,就是于坚曾公开声称要“拒绝隐喻”,他的大致意图是,在诗歌表达中,所见即所得。以其《事件·写作》(1989/1994)为例,秃鹰就是秃鹰,不是一个衍生自陈腐的文化符号的、为权力歌功颂德的象征。总之,在先锋诗歌内部,于坚堪称本书称之为“世俗”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甚至是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并不是所有的评论者都把于坚在语言上“拒绝隐喻”看做一个既定事实,或是由诗人决定的东西。然而,他们至少同意,于坚在诗歌中对语言作为诗歌的物性、具象介质,以及语言与存在、现实之关系,进行了创造性反思,在这方面,他比大多数同代人都走得更远。有一些批评家从中国传统诗学出发,指出于坚没有遵循“抒情言志”或“文以载道”的常规;相反,他对物质世界冷静的观察与审视,使人类体验陌生化了,从而在写作中建立了客观性或客观再现。如果理想化地看待这一点,可以说,于坚的写作体现了为世界“更名”的能力,或者,据他本人的说法,是对世界“重新命名”。
以上关于于坚诗歌的讨论,都很切中肯綮。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于坚写作中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但不是“客观性”和“客观再现”。我认为,“客观化”是于坚作品特色中的核心机制。这里所说的“客观化”并不是指对“他者”主体性的否定,比如把女性贬低为男性注视下的欲望客体。于坚诗歌中的“客观化”,是摆脱了社会因袭的、常规和习惯性的见解与阐释后,对人类经验的再现。“客观化”是一个过程,一种对客观性的追求,而不是“客观”的实现;后者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文艺语境下。在作为“人造之物”(made thing)的诗歌中,只有在我们认识到“客观化”是“人为”的,其实是诗人操纵及干预的结果,因此,归根结底说来,“客观化”是诗人的“主观性”表达,然后,“客观化”这个概念才能派上用场。基于这些限定条件,“客观化”提供了一个进入于坚诗作的有益视角。当然,“客观化”机制绝非于坚诗歌所独有,但他对“客观化”的独特运用方式,值得审视。
这里,尤其要说的是,作为于坚诗作中一个全局性的动力的“客观化”,在个体的作品和诗句中常常与我称之为“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的概念互动。也就是说,于坚对事物的想象性的、拟人化的关注,使得事物自身成为主体。西敏(Simon Patton)曾精心挑选了两个例子——于坚笔下的“雨点”与“瓶盖”——来分析这个问题。③“主观化”与“客观化”这两个互动的概念,对主客之分及其层级关系有所质疑。在此,我虽然不就此多谈,但这个论断值得注意,因为这与下文还要讲到的于坚解构崇高与低俗之等级关系的做法有所关联。
为了将成熟期的于坚和早年的于坚相对比,且让我们先看一首他写于1981年的无题诗。④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于坚在出道时是这样写诗的:
1
冬天
太阳的肉
冻得通红
2
剥掉黄皮的月亮
白幽灵
吊在树林间
3
这里有一片蓝天
风去向乌云告密
4
患癌症的世纪
法律禁止行医
……
熟悉《今天》杂志上的朦胧诗的人们,应该会由此想到芒克的《天空》(1973)、北岛的《太阳城札记》(1979?)等那些著名的诗篇。跟那两首诗一样,于坚这首诗包含一系列被编号的诗节或小诗。除了这个特殊的形式,这首诗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早期朦胧诗的影响:依托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该诗语言蕴含明确的隐喻指向;“癌症”及“法律禁止行医”等意象,是从病理学的角度暗示20世纪中国经历的动乱和苦难。于坚最初向朦胧诗学习的另一例是他的《不要相信……》(1979), 这让人想起北岛早期著名的诗句(我—不—相—信!)及其意象;类似的意象在于坚诗句中也可见到:
不要相信那颗星星
说它是爱的眼睛
以及:
不要相信我结实的手掌
说它会把稳爱的小船
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出现在《罗家生》(1982)一诗中。这首诗可算是于坚之独创性的开端。尽管诗歌直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但风格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已相去甚远:
罗家生⑤
他天天骑一辆旧“来铃”
在烟囱冒烟的时候
来上班
驶过办公楼
驶过锻工车间
驶过仓库的围墙
走进那间木板搭成的小屋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看到他 就说
罗家生来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谁也不问他是谁
全厂都叫他罗家生
工人常常去敲他的小屋
找他修手表 修电表
找他修收音机
“文化大革命”
他被赶出厂
在他的箱子里
搜出一条领带
他再来上班的时候
还是骑那辆“来铃”
罗家生
悄悄地结了婚
一个人也没有请
四十二岁
当了父亲
就在这一年
他死了
电炉把他的头
炸开了一大条口
真可怕
埋他的那天
他老婆没有来
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
他们说 他个头小
抬着不重
从前他修的表
比新的还好
烟囱冒烟了
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
罗家生
没有来上班
根据各方面的说法,《罗家生》是于坚的成名作,至今依然是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80年代初期,读者们刚刚见识到充满隐喻、有时隐喻过多的朦胧诗,以及对中国历史和神话有高深指涉的寻根派。在他们看来,《罗家生》开启了新的诗歌写作方向,这一点,与韩东《有关大雁塔》很相似。这两首诗,关注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诗行短,口语化,语言简约,追求不经意间的震撼效果。在《有关大雁塔》中,有人爬上大雁塔,不是尽情赏景后再下楼,而是爬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骄傲之象征的大雁塔顶跳下自杀;在《罗家生》中,罗家生是死于毫无意义的工作事故。
《罗家生》体现了于坚对低调风格的熟练运用,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另辟蹊径。例如,该诗的最后两行平淡、不经意的语气(“罗家生 / 没有来上班”)使其鲜明有力。这首诗在总体构思上同样有典型的于坚特色。诗人以超然淡漠的语调,把令人感动的葬礼场景和貌似罗家生工友的个人记忆结合起来:“从前他修的表 / 比新的还好。”客观化亦见于言说者对事物刻意的表面化的观察。这个特征在于坚的诗作中反复出现,是另一个与韩东诗作相似的地方。我用表面性这个概念,不是意味着一种后现代手法,而是意味着,通过屏蔽开传统的推理及联想机制,实现叙述或描写的陌生化。例如,言说者未曾言明领带与罗家生被逐出工厂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首先,这调动了读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背景知识,即领带当时可能被当作小资产阶级心态或追慕西方的标志;其次,这让事件“客观地”陌生化甚至荒诞化了;再次,这实际上恰恰暗示着某种作者假装自己没有的、强烈的道德判断。
虽然于坚诗作在风格上极其分明,但又很是多样;为了防止客观化这一概念限制了我们对此多样性的判断,这里,且让我们分析一个风格迥异的文本。《墙》(1983)也是于坚早期的作品,但与《罗家生》迥然不同:
墙⑥
没有季节的墙
即使在中午也照不到阳光的墙
没有人迹的墙
透射着各种暗影的墙
被探照灯突然脱光的墙
写着“此路不通”的墙
窗子死死关着的墙
无声的墙 震耳欲聋的墙
发生过一次凶杀的墙
吃掉了窗子的墙
教授写在墙上的墙
她眼睫毛下的墙
坐在你对面睡在你身边的墙
藏在短裤里的墙
文字组成的墙
眼球制造的墙 舌头后面的墙
笑着的墙 毫无表情的墙
荒原上的墙 大海中的墙
挂着日历的墙 属龙的墙
隔着父母的床的墙
死掉的墙 回忆中的墙 不朽的墙
每秒钟都在呱呱坠地的墙
沙发和壁毯伪装起来的墙
把视线躲朝任何一方
都无法逃避的墙
说不出来无法揭发指证的墙
描写上述这些墙的那一堵
捏着笔就像握着镐头的
墙
原文中每行都以“墙”字结尾,只是最后五行中“墙”这个名词前所带修饰语分别延伸了两、三行。因为汉英语法之别,所以英语译文中的wall(墙)是放在每行开头,连续重复的文本效果与原文类似。在前十行(直到“吃掉了窗子的墙”)中,“墙”似乎是室外墙,与诗最后三分之一部分的室内墙相对。第1—7行多少呈现了经验式的观察,与第5行及第8—10行中对个人感受的表达相伴相随,兼具感观性(“震耳欲聋”)和想象性,拟人性和隐喻性(“被突然脱光”“凶杀”“吃掉了窗子”)。第11—17行或第18行中,作为隐喻的“墙”表示无法介入,包括无法介入学术文体、身体语言及性。从写作技术上看,文本后三分之一的连贯性弱于前三分之二,因为后一部分吸引读者用字面和隐喻交替的方式来解读“墙”,而全诗最后走向包罗尽所有意象的抽象表达。
《墙》这个文本有两个方面体现出了于坚诗作的典型特征。第一,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审视单个词语(word)。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诗歌语言也具有指称功能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他重复审视的是单个事物(thing)。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相互隔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经验范畴结合在一起,或形成对比关系。如果说只能在二者中选择其一,那么,我认为,《墙》审视的是一个事物,而非一个词语。反之,在我看来,《对一只乌鸦的命名》(1990)是指称“乌鸦”这个词语而不是指称“乌鸦”这个事物。《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也是于坚一本诗集的名字。⑦第二,《墙》中流露出一种幽默感,这里否弃了朦胧诗的严肃性,在多个方面体现出当代诗人诗作的另一些特征,比如韩东,也比如在写作中使用粗莽语言的莽汉诗人李亚伟和万夏、非非诗人杨黎等。⑧幽默感在于坚后期作品中尤其突显。
于坚开始发表作品以后,能与《罗家生》的经典地位相提并论的唯一文本是《尚义街六号》(1985)。《尚义街六号》是于坚老家昆明的一个古老地名,是吴文光故居所在地。于坚在昆明生活了一辈子,对这座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吴文光是个重要人物,现居北京,在中国纪录片制作、戏剧及广义上的先锋文化界享有盛名。诗中,吴文光的家是一群哥们儿厮混的地方,以下是该诗第一段节选: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请读者见谅,该诗的英译本将“打开灯”译成了open the window(“打开窗”)。常规译法应为turn on the light,逐字译法应为open the light,但后者不通,英文里没有这种表达。因此,我用了另一个可open的物件来代替light。“打开”一词在不同语境中重复出现,这显示了于坚把玩日常语言用法的习惯。在此,诗人将无生命的器皿(烟盒、灯)与嘴巴放在一起,迅速、机械地逐一“打开”,这样做所产生的效果即是明显的主观化。“打开”嘴巴通常让人联想到语言,而语言是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之显著体现,这首诗轻视了嘴巴上述的正常含义又是一种客观化。以上段落中还有另外两个类似的使用重复手法的例子,它们也表达了作者对笔下人物类似的善意嘲讽。首先,我们读到李勃告诉其他人应当怎样做一些日常“琐事”,包括睡觉,这些本来应该人类无师自通、天生就会的事。接着,言说者列举了吴文光的“所有物”,从家用物品、排泄物到与他亲密程度不一的同伴。作者对常规分类进行了刻意表面化的重新排列,在这一例句中最为清晰:“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至于诗中提到的真实人名,包括于坚自己,读者或许想要把这些看做该诗之“真实性”的证据,就像谢有顺和其他一些批评家,是把这些细节看做历史文献或生活经验的记录。⑨也许这样的写法,会让读者想到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世界、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但《尚义街六号》与传统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读者通过这里所展现的生活经验,无法洞察作者的行为以及他在现实中的位置;而在传统文学文本中,这一点是无需置疑的。⑩这首诗只是于坚写下的多首提及真实人名的诗作之一,并且这些被提及的人物还常常是文坛活跃分子。比如,《有朋自远方来》(1985),诗名取自孔子《论语》的开篇,描述的是“他们”诗人韩东和丁当,这两个人作为“真实人物”在文本中出现,并没有为这首诗增加什么额外的意义。在《尚义街六号》中,真实人名的功能是引发读者去关注艺术家成名的过程,以及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其公共形象与个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对立等问题: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来到街上
空荡荡的大厕所
他第一回独自使用
也许《尚义街六号》叙事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我们核查诗歌“确有其事”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作者令人信服的、以冷嘲热讽的方式叙述出来的场景:这首诗把普通人、哥们儿情谊描绘成一种有可能发生、诗人有可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诗歌经验。即便如此,诗中出现的个人经验,还是在不经意间与可考证的文坛公共生活史扯上了关系。在“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这样的诗行中,意味着“晦涩”“悲情”“模糊”的“朦胧”一词,也是形容朦胧诗人的词语,而《尚义街六号》写作之际,正是于坚与志同道合的写作者们忙于摆脱“朦胧诗人”的时期。同样,于坚本人(当时他的笔名是大卫)、吴文光、费嘉、李勃、朱小羊等主人公全都是昆明非官方刊物《高原诗辑》(1982—1983)的撰稿人。顺带要说的是,《高原诗辑》第四期刊载了吴文光写于1983年的《高原诗人》一诗,这首诗很可能是于坚创作《尚义街六号》的直接灵感源泉。⑪
这首诗里还提及更多的文学史事实,大多是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呈现出来。李勃掌握的内幕故事使他成了“百事通”,随后我们读到: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怀旧是这首诗的主要情绪:
那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同伴们分道扬镳了,那些欢乐时光随之结束,诗歌也戛然而止:
吴文光 你走了
今晚我去哪里混饭
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旧唱片 再也不响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真实的”、历史的尚义街六号或许没有成为文化地标,但《尚义街六号》一诗却已如此。
于坚还有一些诗作,其标题由“事件”和随后对事件的描述组成,除了其中一首,其他都是在1989—2002年间写成,如《事件:停电》(1991)和《事件:呼噜》(2000)。这些都被收入《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和《于坚的诗》两部诗集中,单列为“事件”部分。于坚的个人选集中一共收录了17首类似标题的诗。就像对他评论性的文字一样,于坚对自己的诗作曾有一些改写。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的《三乘客》一诗(1982)在《于坚的诗》中更名为《事件:三乘客》;他的非官方出版的诗集之一里的《经历之五·寻找荒原》(1989)在《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于坚的诗》和《于坚集》里则更名为《事件:寻找荒原》。⑫在1993年《对一只乌鸦的命名》问世以后,于坚好像把“事件”这样的系列命名方式当做自己一个标新立异的文本类别延续下去。早些时候,他也曾用“作品”系列命名自己写于1983-1987年间的数十首诗作,如《作品1号》《作品108号》,且这个系列不是严格按照数字顺序排列的。这样的系列化命名方式促进了其作品内部的客观化机制。以“作品”系列为例,除了冷硬的编号之外,并没有其他命名;“事件”系列则表明了诗人是把诗歌当作纪录或报道手段的构想。这样的命名方式,使得诗歌摆脱了浪漫灵感和高雅艺术概念之类的东西,诗歌写作被呈现为各种用相似的路数进行产出的活动之一,就像官僚机构的运转会产出就事论事的、符合特定格式的纪实报告一样。除了诗歌标题,客观化及主观化还贯穿在多首“事件”诗中,相关例子随处可见。
这里我们首先考察,在这些诗作中,文本在想象性地关注这些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客体时,所怀有的主观化冲动。《事件:停电》一诗细致地描写了停电时人们在家里熟门熟路地摸黑走动的情形。在《事件:棕榈之死》(1995)中,言说者对棕榈树详尽无遗的描述,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赋”体。人类对棕榈树缺乏敬意,策划在棕榈树站立之处兴建大型购物中心,导致了树的死亡。另外还有几个顾名思义的标题,如《事件:围墙附近的三个网球》(1996)、《事件:翘起的地板》(1999)。反之,在“事件”系列诗作的语境中,于坚把“诞生”“结婚”等平时算是人类生存及感情生活中的大事与烧坏的保险丝、砍倒在路边的大树、丢失的网球、有瑕疵的木工活儿同等对待,比如,同时被收入诗集《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和《于坚的诗》中的《事件:诞生》(1992)及《事件:结婚》(1999)。因此,于坚在“事件”系列诗作中重新组合了不同的经验领域,正如他在其他作品中也做的那样,这个手法甚至体现在《尚义街六号》的单行诗句中。⑬
诗歌标题方面的另一例子是《事件:写作》。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性再现活动,当然比打呼噜之类的“事件”更有价值,特别是在诗集这样的文本语境中。在《事件:写作》这首诗的主体部分,于坚通过关注具体的语言工具(墨、笔、纸)以及文学与语言学的术语(隐喻、主语、状语),着力将(书面)语言的使用进行客观化处理。然而,与其他“事件”诗相比,看上去夸张、浮华的段落削弱了其客观化效果。哪怕是以于坚的标准来衡量,这些诗行也过长。⑭因此从此处开始,引文中用的字体要小些,偶尔会采用缩排换行的方式。
写作 这是一个时代最辉煌的事件 词的死亡与复活 坦途或陷阱
伟大的细节 在于一个词从遮蔽中出来 原形毕露抵达了命中注定的方格
在《事件:写作》中,于坚对自身诗艺的反思强烈而执著,这反而妨碍了其诗歌天分的发挥。抽象化、概念化及阐释,让此诗不堪重负,因此未曾像其他“事件”诗那样出色而传神。可以说,《事件:写作》是理论而非实践,是诗学而非诗歌。
“事件”系列的写作方式在《事件:铺路》(1990)一诗中尤显效果,因为这首诗是在展示而非讲述:
事件:铺路⑮
从铺好的马路上走过来 工人们推着工具车
大锤拖在地上走 铲子和丁字镐晃动在头上
所有的道路都已铺好 进入城市
这里是最后一截坏路 好地毯上的一条裂缝
威胁着脚 使散步和舒适这些动作感到担心
一切都要铺平 包括路以及它所派生的跌打
药酒 赤脚板 烂泥坑和陷塌这些旧词
都将被那两个闪着柏油光芒的平坦和整齐所替代
这是好事情 按照图纸 工人们开始动手
挥动工具 精确地测量 像铺设一条康庄大道那么认真
道路高低凸凹 地质的状况也不一样
有些地段是玄武岩在防守 有些区域是水在闹事
有一处盘根错节 一颗老树 三百年才撑起这个家族
锄头是个好东西 可以把一切都挖掉 弄平
把高弄低下来 把凹填成平的
有些地方 刚好处在图纸想象的尺度
也要挖上几下 弄松 这种平毕竟和设计的平不同
就这样 全面 彻底 确保质量的施工
死掉了三十万只蚂蚁 七十一只老鼠 一条蛇
搬掉了各种硬度的石头 填掉那些口径不一的土洞
把石子 沙 水泥和柏油一一填上
然后 压路机像印刷一张报纸那样 压过去
完工了 这就是道路 黑色的 像玻璃一样光滑
熟练的工程 从设计到施工 只干了六天
这是城市最后一次震耳欲聋的事件 此后
它成为传说 和那些大锤 丁字镐一道生锈
道路在第七天开始通行 心情愉快的城
平坦 安静 卫生 不再担心脚的落处
《事件:铺路》不偏不倚,详述了连贯的、具体的意象:一方面是工具、机器及人造材料(如水泥及沥青),另一方面是被替换和破坏的真实“物体”(如树根、烂泥坑、石头、动物和人的赤脚)。正如《事件:棕榈之死》,这首诗同样表达对现代化的控诉。现代化给属于自然环境的人的身体带来了破坏和漠视,即使人在现代化所召唤的未来中会受到现代化的保护,不会再遇上“威胁脚”的烂路的坍塌和磕绊。因此,《事件:铺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自1980年以来城市转型所带来的破坏性的一面。于坚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及这个话题,其中特别提及昆明。⑯由于蚂蚁、老鼠和动物之死通常是“不算数”的,但在这里作者却用精确的数字记录下来,所以文本虽然没有愤怒的控诉,只是表达自己假装中立的立场、节制而如实的观察,但意图已相当明显。
尽管于坚自称拒绝隐喻,但读者仍有充分的理由把整首《铺路》看做隐喻,把文本解读成一种抵抗的表达:抵抗的是地域和个体身份在集权和标准化的背景下被“抹除”和“铺平”。在这类问题上,于坚写作最重要的题材是关于语言的。在国际层面,他把外国或“西方”语言(通常指英语)与中文对立起来;在国内层面,他把标准语言或“普通话”与地方话或“方言”(如云南话或昆明话)对立起来。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可以说是前者侵犯了后者。他把中文和地方习语的消失,及外语、普通话对中文、地方话的压制等“语言学”问题,看做英文想要称霸世界、普通话想要独据中国的结果。他指出,英文和普通话是代表政治权利的统治地位所产生的话语。在他评论性的文字中,于坚热情洋溢、振振有词地为汉语和地方话辩护着。在诗歌中,他交替使用随意、非正式的语言与政治正确的短语,后者多出自官方出版物。换句话说,他让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及其所代表的“民间”与“官方”现实交替出现。在《铺路》中,官方话语在“好地毯上的一条裂缝”“一切都要铺平”“确保质量的施工”“熟练的工程”等处可找到共鸣,还有风趣的“填掉那些口径不一的土洞”等。这样的叙述效果,可在“这种平毕竟和设计的平不同”一句中得到例证——遍布字里行间的反讽,是悲与喜的结合、绝望与苦涩的结合。
于坚式的欢快,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是鲜见的;80年代的莽汉诗派及21世纪初以来像“下半身”诗歌那样的“世俗”美学的极端表现属于例外。莽汉、“下半身”等诗作的欢快风格更近于一种浑不吝的挑衅。诗作《事件:谈话》(1990/1992)中的欢快不同于《事件:铺路》。《铺路》是在平实严谨的文字表象中,向现代化及其在社会物质方面的影响发动挑战,而《事件:谈话》则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这首诗极其滑稽,讲述了一个熟人为了躲雨而造访言说者的经历,他是带着一位陌生人“闯入”了言说者的家。这首诗的滑稽之感,同样源于客观化与主观化的综合效果。故事大约发生在一个湿漉漉的七月,之后我们读到:⑰
都在家里呆着 而用来流通的道路 就只有雨在漫步
这样是好的 家是家 雨是雨 一个不为了另一个存在
当门终于停下来忠实地供奉它的职位 我们却期待着一次入侵
毛孔在饭后打开 淫荡的孤独中 我们辨认着外面的声响
晚七点 天气预报完毕 雨还要持续一周
某人来访了 胖子或是瘦子 黑伞或是白伞
记不得了 入侵者的脸 干还是湿 我们从来不注意具体的事实
“我们从来不注意具体的事实”,读起来像是一种挖苦,挖苦对象是于坚向来乐此不疲地挑战的“总体话语”。在他看来,“总体话语”的抽象化操控,损害了人们的具体经验,尤其在文化政治中。在《谈话》中,一些短语把语言刻画成仪式化的、涵义空洞的社会交往,即使最乐观地看,也只有一种纯粹交际的(phatic)功能,确认“你”“我”在谈话但又“谈”不出任何真正的话题。如果不那么乐观地看,文本是在表达:语言是乏味的,甚至因其任意性而变得古怪离奇、荒诞不经:
谈着话的忽然不翼而飞 只剩下嘴巴 牙齿和舌根那儿的炎症
话再一回响起来时 漂移已在别一片水域了
这回的语法是 如果……就 假如……就好啦
还有 怎么办呢? 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雨是朝天空那个方向下就好啦 意味着一种拯救
说得很好 有意思 总有一人会恰到好处把关键指出
然后咧嘴一笑 嘴就那么残酷地往两边一闪
避开了爆炸的牙齿 但是……当这个词出现
就预示着一个高潮近了 有人将要愤怒 有人将要把水吐掉
有人将要思考反省 但是先喝点水 把痰咳净
换支烟 一整套的动作 谈话中的体操 具有音乐的秩序和美
舌根再次挤着上颚 像是奶牛场 那些工人在搓捏乳头
(中速) (行板) (庄严的) (欢乐的) (快板)
(热情) (缓慢 宁静) (3/4 拍) (渐起)(重复第四段)
通常 一张嘴爬着三到七只耳朵 而另有几只
早已骑上摩托 溜得无影无踪 长着耳朵的脸
看见这些话 以主谓宾补定状排列 刚刚迸出牙缝
就在事物的外表干掉 无论多么干燥 主人也得管住自己的耳朵
专心听讲 点头 叹息 微笑 为他换水 表示正在接收
谈话者就相当兴奋 娴熟地使用唇齿音 圆唇和鼻音
像在修改一位夜大学生的作业 在这里划上红线
在另一行写上?在结尾 他批阅道 主题还不深刻
雨还在下 有什么开始在渗漏 不管它 话题得再搬迁一次了
交流开始有些艰难 幸好 这房间是干的 我们就谈干的东西
干的家俱 干的婚姻 干的外遇和薪水 干的卫生间
干的电视和杂志 干的周末 在干的地方度过的干假期
谈话者,或“谈着话的”人,沦为一张自由漂浮的嘴巴,生出语言结构,如句型(“如果……就”和“假如……就好啦”)和符合所用语言音韵的声音(唇齿音、圆唇、鼻音)。把这种写作手法当做转喻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于坚的做法是赋予嘴巴以自主性:它不再再现或代替谈话者。“假如……就好啦”的句式在彬彬有礼的谈话中显得了无意义,与其充满想象的用法形成对照。“假如”的所谓想象的用法在于再现了真正意味深长又难以置信的场景(“假如雨是朝天空那个方向下就好啦 意味着一种拯救”),不像言说者和访客之间无关紧要的闲聊。
语言的俗套特征,同样显现在可预见的对话及互动过程中。哪怕仅仅是为了留客避雨而拖延时间,对社会和谐的期许也压倒了本来应该导致冲突的信息。连词“但是……”标志着一触即发的冲突,但言说者很快用续茶、续烟及尴尬地清嗓子等动作化解了冲突:“谈话中的体操/具有音乐的秩序和美。”主人公选择妥协而非冲突,“说得很好 有意思 总有一人会恰到好处把关键指出”,主人“表示正在接收”等表达,都讽刺意味十足,尽管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空洞结构的机械运作而已。言说者援引老师批改作业时那些老掉牙的评语,将这些谈话比作支配着正规教育的规则,这是于坚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诗中没有单数第一人称,但由于言说者的视角与主人接待访客的视角频频重叠,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主人眼里的主人公的自画像: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英雄,沉浸于宽容的自嘲,不作价值判断。
以“通常一张嘴爬着三到七只耳朵”为开端的那一段,既例证了于坚想象及关注事物的荒诞方式,又将谈话场景看做是潮湿的物质要素,明显与潮湿的空气、齿间横飞的唾沫有关。文本从谈话回到雨中,通过下一行“雨还在下”来回应“主题还不深刻”。雨点继续飘落,让人感觉到不祥,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渗漏进来,而将这种东西拒之门外的惟一办法是从头再来,谈论别的什么事。在此,谈话成了有意抵消恐怖骇人的自然世界形象的人类行为。我们也再次遭遇不同经验领域的重组,以及在多个语境中重复一个单词的另一例,如“干的家俱 干的婚姻”等等。这一行诗和下一行中所列的“干”物体有着不同的经验状态,从体制化的人际关系到消费项目,但全都是貌似合理的随意聊天的话题。不久后,诗歌结束:
十一点整 这是通常分手的时间 规矩 大家都要睡觉
雨是次要的 再大的雨 都要回家 走掉了
熟人和某某 打开伞 在雨中制造出一小块干处
雨仍然在下 它在和大地进行另一种交谈
大地回应着 那些声音 落进泥土
消失在万物的根里
正如谈话一样,客人的到访与离开取决于生活常规:分别是晚餐后及晚上十一点。“大家都要睡觉”这长辈式的陈辞滥调,强化了人际间交往的机械特征。在最后几行诗中,言说者对雨伞的功能做了典型的于坚式的描述,之后的句子则多少带有哲学思考色彩。雨水和土地之间所发生的谈话,伴有声音落入泥土这一鲜明有力的意象,或许比主人公们之间的谈话更有意义——但是否真的如此,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在下一首诗作中继续观察雨。《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1998)也是一首长诗,以下为71行诗句中的前38行:⑱
哦 要下雨啦
诗人在咖啡馆的高脚椅上
瞥了瞥天空 小声地咕噜了一句
舌头就缩回黑暗里去了
但在乌云那边 它的一生 它的
一点一滴的小故事 才刚刚开头
怎么说呢 这种小事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我关心更大的 诗人对女读者说
依顺着那条看不见的直线 下来了
与同样垂直于地面的周围 保持一致
像诗人的女儿 总是与幼儿园保持着一致
然后 在被教育学弯曲的天空中
被弯曲了 它不能不弯曲
但并不是为了毕业 而是为了保持住潮湿
它还没有本事去选择它的轨迹
它尚不知道 它无论如何选择
都只有下坠的份了 也许它知道
可又怎么能停止呢 在这里
一切都要向下面去
快乐的小王子 自己为自己加冕
在阴天的边缘 轻盈地一闪
脱离了队伍 成为一尾翘起的
小尾巴 摆直掉 又弯起来
翻滚着 体验着空间的
自由与不踏实
现在 它似乎可以随便怎么着
世界的小空档 不上不下
初中生的课外 在家与教室的路上
诗人不动声色 正派地打量着读者的胸部
但它不敢随便享用这丁点儿的自由
总得依附着些什么
总得与某种庞然大物 勾勾搭搭
一个卑微的发光体
害怕个人主义的萤火虫
盼望着夏夜的灯火管制
就像这位诗人 写诗的同时
也效力于某个协会 有证件
更快地下降了 已经失去了自由
从诗歌标题起持续贯穿全诗,雨点这种通常看来卑微低贱的无生命物体,与诗人这种通常看来崇高的人类形成对比。对比的效果不仅从本体上提升了雨点,同样也从本体上降低了(男性)诗人,前面的话(“这种小事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关心更大的 诗人对女读者说”)已为反讽开路。在第9行(“依顺着……”)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没有人称代词标记的主语从诗人转换到了雨点,随后这样的情形还有几次。于坚原本可以使用中性的第三人称单数“它”,但他没有,读者只有回过头来才会发现主语的转换。这就是客观化和主观化相结合在句法上的体现。
接着,诗人与雨点的相异,转变成了雨点与诗人女儿的相似。雨点和诗人的女儿都顺从于一个大的体系中的某条看不见的直线,他们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两个体系绝不会允许他们独立存在:第一个是自然法则,第二个是教育规范。这样的题材在于坚作品中是常见的,另一个常见的手法是语域的混合。这又一次尖锐地指出,语言绝不是描绘“现实”的透明、中立、可靠的工具,体制化语言,比如正规教育和政治意识形态所使用的语言,最能显示语言之塑造和扭曲经验的潜能。雨点“脱离了(革命)队伍”这一说法,即可为证。
下一步,诗歌不是将我们带回到诗人和雨点,而是带回到雨点和诗人:顺序已颠倒。雨点有它显在的自由,却又不敢沉溺于这样的自由,它变成了一切的尺度,也适用于衡量诗人的生存状态。在第38行(更快地……)发生了第二次匠心独具的、没有明确提示的主语切换。第9行的第一次切换,让读者做好了准备,接受了主语从诗人无缝地回到雨点(“更快地下降了”)。然而,读到第38行后半句(“已经失去了自由”),又考虑到第36、37行说诗人在写诗的同时也效力于某个协会,之前的20或30行诗句都是在描述庞大体系如何吞噬着个体生存,那么则可以看出,这些描述,不仅适用于雨点和诗人的女儿,也适用于诗人自己。就那个庞大体系来说,由于之前提到了自然法则和教育规范,所以我们又大可把文学界想成第三个这样的体制。
在第41行中(此处未节选),雨点“终于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雨点与诗人相等同,这在第50至57行中再次出现:
……它似乎又可以选择
这权利使它锋芒毕露 具备了自己的形式
但也注定要功亏一篑 这形式的重量
早已规定了是朝下的 一个天赋的陷阱
就像我们的诗人 反抗 嚎叫
然后合法 登堂入室
用唯美的笔 为读者签名
拼命地为自己抓住一切
如前面(第35行),第54行有一个直白的明喻:“就像我们的诗人。”按字面意义,作为个体的雨点难免于向下坠落,这被明喻为诗人“向上的”社会流动。这让读者回想起《事件:谈话》里那个轻率的假想:“假如雨是朝天空那个方向下就好啦 意味着一种拯救。”
记住这一点,我们或可相信,在诗行结尾,雨点和诗人的相遇不仅仅是巧合,而是两者难分难解,甚至他们在根本上是同一的:
它一直都是潮湿的
在这一生中 它的胜利是从未干过
它的时间 就是保持水分 直到
成为另外的水 把刚刚离开咖啡馆的诗人
的裤脚 溅湿了一块
【注释】
① 本文为作者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原名为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深圳大学教授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第七章的节选。英语原文主要读者群为外国人,下文中的某些问题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非新鲜之事,但或许作为文化交流一例也不无价值。第七章的全文开头划出于坚诗作的国内外出版史和接受史,以及于坚作为诗人兼评论者在批评话语中和诗坛上操作的作用。下面的文字为该章的中间部分,主要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解释于坚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几部作品
② 参见陈仲义:《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参见西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Simon Patton, “Raindrops and Bottle Top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in the 1990s” (雨点和瓶盖:介绍1990年代的中国诗歌),1998年11月10日。
④ 于坚:《于坚集1975-2000》,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于坚:《于坚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他版本在“领带”和“他再来上班的时候”之间有分节空行,但于坚2004年版却没有空行。此诗中分节的功能性表明,没有分节空行为印刷错误。
⑥⑦⑫⑬⑭⑮⑰⑱ 参见于坚:《于坚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 Michael Martin Day,China’s Second World of Poetry: The Sichuan Avant-Garde, 1982-1992 DACHS:http://leiden.dachs-archive.org/poetry/ md.html
⑨ 谢有顺:《回到事物与存在的现场:于坚的诗与诗学》,《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
⑩ Stephen Owen,“Transparencies: Reading the T’ang Lyric”, 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2期。
⑪ Maghiel van Crevel,“Unofficial Poetry Journal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Research Note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MCLC Resource Center: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ancrevel2/
⑯ 参见于坚:《棕皮手记》,上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1997年版。
作者简介※荷兰莱顿大学中国文学和语言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