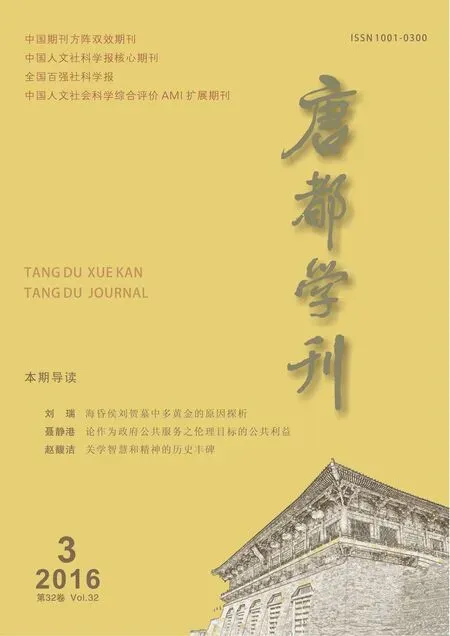汉代自杀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论析
2016-12-06罗启龙吴昭贤
罗启龙, [韩]吴昭贤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南京 210097)
汉代自杀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论析
罗启龙, [韩]吴昭贤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南京 210097)
汉代自杀群体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因素密不可分。该群体对自杀方式的选择,往往因身份、环境及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汉人的生死观是汉代自杀现象频发的深层原因之一:“死后有知”及“死后能与已逝亲人相遇”等观念减少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鬼魂能与天产生共鸣”观念的认可,使蒙冤者为证自身清白而轻生。汉代人们对家族的看重,也使得一部分人面对家庭蒙难时选择舍身保家。此外,在当时孝道观念影响下,牺牲个人保全长辈的安全与尊严的行为也受到鼓励和支持。同时,政府的放任亦是汉代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一。
汉代;自杀行为;文化因素;生死观;家庭观;政府
吴昭贤,女,韩国平泽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古代人对于生命比较敬重,追求平稳生活,而汉代自杀现象频发,自杀方式多样,表现出汉代统治者面对相关问题时所采取政策的不合理性,并反映出时人对待生命多元化的看法。通过对社会文化因素中的生死观、家庭观念进行探讨,能够理解汉代民众自杀的深层原因,并找出这种激进行为产生的源泉。
一、汉代自杀方式的选择及特点
汉代自杀方式呈多样化。经彭卫先生研究,汉代的自杀方式有11种[1]。其中,常见的自杀方式为自刎、饮药、绝食、自缢、自溺等。自杀者因性别、社会地位的不同,对自杀方式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同阶层中,不同的自杀动机也会使当事者采用不同的自杀方式。
(一)自刎

(二)服毒
服毒自杀与自刎相同,也是汉代各阶层的主要自杀方式。其流行原因应是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理念的影响。相较于其他自杀方式,服毒对自杀者身体外在的影响相对较小,不仅符合时人的孝道理念,而且能使当事者逝后留有一定的尊严,如河南尹李咸上书所言:“如遂不省,臣当饮鸩自裁,下觐先帝,具陈得失,终不为刀锯所裁”[4]。愿饮药而死从而免于刑戮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汉代所用毒物取于有毒的植物与动物,如《论衡·言毒》载:“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凑懑,颇多杀人”[5]949。常见毒药有乌头、巴豆、野葛、鸩毒等。而鸩毒是史载官员自杀使用最为普遍的毒药,如萧望之“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2]3288,家中便存有鸩毒。其中,亦不乏级别较低的官吏使用鸩毒的案例,如从事张贤“乃先以鸩与贤父曰:‘若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3]1109鸩毒之所以流行,其一,毒性强烈,使用者可立死,避免痛苦,且制作简单,如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2]1988。其二,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的法律条文规定:“有挟毒矢若谨(堇)毒、,及和为谨(堇)毒者,皆弃市。或命谓鼷毒。诏所令县官为挟之,不用此律。”[6]10堇即乌头,据整理小组考释,即附子,亦属乌头。植物毒中,乌头毒性最强,所以汉代明令禁止私人使用乌头制毒药。而巴豆、野葛等毒药均需大量服用才能使人致死,远不如鸩毒方便。汉代平民家中存有毒药的情况应不罕见,王符曾言一些妇女为守贞洁“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7],但平民常用何种毒药自杀却未有详载。
(三)绝食
绝食自杀指自己停止饮食而身亡,持续时间较长,往往需要数日至十数日,如龚胜绝食“积十四日”[2]3085而死。因绝食自杀时间漫长且痛苦,故较少被人采用。与其他自杀方式的不可逆性不同,绝食自杀过程中可变因素多,容易导致自杀失败,故自杀者需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因而当事者的动因大多是通过数天的绝食抗议向世人证明自身的某种信念或品质,如东汉女子玹何“郫何氏女,成都赵宪妻也。宪早亡,无子。父母欲改嫁。何恚愤自幽,不食,旬日而死”[8]736。此类自杀者往往生前具有或死后获得较大的声望,如龚胜为当时经学大师,玹何死后郡县为其立碑刻石。
(四)自缢
自缢是通过绳索等软物,一端绑在高处,另一端打好绳结,将脖颈深入结内造成大脑缺氧或心脏骤停而产生的死亡。自缢是汉代自杀的人选择最多的方式之一,汉代史料中,有较多关于自缢的记载,如曹宫六名宫女“即自缪死”[2]3991,东海孝妇之姑“自经死”[2]3041等,由于自缢相较于其他自杀方式取材简单、地点较容易选择,且自杀时会迅速窒息昏厥,痛苦时间短,故常见于自杀案例之中。因自缢致死性高,平民与中下层官吏选择此方法时一般带有很强的死亡意念。如秦代曾出现“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2812的情况,民众对生活无望,集体“自经于道树”,而并非一时冲动。东汉烈女荀采“以衣带自缢”[3]2799前便“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其自杀动因存在已久。
(五)自溺
自溺是指将自己投入水中造成窒息死亡的自杀方式,也是汉代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自杀人群多为女性,地点为水井与江河。除与其他自杀方式相同的动因外,选择自溺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为死去的亲人殉亲。如孝女曹娥因其父“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3]2794因溺亡于江河者的尸身不易找到,当事者因追思亡者,选择在相同的地点以相同的死亡方式追随而去,如东汉孝女叔先雄“父泥和……乘船墯湍水物故,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常有自沉之计……雄因乘小船,于父墯处恸哭,遂自投水死”[3]2800。自杀地点的同一性,是自溺的特点之一。
二、汉代生死观对自杀的影响
自杀者虽然采用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动机却有相似,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原因,如生活的困境使其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或基于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和信仰,而选择主动放弃生命。另一方面,春秋以降,民间流传的生死观对一些当事者亦造成不小的影响。多数自杀者面对生活的困苦,内心真正向往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寻到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死的认知,恰恰为当事者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提供了依据。
其一,汉代士大夫对死后世界的认知并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死后的世界是幽深黑暗的,如汉武帝之子刘胥自杀前曾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2]2762另外南阳市东关李相公庄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的一段诔文中的两句对阴间世界有所描述:“痛哉可哀,许阿瞿□,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9]表明时人印象中的阴间是黑暗可怕、与家人隔绝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持与此相反的观点,如马王堆一号墓中的昆仑山图像象征的死后世界与前文所述完全不同,认为死后会生活在一个极乐世界[10]。
但无论死后世界是黑暗可怕还是美好的,都建立在“死后有知”的基础上。可是汉代学者王充根本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试以物类验之,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何以验之?验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世能别人物不能为鬼,则为鬼不为鬼尚难分明;如不能别,则亦无以知其能为鬼也”[5]871。既然对鬼神之说都予以否定,自然更谈不上有死后世界了。正是由于士大夫阶层对“死后世界”多元化的认知,一些官吏对世人所构建的彼世态度并不明朗,如东汉学者任末的遗命:“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3]2572。对于死后是否会有感知,并不肯定,因而要“致尸于师门”,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其中一些自杀者的死亡观也是不明确的,如东汉武威太守张猛自杀前曾言:“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有知,岂使吾头东过华阴历先君之墓乎?”[11]这种对死后情况的模糊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者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且身处绝境中的人在心理上更希望能通过这种途径改变自己的困境。
其二,与前文对生死观模糊的认知不同,汉代主流观点认为灵魂是有知的。王充曾描述:“谓死者有知,鬼神饮食,犹相宾客,宾客悦喜,报主人恩矣。”[5]1047山东苍山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出土的二石题记中载有:“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立廓毕成,以送贵亲,魂灵有知,柃(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12]不难看出,汉代社会对灵魂有了形象的看法,认为人死后的生活同活人的生活相差无几,这点亦可从汉代诸多出土墓葬中看出,并且汉代人认为鬼神具有保佑子孙的能力。而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一篇中,共载有22种鬼,并且具有超自然的能力[13]。可见,在秦汉之际,人们普遍认为鬼神能力是活人无法企及的。汉代部分自杀者的动因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受“灵魂有知”的影响,自杀者把自杀的“我”与受重视的“我”混合在一起,其以为主“我”在自杀之后仍能获得重视,而死去的宾“我”能作为主体享受到别人的重视。如龚胜所云:
“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2]3085
从龚胜的遗命来看,其对于灵魂有知的观念是较为认可的。祠堂是汉代亡魂的归附之所,汉代人们祭奠先祖的地方。山东东阿铁头山芗他君祠堂有题记云:“起立石祠堂,冀二亲(灵)有所依止。”[14]可见,龚胜相信死后仍能获得别人的祭奠与重视。
另一方面,汉代社会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时人相信当受冤而死时,其冤魂会与天产生共鸣,而引发灾异,以警醒世人,从而为自己洗刷冤屈。如汉代东海孝妇之事:
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而下云。”[15]
此事虽为传说,但在汉代士大夫所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柱石之下,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深的影响。后东汉太守殷丹为郡县求雨时,孟尝言道:“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3]2473。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人不畏惧死亡,甚至以死抗争,以表达自己的冤屈。汉代杨震饮鸩自杀后,“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郡以状上。时连有灾异,帝感震之枉”[3]1767。灾异的出现,常使统治者感到惶恐,反省自身,进而采取措施抚慰冤魂。大司农朱宠在邓骘一门因罪自杀后便上疏“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3]617认为“率土丧气”是因“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引起“逆天感人”所造成的。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当人们生前无法证明自身的某种品质,或对某种境况无力改变的时候,往往会设想死后利用鬼神的超自然能力来改变自身的现状。
其三,蒲慕州先生推测“当时人应该相信一般人死后仍然得以继续追随先王。如果不能追随于天上,至少也能追随于地下。东周金文中亦有死后事先王于地下的说法。这追随于地下的观念到了汉代以后是相当普遍的。”[16]如蒲慕州先生所言,汉代的许多自杀案例,正是基于追随先主的观念下产生的。如西汉时期,赵王刘元临逝之前“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2]2421,胁迫的目的即是为了死后能继续享乐,这种行为的起因也是相信“人死后仍然得以继续追随先王”,故使奴婢自杀从而追随其于地下,以便继续服侍他。也有不少士大夫,深信死后能见到故主,如冯参自杀前感叹道因“今被恶名而死”而为“伤无以见先人于地下”[2]3307感到遗憾。平民当中,这种观点亦相当流行,如东汉叔先雄父亲溺亡后,自己随之投河而死,其魂便追随其父,“弟贤,其夕梦雄告之:‘却后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浮于江上”[3]2800。孝女曹娥亦是因父溺亡而“遂自投于江而死”,尔后“五日后抱父尸出”。这些事迹虽然荒诞,但体现了民众对灵魂观点的认知,“死后能与故人相遇”的观点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这也是部分人群在亲友逝世的悲痛情绪的影响下,产生自杀欲望的主要诱因。
迪尔凯姆认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传统的、因而也是必须遵守的许多信仰和教规。这些集体的状态越多越牢固,宗教社会的整体化越牢固,也就是越具有预防的功效。”[17]167宗教对自杀的预防是与其统一度成正比关系的。而汉代社会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民间的精神信仰处于多神与功利的状态,对生死观的理解也具有较大的分歧,远未达到一体化。自杀属于“极度自我放纵”[18]150,汉代信仰的多元化的特点并不能有效抑制这类行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成为自杀的助力。
三、汉代家庭观与家庭法对自杀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对家庭的传承与延续极为重视,滋贺秀三先生指出:
人、祭祀、财产这三个方面的不断延续,使得一个家族得以传承下去,死去的人的生命也就通过后代的繁衍和祭祀活动而延续下去。父子(母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构成了理解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原则。[18]96-97
汉代社会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之下,人们对家族后嗣的绵延也是极为看重的,认为“人道所以有嫁娶何……重人伦、广继嗣也”[19]。“保全家庭”,正是汉代犯罪官吏选择自杀的主要动因。
汉承秦制,对罪犯家属往往实行缘坐,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中的简文:“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6]18。家属要判为徒刑“城旦舂”。而根据《二年律令·收律》中载:“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6]32罪犯受刑在“城旦舂”或“鬼薪”以上,财产要被官府征收,其妻子也要充为官奴。而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所载条例来看,对罪犯家属处以缘坐的法律条目十分繁多,其严苛成为汉代官员自杀现象频发的一个外因。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建议国家应效仿上古时期“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而刑之也”的做法,不公开刑戮犯罪官员,以保全其尊严,从而达到“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2]2257的目的。其意见被采纳,“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2]2260。此后,自杀便成为朝廷对官员施行“隐诛”的一种方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刑罚手段。如王嘉入狱时,其主簿便逼促其饮药自尽“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2]3501。有汉一代,因罪自杀者极多,俨然成为一种风尚,“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宁轻生以免辱,亦一时风尚使然也。后遂有以此为例,而逼令死于家者”[20]。汉代犯罪官员之所以选择自杀者居多,除因保全尊严外,使家庭免受牵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汉文帝时期朱建“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杀为?’建曰:‘我死祸绝,不及乃身矣。’遂自刭。”[2]2118自杀者家庭可免除刑事连带的责任,已成为当时一种减罪条例。一些官员甚至罪不至死,为了家庭免于处罚而选择自杀。东汉郅寿“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3]1034受汉代的家庭观念影响,人们认为家族的兴旺与否远比个人安危重要,正因如此,基于汉代法律政策下,许多人罪不致死却选择舍己而保家。
甚至常常会出现以家庭相挟迫令其自杀的情况,如东汉时期梁冀威胁杜乔“早从宜,妻子可得全”[3]2093。虽然因犯罪者自杀而免除家属连带责任的案例常见于史料之中,但这种情况仍属特例,而非常例。缘坐法仍是当时刑罚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当亲属获罪,人们出于各种动因而选择自杀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如前文所引汉代政府“劫人、谋劫人求钱财”与“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罪犯家属处罚并不一致,可见家属的连带罪责的大小往往视犯罪者的罪行而定。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所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6]7谋反、降敌等罪家属要处以“腰斩”的极刑。因而,当某人犯有重罪时,其家属往往出于恐惧或私人感情而选择自杀。如刘旦因篡位未果,“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即以绶自绞。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2]2795。犯罪者家属自杀并不全因个人感情因素,对法律的畏惧也是一方面原因。冯参因其姐中山太后被告祝诅而畏罪自杀,“参以同产当相坐,谒者承制召参诣廷尉,参自杀”[2]3307。正是在家庭缘坐法的压力之下,无奈自杀。除法律因素外,政治因素也是官吏家属自杀的主要诱因,如大将军邓骘“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骘为罗侯,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惟广德兄弟以母阎后戚属得留京师”[3]617。邓骘及其家族正是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导致家族成员自尽。晁错之父也是因政治原因担心祸及自身而选择自杀。“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而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2]2300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自杀的人往往自身或其家属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中下层官吏与平民则鲜少因此而自杀。此外,也有官吏因家属犯罪而感到羞惭而自杀的。“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再宿,狱掾实不知。掾惭恐,自杀。”[2]3390故汉代因家庭而自杀的案例往往涉及法律、道德及政治等多方面因素,以前两者对平民的影响最大。
除上述家属连带责任的原因外,汉代孝文化成为影响自杀者的家庭因素中的特殊一环。汉代施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孝道”已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家庭伦理道德的范畴,而上升至国家政治的层面。汉代统治者一方面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不孝者进行严惩,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规定“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对不孝的行为要给予弃市的处罚,并且不能赦免,甚至“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6]13。另一方面,对“孝道”进行广泛的教育,“硕水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21]。汉代幼童即要学习《孝经》等内容。此外,统治者对“孝行”也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251。一些因孝行的犯罪行为不予追究。政府采取法律与教育两方面规范着整个国家“孝道”统治,该统治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居民的思维,民众之中,出于尽孝的动机而导致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市行,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投缳而死”[3]2101。正是在汉代盛行的“父辱子死”[3]2673的道德观影响下,毋丘长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以维护长辈尊严,从而导致其自杀身亡。此外,在家庭内部产生矛盾时,也有因尽孝而无奈选择自杀的案例,如周郁妻赵阿因规劝周郁无效,而受到周郁之父指责,后在无奈之下选择自杀。“‘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杀。莫不伤之。”[3]2784因“不奉教令”与“违父而从妇”的后果均为不尽孝行,赵阿无论做何种选择皆无法达到尽孝的目的,故而自杀。维护父母的尊严与安全,是汉代基本的尽孝的表现形式,也为大多数人所恪守。三国时期,涪陵人李余“父早世,兄夷杀人亡命,母慎当死。余年十三,问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不?’人曰:‘趣得一人耳。’余乃诣吏乞代母死。吏以余年小,不许,余因自刎死”。因维护父母安全,代其受刑而自杀,是尽孝的极致,是符合政府的统治理念的,故而统治者对这类行为一般是持纵容甚至鼓励表彰的态度的,如李余死后“吏以白令,令哀伤,言郡,郡上尚书出慎。太守与令以家财葬余,图画府廷”[9]820。对于履行“孝道”而自杀的情况,政府的认可与宣传是家庭自杀事例频发的一大助因。
汉代家庭成员的自杀,主要是以法律、政治等外因以及“孝道”观念等内因引发的。外因造成了联系家庭的纽带断裂,引起了家庭巨变,进而对家庭成员内心造成了巨大的波动,故而容易引起自杀。而内因则是中国古代家庭生活中所具有的“道”,自杀则是人们对“道”追求的一种极致。
四、秦汉法律对自杀的干预
汉代统治者对自杀的态度并非全然默许与接受的,一些情况下,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自杀行为进行干预与防范。如上文所引《二年律令》“有挟毒矢若谨(堇)毒、,及和为谨(堇)毒者,皆弃市。或命谓鼷毒。诏所令县官为挟之,不用此律。”对乌头等易使人致死的药物政府是禁止私人使用的,违反者要被施以“弃市”的重刑。其次,在某些环境下,政府对协助他人自杀者予以严惩,《居延新简》中记载:“以兵刃索绳它物可以自杀者予囚以自杀、杀人,若自伤、伤人而辜二旬中死,予者髡为城旦舂……”[22]。对保辜期限内的伤者提供“兵刃索绳它物”而致其自杀要处以“髡为城旦舂”的刑罚。总体来讲,汉代政府受时代局限,并未采取专门针对自杀的举措,往往是因其他政治或法律的需要才涉及相关问题,如上述对被伤者的自杀防范也仅局限于保辜期限之内。
另一方面,秦汉之际政府对于自杀案件,并非任其家属处理,需要告知官吏“或自杀,其室人弗言吏,即葬狸(薶)之,问死者有妻、子当收,弗言而葬,当赀一甲”[23]111。如自行埋葬,要被处以罚“一甲”的惩罚。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经死》一文看到,政府要求自杀者家属上报的目的是对现场进行勘察检验“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不智(知)故,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判定当事者是否属于自杀:“道索终所试脱头;能脱,乃□其衣,尽视其身、头发中及篡。舌不出,口鼻不渭(喟)然,索不郁,索终急不能脱,□死难审(也)。”其自杀动机也要探明,“自杀者必先有故,问其同居,以合(答)其故”[23]158,以防止他杀被当成自杀处理,事后需作出“爰书”的文书报告。
总而言之,除政治或法律需要外,统治者基本是以听之任之的态度来对待自杀事件的。究其原因,一是统治者认为在不影响其统治秩序的情况下,人们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二是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思想的影响,政府对自杀是无能为力的。故而秦汉时期政府对自杀的干预十分有限。
五、结语
通过笔者的研究不难看出,汉代自杀现象频发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在政府对自杀行为极少干预的情况下,社会文化成为自杀动因形成的决定因素,其中时人的生死观影响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与西方宗教不同,汉代社会的精神信仰并未形成统一的教义,正如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分散式的宗教对自杀并不具有很强的节制能力。此外,对死后世界的认可,使得人们在面对生存困境时,更轻易地放弃生命。同时,另一方面,在汉代家庭观念的作用下,人们的行为是以维护家庭稳定与传承为目的的。故而,当家庭面对变故时,人们会为追求家庭的平稳或社会所崇尚的“孝道”而做出极端的选择。
[1] 彭卫.论汉代的自杀现象[J].中国史研究,1995(4):55-66.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袁宏.两汉纪·后汉纪:卷23[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458.
[5]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7] 王符撰,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8.
[8] 常遽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9] 南阳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J].文物,1974(8):73-75.
[10]郝利荣.汉代石椁画像与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从汉代墓葬建筑的“象生环境”和“死而不亡”的理想境界谈起[J].文物世界,2013(5):13-19.
[11]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548.
[12]李发林.山东画像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2:95.
[13]刘伟.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中的鬼、神和怪[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5):10-12.
[14]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204.
[15]干宝.搜神记[M].马银琴,周广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05-206.
[16]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2-73.
[17]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8]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9]班固.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451.
[20]赵翼.陔余丛考[M].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88.
[21]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71.
[2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61.
[2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朱伟东]
Analysis of Cultural Factors for Suicide Behavior in the Han Dynasty
LUO Qi-long, WU Zhao-xian
(CollegeofSocialDevelopment,HistoryDepartment,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97,China)
The occurrence of suicide group wa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choice of suicide methods varied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motivation.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in the Han Dynasty is one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for the frequent suicide phenomenon in the Han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fe after death” and “meeting the deceased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fter death” and other similar view of life and death, people tended to be less afraid of death. Believing that “ghosts could resonate with God”, the wronged people chose death as a way of proving their innocence.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valued family reputation very much, so some of them chose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faced with their family’s sufferings. Moreover, due to the prevalence of filial piety in the Han Dynasty, people were encouraged to protect the safety and dignity of their elders by sacrificing themsel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issez-faire policy of the Han Government was also one of the causes for the high rate of suicide in the Han dynasty.
Han Dynasty; suicide behavior; cultural factor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family view; government
K234
A
1001-0300(2016)03-0017-07
2016-02-15
罗启龙,男,河南洛阳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