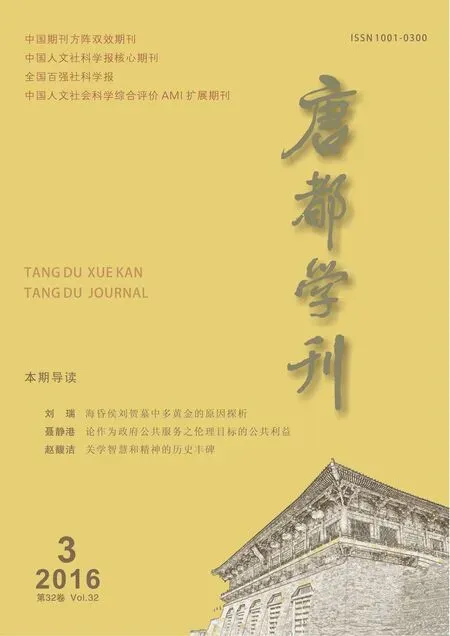理查德·罗蒂论反讽概念与私人完美
2016-02-02黄泰轲
黄泰轲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院,长沙 410081)
理查德·罗蒂论反讽概念与私人完美
黄泰轲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院,长沙 410081)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本质,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对本质的发现之上。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认为,企图通过发现本质而成就人生是一种虚妄。借助反讽概念,罗蒂批判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所谓本质的世界,其实充满着偶然,创造而不是发现才是我们私人完美的关键。罗蒂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私人完美的过程中,要注意个体对共同体的义务,加强公共团结。通过反讽概念的揭示及对团结的强调,罗蒂把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爱国主义的传统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理查德·罗蒂;反讽;私人完美;公共团结
反讽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我们多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它。事实上,西方思想史上,也有一条明晰的反讽研究线索,苏格拉底、施莱格尔、黑格尔、克尔凯郭尔等均使用或阐释过反讽。在苏格拉底那里,反讽首先表现为一种论辩技巧,它意味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对外在伦理规则的质疑;在施莱格尔那里,反讽意味着毁灭、创造,意味着“优美的自我镜像”;在黑格尔那里,反讽意味着“有限的主体与腐化堕落的外在世界之间矛盾”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反讽意味着人之有限与无限之间矛盾的揭露,意味着“个体的人”摆脱有限进入无限的精神成长。以反讽概念研究为博士论题的克尔凯郭尔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倡、引进反讽的是苏格拉底”[1]论题10、“现代的反讽首先归于伦理学”[1]论题11、“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1]论题15。梳理思想史上的反讽概念,我们发现:尽管不同哲学家对反讽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阐释点:反讽指涉个体的精神成长。我们也把个体的精神成长称为私人完美。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更为明确定义了反讽概念并且从哲学的角度说明了反讽概念与私人完美的关系。罗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意识到个体对自己私人完美的促进这一人生义务及私人完美应注意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罗蒂论反讽概念与私人完美的旨要。
一、私人完美:成就普遍性还是独特性?
哲学家和诗人总是在关注人生的完美问题,但其关注存在明显的区别。罗蒂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作出说明,他是从解读诗人拉金的一首诗入手的。在这首诗里,拉金把人生的旅程比作一张装载单。这张装载单有什么用处呢?“届时,我们依稀辨识了,我们一切言行载负的模糊印记,才能将它追根究底。”原来,正是依靠了这张装载单,我们才能去回溯我们那独特而多彩的人生,从而给逝去的生命以安慰。但有时我们也不满意,因为这张装载单“只一回适用于一人,而斯人将逝”。我们失落地发现,这张装载单仅仅只适用于我自身而已,与他人没有共同的东西,对他人没有什么参照作用。
罗蒂对拉金的诗进行了如下解读:“拉金的诗本身为他所恐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暗示了一条解开谜底的线索……我认为,丧失那个差异性,乃是任何诗人——任何制造者、任何期望创造新东西的人——心中最大的恐惧……但是……他暗示,除非一个人发现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共通的东西,而不只适于一人、一回,否则他不可能死得心满意足。”[2]39-40在罗蒂看来,拉金在这首诗中表达了两种焦虑: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和没有成就一种普遍性。罗蒂认为,拉金既想做一个有个性的诗人,又想成为一个发现普遍性的哲学家。罗蒂从哲学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我认为,拉金这首诗之所以耐人寻味、具有说服力,就在于他把诗与哲学的古老争辩,旧事重提。自来,承认偶然并努力成就自我创造,和超越偶然并努力成就普遍性,两者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2]41
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最早提出了诗与哲学之争的话题。他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而使理性屈服于激情和冲动的诗歌是哲学的天敌。在《国家篇》中,他似乎不打算批准除了颂神诗和赞美诗以外的任何诗歌进入他所设计的“理想国”。柏拉图的这个观点一直影响着黑格尔之前的许多哲学家,在他们看来,与普遍性相比,个体生命的独特和偶然是不重要的,诗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在独特性、偶然性上大做文章,这与探求真理及追求有价值的人生无补。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这一传统哲学理念遭到了黑格尔之后尤其是尼采之后的不少哲学家的激烈批判,他们认为,传统哲学僵硬的思想体系窒息了人生,他们坚持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偶然性,“让哲学向诗投降”。罗蒂认为,尼采是第一位公然呼吁丢弃“普遍真理”这种想法的人,尼采说真理是“隐喻的机动部队”,这表明世界并不存在本质而是充满了偶然,尼采以为,只有诗人才能真正体悟偶然,我们应该向诗人学习。罗蒂甚至说:“在尼采看来,无法成为一个诗人,就等于无法成为一个人,就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描述,执行一个已先设计好的程式,或顶多只是根据前人写就的诗作,写出优雅的变体而已。”[2]43
在考察了诗与哲学之争后,罗蒂明确指出哲学家与诗人在私人完美这一问题上的路径差异,这种差异在下面这段话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依照西方哲学传统的看法,个人生命的极致,就在于它突破了时间、现象、个人意见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永恒真理的世界。相应的,在尼采看来,极致生命所必须越过的重要关卡,不是时间与超时间真理的分界,而是旧与新的界限。他认为一个成功极致的个人生命,就在于它避免对其存在偶然作传统的描述,而必须发现新的描述。这正是真理意志和自我超克意志的差异所在,也是两种救赎观念的分野:一个认为救赎就是与一个比自己更伟大、更永久的东西接触,另一个认为——如尼采所言——救赎是把一切‘曾是’皆重新创造为‘我曾欲其如是’。”[2]45罗蒂认为,哲学家与诗人为我们提供了两条走向私人完美的路径:追求普遍性和追求独特性。前者以柏拉图为代表,后者以尼采为代表。在柏拉图看来,人生的完美在于对本质(真理)的追求,可在尼采看来,人生的完美在于把握偶然从而对自己不断进行新的描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一个存在普遍本质的世界还是一个充满偶然的世界呢?
二、本质的幻灭与偶然的存在
罗蒂认为,通过真理获得人生永恒,这是一个肇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此传统所追求的知识“是关于人类是什么的知识,既不是关于希腊人或法国人或中国人是什么的知识,而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转引自顾林正的《从个体知识到社会知识:罗蒂的知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即关于“本质”的知识。有学者这样分析传统哲学藉普遍知识获得人生永恒的思路:“知识论的方式试图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就预设了‘是者’,就是从对象那里确定‘我’是什么,把一定语境之下对某个对象的描述固定下来,并使之永恒化,以为抓到了真实的自我……自我具有一张唯一的正确的装载单,这种装载单上有自我的全部描述,它可以逃脱随机和偶然,抓住大写的实在的自我之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一劳永逸。”[3]拉金想要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一劳永逸”装载单,上面写满了“本质”“实在”“必然性”“客观性”“真理”等词汇,这些词汇告诉我们,对人生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传统哲学认为,任何一个追求私人完美的人都要从学习、理解、把握上述基本词汇开始。罗蒂也不例外。先是学习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再是接受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但后来,罗蒂逐渐对这些感到厌烦,乃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境》这一著名序言中,罗蒂对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产生了怀疑,紧接着,在70年代又花了整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地推进了这种怀疑,其最终研究成果体现在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境》一书中。在该书中,罗蒂对传统哲学有一个总的批判和清算:他反对康德所主张的哲学为整个文化立法和提供基础的观点,反对笛卡尔所主张的心灵作为外在世界的镜子的观点,反对柏拉图所主张的真理是对表象准确再现的观点,循着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道路,借助后分析哲学家们的论证,罗蒂得出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的结论,彻底摧毁了传统哲学家形而上学的迷梦。罗蒂认为,传统哲学的基本词汇都是不诚实和虚幻的言说。罗蒂旗帜鲜明地说:“我非常讨厌逻辑、形式主义和一切带有永恒性意味的东西,一切拒绝成为偶然性囊中之物的东西。”*转引自张国清的《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页。在罗蒂看来,与传统哲学词汇相比,我们更密切地联系于“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等词汇。本质幻灭后,罗蒂从语言、自我和自由主义社会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偶然的普遍存在。
语言的偶然。西方哲学发展到20世纪,发生过著名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企图通过探讨语言的本质来把握世界的本质。罗蒂指出,语言没有本质,语言是具体的、个别的、偶然的存在。借助戴维森和赖尔等人的理论,罗蒂论证了语言的偶然性,进而也表明了真理的偶然性。罗蒂说:“戴维森让我们把语言及文化的历史,想象成达尔文所见到的珊瑚礁的历史……这个类比教我们把‘我们的语言’——20世纪欧洲文化与科学的语言——看作只是许许多多纯粹偶然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化,跟兰花及类人猿一样,都只是一个偶然,只是千万个找到定位的小突变(以及其他无数个没有定位的突变)的一个结果。”[2]28罗蒂同意戴维森认为语言是一种与描述对象之本质毫无关联的“隐喻”的说法,隐喻不是隐射一个需要我们去猜测的本义,隐喻本身不具意义,不具必然性,它的使用根源于人们的想象力,一个隐喻可能流行起来,往往是偶然机遇的结果。罗蒂引申说,一部思想史就是一部隐喻史,“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4]。罗蒂认为,戴维森所说的“隐喻不具有意义”看起来虽像一句俏皮话,但与建立在传统真理观上的人生观相比,它其实暗含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发现。
自我的偶然。哲学史上,早期的祭师,后来的希腊哲学家,随后的经验主义科学家以及更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都宣称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必然的、本质的、有目的的、且构成人类本性的戳记。他们认为,一旦人们把握了自我的本质,也就是认识了真理,完美了人生。罗蒂借助尼采和弗洛伊德对此进行了批驳。在尼采看来,“获得这类自我认识,并不等于认识到一个任何时候都存在那儿(或存在内心深处)的真理。相反的,他认为自我认识是自我创造。认识到自己、直接面对自己的偶然、对自己的原因追根究底的过程,与创造一个新的语言、独创一些新的隐喻的过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2]43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也使我们看到,自我并没有任何柏拉图、康德等传统哲学家所说的那种普遍本质,它不过是“欲念之网”而已,相比普遍理性,婴儿期被压抑的性冲动、无意识的强迫性观念和恐惧感等或许对个体成长影响更大,天才与卑污之人的区别,是由偶然因素所致,而并不在于谁更接近、更占有普遍的人类本性。罗蒂说:“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一个在社会上看起来是无意义、荒诞不经或卑污低下的东西,如何可能变成一个自我认同中的关键因素,变成一个人以其独特方式追究其一切言行的盲目模糊印记时所运用的关键因素。相反的,如果某个私人的强迫性观念所产生的隐喻被一般人认为有用,那么我们就会说那是天才,而不是疯癫或叛逆。天才与幻想的差异,不在于天才的印记掌握到了普遍的东西,或先已存在外在世界或内心自我中的实在,而幻想则无。反之,这差异只在于天才个人独具的东西,‘凑巧’地被其他人所熟悉和流传——之所以是巧合,是因为某些历史情境的偶然所使然,是因为那个社会‘凑巧’地在那个时候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需要。”[2]56也就是说,人的道德品质并不是由他身上的普遍人性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特殊生活经历、心理体验、个人气质等综合塑成的,而这些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因素又往往具有偶然性。罗蒂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道德更多的是来自偶然和运气,而不是人的普遍理性。他说:“作为一名十几岁的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我有一种比我的同学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先天自大感,他们的父母一直要等到莫斯科审判之后才与美国共产党决裂,同我的父母在1932年就与美国共产党决裂相比,已经整整晚了五个年头。如果我持有与希钦一样的观点,我将以为我的父母当属头脑特别灵活、心底特别诚实的那一类人,但事实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他们曾经碰巧与一些美国共产党要人亲密共事过,而绝大多数美国共产党员同路人未曾有过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知道别人后来才知道的许多内幕。”[5]罗蒂借弗洛伊德的话说:“我们都太容易忘记,打从精子和卵子交会的一刹那开始,与我们生命有关的每一件事物,事实上都是机缘。”[2]47
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在罗蒂看来,不仅语言和自我是偶然的,更有甚者,连西方自由主义制度也是偶然的。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自由主义社会之所以是好的,乃是其体现着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也即其有着真理的基础。在《民主先于哲学》一文中,罗蒂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有一个哲学基础。他认为,自由主义制度之所以是好的,不是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保障的,而是西方人的一种实践选择,比如西方人恰恰幸运地选择了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科技革命等,而这些带有偶然性的选择才成就了我们“富裕的北大西洋民主社会”。罗蒂援引杰弗逊和杜威来证明自己,他说:“杰斐逊和杜威都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实验’。如果这个实验失败了,我们的后代可能会知道某些重要的东西。但他们不会学到一个哲学的真理……他们只会在做下一个实验时就应该留心什么得到些暗示……也许我们的后代还会记住,社会制度可以看作是合作的实验而不是想包含一种普遍的、非历史秩序的企图。”[6]在罗蒂看来,启蒙哲学给予社会历史和自由主义以合理证明并提供哲学基础的企图是失败的,不仅如此,这种企图对自由主义社会的实验还是有害的,罗蒂说:“我将设法指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词汇,虽然与自由主义民主的肇始息息相关,但已经变成了民主社会延续与进步的障碍。”[2]67
三、反讽:一种自我创造的私人完美
本质的幻灭和偶然的无处不在,使得罗蒂在私人完美问题上选择了诗人提供的路径而不是哲学家提供的路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罗蒂承继了思想史上的反讽概念并做了更为明确的定义和阐释。罗蒂这样定义反讽的概念:“依我的定义,‘反讽主义者’(ironist)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1)由于她深受其他语汇——她所邂逅的人或书籍所用的终极语汇——所感动,因此她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2)她知道以她现有的语汇所构作出来的论证,既无法支持,亦无法消解这些质疑。(3)当她对她的处境作哲学思考时,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实有,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在她之外的任何力量。具有哲学倾向的一些反讽主义者,都不会认为不同词汇的选择,乃是一个中立的、普遍的超词汇范围内进行的,或由企图穿透表象、达到实有的努力所达成的;他们认为,不同词汇间的选择,只是拿新语汇去对抗旧语汇而已。”[2]105-106依罗蒂的定义,反讽首先是我们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即我们并不能通过某种标准词汇去把握世界的实有。事实上,“反讽主义者”是相对“形上学家”而言的。形上学家是指追随以柏拉图、康德为代表的哲学传统的人。他们企图选择、运用、发展一套唯一正确的终极词汇来窥探世界的内在本质。反讽主义者根本否定有这样的本质和这样的词汇。反讽者认为,所谓本质和窥探本质的终极词汇只是西方人的俗见而已,反讽者抛弃对本质及窥探本质的终极词汇的坚守。他们在多套词汇间比较、选择,他们不停地选择又不停地否定自己的选择,他们追求多样性和新奇性,而非普遍性和终极性。
基于对偶然的推崇,反讽者反对传统哲学对本质自我的认识与追求,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本质自我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人生的唯一使命是创造自我而不是发现自我。“强健诗人”是这方面的代表。罗蒂说:“克尔凯郭尔、尼采、波特莱尔、普鲁斯特、海德格尔和纳博科夫等人的用处,就在于他们是人格的模范,告诉我们私人的完美——亦即自我创造的、自律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原来自己依稀仿佛也有变成一个新人类的需要,想要变成一个我们还没有语言加以描述的新人类。”[2]4-5正因为如此,反讽者谨慎选择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语言,他们害怕被传统哲学所谓的标准语言误导而影响了自我创造,罗蒂说:“反讽主义者花时间担心她是不是可能加入了错误的部落,被教了错误的语言游戏。她担心,给她一个语言并使她变成了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也许已经给了她错误的语言,从而使她变成了错误的人类。”[2]107反讽者心目中的裁判就是他自己,他想用他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其他的标准语言总结他的人生。“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就是这样的典范。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类生活的世界并不像黑格尔所宣扬的那样,到处充盈着理性的胜利和进步的必然,人其实生活在由偶然和荒谬所编织的生存境遇之网中,我们要用反讽来对抗这种偶然和荒谬。克尔凯郭尔把反讽定义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1]225。他认为,否定、反抗和超越是反讽的本质诉求,反讽者的使命是彻底揭露旧的事物的缺陷,竭尽全力摧毁对于他来说即将消逝的事物,为新的事物而奋斗,反讽者注定是为迎接新事物的来临而出生的斗士、英雄,他说:“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存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1]224-225反讽使主体脱离了现实性的种种束缚,激发和孕育了主体的无限热情,使主体徜徉在自由的空气中并陶醉于无限的可能性之中,因此“反讽一旦被掌握,它的运作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以便个人生活能够获得健康和真理”[1]285。正是在反讽的激励之下,克尔凯郭尔才完成了从美学的人到伦理的人到宗教的人三阶段的跳跃,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个体的人”,也正因如此,罗蒂才把克尔凯郭尔称为“强健诗人”的典型。
发现自我还是创造自我,这是“形上学家”与“反讽主义者”不同私人完美路径的实质区别。罗蒂把青年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普鲁斯特都看作反讽者。但在罗蒂看来,他们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罗蒂把前面三位哲学家称为“反讽主义理论家”,而把普鲁斯特这样的小说家称为“一般反讽主义者”。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区分,是因为罗蒂认为前面三位哲学家身上还有挥之不去的传统哲学形而上的味道。罗蒂说:“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杜撰了一个大于自我的主角,利用这个主角的生涯来界定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乃是他们三人与普鲁斯特的真正不同之处,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是理论家而不是小说家,是观照大事大物的人,而不是建构芝麻小事的人。虽然他们三人都是道地的反讽主义者,而不是形上学家,但是他们都还不是彻底的唯名论者,因为他们都不以安排芝麻小事为满足,而想要描述一个巨大无朋的东西。”[2]143在罗蒂眼里,“反讽主义理论家”的自我创造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不是要使自己焕然一新,而是要使前辈哲学家的理论焕然一新。所以,在罗蒂看来,“反讽主义理论家”其实面临着一个矛盾和尴尬:理论要求他们实现形而上学最后留下的可能性,达到一种严肃和崇高,而自我创造要求他们开创新的可能性,时时刻刻进行自我解构。在罗蒂看来,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因对“伟大形而上学家的那种崇高严肃性”的迷恋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明信片》为代表作品的后期德里达将哲学理论私人化,以抛弃理论的方式才彻底解决了“反讽主义理论家”的难题。
四、反讽之后,走向团结
私人完美是一种自我创造的完美,苏格拉底、克尔凯郭尔、尼采等都是私人完美的典范。但是,罗蒂也注意到了这种私人完美存在的问题:一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或坏的政治制度对私人完美的限制和打压,一是私人完美对他人或社会潜在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死涉及前一个问题,而克尔凯郭尔与恋人及基督教会的关系涉及后一个问题。罗蒂把上述限制与伤害称为两种残酷。通过解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罗蒂更全面诠释了他所言的两种残酷。他认为,前一部小说揭示的主题是极权主义对私人完美产生的残酷,后一部小说揭示的主题是私人完美对他人及社会产生的残酷。罗蒂坚持认为,残酷是社会团结最大的敌人。为了减少残酷,维护社会团结,在私人完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意避免两个问题:第一,该如何避免私人完美对他人或社会的伤害?第二,该如何避免一个坏的共同体或坏的制度对私人完美的伤害。避免前一个问题,罗蒂认为,要提高我们对伤害他人而使他人产生痛苦的敏感度,扩大我们的道德同情心,要多倾听他人的语言并予以尊重,一旦我们进入公共生活,我们要将追求私人完美的语言转换为保证公共团结的语言;避免后一个问题,罗蒂认为,我们要努力地“筑就我们的国家”,要从对共同体消极的批评转变为积极的建设,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上述应当规避的两个问题最终可归于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建构一个好的共同体,而该共同体能为我们私人完美提供好的条件与空间。每谈及此,罗蒂总是对“我们富裕的北大西洋民主社会”倾心不已,认为它为私人完美和社会团结提供了条件和空间。罗蒂认为,私人完美与社会团结的基础不是某种哲学理论,个体拥有好的经济状况、好的教育程度、好的安全及休闲环境,这才是私人完美和社会团结的关键。抽去私人完美与公共团结的哲学基础,批判传统哲学并把政治、经济等置于哲学之先,罗蒂的这种思路被人批评为虚无主义,罗蒂回应说,这种思路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社会希望”,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于罗蒂的这一思路,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把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与一种爱国主义的传统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实现了一种哲学—政治的互动[7]。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反讽时代”[8]。身处这样的时代,研究罗蒂反讽概念与私人完美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个方面看这一研究的意义。对私人领域而言,反讽否认了本质和真理的存在,它推崇个体的自由创造,罗蒂坚持,应该给私人创造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条件,这一点启示,在缺少私人空间的东方社会,显得尤为珍贵;另外,对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反讽的姿态无疑是对迷信权威、迷信传统、迷信真理等因循守旧之风的当头棒喝;还有,在雅斯贝斯所谓的“技术性的群众秩序”[9]的时代背景下,人之生存受物质、技术及大众文化的压榨而变得非个体化、非精神化,作为个体自由最重要内容的精神创造遭到了扼杀,运用带有个体独特印记的语言塑造自己,促进个体之精神成长便是一个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反讽让我们重视了人对自己的义务,是对我们精神成长的召唤、提醒和激发。对公共领域而言,私人完美有对他人或社会带来残酷的可能,而残酷是社会团结的最大阻碍,罗蒂认为,残酷的减少既要靠我们同情心的提升,也要靠共同体的建设,更多的经济、教育、安全与休闲的机会才是私人完美与社会团结的保障,因此要努力地“筑就我们的国家”。罗蒂的这种思路启发我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互动。
[1]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M].汤晨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董山民,陈亚军.罗蒂的“自我观”及其政治意蕴[J].南京社会科学,2008(4):12-18.
[4]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9.
[5] 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M].张国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6]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81.
[7] 黄泰轲.理查德·罗蒂论在叙事中成就私人完美与公共团结[J].唐都学刊,2015(4):28-33.
[8] 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4.
[9]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4.
[责任编辑 王银娥]
Richard Rorty’s Concept of Irony and Personal Perfection
HUANG Tai-ke
(ResearchInstituteofEthiccultur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Plato, the world is a world of essenc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are based on the discovery of nature. Rorty,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er, thinks that any attempt to perfect one’s life by discovering essence is a kind of disillusion, With the concept of irony, Rorty criticizs the essentialism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believing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is full of accidental coincidence, creation instead of discovery is the key to personal perf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personal perfection, Rorty also reminds us of the individual obligations for the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solidarity. By revealing the concept of irony and emphasizing on solidarity, Rorty combins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ism with the traditional patriotism.
Richard Rorty; irony; personal perfection; public solidarity
B712.6
A
1001-0300(2016)03-0116-06
2015-12-03
黄泰轲,男,湖北罗田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伦理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