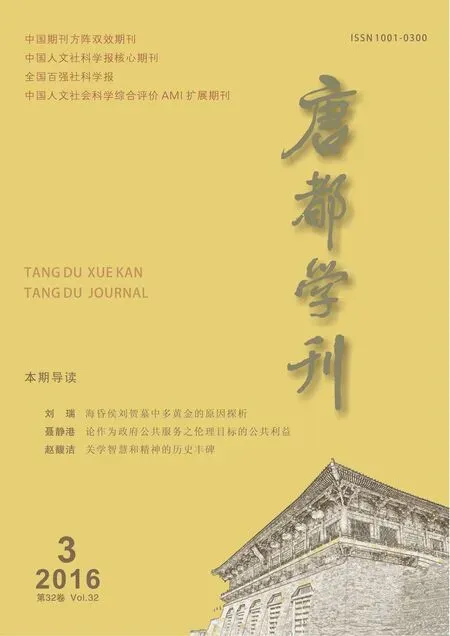《三侠五义》叙事写人的现代价值发微
2016-02-02冯媛媛
冯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三侠五义》叙事写人的现代价值发微
冯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传统小说的某些内蕴和议题,一旦遭遇理论的撞击,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三侠五义》正有这样的特点。首先在叙事形式上,它的“平话习气”,体现的是叙事的“平民化”立场。这是对“文体等级”的颠覆,对“平民文学”的回归。在这种“平民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叙述的“民主化”倾向。这里所谓的“民主化”,是就其内在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精神而言的,专指一种“文化型态”而非政治概念。其次在人物塑造中,“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也不可有我”的观照视角,体现的恰是一种摆脱了“主体性原则”的“他者性原则”。它不但可为当今的小说创作提供一种借鉴,也可为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建立人际关系,提供一种具有现代价值的本土资源。
《三侠五义》;叙事特点;人物塑造;平民文化;他者视角
王德威先生指出,在古典的议题中蕴含着庞大的论述能量,“一旦遭遇现代、西方文论的撞击,自然应该产生日新又新的意义”[1]。此说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那么若以此来重新观照《三侠五义》系列小说*本文将《三侠五义》及其由此而来的《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同一系列的小说,统称为《三侠五义》系列小说。便会发现,虽然自从它们问世以来便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尤其在晚清可谓形成一股侠义小说热,但在今天的艺术评价中,却地位不隆,尚达不到“经典”的高度,但就其叙事特点与形象塑造两个方面而言,却内蕴着新的意义与价值。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另辟蹊径,对之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使其在小说史上的创新之处不致被遮蔽,现代性价值不致被淹没,也为艺术特征的分析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以打破就文本论文本的习见套路和自说自话的描述性方式。
一、叙事的“平民化”立场及其“民主化”倾向
其实在批评界,对《三侠五义》及其系列小说在艺术上的长短,因观照问题的角度不同、视界融合的程度不同而评价有异。问竹主人以让步的方式评曰:“虽系演义之词,理浅文粗,然叙事叙人,皆能刻画尽致,接缝斗榫,亦俱巧妙无痕,能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2]359尽管对其不无好评,但首句则明显是站在“正统”的立场上,视“小说”为“小道”而已,说其“文粗”,也是以文人的眼光和趣味为准作出的评价。今天的评论,在立场和趣味上,虽不能说与之完全相同,但实际上并无多大的差异,所以它们始终难以完全进入研究者的视界并获得认同。对此,我们不妨转换视角,从它的文体特征和叙事的“平民化”立场入手,它的独到之处,或可得到彰显,而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等级之分和纯粹的艺术判断上。
众所周知,《三侠五义》原是民间艺人石玉昆的说书文本,后来虽经文人的加工和重新命名,但其“平话”的风格却得到了保留。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本是茶馆中说书,别开生面,很是新奇,于是,后来能文的人,把它写出来,就通行于社会了,而且流行得特别快,特别盛。”[3]这是探底之论,并旁涉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和它所以受欢迎的原因。它的“别开生面”的趣味,实则是对正统文学所规定的“文化区隔”的颠覆和突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一切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以及阅读)以及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都首先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它所预设的便是各种趣味(tastes)发挥着阶级(class)的诸种标志的功能。……必须看到,正是文化实践的难以估量的作用区分了种种不同的、有高低之别的文化习得(acquisition)模式。”[4]8-9他指出,日常生活的所有的文化实践和符号交流所体现的“趣味”倾向,都是社会“区隔”的表露。“趣味进行区分,并区分了区分者。生活主体由其所属的类别而被分类,因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区隔区别了自身,如区别为美和丑、雅和俗。”[4]12“区隔”设置边界,划出高雅趣味和低俗趣味、肤浅快感与纯粹快感的等级和界限,从而“建构了文化的神圣空间”,实现让“社会差异合法化”的功能。这也就是说,“被建构的文化等级一方面区分、分隔不同的阶级、阶层,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被人为建构的区分标准经符号权力合法化,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效果被社会成员信奉为天然如此的自然等级”[5]。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非随意套用西方的观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本就是一个讲究尊卑有等、伦常有序的社会,扩而大之,在一切领域均有等差的区分与设定,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被学界广为称赞的概念,即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差序格局”,这一格局其实就是“区隔”的划分与建构,这不仅表现在社会领域,也表现在文学审美领域。
问竹主人因《三侠五义》“系演义之词”,便有一种先入之见,从文体等级上为其做了“区分”;紧接着“理浅文粗”的评价,也是由上述文体等级所建构的文化“区隔”而作出的“趣味”判断。他下来的好评倒是窥探到了该书的叙事特点,而这种特点,用布尔迪厄的观点看,恰在客观效果上是对“区隔”等级的冲决与颠覆。所谓“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的语言选择和叙述方式,亦恰在客观效果上构成了对“趣味合法性”的质疑,对其所代表的“符号权力”的解构。
鲁迅先生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评曰:“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6]273这分明是为“大众化”趣味张目,并就其小说史意义而论道:“(《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儿女英雄传》亦然,……特有‘演说’流风。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6]278就结构而言,平民大众并不会去关注这些文人的欣赏习惯,对他们来说,只要故事新奇,合乎他们的欣赏趣味就足够了。这种“别开生面”的叙述形式,这种生趣勃勃的演说风格,这种粗豪脱略的风神气韵,不正是对“贵族趣味”的颠覆、对“欣赏习性”的解构、对“文体等级”的冲决、对“平民文学”的回归吗?
这里还有必要引述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的一段论述:“‘五四’以后的小说论者,所欣赏的都是文人小说家而非民间说话传统,所偏爱的小说也仍以文采可观者为主。至于小说的写作,亦复如此。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曾指出:现代小说不是比古典小说更大众化,而是更文人化;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小说形式感的加强及小说人物的心理化倾向,全部指向文人文学传统而非民间传统;小说书面化的倾向,也转变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五四’以后的小说评论者,虽然在理念上宣扬民间通俗文学,以打倒贵族山林文学;但他们作为一高级文化人,在文学品味上却很难认同平民文学。所以这其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矛盾。……推崇纯文学、贬抑通俗文学,推崇文学、贬抑说唱的艺术位阶,正是近代论小说者的通病。”[7]这也可以说明,此种文体的等级观念和它所设置的“文化区隔”,一直掌控着我们的价值评判和艺术评判,阻挡着我们的眼光,影响所及,至今未变。
那么《三侠五义》的叙述形式究竟有何特色呢?上已述及,《三侠五义》既来自于“说话”,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说话”的痕迹,保留了“平话”的某些文体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已遭到文人的修改,脱去了现场传诵的效仿模式和“虚拟情境”*韩南教授曾将古典中国白话小说对说话形态无休止拟仿称为“虚拟情境”,意谓“假称一部作品于现场传颂的情境”。对此的论述,见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0页。,但“且说”“话说”的开端语,依然历历在目,说话的叙事习性依然分明。《三侠五义》的修订者俞樾即看出了这一点:“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8]此处以柳敬亭说书作比,颇能抓住“说话”的特点。对此,我们无须多言。这里要讨论的是,这种“平话”式叙事所体现的文化,我们可称之谓“平民文化”。而“平民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叙述的“民主化”倾向。这里所说的“民主化”,主要是与“贵族化”或“雅正观”相对,就其内在的文化立场、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而言的。
丹尼尔·贝尔在讨论现代性症候时,曾涉及“天才的民主化”问题。他指出:“强调艺术中的等级观念和读者、观众的文化分类(例如:高雅人士、中流人物、下里巴人)观念,……其中势必蕴含着对标准的捍卫、确定这些标准的一种职业——也就是批评——的看法。”[9]178他通过对20世纪40至60年代批评变化的勾勒,说明“在这一切现象中,有一个文化的‘民主化’问题。因此不能说什么东西高级或是低级。这是一种风格的融合。”[9]180弗雷德·英格利斯也指出:“塞拉·本哈比重新定义了民主的领域,认为其既是政治性的又同时具有文化性。”[10]余英时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也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民主仅仅看作是一种数量的政治,或者仅是一个政治体制,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型态。”[11]笔者采用这一概念,也正是从“文化型态”和“叙事伦理”的角度立论的。
回到本文中来,让我们先从“平话”的定义说起。“平话”亦作“评话”。何谓“平话”?一般解释谓,“平”是“评”的简写,有评论、评议之意,合起来即讲史而加以评论[1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之解释为:“‘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13]现在我们尚不能断定哪种解释更合理,但这种“平常口语”的使用和“平易”的文风,从文化精神上看,正是一种“平民”立场的体现。这种平民立场,使它在叙述形态上是“民主协商”的,而不是“独白”的,尽管说话人时常以“看官听说”的方式进行说教,并对事件作出裁判,但他或他们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听众对话,其中包含着对听说者的尊重。换句话说,他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硬性强加给接受者,而是通过具体事例的导引,以“民主化”的叙述策略,让其自然而然、心悦诚服地接受。因而不是“独白型”的,而是“对话型”的。在这种“对话型”的叙述方式中,“说话人”与“接听者”的直接沟通,既有利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开展,又可培养接听者(或读者)的审美兴趣,调动他们对故事背后意义的探寻和发问。
就叙事者“说话人”而言,与普通文本的“作者”也有很大的区别,王德威先生引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说,说话人的声音是“一个集体的、匿名的声音,其源头是一般人的知识的总合”[14]。因之相对于“作者”而言,它富有“公共性格”或曰“大众化性格”,与“作者”的私人创作界限分明。职此之故,我们可以引申说,说话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体现的是平民的社会诉求和审美趣味。鲁迅先生说《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从此一角度看,正是对它的“话语诉求”的揭示和“公共性格”的彰显。所以,“平话”是由“平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正因为大众掌有了叙事权,所以它也是对文人话语霸权的抵制,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在叙事风格和美学趣味上,打破了正统文学所遵循的“雅正观”。本文所谓的“民主化叙事”,即是对这种大众叙事特征的一种描述,对其文化身份、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的一种揭示,对其深含的叙事伦理的发掘。市场有市场伦理,做人和做事有道德伦理,叙事也有叙事伦理,它规约着叙事的立场和方法。另在具体故事的叙述中,常以“你道如何?只因……”“你道此人是谁?听我慢慢叙来”等方式,拉近说话人与接听者的距离,使听众(或读者)产生与故事的亲近感。段与段之间,常用“且说”领起,用“再说”过渡。这些方式,虽出自说话的套语,但正是在这一套语中,在在表明叙事者与听众(或读者)的对话关系,隐藏着“平民化”的立场和“民主化”的文化精神。
也正是因为《三侠五义》在叙事上保留了“说话”的特点,具有精神上的“民主化”倾向,才能在民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除了前引问竹主人的《忠烈侠义传序》外,同时代的入迷道人也说道:“虽系演义,无深文;喜其笔墨淋漓,叙事尚灭冗泛”[2]361。这正如前文所列俞樾所言:“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当然,“如此平话”也得自于后来文人的修改润色。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人的参与创作,并非对前者进行简单的抛弃,而是仍然保持了平话的“叙述声音”和“叙述形式”。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特点及现代意义
《三侠五义》系列小说在侠客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有着独特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这些侠客不仅行为粗豪,具有显著的侠义风范,而且一个个性格鲜明,极具特色。这不可不谓是《水浒传》之外的又一高峰。
在众多的侠客中,性格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无疑要数“锦毛鼠”白玉堂了。小说曾借另一人物丁兆蕙的视角,如此来描述白玉堂:“惟有五爷少年华美,气手不凡,为人阴险狠毒,却好行侠作义,就是行事太刻毒,是个武生员,金华人氏,姓白名玉堂,因他形容秀美,文武双全,人呼他绰号为锦毛鼠”[15]147。书中曾记述一事:白玉堂因为不愿意在名号上向展昭服输,因而专程来京向展昭挑战,卢方也曾问他:“(与展昭)既无仇隙,你何恨他到如此地步?”白玉堂说道:“小弟也不恨他,只恨这‘御猫’二字。我也不管他是有意,我也不管是圣上所赐,只是有个‘御猫’,便觉五鼠减色,势必将他治倒方休。如不然,大哥就求包公回奏圣上,将南侠的‘御猫’二字去了,或改了,小弟也就情甘认错。”[15]210白玉堂的这一好强任性的行为,显然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有关。为了说明这一点,小说还专门就他的“挑战”心理做了详细的展示:“我看姓展的本领果然不差。……圣上只知他的技艺巧于猫,如何能够知道我锦毛鼠的本领呢!我既到了东京,何不到皇宫走走,倘有机缘,略略施展施展。一来使当今知道我白玉堂;二来也显显我们陷空岛的人物;三来我做的事圣上知道,必交开封府。既交到开封府,再没有不叫南侠出头的。那时我再设个计策,将他诓入陷空岛,奚落他一场:‘是猫儿捕了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哪怕从此倾生,也可以名传天下。”[15]187于是他不惜做下几件大事:夜闯皇宫题词、大闹庞府、夜入开封府偷盗走“三宝”,终于成功将展昭引入陷空岛。可这一切他仍不满足,于是在他用机关将展昭拿下后,又要求展昭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从他手中抢回开封府“三宝”。这一略带“游戏”成分的做法,既有“个人英雄主义”的风格,又有“草莽英豪”的率真个性。二者互为因果地结合在他的身上。最后,经过一番周折,白玉堂才被众义士与包公感化,并获得皇上的赏识,钦封四品护卫,他也因此而名扬天下。
然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行径既带来荣耀,也为他带来厄运。蒋平在白玉堂四处寻觅展昭之时,就已经预言了他的下场:“五弟未免过于心高气傲,而且不服人劝。……据我看来,唯恐五弟将来要从这上头受害呢!”果不其然,在随颜大人征讨襄阳王时,他曾两度夜探襄阳王藏匿盟单的冲霄楼,终因“铜网阵”机关重重而不得不罢手。其后,因他的自负与疏忽,使颜大人丢了印信,白玉堂倍感无颜,顿生盗取盟单、将功补过之念,于是便不辞而别,三探冲霄楼。这种急于立功的欲望,让我们再次看到白玉堂的“个人英雄主义”特点,而“个人英雄主义”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我能解决一切”,但也终因“心高气傲”、过于自负而为之带来杀身之祸。
胡适先生就非常叹服小说对白玉堂这个人物的塑造,他在《〈三侠五义〉序》中指出:“白玉堂的为人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这正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向来小说家描写英雄,总要说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样,所以读者不能相信这种人材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叫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理近情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向来小说家最爱教他的英雄福寿全归;石玉昆却把白玉堂送到铜网阵里去被乱刀砍死,被乱箭射的‘犹如刺猬一般,……血渍淋漓,漫说面目,连四肢俱各不分了’。这样的惨酷的下场便是作者极力描写白玉堂的短处,同时又是作者有意教人爱惜这个少年英雄,怜念他的短处,想念他的许多好处。”[16]299-300这确是《三侠五义》在人物刻画上的高明之处:侠义英雄毕竟不是“神”,他的短处和长处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有长有短的性格刻画,正是侠客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该小说所透显的现代意义之一。
英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指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接受伟大人物的方式。凭人们确实的直觉会感到在伟大人物身上总有某些神一般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否把他当作神、当作先知或者其他什么,这倒是一个重大的问题。”[17]47只要我们将其中的“伟人”转换成“侠义英雄”,此话也颇适用于对侠义小说中人物的评价。通过白玉堂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大致窥探出时代对侠义人物的接受方式及其认识观念的变化。概而言之,如果把唐传奇及其受其影响的部分小说中的侠客,视为对“侠客崇拜”的第一阶段,有明显的“神化”特色;那么,至《水浒传》及《三侠五义》,则可视为对“侠客崇拜”的第二阶段,他们已被充分“人化”了,侠客已不再被信奉为来去无踪的“神道异人”,而是有着诸多短处的真实的原本的人。托马斯·卡莱尔说:“对英雄的崇拜总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形态,但是任何时代都难于做得尽善尽美。实际上人们可以说,时代的所有任务的核心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17]48扩而大之,小说创作不也是在努力做好这件事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大批“个人英雄主义”,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言:“对于伟人完全盲目地沉浸在爱戴和敬慕的狂热状态,并非好事。但是,同样盲目地,而且是非理性地目空一切的冷漠,恐怕情况更坏!”[17]48白玉堂“争强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虽显现出极端的特点,且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但谁说这又不是他的可爱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正乃“侠”的精神所在,它所招致的灾难,也正是侠之“不爱其躯”(司马迁语)的行为表现。相较于小说中刻画的另一位侠客——展昭——的沉稳机智与顾全大体,白玉堂的个性更为鲜明生动,也更富有人民心目中“侠客”的特点。
在人物塑造上,与白玉堂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连贯出现在《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三部小说中的小侠艾虎。尽管其急于立功的“个人英雄主义”心理,与白玉堂如出一辙,但与后者心高气傲、略显狭窄的心胸相比,他的性格更显圆通一些。他的出场,与其师父智化的设谋有关:为了“与国家除害”,将奸臣一网打尽,需办四件难事,其中最难之事则是要一人去开封府诬告四指库总管马朝贤与襄阳王有私通的“奸谋”,并偷盗圣上的九龙冠,艾虎小小年纪,挺身而出,主动应承了此事,并说明自己承担此事,就会有三桩益处,前两桩是谈自身固有的便利条件,而第三桩则涉及他的内心动机:“第三益却没有甚么,一来为小侄的义父,二来也不枉师父教训一场。小侄儿若借着这件事出场出场,大小留个名儿,岂不是三益么?”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听后,拍手大笑道:“好!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这一“志向”,使他后来在看见开封府的阵势后,虽也心惊胆战,两股栗栗,但却提醒自己:“你为救忠臣义士而来,慢说铡去四肢,纵然腰断两截,只要成了名,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来”。“成名”正乃“个人英雄主义”心理的流露。之后在随颜大人平息襄阳王叛乱的过程中,艾虎为求立功,时常单独行动。一次,颜大人被沈仲元掳走之后,众人商议如何寻找,艾虎听闻后,私自一人上娃娃谷寻访。小说于此特别写道:他“岁数虽小,心高气傲,自己总要出乎其类的立功”。后来,在众人破“铜网阵”之时,为了争取头功,他依然如故,不服分配,偷偷行动,一心想着将“盗盟单”“盗王爷”两件事全办了。
除了上举二人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侠客,包括做事沉稳的展昭、诙谐刁钻的蒋平、机智伶俐的智化、深沉老练的欧阳春等,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套用金圣叹评《水浒》的话来说,真可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2]301。但一般来说,性格各异的描写,尚不算难事,更难得的是能于“同中见异”——如金圣叹所言,让读者看去,知他“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2]301。如对同以机智过人著称的“翻江鼠”蒋平与“黑妖狐”智化的刻画即是如此,此也犹如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所评的那样,其妙处“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18]。从小说史的角度看,这些显然是上承《水浒传》而来的,但它在理论上却有着不同凡响的现代意义。对此胡适先生有经典的评论和对比说明。他把该小说人物与《水浒传》做纵向比较、与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侠隐记》做横向比较之后,论道:“书中写智化,比蒋平格外出色。智化绰号黑妖狐,他的机警过人,却处处妩媚可爱。一百十二回写他与丁兆蕙假扮渔夫偷进军山水寨,出来之后,丁二爷笑他‘妆甚么,像甚么,真真呕人’。智化说:‘贤弟不知,凡事到了身临其境,就得搜索枯肠,费些心思。稍一疏神,马脚毕露。假如平日原是你为你,我为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须将你之为你,我之为我,俱各撇开,应是他之为他。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设身处地的做去,断无不像之理。’这岂但是智化自己说法?竟可说是一切平话家,小说家,戏剧家的技术论了。写一个乡下老太婆的说《史》《汉》古文,这固是可笑;写一个叫化子满口欧化的白话文,这也是可笑。这种毛病都只是因为作者不知道‘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一切有志作文学的人都应该拜智化为师,努力‘设身处地的’去学那‘他之为他’。”[16]301-302
撇开故事不论,其中被胡适高度赞扬的“你/我/他”之论,不仅是作者刻画人物的经验之谈,是造成“同中有辨”的主要原因;而且只要稍作引申,其中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他者”视角——“既不是你我,必须将你之为你,我之为我,俱各撇开,应是他之为他。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也不可有我”。只要将此作一种现代的转换,其意义就能立刻得到彰显,它不但可为当今的小说创作提供一种借鉴,也可对“主体性”的反思提供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
众所周知,“主体性原则”(subjectivity)是现代思想的基本原则,“从思想语法上看,人们在思考‘我与他人’的关系时一直使用的是主体观点,即以‘我’(或特定统一群体‘我们’)作为中心,作为‘眼睛’,作为决定者,试图以我为准,按照我的知识、话语、规则把‘与我异者’(to heteron)组织为、理解为、归化为‘与我同者’(to auto)……这实际上是对他人的否定,是实施了一种无表的暴力”[19]。只有摆脱这种“主体性原则”,从他人的观念出发,才能演绎出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关系。这种“他者性原则”(the other-ness)是我们在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及建构人文知识时,必须遵循的立场和视角。从这一角度看,智化之所以名为“智化”,正以其超前的智慧来化解我们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痼疾。
综上所述,《三侠五义》不论是叙事的“民主化”倾向抑或写人的“他者性”视角,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均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63.
[2] 朱一玄编,朱天吉校.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M]∥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9.
[4]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G]∥朱国华译.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5] 张意.文化与区分[G]∥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0.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1.
[8] 俞樾.重编七侠五义传序[M]∥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广百宋斋石印本《七侠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
[9]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0]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M].韩启群,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6.
[11]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54.
[1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6-167.
[1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4.
[14]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2.
[15]石玉昆.三侠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7]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8]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M].凌赓,恒鹤,刁宁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8.
[19]赵汀阳.我们和你们[J].哲学研究,2000(2):25-34.
[责任编辑 张 敏]
Modern Value of Narrative Features and Character Portrayingin The Three Heroes and Five Gallants
FENG Yuan-yuan
(SchoolofLitera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Some implications and topics in the traditional novels, once collided with theory, will take on new meanings and values, which are typical of the novel, entitledTheThreeHeroesandFiveGallants. Firstly, when it comes its narrative form, its narration is featured by the civilian culture, which is a subversion of style grade and a restoration of civilian cultur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s its trend of democratization in narration. The so-called democratization refers to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and spirit, designated for a cultural pattern instead of a political idea. Secondly, in the character portraying, the perspective that “he is him, neither you nor I” reflects the otherness instead of subjective principle. It not only offers an example for today’s novel creation but also provides local resource for modern value for coping with others and establishing prop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ThreeHeroesandFiveGallants; narrative features; character portraying; civilian culture; onlooker’s angle of view
I207.41
A
1001-0300(2016)03-0122-07
2016-02-26
冯媛媛,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