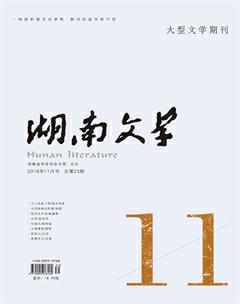话说长沙
2016-12-05宋元
宋元
我在长沙一辈子了。
五十年代至今,我与这座城市一同感受了无数欢欣、忧伤、或者困惑。我的思想的背景就是我所熟悉的山水洲城,我的人生经验得自于这块土地上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我的情感也全部由本地湘音来累积、丰富并传达。我对这座城市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
长沙城临江而立——许多城市都因水而生,有水,方能安居乐业,永续民生。长沙是中国唯一城址历三千年而不变的城市,屈贾之乡,楚汉名城。湘江由南至北,穿城而出,下洞庭,入长江,通四海。湘江多支流,泽润万顷,福被八方。
因此长沙气候长年比较潮湿。人们吃姜,一日三餐猛吃辣椒,事出有因。春天是漫长的雨季,细雨连绵,不仅适合植物努力向上,也促使人滋长出细致的诗情,以及对一切深厚遥远广大事物的不倦探究。从古至今,长沙出过大量艺术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有美诗美文,小桥流水杨柳依依,满目江南胜景。有对人生对社会对未来的忧虑,和缜密严肃的思考。学术上开宗立派,兼收并蓄,传承有序。更有一众英雄豪杰,以天下为己任,挥斥方遒,浴血沙场,成就大业。长沙勇敢地参与和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变革的进程。
长沙城虽处内陆,流逝的也只是平常日子,但长沙人喜欢操世界的心。
记忆当中,我对长沙最早的印象是湘江河里轮船汽笛的声音。那时我小,那时还没有湘江大桥,城市也不大。人员货物往返河东河西,主要靠轮船。到晚上,我缩在被窝里,总习惯尖起耳朵,屏声敛气听。果然:呜——呜——汽笛声悠长,雄浑,透出庄严,缓缓地一波一波,几乎传遍长沙城的每处角落。长沙的细伢子细妹子被如此辽远的汽笛声抚慰,做透明的梦,一天天长大。
七〇年代初,湘江大桥竣工。从此一桥飞架东西,是全城的大事。通车典礼那天,老百姓扶老携幼,争相目睹第一座大桥的身影。据说,桥梁的设计者为减小桥拱弧度,花费大量心思,尽可能让桥面变得平缓,因为那时汽车还少,城里马路上跑得最多的是板车。要是桥面拱起很高,固然结实 ,固然好看,但拖板车的工人就会比较为难,上坡费力,下坡容易出事。所以无论如何,这座桥大体上是平坦的。这是一座有人情味的桥。它应该是那些年最大的建设项目,花销一定不小,当日主事者,尽管权钱在握,仍念及底层穷苦大众的艰辛,有菩萨心肠。
我一个叫冯建国的小学同学,他爸爸就是拖板车的。冯建国经常挨老师骂,因为他旷课。他旷课是因为他帮他爸爸推板车。他爸爸虽然从事这个全靠力气的工作,人却矮小,需要加上他崽的劲。有次冯建国问我,想不想赚钱。我说想。于是跟他去推了一回板车。我们班好多同学都跟他推过板车。记得我们先是到松桂园的煤栈,叫四煤栈,装满满一车煤。他爸爸打赤膊,精瘦,腰上扎着绑带。深蓝色的绑带勒得很紧,在他腰杆子上缠了好多圈。这是长沙板车工人的标准打扮,据说这样不容易受伤。他拿铲子使劲往车上拍,把煤拍紧实,“啪,啪,啪……”可能他想尽量多装点,也可能是怕一路上煤掉下来。好不容易车装好了,我和冯建国并排站到车后,伸出手,刚准备要用劲推,只见冯建国的爸爸忽然扭回头来,脸特地朝向我,抱歉样的笑了一下。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他的脸真是墨黑,显得牙齿比较白。板车经过老火车站,爬到浏城桥岭上,我已经通身大汗,嘴巴张到最大拼命喘气,连腿肚子都要抽筋了。我累得脑壳一片空白,那车煤最后拖到了哪里,根本搞不清方向。但确凿无疑的是,我看见冯建国的爸爸开始解绑带,一圈,一圈,又一圈。那条绑带已经变成黑色,湿沥沥的浸透了汗水。在绑带的尾端,有个夹层,冯建国的爸爸把乌黑的手指探进去,掏出一个五分的硬币递给我。那枚上面沾着煤屑的硬币,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它是我平生挣得的第一桶金。
后来又传说,湘江大桥修好后,毛主席还亲自到桥上看过。传说毛主席在桥中间下了车,走一阵,扶着栏杆眺望。他这是故地重游。他看到了什么?他会想些什么?大概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长沙的形势比较复杂,全中国的形势都比较复杂。以后有湘江二桥、三桥、四桥……桥越修越大,越修越多,轮船渐渐稀疏,汽车开始汹湧。
天气好,人们在河东可以望到河西岳麓山。秋天甚至能直接欣赏到山腰和山顶的红叶,很斑斓的色彩,有中国画浸染的味道。隔岸观景,是长沙的特色,是一般城市难得的境界。湘江中间有橘子洲。橘子洲像条露出背脊的大鱼,安静地卧在水的中央。洲上确实四处栽得有橘子树,橘子开的花小,白色,星星点点落满一树。刚出世的橘子油绿,绿到发亮,变成墨绿,橘子慢慢饱满,大到足以引诱嘴馋的孩子。我读小学和中学,都有同学因为到橘子洲偷橘子被抓,等他们放出来,脸上就多了角色样的高人一等的神气。橘子洲一度还是最好的天然游泳场。沙滩干净细白,踩上去,脚板底下软软的,麻麻的,像挠痒,于是放肆踩。还在很小的年纪,大概刚发蒙,我就在橘子洲学会了游泳。踩水,蛙泳,仰泳,自由泳,随便。长沙人大多在这里开始第一次体验水性。我最喜欢仰面朝天躺在水上,望蓝天白云,觉得江很大,人很小。好大一江水托着身体,轻轻摇晃,人就有些恍惚……想起以前娭毑天天晚上带我睡觉,跟我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我可能有点调皮,十四岁那年,居然瞒着家人,和几个同学打遛票坐火车到武汉,一口气从武昌游到汉口,不在话下。横渡长江,仿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举动。只是以后想起,觉得多少还是有危险——站在武昌这边,隔着长江望汉口,根本看都看不清,远得很。我一直觉得,湘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作用,总是给我信心和勇气。别的城市也有河流,别的城市的少年也到河里游泳,但长沙似乎另有不同。我和小伙伴们在橘子洲游泳,常常会不晓得受了什么刺激,无端就兴奋起来:“自信人生二百岁,会当击水三千里”;或者,“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丛林尽染……”我们用童稚的声音,发出近于老成的感慨。这是为什么呢?说不太清,也许因为,我们从小最早接触的诗句,就有关岳麓山有关湘江,也许仅仅因为,这里是长沙的缘故。这里可能更容易生长激越浪漫的情怀。
长沙因为依偎名山大川而得天独厚,声名远播。岳麓山云麓宫有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这是登高远眺的姿态,胸襟开阔,写得很有气势。山脚下盘踞着可以上溯千年的岳麓书院。书院又有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就不是一般的气势了,是指点江山,踌躇满志,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岳麓山脉,于是汇聚世代文气,积蓄万千志士仁人修养,酝酿惊天动地事端。即便一般市民,无论学识多寡,只要问及本地人物,通常能道出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长沙人普遍愿意以自己的城市为骄傲,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座城市的历史,仰仗推动这座城市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辈伟人。这是长沙城的荣耀,和长沙人的荣耀。
自然而然,长沙人得意于动辄文治武功,往往偏重人的精神,执意于胆识和气魄,总之不甘寻常。
若因此就断定长沙人好高骛远,言过其实,却又有失公平。细细一想,长沙人倒是极为务实,简直实在得很。这里历来顽固地沉积着浓厚的市井气息。长沙城日常与世俗的一面,只消到蜘蛛网一般牵连的巷子里走一趟,就不难感受。
长沙多巷子。北京叫胡同。北京的胡同大多宽而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理直气壮的派头。长沙的巷子不同,都比较节制,并不太宽,而且明显缺少方向感,弯来弯去,有点信马由缰随遇而安的意思。不熟地理的外地人到长沙,只要进巷子,很容易迷路。不过那些巷子的名字,倒是真正有味。拿我去得多的地方举例,比方:荷花池、小瀛洲、凤凰台、斗姥阁、赐闲湖、惜字公庄、西园百里……每个地名都好听,漂亮,文雅,都应该藏得有曲曲折折故事。
我有个叫张咏絮的初中同学,家住水月林——水月林,一听就是几多有味的去处。水月林就是条不宽的巷子,平房一幢挨一幢,青瓦,白墙,或者别的颜色斑驳的墙。也有两层楼的,不多。有的人家坦荡,房门随时随地敞开,展览自己的休养起居。张咏絮家里有道矮围墙,推开木栏杆进去,是个小院子,栽得有一棵梧桐树。树很高,比屋顶高出一截,我有时和张咏絮就坐在树底下讲话。梧桐叶子很大,一片挤一片,在头顶上沙沙作响。我们讲同学的事,老师的事,长沙城里各式各样大情小事,常常一直讲到他妈妈喊吃饭。张咏絮的妈妈是河西裕湘纱厂的纺织工,三班倒,她下晚班回家也不睡觉,忙出忙进,洗衣浆衫,煮饭炒菜。她对我很好。或许她觉得,她的崽同我玩得好,就有理由也要对我好。她特别会炒菜。我吃过她做的各种菜,其中最精彩的是青辣椒炒肉。那碗菜一旦端上桌,肯定就要制造隆重的气氛。它太好看了,辣椒鲜绿,肉片又匀又薄,稍微卷曲着,散发出油亮的酱色,在辣椒和肉片之间,埋伏着白嫩的细如米粒的大蒜籽。并且,当然,浓烈的香味即刻充满了整间屋子。张咏絮的妈妈老往我碗里夹肉,老是说,你吃,你吃。搞得我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回忆起在张咏絮家吃饭的情形,心里还是觉得温暖。张咏絮的爸爸是条壮汉,不大作声。他是交通机械厂的车工,开C618的车床。我从他那里晓得世界上有种叫C618的车床。不过他似乎更喜欢做木匠。碰到别人不要的木板子、木棍子,都捡回来备用。他在院子里锯,刨,凿,吭哧吭哧的。斧头挥起来时,他手臂上的肌肉就一棱一棱地滚动。他家的平头床、五屉柜、书桌、吃饭的四方桌、靠背椅,都是他一件件亲手做出来的。这些家具还薄薄地上了油漆,又被张咏絮的妈妈反复擦拭,显得干净明亮。这个家里,好像永远洋溢着一种既辛劳又温饱的气息,大概可以算作那个时候长沙一般人家的缩影。吃过饭,我和张咏絮要不跑到外头玩,要不就听他外公讲话。张咏絮外公脚不好,走路拄拐杖,他多半时间都坐在一张竹靠椅上,头发不多,话多。他跟我们讲得最多的是长沙会战。他讲他参加过长沙会战,是正规部队的二等兵。他讲:长沙这一带地形以丘陵为主,黄土多,土质粘硬,修防御工事费时费力。讲:部队配的工兵铲不得力,搭帮附近老百姓送来很多锄头,进度才加快。讲:仗打得很激烈,烟雾冲天,死伤无数,可怜死的多半是十几二十岁冇结过婚的年轻伢子。讲:炮弹落下来之前,天上会嘶嘶作响,然后再轰——,耳朵嗡嗡乱叫,会要聋样的。讲:敌人的司令官是冈村宁次,这个人赫赫有名,不过他在长沙会战算是真正碰到了硬钉子,我们反正不怕死,要死卵朝天。张咏絮的外公讲一口老长沙话,他讲日本鬼子是“日本拐子”,所以他左一个“日本拐子”,右一个“日本拐子”,听得我只想笑。我头一回听说,还有不是八路军的军队打日本人,开始根本还将信将疑。不久,我就有了更大的疑惑,因为文化革命了。学校停课,我和张咏絮不必读书,日日在街上乱跑。到东风广场看集会游行,到五一路市政府门口看大字报,还在青少年宫的批斗大会上撞见了张咏絮的外公。他外公五花大绑,颈根上挂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国民党残渣余孽。毛笔字很黑,张咏絮的脸瞬间刷白。他外公和几十个挨斗的人跪成一排,打得满脑壳血。参加斗争和看热闹的群众混做一堆,人山人海,口号震天。听说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也在搞批斗,斗老师,斗书记和校长,揪出一大批牛鬼蛇神。我们校长是老地下党,但逃不脱跟张咏絮的外公一样,打得满脑壳血。五一广场发生激烈的武斗,通晚枪声大作,湘绣大楼起火,红彤彤的火光照亮了夜空。
随后我娭毑也成了逃亡地主,从宿舍赶出来,流落街头。她在离清水塘不远的炮队后街,靠着别人家的院墙,用几根竹篙和油布,搭了个栖身的棚。我去看过她,有次去正碰到落大雨,棚子里面同外头一样水汪汪的。她从头到脚都淋湿了,一脸愁苦,嘴巴扁着,像要哭的样子,坐在板凳上发抖,什么话都讲不出来。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额头上一道道很深的皱纹,心里又急又怕,却拿不出半点办法。我担心她很快会死去,结果,真的。几天后,我东寻西问,在现在的建湘路,当时的老汽车东站对门一个小院子里,找到火葬场驻城办事处。隔着很高的柜台,我把户口本递进去。里面的人十分惊讶,问:怎么来你一个细伢子?你屋里大人呢?我不做声,我不想跟他们讲我父亲关起来了,我只能独自处理我娭毑的后事。似乎我也不怎么悲伤,只是无助。我在炮队后街等一阵,来了辆三轮摩托,跳下两个戴口罩的人,把我娭毑放到一个绿色的铁皮盒子里,然后三轮车突突突响,冒着烟,一转眼就不见了。直到这个时刻,我好像才醒过来,我再也没有娭毑了。我的胸口像被什么扎过一样痛。我是我娭毑带大的,我自己现在也是老人了,有时半晚做梦,还会想起她。我娭毑是宁乡人,几岁就卖到了祖父家里,做童养媳。她裹过脚,所以是小脚,走起路来身体总是往前探,步伐格外快,好像前面永远有十万火急的事似的。她手脚不停做了一辈子的事,吃了一辈子的苦。
和中国所有地方一样,十年浩劫是长沙永远的痛,也是长沙人民永远的痛。为长沙的未来计,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没有理由忽略曾经的伤痛,不应该让长沙的记忆留有空白,历史出现断层。当我们念想那些共同经历过的困苦,会更真切地体会今日长沙的变化,晓得长沙的每一点发展,是如何样的得来不易。
就在几年前,我第一次从营盘路隧道经过,两旁灯光嗖嗖地扑面掠来,想到湘江正在头顶浩浩荡荡,跟千万年以来那样自顾流淌,心里难免惊叹,仿佛时空穿梭。长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老街拓宽,新路伸向四面八方,楼盘不断落成,城市迅速扩张。巨大的玻璃幕墙矗立,镜子一般映照出远近更多更摩登的大厦。还有新建的地铁、机场、环线。据说,不久长沙就会形成几纵几横的格局,完全不比广州、上海甚至北京差。虽然又有另外的意见指出,雷同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严重问题。
欣欣向荣是确实的。夹在现代建筑之间的老城区,似乎也找到了新的动力。古旧的巷子,民国时期的公馆,都演变成时尚。酒吧,咖啡馆,茶厅,文艺书店,小吃铺子,KTV,灯红酒绿。尤其夜市,隔好远都闻得到香气,生姜切得细细的,大蒜切得细细的,辣椒切得细细的,香葱切得细细的,五颜六色一律津津有味的式样,显出长沙人对日常生活热衷得近于苛刻的态度。于是衍生了城市的“市”,人在流动,钱在流动,商品在流动,服务在创新,竞争在升级,梦想在壮大,长沙得以似锦繁华。
长沙就是这样,无论何时,总能把理想与现实,宏大与琐碎,用一种淡定的方式,融合起来,包容共生。体会长沙的种种进步,我当然高兴,不过也有遗憾,要为我的表哥叹一口气。表哥略长我几岁,本在湘东老家种田,后来同一群老乡结伙,由包工头领着,到长沙打工。先在蔡锷路一处工地做小工,整天挖土,挑沙子,拌水泥,累得要死。不过他倒好像不在意,看上去,他比我健康,黑里透红,劲头十足。他说要放肆赚钱,他的女会读书,要送她读大学。我问他的女多大,他说小学二年级。我暗暗觉得不靠谱,才二年级,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到蔡锷路工地看过,表哥住彩条布围的工棚,四处透风,睡通铺。我指着起码睡三十个人的通铺问,这怎么能睡?他说能。他在那个通铺上睡了两年多。然后转到韶山路盖写字楼,到月湖修别墅,还参加过高铁站施工,南湖路改扩建,在各个工地辗转。二十年,我表哥在长沙打工,出过好多力,流过好多汗,还受过伤。他很少休息,怕扣钱。我们兄弟也见得少,他不肯麻烦我。前年春节他回老家,说不来了,再做吃不消了。所幸他的女争气,考得中南大学,又到复旦读研究生,已经开始上班赚钱。我送表哥到五一路火车站。在闹哄哄的候车室里,我叮嘱他时刻要看住行李,安检后记得收好身份证,小心钱莫被扒手扒走……后来我就闭嘴了,晓得自己讲的不过是些废话。我们于是沉默着,站在那里等,直到进站。表哥显老了,开始秃顶,脸色也不好。他背两个大号蛇皮袋子,努力朝前挤,很快被人流淹没了。我当时有点难过,觉得亏欠了他。也怀疑我们长沙,亏欠了很多像我表哥一样的人。
那天我在车站广场待了一阵。这里是长沙的标志性建筑。我听见钟楼响起熟悉的音乐,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楼顶直指天空的火炬,也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有的已经变了,有的还没有变,这就是长沙。记得当年建车站,我还来参加过义务劳动,懵懂青年一个,觉得什么事都好玩。那时的义务劳动场面热烈,响动很大,城里四面八方都来人,男女老少,不认得也不要紧,大家一队一队排好,蚂蚁搬家样的,把一块一块的红砖,从第一个人手里传到第二个人手里,再传到第三个人手里,一直传,一直传……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