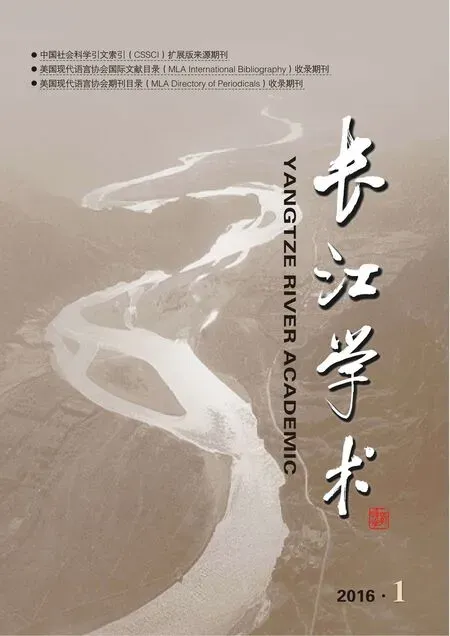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方法和理据之检讨
2016-12-05张峰屹黄泰豪
张峰屹 黄泰豪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方法和理据之检讨
张峰屹黄泰豪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以陈乔枞、王先谦为代表的清代学者所辑录的三家《诗》学佚文,成就卓著,影响甚大,迄今为学界所信重。但是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基本方法和理据——以师法、家法为依据安置佚文之归属,是不可靠的。前贤对清人三家《诗》辑佚成果虽有一些具体指摘,但未能从根本上清理他们的辑佚方法和理据。本文从清人对于三家《诗》学佚文归属之判断纠纷、汉代师法家法的实际情状两个方面,论析清人此一辑佚方法和理据的失误。
三家《诗》辑佚师法家法
蒐辑三家《诗》学佚文①宋清以来所谓“三家《诗》”者,其实也包括三家《诗》文本之异文在内,不止其《诗》说而已。惟因三家《诗》文本亡佚,其异文之情状,零星散存于各自《诗》解之佚文中。本文统称为“三家《诗》学”。,盖始于南宋王应麟《诗考》(一卷,列入其《玉海》附录)。《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王氏此著有“筚路蓝缕”之功,然亦指出其缺憾:“所引《韩诗》较夥,《齐》、《鲁》二家仅寥寥数条。”其后虽有元明学者陆续辑补,但不成规模体系。直到清代,才有了大规模的辑佚成果。
清代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学者较多,其中成就较大者,首先是一些辑佚专书,主要有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十卷②范家相:《三家诗拾遗》,有乾隆十九年会稽范氏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钱熙祚校本(此种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等。、阮元《三家诗补遗》三卷③阮元:《三家诗补遗》,有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叶氏郋园《观古堂丛书》本、清末李氏《崇惠堂丛书》本(此种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6册)等。、冯登府《三家诗遗说》八卷④冯登府:《三家诗遗说》清抄本,李富孙校(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6册),此著可代表冯氏辑佚三家《诗》的总体成就。冯氏还有相关著述多种:《三家诗异字诂》、《三家诗异文释》、《三家诗异文疏证》、《诗异文释》、《三家诗遗说翼证》。参见房瑞丽《冯登府三家〈诗〉著作考述》,载《文献》2011年第4期。、丁晏《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⑤丁晏:《诗考补注》,有《颐志斋丛书》本、花雨楼张氏校刊本(此种收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第108册)等。、臧庸《韩诗遗说》二卷⑥臧庸:《韩诗遗说》,《灵鹣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排印。、宋绵初《韩诗内传征》四卷补遗一卷⑦宋绵初:《韩诗内传征》,清乾隆六十年志学堂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5册。、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四十九卷⑧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有《左海续集》本(此种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6册)、《清经解续编》本等。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等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915年虚受堂家刻本,中华书局1987年据此点校排印。,尤以后二者最负盛名。其次,就是辑佚丛书之中的三家《诗》学辑佚部分,主要有:王谟《汉魏遗书钞》⑩王谟:《汉魏遗书钞》,清嘉庆三年金溪王氏刊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199—1200册。,辑录《鲁诗传》一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翼要》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⑪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光绪九年长沙嫏嬛馆补校本(此种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200—1205册)、光绪十年楚南书局刊本等。,辑录《鲁诗故》三卷、《齐诗传》二卷、《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薛君韩诗章句》二卷、《韩诗翼要》一卷;黄奭《黄氏逸书考》①黄奭:《黄氏逸书考》(又名《汉学堂丛书》),1934—1937年江都朱长圻据甘泉黄氏版补刊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206—1211册。,辑录《鲁诗传》一卷、《齐诗传》一卷、《韩诗内传》一卷;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②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稿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206册据此影印。,辑录《鲁诗韦氏说》一卷、《韩诗外传佚文》一卷、《韩诗翼要》一卷、《韩诗赵氏学》一卷。
从以上粗略举出的辑佚要籍,已大抵可见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辉煌成绩。由于清人治学谨严精审,他们钩稽整理的三家《诗》学佚文,往往为今天治研三家《诗》者坚信不疑。尤其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集清人三家《诗》学辑佚之大成,已经成为三家《诗》研究者进行疏解立说的不二依据③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三家《诗》研究专著,似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先后有林耀潾:《西汉三家〈诗〉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赵茂林:《两汉三家〈诗〉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俞艳庭:《两汉三家〈诗〉学史纲》(齐鲁书社2009年版)、房瑞丽:《清代三家〈诗〉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只有赵茂林的著作,曾概要指出清人的研究和辑佚存在着“强分今古”、“胶固师法家法”、“三家同体论”的弊端,行文中也以一个三级标题简单讨论了两汉的师法家法问题。由于赵著是全面研究两汉时期三家《诗》的种种问题,重点不在清人辑佚,因而问题的讨论尚不够深入。其他几种著作,则基本是信从清人辑佚的。其中房瑞丽的说法,值得特别提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清代的三家《诗》研究存在着这些问题(按:指赵茂林揭出的三点弊端)。但有些问题的存在,乃是学者面对亡佚之学时的一种折衷选择,只有采取这种迂回的方法,才能使残缺过甚的三家《诗》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如‘胶固师法家法’之说……清代三家《诗》研究重视师法家法,一是对自汉代以来就形成的传经传统的继承,二是面对亡佚之学,在搜辑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研究将无法进行。”(26页)这就是说,明知清人三家《诗》学辑佚成果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由于“亡佚之学”难为,我们今天只能同情理解并将错就错,以便维持“研究得以顺利进行”。这个观点,可能代表着学者的普遍默识,否则就不好理解近代以来何以无人认真指摘清人的三家《诗》学辑佚成果、反而往往信从不疑的情状。不过,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求确,不能因为难以考实便随意安顿史料,后人更不可以讹传讹。如果为了研究得以展开而顺任并使用错误的史料,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是,清人辑录三家《诗》学的工作成果并非完美无瑕,反而可能还存在着较大的失误,实不可尽信。
一
早在1980年,台湾学者叶国良即发表《〈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一文④叶国良:《〈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载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九卷第一期,1980年6月。,以郑玄三《礼》注、《汉书》、《白虎通》、《盐铁论》中所存三家《诗》说为例,简要分析王应麟尤其是清人辑录三家《诗》说佚文的动机和方法,指出他们辑佚中歧见纷仍的情状,并提出重辑三家《诗》说佚文的几点建议。该文分说三家《诗》说辑佚问题堪称周延,可惜未能深入检讨清人的辑佚方法和理据,也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很显然,衡量辑存古籍佚文之成就得失的唯一评判标准,是所钩稽整理出来的佚文文本是否可信可靠;而辑佚者所运用的方法及其理据是否正确,则直接影响着辑佚成果的信实与否。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之甚大功劳无需多说,但毋庸讳言,也存在着武断安置《诗》说佚文等重大舛误。在笔者看来,问题主要是出在他们辑佚的方法和理据之上。
洪湛侯《诗经学史》总结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基本方法,比较平实明晰,今引录如下:
(1)以《三家诗》书名为据者;
(2)书中标明属于某家之学者;
(3)可推知其师承关系者;
(4)用时代断限,推知其所属家派者;
(5)三家中二家之说同,推谓另一家当亦如之⑤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3—145页。。
洪氏所揭五种主要的辑佚方法,可分三类来看:第一类,即第(1)(2)两个方法,佚文所出的源文献中有明确标识,如《国风·周南召南》目下所辑《韩诗叙》佚文,出自《水经注》卷三四引“韩婴叙诗”,《周南·关雎》首章所辑《韩诗章句》佚文,出自《后汉书》注和《文选》注引薛君《韩诗章句》等,这类佚文的归属自然没有疑问①值得注意的是,清人所辑三家《诗》说佚文,源文献中明确标识书名或家派的,一般都是《韩诗》,《鲁》、《齐》二家几乎没有这样明确的佚文。这当与《齐》、《鲁》早佚,《韩》亡佚最晚并残存最多的实际情形有关。。第二类,即第(3)(4)两个方法,是以考定说《诗》者的师承、家派为依据,来安顿佚文归属的。此种做法的理据,是认定汉代人传经恪守师法、家法。这个认识,其实大有可疑(详下)。第三类,就是第(5)个方法,如王先谦《集疏》中多有“齐、鲁与毛同,韩盖无异义”、“鲁、韩如此,齐义当同”之类判断,显然就是没有实际根据的推测了。这种妄断佚文之家派归属或妄断三家《诗》义的情形,还有色色不一的情状,如陈乔枞把荀子说《诗》、陆贾说《诗》均一概阑入《鲁诗》遗说,王先谦则往往在三家无《诗》说存留之处断然写上“三家无异义”,是其荦荦大者。
以上三类方法中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因其正误是非十分鲜明,无需申说;第二类,即以师法、家法为依据来判定三家《诗》说佚文之归属,是大可思量的。
汉代的经学传授,固然重视师法、家法,这在《史记》、两《汉书》中多有记载。后人也不断重申、确认这个认知,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郑方坤《经稗》提要:“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胡朴安《诗经学·三家诗》也说:“搜采三家《诗》,有一事须先辨之极明者:即两汉学之家法是也。三家《诗》既亡,今从群书中录而出之。使不明两汉之家法,则本《鲁诗》也,或入之于《齐》;本《齐诗》也,或入之于《韩》。惟深明两汉之家法,知某氏之学,授之于某;某氏之学,为某氏之所自出。……家法既明,搜采始无误入之处。”②胡朴安:《诗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9—70页。在古今很多学者的认知里,汉代经学授受过程中师法、家法极为严格,弟子、后学必然因循各自的师法、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殊不知,若果真如此,两汉四百年之久的经学怎能发展演进?其生生不息的活力何在?
以师法、家法为根据安顿三家《诗》说佚文,这个辑佚方法应该是南宋学者的发明。如王应麟说:“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康成从张恭祖受《韩诗》,注《礼》之时未得《毛传》,所述盖《韩诗》也。”(《诗考后序》)范处义也说:“盖《鲁诗》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向乃交之孙,则向之言必本于《鲁诗》也。”(《诗补传》卷六)清代学者沿用这个方法,并提升为钩稽三家《诗》说佚文的理据和通则。
不过,事实总是要比思想更复杂。即便是专治三家《诗》的清儒,对汉代师法、家法问题,其实也还有不同的认知。深信不疑并援为辑佚理据者,自然有之,可以陈氏父子为代表:
汉儒治经最重家法,学官所立,经生递传,专门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馀年,显于儒林。虽《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文字或异,训义固殊,要皆各守师法,持之弗失,宁固而不肯少变。(《齐诗遗说考自序》)
陈氏父子认为“汉人传经最重家学”(《鲁诗遗说考自序》),固守师法不变。王先谦完全赞同这个认识,其《集疏·序例》云:“穷经之士讨论三家遗说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陈氏最为详洽。”之后照录陈氏《三家诗遗说考》的三篇序文,以示完全认同。
与此同时,也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例如:
郑氏虽从张恭祖受《韩诗》,但其学该博,不名一家,如笺《诗》宗毛,有不同则下己意;注《礼》时未得《毛传》,大率皆《韩》、《鲁》家言。若确然定为《韩诗》之说,恐未必然也。(宋绵初《韩诗内传征序》)
《韩诗》后亡,故宋以前群书所引者,皆有明文;又有《外传》为之左验。《齐》、《鲁》亡独早,言三家者仅据其传授推之。……群书引三家义,只《韩诗》直引其文,其馀二家仅凭推测,不可为据。(阮元《三家诗补遗》叶德辉《叙》)宋绵初认为,郑玄学殖庞杂,若遵循师法把他的《诗》说一概归入《韩诗》遗说,并不妥当。而叶德辉《三家诗补遗·叙》,提出陈乔枞将班固《诗》说入《齐诗》而阮元则列入《鲁诗》,陈乔枞把《盐铁论》说《诗》入《齐诗》、《潜夫论》说《诗》入《鲁诗》而阮元则均列入《鲁诗》,陈乔枞以郑玄《诗》说入《齐诗》①胡朴安虽赞同清人依据师法、家法安顿三家《诗》遗说,但对此亦不乏批评:“郑康成未笺《毛》以前,本学三家《诗》;注《礼》所用者,果为何家,无从分别。陈氏断为用《齐》,未免稍过。”见其《诗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4页。而阮元则有所抉择等情形,细加考证,以证陈氏或“凭空臆度”,或“未免臆断”,而阮元的作法则往往“有志文可据,亦胜于凭空臆度者”。他还指出,由于《韩诗》亡佚最晚以及尚存《外传》可以佐证,诸书引证《韩诗》一般比较明确;至于《鲁》、《齐》遗说,则大抵是辑佚者“仅凭推测,不可为据”。
总之,以师法、家法为依据安顿三家《诗》说佚文,虽说是清人辑存三家《诗》说的主流,其辑佚成就也最大,并且得到迄今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可,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这本就说明:以师法、家法为依据辑录并安顿三家《诗》学佚文,一直都还是个有争议问题。
二
前人关于汉代经学传承恪守师法、家法之成说,其实不可尽信②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考辩较详,载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5—220页。。汉代经学受授的实践,情形十分复杂,并非单纯固守师法、家法。
先看两汉设立经学博士的实际情形。自汉文帝始立经学博士、武帝建全《五经》博士始,即不限于一经立一博士③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考文景时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公,如辕固,如韩婴,皆《诗》博士;如胡母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77页。;其后不断增多。《汉书·儒林传赞》云: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这段记载,还只是纲要而已,遗漏颇多(可比参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但它已经呈示了西汉经学博士逐渐增多的实际趋势。至后汉初年,则有《五经》博士十四人。《后汉书·儒林传序》云:
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
广东地处于珠江下游河网地区,船闸主要分布在上游北江和东江航道上。随着北江航道扩能升级工程的推进,清远枢纽二线船闸、飞来峡枢纽二三线船闸、白石窑枢纽二线船闸等由交通运输部门投资改扩建和新建的多线船闸也将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如何协调与原枢纽船闸业主的关系、解决多线多梯级船闸联合调度的难题也迫在眉睫。为了推动船闸规范管理,2017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专门组织开展了《广东省船闸通航规范管理体制方案》研究工作,参照广西所采取的“三统一分”的船闸委托代管模式,结合广东实际,研究提出以北江为试点,将北江全线船闸由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统一管理,实现北江多线多梯级船闸联合调度。
《汉书·儒林传序》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是为汉世《五经》传授之源。如果弟子、后学受授《五经》均严格祖述师法、家法,“宁固而不肯少变”,绝无异说抑或增删,则一经一家立一博士足矣,何必另辟多条学脉!
并且,钱穆早已指出,汉代“为博士者,初不限于专治一经。如韦贤,并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征为博士(《本传》)。又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儒林传》);而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韩婴为博士传《诗》,然亦以《易》授人。后苍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然仲舒见称通《五经》。又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兒宽为弟子(见《兒宽传》)。”①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汉博士家法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7—208页。一经一家不限于设立一个博士,同时,博士也不限于专授一经,如此情境下,如何确认汉人恪守师法、家法,宁固不变?
再来看两汉学人的实际研修受授情形。随意翻检一下两《汉书》的学人传记,即不难发现诸如“为学精熟,所问非一师也”、“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遍习《五经》,诂训大义,不为章句”、“通《五经》,贯六艺”之类记载,这就明示着所谓师法、家法约束力的脆弱。为了透彻理解这一点,来看几个典型学人的例子:
一个是刘向。古今学人的主流意见,乃判定刘向《诗》学属于《鲁诗》一派。理由是:其高祖父楚元王刘交习《鲁诗》,《鲁诗》是元王一系的家法②如南宋范处义《诗补传》卷六、王应麟《诗考后序》,清人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三家诗源流》、朱彝尊《经义考》卷九九、陈寿祺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之《自叙》及《鲁诗叙录》、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五等均持此说。今人也多坚持此说。。但是这个理由颇有可疑:
断定刘交所习为《鲁诗》,乃是因为他与鲁人申培同学《诗》于齐人浮丘伯,而申培传《鲁诗》,故判定刘交也是《鲁诗》派。这其实是一个逻辑并不严密的判断。关于此点,可思辩的问题较多,择其要者:其一,《诗》学(以及经学)分派分家,乃是汉代立五经博士以后的事③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论证甚周详,其结论云:“今考汉博士经学,分经分家而言‘师法’,其事实起于昭、宣之后。……窃疑《诗》分齐、鲁、韩三家,其说亦后起,故司马迁为《史记》,尚无《齐诗》、《鲁诗》、《韩诗》之名。……至班氏《汉书》则确谓之《鲁诗》、《齐诗》、《韩诗》焉。是三家《诗》之派分,亦属后起。……石渠议奏不及《诗》,是《诗》分三家,疑且在石渠后矣。”文载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1—216页。。浮丘伯是荀子的弟子,生活于战国末至西汉初年,那时并无派别抑或师法、家法。所以申培在文帝时成为《诗》博士(后称《鲁诗》④“鲁诗”之名,起于鲁人申培立博士之后,《汉书·楚元王传》言之甚明:“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颜师古注:凡言传者,谓为之解说,若今《诗毛氏传》也),号《鲁诗》。”可见申培为《诗》学博士之时,尚无家派之分(参见上一条注释)。这里有两点须注意:第一,《史》《汉》之《儒林传》均言:“(刘)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汉书》作“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汉书》作“训故”)以教,无传(颜师古注: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疑者则阙不传(司马贞《索隐》:谓申公不作《诗》传,但教授,有疑则阙耳)。”又《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据此二条史料,则申培传《诗》,唯有“训故”而无“传”。颜师古《汉志》注云“故者,通其指义也”,又其《儒林传》注云“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见上),则“训故”与“传”均为阐释《诗》义(不止文字训诂),唯“训故”简要切近、“传”繁多游离耳。所以《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有“(三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之说。准此,则《楚元王传》所谓“申公为《诗》传”,当是指“训故”。第二,《汉志》著录四家《诗》,唯《鲁诗》无“传”,仅有“故”、“说”:“《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此可与《史》《汉》《儒林传》及《汉志·六艺略·诗类序》互证,而益明《楚元王传》“申公为《诗》传”之所指。至于《鲁故》、《鲁说》,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鲁故》,即申公作”;“《儒林传》:《鲁诗》有韦、张、唐、褚之学。此《鲁说》,弟子所传。”允称卓识。),并不能说明刘交所习所传也是《鲁诗》。何况刘交曾自作《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本传)。只是《元王诗》汉时即鲜见⑤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先慎说:“《艺文志》不载《元王诗传》。《志》本《七略》,刘歆不应数典忘祖。当是次而未成,故班史传疑云。或有以示未见之意。”,后竟不传,今天更无法参看判断。其二,荀子传《诗》与后世四家《诗》均有极大干系⑥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汪中《荀卿子通论》:“《毛诗》,荀卿子传也。……《鲁诗》,荀卿子传也。……《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毛诗》,得郇卿之传也。……《鲁诗》,得郇卿之传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流传时代》:“《韩诗》今存《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则《韩诗》亦与《荀子》合。”综合诸贤之说,则荀子传《诗》与后世《鲁》、《韩》、《毛》均有渊源。又,《史记·儒林列传》:“韩生推诗人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魏源《诗古微》卷一《齐鲁韩毛异同论上》:“且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是谓《齐诗》与《鲁》、《韩》颇多相同,然则亦与荀子有渊源。,不专主哪一家(这当然是后人的溯源之论,在荀子那里并无家、派的问题)。如果因为申培、刘交是同学而判断刘交也习《鲁诗》,则循此思路逆推,齐人浮丘伯所传就是《鲁诗》,荀子所传也是《鲁诗》——这样的看法无疑是荒谬的①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鲁诗遗说考》即赫然把荀子说《诗》归入《鲁诗》。。
至于刘向本人,他兴趣广泛,学术背景和学术修养比较复杂,并非固守家法的学者②详见拙著《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第五章,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9—70页。。其家学传统本即儒、道并行,其本人更是学殖博杂:既精通正统经学(如家传《诗》,专习《穀梁春秋》,讲论《五经》于石渠,掌校《五经》祕书),又兼及阴阳灾异之学(如作《洪范五行传论》、多次上书言灾异)、神仙方术(如热衷“为金之术”、“延命方”)等。而其编纂《列女传》、《说苑》、《新序》,又是通经致用的方正之言。《汉书》本传说“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刘向固然是精湛的经学家,但无论从他的家学传统看,还是从他本人的学术修养和兴趣看,他绝非固守执滞的腐儒,而是博学兼擅、追求通经致用的通儒。
刘向《诗》学归属,除上述主流观点(《鲁诗》)外,也有少数学者判断刘向所习为《韩诗》。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刘向述《韩诗》”条即说:“向所述者,乃《韩诗》也。”又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郑笺〉多本〈韩诗〉考》也说:“刘向所述多《韩诗》。”甚至有学者以为刘向亦采《齐诗》。如范家相《诗沈》卷二《鲁诗》:“朱氏(指朱彝尊)以刘向所述皆《鲁诗》,本之王厚斋(即王应麟)。以向乃元王后,必当守其家学也。然《儒林传》不言向说《诗》之自。盖向之学极博,又笃好《左氏传》,其于《鲁诗》不无出入。故《新序》所载《黍离》之说,先儒疑是《齐诗》也。”这些学者各持不同推断的情形,也可说明:难以用师法、家法对刘向《诗》学作出简单判定。
再一个是班固。古今学者大多认为班氏世习《齐诗》,班固的《诗》学观念也是《齐诗》的承传。仔细检讨此种看法,实大可商榷:
首先,说班固传习《齐诗》的主要根据,是其伯祖父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汉书·叙传上》),而师丹“治《诗》,事匡衡”,传《齐诗》(见《汉书·师丹传》)。因此认为,班伯既传习《齐诗》,则班氏家族即世习《齐诗》,班固也必然传习《齐诗》。其代表说法如:
班固之从祖伯,少受《诗》于师丹,诵说有法,故叔皮父子世传家学。《汉书·地理志》引“子之营兮”及“自杜沮漆”,并据《齐诗》之文。又云“陈俗巫鬼,晋俗俭陋”,其语亦与匡衡说《诗》合,是其验已。(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序》)
《汉书·叙传》:“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传》:“治《诗》事匡衡。”是班伯习《齐诗》。固传家学,亦当是习《齐诗》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二《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
班伯受《诗》于匡衡③此说误。班伯受《诗》于师丹,是匡衡的再传弟子。,《齐诗》乃班氏家传。(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六)
这里所谓“叔皮父子世传家学”、“固传家学”、“《齐诗》乃班氏家传”云云,都是根据师法、家法的理念所作的推论,并没有明确的文献依据。
早在南宋时,王应麟《诗考》蒐辑《齐诗》遗说十三条,尚有明确的文献根据。其中与班固有关的两条,一是“子之营兮,遭我虖嶩之间兮”④《齐诗·齐风·营》诗句。《毛诗》该诗名为《还》,诗句中“营”亦作“还”。,二是“自杜沮漆”⑤《齐诗·大雅·绵》诗句。《毛诗》“杜”作“土”。。王氏钩稽这两条,不仅仅以出自《汉书·地理志》为据,还有其它明确的文献依据:“子之营兮”二句,《地理志》明确说“《齐诗》曰”;“自杜沮漆”句,《地理志》云“《诗》曰‘自杜’”,颜师古注:“《大雅·绵》之诗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齐诗》作‘自杜’。言公刘避狄而来居杜与漆、沮之地。”至清儒增补王氏所辑三家《诗》,开始时也还颇重文献明确记载的依据,比较客观,如清初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三家诗源流》即说:“班固《白虎通》多引《韩诗内传》(按实仅有四处),亦时述《鲁诗》;《汉书》亦然。盖三家《诗》俱有之。”指出班固著作引述《诗》说,乃是兼及三家。再到后来的学者,则基本以师法、家法为依据来辑佚了,陈氏父子即因班固伯祖父班伯习《齐诗》,于是将班固著作中引述的《诗》篇及《诗》说,均视为《齐诗》遗文及《齐诗》说(见《齐诗遗说考》之《自序》及卷一)。
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明显与两《汉书》所述不符。《汉书·叙传》只记载“(班)伯少受《诗》于师丹”,但并未明确说班家其他人也修习《齐诗》。如说班伯的二弟班斿“博学有俊材”,曾与刘向校祕书,未具载其师承、学业;记述班伯的三弟班穉(班固祖父)的事迹,亦未载其学殖。又如说班斿之子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说班穉之子班彪(班固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然亦未具载其学业传承。班彪《王命论》征引《论语》、《春秋》、《易经》乃至图谶,却并未引用《诗经》。至于班固本人,《叙传》自谓“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所撰述之《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没有交代其经学师承。《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其学业稍详具: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从《汉书·叙传》所述班氏家族诸人的学业看,各有取资志趣,班氏家族似乎并无严格的《诗》学家法。统观两《汉书》述班固之学——“专笃志于博学”、“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不难了解,班固并非固守师法、家法的学者。因此,以班伯受《齐诗》来判断班固必传习《齐诗》,证据并不充分。
其次,班固作为醇正的儒家学者,他的《诗》学思想固然较多继承了有汉以来儒家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为强调《诗》的经学性质和政教目的,但是,他也并非完全拾唾前人,而是有不少开拓创新之论。其中最为耀眼者有三:一是在确认《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性质和目的之同时,更加集中地突出了情感的生发感动特质。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诗歌的本质特征,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他批评三家《诗》“咸非其本义”,表现出追求《诗》之“本义”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在今文经学极盛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是《诗》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演变;三是他在司马迁以地理环境论社会风俗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开辟了从地理和风俗的视角评论《国风》的思想方法。这一卓越思想,对今天的《诗经》研究乃至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甚至示范意义①关于班固《诗》学思想之特征、贡献,以及班固署名诸书之著作权如何理解的问题,详见拙著《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第六章,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3—97页。。这些《诗》学观念,都是恪守师法、家法之说所不能解释的。
第三个是郑玄。他笺《诗》兼收今、古,旁及谶纬,更非师法、家法所能牢笼。关于郑玄的学业,《后汉书》本传载:年少时“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一说当作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马融弟子),事扶风马融。”张恭祖兼授其今、古文经,毋论矣;马融也是东汉学业博通的大儒,他师事“名重关西”的挚恂,而“博通经籍”。安帝初拜校书郎,“诣东观典校秘书”。“才高博洽,为世通儒。……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后汉书·马融传》)可见马融于精通古、今经学而外,也擅长诸子和楚辞。《郑玄传》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似是未得马融亲传。但是既有三年师门之熏染,又有高弟代为授业,郑玄之学业受益于马融,应是不成问题的,故郑玄东归,马融谓其门人曰“吾道东矣”(《马融传》)。
郑玄的著述,《后汉书》本传载:“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馀万言。”但是这份著作目录还是比较粗疏的。据杨天宇的稽考,郑玄的著作包括注释类(又分为经传、纬书、杂注三小类)、著作类、门弟子所辑类共有五十六种之多①见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之《通论编》第二章《郑玄著述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9页。,遍及经、传、谶纬及律历、数术等多个科类。
据上简述可见,无论从学殖修养还是从著述看,郑玄都是一位以经学为主业、博学旁通的儒者。就其经学建树来说,乃是今、古、谶纬兼通;仅就《诗》学而言,也是三家《诗》、《毛诗》并擅②陈奂《诗毛氏传疏·叙》云:“郑康成殿居汉季,初从东郡张师(张恭祖)学《韩诗》,后见《毛诗》义精好,为作《笺》,亦复间杂《鲁诗》,并参己意。固作《笺》之旨,实不尽同《毛》义。”又其《郑氏笺考征》云:“郑康成习《韩诗》,兼通《齐》、《鲁》,最后治《毛诗》。笺《诗》乃在注《礼》之后,以《礼》注《诗》,非墨守一氏。《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例不外此二端。三家久废,姑就所知得如干条。《毛》古文,郑用三家,从今文。于以知毛与郑固不同术也。”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苏州漱芳斋咸丰辛亥(1851)刻本。。《后汉书·郑玄传论》云:“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馀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范史之论,实已指出郑玄学冠古今、广综博通的经学思想特色。不专擅一经、不固守家派,并且博学旁通,是后汉许多儒士知识思想的普遍特点,一代宗师贾逵、马融都是如此,郑玄集汉世儒学之大成,是体现这个特色最为透彻鲜明者。
总上所述,两汉经学传授中固然有师法、家法之规则,但是它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么严格。尤其对于像刘向、班固、郑玄这些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儒学大师而言,不会专经固守,才是其学术传承的常态。所以,宋清学人一味地以师法、家法为依据,安顿三家《诗》说佚文,其准确性、可靠性是会大打折扣的。这里还要附带说一句:叶德辉《三家诗补遗·叙》有所谓“两汉经师惟列传〈儒林〉者其学皆有家法,自馀诸人早晚皆有出入”之说,较之陈乔枞、王先谦等笃信并贯彻师法、家法的学者,显得更加客观些。但是,叶氏这个说法,也难以在今存的经史文献中得到有效证明,唯聊备一说而已。
至于清人安顿三家《诗》说佚文之归属,呈现出《鲁》、《齐》、《韩》各自判定不一、歧见纷纭的实际状况,更切实证明了以师法、家法武断三家《诗》说佚文之归属的方法和理据,在很多具体情形下是很不可靠的——这一点,叶国良《〈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一文已有较多指摘,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Research on the Basic Method of Complilation of the Theory Collection of Shijing of Sar jia of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Zhang FengyiHuang Taihao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outstanding complilation of the theory collection ofis the work of Chen Qiaozong and Wang Xianqian,who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mong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However,the basic method of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which was to figure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posers according to scholar and family pedigree,is not reliable.Though some scholars made achievements in figuring out the problems of the basic method of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mentioned above,the essential approach is not clear yet.The intention of this essay is to point out problem of the basic method of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by taking the argu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poser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cholar and family pedigree of Han dynasty into consideration.
Complilation of the Theory Collection ofScholar and Family Pedigree
责任编辑:陈水云
张峰屹(1962—),男,山东蓬莱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唐文学与文论研究。黄泰豪(1968—),男,台湾高雄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先唐文学与文论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汉文学思想史》(14BZW026)的相关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