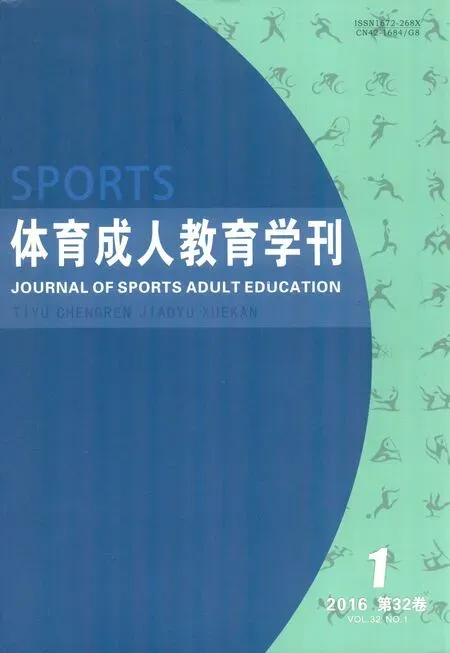论公民社会体育权的环境法保护*
2016-11-28王腾
王 腾
(湖北经济学院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论公民社会体育权的环境法保护*
王腾
(湖北经济学院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公民社会体育权实现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环境是公民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公民社会体育权益实现的逻辑前提,同时公民社会体育活动也是损害自然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一。公众的社会体育权呈现多层次特征,环境法对公民社会体育权的保护可以从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以及体育自由权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关键词:社会体育权;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体育自由权
体育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对于提升民众身体素质、提高民众幸福感、保障民众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体育活动的类型进行划分,大众体育一般分为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其中开展竞技体育的活动主体一般是运动员,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竞技利益或供群众娱乐观赏;学校体育的主体一般是在校师生,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展体育教育。以上两种体育活动类型主体范围有限,开展活动所需的资源配置一般相对充足,保障该体育活动得以开展的主体往往是公共部门,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学校等,因此,此两种体育类型对于公民而言具有公益性特征。而社会体育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对象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普通公民开展社会体育运动不以公共部门提供特定资源为必要前提,而较多地以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与环境要素为基础,活动过程一般根据个体自身意愿完成,因此,社会体育一般属于公民私益的范畴。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在我国,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依然把竞技体育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点,学校体育因其受到教育体制与政策的保障也发展较快,而社会体育需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其原因在于社会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私益性特征。在缺乏公共部门的制度保障与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公民开展社会体育利益的实现容易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因素之一即为社会体育活动所依赖之最重要介质——环境。实际上,公民环境利益与社会体育利益均是公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两种利益类型无论是在实现形式还是在表现内容上均存在诸多交叉重叠之处。因此,本文从保障两种利益得以实现的权利机制入手,借助权利竞合理论,探讨公民社会体育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关系,并立足新《环保法》相关制度设计,探研环境法视野下公民体育权实现的路径与内容。
1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实现途径
1.1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权利属性
对公民社会体育利益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对公民体育权的确立与维护,而实现公民社会体育权,首先应从其权利属性的认定予以展开。权利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素有公权和私权之分。公权和私权如何界定,学界并无定论。有人将公权和私权都视为个人权利[1],有人认为公权既包括公民个人的公权,又包括国家的公权[2],还有人认为公权即公共权力[3]。 以上公私权利的划分主要采用主体标准,即以个体作为权利主体,则公权也当然包括个人公权,而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公权为公共权力,私权则为个人权利。基于社会体育运动一般关涉公民个体利益,本文采用个体标准,即以个体的视角去厘清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属性问题。
针对公民所享有之公私权划分古已有之,古罗马市民享有一种专属性的权利即“市民权”,其内容即包括公权与私权。公权是指市民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私权则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4]。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等级制度消失,私法逐渐演变为现今的民法,即所谓“市民社会之法”,而公法被认为是国家介入保障公民私权得以有效行使的法律依据,换言之,公法所保护的对象是为公民实现全体私益的一种“公益”。一般认为,民事私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私权的享有不以国家公益资源的提供为必要,如婚姻权,本属私人的自然权利,法律只是明确了这种古已有之的自发秩序,个人私权的义务对象则一般是个人或与自然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社会组织,而个人公权利益的实现一般需要公共部门介入予以保障。比如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需要政府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的渠道与资源,公民的诉权需要通过司法机关提供审判资源予以保证,公民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也是通过政府部门给予复议渠道与机制保障才能实现等等,以上公民个人公权的义务对象一般为国家等公权力机关。
就公民体育权而言,学界研究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公民体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属于宪法权利[5],有学者提出体育权是宪法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6],也有学者提出体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7],体育权利诠释着尊严的民权含义[8]。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体育权是生来就有的,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9],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0],也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总体归属社会文化权利[11],还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是生命健康权的下位概念[12]等等。我们认为,对公民体育权的属性认识应不能停留在公民体育活动这个整体层面上来考量,而应根据不同体育活动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来予以更为细致的探讨。按照公民开展体育活动的形式划分,其一般包括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公民竞技体育权与学校体育权的实现需要公共部门介入,竞技体育活动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组织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一般均属于公共部门。在我国公民竞技体育基本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各类体育竞赛的组织、运动员的遴选以及奖励的主体等都具有国家公权力性质,学校体育范围则更为明确,管理的主体为学校这一具有公权力谱系的组织,因此,公民的竞技与学校体育权利应归属公权范畴。而社会体育权的实现则更多依赖个体自身,个体依照自身意愿自由开展体育活动,不受其他个体与社会组织干扰或妨害,公权力一般无法直接控制与管理公民的社会体育活动,而只是在公民社会体育权受到侵害时给予救济性保障而已,因此,基于社会体育权的私益性、个人性,其应归属于私权范畴。如在私权体系内对公民社会体育权进一步予以划分,则可将其归为人身权——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与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支配权——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绝对权——效力及于一切人,即义务人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权利。
社会体育权作为公民最普遍的开展体育活动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设专章规定了国家保障这种权利得以实现的主要形式与内容,但却没有明确该权利的性质及其救济手段,这不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厘清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属性则有助于帮助我们弥补这一部门立法的缺憾,从整个法律体系,或者更明确而言,是在民法体系中寻找其权利实现的基础与救济途径,以使公民社会体育权不再虚幻,而更具实感。
1.2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实现
公民体育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是公民自由支配自身身体不受妨碍地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未有明确规定,但基于其人身权属性,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项权利内容:一是体育自由权,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自由是权利实现的根本目的,也是权利得以实现的原因,个体进行社会体育活动首先应属于个人自由支配自身身体的一项民事权利,这项权利既包括民事主体绝对权的行使,即对身体运动的自由支配,也包括相对权的行使,即因他人侵犯自身开展体育活动的自由而享有的侵权给付请求权,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二是体育发展权,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平等是民法权利产生与实现的基础,因此,任何社会主体能够平等地开展体育活动,并因此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三是体育健康权,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作为人身权范畴的一项重要子权利,健康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权利。一般而言,人类获取健康的方式存在两种类型:一是被动型,即政府应充分保证公众能够享有获得健康的环境与机会,不能因为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公众健康的丧失;二是主动型,即公众能够通过自身主动作为而促进自身身体的健康,比如体育运动就是个体获取健康的主动性作为。
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虽均属于公民体育活动的范畴,但三者在实现途径上存在显著区别,前二者权利的实现是以国家强制保障为前提,如当学校不给予学生充分的体育活动时间,或者不能提供合理的体育场所,学生可通过行政申诉这种公共渠道实现其权利。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权益的实现也是依托于国家行政公权的保障,如当有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导致对其他运动员公平竞技权的损害,国家也应采取行政干预手段予以解决,如国家怠于履行其义务,公民则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等方式实现其公共权利,因此,这两种权利的实现更多依赖于行政法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职责履行。但社会体育权则明显区别于前二者,公民社会体育活动中的自由权、发展权与健康权作为一种私权,是当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抗争而得以表现与实现的,即当外在的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影响到了公民的社会体育活动时,公民将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为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害而斗争,如权利主体放弃抗争,则这一权利就归于消灭,这里的法律及权利的实现形式可由权利主体自主选择,不以国家强制力主动干预为必要。因此,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实现依赖于对其具有法益保护的所有法律的整体支持。
2公民社会体育权与环境要素之关联
由于我国《体育法》没有对个体社会体育权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对社会体育权内容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权利的实现逻辑及其标的,从而将社会体育权放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框架中予以界定与保障。从社会体育权所保障的标的来看,自由、平等、健康等利益要素是权利实现的最终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仅仅依赖于民事法律所确立的人身权保护一般性条款予以解决,我们应进一步放宽视野,按照权利保障标的所涵涉的利益范围及其权利实现的相关性,在整个法律体系框架下进行全景式扫描,以实现公民社会体育权得到更加全面与整体的法律保护。按照法益是否重叠的标准,我们认为环境法是公民实现社会体育权的一项重要法律部门,其主要体现在环境利益与社会体育利益二者之内在的紧密关联性上,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自然环境是公民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载体
自然是社会文化的母体, 孕育了人类的一切精神成果, 这些成果组成了社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有包括体育在内的人类的一切文化行为[13]。自然环境是公民开展体育活动的载体,且其制约着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第一,环境为公民社会体育提供了活动空间、物质资料以及其他能从自然环境中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支撑体育运动的元素,如良好空气、清洁水源、优美景观等。第二,从社会体育项目的产生渊源看,自然环境严格制约与影响着某些体育项目的布局与产生形态。比如龙舟、赛马、摔跤等所谓的传统体育项目都是人类在特定地域与自然条件下生存和生产的产物,与自然环境资源相适应的体育运动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第三, 公民社会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因素的支撑,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 缺乏环境支持体育活动将无法正常开展。如从 1994 年美国足球世界杯的炙热天气到2002年美国冬奥会的暖冬缺雪,异常气候频繁闪现,雪上运动遭遇瓶颈,冬奥会的处境十分尴尬;众多江河湖海污染严重,亲水性的运动危机四伏;此外,大量自然水体常年干涸断流,水上运动发展面临困境[14]。今后,恶劣的环境可能会更严重影响到体育运动的开展,由于气候以及环境状况原因导致的体育发展不平衡也更加突出。
2.2公民社会体育活动为损害自然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多层次需要的日益剧增,体育及其相关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和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首先,公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需求促使大量体育场馆设施的兴建、扩大,直接影响了生态环境。如任何一项群众性社会体育活动的举办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大量的拆迁与体育设施改造任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原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与自然空间样态,导致了大量集中的自然空间和土地资源被占用,周围的原始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日本通过购买部分东南亚国家廉价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满足本国居民奢侈社会体育消费的需求[15]。其次,由于体育活动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即人类自身对环境的影响也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各种与环境资源联系紧密的体育活动中,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公民以及体育运动工具可能会对自然资源造成直接破坏,比如水中游艇爱好者开展运动可能由于不当操作造成机油对水体的污染,无规划的伐木运动对森林生态产生恶劣影响等。二是参加社会体育活动的观众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如观众在体育活动现场乱扔垃圾,随意践踏天然草场,利用高音喇叭对周围居民带来噪声侵扰等。
2.3环境保护是公民社会体育权益实现的逻辑前提
虽然学界对“体育权”内涵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权利泛化语境下的虚构概念[16],但基于体育活动本身对公民人身利益保障与促进的重要作用,学者们仍并未否认体育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类型存在的现实价值。一般认为,“体育权是由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人们能够通过接受体育教育进行体育锻炼和参与体育竞赛的方式获取身体健康和精神满足之利益的意志和行动自由的可能性”[17]。对于参与主体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体育权而言,除民法在民事基本权利层面上给予其基本保障外,其他法律部门的保障亦广泛存在。如据《宪法》第 21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此两条是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体育权的概括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明确了国家对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法律保障。就以上法规确立的公民体育权体系而言,体育健康、体育发展以及体育自由等元素构成了作为权利维护对象的公民体育利益的核心要素,而实现以上核心元素的前提是环境空间的质量安全、公平配置以及充分供给。具体而言,环境质量安全是公民获得体育健康利益的基本前提,没有良好环境的支撑,体育与健康之间就会失去稳定的介质基础,两者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将会受到严重干扰;生态环境决定着发展体育运动的项目、内容和规模[18],环境资源的公平配置是不同地域与空间实现体育普及的现实基础,环境资源配给与保护的失衡将导致公民参与体育活动机会差异,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体育普及;环境资源的有限供给限制了公民体育活动的自由度,人们通过体育运动获得健康的空间范围受制于环境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与有限性。因此,通过环境保护,确保环境质量的安全,实现环境资源公平配置,维持环境资源的容量与持续供给,是公民充分享有体育权的逻辑前提。
3公民社会体育权实现的环境法路径
体育既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能够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因此,公众的体育权呈现多层次特征。如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的体育权利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在人权之下又可划分为自由权、发展权、公平竞赛权、受教育权以及身体健康权等等[19]。在环境法领域,环境权也是以公民之环境利益为角度来创设的一种权利类型,在权利标的的范围上,公民的环境权与社会体育权存在交叉重叠之处,符合针对同一个体的权利竞合之要件。比如环境权的保护利益包括公民对环境的自由使用、对环境决策的参与、在环境中获取健康以及发展等等,从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标的来看,既包括公民自由开展社会体育运动的权利,也包括通过社会体育活动获得发展、健康的权利,因此,环境权与公民社会体育权存在的交叉范畴在理论上应包括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以及体育自由权。
3.1对体育发展权的保护
体育发展权是人类参与、促进并享受体育的一项新型人权,作为发展权的一项子权利,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全体个人及集合体所享有的参与体育过程,促进体育发展,并享有体育成果的平等的权利。可以说,体育发展权是体育领域内对涉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层面的高度抽象和凝结,是各项与人的全面发展直接相连的体育发展权利的有机统一和全面概括, 它意味着人在体育各个领域内的全方位发展, 表明了权利主体在体育领域所拥有的最广泛最深刻的自由[20]。体育发展权的实现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权利均等,即所有人平等地参与体育过程,促进体育发展的权利。二是体育成果共享,即所有人都有从体育运动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获取利益的权利。然而,从当前情况看,由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体育发展权的实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第一,人们无法平等地享受到体育权利。比如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城乡在体育公共基础设施的配给上差异巨大,其中一部分差距是由于城乡环境差异造成的。一些城市生态环境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可以通过人造体育场馆或设施予以弥补,比如建造游泳馆,可以减少人们对天然水体的需求,但在农村湖泊河流的污染,将直接导致村民无法从事大众游泳运动。第二,人们难以从体育发展中受益。比如一些大型体育场(馆) 设施, 如滑雪场、高尔夫球场、足球及棒球场的修建, 破坏了生态环境,引起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的批评和反对。在日本, 许多球场建在山脚下的森林区,开发商修建时砍掉了树木, 用推土机把山坡推平并整平山谷,用这种方式修建的高尔夫球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21]。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以减损部分群众的生态利益为代价来发展少部分人对体育的需求,是有碍体育发展权实现的表现。因此,通过环境法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其一方面加大了违法者的污染成本,实现了潜在污染者与政府管理者对公民城乡生态环境利益的平等尊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污染者付费的制度措施,实现体育发展收益者对生态环境受损者的利益转移,从而真正实现公众对体育发展收益的共同分享。
3.2对体育健康权的保护
在健康权的实现过程中,体育具有重要价值,进行体育活动是实现国民健康的重要途径[22]。体育健康权可被认为是健康权下属的一个子概念,其主要是指公民能够通过体育活动获得健康的权利,此权利体现的是一种对健康实现途径的保障。要实现体育健康权的保护,一是要给予公众广泛的参与社会性体育活动的机会与空间,二是要保障公众能够通过参加社会体育活动获得健康。《体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提倡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康。社会体育活动应当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遵循因地制宜和科学文明的原则。”该条款规定了公民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加身心健康,明确了公民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当前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公民的体育健康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运动与健康之间的载体——环境出现了问题。众所周知,运动无法脱离于特定的环境,缺乏良好环境的支持,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的几率就会降低,比如著名的匹司开特威烟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971年9月16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匹司开特威市,上午八时,在纽瓦克停车场,用大气污染测量仪自动记录,测得氧化剂浓度为0.022ppm,高于平时水平,但认为还不到警报点。下午三时,氧化剂浓度剧增,已达到0.80ppm。基伯里顿中学中学生正在踢球,突然发生多泪、喉痛、呼吸困难、咳嗽、以及吸气时胸痛,还表现全身症状,如呕吐、腹痛、肢端麻木感,有些学生腹痛持续两天左右,共有15个足球队员受到同样影响,周围至少六个学校的运动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23]。因此,自然环境载体的破坏妨害了公众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的权利,对环境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对公众体育健康权的一种有力保障。新《环保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该条款确立的环境健康监测、调查与评估制度的效力范围,应包括环境质量对公众开展体育运动而获得健康的影响,关于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以及对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实际上可视为针对维护公民体育健康权的保障性措施。
3.3对体育自由权的保护
一些学者认为:“自由是体育本质最高层次的实现,是构成体育本质的另一重要元素。这种自由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体育操练的过程是一个从意志操作到自由观照的过程。”[24]体育自由权是人们自由选择体育运动的权利,其既包括选择与参与不同体育运动的权利,也包括在不同空间地域与时间范围内选择体育运动的权利。《体育法》按照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类型对公民体育权进行了明确与划分,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些规定都是从保障公民能够自由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的。然而,实际情况与法律目标设定的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在日常生活中公众的体育选择权的实现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方面,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被誉为“家门口的运动”的社区体育项目正急剧削减[25],大众在选择类似项目的自由度受到较大限制,如部分地区大兴挖山建房,导致公众的休闲爬山运动无法正常开展;一些地区为了修建公共设施,破坏天然草皮,导致足球运动无法向大众普及。这些环境污染事实上直接导致了公众无法自由利用原有的自然资源空间开展习惯性的体育项目,民众自身的体育自由权受到了侵害。在体育项目时空选择方面,一是受污染的环境空间限制了公众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比如体育专家认为,我国冬季、春季的头一两个月空气污染最严重,而在一天之中中午和下午的空气较为清洁,早上和晚上空气污染较严重,晚上7点至早晨7点为污染的高峰时间。因此,基于健康的考虑,人们无法在污染严重时段开展户外运动。二是环境污染导致了公众运动空间的减少。以上事实说明了环境是影响公民自由开展体育活动权利实现的主要因素。鉴于此,需要从环境法保护的层面,通过依法开展环境治理与严格监管,保证体育运动所依赖的环境介质符合健康标准,从而让公众能更自由地选择体育运动的项目类型、时间与空间,保障公民体育权的完整实现。同时,新《环保法》第4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这一条款通过增加政府环境信息供给的义务,保证了公民能够在更加有效与充分的信息供给前提下,实现自由选择开展健康运动的时空与类型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2-25.
[2] 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M].黄冯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5-126.
[3] 韩忠谟.法学绪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78-179.
[4] 周丹.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9-100.
[5] 谭小勇.国际人权视野下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学诠释[J].体育与科学,2008(5):33-37.
[6] 王湧涛,刘苏.论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保障[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13-15.
[7] 巴玉峰.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理论分析[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6(4):33-35.
[8] 刘成.从“尊严论”探视公民体育权利的发展契机[J].体育科学研究,2011(5):34-37.
[9] 张振龙,于善旭,郭锐.体育权利的基本问题[J].体育学刊,2008(2):20-23.
[10] 冯玉军,季长龙.论体育权利保护与中国体育法的完善[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3):114-119.
[11] 王岩芳,高晓春.论体育权利的内涵及实现[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9-12.
[12] 姚学英,朱爱民,姚学进.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内涵与实现[J].山东文学,2007(8):49-51.
[13] 邓跃宁,李峰.论体育生态文明[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7(1):5-7.
[14] 陈卫峰,赵满凤.体育与环境保护的关系[J].搏击.武术科学,2008(4):87-88.
[15] 陈俊钦,黄汉升,朱昌义,等.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与趋势[J].中国体育科技,2003(1):1-6.
[16] 杨腾.体育权:权利泛化语境下的虚构概念[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6):33-37.
[17] 王岩芳,高晓春.论体育权利的内涵及实现[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9.
[18] 林仪煌.体育与环境[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68-69.
[19] 董小龙.中国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保护[J].宁夏党校学报,2009(2):49-50.
[20] 汪习根,兰薇.论体育发展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95-99.
[21] 陈慧敏.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与趋势[J].中国体育科技,2003(1):7-10.
[22] 叶小兰.健康权视野下的体育公共服务探析——基于人权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2(3):26-29.
[23] 苗瑞菁.空气污染与运动健康的相关性研究[J].商业文化: 学术版,2010(6):182.
[24] 刘媛媛.身体·感性·自由——体育本质新诠释[J].体育科学,2007(11):70-73.
[25] 曾庆欣,刘志刚.社区体育与生态化发展[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7-92.
Environmental Law Protection of Civil Social Sport Right
WANG Teng
(Law School, Hubei Economic Inst.,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social sports righ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social sports activities and the logic pre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social sports right while the civil social sports activity is a risk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ublic social sports right is multiple leveled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social sports right is embodied in the aspects of sports development right, sports health right and sports freedom right.
Key words:social sports right; sports development right; sports health right; sports freedom right
(收稿日期:2015-11-16)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6)01-0029-06
*基金项目: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5Q164),湖北经济学院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重点项目(XJ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