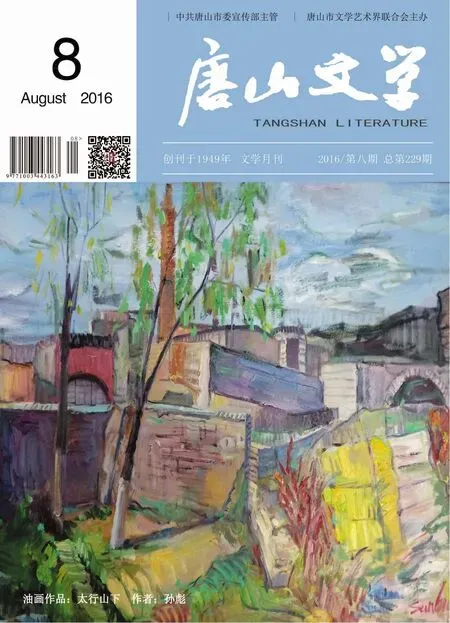灵动的生命,中和的审美
——论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
2016-11-26乔瑢
乔 瑢
文学评论
灵动的生命,中和的审美
——论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
乔 瑢
本文从冯至的代表作《十四行集》《伍子胥》出发,探讨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写作的主题,并从艺术加工和个人经历等层面分析主题产生的心理机制,得出“灵动的生命”主题是作者内化了各种经历、影响之后得出的,其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创作具有“中和之美”的中国式审美意味。
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冯至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诗集《十四行集》、小说《伍子胥》,出版了散文集《山水》,发表了学术著作《杜甫传》。其中《十四行集》和《伍子胥》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本文以这两个文本为依托,探讨四十年代冯至的创作。
一、灵动的生命
《十四行集》以诗的形式传达生活经验,侧重于对死亡、孤独等的独特体验。
《十四行集》第二首诗集中呈现了生命对于死亡的独特体验。在这里,死亡不是一种不可控的无奈,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安排:“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而生命体应该做的,是坦然地接受,如同秋天的树木“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这种乐观、旷达的死亡观展现给我们面对死亡的智慧:向死而生。对冯至影响深远的里尔克曾说“死亡是我们掉头而去和未被我们照亮的那一部分生命”,冯至也曾说过“生命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生命的开始,因此二者是同一的,没有光明就无法想象黑暗”。《十四行集》将“死”纳入“生”之中,传达出人生中的大智慧。
《伍子胥》以小说的形式来叙述成长,侧重于体现主人公的决断和承担。
第五章《昭关》是对伍子胥“承担”精神的一次聚焦和升华:伍子胥出关时遇到了严格针对自己的搜查,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后他的头发一夜变白,得以出关。昭关的艰难不仅在于严格的搜查,还有一路上积压起来的疲倦、寂寞和重量。对此,伍子胥没有拼尽力气去闯关,也没有宣泄,而是做了一个停留思考,观察他人,反观自身。在思考中,他体会了“旧日的一切都枯叶一般一片一片地从他身上凋落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清爽”。他用“蜕变”成功地承担了它,“以一个再生的身体走出了昭关”。借用动物界的“蜕变”概念,小说成功地勾勒出了伍子胥所做出的巨大承担,伍子胥的勇敢担当使他通过了生命中的一道关卡。
尽管两部作品侧重点各不相同,却有着相同的主题——灵动的生命。
《十四行集》在传达对死亡、孤独体验的同时,仍未忘却对温暖的体验:第二十三首诗中,初生的小狗在连续阴雨后被母亲衔出去晒太阳,它们领受了光和暖后,在深夜中吠出光明。这是多么温情的一幕!将温暖用自己的方式延续、传递给他者。生命体互相关心、支持所给予的温暖,是冯至十分注重的,他曾写到“人生的意义在乎多多经历, 多多体验, 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
《伍子胥》在聚焦主人公隐忍、担当的同时,仍有灵动飘逸的一笔:《潥水》一章,主人公和浣衣女对于彼此有了“半情半知”的直觉性把握:相遇前,浣衣女不知道“我”以外还有一个“你”,饥饿则使伍子胥精神、身体疲乏。相遇之时,二人都没有做声,所想也各异,却又对彼此的所思“穿梭似的彼此感到了”,相遇赠饭之后,浣衣女明白了“取”和“予”,“你”和“我”,伍子胥则体会到了“沉重的馈赠”。这一直觉把握净化与扩展了他们各自的生命,呈现出了一副唯美的生命图景。
综上,《十四行集》和《伍子胥》所体现出来的生命体,是内涵丰富的整体。生命没有因沉思而沉重,也没有因关注自我而忽略他人,体现出了一种生动活泼的灵动之美。
二、中和的审美
1941年,冯至在中断创作十多年后,经过长期的沉淀,火山爆发似地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二十七首的《十四行集》。而小说《伍子胥》则是早已喜欢的故事题材在十年之后的重新提笔。两部作品都经历了漫长的沉默过程,这正是作者不断沉思、内化,形成自己作品的独特主题与审美风格的过程。
对比冯至的日记可知,他创作时总是倾向于消解自己的茫然与困惑,赋予描写对象正面的、积极的力量。日记中对有加利树的感受是“惊悚”,《十四行集》中则写道“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日记中对飞蛾的感受是“虚幻”,在诗集中他写道“在它的飞翔内/时时是新生”。小说《伍子胥》,在作者的想象里本是“奥德赛”式的历险,却最终加工成了生命成长、圆满的诗化小说。经过艺术加工,作品中饱含着对生命的肯定,展示了坚韧的力量。
上世纪四十年代,冯至刚刚从欧洲游学归来。在“存在主义的圣地”德国海德堡大学,他聆听了雅斯贝斯、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课程,受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他没有将存在主义思想完全呈现在自己作品中,而是内化了存在主义思想,有自己的加工、再创造:作品中的生命体没有过多倾向于对孤独、虚无的体验,而坚持强调对责任的承担;没有过分强调自我本体,而是表现出以大我为本位、以群体为依托的群体本位思想。对存在主义的接受与消解使作品中的生命不是孤芳自赏,而是拥有昂扬向上的主体精神,是勇敢承担的生命体。
同时,冯至在留学期间,阅读了歌德、里尔克的大量著作,回国后又对杜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为他写传记。可以说,里尔克、歌德、杜甫是对冯至影响深远的三个人。里尔克是探索孤独、生死的个体诗人,歌德倾向于人格的完善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杜甫则是“人民的喉舌”,冯至在里尔克那里学会了忍受孤独,在歌德那里领悟了“向外又向内的生活”,在杜甫那里感受到了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的伟大。但是冯至在接受他们的同时有了自己的加工与创新,他避开了里尔克所看重的个体身心的神秘体验,避开了歌德对自然科学的热忱,避开了杜甫一生所处的微妙复杂的政治环境,因而他笔下的生命体既有对孤独的体验思考、与外界的互动,又有对自己命运的担当,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主题与风格——灵动的生命。
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即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冯至居住在相对安静的昆明,却也没有完全沉浸在象牙塔中,而是在体会着战争所带来的亲友离散、病痛折磨时,在文学创作中埋下安定的种子,以“灵动的生命”为主题创作,以求包孕自己思想的同时告慰大众的心灵,寻觅向上的力量。这一主题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承担与人文关怀。
综上可知,“灵动的生命”这一主题是冯至有意为之的艺术加工过程,他将自己受到的所有影响、自己的生命感悟内化为一股可控的力量,赋予了自己作品独特的内涵和审美气质。即避开生命中过于消极与悲观的因素,将孤独与温暖并列,从而使整个作品体现出“中和”的审美风格。
“灵动的生命”是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作品中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不仅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有所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里也有体现,例如散文集《山水》以作者自己的生活为切入点,用朴素自然的语言传达了他的生命体验。
四十年代的冯至,处于生命的沉潜阶段,在昆明平凡质朴的山水间得到了短暂的安宁。这一期间,他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内化了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各方面力量,以生命为出发点体悟、沉思,以中和为艺术手段加工、创造,“灵动的生命、中和的审美”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特色。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
乔瑢(1991—),女,汉族,甘肃岷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审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