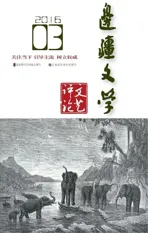关于废名和孙犁
2016-11-25朱霄华
◎朱霄华
关于废名和孙犁
◎朱霄华
作家与作品
主持人语:本期的编辑,读到一篇评论张直心《晚钟集》的文章,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张直心乃云南出到沿海地区的一位评论家,他在云南时就写过不少有见识有分量的文章,如今评论他的书评来了,也说出了一些道理。比如作者认为:此书“从民族‘文化史’、甚至‘精神史’的高度出发,让笔下画幅缓缓舒展,同时揭示出相关作品文学意义上的‘文本价值’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价值’”。“著者以自身的治学实践和实绩再次证明:任风声雨声裹挟家事国事,无论‘载道’ 、‘言志’ 抑或‘抒情’,有质感、有质地、有质量的思考和研究,均会因其坚卓的姿态、坚实的内核而外延深远,回响不绝!读书评令我怀想过去了的时光,有几分惆怅,也有几分欣喜。(蔡毅)
把小说当散文来写,又把小说、散文都当诗来写,而且都是极高明的,在现代文学史里,这个人舍废名其谁?
下午坐在丹霞斋,突然起身,从故纸堆里把废名找出来看,感觉当真有些花雨满天的意味。
我接触废名的作品是在很多年以前,从旧书摊上捡到一本砖头厚的古色古香的书,一看作者,居然署了一个“废名”的名字,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居然连名字都可以废弃了不要?就赶紧翻开来看文字,立即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我看到的最初几行文字,是《竹林的故事》里面的。站在旧书摊上一口气读过来,服了。中国白话文能够玩到这个份上的人,少见。后来听说连沈从文、汪曾祺师徒都在心里认他做老师,就更是对这位不见经传的白话散文大师恭敬有加。
作家要靠文字说话,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读废名,我读出来一种古意,他把中国文言诗词中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气通到白话里面来了。废名玩的是极少主义,高蹈、出世、有无、阳春白雪那样的东西。有无相生,有是着相,无是真相,废名把他要的那个现代汉语的真相——那个身体找出来了。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一般都要消化两个东西,一个是把西方的现代语体拿来用,一个是从自家的古语传统里面化出来,末了还要把两个东西弄成一个。这是一道工夫活,很不容易。你掌握了技术,还得有格物的本事,把时代的物格出来。两个功夫到家,写出来的白话才不至于变成白开水一样的东西。
现在回头看“五四”一代作家弄出来的白话,气息大多都对,但是落在语言层面上,问题就来了,大多数作家的语言都是夹生的,青涩的,有时是表达的方式太过于欧化(如李金发、曹禺),有时则是表达的内容手段太过贫乏(如徐志摩、戴望舒)。像老舍、张爱玲、胡兰成、沈从文、孙犁、赵树理这一路能够把民间语体植入书写的作家,不多。在他们手里,现代白话文就丰饶起来了,活起来了,很有些左右逢源的意思。这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文体大家。废名自然也是了不起的,如果照今天的说法,在现代白话小说一途,他完全就是一位所谓继往开来的人物。我以为,这是一个置身于现代的黎明却仍然安坐在油灯下写作的文体家。
沈从文有一篇论废名的文章《论冯文炳》: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文字,画出一切风物姿态轮廓……文字方面是又最能在节制中见出可以说是悭吝文字的习气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同一时是无可与比肩并行的。”
沈从文对新文学的辨别力无疑是一流的,他一眼就看出了那个时代最好的、但通常又是被时代的趣味所局限所忽略的东西。废名行文的语调,像是自言自语,把话说给自己听。很软。我以为这才是写作的本质。一个好的作家,总是把东西写给自己看的,鲁迅、孙犁、沈从文、郁达夫、汪曾祺,无不如此。声音一跑出来就龇牙咧嘴,关不住气,不沉着,像个站在云端里大喊大叫的女神一样,就不很文学了。
废名身上似乎还完整地保留着为旧时代所视为圭臬而又为新时代所抛弃的那个传统。他的语言总是自然的,本色的,一方面显得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又真气鼓荡,禅意十足。他是他那一个时代的另类,一个不单是会写小说的大学问家,他应该对佛陀所致力于抵达的世界亦有着很深的体会。
单就语言而论,我以为废名不在鲁迅、孙犁、沈从文、胡兰成之下。在他的那个时代,鲁迅的战场,张爱玲的市井,孙犁、沈从文的乡土,郁达夫、胡兰成的书斋,都得益于活性传统汉语方言诗性的汁液,但都比不上废名根深叶茂。废名好像是一个汉魏时代的人,突然跑到现代来定居、写作一样,把古汉语用毛笔写成了白话文。我记得废名的某个集子有一幅他本人的肖像照片,骨骼清奇,阔额,方面大耳,耳朵尤其大,耳朵往两边伸展得很开地立起,但是很安静,似乎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和听到。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一定是看到和听到了什么我们所从未了解的东西。
废名在以前官方编撰的现代文学史里面,一般都是略过不提。略过不提好,这样一来,他的名节就保住了,再说,真要去说他,恐怕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意识形态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面,不用翻书都晓得,孙犁大概是排在乡土文学那一章的某个小节,他被安排在为那些庞然大物的阴影所占据的某个角落里,是一个连脸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的人物。
记得大学的文学史教材,沈从文也是这个位置。他似乎立在孙犁的后面。
其实,站在这部垃圾文学史的什么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是从成千上万的读者中成千上万次地挑选出来的那少量的读者眼里射出来的那一缕贼亮的光。一代代的作家死去,湮灭于尘土,但总有一两个、两三个会慢慢地从凌乱而荒凉的乱坟岗走出来,被这缕贼亮的光照亮。
我把这种阅读的还魂术称之为文学考古的返祖现象。所谓的不朽与永久失踪,其最终的表决权到底还是又重新回到了万能的读者的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些站在时间铁幕背后的无名的读者,往往会作出使我们诧异的决定,文学气候的阴晴变化,跟他们脸色的明暗程度有关。
突然,一瞬间,几乎就是一瞬间,我听到来自黑暗的图书馆里的一声咳嗽,简直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孙犁这个老古董被发现了。在网上,孙犁的文学小册子动辄就冲到数百元、上千元的拍卖价位,1951年初版的《风云初记》280元,1959年初版的精装插图本《铁木前传》200元,1963年版的作者签名本《风云初记》888元,1959年版的《铁木前传》签名本360元,1982年版的彩色连环画《荷花淀》320元,1947年海洋书屋版的《荷花淀》820元,1947年东北书店版《荷花淀》480元,1950年读者书店出版的《农村速写》280元。就连1992年版的《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也卖到了680元,而原来的定价却只是280元。最贵的一套书,1992年百花版、有作者印章的《孙犁文集》珍藏版2000元,无加盖印章的,1000元。
当代中国文学界,长期浸淫在西方现代语境中写作的新一代小说家们,似乎是最近几年才突然醒悟过来,要想写出纯正中国味道而同时又可以抵达不朽的小说,希望并不寄托在西方的某个大师身上,原来我们身边也有过大师,比如,孙犁。2009年,11卷本的《孙犁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精装本的形式出版,以便在满足那些品味纯正的汉语读者的同时补充作家们日益枯竭的语言资源。
孙犁的作品究竟存在着何种魅力,乃至于让那些隐身的版本收藏家、潜在的读者、动机可疑的出版社在一个已经全盘西化了的时代如此眷恋不已?是表层的欲望已经退潮,还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浮躁的社会正在面临着新一轮的心理转型?不知道,总之是孙犁那些清心寡欲的、几乎被遗忘的作品再度回来了,人们在趣味坎普的客厅,在貌似高雅的文化沙龙,对孙犁如此津津乐道,就像在谈论着某位当年被主流意识形态开除的、具有着不俗品味的、只阅读线装书的祖父一样。
确实,孙犁作为一位寄身于红色阵营灰色地带的乡土作家,对总是对把自己推到时代鼓手位置上的新势力,对仅仅是来自于左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遵命文学,常常有着一种消极的,有时是一种经过伪装的反抗和免疫力。他没有被说成像沈从文那样的粉红色作家,乃是因为从他的笔端冒出的许许多多普通的小人物,乃是来自于乡土的民间,而这些小人物又通常都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处在危难时刻的民族的脊梁,更何况这些小人物组成的群体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有革命觉悟的,是在某种政治正确的方向的引导下的沉默的大多数。孙犁最好的作品,是他描写解放区男男女女的那些极为出色的小说和散文,是《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荷花淀》和《山地笔记》。这些作品的主题不单是具有着罕见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性,它们同时也是自然主义的,人性的,温和的,对具体的某一个来到笔下的人物总是采取一种既客观又克制的态度——说到底,身为作家,孙犁采取的是一种对人对己、对那个时代及其那个时代的文学都极端负责的态度,他并非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并非是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为所谓的经典写作的作家。孙犁的文学道路并不具有任何的传奇性,他只是把他见到的、打过交道的平凡众生照实写下来,如此而已。然而,他又是一个文体意识极为强烈的作家,严格遵守着为传统的语言炼金术所发明的那一整套律法:任何形式的文学语言,都必然建立在其本身自成一体的生命系统之上,因为语言自己本身会呼吸。
在一篇并不引人注目的、题为《光复唐官屯之战》的通讯体报道里,孙犁描写了一座城池的解放,解放军是怎样从国军手里把这座城收回来的。在我看来,这篇通讯堪称报道体文学的一个罕见的典范,孙犁在处理这个纷纭的题材时发明了一种结构主义的诗学,既惜墨如金又不放过任何细节,短短1200字的篇幅,分成八个片段,叙事与描写交叉进行,语言客观,简练,不动声色,攻打一座城的前后过程,呼之欲出,如在眼前。这篇通讯报道让我看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作家是怎样成为功力深厚的语言大师的。
与孙犁同时代和处在同一语境之下的作家,湮灭者十之八九,作品不能流传是总体的命运。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跟革命、乌托邦、集体主义的流行话语有关。孙犁是低调的,他只描写那些为他所亲历和感兴趣的小事件和小人物,但这些小事件和小人物一旦来到他的笔下,就会变得栩栩如生,散发出鲜活、朴素的魅力。阅读孙犁的作品是一种享受,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作家。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