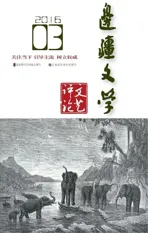西南联大诗歌小说散论
2016-11-25◎余斌
◎余 斌
西南联大诗歌小说散论
◎余 斌
学人观点
主持人语:余斌先生的历史文化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自出版以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这期刊发的《西南联大诗歌小说散论》,依旧显示出余斌先生治学、撰述论从史出的严谨与识见。在这篇论文中,余斌先生以充分的史实论述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多元色彩,指出了“昆明现代派”在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中心地位及其诗歌精神在当代的传承。论文写得平实,字里行间隐含颇多识见。
青年学子王慧的论文从“秘史”的角度探讨了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表现特征与思想内蕴。论文视角独特,解读细致,对小说“秘史”的特征有所阐发。陈忠实先生前久不幸病故,刊发这篇论文亦是表达本刊对这位当代杰出作家的哀悼与致敬。(胡彦)
引 子
西南联大是个说不完的话题。的确,西南联大有许许多多的传闻、逸事、掌故被津津乐道,少数可考,大多数只能姑妄听之。但那些传闻也有其价值,它同一般民间歌谣、传说一样,虽不能究其实却可以采其神,古人采风不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吗?《汉书·艺文志》有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西南联大的许多传闻之所以长期被人津津乐道,不正表露着一种仰慕和向往吗?从中不是可以得到“知得失,自考正” 的启示吗?
当然不能将传闻一类不加辨析、考证就当史料来用,此乃治学之常识。西南联大研究怎么可能靠传闻一类来支撑?笑话了。
西南联大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已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在云南文学史上让西南联大缺席显然不当,它毕竟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发的。八九年的时间不算长可毕竟也是一个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
西南联大作家可分教师和学生两类。前者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钱锺书、叶公超、陈铨、孙毓棠、川岛,后者如汪曾祺、马识途、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王佐良、罗寄一、马逢华、鹿桥、宗璞、董易、赵瑞蕻,等等。
联大教师里的名家不少,但大多忙于教学和研究,文艺创作不大顾得上了,虽然也还参加文艺活动,是著名作家但不是一线作家了。
一线作家主要是沈从文、冯至、陈铨三位,比较特别的钱锺书、卞之琳、叶公超三位也值得一说。
西南联大文学也分两类,一是师生们在校时期(抗战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二是战后创作的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是小说)。试以小说、诗歌这两大门类为例,对西南联大文学做一些初步的梳理和评述。
联大诗人很多,教师里有闻一多、陈梦家、冯至、卞之琳,学生诗人比老师多,主要是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王佐良这五位。罗寄一、马逢华、赵瑞蕻也是不错的。
一般所说的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主要指这些联大学生。老师其实也应该算进去。冯至在昆明写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联大的叶公超和云大的赵萝蕤两位老师也该算进去。叶公超是将艾略特的诗和诗论向国内进行介绍的第一人。艾略特《荒原》第一个中文译本(1937年,上海)是赵萝蕤翻译的,叶公超为之作序。1940年春,重庆中央大学宗白华教授约赵萝蕤为《时事新报·学灯》写了《艾略特与<荒原>》。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联大诗歌,主要着眼于那些诗人已经形成流派,其影响延续到八十年代,乃至今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1948年正式形成的九叶诗派,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都是重要成员。九叶派诗人并非只有九位,那九位是核心,包括辛笛、唐祈、唐湜、陈敬容、杭约赫,他们五位不是联大的。
联大写小说的作家也不少,老师有沈从文、钱锺书、卞之琳三位。钱锺书写《围城》广为人知,知道卞之琳写过游击队打日本的短篇小说《红裤子》的人极少。学生写小说的比老师多一点,如中文系的汪曾祺、马识途,外文系的鹿桥,历史系的董易,联大附中学生宗璞,创作成就都值得认真研究。他们先先后后,各写各的,除汪曾祺外开始创作都在离开联大以后,有的像董易,开笔已到晚年。他们各写各的未形成流派。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形成流派才有文学史价值,多声部交响乐也是非常好的。
西南联大诗歌
先说联大诗。
穆旦(1918─1977)写的那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为经典。1945年初,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探险队》。两年后又在沈阳出版了《穆旦诗集(1939—1945)》。王佐良的评论《一个中国新诗人》附于集后。在这篇文章中,王佐良不但对穆旦的诗作了独到的分析,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在中国文学界第一次对“那年轻的昆明的一群”进行整体审视,分析了他们的诗作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西南联大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关系。在王佐良晚年写的关于穆旦的文章中,这“一群”被明确地称为“四十年代在昆明出现的中国现代主义”,或“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这群西南联大学子的校园诗,标志着昆明现代派的崛起,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奇特的高峰”(张同道语)。而穆旦就是这一群这一派的旗帜。王佐良的此一观点已为学界相当认同,有些学者评价更高,认为穆旦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而不仅仅是“之一”)。
杜运燮(1918─2002)也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他1945年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辗转于重庆、新加坡、香港等地。后投入新中国建设,1951起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和翻译,晚年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杜运燮人生经历的亮点是抗战时期参加中国远征军,历经从云南到缅甸到印度的战争死亡线,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都产生了不同于常人的感悟和认知。他1942年写于昆明的诗《滇缅公路》广为人知,时24岁。这是一首独特的彰扬中国军民抗日精神的诗,其特点是把“静止的公路作为动物来写,使它进入充分的动态”(袁可嘉语)。他既是 “昆明现代派”的重要诗人,也是稍晚形成的“九叶诗派”(1948)的重要成员。杜运燮比穆旦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新浪潮。他1979年写的一首题为《秋》的诗,发表后被一位部队作家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中提出批评。当时正在崛起的一个以舒婷、顾城为代表的诗歌群体,因之而被称为朦胧诗派。这正好表示出这位老诗人诗歌生命之树常青。他的诗集主要有《诗四十首》、《南音集》和《杜运燮诗精选100首》等。晚年与北师大诗评家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
郑敏(1920─)福建福州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稍后即转哲学系1943年毕业。郑敏是此一群体中的唯一女性,早期主要作品为《诗集1942─1947》,与穆旦、杜运燮两位后来被人并称为“联大三星”。1948年赴美留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60年起任教北师大外语系。到了新时期,早被边缘化的郑敏不再囿于书斋,她以一首《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重新露面,欣喜地投入中国诗歌新浪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日本学者秋吉久纪夫1999年编译出版的《郑敏诗集》,除旧作外还收入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等1986─1991年以来先后问世的新诗集,该书由日本土曜美术社出版。(这里顺便一提,由日本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诗人”丛书计十种,西南联大师生冯至、卞之琳、穆旦、郑敏占其四。)
同时女诗人以开阔的视野,与时俱进地投入诗的研究与评论,深度介入现代诗的论争。《诗刊》1980年8月号上那篇《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署名晓鸣)就是她对《令人气闷的朦胧》的回应。1982年她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创刊号发表评介西方现代主义的文章《庞德,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力度加大,锋芒更露。厐德是美国现代诗人理论家,他的“意象”理论和《诗的几条禁例》,是针对冗长、陈腐、喜欢感伤、布道的十九世纪末诗歌,投去的两颗手榴弹,轰开了现代派诗的操作面。郑敏秉承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的革新精神,针对八十年代中国诗坛也大胆提出《几条禁例(仿厐德)》,如:“不要让诗变老,瘦骨嶙峋,没有丰肌”;“不要只求得粉红色的肌肤而没有健康的骨骼”;“不要让教条当红灯截断了真情实感的潮流”;等等。更引人注目的是,郑敏近些年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回顾,对新诗现状的观察更宏观也更历史,提出要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主张借鉴古典诗词,使民族传统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相交融。已出版《郑敏文集》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社,2012年),文论占其三。这位当年的联大女诗人如今是中国当代诗学理论重镇,倍受尊崇。
袁可嘉(1921─2008)不能被遗忘。他是浙江慈溪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后任教北大,再后长期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晚年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纯粹一位学者。其实他是从写诗起步的,早在1944年他就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歌颂抗战的《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战后他又写出了“应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沉钟》);“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难民》)这样耐人咀嚼的诗篇。也许袁可嘉在校时写诗尚少未被列入“联大三星”,但在四十年代末出现的“九叶诗派” 中,袁可嘉毫无疑问是-位要角,他集作诗、译诗、评诗和选诗于-身,在诗学理论上建树尤隆。在八十年代的新诗潮中,袁可嘉更是一位现代主义的启蒙者,他的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和多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成为那一时期青年学子和青年诗人、作家趋之若鹜的启蒙读物。
除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外,此一群体还包括外文系的王佐良、赵瑞蕻和经济系的罗寄一、马逢华等。
赵瑞蕻挑出来单独说一下,读过他翻译的《红与黑》和《梅里美短篇小说集》的人极多。他年轻时也写诗,并写过一首很特别的诗,题为《一九四0年春:昆明一画像》。赵数十年后回忆说,“这首诗或许是我国新诗中采取现代派手法唯一集中描写日本鬼子轰炸的长诗” 。诗160行,在当年算长诗了(不比现今,动不动就是几百行)。长不长且不论,要看他怎么个“现代”法。开头先写学校午饭后的休闲时光:有同学在弹吉他, 还有同学在念艾略特的诗,说这可助脑神经消化。还有同学说刚吃过中饭干吗这么用功?接着是报纸新闻讲蒙自昨天被敌机轰炸:“青青的麦穗受了重伤,三十九架,/沿着滇越铁路,盲目投弹;/啊!我们亲切的南湖,尤加利树,/树上栖着,飞着灰白色的鹭鸶,/蒙自,那可爱的小城又遭殃!” 才写着蒙自遭袭的新闻,马上又闪回昆明,闪回联大学生宿舍,闪回三千里外家园,再后又闪回此时此刻的昆明:“听说又有‘预行’,很可能要来了!/隔壁双层床上打鼾声,有人酣睡,/(宰予昼寝,朽木不可雕也)/他是个大胡子,学中国哲学的,/(秋夜灯下,展读《罗马帝国兴亡史》,/做着夕阳古道的残梦,一切都在消逝……);/同学Y爬上摇晃的上层床,呆坐着,/忽拉起胡琴,调子是凄清的;/有人急忙地从外边跑进来,报告:/已挂上红灯笼了!人们开始往外逃,/(对,正好,我讨厌下午第一堂课)/还在做梦:三千里外的家园,/母亲来信说:今年桃花分外艳鲜,/可是满城骚乱,海上常有敌舰游弋……/那些抒情诗的年华已烧成灰烬!──/穿红衫,骑青骢,结伴踏青,/还有断桥,采菱船,杏花春雨;/(整个华北苦难的雨正在滂沱……)/梦着五十九架,三批,突袭滇南,再往北,/心猛然一跳!越过红河,弧形的是铁路线,/闯入棕黄色的大地,莽莽山林里……/啊,昆明震动了!昆明站起来颤抖,/昆明再一次愁眉苦脸,/下午三点又三刻钟。人们惶恐,/走,一块儿走吧,别太紧张,/带副朴克、象棋,一本浪漫派小说,/今儿可糟了,真来了吗?空袭!”
下面才开始写当天下午三点三刻跑警报后的情形:
一口气跑了两里半,流着大汗,
沿着公路两边田沟里走,
怀着希望,疑惧,躲进柏树林里吧;
……
坐在地上,背靠树木,年轻的一群——
不知什么经纬度上长出了烦忧?
什么心田能萌芽爱情诗的灵感?
……
这会儿,溜进一个防空洞,
竟有人开着话匣子:红鬃烈马;
……
(今天又有警报,钱塘江大桥早炸了,
是咱们自己干的!对,阻挡敌骑南闯;
又炸死上百人,家里逃到乡下了……)
我忽然想起故乡的落霞潭,
双亲在日夜想念着我……
这会儿,我遇见好几位教授,
多可敬的老师啊,艰苦环境中,
坚持讲学著述,颗颗热挚的心!
抽烟斗的,跟同学们聊天的,
什么也没带,只是笔记本、讲义,
一块灰白布裹着一部手稿,
几本心爱的书;还有比这些更珍贵的吗?提只破皮箱,智慧在里面欢唱;
逻辑教授笑眯眯的,踱来踱去……
接着又是颐和园,水木清华,《浮士德》里的名句,紫丁香花瓣夹在一本C.罗色蒂诗集里,……突然,敌机到昆明了:“绮梦破碎了!轰炸!轰炸!/敌机飞临头上了!──/昆明在颤抖,在燃烧,/不知哪里冒出浓咽,乌黑的,/仿佛末日幽灵;叫喊声,/哭声,血肉模糊──/轰炸!炸死脆弱的诗句吧!”
诗一引才觉得确实是长诗,不能再引,但风貌应该可以看出来了,意识流式的,小说可以那样诗也可以。有意思的是赵瑞蕻这首诗有个副题叫“赠诗人穆旦” ,似有与诗友切磋之意:你看我这首这么写行不行?诗是1940年在联大写的初稿,两年后在重庆中央大学订正,在昆明版《中央日报》上发表,该报文艺副刊《平明》是由朱自清、沈从文两先生合编的,老师的扶持不言而喻。
这里之所以特别将赵诗引出,又引了那么多,意在说明两点:第一点,这首写联大师生跑警报的诗虽然手法比较现代,但现实主义色彩仍然鲜明,此乃战争环境使然。此诗写于40年代初,汪曾祺那篇《跑警报》写于三四十年之后;前者写的是“当下”,后者写的是回忆,染上了比较浓的玫瑰色,浪漫一点,温馨一点。诗人赵瑞蕻为昆明1940年春作的“画像”当更接近于历史。再一点,赵瑞蕻后来虽以译家名世,当年却也热衷于诗,而且起点高,很难得。这与联大当年的环境氛围很有关系。朱自清早年写过不少诗。专心写小说的沈从文也写过诗,陈梦家编的那本《新月诗选》里选沈诗六首(朱湘、卞之琳、林徽因各四首),并赞沈诗极近于法兰西的风趣,质朴的词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汪曾祺1957年初发表的小诗《早春》仅三行:“(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象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挺新派的。我未见过汪曾祺在联大读书时写的诗,想也写过吧。联大诗风是很盛的。
还说“联大三星”里最亮的穆旦吧。可叹的是他走得太早,他活到文革终止一年之后的1977年(才59岁),却未能与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西南联大的那些同学们和诗友们一道,再次投入中国诗歌的新浪潮,可惜啊。庆幸的是,正是在穆旦历史性缺席的八十年代,这位杰出的诗人被重新发现并真正被认识了。不少人以惊喜的然而又是崇敬的心态读穆旦,学穆旦。这么看,穆旦并未缺席,他以自己的作品投身于八十年代,影响着那个年代。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从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王佐良等西南联大诗人群(或称“昆明现代派”)在三四十年后的新诗潮中的表现来看,说此一群体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演进历程中承先启后,是一点不带夸张的。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诗的基地在大学校园(张同道)。的确,校园诗的走向和流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尽管还不是决定着)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事实上,四十年代的中国诗歌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延安的工农兵诗歌(以学民歌为主流,比较接地气),一个是昆明的现代派诗歌(视西方现代派为圭臬,人文色彩浓)。昆明现代派之所以产生并崛起,主要原因有两点。无可否认的一点是西南联大有独特的文化环境,具体讲就是外文系教授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传播。中国老师主要是冯至和卞之琳两位,他们当时都在作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现代主义探索,并把这种探索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冯至,他在昆明金殿后山写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的、标志性的收获。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对外文系学生讲授艾略特和奥登,他们都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燕卜荪不是二传手,他本身就是深受艾略特影响的英国现代诗人,他的传播是第一手的。这点很重要。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战争环境,这是昆明现代派形成并崛起的极重要的条件。战争拉近了青年与社会与现实的距离,促使人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不仅仅是跑警报,不仅仅是感受到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的艰难。有些学生直接参战当兵,当美军翻译。其中两位参加远征军到了缅甸和印度。这样的战争经历使他们有机会认识了中国和战争的另一面。因此,他们写诗就不会是对西方现代派的简单模仿,他们还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情感投入,其中有爱国主义,也有非机械反映论式的现实主义。如果缺乏这种民族式的情感投入,那么所谓学艾略特学奥登,将不过是学生做习题式的技术训练罢了。穆旦那一群青年诗人当然不是这样。
是的,昆明现代派存在时间没有几年,但成就很大,影响也很大。他们的诗作和诗学理论深度介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新崛起。2014年,昆明地区的部分诗人和诗评家在云南师大集结,打出“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旗号整体亮相。我们有理由对此抱以期待。
西南联大小说
联大时期的沈从文无疑是联大小说的主帅,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是沈从文昆明时期在创作上的重要成果。这是继《边城》之后沈从文的又一力作。沈从文还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小说《摘星录》《看虹录》。至于学生写小说,那可是凤毛麟角。何以故?就作者讲,写小说需要较多的阅历和生活积累,下笔不易,这与偏于主观表现的写诗毕竟有所不同。就客观而言,小说体量较大,靠一般壁报或油印显然困难。沈从文在联大教写作课于此深有感受,他想到办刊物这一环节的重要。说刊物是园地也好,阵地也好,反正要有个地盘。他在1941年2月3日给施蛰存的信中对此有所涉及。施氏抗战初期原在云南大学任教,与沈极熟。两三年后施氏离滇转赴东南沿海。沈氏在信中议论联大及昆明文坛情形,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真是作家眼力,一下就发现了文学人才。但只有学生壁报是不够的,应该还有正式出版面向社会发行的刊物才行。而现状却难让人满意,昆明文协先后办过《文化岗位》和《西南文艺》两个刊物,报纸副刊版面有限。联大教授办的《今日评论》,云大、联大几位教授办的《战国策》,虽也编发一点文学稿件(正好由沈从文来编),但刊物性质毕竟不同,不可能像以前他为《大公报》编副刊那样,为联大的汪曾祺们尽力,所以他在给施氏的信中又说:“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很是无可奈何。汪曾祺昆明时期有小说发表,但不多。如写于1945年前后的《复仇》《老鲁》和《落魄》,都是短篇,单薄些,1981年有所修改,少了些青涩。《悒郁》是1940年的草稿,模仿沈从文老师的痕迹还比较明显。汪曾祺,还有其他一些联大毕业生,进入大社会后才得机缘进一步展示写小说的才华。
沈从文、汪曾祺不再议,下面只就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的几部长篇小说,即鹿桥的《未央歌》、宗璞的《东藏记》和董易的《流星群》作评述,钱锺书的《围城》也顺便一说。
《未央歌》是一部写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校园小说,在台港及海外华人圈已走红数十年。大陆比较隔膜,1990年才由山东一家出版社出过,据闻营销不善,印出的书基本上又还原为纸浆,十分可惜。未想十多年后安徽重新推出,而且引起了相当的注意。
我之所以注意此书是因为它写的是西南联大,写的是抗战时期的昆明,对我来说这就是看点。这方面的小说以前很少,能数得上的恐怕也就前些年获奖的宗璞那部《东藏记》(此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和董易的两卷本长篇《流星群》了。前者主要写教授,后者专写联大地下党,都很有价值。鹿桥的《未央歌》主写西南联大校园,也写昆明风情,写得都好,写得饱满(五十五万字),而且写得早,1945年在美国脱稿。
鹿桥本名吴讷孙(1919-2002),祖籍福州,生于北京,长于天津,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留美入耶鲁大学专攻美术史,日后成为著名的艺术史教授。他在小说的《前奏曲》里说自己十分怀念那段才结束不久的“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可惜“已无力挽住这行将退尽的梦潮了”。说是这么说,鹿桥还是将他的梦潮挽住了。他毕业留校不久就去了重庆,在那恶劣的环境里更加怀念在联大、在昆明的岁月,于是萌生了写作的想法。《未央歌》共十七章,前十章于1943底在重庆写成。第二年他考取自费留美,并在1945年夏写完小说的后七章,时年26岁。但这部作品直到1959年才在香港自费出版,随即在台、港两地引起轰动。1967年该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80年普及本已达26版之多。
通过以上一段文学背景的回溯,可以看出《未央歌》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以普通学生视角写西南联大校园,一是以“外省人”视角写昆明。这里只说第一点。
早先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的作品,包括小说在内,大都着眼于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毫无疑问,这是西南联大历史的极重要的一面,应该大写特写。事实上也确实写了不少(小说不多,主要是回忆性文字),也可以说是“大写”了,而“特写”则说不上。民主运动是重要的一面,但一面毕竟不等于全部,都写这一面,就不“特”了。宗璞二十多年前开始出版的长篇系列《野葫芦引》可以算很特的一部。从作者的整体构思来看,以历史系教授孟樾一家为中心,从流亡南渡写到胜利北归(另两卷名《西征记》和《北归记》,后者尚未问世),显然是历史的大视角。从前两卷看,《南渡记》写北平沦陷前后,末两章开始南渡,止于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小说里的“龟回”指蒙自)。正面展开写西南联大昆明生活的是《东藏记》,里面写了教授们的情感、操守、艰苦及人情世态,也涉及民主运动,但比较间接,是作为背景。宗璞是老作家,当年就生活在联大环境中(联大附中学生,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文字相当地雅驯,简洁,小说的品位没说的。但读后会感到不满足,主要是觉得生活面的书写欠饱满,现场感有些弱,无论大环境的呈现还是生活小环境的细节,都让人觉得笔墨过于省俭。
《流星群》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部小说专写西南联大地下党活动,分两部,第一部叫《青春的脚步》,以昆明为背景;第二部叫《走彝方》★,背景为滇南彝区。小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可惜反响不大。这部小说虽然题材不算新,但写法可以算“特”。特在两点。一是有相当的文学性,这与早年那些正面写一二·一运动的作品一比就高低自现。第二点更要紧,小说是以反思精神来写那一段青春岁月的,其中有关于革命理想主义被庸俗化为教条主义的反思,有关于人性被“异化”的深度思索。这些思辨的光辉不但是此前关于西南联大的同类作品中所无,也是杨沫那本影响极大的《青春之歌》所不曾有过的,应该说也是不可能有的。有论者指出,思想家顾准用最后的生命之光探索的那些问题,正是《流星群》以文学的方式来探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流星群》最大的亮点,十分难得。我们今天要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思想谱系和不同的思想表现,我想应该不限于研究教授们(这无疑是主要的),而且要研究那些又有理想又会思想的学生们,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和思想的“流星”。在这个意义上讲,董易的《流星群》有着其它联大题材小说所不可能有的价值。虽然这部小说至今读过的人尚少,不像另三部那么广为人知(《围城》《未央歌》在海内外早享有盛誉,《东藏记》2005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董易原名董葆先(1919─2003),满族(父亲董鲁安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赴延安),1938年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就读,并从事地下党活动,五十年代初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晚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流星群》书稿是董易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开始动笔的一部遗作,生前无人知晓,包括亲人。这部小说虽然与此前的同类作品相比具有相当的文学性,但文学性还不能算很高。作品特在思想,胜在思想,却也存在此前同类作品常见的“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这使作品的可读性难免受到影响。
鹿桥的《未央歌》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在写作时间上比董易的《流星群》和宗璞的《东藏记》早了三四十年。鹿桥刚离开联大就动笔写,那是一种激情难抑的青春书写,才过去没几年的校园生活,还来不及定型为“记忆”就被他鲜活水淋地写出来了,从而定格为真正的记忆。加之早年的文化语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与数十年后之不同,以及外文系一个普通学生的特点,这些因素的合成,对作品风貌,对作品特质的形成,是有决定意义的。概而言之,作者正在形成中的记忆尚未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这使他的作品更多地具有校园生活的原生态面貌。所以在《未央歌》里,我们看到的是西南联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以及昆明的山光水色和乡土风情。至于教授师长,偶尔也写到一点,点缀罢了。鹿桥不可能去写宗璞写的那种教授生活,他不熟悉。鹿桥更不可能去写董易写的那种地下党活动,那在普通学生的视野之外,我甚至怀疑鹿桥是否知道那种生活的存在。据史料可以看出,学生与政治的距离是各各不同的,比如外文系学生,他们经济条件一般较好,与政治的距离一般来说也就比较远;读师范的学生经济条件一般较差,与政治的距离一般来说也就比较近。这当然不是绝对的,比如《流星群》里写的人物陶思懿,其原型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家在重庆,经济条件不可谓不优裕,读的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系,她入学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类似的例子绝不止一个两个,但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估计。据党史资料,师范学院是地下党工作的重点,这绝非偶然;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的四位烈士中有两位是联大学生,一位叫潘琰,一位叫李鲁连,都是师院的学生,这同样也非偶然。
西南联大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多元素、多色彩的生活,说它丰富也好,复杂也好,反正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好说写哪种色彩真实,写哪种色彩就不真实。多元的生活,在文学(主要是小说)里就会作多元的呈现。《未央歌》所写的联大校园生活,与《流星群》写的地下党活动(也是学生),确实差别太大,它们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在艺术上,《未央歌》像一部抒情歌剧,而《流星群》却有着浓厚的悲怆色彩,它是一群命运失败者的颂歌,作者怀着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去写他和他的同志们、同学们在联大在云南的那段青春岁月,回头看大家都像流星,一颗一颗地坠落了。总之,当年联大学生写的这两部小说在思想光谱上和艺术色彩上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所具有的思想史的和文学史的双重价值,不应该被我们忽视。
当然,对一部作品,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读者群,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再正常不过。比如《围城》(作者钱锺书抗战初期也曾在联大任教),虽获普遍赞誉,但据说不少“联大人”并不喜欢。揣度起来,大约钱锺书这部小说也有西南联大的人事影子,而部分“联大人”却不认同钱氏那种“戏说”的写法。这没什么,各写各的。《东藏记》也写教授,但视角与《围城》不同,风格亦异。《东藏记》是正剧,《围城》是喜剧。《未央歌》与《围城》当然也可以比,前者写学生后者写教授,这是题材选择上的区别;至于风格,《未央歌》有作者的影子在,精神自传的味道比较明显,而《围城》像一位智者高坐山巅笑看人间喜剧。
关于《未央歌》这部小说的总体评价,大致来讲,台港及海外评价较高,大陆则比较低调、保留。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说自己在研读了近百部小说之后,认为在战时战后时期,巴金的《人间三部曲》(即《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名书》和鹿桥的《未央歌》,构成了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还说这部《未央歌》“尤使人神往”,它既是一部“可歌的散文诗”,也是一部“巨篇史诗”,评价极高(见司马氏著《中国新文学史》)。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与世界各地华人专家联合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未央歌》列第七十三位。大陆学界则比较漠然,难见评论,但在一篇党史文章里却也透出消息,作者熊德基(1913—1987)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与鹿桥同为1942年毕业。在校时期历任师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和联大总支书记,晚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对《未央歌》明显持保留态度。他在谈到对西南联大的认识时说,联大“决不是如小说《未央歌》所反映的那种安乐窝或世外桃源。虽然小说中描绘的昆明风土人情,有其符合真实之处,但书中的人物在联大师生中只能代表极少数,并不具有典型意义。这部小说虽然曾在台湾和海外青年中风靡一时,实际上没有写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见1988年发表的熊氏遗稿《我在西南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或许,这正是海内外视角之不同罢。但这个不同是会变的,毕竟数十年过去了,海内外的认知会渐趋于同。有趣的是,上面说的三四部小说均出自“联大人”之手。《围城》写一面,《东藏记》写一面;《未央歌》写一面,《流星群》写一面。将这几“面”合起来,读者就会看明白西南联大这个色彩斑斓的多面体。这很好。
插 曲
抗战初期诗人卞之琳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红裤子》,是八路军的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乍一听有点意外,问是不是那个写《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我说就是那个卞之琳。
事情是这样。诗人卞之琳1940年起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前曾任教于四川大学(1937─1940),其间一度赴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39)。还写过一系列关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如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和诗集《慰劳信集》等,其中有篇小说叫《红裤子》,说的是山西八路军游击队引导农民抗击日寇的故事。山西省有个离同蒲路不远的村子常受日寇侵扰。一日村里得消息说日本鬼子要来“宣抚”,如果预先逃跑一人,“皇军”到了就不给村子留下一所房子。“于是全村震动了。娘儿们一下子就学了‘摩登’,把头发都剪短了。不过最惹眼的还是红裤子”。村里的女人平时都穿红裤子,只好都一齐换掉了红裤子。游击队员关小双的老婆最漂亮却为无裤子可换正发愁,关小双决定夫妻换裤,老婆穿他的黑裤,他穿着老婆的红裤子跑了。有三个日本鬼子一看是红裤子就追,愈追愈远,追到山里去了再没回来。结果是游击队活捉了三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夺获了三支步枪三匹马,招来一村男女老少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司令部说要犒赏关小双,还穿着老婆红裤子的关小双说“我只要一套军服”。
卞之琳将作品寄昆明友人,用笔名“薛林”发表在昆明《今日评论》上。这篇《红裤子》很快就被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叶公超译为英文刊于英国杂志。其间的情形据卞之琳讲是:“公超也热心抗战,读了这篇短篇小说(《红裤子》)就把它译成英文,由燕卜荪介绍给英国《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发表了。”
这里要作个说明,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形,笔者托伦敦王丹璐小姐搜索刊发英译《红裤子》那期的《人生与文章》杂志。经查,这家刊物几度更名,刊发《红裤子》时刊名为《今日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 TO-DAY),栏目为“故事”(STORIES),篇名仍为《红裤子》(THE RED TROUSERS),作者薛林(Hsüeh Lin),叶公超译(Translated by Yeh Kung Ch'ao),刊期为第23卷第26期(1939年10月)。
这可视为联大作家群的一段很有意味的插曲,对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或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都有一定的价值。
*这里顺便一提,“走彝方”似应为“走夷方”。在云南,所谓夷方并不限于彝族地区,而是泛指滇西、滇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及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地域覆盖面上与南方丝绸之路相近。“夷”并非专指彝族。《史记》讲的“西南夷”即泛指西南少数民族,涵盖面很广。《走彝方》的作者或编者,许是觉得“夷”字隐含贬义而改用“彝”字吧,其实不必,反映民族融合的“夷娘汉老子”一语就未改,一改范围就缩小了。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