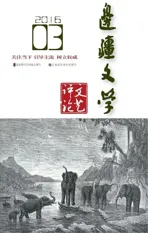作为“秘史”的《白鹿原》
2016-11-25◎王慧
◎王 慧
作为“秘史”的《白鹿原》
◎王 慧
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之所以如此,从作家创作的一面讲,离不开作家对传统小说创作规范的大胆突破。这种突破是多方面的,从思想的深入开掘到刻意求新的审美表现,无不体现着作家锐意进取的姿态和突出禁区的决心,而在所有这些突破性的创作实践中,立意写一部“秘史”,应该是作家立场最鲜明又最易于被认识和把握到的一个方面。本文对《白鹿原》的认识,正是围绕对作品“秘史”性质的阐述而展开的。
一、如何界定秘史
对“秘史”的准确把握和界定,应该是认识和理解《白鹿原》“秘史”性质的第一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白鹿原》开篇之前,陈忠实引用的这句巴尔扎克的名言是我们把握和界定“秘史”含义的起点和重要线索。本文之所以选择“秘史”一词作为论述的中心,正是基于作家的这一引用。当然,从根本上讲,是作品内容的某些方面与这一名词的强烈契合决定了这样的论述切实可行。另外,因为“秘史”是被用在《白鹿原》这一特定语境中的,这就决定了“秘史”有其特定的含义,也即,对其含义的把握和界定应该从《白鹿原》这一文本的语境出发。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笔者认为,《白鹿原》中的某些事象表现出的神秘化、奇观化的倾向是“秘史”一词在文本中的特定含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作家立意表现并在整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这反过来证明了,作家在开篇之前对巴尔扎克名言的引用也不是偶然,它必然是一种建立在对作品整体把握基础之上的引用。因而,我们对“秘史”的分析和对其含义的界定也是有意义的。
具体而言,《白鹿原》的“秘史”性质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性的题材
《白鹿原》中有大量对性的描写。在性与秘史的关系方面,作家本人就有专门论述,这些论述正是基于《白鹿原》的创作展开的,作家在《性与秘史》一文中说道,性是“揭示白鹿原民间‘秘史’和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构件”[2]。在这一句话中,作家同时道出了性描写的“秘史”性质,及其在《白鹿原》这一具体文学作品中发挥的作用。
从文学与性的关系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在性这一命题的涉及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白鹿原》正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写性的典型代表。这之前,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中,性是不宜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的,这是由封建的道德观念决定的。
此外,性的私密性也决定了性与“秘史”的必然联系。
(二)民俗仪式的原生态描写
《白鹿原》是表现封建家族命运的小说,封建农村社会中的民俗仪式在其中有大量而生动的表现。民俗仪式之所以具有秘史性质,是由它的民间性决定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民俗仪式的非官方性质,使得不同的民俗仪式总在特定的地区和时期内流行,进而使其隐秘性和独特性得以彰显。
另外,在传统观念中,民俗仪式中包含了许多积极有益的东西,同时有另外一些神秘性的东西,长期被简单地视为文化糟粕、封建迷信。传统的文学创作在处理这一类描写对象时,往往采取一分为二,选择性表现或批判的立场。《白鹿原》则突破了这种思维,作品对几乎所有的民俗仪式均本原地展示,不作褒贬,以期忠实地表现民俗仪式中的人及其心态、精神世界,使读者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判断。这是《白鹿原》可以称为“秘史”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原因。
(三)超验事象的展示
鬼魂、神灵、梦境等事象充分表现了秘史在神秘性方面的作为,也是《白鹿原》对写作传统大胆突破最重要的一个表现。这类事象的展示在作品中俯拾即是,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成为了深化作品思想内蕴和审美境界最为有力的创作手段。这类事象的展示又是多样的。比如在白鹿神话中,白鹿被描写为原上的精灵,与原上人事有着重要而隐秘的关联,并且成为了一条贯通全书的叙述线索。比如作品中的朱先生,作为人却常常有着类似神的预见和作为。又比如作品中人物的梦境,不同的人常常做相同的梦,又总是与现实相关,甚至在现实中得到毫厘不爽的应验……所有这些,形式多样,但都应当是秘史的一部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秘史”,在笔者认为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个词,是一个整体,单独说“秘”与单独说“史”,都不足以表现作品中以上三类内容所代表的全部意蕴。比如第一条,“大量写性”,离开了“史”的意义,就不成其为“秘”,就不足以展示作品中此类描写的完整意图。因而,本文所讲的“秘史”,不会专门涉及《白鹿原》的史诗性质,而是将“秘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进行论述。
二、“秘史”的意蕴
笔者从《白鹿原》这一特定文本的语境出发,将“秘史”的内容界定为三类,并对界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简单论述。无论是对性的大量描写,对民俗仪式的原生态展示,还是对鬼神、神灵、梦境等超验事象的展示,在它们背后,都包含着作家特定的写作意图。以下,笔者将相应地把论述分为三个部分,并分别从每个方面入手,来探究“秘史”的各部分内容所要表达的真实意蕴。
(一)写性:站在人性复归的立场上
古人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对每一个正常人来说,是但凡生存于世都必须面对的,是人之本性。既然性的命题与人类关系如此紧密,那么,性也必然是以“人学”自命的文学所无法回避的。《白鹿原》一反传统,突破旧有观念中对性描写避之唯恐不及的思维,大量写性,也正是站在人性复归的立场上必然做出的选择。
作家破除性描写禁忌的决心,从《白鹿原》一开篇就得到了旗帜鲜明的表现。作品大幕拉开,是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接下来,立马转入的是对白嘉轩马拉松式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娶亲“流水账”般的叙述,而每一次娶亲,都没有离开对新婚初夜的描写。这些描写,或详细或简略,其实都遵从了作家为自己定下的写性的十字原则,“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2]。在这样的原则背后,蕴含了作家对性描写的清醒认识,或者说,作家从传统的性观念中走了出来,从人性出发,将价值做了一次重估,将偏斜的关于人与性的观念做了一次校准。“不回避”是起点,也是对人性的正视,“撕开写,不做诱饵”,则是对创作层面的具体标准所做的规定。
作家站在人性复归的立场上展示白鹿原上的性的秘史,自然不会忽视一点:封建传统中女人由于其及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其人性是最受压抑的,而性,正是所受压抑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性与秘史》是作家围绕《白鹿原》中的性描写所作的一篇专论,在文中,作家开笔就写道,“我在查阅《蓝田县志》时,面对卷帙浩繁的《贞妇烈女卷》所发生的始料不及的深度震撼,最直接的是冲面而来的声浪,这陈年老本里封盖着多少痛苦折磨着的女性灵魂。在《白鹿原》书尚无任何人物和情节构想的情境下,田小娥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2]。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完全可以窥见一些作家写性的动机,这些动机,或许可以说是,站在人性复归的立场上叙写历史与传统道德观念带给人的苦难,另一方面,我们借这一段话同时发现,对田小娥这一反叛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将是理解白鹿原上与性相关的这道秘史所表达的深意的钥匙。
许多论者一致以为,田小娥是作家在《白鹿原》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女性角色,甚至放在所有角色中,也是毫不逊色的。她的反叛,她所受到的压抑和痛苦在《白鹿原》中的所有女性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就决定了,作家在田小娥一个角色上面,倾注了同情,也倾注了大部分作家对封建传统带给女性苦难的思考。同样是在《性与秘史》一文中,作家写道,“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我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我再睁开眼睛,顺手在一绺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几个字……”[2]田小娥的痛苦大部分是时代给予她的,或者说,是时代欠她的,她的反叛是不自觉的,也是完全合乎人性的。在这里,作家找到了写性的理由:性描写不仅是一种正常的人性表达,甚至因为这种人性的被压抑,更加凸显了这种表达的意义。它表达的是,我们做着合乎人性的事情,在那样的时代里,却不可能受到合理的对待,不可能得到完满的结局。田小娥只能是受压抑受迫害的,只能选择痛苦不堪地活着,而作家对性的描写,只是站在一个公正的,合乎人性的立场上,写出一个完整的人,尽管这个人有的只是一个悲剧的人生。
在《白鹿原》中,可以拿来同田小娥作比照的,还有一个女性,那就是冷先生的女儿,鹿兆鹏被包办的妻子。这一女性形象的不幸在于她是完全被压抑的,没有任何反抗,更没有任何人来理解她,同情她,她的结局并不比田小娥多几分幸运。作家自然没有机会在她的身上进行性的描写,但恰是如此,恰是没有机会写性,恰是以一个婚姻不幸,没有爱,甚至连性也没有的女人的悲剧,反证了写性的意义。
作家在《性与秘史》中写道,“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空缺”[2]。在这段话里,作家显然意识到了性是“秘史”不可空缺的一部分,作家要做的,现在已经完成的,就是将“性这根重要构件”还原到“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去,启发读者站在人性复归的立场上加以辨别、审视。
(二)民俗仪式:窥探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和精神世界
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序列中,《白鹿原》常常被归为新历史小说一类,在这类小说中,作家往往有意识地拒绝政治和权力对历史的介入和规定,取而代之的,是以新的理论和视角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像苏童的《妻妾成群》一样,这类小说对民俗仪式的重视和开掘是空前的,回到《白鹿原》,作家的立意是要写一部“秘史”,于是,大量的民俗仪式由作家的经验和想象而来,经过大胆的加工运用,让读者在动人心魄的描述中陷入了对传统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思索。
《白鹿原》有着广阔的民俗视野,其中的民俗仪式涉及到了传统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们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对这些民俗仪式的细致而广泛的描画,一方面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般,是一种画卷般的展示,由于它们的地域性和独特性,这种展示本身便具有了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有不容忽视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含量,作为一部小说,这也是《白鹿原》之所以具有深广内蕴的一个先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创作并没有仅仅止步于民俗和仪式的展示,展示之外,作家的努力在于,这些民俗仪式必须和人物、情节融为一体,必须具体化,而越具体,则越见得真实触目,越能深刻地反映人物的信仰、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精神深处的真实面貌,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完整又准确地描画出封建乡土社会里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概括而言,一部《白鹿原》,涉及到的民俗仪式的内容主要包括的是与乡民的切身生活紧密相关的几个方面,诸如嫁娶仪式、丧葬仪式、驱鬼仪式、祈雨仪式、祭祖仪式等。这几类仪式都是书中着力写到的,少则一次,多则数次,作家不吝笔墨地将它们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也达到了表现人物的信仰和精神世界的目的。
最早出现在《白鹿原》中的仪式是一场细节逼真,短促而紧张的驱鬼仪式。白嘉轩的第六任妻子娶来不过才四天,便在夜里惊呼有鬼,说自己看到了白嘉轩的前五房女人来找她,五房女人的相貌,她都能历历道出。奇怪的是,她并未在五个女人的生前见过其中任何一个,她的描述却能与五个女人的真实面貌一一吻合。于是,当白嘉轩告诉母亲白赵氏这些时,白赵氏当即命令式地说,“今黑就去请法官,把狗日的一个一个都捉了”[1]。虽然篇幅只是一段,接下来的捉鬼仪式却写得异常神秘而动心骇目。直接说明了,这种仪式包含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即人的精神层面的真实存在,具体说来,则是人对神力的信仰:法官可以借助仪式获得神力,驱逐鬼魂。
大旱祈雨的仪式也是《白鹿原》中着力表现的一幕,同驱鬼仪式类似,对这一仪式的表现仍然是完整细致的,也仍然没有回避过程中的神秘意味。从这一仪式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一个面貌。需要指出,中国民间信仰与西方多有不同,西方的信仰是宗教信仰,而中国民间的信仰则不然:一来,中国民间的信仰因地域不同而不同,往往一地有一地的传统,因而是多元的;二来,中国民间的信仰与西方的宗教信仰相比,程度也是不同的。佛教与道教在中国有一定历史,但不是民间宗教,比如,民间信仰的掌水之神不是来自佛教,也不是来自道教,而是龙王——龙是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崇拜的图腾。
大旱祈雨的仪式是在白鹿两家的族长白嘉轩的号召和主持下进行的,这种带有神秘性的求雨仪式得到了族人广泛一致的响应。作家对这一过程的描写不遗余力,尤其是人神感应的一幕,其中的一个细节是,白嘉轩用手抓住铁铧钢钎穿过两腮。这一细节象征人过渡为神,并显现出超凡的力量。正是通过一系列神秘奇异的程序,神被召唤,并在人们的想象中降临。白嘉轩口诵“我乃西海黑乌梢”一句密语,是将人化身而进入神的世界,乡民则在这时候向其恭行规定之礼,于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气氛变得庄重、崇高而神圣了,人们在这种氛围中想象着神的显灵。整个仪式有一个规范的程序,将人与神的感通作为途径,颇带有巫风的性质。在神面前信众虔诚的跪伏于地,又有几分对神‘刑天舞干戚’的威慑,百姓在饥馑之年表现出了两种对立的民族心态——‘敬畏与诛伐’。这个极富民俗性的族群性巫术仪式,形象的再现出了民间的信仰结构。
由对以上两个民俗仪式例子的分析可以见出,《白鹿原》中的民俗仪式描写明显有别于过去文学作品中的此类描写,它更完整,更细致,也更大胆,描写的目的,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民俗学、审美的意义更多一些,在民族精神和信仰方面的探索则多是无意识的,浅显的,而在《白鹿原》中,前一方面的意义固然也具备,但更多的,作家是致力于表现和探求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结构的。毫无疑问,《白鹿原》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出色的,成功的。
(三)超验事象:对理性思维的反拨
人死了魂还在,鬼魂可以附体;朱先生是人,在某些时候却有着神一样的预见和作为;梦境是与现实相关的,可以应验所有这些奇异的超验事象,在《白鹿原》中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它们的出现,其实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白鹿原》中的超验事象是复杂多样的,研究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从大处着眼,宏观把握,则不难见出,《白鹿原》对原始和神秘的张扬,都可以从理性思维的反拨这一角度来察看。
当然,在我们探讨理性思维的反拨这一命题之前,关于超验事象的作用或意义,有几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不妨略作陈述。首先,超验事象有其审美等艺术价值。这种价值,直接体现在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上。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神秘的意味:论<白鹿原>中的奇异性事象》一文中写道,“小说需要一种魔力,一种把读者的兴趣、注意力、想象力,紧紧吸引住并推激起来的魔力”,评论家认为,《白鹿原》中的神秘性事象,“显然也起到了增强小说魔力的作用”[3]。所以,神秘的、超验的事象,首先可以视为一种增强小说可读性和美学价值的手段来理解。除此之外,超验事象在小说中还起着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鬼魂附体这一超验事象来论,在《白鹿原》中,作家对这一事象的描写最生动地体现在鹿三被田小娥的鬼魂附体这一事件上面。在这一幕的描写中,作家的笔触是极为精细的,这种精细使读者不再仅仅注意附体的情节,而是由情节深入进去,思考比情节更复杂的问题。正如李建军所说,“陈忠实把这一神秘现象发生的心理过程,揭示得非常充分,即把鹿三杀死小娥以后的不安、惊恐的复杂心理写得真实而细致,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公公刃杀儿媳的这一悲剧事件所包含的文化及人性内涵的深思方面来了。”[3]这种说法是完全切合作品的。实际上,如前所说,各种超验事象在作品中的表现都是复杂的,解读方式也是多样的,但,唯其复杂难解,才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深度和广度,留给读者和批评家以极大的批评和解读空间。
对超验事象的解说是难以穷尽的,笔者的意图更在于从宏观对其进行探讨和把握,在这方面,笔者以为,作家对神秘和原始的张扬,应该是西方原始主义、非理性思潮在中国的呼应。方克强在《文学人类学批评》一书中说,“原始的世界观是神秘主义的世界观。神秘性渗透于原始人的信仰,其基础,便是他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验的世界,那里活动着的诸神、鬼魂与万物的精灵,而且这两个世界是相互沟通、神秘感应的。”[4]这段话基本上阐明了原始的、神秘主义的世界观的存在方式。这种世界观是全球性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过,“对于颇具中国特色的迷信鬼神与命运,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没有了罢,在中国还很盛。”[5]二十世纪,原始主义在西方形成思潮,蔚为壮观,影响深远,原始主义主张非理性的回归,原始主义的主张者认为,过度的理性已经形成了对人性的压迫,为了使人性健全发展,必须让非理性成为天平的另一端,以获得平衡。在中国,西方原始主义思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得到回应,在文学上,则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寻根”意识的萌发,到九十年代,“寻根”进一步发展,多角度审视和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大胆张扬原始和神秘,已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自觉。《白鹿原》的出现,在此方面是一个代表。
白鹿神话是《白鹿原》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在乡民的想象中,白鹿是原上的精灵,“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那是怎么美妙的太平盛世!”[1]由此看来,白鹿代表了原上生民的福祉。但作家不满足于让其仅仅停留在神话、仅仅供乡民传说的位置上,作家让白嘉轩出场:白嘉轩相信白鹿神话,当他偶然在鹿子霖家的田地里发现了一株奇特的植物,立刻去找朱先生,当他在朱先生的点拨下,认识到这株植物竟有白鹿的形状,立刻设计买下了鹿家的这块地,并着手迁坟,深信如此便能得到白鹿的福佑。作家并不打算让白嘉轩的愿望落空,他反其道而行之,让白家如愿转运,小说结尾,白孝文坐上了县长的位置,白嘉轩“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精灵的情景”。[1]原始世界观下的人们对自然有着充分的敬畏,这种敬畏是非理性的,它存活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对事物的判断。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理性思维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然而,唯理性是从的价值标准并不符合人性的实际需要,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理性并不能解决人类在生存中面临的一切问题,将理性与非理性对立起来,将神秘和原始全盘否定、如数摒弃,并不利于人性的健全发展。笔者相信,这是白鹿神话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白鹿原》中涉及到的超验事象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那就是朱先生这一角色。朱先生特殊,在于其半人半神形象的神秘性,他具有通达的智慧,有让普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预见,这样,在读者眼中,他便有了先知一般的神秘感。将近乎神的能力毫不避讳地表现到人身上,在对待超验事象的立场上,作家的态度可谓空前鲜明:作家显然是站在了理性的另一面。然而,作家并不是为神秘而神秘,像白鹿原中所有的超验事象一样,它们共同体现了作家在创作中力图使理性与非理性达成和解的努力。
三、结 语
以上,笔者对《白鹿原》的“秘史”性质做了简单的论述。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见仁见智的,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力作,自问世以来,由于意蕴的深厚,对它的解读至今仍在继续。“秘史”是《白鹿原》之所以耐读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作家陈忠实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2]陈忠实:《性与秘史》,《商洛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3]李建军:《神秘的意味:论<白鹿原>中的奇异性事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方克强:《文学人类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