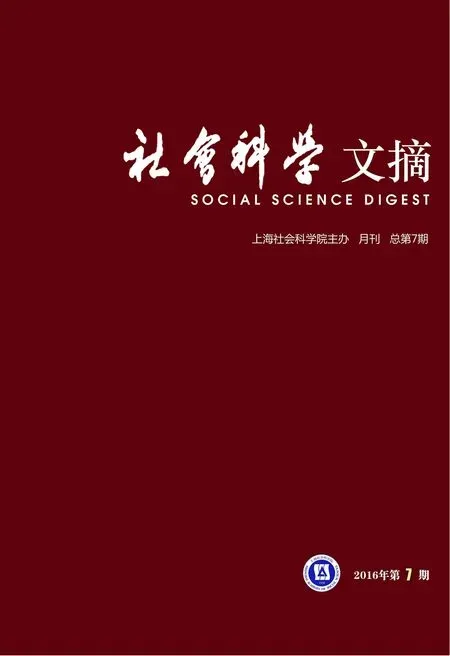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
——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
2016-11-25童世骏
文/童世骏
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
——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
文/童世骏
冯契先生的工作可以用“三三三”来概括:研究真善美,融贯中西马,连接往今来。“三三三”的最后一项,“连接往今来”也有三层意思:第一,他通过对以往哲学历史的研究、与同辈哲学同行的讨论为未来哲学发展留下“经得起读的”(他对毛泽东和金岳霖著作的评价)的文本;第二,他继承发扬其老师的学术传统认真参与其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悉心指导年轻学子的成长;第三,他立足李大钊所说的“今”,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进行“述往事”而“思来者”。
因为冯契先生主张在“述往事”和“思来者”的基础上“通其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在冯契开始其哲学生涯时被全国各界急切讨论的社会问题,在追求“以道观之”的智慧说当中,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
在其《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冯契几乎是一开头就这么写道:“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是一个哲学问题,冯契自己提供了解释,那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而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观的角度,来回答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规律的问题,也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回答如何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更需要把历史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解决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的问题。这里其实也体现了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思想。
在我看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之所以是一个哲学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是因为冯契先生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也看作是“中国人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重视的原因。
在抗战期间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冯契说“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如果说《论持久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回答了“抗战向何处去”,那么,《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提出的这个问题,作者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加以回答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的重点是放在文化上的。这不仅因为该文的基础是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随后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而且是因为在我看来,就像对一个人来说,“做何事”“有何物”和“是何人”这三个人类最基本问题当中,“是何人”是最重要的问题一样,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何人”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涉及的是“做何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原则、方式和途径;经济涉及的是“有何物”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物质资源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而文化涉及的则是“是何人”的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之成员的价值取向、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是何人”的问题与康德的四大哲学问题(“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人”这个哲学人类学问题显然有密切关系,但我觉得,它与“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宗教哲学问题也有密切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很高的语境当中,“我可以希望什么”更适合在价值论和历史观的范围内加以回答。或者说,把“中国向何处去”理解为“中国人向何处去”加以回答,既预设了对“我可以希望什么”和“什么是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会丰富对“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康德把“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这两个问题与认识论分开,而冯契则把类似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当作广义认识论的四个问题之一。在这里,冯契把一个看似属于价值论的问题作为认识论问题来对待,似乎与有些西方哲学家近年来谈论的“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比较接近;但在我看来,他不仅是要用价值论来丰富认识论讨论,不仅是要讨论认识过程中德性、价值和规范的重要性,而且是要让对于价值观(以及历史观)问题的讨论,反过来受到认识论的影响,是要使得认识论当中对于理性的讨论,对于客观实在、主观认识和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等等,也影响对于真善美价值的讨论,影响对于人的自由观的讨论,影响对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关系的讨论、对人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关系的讨论。确切些说,他是要在价值论和认识论的互动当中超越狭义价值论和狭义认识论的局限性,一方面克服价值论领域的虚无主义与独断主义之间的非此即彼,另一方面克服认识论领域的实证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非此即彼,从而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对这个我觉得唯一真正具有“哲学基本问题”地位的哲学问题,做出恰当的回答。
价值论和认识论的结合,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价值论和认识论的结合,就是冯契看作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最重要成果(没有之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冯契提醒我们,“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概念,并不是在《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更加典型而且更加出名的毛泽东哲学著作当中提出的,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提出来的。这可以说是冯契把《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哲学文本予以高度重视的最直接原因。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冯契在说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一词,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所以,这个词集中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个概念把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践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统一起来,而实践则可说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把冯契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做一个比较。冯友兰在其晚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讨论了《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把毛泽东这个文本当作一个哲学文本来讨论的,但是没有提到其中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全新的哲学概念。
再往前面看,冯友兰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写了《新事论》一书,其副标题是“中国通往自由之路”,可以说也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冯友兰先生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提高到认识论的角度来提出和回答问题,更没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因此,该书虽然讨论了许多关系问题,如共殊、城乡、家国,等等,但就是没有讨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知行关系、群己关系,以及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关系问题。
从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冯契对于“自觉”和“自愿”的讨论,尤其值得重视。冯契强调真正自由的行动既要符合理性的自觉原则,也要符合意志的自愿原则。在他看来,重自觉原则而轻自愿原则,容易导致听天由命的宿命主义,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危险尤其值得警惕;而重自愿原则而轻自觉原则,则容易导致随心所欲的意志主义,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危险尤其值得警惕。冯契认同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但提出不但要防止“以理杀人”的独断主义,而且要防止因为克服独断主义而走向虚无主义,尤其要防止独断主义的唯我独尊与虚无主义的没有操守的独特结合:拿独断主义吓唬别人,拿虚无主义纵容自己。
冯契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不仅是因为他把这个问题当作“中国人向何处去”的问题来讨论,而且因为“中国”本身的重要性,而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具有历史哲学的意义。“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因为古代中国是差不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同时诞生的几大“轴心文明”之一,也因为当今中国已经在经济上位居世界第二,在政治上因为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而对全世界引起越来越强的反响。“中国向何处去”越来越意味着“世界向何处去”。
最后,把“中国向何处去”理解为一个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对这个问题,冯契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哲学本身来看,也有一个古今中西的关系”,“与民族经济将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发扬民族特色而逐渐走向世界,将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作为学者、教师、普通人的所有方面,冯契先生也是言行一致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哲学家,创立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承担许多西方哲学博士论文的评审,主持西方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尤其是在其著述中,广泛征引欧陆和英美各派哲学家的论著,利用中西哲学资源,对理性和意志、存在和本质、逻辑和历史、内在性与超越性等世界性哲学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