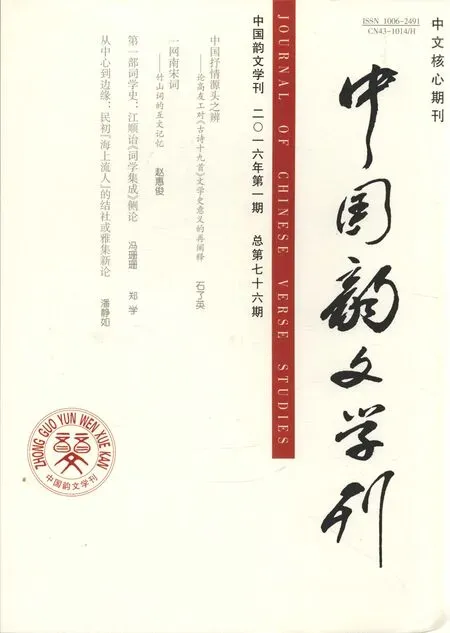陈廷焯研究综述
2016-11-25张海涛
张海涛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陈廷焯研究综述
张海涛*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陈廷焯是晚清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学界对他的研究历经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末是陈廷焯研究的酝酿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率先将陈氏的词学理论纳入学术研究视野;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陈廷焯研究的发展期。此期研究以“沉郁说”为主,而新材料的发现带动了新领域的开拓;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陈廷焯研究的繁荣期。此期形成以陈氏词学思想研究为主体、诗学思想与诗词创作研究为两翼的研究格局,出现了多篇学位论文和多位研究专家。而陈氏的诗学、前期词学、《词则》三个领域有待今后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陈廷焯;《云韶集》;《词则》;《白雨斋词话》;研究综述
陈廷焯(1853-1892)字伯与,号亦峰,镇江丹徒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未仕,年仅四十而殁。他著述颇丰,却多有散佚。传世著作有《骚坛精选录》《云韶集》《词坛丛话》《词则》《白雨斋词话》《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
陈廷焯一生致力于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其中以《白雨斋词话》(以下简称《词话》)为代表的词学著作体系严密、影响深远,尤为后世所重。百余年来,随着现代词学的建立与发展,关注并研究陈廷焯的学者不断增多,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目前,已有文章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2003年,陈水云先生发表《〈白雨斋词话〉在二十世纪的回响》(《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2012年,陈廷焯之孙陈昌发表《〈白雨斋词话〉百年研究及论文录述》(《文津流觞》2012年第4期)。这两篇是陈廷焯研究综述类文章的先行者,开拓之功自不可没。但它们没有涉及陈氏其他著作的研究情况,且近年来又有新的一手资料和相关成果问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陈廷焯的研究状况做一番更为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一酝酿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末是陈廷焯研究的酝酿期。在这七十余年中,《词话》一版再版,渐为学界所熟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率先将陈氏的词学理论纳入学术研究视野,这为后来的陈廷焯研究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光绪二十年(1894),陈氏弟子将其《词话》十卷稿本删为八卷,经陈父铁峰先生审定后木刻刊行。在陈氏著作中,《词话》问世最早,其影响也最大。1932年,署名“春痕”的作者发表《读〈白雨斋词话〉》①题目原误作《读〈白雨斋诗话〉》,载《微音月刊》1932年第4期。。文章认为《词话》源于常州词派,是中国文学批评中难得的有统系、有组织的著作。该文作者归纳其主旨为“沉郁”二字,认为陈氏以之论词,既有平允独到处,又有偏颇过当处。该文虽然篇幅不长,近似一篇书评,但却指出了《词话》的渊源、主旨、价值和不足,初步具备了研究的雏形。而将陈廷焯真正纳入学术研究领域,则要归功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1927年,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史——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该书虽提及常州词派,但仅论列张惠言、周济、冯煦,而没有提到陈廷焯。1944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朱氏视陈廷焯词学为清代词论之结穴,将其置于全书之殿,这是陈廷焯正式进入学术研究视域的开始。朱氏认为陈氏的“沉郁说”源于张惠言,但同时提出“亦峰之言,本不尽守常州派师说”[1](P352)的观点,这是很有见地的。194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出版。全书末尾提到常州派词论,并以陈廷焯《词话》作为晚清常州派的代表。郭氏认为,陈氏所谓沉郁之旨,即是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沉郁为词格,比兴为词法。清季词学的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性灵说的反动。郭氏之论虽然不长,但提纲挈领,颇能抓住要点。且将陈氏的学说置诸整个文学思想史中来考量,亦能给人以启发。众所周知,郭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其纳陈氏于书中,无疑巩固了陈廷焯词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词话》的不断再版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自1894年初刻后至20世纪60年代,《词话》尚有如下版本: 1927年苏州中报馆《词话汇刊》铅印本、1929年上海文瑞楼书局鸿章书局王启湘评点石印本、1934年《词话丛编》铅印本、民国间开明书店铅印本、1954年台湾开明书店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维沫校点本、1967年台北广文书局《词话丛编》本。其中以《词话丛编》本和杜维沫校点本最为通行,成为后来人们研究《词话》的主要依据。
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陈廷焯的词学理论进入学术研究的视域,这标志着陈氏词学的理论价值得到了肯定与确认。而《词话》的不断整理再版,也为进一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可以说,关于陈廷焯的研究已经蓄势待发。
二发展期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陈廷焯研究的发展期。台湾地区的学者起步较早。随着“文革”的结束与思想的解放,大陆学术界也开始复苏。关于陈廷焯的专题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在深度与广度方面均有所开拓。
1971年,台湾的陈宗敏发表《〈白雨斋词话〉概述》(《大陆杂志语文丛书》第三辑第四册,大陆杂志社印行)。据笔者所见,这是第一篇研究陈氏的专题论文。文章认为,“沉郁”指词作的情感内容,也是指词作的表现技巧,含有温厚、雅正、蕴藉、含蓄、缠绵、委婉等诸多意义。该文最大的价值在于注意到“沉郁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对其简单地下定义。1979年,台湾林玫仪先生的博士论文《晚清词论研究》第六章专门讨论陈廷焯。次年,研究陈廷焯的首篇学位论文——国立政治大学陈月霞的硕士论文《〈白雨斋词话〉之研究》也在台湾地区问世。可以说,在研究陈廷焯方面,台湾学者走在了大陆学者的前面。
大陆方面,人们亦对“沉郁说”加以重点关注,并试图对其阐释。然而受困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对于“沉郁”的解释明显带有两种倾向。其一,学者多以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思维来定义“沉郁”。大陆学者普遍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对于唯物辩证法颇为熟稔。当他们面对《词话》的时候,往往运用辩证法思维进行思考和阐释。于是,“沉郁”就变为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体。如袁謇正认为“沉郁”是既重内容又重形式,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的审美理论[2]。廖晓华认为“沉郁”要求内容深厚深沉,并主要对艺术技巧提出了要求[3]。在这里,我们并非反对用内容与形式等概念来分析“沉郁”,只是觉得应当避免这种分析流于简单化。其二,在分析“沉郁”的时候,学者往往聚焦于“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两句话。《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4](P1165)论者在研究“沉郁说”的时候必然会引用这段话。有意思的是,此期大陆学者特别关注“意在笔先”二语,不惜笔墨对其展开论述。如袁謇正认为“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要求词人创作前要有成熟的形象思维,将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深深寄托在完整的形象之中。从艺术上看,“沉郁说”实际就是“形象”说[2]。廖晓华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3]。而屈兴国更是追溯了“意在笔先”之源,认为陈氏意识到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是以具体形象进行思维的,并用“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两句话概括了文学创作从构思到完成以至读者再创造的全过程的主要特征[5]。学者之所以热衷讨论此二句,与当时的文艺思潮密切相关。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信中说道:“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文艺界由此对形象思维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袁謇正等学者对“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不遗余力地阐发,正是这一思潮在陈廷焯词学研究中的反映。
除了集中解释“沉郁”外,有学者开始关注《词话》中与“沉郁”相关的其他批评理论。如“顿挫”这一范畴,金望恩《陈廷焯词论中的“沉郁顿挫”说》释之为用摇曳多姿、似断实连、余味无穷的艺术形式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6]。再如陈氏的词人批评论,孙维城《白雨斋论张先词试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又如“沉郁”与《风》《骚》关系的研究,周建忠《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认识到《楚辞》在陈氏词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陈廷焯论词以权威的《楚辞》为尺度,既有客观基础上的相似性,又有无法否认的内在矛盾[7]。虽然此期对于《词话》其他问题的研究文章还很少,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的学者正是沿着这种思路开疆拓土,终成蔚然大观。
这一时期陈廷焯研究最为突出的成绩,是一批新材料的发现以及利用新材料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屈兴国先生。80年代以前,人们所能看到的陈氏词学著作只有八卷本《词话》。虽然通过《词话》中的记载,可知陈氏还编有词选《云韶集》和《词则》,但一直无从得见。为了寻觅陈氏遗著,屈兴国先生先后赴上海、苏州、南京陈廷焯的嫡系孙辈之间实地调研,终于在南京陈氏后人处,觅得保存至今的《词话》十卷手稿本。屈先生据此于1983年出版了《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该书不仅将《词话》足本公诸于世,还征引了大量《云韶集》和《词则》中的批语,并将《云韶集》前的《词坛丛话》全文录出。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词话》十卷稿本与《词则》二十四卷稿本影印出版。至此,关于陈廷焯的词学资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新材料的发现扩大了陈廷焯研究的领域,屈先生率先在三个方面做出开拓。首先是对《云韶集》的研究。《云韶集》是陈氏22岁编选的大型词选。通过考察《云韶集》及所附《词坛丛话》,屈先生认为该书以贯彻和推衍浙派词学主张为宗旨,但其中的南北宋词不可偏废论和重视豪放派作家作品,则是陈氏取法浙派而不泥于浙派的卓见[8]。其次是对于《词则》的研究。《词则》是陈氏后期编选的一部大型词选。屈先生认为《词则》与《词话》互为表里,但二者不能彼此替代。《词则》是陈氏从正变说向《词话》温厚沉郁说的过渡[9]。最后是关于陈氏前后期词学转变的研究。《云韶集》及《词坛丛话》的发现,使得研究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演变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屈先生比较《云韶集》和《词话》后,认为陈氏的词学思想是从浙派入手,重醇雅,重格调。其后发展到以常派为依归,重比兴,重沉郁。作者还认为《云韶集》较《词话》虽有大段不可及处,但陈氏早年的某些见解,反而比晚年高明[10]。以上这些论断,都是屈氏考察一手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比较有说服力,也为后人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关于陈廷焯的研究稳步发展。一方面出现了相关的学位论文,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如屈兴国先生这样的领军人物。此期研究以“沉郁说”为主,而新视角的发现、新材料的问世与新领域的开拓,都预示着陈廷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即将到来。
三繁荣期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陈廷焯研究的繁荣期。相关研究文章数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并出现多篇学位论文和多位研究专家。此期关于陈廷焯的研究,已扩展到陈氏词学、陈氏诗学和陈氏诗词创作三大领域。
(一)关于陈廷焯词学的研究
陈廷焯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词学领域,故其词学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与此前独重“沉郁说”不同,后来的学者对陈氏词学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发掘。概括起来,研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词学理论范畴。“沉郁说”仍是人们研究的焦点。对于“沉郁”一词的诠释,学人逐渐摆脱过去的思路,不再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从多个角度去呈现“沉郁说”的丰富内涵。有分析“沉郁”所包含的特质或要素者。如林玫仪认为“沉郁”具有三种特质:有寄托,有言外之意;有比兴,有烟水迷离之致;有性情,能忠厚[11]。张宏生认为沉郁“以深刻的思想性作为出发点,以比兴寄托作为表情达意的形式,以‘欲露不露,反复缠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审美体验,以温厚忠爱作为全部创作活动的指归”[12](P112)。毛宣国、盛莉、傅蓉蓉等人皆以此种方法诠释“沉郁”①参见毛宣国、孙立《试论词体风格特色“沉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1期;盛莉《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厚”》,《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傅蓉蓉《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晋阳学刊》2010年第1期。;有分析“本原”以理解“沉郁”者。由“沉郁”向上追溯,便是以《风》《骚》为代表的儒家诗教精神。这是陈氏后期词学的“本原”,弄清这一点,于“沉郁”则思过半矣。曹保合《谈陈廷焯的本原论》即从“本原”的视角来探究“沉郁”。文章认为词的渊源是《风》《骚》,《风》《骚》的根本是温厚,温厚是正情的道德依据,使寄托实现沉郁莫善于用词,沉郁是得本原的最终标志[13]。步步推进,清晰明了。马涛《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亦是一篇“洞悉本原,直揭三昧”的佳作。文章将“怨慕”之情、“弱德”之美视作“沉郁”的伦理价值核心[14],颇有见地;有分析“沉郁”的多个意义指向者。迟宝东《常州词派与晚清词风》将“沉郁说”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即作为宗旨论、创作论和体性论[15](P191-211),这比单纯分析“沉郁”的特质或要素更为明晰和准确;有以哲学视角分析“沉郁”者。2002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欣发表《“沉郁”风格新释兼论陈维崧词》。该文认为陈廷焯对“沉郁”之强调根源于对道德意识在文学审美中重要性的确认。“沉郁”之所以要求“意”不能道破,只能以“比兴”来寄托,内在原因是道德意识因其超验性而使经验语言无能为力[16]。据笔者所知,这是唯一以哲学视角审视“沉郁说”的文章。其所论或许未必尽然,却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启发。
此期学者还对与“沉郁说”密切相关的“顿挫”“比兴”等概念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人们普遍认同“‘沉郁’更偏重于词中情感表现的深度,‘顿挫’则指词中具体表现手法”[17](P303),对“顿挫”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如彭玉平认为顿挫之法约可归为六种:颠倒、直婉、虚字、进深、交错、结醒[18]。迟宝东认为顿挫之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宜吞吐尽致,这是就某一种具体的情感质素而言;二是词宜离合转折,这是就整个词篇中多种情感质素间相互关系而言[15](P204-206)。这些论述都具体而微,鞭辟入里。“比兴”在“沉郁说”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实现“沉郁”的重要手段。在陈氏心中,“比兴”并非修辞学的范畴,而是带有某种审美意味。这些论断学者多有提及。方智范先生则特别指出,陈氏把比兴寄托“由具体表现方法的层面,提高到了审美境界的层面。……陈廷焯的比兴说作为理论探讨是很有启发性的,但对词的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很有限的”[19](P371),一语道出“沉郁说”中“比兴”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不足。
作为一种词学理论,“沉郁说”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学者在诠释“沉郁”的同时也注意到它的矛盾与缺陷。90年代以前,学界从反封建的角度对“沉郁说”中蕴含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加贬斥。儒家诗教的保守性的确存在于“沉郁说”中,这一点无须讳言。但另外一个事实,则是陈廷焯的很多与沉郁相关的词论都被学界奉若圭臬。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学者对“沉郁说”做了更为细腻、公允的评价。如皮述平认为陈氏论词全然没有道学气或腐儒气,原因在于“沉郁”将道德与美学意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符合传统文学的最高标准[20](P175-182)。朱崇才的观点与之相近,他认为“沉郁说”“在属于伦理学范畴的传统‘诗教’中,注入了美学因素,以便使其更好更贴切地运用于词学”[21](P325)。他们都道出“沉郁说”虽有儒家诗教的因子却仍能在词学殿堂大放异彩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柏岭《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偏颇性与合理性》一文。文章透过一般的道德或美学等概念而直探问题的根源,认为陈氏在探求词的本原问题上,存在着诗学精神的本初理念和词体艺术的本性观念之间的矛盾,这才使得他的词学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偏颇性和一定的合理性[22]。该文洞察深刻,思辨性极强,可谓从根本上理清了“沉郁说”的功过是非。
除了“沉郁”外,此期学人还试图提炼陈氏其他的词学范畴。如彭玉平、盛莉、孙维城等论“厚”①参见彭玉平《陈廷焯词学综论》;盛莉《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厚”》;孙维城《论陈廷焯的“本原”与“沉郁温厚”——兼与况周颐重大说、谭献柔厚说比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1期。;彭玉平、王吉凤、朱惠国、苗珍虎、焦亚东等论“雅”②参见彭玉平《陈廷焯正变观疏论》,《词学》(第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吉凤《雅:陈廷焯论词的审美倾向》,《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朱惠国《论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以及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词学》(第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苗珍虎、焦亚东《尚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基点》,《求索》2009年第11期。;邓新华、杨爱丽等论“味”③参见邓新华、杨爱丽《从“诗味”到“词味”——陈廷焯的词学理论初探》,《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这些文章各有可观,为进一步挖掘陈氏的词学理论提供了启发与参考。
其二,词学批评思想。以《词话》为代表的陈氏词学之所以备受推崇,原因之一是它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具体表现为拈出“沉郁”为核心,并以之作为最高标准通论古今的词作、词人、词史和词学著作。因此,陈氏的词学批评思想亦非常丰富。对此,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人批评论、词史观和词选思想。
陈廷焯在其词选、词话中对历代词人进行了大量评论。通过考察其具体的词人批评,可以以小见大,充实陈氏词学思想的研究。1987年,孙维城《白雨斋论张先词试评》迈出了研究陈氏词人批评的第一步。90年代至今,学者论及的陈氏词人批评包括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李清照、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朱彝尊等,其中关于王沂孙的文章最多。王沂孙是陈氏在“沉郁”标准下推举的最高典范,分析陈氏对王沂孙的批评,对于深入理解“沉郁说”大有助益。总体来看,这类研究文章绝大多数以《词则》《词话》为依据,实际上是研究陈氏后期的词人批评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发表了顾宝林《规模前辈,益以才思——由〈云韶集〉〈词坛丛话〉看陈廷焯前期对晏欧词的研究与批评》。该文以《云韶集》和《词坛丛话》等代表陈氏早期词学思想的著作为依据,为全面研究陈氏的词人批评理论开了一个好头。
较早论及陈氏词史观的是彭玉平先生。他的《陈廷焯词史论发微》从宏观视野出发,将陈氏由唐至清的词史观分作创古、变古、失古、复古四个阶段予以阐发。彭先生认为,陈氏的词史观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但也被复古思想所遮蔽[23]。彭氏之后,孙维城先生揭示出陈氏词史观的重大价值。孙先生认为《词话》是传统社会唯一的一部词史,且以“沉郁”之理论为经线,而以词的发展为纬线,勾勒出一部波浪起伏、观点鲜明的词的发展史。孙氏在书中具体而微地分析、辩驳了陈氏的词史构建,并以“史论结合”作为《词话》的重要特点[24]。可以说,孙维城将陈廷焯词史观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廷焯对词选非常重视,既编选词选,又批评词选,形成了自己的词选思想。关于陈氏的词选编辑,赵晓辉认为从《云韶集》《词则》再至拟选而未果的《二十九家词选》,可以清晰看出陈氏词选思想的发展变化[25]。彭玉平亦据此三种选本立论,认为选本的变化体现了陈廷焯词史意识的成熟,也反映其词学观念从信奉浙西词派到尊崇常州词派的转变[26]。关于陈氏的词选批评,彭玉平《选本批评与词学观念——陈廷焯的词选批评探论》梳理了陈廷焯对于历代词选的批评,并以其对《词综》和《词选》的批评为考察重点,分析其词学观念在前后期的变化轨迹[27]。不难看出,学者对于陈氏词选思想的研究,落脚点都放在陈氏词学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上。
其三,前后期词学之转变。随着《云韶集》《词坛丛话》《词则》的发现,陈氏词学思想前后期的转变成为继“沉郁说”之后又一个研究热点。屈兴国先生早在80年代就指出陈氏早期崇尚浙派,后期转归常派。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词学家的思想演进具有延续性和统一性。单纯的前后对比,不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于是,在“变”中寻找“不变”,成为学者们新的研究课题。如李睿通过比较《云韶集》和《词则》,认为二者虽代表不同思想,但不能截然分开。像陈氏前期推崇陈维崧,主性情,亦为后来所承续。而《词则·大雅集》多选南宋词,也可见浙派之余风[28]。邓新华、杨爱丽更是认为陈氏早年服膺的浙派“醇雅”“清空”理论仍然惯性地存留下来,成为“沉郁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9]。虽然其论断有待商榷,但这种研究思路是应予鼓励的。除了具体分析这种转变外,探究转变背后的原因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庄棫的影响是陈氏词学思想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对于陈氏的由浙入常,屈兴国先生认为与时局的变化、陈氏阅历的增长有关[10]。林玫仪不认同这种解释。她认为陈氏欣赏豪放派词家,这就与排斥豪放派词人的浙派思想产生了矛盾。而常派理论从内容着眼,对外在风格并不看重,故陈氏的矛盾在常派体系下可以得到解决[11]。孙维城则认为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之间并非针锋相对,二者在联系社会现实、提倡雅正、推尊词体、主张兴寄四个方面是一致的,而这都是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为一个封建士子,陈廷焯认同以上内容,这是他顺利由浙转常的内在原因[30]。
1992年,台湾大学金鲜的硕士学位论文《陈廷焯早晚期词学观念之转变》,即以陈氏词学前后期的转变为论题。文章从论词标准、尊体观念、源流观念、正变观念和实际批评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归因于时代环境、庄棫影响和浙派理论的缺陷。虽然问世于20多年前,但自今天看来,这仍是一篇全面详实、颇具参考价值的论文。
其四,与况周颐、王国维词学的比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并称为“晚清三大词话”。这促使一些学者将陈氏词学与况周颐词学、王国维词学进行比较研究。早在1932年,春痕的《读〈白雨斋词话〉》便认为陈氏的“沉郁说”与况周颐的“重拙大”之说殊途同归。这种观点在9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仍时有回响。如梁荣基认为陈氏的“沉郁说”与况氏的“重拙大”说,立论虽然不同,但皆本于“居心忠厚,托体高浑”[31](P231)。胡遂、邬志伟则认为陈氏的“沉郁”说与况氏的“沉著”说都揭示了词的一种情感境界和词之所表达的感情深沉蕴藉的本质特征[32]。至于与《人间词话》的比较,学者多从“词境”的角度切入。谢桃坊认为陈氏以“沉郁”为“意境”中最高的层次,这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形成是有启发的[33](P371-372)。傅蓉蓉持类似观点,她认为陈氏的“词境说”真正体现了理论家将词归入“诗歌”范畴作一体观的批评眼光,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34]。笔者认为,上述文章讨论陈氏词学与况、王词学的关系,其方法与结论都还有欠深究。
孙维城先生对三大词话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他从沉着深厚、比兴寄托、意境论、论“真”、宗尚宗主和词史观这六个词学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比较三部词话著作。如沉着深厚方面,孙先生辨析了陈氏与况氏面对这一儒家要求的区别,即陈氏是亦步亦趋的坚持,况氏则以性灵调剂沉着,以厚重冲淡忠诚。又如在意境论方面,孙先生认为陈氏强调词的意境之儒家标准,而况、王则从词的艺术审美出发。他并不认为陈氏的词论对王氏的“境界说”有所启发[24](P393-424)。总之,孙先生对三大词话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形成对于陈、况、王三人的历史定位,即陈廷焯是传统诗教的守望者,况周颐是传统的审视者,王国维是传统的批判者。在这种深入研究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再来比较陈氏词学与况、王词学的异同,其所得结论无疑更具说服力。
其五,在常州词派及晚清词学史中的地位。常州词派自张惠言兄弟始,历董士锡、周济、谭献、庄棫以至陈廷焯。其中,张惠言、周济、陈廷焯三人对常派的理论贡献尤巨。因此,给予陈氏词学在常州词派及晚清词学发展史中一个准确的定位,亦是学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学者普遍认为陈氏的“沉郁说”是对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延续与发展。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陈廷焯词学实为常州词派的一大转折。朱惠国和欧阳明亮均指出这一点。前者认为在陈廷焯之前的常派词家,其身份或是经学家(如张惠言、庄棫),或是史学家(如周济),故常州词派不免受到常州学派的笼罩。而陈廷焯的出现,初步打破了常州学派对常州词派的牢笼,使常派由学人词派向词人词派转化[35]。后者则以四首《蝶恋花》为参照物,通过分析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对这四首词作者的不同判定,认为陈廷焯在具体的解词过程中,比张惠言、周济更加注重作品本身的“笔法”技巧与词意表达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常派词论的关注重点由作品之外转入作品之内。这就使得常派的解词理路向着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的方向迈出了更为彻底的一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陈氏校正了常州词派的理论视野,使之融入到晚清民初词学思想的建构潮流之中[36]。可以看出,朱先生与欧阳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前者从宏观着眼,后者从微观剖析,可谓殊途同归。
(二)关于陈廷焯诗学的研究
除了词学,陈氏亦浸淫诗学有年,并尤为推崇杜甫。他的“沉郁说”便是援引杜诗之论入词学,《词话》等著作中亦有一些论诗之语。此外,陈氏还编有诗选并进行评点,《骚坛精选录》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的陈氏诗学著作。通过研究《骚坛精选录》以及陈氏散见的诗论,不仅可以了解他的诗学思想,还可以为其词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彭玉平先生是研究陈氏诗学的发起者和领路人。1989年,彭氏在陈廷焯的子媳张萃英女士处,意外发现了陈氏《骚坛精选录》的残稿。1994年,彭氏《陈廷焯前期词学思想论》(《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2期)已引及《骚坛精选录》中的部分批语。2007年,彭氏发表《陈廷焯〈骚坛精选录〉(残本)初探——兼论其诗学与词学之关系》(《文学评论丛刊》2007年第2期),介绍了这部诗选的基本情况。其后,彭氏辑出《骚坛精选录》的全部批语,并与《云韶集》《词则》《词坛丛话》《白雨斋词话》中的论诗之语汇辑在一起,命名为《白雨斋诗话》,交由凤凰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至此,《骚坛精选录》才真正呈现于世人面前。目前,研究陈氏诗学思想的文章仅有两篇,除了彭氏之文外,还有一篇是彭氏弟子彭建楠的《陈廷焯〈骚坛精选录〉及其诗学思想》(《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4期)。彭玉平的文章首先介绍了《骚坛精选录》残存部分的情况,即残留的主要是南北朝与盛唐诗歌部分;其次,介绍了陈氏标举的诗史四位“大将”和若干“名将”,并以杜甫为至圣;再次,认为陈氏的诗学思想受到了沈德潜、潘彦辅等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追求汉魏风骨、沉郁而富于教化、顿挫而饶有姿态三个方面;最后,认为陈氏诗学和词学的根基建立在对杜诗的理论解读上,把作为诗学核心之一的“沉郁”升格为词学核心的唯一,体现了其诗学与词学的紧密关系和彼此区别。彭建楠则对陈氏诗学思想做了更为细致的探讨。文章认为《骚坛精选录》的编选宗旨是维护诗教正统,陈氏以忠厚的品格为诗歌之本,推崇比兴和古质的形式以达到沉郁的意境,并以杜甫为古今典范。通过这些分析归纳,彭建楠认为陈氏所秉持的诗教观影响了他词学思想的形成。
由于《骚坛精选录》是一部残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陈氏诗学思想的全面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现有的两篇论文已经解决了陈氏诗学的所有问题。随着《白雨斋诗话》的出版,相信会有更多学人投入到陈氏诗学的研究中来。
(三)关于陈廷焯诗词创作的研究
与《词话》等学术著作受到热捧不同,陈氏的文学创作长期被忽略。陈氏传世的文学作品只有诗词,主要收录在《白雨斋词存》和《白雨斋诗钞》,部分散见于十卷稿本《词话》中。目前,学界对陈氏诗词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发现文献价值。林玫仪先生最早发现《词存》和《诗钞》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她认为,结合《词存》《诗钞》与稿本《词话》所载的相关记事,可补陈氏生平之阙;由《词存》《诗钞》中之评语,可以了解陈氏之交游情况;《词存》有部分词标注章法,有助于词意之了解[37]。我们说,关于陈廷焯的史料记载非常有限,《词存》和《诗钞》恰好可以提供一些陈氏生平、交游的线索。
其二,发掘理论价值。文学研究中,将一个人的理论与创作互相比对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陈廷焯的“沉郁说”是其论词、填词的统一标准,故这种方法对陈氏尤为适用。张宏生先生曾指出,陈氏在《词话》中详细分析自己的作品,这并非一种盲目自大,而是反映出陈氏希望以创作实践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并以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接武前贤,昭示后学[12](P135-138)。因此,理解陈氏的词作,对理解其“沉郁说”大有帮助。其诗作与诗学思想的关系,亦复如是。林玫仪也认识到这一点,她指导的硕士生李淑桢便以《陈廷焯词论及其诗词创作实践之关系》为学位论文(台湾国立中山大学,2009年),分析了陈氏的诗词创作论与其诗词作品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陈廷焯的研究进入全盛阶段。此期发表了百余篇研究陈氏的论文,其中包括至少14篇硕士学位论文①大陆地区9篇:彭玉平《陈廷焯词学研究》;杨咏诗《陈廷焯〈词则〉研究》(中山大学,2001年) ;王吉凤《陈廷焯沉郁说的词学理论体系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7年) ;李阳《从〈白雨斋词话〉看陈廷焯的词学观》(辽宁大学,2009年) ;李锐《陈廷焯词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陇兴龙《〈白雨斋词话〉论词思想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09年) ;王喆《陈廷焯“沉郁”说词学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 ;林枫竹《陈廷焯〈云韶集〉研究》(南京大学,2013年) ;宋蔚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4年)。台湾地区5篇:宋邦珍《〈白雨斋词话〉沉郁说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1990年) ;金鲜《陈廷焯早晚期词学观念之转变》(国立台湾大学,1992年) ;侯雅文《〈白雨斋词话〉“沈郁说”析论》(国立中央大学,1996年) ;李淑桢《陈廷焯词论及其诗词创作实践之关系》(国立中山大学,2009年) ;吴锦琇《陈廷焯〈词则〉选评“王沂孙词”析论》(国立政治大学,2009年)。,并出现了如孙维城、林玫仪、彭玉平等一批研究陈氏的专家学者。尤为可喜的是,陈廷焯研究业已形成以词学思想研究为主体,诗学思想与诗词创作研究为两翼的研究格局。三者之间彼此沟通,相互支撑,共同推动陈廷焯研究向更高、更广的领域迈进。
自1894年《白雨斋词话》刊行至今,学术界不断涌现新材料,尝试新方法,获得新结论,使得陈廷焯研究如同一股源头活水,始终生机勃勃地向前推进。而陈氏的诗学、前期词学、《词则》三大研究领域相对薄弱,尚有待诸贤进一步开拓。2013年9月,孙克强先生主编的《白雨斋词话全编》出版。2014年3月,彭玉平先生纂辑的《白雨斋诗话》出版。至此,陈廷焯传世的著作已全部整理出版。在文献基础与理论基础均已完备的今天,全面研究陈廷焯的博士论文、专著或当应运而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1]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袁謇正.陈廷焯的“沉郁”词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3]廖晓华.论陈廷焯的“沉郁”说[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4]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屈兴国.《白雨斋词话》的“沉郁”说[A].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3.
[6]金望恩.陈廷焯词论中的“沉郁顿挫”说[J].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3).
[7]周建忠.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J].学术交流,1989(5).
[8]屈兴国.记陈廷焯《云韶集》稿本[A].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3.
[9]屈兴国.《词则》与《白雨斋词话》的关系[A].词学(第五辑)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0]屈兴国.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A].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3.
[11]林玫仪.新出资料对陈廷焯词论之证补[A].词学(第十一辑)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2]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3]曹保合.谈陈廷焯的本原论[J].文学遗产,1996(4).
[14]马涛.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15]迟宝东.常州词派与晚清词风[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16]李欣.“沉郁”风格新释兼论陈维崧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17]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8]彭玉平.陈廷焯词学综论[A].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1辑)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9]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0]皮述平.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1]朱崇才.词话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2]杨柏岭.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偏颇性与合理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23]彭玉平.陈廷焯词史论发微[A].词学(第十一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4]孙维城.千年词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词话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25]赵晓辉.陈廷焯词选思想探析[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26]彭玉平.选本编纂与词学观念——晚清陈廷焯词选编纂探论[J].学术研究,2006(7).
[27]彭玉平.选本批评与词学观念——陈廷焯的词选批评探论[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28]李睿.从《云韶集》和《词则》看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演进[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9]邓新华,杨爱丽.陈廷焯的“沉郁”说与浙西词派的“醇雅”、“清空”理论[J].中国文化研究,2010(3).
[30]孙维城.陈廷焯词学思想前后期不同的共同基础[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31]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2]胡遂,邬志伟.陈廷焯“沉郁”说与况周颐“沉著”说之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6(11).
[33]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34]傅蓉蓉.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J].晋阳学刊,2010(1).
[35]朱惠国.论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以及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A].词学(第十九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6]欧阳明亮.从“非欧公不能作”到“欧公无此手笔”——从周济、陈廷焯在四首《蝶恋花》归属问题上的分歧看常州词派的理论演变[J].文艺理论研究,2011(3).
[37]林玫仪.陈廷焯《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考论[J].中国韵文学刊,2009(2).
责任编辑 李剑波
I207.23
A
1006-2491(2016) 01-0086-08
张海涛(1987-),男,天津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