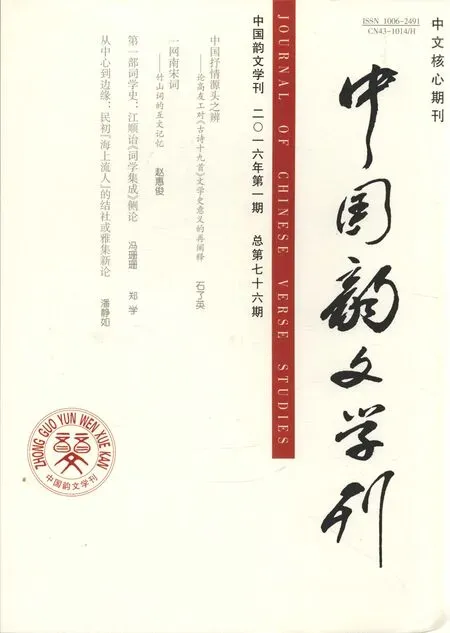《诗经·野有死麕》事义考
2016-11-25邵杰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邵杰(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诗经·野有死麕》事义考
邵杰*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野有死麕》一诗事义,历来异说颇多,排除掉无法自圆者,其余诸说,皆认为诗篇含有男女之情,但立场各不相同。诗篇首章的士女对言,更加突出士作为男性的性别色彩,推求之下,可知此一现象当发生在东周时期;吉士作为贵族,在东周时期地位有所下降。而女子身份则为庶民。二人互生情愫乃至林中欢会,虽属男女相悦的范畴,但于当时之礼俗不合。此诗入选《诗经》,可知其大旨是对男女之行为进行道德批判。
《野有死麕》;贵族;庶民;礼俗
《野有死麕》一诗,历来异说颇多,在近代以来,多被解为男女相恋之诗。学界对于传统时期的诗说,简单否定者居多,并未有系统、合理的回应。而对于关乎诗篇意义指向的人物身份,则多作模糊处理,深究者无多,是以于诗篇大义每多交臂。笔者不揣浅陋,于此略申己说,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野有死麕》的事义,历来阐释者极多,按照其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归纳为以下数种:
(一)恶无礼说。此说起源最早,是传统时期的主流解释。根据其中各说对于“无礼”的不同理解,又可分为以下数类:
1.恶无礼之淫风。此说导源于《毛诗序》:“《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1](P292)不过,为毛《诗》作笺注的郑玄,已将理解的中心转移。孔颖达等的《疏》再次肯定了《毛诗序》的说法:“作《野有死麕》诗者,言‘恶无礼’,谓当纣之世,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之俗。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其贞女犹恶其无礼。经三章皆恶无礼之辞也。”[1](P292)因为《毛诗正义》的正统地位,此种说法遵从者甚多。持此说者,显然是将诗作的背景理解为殷末周初。
2.恶婚礼失节。此说源自郑玄,其对《毛诗序》中的“无礼”作了关于婚姻之礼的解释:“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胁以成昏,谓纣之世。”[1](P292)显然,其关注点已转移到婚姻之礼。此说在后世引起了不小反响,尤其是以礼解《诗》者的信从。
3.恶无礼以正风化。此说将“恶无礼”导向风化之正。虽仍脱胎于《毛诗序》,其实已另图新意。代表性论说,可参《毛诗名物解》《御纂诗义折中》等。
(二)美婚姻之正。此说一改毛、郑旧说,不以“无礼”为辞,而以全诗基调为美正。最早提出此说者为南宋的王质,其曰:“媒妁之来尚欲使舒徐无喧动,贞女可知。……寻诗时亦正,礼亦正,男女俱无可议者。”[2](卷1)这个说法在后世反响不大,目前看来,仅有朱谋玮、姚际恒等寥寥数人。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者龚红林从楚地婚俗出发,断此诗本义为楚人嫁娶时所唱的仪礼歌词[3],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此说的意脉。
(三)美南国女子贞洁自守。此说与《毛诗序》“恶无礼”说有一定的精神相通,但将诗篇重心放在女子之行,不同于传统的“恶无礼”说、以诗作者的立场表达意愿。这个转变突出了诗篇本身的事件,不再是较为单纯的道德训诫。最早明确标举此说者,是朱熹的《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4](P418)这样的解读,在后世得到了极多的赞同,几乎可以与“恶无礼”说分庭抗礼。
(四)淫奔之诗。此说起于南宋,王柏主张将《诗经》中32篇淫奔之诗删去,首当其冲者即为《野有死麕》[5](P1)。其弟子许谦虽认为此诗为淫奔之诗,但他并未如其师将其删去,而是认为此诗类似郑、卫之风,不应在二《南》之中[6](P418)。明代季本《诗说解颐》亦认为此诗乃淫风[7](卷一)。
(五)戒刺无礼。此说较为晚起。其与传统的“恶无礼”说亦有相通之处,但从创作论角度出发,将诗篇作为刺诗,则是其特色所在。代表性的看法,如明代曹学佺:“或刺淫者之欲,使人归于无邪也。……《左传》子皮赋以规赵武,欲其不以非礼相加。则为刺诗明矣。”[8](P14)清代数位学者,亦有类似言论,如范家相、庄有可等,皆以戒刺对象为男子。不同的意见出于郝懿行:“《野有死麕》,戒淫也。假为贞女告邻女之辞。一章、二章斥他人,故言有女;三章自明己志,故言我。”[9](P184)显然是将告诫的对象设定为女方,亦将告诫的施行者设定为女方。
(六)士托言以拒招隐。此说仅见于清代方玉润:“《野有死麕》,拒招隐也。……唯章氏潢云‘《野有死麕》,亦比体也。诗人不过托言怀春之女,以讽士之炫才求用而又欲人勿迫于己’者,差为得之。……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10](P113-114)
(七)男女相恋之诗。此说起于20世纪20年代,近一个世纪内成为绝对主流。顾颉刚先生是此说的先驱,他认为卒章最重要,将其解读为:“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诚恳的叮嘱。”[11](P440)这个说法与传统的“淫奔”说颇有关联,不同的是,因为社会的变迁和立场的转换,男女之间的感情、欲望得到了正常的重视。胡适先生对此提出商榷意见:“‘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12](P442)此后,顾颉刚、俞平伯、周作人、钱玄同诸人皆参与讨论此诗,大都认同此诗所表现为男女之恋情。20世纪下半叶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基本保持着20世纪上半叶的说法;大陆地区的学者,在认定男女恋爱之诗的同时,基本都将男子身份确定为猎人。对于女子的身份,则言者不多,似仅有林庚先生认定为猎户人家之女[13](P36)。
二
诸说之中,“士托言以拒招隐”说当可首先排除。方玉润此说,极富想象力,但显然不合逻辑。既为拒绝招隐,何必托言“怀春”呢?既言怀春,可见是心生被赏识、被接纳之念头,若再抱璞怀贞,岂非坠入虚伪一路?如此安得称为高人逸士!方氏解读末章更显滑稽:“亦惟望尔入山招隐时,故徐徐以云来,勿劳我衣冠,勿引我吠尨,不至使山中猿鹤共相警讶也云尔。吾亦将去此而他适矣。”[10](P114)既在山隐居,自当恬淡其志,何存“衣冠”之谓?且招隐之迟速,与隐者衣冠之劳,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联。至于山中猿鹤、改适他方等辞,皆属借题发挥。方氏此说,求之过深,已沦为臆想。
其次要排除的是“戒刺无礼”说。此说将《野有死麕》作为刺诗,证据不足。诗篇中并无证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根据此说的情形,若诗篇为戒刺男士之作,意即吉士不当诱女,那么,对于“有女怀春”一句似无法解释:吉士之所以会诱女,与此女怀春大有关系,否则,若女未怀春,男方之行为应该属于挑弄、招惹,而不能称“诱”。若诗篇为戒刺女子而作,如郝懿行之说,那么,对于“吉士诱之”一句似无法解释:如果男方没有行动,即便女子再如何“怀春”,也不过是一种意愿,如此是不可能产生一种事实供世人借鉴的。也就是说,这个看法将无礼之淫情作为批判对象,但忽视了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男女双方的投入和参与,只是单方面的陈说,根本不合情理,也不能与诗篇文本取得对应。
再次要排除的是“美南国女子贞洁自守”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将诗篇卒章解读为女子凛然不可犯之辞。如果单纯看诗中“无感”、“无使”之词,应有可能是否定“感”、“使”行为的意思;但如果加上“兮”这个语气词,是根本不可能有凛然不可犯的感觉存在的。如果真是一种拒绝,何必言“舒而脱脱兮”!又何必再言帨与尨之事,徒生滋扰!末章为女子口吻,自来研究者多数是认同的,女性在语句末尾加上语气词的时候,如果不是疑问或者简单的陈述,那么多半是要展现女性气质:以示弱来争取主动,以否定来表示肯定。《野有死麕》的卒章,绝非一种拒绝之辞。建立在拒绝基础上的贞洁自守的看法,都未免胶柱鼓瑟,致使失却诗篇真义。
复次要排除的是“美婚姻之正”说。此说将“死麕”“白茅”都作了婚姻之礼方面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汉唐《诗》学里已经存在。如果真是婚姻之礼,那么,如何解释“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呢?当然,他们遵从毛《传》,将“春”解读为季节,将“诱”解读为导引,似乎解决了矛盾。但是,毛《传》的这个解释显然是孤立地解释词语,并未能就诗篇的语境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春,固然是季节,但在此诗中绝非季节那么简单。春季天气回暖,阳气生发,人的情欲亦随之有所复苏,故春常与人之情欲联系起来。古代典籍中所谓的思春、怀春,几乎从来没有解释为思念春天的。本诗中的怀春,亦应遵从惯例,释为女子情欲的苏醒与高涨。以此而论,诱固然可以有导引之意,但在本诗中,显然是引诱的意思。此点欧阳修《诗本义》已有揭示。因此,从情理上言,此诗并非关于婚礼。
另外,将此诗与婚姻之礼联系起来,郑玄是主将。其主要根据为礼书记载。如《仪礼·士昏礼》载:“纳采用雁……纳吉,用雁,如纳采礼。纳徵,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徵礼。”郑玄注曰:“俪,两也。……皮,鹿皮。”[14](P962)可见,士之婚礼需用鹿皮两张。而《野有死麕》诗中只出现了死鹿,并未言是两只,直接由死鹿联想到婚礼所用之鹿皮,于理不合。即便死鹿的出现是为了得到鹿皮从而讲求婚姻。据礼书所载,婚礼除用鹿皮外,还要用大雁、玄纁。而这些在《野有死麕》诗中均不见踪影。仅仅由死鹿推断到婚姻之礼,是索隐过度的表现。清代的顾镇[15]、马瑞辰[16](P96-97),为照顾礼书记载,乃认为诗中的鹿,仅为鹿皮,非指死鹿整体,显然在逻辑上无法圆满:礼书记载婚礼需用鹿皮,并不代表文献中出现的所有之鹿都与婚礼相关、都必须是鹿皮。不得不说,用礼制、民俗等知识来解释《诗》文本,虽时有奇效,但一定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对接,不能生拉硬扯,否则极易落入胡言乱语。如此,“恶无礼”中的“恶婚礼失节”说,亦可排除。
此外诸说,更像是站在不同立场对同一事件所发表的意见。根据这些说法,此诗含有男女之情,已无可疑。那么,考察此种情感之具体语境,对深入理解诗篇的事义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三
诗篇首章之死麕、白茅,在传统解释中吸引了很多注意,目前既知与婚姻之义无关,可知其为普通物象,前八个字是普通叙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中“怀春”“诱之”,前文已有论述。那么,其中的士与女就需重点讨论。
首先,“有女××”的句式在《诗经》中亦有它例:
有女仳离,啜其泣矣。
(《王风·中谷有蓷》)[1](P332)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郑风·有女同车》)[1](P341)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郑风·出其东门》)[1](P345)
根据郑玄《毛诗谱》,此三诗所在的《王风》和《郑风》皆为东周之作[1](P329-330、335-336)。这或许暗示出:《野有死麕》的年代与此是较为接近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据此可知,“有女”乃指真实的而非虚构的女性。
其次,《诗经》中士女对言的情形,有如下数例: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卫风·氓》)[1](P324-325)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郑风·女曰鸡鸣》)[1](P340)
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郑风·溱洧》)[1](P346)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小雅·甫田》)[1](P474)
《郑风》年代皆属东周,已为公认事实。据《毛诗序》,“《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1](P324);“《甫田》,刺幽王也”[1](P437)。可知以上四诗亦皆为东周之诗。显而易见,此种语境中的“士”,往往已非贵族之士,而往往指涉普通的男性。这种指向与历史学者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士”这一原属贵族的阶层与“庶人”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士庶出现合流的趋势[17](P77-80)。也就是说,在东周时期,士这一称谓的社会地位及阶层属性出现了很大弹性,并不太引人注意。尤其是士女对言的语境中,士作为男性的性别色彩显然更突出、更浓厚。以此而观《野有死麕》之“吉士”,当亦有此种倾向,但情况似乎又有所不同。
《诗经》中的“士”,不仅有单字言者,亦有多士、吉士、髦士、庶士、卿士、厥士、良士等复合词。这些词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单字之“士”。“吉士”之称,不见于西周金文,亦不见于《诗经》外的其他先秦典籍①《尚书·囧命》载:“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孔安国解释为“吉良正士”。见《尚书正义》卷一九,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247页。但此篇文字属于伪古文二十五篇之中,真实性有待验证。。在《诗经》中除《野有死麕》外,亦见于《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1](P546-547)其中的“吉士”和“吉人”,郑玄都解释为善士[1](P546-547)。但根据二者分别媚于天子与庶人来看,身份当有所区别。裘锡圭先生曾作解道:“吉士是贵族。吉人可能指统治者从庶人中提拔起来管理庶人的下级官吏,里君也有可能是这种人。”[18](P20)这个推断应属合理,《卷阿》语境中的“吉士”当为贵族,且地位不低。这是否意味着,《野有死麕》中的“吉士”也如此呢?
历来学者解释《野有死麕》诗中的“吉士”,多不出美、善二义。对于其社会地位及阶层属性,似乎并未给予足够重视。《野有死麕》之语境显然不同于《卷阿》,而同样的词语在不同语境之中,往往会有不同的意义。从《野有死麕》中“吉士”对怀春之女进行引诱的行为看,应非“媚于天子”之“吉士”角色了。不过,根据次章“有女如玉”之语,诗中“吉士”仍应属贵族阶层。此处所谓“如玉”,传统解释多从道德角度出发,言女子之德如玉般洁白无暇。朱熹的解释别具一格:“如玉者,美其色也。”[4](P418)这个解释得到了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诗经》中的玉,多种多样,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多有研究。以玉比德,多用于男性;以玉比色,则男女均可。如《魏风·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1](P357)即以玉之观感比当时公族之男子。以往研究中,对于玉在视觉上引起的感觉不够重视。以《诗》而论,言玉之观感早已有之。如《大雅·棫朴》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1](P514)以金玉连言,状其外表之盛。又如《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1](P434)此处两个玉字,即便前一个可作道德上的解释,后一个则绝对是观感之言说。“金玉尔音”是以金玉之美状声音之美,以金玉在视觉上的夺目,形容声音在听觉上的动听。这种感觉的互通,在语言文字中经常出现,钱钟书先生“通感”之称,精确无比[19](P62-76)。从女子怀春而吉士相诱的语境来看,“有女如玉”应非言女子之德,而是如朱熹所言指女子之色。
玉石质地坚硬,以玉来形容女子之色,应非取质地而言。以理推之,应是取玉之色白、泽润,来形容女子之皮肤白润,风貌优美。这首先意味着,男女相会的时间是在白天。因为观察到女子之皮肤、容貌,需要足够的光线才能看见,可知当为白天。其次,玉只有为白玉,才能用来形容女子之色。黄玉、青玉等它种颜色是断断不可的。以玉的发展历史来看,白玉一向较为难得,且色易杂。以白玉来形容女子,当属较为纯质的白玉。关于两周时期的玉,因为数量不大,学界目前还不能有清晰的认知,尤其是玉的颜色,因为时间久远往往会发生改变,根据目前的存世周玉,很难给予精确的定位。不过,根据情理推断,质地纯美的白玉当非寻常人家能够得见。以周代墓葬玉器而论,诸侯和大夫之墓普遍用玉,士和庶民墓用玉比例明显偏低;且诸侯和大夫墓随葬玉器器类丰富,而士和庶民墓所见器类较少;相应地,诸侯和大夫墓葬随葬玉器数量大,而士和庶民墓随葬玉器少或者不用玉器随葬。随葬玉器的质量也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20](P291-292)。墓葬玉器尚且如此,则日常生活之用玉当亦有明显之等级差异。诗篇中言女子之色如玉,不会仅仅是男女之外第三方的陈述,应源自“吉士”之直接观感与认知。这说明“吉士”对于质地纯美之白玉是存有相当认知的。故可知诗中“吉士”仍应属贵族阶层。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野有死麕》中的“吉士”,地位已不如《卷阿》中的“吉士”,且与庶民阶层相差不多,而由白玉的讨论可知,“吉士”仍属贵族,身份似乎并不太低。那么,诗中事件出现之背景,最有可能即是在贵族之阶层地位有下坠之势而余荫尚存之时。以此而论,此诗当作于东周时期,与当时阶层松动的情形是吻合的。
四
男子身份既明,则女子身份亦得言之。根据前文所引,在“有女××”的句式及士女对言的情况下,除《郑风·有女同车》外,女方皆非贵族。《野有死麕》诗中女子,亦非贵族。若为贵族,直接受到“吉士”相诱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也不太可能直接给人以观察皮肤、容貌之机会。另,以全诗情境而言,士、女二者出现在城外之野中,均应属个体行动;而从“怀春”、“诱之”等语可知,两人此前并不熟悉甚至互不认识。这就意味着,两人不可能是经过约定而至于野地的,应属邂逅。那么,女子单独至野,就属于自发行为。以情理言之,女子之居住地必不甚远。所居之地离城外之野不远,可见其所属阶层应为庶民。
两人在城邑之外的野地中相遇,作为贵族的男子,居住地应离事件发生地点较远,其单独至野,应属外出游玩的性质;女子至野的动机,尚不明确。但其受到贵族男子的吸引,则可以肯定。结合诗篇中的死麕、死鹿之语,可以推断该男子是至野打猎。男子的猎物,应即诗中的麕,麕为鹿属,诗中死麕、死鹿当为一物,盖重言之也。鹿之习性,一般喜栖于混交林,不进入密林。男子在野地捕杀之,应属合理。至于诗中的林地,应为男女双方情意既合之后寻找的欢会之地,以其多树木更隐蔽之故。
如此,诗篇中男女双方的阶层是有差别的,男子应为贵族,虽然其时贵族地位已有所下降,可能比起庶民来相差不远,但究属贵族阶层;而女子则为庶民。二人邂逅于野,一见钟情而至于密林幽会、情爱贪欢,显然是为情欲所驱,欲望大于情感。简单地归结为“男女相恋”,恐怕失之浮泛。男女之间,互生情愫、彼此喜欢本无可厚非,但不经媒妁之言、婚姻之礼,直接至林中欢会,则未免与礼不合。以当时主流话语之礼制风俗看来,此种行为显然是一种“突破”。而这种突破在日常状态的社会中,必定会得到负面的评价。尤其是贵族男子的行为,已经清晰地映现出当时贵族阶层道德的滑坡以及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诗的产生,或许并不暗含道德评判,但其入选《诗经》,应当是将其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加以展示。《毛诗序》中“恶无礼”三字,在基本倾向上是起码合拍的。
[1]孔颖达.毛诗正义[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王质.诗总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龚红林.从楚地婚俗看《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本义[J].云梦学刊,2007(4).
[4]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王柏,顾颉刚.诗疑[M].北平:朴社,1935.
[6]许谦.诗集传名物钞[A].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季本.诗说解颐[A].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曹学佺.诗经剖疑[M].《续修四库全书》(第60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郝懿行.诗问[M].《续修四库全书》(第58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顾颉刚.野有死麕[A].古史辨(第三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胡适.论《野有死麕》书[A].古史辨(第三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林庚.读诗札记二则[A].文史(第4辑)[C].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贾公彦.仪礼注疏[M].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顾镇.虞东学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8]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A].文史(第17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钱钟书.通感[A].七缀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0]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徐 炼
I207.22
A
1006-2491(2016) 01-0001-0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出土文献与《诗经·二南》新证”(2014CWX005)
邵杰(1984-),男,河南新安人,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唐前文学与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