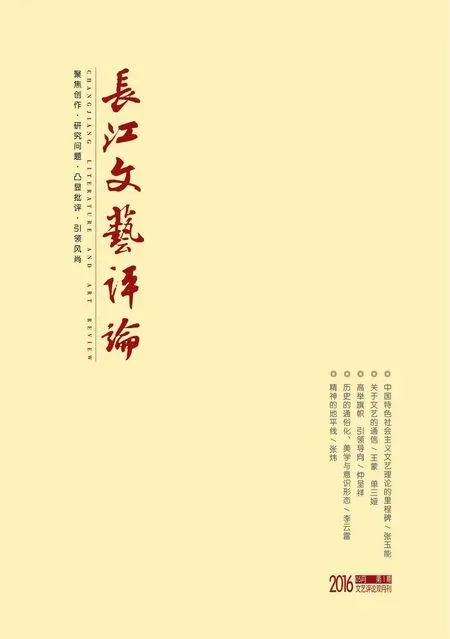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路
——我的文学批评观
2016-11-25杨光祖
◎ 杨光祖
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路
——我的文学批评观
◎ 杨光祖
杨光祖,男,汉族,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文化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当代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百余篇,有多篇散文多次入选全国年度散文选。从2003年起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已经在《人民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200多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收录。出版专著四部:《西部文学论稿》《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杨光祖集》《回到文学现场》。曾荣获甘肃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甘肃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
一
2013年8月的某一天,我们大学毕业20年后重回母校,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会议室里,面对着赵逵夫等几位当年的老师,我作为班长发言,其中我说到了一句话,大家都笑了。这句话是:想当年,我瞧不起搞现当代文学的人,我觉得那里面没有学问,可光阴流转,如今的我已经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10年了。
世事沧桑,造化弄人,大学时代的我是以“杨古典”而驰名全班,教授《古代汉语》的甄继祥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说,读书当如杨光祖,还把这句话写到黑板上,并说,我可以不上《古代汉语》。我感谢甄老师的厚爱,但课还是一直在听。
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是古代汉语、唐宋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是每期必读的。大学时期撰写的几篇作业毕业以后也都公开发表了。进入21世纪,当年教授我们唐代文学的杨晓霭老师,还几次请我加入唐代文学研究会。但我只笑笑而已,我哪里还有那个资格?
大学毕业后,一直很迷茫,几次想考研究生,但懒惰占了上风,无事可干,于是写散文,那几年与诗人张哲交往,倒是发表了很多散文,大多都是报章体。如今看起来,也就是作文而已,学生腔太浓,羞于提起。我真正的散文创作是2007年以后了,这里暂且不提。
写了几年散文,也还是感觉很无聊。1998年,当时在庆阳工作的马步升到省委党校培训。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非常喜欢,那种粗野、恣肆、洋洋洒洒、大气磅礴慑服了我。于是,主动跑到他的房间,认识了他,并为他写了几篇小评论。未料从此就走上了文学评论之路。
其实,我的骨子里,更喜欢古典文学、书画艺术,亦喜欢哲学,虽然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差,但那种喜欢是压不住的。2000年和2012年前后两次跑到北京大学、中央党校进修、访学,名义上在中文系,其实每天都在哲学系听课,主要是听西方哲学。我感谢北京大学西哲老师,比如陈嘉映、靳希平、赵敦华等老师,他们的演讲、课程,给了我人生旅途中极其深厚的喜悦。而在书画一途,研习多年,每每感觉到一种幸福,陈传席、梅墨生两位先生惠我甚多,我的朋友杨海燕在书法领域造诣很深,朝夕相谈,受益匪浅。
因为有了这样的知识视野、艺术兴趣,反过来看现当代文学,尤其当代文学,有时候,就很有一种不满足。现当代文学领域,我最佩服鲁迅先生,他的道德文章,他的文字功夫、思想境界,至今无人企及。在我眼里,当代文学还无法与现代文学相比。我说过,文学不是拔河,哪边人多,哪边就赢了。当代文学就小说而言还无人能够超越鲁迅,散文方面还无人可以超越周氏兄弟,你就不能说你超过了现代。当然,我对那些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作家抱以真挚的敬意。
从事文学评论也近十载,但说实话,快乐着,并痛苦着,无聊着。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作品?我也不知道。面对一部作品,我没有理论,或者说,不用所谓的理论生搬硬套,我只是用我的心去感知,去体悟,然后把这种感知、体悟形成文字。我不是那种可以面对任何文本而洋洋洒洒写万字长评的人,我只对感动了我的作品才有话可说。但这并不说明,我不喜欢理论,我每天读理论书的时间更多。
我深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和危险,如果你还想说真话,按你内心的真实感觉去说。所以,从我出道以来,我很少主动为认识的作家写什么文字,马步升是一个例外。也很少通过我评论的作家去发表文章。我不愿意那样做,觉得很丢人,甚至可耻。我评论的很多作家,我至今还不认识,从来没有见面,即便偶尔碰面了,我也装作不认识,从不谈及这个问题。有时参加全国文学会议,我也不会跑到他们的房间,说,我给你写过评论。一个评论家也有一个评论家的尊严和自由。2007年在北京开全国青创会,红柯正好坐在我的旁边,而我刚好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严厉地批评了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我刚一落座,略有尴尬,不料他主动说,你的文章我看了。我说,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你能主动去买我的书,并认真读完,然后撰写那么一篇文章,我很感谢,这才是真正的读者。
可是,这样优秀的作家在当下的中国并不是很多。有些作家邀你写他的评论,你拒绝几次,人家仍然坚持,你就不好意思再推辞,于是,你就写了。结果,人家看了,很不高兴,嫌批评太多。其实,因为都是熟人,你已经很客气了,批评也藏得很深。但人家还是不高兴,于是约去的稿子就没有了下文。有些一开始就告诉你,你马上写,一周交稿,某大刊下月要出,于是,你什么都扔下了,写完了,人家说,你还是不懂我的作品,于是,也没有了下文。后来,你遇见那个大刊的编辑,人家说,嘿,根本没有这个事。
有些作家希望评论家评论他们的作品,也比较喜欢看你把某某批评得体无完肤,但当你批评到他的时候,他就无法容忍了,而且你还只是劝百讽一。这些作家最拿手的武器就是:你没有读懂我的作品。聪明一些的会稍微改变一下语意:你批评的是我以前的作品,我某某年之后的作品已经没有这些缺点了。其实,你批评的正好是他某某年之后的作品。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告诉我,我的作品你读得太少了。我就问他,你有多少作品?他说,100篇左右。我就正告他,我最少看了你80篇。面对这样的作家,作为评论家,你觉得很无奈,很可耻。因为这是对一位严肃的评论家的一种羞辱。他开始怀疑你工作的态度了。
我喜欢那种和你讲理的作家。你说他的作品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与你讲理,或者不理睬,也可以,各写各的,评论家从来不是作家的附庸,或者奴才、丫鬟,要看作家的眼色行事。不要说“你没有读懂”,你可以说那些地方“你没有读懂”,简单的谩骂或否定,都是一种不负责任。
二
当然,在评论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文学,怎么样才算优秀的文学?并对文学批评本身也进行严厉的反思。评论家有自己的职业尊严,但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职业底线。只有你严守底线,有尊严地进行批评,真正的作家才会尊重你,包括尊重你的工作。
马克思说,资本在狂欢。随着资本的大幅度进入许多领域,艺术也难免其灾。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城市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开始形成,大众文化一枝独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时空秩序被打破,以往的经验方式已经落伍了。
文学艺术,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什么是艺术?如何鉴赏和评价艺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众文化的时代,倘若以大众的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那么,谁的读者多,谁就是老大,或者说,谁的粉丝多,谁就最优秀。问题是,大众靠得住吗?艺术,也和政治一样,人人都有一票吗?民主的普选制,是否适用于文学艺术?如果以粉丝数量来评价,章太炎绝对不是于丹的对手。如今的中国,有几个人能丝毫不费劲地阅读和理解章太炎的著作?
另外一个问题,评论家评价一部作品以什么途径,或者用什么武器?大家都认为评论家必须要库存很多理论,然后凭借那些理论来评价作品。我们的批评家确实也是如此,区别只是有人只有一个理论,有人有几种理论。但拿一套理论评价一部作品时,它的功效如何呢?以前我们用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作品,使得读者倒了胃口。现在很多人用海德格尔理论来评析作品,如果依然是庸俗的、不及物的,那么同样倒人胃口。当评论文字只是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这种碰碰车式的概念游戏,又有什么意义?
多少年来,我们依靠“理论”进行文学“批评”,误人误己呀。我这样说不是否定理论,理论很重要,但理论必须通过学习化为自己的血液,然后通过“直觉”表现出来。张爱玲在《私语》中说:“一切要让人在切身体验中发现它”,可谓至理名言。当代作家,还有批评家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没有感觉,没有对文字的直觉。我经常说,文字必须要经过人的身体,成为一种生理的东西,没有疼痛感的文字,是无生命的。当代中国,借来的理论太多了,可以说是理论过剩,甚至理论恐慌。但是,理论真正起作用,还必须与自己日常生命的存在性发生关联,作为一名评论家,你必须对你使用的理论有感应,最好有一种浸润。然后,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而不要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搬运工。我们很多学院派评论家做的就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的工作。我虽然也经常阅读西方理论,但我不屑于做搬运工,我总是力求用自己的理解,直接进入文本,跟着感觉走,而不是理论走。
我一直觉得审美直觉才是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面对一个文本,你有没有感觉,从心理到生理,有没有触动?不管是反感,或者感动,都必须要有。如果没有一点感觉,只是生硬地搬用一些理论来言说,我觉得这样的批评家非常恐怖。高尔泰在一次访谈中说:“批评家最主要的素质是审美素质。要求评论家必须有罗丹的技术才有资格评论罗丹的艺术,这样的要求是荒谬的。”牟宗三认为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而“真生命与真性情”,也就是“存在之感受”。就文学批评而言,我喜欢做那种“创造性的批评”,我也努力做一名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我对瑞恰兹那种精密的、原则的,甚至科学的文学批评,不太感兴趣。当然,我也知道这似乎是目前的趋势,但我不愿走那条路。
本雅明认为“光韵”是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标志,古典艺术是光韵的艺术,而现代艺术是复制艺术。“光韵”就是作家充盈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内化于作品之中,此乃真正的艺术本性之所在。它是挥之不去的生命呼吸之馨香。本雅明最为看重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神交阶段的自然关系。他说:“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只要生命的原真性存在,生命之光韵才不会消失。而如今的艺术多的是人造的光环,光环与光韵之区别,是它更多的在文本之外,比如艺术家的头衔、名声、地位等等。
现代艺术中光韵的日渐减少,主要原因是现代艺术生产的制作与复制技术的发展。而时代的巨变,也结构性地改变了人,大多数读者、观众已经无法看到古典作品中的光韵了。朱宁嘉说:“现代艺术培养起来的接受者,由于影像的连续刺激,更多时候对艺术的欣赏采用的是反射性感知,即本雅明概括的涣散消遣式,因而,往往感受不到存在于艺术中的灵韵,尤其是古代艺术中的灵韵。”“现代艺术培养起来的感知方式,不只让人无法感受传统艺术中的光韵,往往也致使人们与现代艺术中潜藏的灵韵擦肩而过。”以本雅明的这个理论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也是极其中肯。当代文学,尤其那些走市场的,只是技术品而已。那里可能最多就只有复制了,光韵之类,真的是很难看见了。
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阅读、电脑阅读、iPad阅读、手机阅读的迅速普及,3D、4D、5D电影(影院),尤其7D电影(影院)的诞生,直接将电影与游戏结合,还有微博、微信成为人类日常化生活,都不断地加剧了浅阅读的步伐,和视觉娱乐的发展,原来那种带神性的深度阅读,人与神合一的体验完全消失了。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去认真地阅读古典作品,尤其那些大部头的著作了。他们连读一首短诗的时间、精力、感觉都没有了。现代艺术日益成为一种可制作的快餐艺术。
在这个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艺术迅速沦落为商品,“文人,一如依赖华美的衣着装扮而可以更好出卖自己肉体的妓女,以美的幌子向人们出卖灵魂并兜售虚假的幸福。”(朱宁嘉:《艺术与救赎——本雅明艺术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那些生产者的作家也是如此,他们被资本绑架,以码洋为评价标准。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作家如果还要试图保留批判立场,那将是一个很不好的结局,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商品化社会机制。
在这样的时代,从事文学艺术的评论,就是一种冒险,也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对于评论家来说,有时候真不是一种快乐的审美体验。
三
古人说,天地人神。可是我们远离天地太久了!一个文化人如果一不知天命,二不接地气,那他的文字就只能是温室中的花,好看而不中用,根本经不起风霜的打击。我一直在批评学院派的所谓文学论文,有某知名学者撰文批评我,说我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因此才仇视学院派。其实,我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我也是一名教授。我只是对文学过分学科化、技术化、工匠化看不惯而已,并没有仇视。我以为文学更多的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存在状态,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是很好的。诗人阿信说:“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
我们现在的学院派由于学科体制的需要,在所谓学术的名义下,屠宰文学,摧残文学,使得我们的学生越来越不知道文学为何物。阅读他们的文学论文,满篇是后现代名词,到处是德里达、海德格尔,其实,他们对这些扎根于西方文化厚土的大师了解多少真需要质疑。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与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党八股,“言必称希腊”,并没有多少差距。中国的文化创新、中国的文学创作,还是要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厚土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鲁迅说,从文学概论里走不出作家。我认为也走不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一名文学批评家,他们必须把根扎到民族的大地去,一个与本民族的文化联接最紧密的人,才能知道它的疼与爱,才能与它生命相关。我们必须向别的民族、国家学习,这种学习也不能限制在几个名词上,而是要触到他们文化的生命线上。
在10多年的文学评论实践中,我也积累了不少的个人体验。新世纪以来,是文学评论日益学院化、技术化的时期,文学评论文体日益规范化,或者日益课题化,语言日益教条化。但我一直在抵制这个倾向,我顽固地认为文学评论必须首先是美文,而且必须与你所评的作品息息相关。我们有些学院派的文学评论,其实把文章中的作品换一个别的作品都依然可以说得通。王朝闻说,一个美学家必须掌握一门艺术,这样才能深入美学的堂奥。从事文学评论的人,从事一下文学实践对于体悟作品的细微之处,非常有好处,因为道心惟微,艺术的奥妙就在它的微细之处。我个人本来最早就是写散文的,前后发表了200余篇。后来从事文学评论,散文的写作就很少了,但依然在坚持。近几年,已经在《华夏散文》《西湖》《雨花》《作品》《延河》《书屋》《海燕》《飞天》《黄河文学》等杂志发表了几十篇,并被圈内朋友所认可,多次入选全国散文年选,和各种散文选本。就我个人来说,对我的部分散文我还是很珍爱的。
很多人说我的评论与众不同,一是随笔化,二是太刻薄。我写评论文字,总是尽量散文化、美文化,而不愿意太学术化,干巴巴地让读者为难。至于批评我为文太刻薄,缺乏对作家的同情之了解,我一直不十分认同。年初,美国的一位朋友陈瑞琳女士,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评论家,她看了我的那篇关于西北中短篇小说的文章,给我发来一个短信:“你这文章能发表,那编辑真是开了宏恩!你手上那把刀子总是扎到作者的痛处,作者叫痛,编辑也不好受,我读着都心惊肉跳。”看了之后,我才第一次认真地反思,难道我的文章真得这样厉害吗?最近几年,我在西北文学方面下力甚多,尤其陕西文学,当然主要以批评为主,包括对贾平凹、陈忠实老师.我一直奉守“我尊重,我苛求”的宗旨,我认为对自己喜欢的作家,进行廉价的吹捧,是一种亵渎。古人说,“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我愿意做一个如此的批评者。
我曾经在《南方文坛》2012年5期的“今日批评家”发表短文《我的批评观》,其中说:
文学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的灵魂交流。面对优秀的杰作,心有灵犀,拈花微笑,那当然是最高境界。但面对一些粗制滥造之作,或者反人性、反人类,价值观错位,低俗无聊之作,也需要当头一棒,禅宗所谓棒喝是也。不过,肯定,或批评,文学批评家都是必须用“心”的,不能胡来,成为圈子批评、哥们批评,或者批评棍子,也不能将文学批评仅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谋生的工具。新世纪以来,学院批评的崛起,在强化文学批评理论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批评的尺度。学院式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用西方人的一两个“理论”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但其实与文学文本没有关系,是一种不及物批评。
当学院派用一套一套的所谓理论“研究”那些文学作品时,“文学”就不存在了,在他们那里“文学”早成为了“尸体”。他们指手画脚,说这是“后现代”,这是“后殖民”,这是“新历史主义”,云云,很喜欢分类。这种“文学批评”至少产生两个结果:一、只有“理论”,所谓“文本”随便换一个都无所谓的;二、没有“文学”,也没有“批评”。利维斯说,所谓批评,就是一种差别意识。但在学院派批评家眼里,所有的文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文学批评,其实更像是把“文学”当做了他们驰骋“理论”的“资料”而已。
在那篇文章最后,我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者往往是非常合格的读者,也是作家真正的知音。作为一位批评家,对那些声明赫赫的中青年作家,尤其要有一种批评意识。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致敬。”
美国文学理论家海澄·怀特说,文学在西方被认为是高级文化,或者说是高级文化的最直接的表现。因为文学代表着文化。所以文学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对文化未来的争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事文学评论也是一项非常愉快,而且充满冒险、悬念的工作。我喜欢它。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有一首名诗《未选择的道路》,他说:
树林中岔开两条路,而我——
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
而这已造成重大差别。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