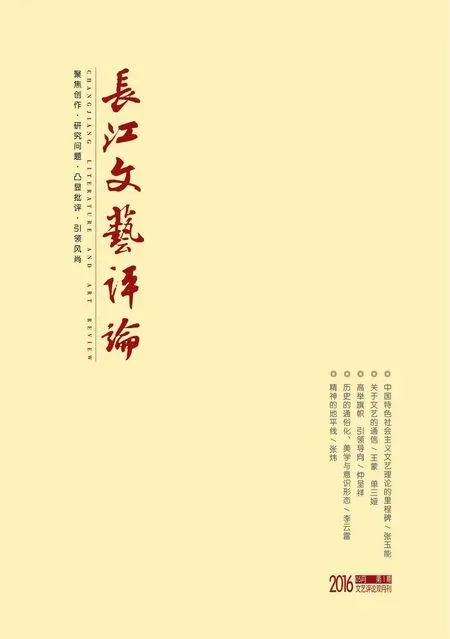生存的镜像与时代的见证
——论郭金牛及其诗歌创作
2016-11-25刘波
◎刘波
生存的镜像与时代的见证
——论郭金牛及其诗歌创作
◎刘波
今天,若再从“底层”文学的角度来谈论打工诗人郭金牛,虽然方便,但不免有将问题简化的嫌疑。他不乏底层普遍的“灰色经验”,但他又有着个体的独特感受,我甚至觉得是后者成就了他的写作。“底层”打工者只是在生存的意义上讨生活,郭金牛虽为其中一员,但仅在社会学层面代表了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在文学的场域里,他是一个热衷于“远方”的草根思考者,其所有的经历,都在精神的意义上赋予思考以力度,他将其转化成分行的文字,这里面又暗含了多少打开自我和他者灵魂空间的可能!
其实,我对郭金牛的认知更多源于疑惑:为什么他能够从打工文学群体中脱颖而出?他凭借的仅仅是会写诗吗?是否还有别的因素促成了他在这个时代向内转?郭金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者,也并非一个单纯的诗人,他背负着几重复杂的身份,这些因素的聚焦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镜像。但无论怎样,对郭金牛的理解,草根身份的定位是一个方面,重要的还是其诗歌本身。没有立足于文本的阐释,言说会显得空洞,尤其当我们今后回过头来考察这段历史时,可能会发现,郭金牛所书写的真实,见证了一代人曾经历过的生活,曾留下的记忆。
一
在新世纪初,郑小琼作为一个见证后工业时代之残酷的诗人被推出来时,“底层”与“打工诗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贴在她身上的标签,但我们除了知道她笔下“冰冷的铁”和“四万根断指”之外,何曾想到过她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实践者?郑小琼的被放大,更多还是因她的生活处境和社会身份,这种外在因素与其写作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一个时代“底层”写作的标签。虽然郑小琼已被定格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历史版图中,但以她的创造力,肯定不仅仅是“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过早地为其下定论,也就是过分简化了一个丰富的灵魂。
或许郭金牛无意也无力去反抗那些贴在他身上的各种标签,但他确实是在以一个草根诗人的身份去介入自己的生活,并让写作显得真实质朴,且富有尊严。可能有人会认为,处于当下的底层,很难有尊严可言,但是诗人内心对诗意的坚守,就是他向时代发出的孤独回应。“如果我在诗中表述有多么虚构,那么,在我内心就埋藏有多么深,那‘深’处使我隐现的良知羞愧。”而依我读其诗的感受来看,他所有的虚构,都有着现实的映照。即便他将工业之残酷比附于秦之暴政,仍然脱离不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底色,由此观之,他的审视就顺理成章吗?懂得良知和羞愧,他应该不会仅仅满足于在修辞上的闪转腾挪,而必须走出封闭的诗之象牙塔。他那些貌似虚构的自我写真,也是带着深深的痛感,就像我们看到郭金牛作为一个历经艰辛之人的沧桑。
没有经历,难言沧桑。20多年的打工经历,郭金牛的感触应该比很多人都深,他所有的回望与书写,都可能是对自我的反思,正像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郭金牛的每一首诗都是在创造性表达中蕴含着内省之力。他只要下笔,就是回忆,但他并未在愤怒中控诉,也没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去抱怨和揭露,相反,他甚至表现得有些隐忍,但冷静的理性中又透着一股言说的坚定。
一群热锅里的蚂蚁还在搬运。钢筋。水泥。阳光。/其中两只,必须挺住。/挺住意味着:堂兄的父亲,我的伯父/癌细胞就扩散得慢一些。/以我们的快换它的慢//也以我们的快,加速城市的快/突然,脚手架,一个人/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9.8米/秒2。
(《打工日记》)
这就是建筑工人在烈日炎炎下的脚手架之痛。诗人没有直接去言说悲剧,他只是以快与慢的博弈,刻画了一场惨烈的审判。当诗人看到662大巴车撞倒一个离乡打工的少年时,他也明晓自己忍耐的极限,可他竟是如此描绘:
我好像一个受伤的穷人,刚刚苏醒,真叫人心烦//我不确定,月亮/是在肺病上撒下一层霜。/还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662大巴车》)
这种感同身受,非一般人所能有共鸣之意。郭金牛兴许是酝酿了好久,才无奈地出示了这样一种姿态,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写下,记录,这正是诗人的隐痛。
郭金牛没有像很多小说家那样,以完整的叙事切入现实,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在冒险中阅读或审视现实。就像杨炼在评价其诗歌时表达过这样的观念:“诗不描述现实,而是打开它,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本隐藏着的世界,一种我们没发现的深层自我。”郭金牛就是在打开他所遭遇的现实,并赋予它以新意,而非复制苦难,所以我们才能从中见到诗。所有的技巧都已化在“入心”的创造里,自然,贴切,无限接近却又超越了他所走过的凡俗人生。
二
郭金牛曾在诗集《纸上还乡》的后记《外省、工业、乡愁与疾病的隐喻》中感慨:“每当异省的风寒吹过,一些文字就会带着风湿般的病痛,不期而至,可能,这就是我无意间的‘追问’,也许‘追问’,才能更着力‘反思’。”郭金牛的写作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他可能并没有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去思索写作的责任,但当他以诗歌的方式面对现实时,“追问”是无意的,那么“反思”就成了一种精神自觉。
画面可见落款的作品有38件。14件作品可见年款;其中10件作品有中文、外文结合的署名,即“铁夫 李玉田”+“L、Y、TEIN”(图3)及年款;4件作品包含了外文署名(“T、F、LEE”)(图4)及年款。另有25件作品仅有外文署名,即“T、F、LEE”(图5),无年款。
从这个意义上衡量,郭金牛可能就是这个草根文学时代的旁证。他的写作也由此证明:诗歌并不是高高在上者的事业,它同样可以在普通人那里获得响应,尤其是他将自己特殊的见闻和经历当作素材。和很多完全依赖想象写作的人不同的是,郭金牛一直就在时代的现场,“我不在工地上,就在工棚里。”(《想起一段旧木》)这种在现场的生活,注定其写作会有与他人不一样的新意。“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外省干活》),交流似乎都成了隐形的障碍,这是在外讨生活的艰难与不易。郭金牛很少渲染悲凉的气氛,他只是以简洁的修辞来呈现,这份简洁里更多是他日常的感触。如果说背井离乡是这个时代打工者的常态,那么,他所写下的每一次不幸,每一场灾难,都是以伤痛累积和叠加出的命运。
郭金牛所经历的时代与现实是破败的吗?至少不是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他试图去与这个“残缺的世界”和解,对此,他是否又能做到内心与现实的平衡?在他最有影响的那首《纸上还乡》中,对于曾热闹一时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同于新闻报道的视角与美学审视。这样的文本,无论对于当下还是历史,也不失为一份重要的参照。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速度,领走了少年/米,领走了小小的白。
他以诗的方式重叙了少年跳楼的过程,虽然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现场,但他以合理的想象重构了那悲戚的场面。
母亲的泪,从瓦的边缘跳下。/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刚刚落下。秋风,/连夜吹动母亲的荻花。//白白的骨灰,轻轻的白,坐着火车回家,它不关心米的白/荻花的白/母亲的白/霜降的白/那么大的白,埋住小小的白//就像母亲埋着小儿女。
这跳跃的想象勾勒出的是陌生化的诗意,然而,那种悲苦又如此清晰,它们体现在“白”这个意象里,令人无限遐思,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透视了生存的不易。最后,他将自己摆了进来。
十三楼,防跳网正在封装,这是我的工作/为拿到一天的工钱/用力/沿顺时针方向,将一颗螺丝逐步固紧,它在暗中挣扎和反抗/我越用力,危险越大……//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
他的工作和对工友的哀悼共同构成了一种荒诞的画面,而即便这样,他也不过是完成了自己最普通的生活。
就像他面对那么多不幸和苦难,除了诉诸笔端,在现实中也只能归结为命运不济。“我有什么资格//写诗。对生活说三道四”(《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这种自我否定,好像也是无力的,但他毕竟道出了真相:令他羞愧的良知,促使自己继续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揭露那些伤疤和疼痛。郭金牛虽然在诗歌里融入了反讽和自嘲,但他还是与时代保持了距离,这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周遭的困境。他不断地打量生活,又返回内心,再写下那些凌厉的句子,这一过程恰好符合“真经验只关乎诗思对人生的发现”(杨炼语)之意,它要求诗人足够真切,足够用心,方可让书写更富力量。
三
在近年春节不断热炒的“返乡体”文章中,很多人看到的是当下农村的凋敝与荒凉,这或许是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当城市的发展以乡村的没落作为代价,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反思这一命题?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却又渴望回到一种宁静的田园生活,这种悖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悖论,才能在文明的意义上安放自己的灵魂?这可能是再多的“返乡体”文章也难以言说清楚的。这样一个时代的盲点,要经由什么样的人来完成对其最终的解密?郭金牛无意于去担当这样的重任,但他在自己的写作中触及了这个主题。
当自己所在的乡村养活不了我们时,出外打工则成了多数人的选择,可打工之地又何尝不遭遇更大的侵袭。
“罗租村,工业逼走了水稻,青蛙,鸟/这些孤儿,又被夺走了/纯蓝//李小河咳出黑血/周水稻失去双亲/赵白云患有肺病/陈胜,飞快地装配电子板;吴广,焦虑地操作打桩机;/渔阳啊渔阳,真要命。//地上烧着书。坑里埋着人。/工业加工业,会不会生下太多的鬼?会不会突然跑出一只,附在身上?/我开始怀念/鱼/怀念花,怀念鸟,怀念害虫。
(《罗租村往事》)
这是工业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郭金牛在回溯往事中对其作了“抵抗”:在无节制的发展和前行中,他希望能够退守,甚至不惜“怀念害虫”,也只有诗人能想到这种还原自然本色的真相。即便如此,他仍然无力回天,这种被工业束手就擒的无力感,深深地击溃了我们试图建立的田园理想传统。
面对工业时代的疯狂,一旦诗人想到了退守,那种浓烈的乡愁便接踵而至,他想回到故乡,可故乡又回不去了。这种乡愁被悬置的尴尬,让诗人感觉到无处归依,而且这种找不到归宿的茫然,终究是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全感。虽然每年春节临近时,像候鸟一样迁徙的打工者也要回到故乡,寻求传统节日带来的安慰,可是,这种短暂的返乡之旅仍然带着无尽的辛酸。
另外一个人民,从年关中/购买/一张车票,从一个异乡搬到另一个异乡/他要把一年的乡愁,也浓缩在/这一天
(《第十二个月份的外省》)
当故乡也已经沦陷时,传统的乡愁就已经变味了。这可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真相就是如此残酷,而这一页何时才会翻过去?诗人又要将希望寄托在何处?一时好像很难找到答案。只是诗人身上所保留的诗性正义,让他打破了那些高歌猛进的虚幻格局,去探寻潜在的秘密。因此,他的诗要比那些完全依靠想象和虚构的写作更具有说服力,也更让人有信任感。
郭金牛钟情于纸上还乡,或许在现实中是出于一种无奈之举,“在异乡遭遇的一切,让我对故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向往。我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还乡。在现实中,我们身处困境,谁又不是在还乡?对于我,离乡背井二十年,故乡只是名义上的家乡,是漂泊经年的游子梦中的一个向往。”于是,还乡就自然成了内心的渴望,也相应地变成了纸上行为,而迷恋抒情,就与此达成了有效的应和。离乡的游子,漂泊中的写者,依然在寻根,他甚至将自己称为“写诗骗子”,混迹于江湖,“随身/扛着三个外国人:艾略特、荷尔德林、叶赛宁/一个中国人:/海子”(《写诗的骗子,是我》),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郭金牛的前提。他可以“在工地的木板上 旁若无人的写诗”,这种对自我的解放,是基于一种热爱,一份激情,但它也在考验着诗人在这个喧嚣时代的耐心。他在爱情与乡愁之间寻找更阔大的空间,以便盛放他所见闻到的苦难、悲剧和那些千疮百孔的卑微人生。
在《左家兵还乡记》中,他以叙事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千里背尸”的当代奇闻,而在《庞大的单数》中,他书写了打工妹屈辱而凄凉的死亡……面对那些鲜活的个体在艰辛的生存之途中走向毁灭,他唯有以诗写下悲伤,而无法做到更多。这种在现实中的无能为力,也促使诗人转向了神秘的寄托。他在好几首诗中都写到了妖,在这种神话的伦理书写中,他赋予了现实以历史感。在《妖》这首诗中,他靠想象完成了对海子的致敬,而“妖”这样一个形象,其实是现实的幻化。当他通过想象来建构这种“妖”的形象时,就已经预示了一种独特的飞翔美学。郭金牛的创作,虽然立足于对现实和工业化的批判,但他的诗性提升,更在于个人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也即是说,他的现实最终是要为文学服务的,而文学则又为他笔下的现实作了注脚,它们是相互的动力之源。
外省、工厂、金属,是郭金牛诗歌的关键词,它们不仅出现在标题中,也渗透在诗的字里行间。这或许正是郭金牛作为草根诗人的优势,靠主题取胜,可当转型成为一种过去式时,他的这种书写是否还有效?很多人对郭金牛写作的质问也由此而来。其实,以其多年的诗歌准备,他还不是到此为止,仅凭那些苦涩的爱情书写,他就依然“在路上”,我们当可对其抱有美好的期待。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