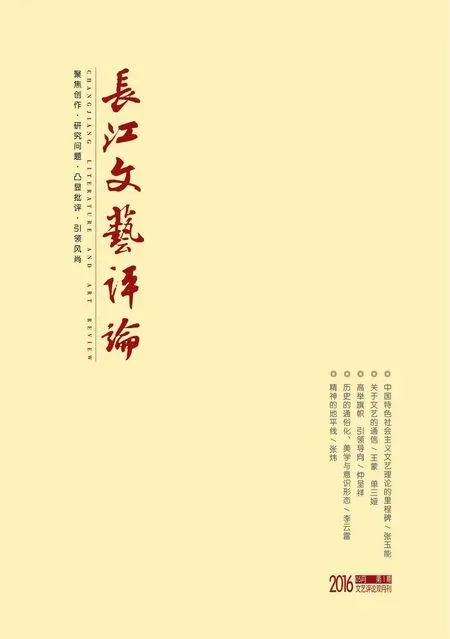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担当
2016-11-25◎徐刚
◎徐 刚
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担当
◎徐 刚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如其所言,“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无疑见出党对于文艺工作,尤其是文艺批评一贯的重视。在此情形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如何理解文学批评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批评基本功能和原则立场的反思,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此,本文着重讨论文学批评的原则、方法、可能性、价值立场以及批评的有效性和“及物性”等,进而深入探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的文艺工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
就文学批评的责任而言,首先当然在于阐释。众所周知,文学批评并不是一项神秘的活动,它只是更为高明的阅读而已。批评者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和文学话语,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更充分,也更具有说服力的探究与解释,进而抵达作品内在的玄妙。在这个基础上,批评家将阐释的结论分享给所在的社群,进而成为知识或价值接受、检验乃至争鸣的契机。这便是对文学批评责任的初步描述。对于批评者来说,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一种个体主义的“发现的愉悦”,更是对于广大群众的知识分享和意识形态统合。作为一种可供分享的知识,它与社群的关注及兴致所在息息相关,而非居于庙堂之上的圣物,亦非个人欣羡赏乐的玩物,因而它需要警惕自身的贵族化,荡涤其不可一世的傲慢、不知所云的文艺腔,以及自我陶醉的唯美情调。
与批评的阐释责任相伴随的是它的甄别功能。批评在其阐释的背后,内在包含着评论与判断,即对于作品的缺点与错误提出意见。在此,批评家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告诉大众什么是好的文学,好在哪里?帮助大众发现优秀作品的优秀之处,提高他们接受文学作品的素质,从而推动全民阅读水准和价值观念的提高。就像陈晓明教授在其《批评的责任》一文中所指出的,文学批评的根本责任和意义就在于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为了这个根本责任,批评者需要作出努力。毕竟,有没有能力去认识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发现优秀作品的关键。为此需要具有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学眼光,熟知传统文学经验和世界文学经验,以及容纳文学多样性的情怀,进而发现作品的创新潜质。[1]这也就像鲁迅所说的,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可如今许多文艺批评都存在“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的弊病,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比如“聪明”的批评家常常囿于某些利害关系,故意将批评理论化、复杂化,而逃避对小说的优劣做出判断。这也提醒我们反思批评的功能,重提批评为大众做筛选,评优劣的能力,这也就是有识者所呼吁的,“提升文学批评的大众化服务功能”的重要内涵。
为了更好地阐释与甄别,批评文风的重建亦显得至关重要。如人所指出的,当前文艺批评的最大问题在于,批评的学理性空前加强,但批评的现实感却极大弱化。其中的缘由与人们常常讨论的“学院派批评”不无关系。当然就“学院派批评”的表现而言,其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至的作品阐释力固然令人惊叹,但其方法与模式的铺排泛滥乃至走火入魔,又容易使之蜕变为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的书斋游戏,从而失去现实的针对性。因而批评有时会沉浸在单纯理论操练的欢悦之中,在纯粹阐释中迷失其批判性力量,而流于一种无效的分析。那些满腹经纶的批评家仿佛执意不愿与群众对话,他们的文章虽不乏某些哲学的、文化的、史学的高端知识,却唯独不愿痛快地告诉人们有关文学与社会的新鲜体验。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伊哈布·哈桑对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的批评,“他的文风完全可能是晦涩费解的、也许甚至是令人讨厌的”,而那些冷僻的“拜占庭式的贡戈拉主义”,实乃出于他们的“过于矫揉做作”。这种“矫揉造作”,实为某种极端自恋的文艺观念在批评中的投影,这归根结底是脱离群众的。这也难怪读者会在“看不下去”、“看不懂”的抱怨中,将这类批评指斥为“学者黑话”。因而批评文风的重建,也顺理成章地意味着追求一种清新平易的书写方式。
二
不同的人对于批评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或是基于某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寻找乐趣;或是基于个人化的阅读感受,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一种他人的生活,进而讲述自我的生存经验和人生启示。但也有人更为关注文学批评作为文化整体的功能意义。因而在笔者看来,批评在其阐释与甄别之外,更为重要的责任在于通过发现新的文艺现象,推介新的文艺作品,传达批评家与文艺工作者所共同获得的新的生存感受。
正像陈晓明教授指出的,文学批评的根本责任和意义就在于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而在什么标准的意义上来阐释、甄别和评判文艺作品,这背后便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杨庆祥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学批评的文化责任》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基于总体文化的要求,对于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理应有着更高的期待。他认为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作品评价,作品评价仅仅是它的一种形式,它更应是以专业的方式达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目的。
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批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批评的立场。确实,批评的有效性意欲完美呈现,势必要将文本的意涵与整个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但批评的结论又不能肆意发挥,倘若要使它靠得住,除了合理的批评尺度中始终恪守的学理和专业品格,还需积极寻求与多数人的利益、态度和情感结构的认同关系,建立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因而批评的责任中最重要的一点正在于批评的立场问题。这是从以上批评功能与批评文风两点衍生而来的最根本的问题。事实上,批评究竟站在谁的立场发言?是普通大众,基于人民和常识发言,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故作高深,抑或是站在资本的立场编织“文艺范儿”的“高级软文”,不同的批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其“引言”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种鲜明的立场意识,为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批评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确实,没有什么比立场更重要的了,因为批评家的思想、勇气、专业智慧乃至人格魅力,只有紧紧围绕他的立场,方能获得真正的效力,从而给人以启发。当然,也许“立场”这个词语又容易给人空泛的感觉,但在今天这个葛兰西所称的“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的时代精神状况中,恰切的立场所彰显的批评的力量,自会日益显出它存在的价值来。
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文学批评所指向的原则、方法、立场和意识形态背后,它也理应具有一个潜在的总体性,一个无论是具体的批评还是赞誉,无论何种方法的呈现,都理应包含的视野和背景。这也是新的文化塑造的题中之义。
最近有关“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毫不夸张地说,这也应该是近30年中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潮之中,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全盘西化成为彼时现代性追求的核心议题。一个全新的“现代视野”曾让国人欢呼雀跃,一时间新思潮的萌动与勃兴所带来的批评繁荣也令人津津乐道。然而,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中,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表征的文学形式开始显示出它的缺陷与流弊。在全新的反思与激辩中,“西化”与“中国道路”的价值选择逐渐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旅美学者张旭东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借讨论本雅明在80年代与90年代接受的不同,讨论批评实践所连带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而指出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的必要性。[2]他其后的许多工作也是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重新审视“中国道路”的积极性与紧迫性。冷战格局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多以欧美为师,然而他们终究在一种世界体系的狂热中失却了中国视野和中国立场。这不仅是对历史进行认知和判断,也是一个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当代中国实现了巨大跨越,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文化生态日趋丰富,就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类心灵,始终代表时代精神性价值的文学而言,无论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创作方式,还是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就像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而伟大的文学则需要刚健、有力、严肃的文学批评和深刻、准确、科学的文学理论。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均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文艺创作的空前活跃,当代文学主体理论的建设却严重滞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点问题的认识模糊,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滋生蔓延,这些都对文学创作和受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消极影响。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人民日报》联合中国社科院共同开设“文学观象”栏目,就当前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进行辨析、探讨,有的放矢地针对当代中国文坛存在的种种乱象,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以期正本清源、引导创作,推助当代文学繁荣健康发展,并由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最近中国社科院的张江教授相继推出多篇长文讨论“强制阐释”的话题,他就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理论的膜拜,以及理论的误用所造成的批评失效等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其目的在于致力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重建。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张江所主张的是回到中国的具体语境,回到批评的本土意识。[3]尽管张江的“强制阐释”的具体展开还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争议,但就其对于“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的追求而言,无疑也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再回到陈晓明教授的那篇《批评的责任》,我们不禁感叹,今天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力去面对当代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从文学的民族和本土经验,以及世界文学经验的多重视野看待中国文学的独特意义,这既是一种知识的选择,也是道义的承担,它孜孜以求的是当代文化的自我建构。毕竟批评的实践不是致力于一种轻率的自我诋毁,而是某种积极的文化建构。在此,批评不仅是一种基于知识的逻辑展开的文本阐释,也是基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世界意义的一种自觉的担当意识。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陈晓明:《批评的责任》,《人民日报》2015年5月22日。
[2]张旭东:《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读书》1998年第11期。
[3]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