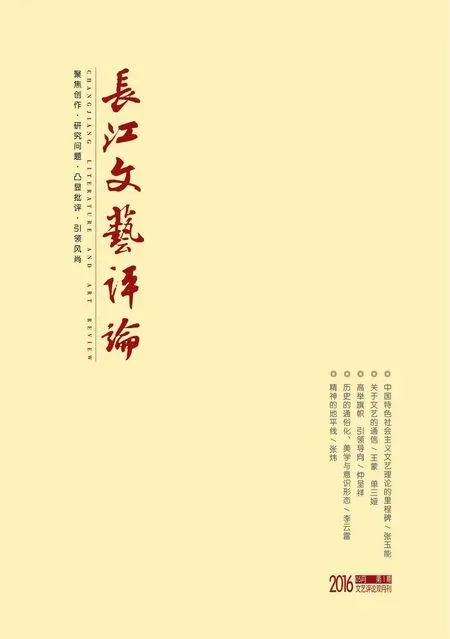历史的通俗化、美学与意识形态
——严歌苓小说批评
2016-11-25李云雷
◎ 李云雷
历史的通俗化、美学与意识形态
——严歌苓小说批评
◎ 李云雷
新世纪以来,严歌苓的小说受到了海内外评论家的高度赞誉,并被频繁搬上银幕,在文学界与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严歌苓的小说虽然文笔细腻,故事性强,但很难说是严肃意义上的文学,而更接近于通俗文学,或者说严歌苓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欢迎,并不是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或艺术的完美,而在于她以流畅自然的方式讲述故事,迎合了流行的社会意识,但她的小说却缺乏对流行意识的质疑与反思。在艺术上也是如此,严歌苓的叙述技巧娴熟,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她并不直面历史、现实或艺术上真正的难题,而是以其叙事技巧绕开需要面对的问题,放弃了写作上真正的难度。这表现在人物创造上,便是人物形象的类型化,而不是个性化或典型化;表现在题材处理上,便是历史的传奇化与现实的奇观化,而不是深入其内在逻辑并做出探索;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便是将时代的流行观念作为主题,而没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严歌苓小说的广泛流传,既可以看作她对当下文化环境的适应,也突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即在泛娱乐化与消费主义的语境中,严肃文学如何转化为了通俗小说,或者说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如何取代了认识启迪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的小说值得探究。
历史的“传奇化”
严歌苓的小说都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在《第九个寡妇》中,是土改之后王葡萄将公公藏入地窖二十几年的故事,在《金陵十三钗》中,是南京大屠杀时妓女拯救女学生的故事,在《小姨多鹤》中,是小姨多鹤和张俭、小环之间的复杂情感,在《陆犯焉识》中,是陆焉识与冯婉喻跨越数十年的苦难爱情。不过严歌苓的故事虽然流畅好读,但却在历史与经验叙述上有明显的问题。譬如,在《小姨多鹤》中,我们看到小姨多鹤在与张俭、小环生活了十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保留着日本人的语音,在1950年代的中国工厂没有受到盘查与质疑,作者显然没有充分进入当时的语境。另一个例子是《陆犯焉识》,我们可以对这部小说做一下详细分析。
《陆犯焉识》的主人公陆焉识出生于上海一户大家庭,在继母的安排下娶了她的娘家侄女冯婉喻,但他对她并没有感情,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读了几年书。毕业回国后,陆焉识在大学教书。在1950年代,他因其出身与不谙世事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在西北大荒漠上改造了二十年。在劳改时,他萌发了对冯婉喻的爱意与思念,开始在心中默写给她的信件,并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逃出荒漠,到上海的家中去看她,但又被抓回。直到“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但苦苦等他归来的冯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两个人跨越数十年的情感故事,写的缠绵悱恻、荡气回肠,令不少读者颇为感动。但在感动之余,我们却发现这部小说除了一个情感故事之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那段历史的新的言说,或者说作者只是将一个言情故事放置在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而并没有深入那段历史内在的复杂纠结之处,相反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简化了历史的丰富性,或者说对历史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
对于《陆犯焉识》中所描述的那段历史以及劳动改造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1980年代伴随着右派知识分子平反及其“归来”,描述右派及其劳动改造的小说在文学界大量涌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等小说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作品描述知识分子的受难、劳改的悲惨遭遇,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及其精神蜕变,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不无值得反思之处,比如相对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中国作家并未将个人与民族的苦难经验,转化为对时代、历史与体制更为深刻的思考,比如相对于历史学家张光直的思考,中国的右派作家更偏重于个人经验与苦难的倾诉,而缺乏超越性思考与开阔的历史眼光。
不过即使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相比,《陆犯焉识》也显得缺乏丰富性、复杂性。在《陆犯焉识》中,我们看到作者只是描述了陆焉识在劳改中的苦难及其情感寄托,而没有涉及其他更丰富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如将陆焉识与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相比,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中,张贤亮试图“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的全过程。在“苦难的历程”中,作者描述了章永璘内在的挣扎与痛苦,这既包括生理上的压抑,也包括内心中忠诚与背叛、信仰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但在《陆犯焉识》中,苦难只是成为了一种背景,一种隔离开男女主人公的障碍,而并没有深入主人公的肌体与内心,也没有参与主人公的人格与性格的塑造。如果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叙述中有很多毛刺,而《陆犯焉识》的叙述则是光滑的,但正是在那些“毛刺”中,却隐藏着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也隐藏着历史中深重的苦难。《陆犯焉识》叙述的光滑流畅,恰恰避开了对历史以及历史中个人的思考,只是将苦难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体制,也就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片面否定。小说在结尾处有一个细节交待,“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小说中这样为冯婉喻辩护,“一个女人拿出什么去营救自己爱人的性命都不为过;一个母亲使出什么手段来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都无罪。”这个情节既增强了两人情感故事的波折与苦难,也对当时领导运动的人做了丑化与否定。在这里,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或许没有必要,但即使仅从叙述方式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情节并没有超出1980年代苦难叙述的成规,即将历史的苦难归咎于掌权者的个人欲望,在这个意义上,《陆犯焉识》并没有新的创见,只不过是将1980年代的创新编织进了她的叙述之中。
人物的“扁平化”
严歌苓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有鲜明的性格,也不是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类型化的人物,她所擅长写的是“圣母”或者“妓女”,这两类人物形象也是女性主义研究中众所周知的女性类型。在严歌苓所描写的“圣母”型女性中,作者没有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小说主人公的执拗、坚持与执著,大多被归因于性格上的“一根筋”,而没有内在的逻辑与原因。在《第九个寡妇》中,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在小说中,王葡萄的“一根筋”的性格是推动故事的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思想与历史内涵,显然这些“一根筋”式的人物并非来自于生活,而是来自于作家的主观意念,或者说作者并没有想理解其内在复杂性,而这则导致了人物形象的单薄与浅白。不仅《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一个扁平化的人物,在《小姨多鹤》中,一触及到现实的危机,小姨多鹤都会显现出一种“呆气”,而在《陆犯焉识》中,冯婉喻则患了“失忆症”,可以说无论一根筋、还是呆气与失忆症,都是作家的一种回避,她无法写出笔下人物的丰富性,只能将之抽象化。我们可以说,将一个抽象化的人物置于极致的环境中,讲述一个传奇故事,这就是严歌苓小说的叙述模式。
在《第九个寡妇》中,不仅王葡萄是抽象化的人物,她的公公孙怀清也是抽象化的人物,在小说中,孙怀清这个地主形象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品涉及到土改这一段历史,比如《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我们可以将《第九个寡妇》与这些作品做一下比较,《第九个寡妇》中的地主孙怀清集各种美德于一身,《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则对地主持批判的态度,这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想象有关,我们姑且不论。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除了地主与合作化的领路人如梁生宝、萧长春之外,还有大量的“中间人物”,这些中间人物中有积极分子,有落后群众,也有各种性格不同的乡村人物,正是这些中间人物展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描述了乡村变革的艰难曲折,构成了一幅幅乡村的风俗画。但在《第九个寡妇》中,我们却看不到中间人物,也看不到丰富的乡村画面,我们看到的只是抽象出来的人物,因而难免是苍白的、扁平的。
严歌苓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将妓女“圣女”化,在《金陵十三钗》《扶桑》中,我们看到的是妓女,但她却将之作为“圣女”来写,这虽然颇具戏剧化的效果,但也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以《金陵十三钗》为例,小说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中关注一群妓女的命运,题材较小,也不无轻佻轻浮之嫌,缺乏对南京大屠杀应有的敬重与反思,而作家将妓女与女学生的命运简单对立起来,也禁不住读者的质疑:小说对这一故事的津津乐道,其实仍然是建立在对妓女身份的歧视之上,作为社会底层的群体,妓女就比女学生更应该牺牲吗?小说中故事的张力来自于不同人物身份的差异,但作者并无意深入历史的内部。《扶桑》中也是如此,“她虽然是妓女,但在她身上从来没有妓女常有的贱、嗲、刁、媚和那种以灵肉作生意的贪婪,她是一个原始的嚣张的自由体,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社会和世俗给予的概念和符号,她没洗过脑,只是一个最低的原初的生命形式,一个淳朴又纯粹的雌性体……”,在这里,作家自认为没有任何“概念和符号”,小说中“她”恰恰被抽去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只留下“纯洁的妓女”这样一个内在矛盾的符号。在文学史上,描写妓女的作品有很多,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日出》、莫泊桑的《羊脂球》、小仲马的《茶花女》,这些小说中的妓女无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以《羊脂球》为例,小说将这样一个妓女形象置于普法战争的背景下,通过她的选择以及别人对她态度的变化,在众人的伪善中反衬出羊脂球的牺牲,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但在《扶桑》中,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个妓女与一个白人间的情感与欲望的故事。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试图写出人性的暧昧、幽暗之处,但这种“人性”在被抽象化之后,便似乎只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她早期的《白蛇》《扶桑》《天浴》,还是新世纪以来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老师好美》等,性都成为故事的核心要素,这是严歌苓进入历史的视角,也是她的小说引人关注之处,但以抽象的人性进入具体的历史,在极致的情境下编织两性的故事,却让她既远离了人物,也远离了历史,小说中呈现出来的便只是扁平的人物,只是主观的抽象世界。
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严歌苓小说中很少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并非没有意识形态,而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具体说来,她是用1980年代的流行观念来反对1950至1970年代的流行观念,而缺乏自己独到的观察与思考,而这些流行观念,反过来限制了她小说的艺术想象与艺术呈现。
《第九个寡妇》对1950至1970年代的历史进行了重述,也对以往的历史观做了颠覆,在这个小说的视野中,这一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地主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作者同情的对象是“地主”孙怀清和“落后群众”王葡萄,而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中,这些恰恰是被批判、争取的对象,这些作品用大量篇幅赞扬的是农村中的“新人”,在梁生宝、萧长春等人身上寄予了农村的希望。《第九个寡妇》可以说反映了严歌苓对“合作化”的认识,但与其说是她的认识,不如说是1980年代的“常识”。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承包”的实行,否定合作化、赞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一种潮流,也成了1980年代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严歌苓的想象也没有超出其外。
但实际上,“土地承包”并非是对“合作化”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合作化的继承与改造。土地承包与“单干”所坚持的土地私有化不同,是建立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而土地的集体所有正是“合作化”的重要成果,它打破了小农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同时土地的定期调整,也为避免贫富分化、保持社会安定提供了保障。在此情况下,对“合作化”的简单否定,是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的。新时期以来对《创业史》等作品的主流意见,是认为它们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但即使如此,透过这一限制,我们仍能看到当时农村中不同阶层的心态和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人们也普遍认为“新时期”以后的作品更加自由、多元,更加艺术化。但是从《第九个寡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样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只不过不同的是,已经到了新世纪,它受到的还是19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如果说《白毛女》讲的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故事,那么《第九个寡妇》则可以说讲的是“革命使人变成鬼,改革使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这里的两种“人”是并不相同的,《白毛女》里的是喜儿、大春、杨白劳这样贫苦农民;而在《第九个寡妇》中,指的则是“地主”孙怀清,在小说中,他重复了喜儿由鬼变人的命运,而王葡萄作为另一个意义上的喜儿(被地主家收养、欺凌的童养媳),反过来拯救了他,这使小说在多重意义上对《白毛女》构成了反讽与解构。无论是《白毛女》中的山洞,还是《第九个寡妇》中的地窖,相对于现实世界,都是另外一种空间,这一空间也是对现实世界批判、反思的空间,或者说这一空间为现实或历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里,对“可能性”的想象是对作家艺术能力的一种考验。在《白毛女》中,想象与呼唤的是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第九个寡妇》所想象的,则是在1980年代已经实现了的具体政策,其艺术的创造力显然不能与《白毛女》相提并论。如果我们将眼光拓展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沃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等影片中,也都开拓了另外一个空间,《地下》的空间是与南斯拉夫历史平行的一种地下生活,《再见,列宁》则在虚构中展现了历史走向的另外一种可能,其历史感与想象力也都是《第九个寡妇》无法比拟的。
不仅《第九个寡妇》,在《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天浴》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作者在演绎流行的社会观念,或者说她无法突破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借助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批判旧的意识形态,而这既彰显了批判的“勇气”,又有政治正确的“安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两全其美”的,但其中唯独少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艺术家的创造性。严歌苓曾说,“作为女人我不是一个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只是我所写的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话虽这样说,但在她的小说中却隐含着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偏见,而这深深制约了她的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
严歌苓小说的故事、人物与意识形态性已如上述,但我们并非要对其小说简单否定,而是对其性质与价值要重新认识,作为通俗文学,严歌苓的小说流畅好读,受到市场的欢迎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我们将之作为严肃文学来对待,势必对之有更高的要求与期待。
李云雷:《文艺报》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