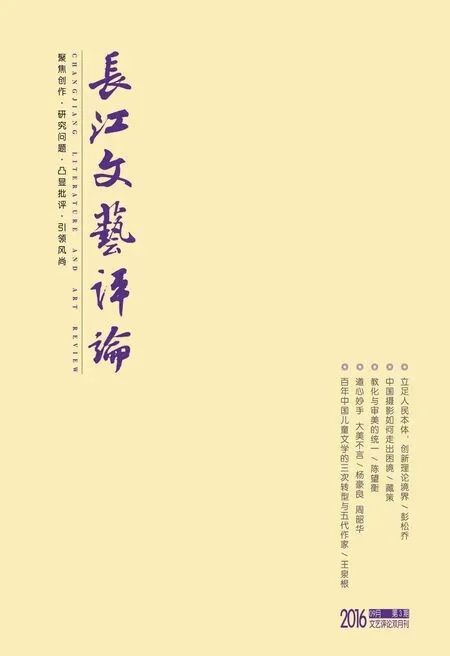重建“世界的镜子”
——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的启示与意义
2016-11-25鲁太光
◎鲁太光
重建“世界的镜子”
——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的启示与意义
◎鲁太光
一
……红花草的花是粉红色的,一串串,像葡萄似的,开得最旺时比朝霞还要灿烂,比火焰还要璀璨。在庄稼人眼里,红花草可真是宝物,既能做绿肥,又能喂牛喂猪,而且看着千娇百媚的,十分养眼……[1]
说起来,似乎连自己都无法相信,刘继明耗费多年心血推出的长达五十余万言的长篇新作《人境》首先抓住我的,竟然是这样一段关于花草的细节描写。
粗略阅读的话,发现这段描写实在没什么奇异之处,作家不过是以极其朴素、写实的手法,把湖北平原上一种过去常见、当下鲜见,但却又出现了的花草——红花草——呈现在了我们眼前,或者说,作家在这里只是画了一幅画——一幅南方村野图,一幅南方村野中的花草图。但细细阅读,尤其是结合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状阅读,却又发现这段文字不仅不那么一般,反而有些新奇乃至脱俗了。的确,说得严重点儿,在新世纪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是不是伪现代主义或伪后现代主义,还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写作语境中,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些平实而有益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不用说那些心目中除了自己再无他人、他物的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就是那些自诩现实主义的作家,似乎也丧失了描写的能力。因而,在海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读不到像样的描写,看不到动人的风景,我们读到的往往是小说人物——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作家自己——的自我怨艾,自我得意,自我迷失,即使偶尔读到一点儿所谓的风景或描写,也往往“抽象”得一塌糊涂。比如,一写花开就是“各种颜色的花都开了”,一写鸟鸣就是“所有的鸟儿都叫了”,一写群体性场景就是“无数的人”……在这样的“抽象”中,作家好像把各种花都端到了我们眼前,让所有鸟儿都飞到了我们耳边,把无数的人都送到了我们身边,然而遗憾的是,在“各种”、“所有”和“无数”面前,我们却看不到花开,听不到鸟鸣,看不到人物。这里有“所有”,这里有“一切”,可这里又“一无所有”。
这就是我看到《人境》中的红花草——多么具体的一种花草呀——后赞赏不已的原因之一。是的,对那些絮絮叨叨的内心,对那些抽象的所谓描写,我已经审美疲劳了。或者说,我早就在期待这样一种精确、及物的描写,早就在期待这样一幅具体、朴素的风景了。实际上,这湖北平原上“大片大片像云霞一样绚丽的红花草”之所以让笔者惊喜,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消失已久的文学空间的失而复得。与新世纪以来诸多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多是单向度、扁平化的空间不同,《人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空间。其最为直接的表征,就是在小说中久已不彰的“环境”又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出现了。
依笔者之见,“环境”借着《人境》的回归,对当下文学的发展,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自1980年代中期以降逐渐流行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潮流中,由于作家宣称只对内心负责,只对人性负责,甚至宣称只对感觉负责,只对欲望负责,因而“向内转”成为最为重要的文学方向,心理描写成为主要的文学手法,致使外部世界——环境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要素——备受冷落。客观地说,“向内转”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维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相当心理深度的作品,但问题是,长期不加反思的“向内转”,却使我们忘记了文学既是作家心灵的“自转”,亦是外部世界的“公转”,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则往往是作家心灵“自转”与外部世界“公转”屡经摩擦、碰撞之后完美契合的产物。这就是说,在长期的心灵“自转”中,我们的作家往往沉溺于自我感觉世界,而忘记了没有外部世界的碰撞,心灵“自转”必将缺乏充足、长久的动力,忘记了外部世界也是展现人、人心、人性的重要舞台,忘记了“环境”是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是人心得以展开的重要空间。
关于这一点,我们上文提到的关于红花草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站在唐草儿的立场上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云霞般绚烂的红花草映衬出的美丽的田园风光,如果没有马垃和同心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同心协力营造出的“希望的田野”,没有马垃和小拐儿这一个独身男人和一个孤儿共同营造出的简单却幸福的家的氛围,那么很难想象,这个为浮华、功利的都市文化所浸染而变得颓废、放荡的蛋白质女孩会实现心灵与人生的双重逆转,会由一个只知憎恨、索取的绝望的吸毒女转变为一个芙蓉般清丽,感恩、奉献的少儿音乐培训学校负责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美丽的红花草开启了唐草儿的转型心路。
这告诉我们,伴随着现实的文学空间的修复,我们的情感也将得以修复。
关于这一点,小说对大林、小林的描写,有着更为精彩的呈现。
二
一天早上,当马垃正在外滩上桃园里给那些被洪水泡得半死不活的猕猴桃树培土时,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吱吱声。他猛一回头,看见两只小刺猬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眼一亮,认出是大林和小林,失踪了这么久,他以为它们早就被洪水淹死了,此刻一见它们尖尖的小嘴和滴溜溜的小眼珠,他的心头一热,蹲下身,一下子把它们抱进了怀里。[2]
即使不看小说全文,只看引用的部分,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一段中,作家比描写红花草那一段时投射了更多的情感。或者说,通过这一段,我们看到,随着小说空间的不断展开,小说的情感也愈益丰富。不过,这一切,都要从大林、小林这一对不速之客的由来及遭际说起。
在神皇洲安定下来后,马垃在荒凉的外滩栽起了一片猕猴桃园,整整三年之后,猕猴桃树终于挂了果,“初夏时节,每次看到才指甲大小的幼桃在枝头颤颤悠悠地晃动,仿佛襁褓中熟睡的婴儿的脸蛋,马垃就会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为了照料这些可爱的“孩子”,马垃和他收留的孤儿小拐儿晚上轮流值班,看护桃园。一天晚上,轮到小拐儿值班,快半夜时,半睡半醒间,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小拐儿四处寻找,什么也没有。第二天晚上,在马垃带领下,我们和小拐儿才洞悉了事情的真相:
这天夜里,马垃跟小拐儿一起留在桃园里。快半夜时,又响起了咳嗽声。马垃对小拐儿使了个眼色,拿起手电筒,小拐儿也操起了铁锹,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桃园。
在一棵猕猴桃树下,马垃把手电筒的光对准了树根下一团毛茸茸的东西。起初,小拐儿还以为是一堆杂草,可手电筒的光照了没多会儿,那堆杂草竟然动了起来,然后弹出一张粉红色的小脸,一双绿豆般大小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张开肉乎乎的嘴巴,发出的声音跟小拐儿听到的咳嗽声一模一样![4]
粉红色的小脸,滴溜溜的眼睛,肉乎乎的嘴巴……多么生动的描写,多么迷人的场景。读到这里,我们一定会跟小拐儿一样,发出惊讶的叫声:“刺猬!原来是这个小家伙在咳嗽呀!”
由此,这两只小刺猬就在桃园住下来,成了马垃和小拐儿组建的这个略显单调的家庭的一员,后来,又被命名为大林、小林,不仅使马垃和小拐儿组建的这个家不再单调,反而充满乐趣,并进一步成为桃园的“形象大使”,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都体验到难言的童趣。而当神皇洲在天灾人祸的合力之下被洪水淹没,村民四散,就连同心农业合作社的成员也不得不接受政府安置,离神皇洲而去,只有马垃一个人,孤独地固守在神皇洲,孤独地固守在猕猴桃园,孤独地固守在为洪水所洗劫的家中,就在这个时候,消失已久的大林、小林竟悄然出现,又回到了神皇洲,回到了猕猴桃园,回到了马垃身边……
我们还看到,小拐儿是在大林、小林之后回到马垃身边的。这样的安排,这样的组合,这样的场景,既苍凉,又温暖,格外的意味深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说中关于刺猬——还是叫它们大林、小林吧——的几次生动描写,进一步修复了小说的空间,也进一步修复了我们的情感。行文至此,笔者想说一句也许并非多余的话,即现在流行类型小说,其中的一种是环保小说,我自然支持这种对环境充满善意和敬意的小说,但实际上,从文学的根本意义上看,如果我们能够在小说中写活一株花草,写活一种动物,写活一片风景,写活一类环境,就像刘继明在《人境》中所做的那样,也许比写几部所谓的环境小说还要有价值,因为,这种在文学作品中活起来的花鸟虫鱼,相应的,还有活起来的物与人,比单纯的类型文学作用也许要大得多。不过,这也是因为在环境文学方面,我们还雷声大雨滴小,缺乏好作品。
当然,《人境》中关于大林、小林的描写,作用绝非如此简单。
如果细细品读相关描写,我们会发现,正是大林、小林使小说中几位相关人物的情感渐次丰满起来:首先是小拐儿,由于父母早逝,这个早早为苦难所捕获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童年,即使马垃收留他,但他在马垃那里所体会、学习到的,也多是严肃的生存之道,而少有童趣,恰恰是大林、小林的适时出现,激活了他儿童的眼光和心灵,因而也给了他童年的乐趣和幸福——这么一想,大林、小林刚出场时让他虚惊一场的咳嗽声,是多么有益的童年经历呀。对马垃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纵览全书,我们发现马垃的生活基本上是沉重的、严肃的、枯寂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独特的时代及家庭原因,他几乎在童年时期就步入了成年人的世界,而步入成年人的世界后,他所经历的,是更为沉重、严肃的人生课题,这沉重压得他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他努力挣扎着想“成长”,想“成熟”——换个角度看,他是多么想幼稚、天真一回呀。正是大林、小林的出现,适当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想一想,连大林、小林的名字都是马垃从童话中找来的呢。当然,大林、小林之于马垃的意义还更为丰富,更为多元——除了童趣,它们还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当。因为,马垃与大林和小林之间的情感是一种更为宽广的情感,只有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之上,马垃与小拐儿、唐草儿、神皇洲父老乡亲们之间的故事,才显得更加真实,更加饱满。而大林、小林在洪水后的适时归来,则进一步温暖了马垃,坚定了马垃,使他在沉思、寻找的路上,走得更为执着、从容。还有唐草儿,我们上文已经说过红花草对于她的意义,其实,大林、小林对于她的意义,绝不逊于红花草,要不,她不会在听小拐儿讲完马垃与大林、小林的故事后感叹:“这本身就是一篇童话。”实际上,她本人就是为马垃、小拐儿、红花草、大林、小林所共同建构的这则“童话”所吸引,才一步步迷途知返、返璞归真的——这是另一个“童话”……
在这样的“童话”面前,我们的情感能不丰满吗?
不过,这情感还要在社会空间的修复中得以丰润。
三
望着鹿鹿近在咫尺,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那张稚气未脱、隐约还有几粒细小青春痘的脸,甚至看得清脸上淡淡的绒毛,慕容秋觉得,女儿像一片漂浮不定的云朵那样,离自己越来越远。看来,女儿真的长大了……
鹿鹿听到了慕容秋那一声轻微的叹息。她悄悄地抬起脸,正巧同一双正在凝视自己的目光相遇,这是典型的只有母亲才有的目光,其中隐含着某种难以察觉的忧伤,鹿鹿捕捉到了,而且还发现,妈妈那一般女性少有的宽阔的额头上,呈现出几条深深的皱纹,像是刚刚被铧犁耕过,或者用雕刻刀镂刻下的,而在这之前,鹿鹿印象中妈妈的额头一直是那么光洁、平坦,几乎像年轻人那样圆润的。一种隐隐的不安和内疚袭上鹿鹿的心头,她情不自禁地再次叫道:“妈……”[5]
这是怎样的两张脸呀!或者说,在这两张脸上,写着多么丰富的信息呀!然而他没有充当脸的阐释者——就像我们的许多“现代”作家所做的那样,而只是运用敏感、细腻的笔触,把这两张意蕴丰富的脸,把这两张脸上每一个意味复杂的表情,甚至连那一声轻微而又深长的叹息,都给我们“画”了下来。
作家这是把阐释权交给了我们,因而,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解码。实际上,慕容秋是《人境》下部中最为核心的人物之一,作家之所以在小说中设置这么一个人物,除了以隐秘的方式呼应小说上部,并且与马垃等人物一起思考、求索并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外,其更直接的作用,是引领我们进入都市空间,使我们观察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都市社会天翻地覆而又无微不至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是想借助慕容秋知识分子这一在新时期以来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使我们看到在知识界展开的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化的不同认识与明暗争斗。就个体而言,知识分子或许并不那么突出,然而,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社会人格来看,则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权力、资本、知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铁三角的当下,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在中国知识界上演的知识的“戏剧”,往往是在为中国社会变化书写“脚本”,或者是对即将到来的变化进行“预演”,因而,对这一群体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演变。遗憾的是,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却被“忽视”了,不是被写“小”了——作家往往将知识分子臆想成像自己一样的无能的个人主义者,除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再无其他关切,就是被写“轻”了——在一些小说中,知识分子除了一副沉重的皮囊,除了声色之乱,除了职称、课题之争,再无其他抱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作家自我臆测的结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刘继明在《人境》中塑造了慕容秋、何为、旷西北等一群不一样的知识分子,就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发展——至少从钱锺书的《围城》开始,我们就很少看到过像样的知识分子了。更何况,作家还是在一个别开生面的维度上向我们敞开“他们”的世界的呢。
这个别开生面的维度,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两张脸,尤其是慕容秋的脸,也就是说,作家是通过对慕容秋情感之路的勾勒与描摹,来敞开她自己以及何为、旷西北等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从而拉开知识界明暗争论的帷幕的,并最终拉开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大幕。这样,作家就在内外、轻重、远近之间,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果不是借助鹿鹿这双“女儿”的眼睛,我们几乎无法看到慕容秋脸上那深刻的“皱纹”,无法看到这张脸上那“难以察觉的忧伤”,无法看到刻写在这张脸上及其心上的“伤痕”,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候,她让我们看到的,多是端庄、安静、内敛、犀利的知性本色。幸运的是,作家借给我们一双“女儿”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了原本无法看到的内容——慕容秋的情感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而又难言啊:因为辜朝阳的始乱终弃,离异后的慕容秋未曾再婚,始终与女儿相依为命,在这过程中,随着情感的延宕,岁月飞逝,容颜渐老,她不仅成为老父亲的牵挂,也成为女儿的“内疚”与“不安”。而且,尴尬的事情接踵而来,比如被中学同学潘小苹当作礼物介绍给“老干部”,比如被当年的小岳、眼前的搭档、即将的“上司”老岳盯上,被倾诉,被求爱,想想老岳烂絮般破败的情感生活及其扭曲的心理,慕容秋的尴尬与不堪,可谓一言难尽。然而,让慕容秋难堪、难言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她的情感空间之所以越来越逼仄,越来越晦暗,除了个人的原因外,似乎还有时代的捉弄,或者说,因为她随着时代顺流而下,才导致了眼前的这种尴尬局面——前进不得,后退不成。关于这一点,慕容秋自己的反思颇为有力:“她曾经为之怦然心动、热血澎湃的爱情,也随着一个人的意外殒命和一个时代的悄然落幕无疾而终。多年来,她之所以一直单身,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已失去了爱的能力和勇气。”[6]
是的,这一切,既是个人的不堪,也是时代的不堪,更是个人背弃青春、理想、时代的不堪。我们看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慕容秋不仅逐渐修复自己的人生与情感,似乎也在逐渐修复时光与时代。这是她放弃本能的母爱,同意甚至鼓励女儿鹿鹿在大学名校毕业后放弃出国机会和稳定工作,而与旷西北一起“自主创业”创办“民生网”的原因,是她同意女儿鹿鹿与旷西北之间的“师生恋”,并鼓励他们深入民间,用双脚丈量大地、寻路中国的原因。因为,在女儿的选择中,她依稀看到了自己的青春,看到了自己的理想。所以,慕容秋的作为,既是一种超越性的母爱,更是一种自我救赎,自我修复。更为感人的是,我们在小说结尾,看到她终于冲破这种蛛网般的囚禁,再次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现实世界:“不能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继续待下去了。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下个学期就带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7]自新时期以来,我们就谈人性,以人性为文学的旨归。如果说,这口号在新时期还有一定的适用性、解放性的话,那么,从文学实践看,在新世纪,这口号连文学的遮羞布都算不上了——我们有那么多号称写人性的作家,有那么多号称写人性的小说,可在我看来,所有那些停留口头上和字面上的人性总和,也不如写在慕容秋脸上的人性内涵丰富、生动、深刻,因为,归根到底,离开了对现实的深刻认知与深度提炼,一切的人性,都将无所附丽,都将无所体现。
四
慕容秋站在岸边的一道土坎子上,向江上望去,只见宽阔的江面上,有个人正朝着江中心游过去。水流得很急,加之刚驶过一艘轮船,波涛起伏,一浪高过一浪,那个人在波峰波谷之间忽隐忽现,仿佛随时都会被吞没似的。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晖把江面映照得一片火红,那个人仿佛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划开一道道激流,顽强地朝江中心的沙滩移动,越来越近。[8]
随着慕容秋等小说人物的情感河流逐渐得以修复、展拓、流畅,小说更加本质的力量也渐次凸显出来:在这汩汩流淌的情感的河流之下,是思想澎湃激流。在这激流的推动下,不仅失落的文学空间得以修复,在文学中几近消失的时间也如江流一般,一下子包围了我们,簇拥了我们。在这样的包围和簇拥中,我们看到两个时段的中国——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在激烈的冲突、碰撞和交流中,向着我们展开,向着我们展开各自的面容与襟怀。
小说中关于革命中国的叙述,主要集中在马坷身上。作家处理得相当巧妙,他没有径直跳入历史的江河,直陈革命中国的故事,而主要是通过马垃、慕容秋、大碗伯等人的回忆,生成一双“回望”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马坷这位革命青年的成长与夭折,从而以之隐喻革命中国的成长与夭折。毋庸讳言,由于痛感新时期以来对革命中国的“伤痕叙事”过甚,以至于使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忘记了革命中国的初心,因而,作家在这马坷身上,从而在革命中国身上倾注了充沛的情感,始终以一种青春、理想、礼赞、缅怀的眼光观照他,因而,几乎没有触及革命中国的困顿与挫折,但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较好地平衡了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使革命中国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首次以端正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通过马坷,这位不乏清教色彩的革命青年的生命历程,暗示了革命中国在展开自己理想时所面对的艰难处境,而他的突然陨落,则使我们意识到,虽然那个时代的帷幕已经拉上了,但其遗产,其青春的理想却不能被遗忘,甚至被背叛。而这,为时光对接留下了空间。
关于改革中国的叙述,则主要集中在逯永嘉身上。关于这位改革的化身,作家似乎较多批判意识。但实际上,如果深入文本内部,我们会发现,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作家虽然不无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剖析的意识,可骨子里,却又无法不对逯永嘉这个人物,从而对改革时代的中国投入充足的认同与敬意,或者说,作家对改革中国的反思是建立在足够的认同与肯定上的。这也是作家与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由于缺乏反思能力,许多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将对时代的认同变成了无原则的自我爱恋。实际上,就是在对逯永嘉放荡的个人生活进行“批判”时,作家不也恰恰是在“赞美”他吗?他那被夸张了的生殖器,除了是欲望,是贪婪,是劫掠,不也是生命力,不也是浪漫精神,不也是“文学性”吗?更不用说,作家还直接描写他在市场大潮中的英雄本色,而他那“资本这头烈马总需要人驾驭”的感慨即使在今天听来,也依然振聋发聩。更何况,他的改革、他的创业,还包含着更多的雄心壮志。创业前,他和马垃在河口镇中学那间简陋的宿舍中的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马垃说:“逯老师,也许我们将来都能成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呢!”
“企业家?”逯老师突然从床那头霍地坐起来,鼻子哼了一下,“你要记住,当企业家只是我们事业的第一步。等赚到足够的钱,我们就去购买一座海岛,在全国,不,在世界招募一千名男女青年来岛上生活。我想好了,这座岛的名字就叫‘理想国’。岛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享受教育、住房和医疗,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生活。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既不受国家的限制,也没有家庭的约束,就像摩尔在《无有乡消息》中描写的那样……”[9]
是的,逯永嘉之所以背水一战,投身商海,是因为他心中还有理想,还有“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除了物质的富足,还有自由、平等,还有民主、文明。一言以蔽之,还有来自“乌有乡”的“消息”。而这,恰恰是他最打动马垃的地方。如果联系到当时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流话语,我们就会认识到,改革在其开端其实是有其远大理想的,这种理想,在某个维度上与革命中国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关于革命中国,不管是其批评者还是肯定者,一个共用的关键词不就是其乌托邦/理想国属性吗?说到底,无论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于民众而言,都无异于一种“社会契约”,即不仅要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而且还要实现民众的自由、平等、幸福。正是这种“社会契约”将革命中国与改革中国联系在一起,尽管其内涵不乏差异。从这个角度看,革命中国之所以在新时期遭到改革中国的反思与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对这种“社会契约”的背离,而改革中国之所以在当下又遭到革命中国回光式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其“理想国”本质和“社会契约”精神。关于这一点,逯永嘉和马垃开创的鲲鹏公司的发迹及其堕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而这,才是马垃重回神皇洲的意义所在。没有这种归来,就没有对这两个时段中国的系统观照,没有这种系统观照,就没有未来。这也是马垃陷入长期困顿的原因,是他虽然已经老大不小了,在神皇洲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却始终觉得自己没有“长大”,没有走出两位“兄长”、“导师”——马坷和逯永嘉——的阴影的原因,是马坷和逯永嘉在他心中不时辩论、争吵的原因——他需要时间和空间消化这种激烈的辩论和争吵,也就是说,他需要时间和空间消化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留下的遗产。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他已逐渐将这两个时段的中国留下的遗产较好地结合了起来,或者说,他既能很好地运用他在市场经济中练就的驾驭资本这匹野马的能力,带领神皇洲老弱病贫的乡亲建立同心农业合作社,就是这初心的初步展现。最后,在慕容秋的引导和启示下,他终于克服了根植内心已久的那种莫名却又真切的“羞耻感”:“马垃的心中像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暖流,原本沉重的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仿佛整个儿脱胎换骨了一般,他似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10]
“一个全新的人”。对,马垃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他是作家依据历史和现实提炼、升华、创造出来的一种理想人格,一种未来人格。通过这种理想人格、未来人格,作家不仅很好地串联起断裂的历史,而且还有力地为我们敞开了面向未来的空间。这是作家的又一贡献。
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人境》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不一样的文学形象,比如慕容秋、何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比如辜朝阳这种“野心勃勃而又精明透顶”的以本民族敌人面目而出现的新买办形象,比如丁友鹏这样的小官僚形象,比如谷雨这样的新农民形象,但毫无疑问,《人境》中最重要的文学形象是马垃,因为他既是对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进行综合的产物,更是对未来进行敞开的需要。围绕着他,旷西北、鹿鹿等新一代人——为未来所需要的“全新的人”,也呼之欲出。
这种“全新的人”的出现,对当下的中国文学而言,意义重大。
1908年,在《个性的毁灭》中,高尔基对俄国知识界和文学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现代的文学家是不是关心祖国的前途,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社会问题不能刺激他的创作了,诗人变成平庸的文学家。从天才概括的高处滑到了生活琐事的平面。只在日常事件中间摸索着。形式越来越单调,字眼越来越冷淡,内容越来越贫乏。真挚的感情熄灭了,激情没有了,作家已经不是世界的镜子,而是抛在街头的灰尘中的一小片碎玻璃,它无法用它的破面去反映出世界的伟大生活,只能反映出庸俗生活的片段,反映出受损害的灵魂的小碎片。”[11]现在看,高尔基的话,好像是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量身定做的,是那么的犀利,那么的准确,那么的发人深省。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就是沉溺于遍地的埃尘与碎玻璃中,丧失了激情,毁灭了个性。然而,凭借着现实主义的整体文学观,凭借着强大的思想力,凭借着蓬勃的责任感,当然,也凭借着精心的构思,精细的描写,凭借着马垃、鹿鹿、旷西北等“全新的人”,刘继明在遍地埃尘与玻璃碎屑中,为我们树立起一面巨大的镜子,让我们再次看到时间,看到空间,看到在时空交织中生长的万物,看到在时空型构的舞台上活动着的人、人们,以及他们跃动着的心,从而再次看到文学的个性,人的个性,甚至中国的个性。而这使《人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尤其是当下流行的“纯文学”,使自己获得了更宽阔的意义空间。
或许,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修复。
或许,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开始。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
注释:
[1][2][3][4][5][6][7][8][9][10][11]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32页,296页,211页,213页,305页,400页,476页,21页,478页。
[12]【苏】高尔基:《个性的毁灭》,转引自《林默涵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