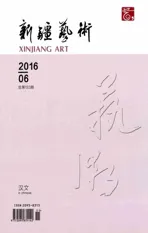守护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家园
——评黎羌新著《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
2016-11-21郭英杰
□ 郭英杰

“守护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家园”本来是黎羌教授的新著《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后记”中的标题,笔者读后特别喜欢,就直接“拿来”作为立论言说的重要依据。《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这部学术专著是作者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打造而成的一部学术精品,延续了他一贯求真务实、踏实严谨的文风,视野开阔,涉猎广泛,笑谈于古今须臾之间。
其实,关于该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西北大学文学院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贾三强教授已在此书序言“长安学、长安文学和民族文学”中有十分明确和清晰的定位:“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黎羌教授(本名李强)大著《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出版发行,这是‘长安学’研究中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黎羌教授继往开来试图“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他“将中国包括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学融会贯通,形成一种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学”,“把56个民族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幅巨大的中国文学地图中重绘……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夺目光彩”,“这是一个需要大智慧、大学问、大胆略才能开创并一步步前进的重大课题”。
一、我们都是新疆人
黎羌于20世纪末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还曾经在中国电影刊授学院、中国电视剧艺术中心、广东商学院等地进修学习。饱受艺术熏陶的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担任过《新疆文学》编辑,《新疆艺术》责编和《新疆文艺志》副主编;后来升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新疆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由于黎羌在戏剧、戏曲、乐舞、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等方面成就突出,在调至内地高校后,被山西师范大学特聘为教授、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外国戏剧教研室主任。21世纪初,曾经作为著名学者前往澳门理工学院、香港浸会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印度德里大学、斯里兰卡佛学院等进行访学交流。同时多次主持与参加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受邀去全国各地举办讲座与学术考察。

黎羌在新疆阿拉山口
目前,黎羌受聘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为校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与此同时,他还具有多种社会角色,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通讯评委,《长安学术》杂志社编委,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西域艺术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理事、中国东方文学学会理事、西安大唐西市历史文化中心特聘研究员,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所所长等等。
笔者认识黎羌教授,还是因为他曾经于2012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主持召开规模盛大的“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参加该会,笔者撰写了一篇题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的文章,后有幸被收录进他主编的《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随后,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开题、预答辩以及最后毕业答辩过程中,黎羌教授都扮演了重要的评论者、引导者和激励者的导师角色,伴随着我戴上博士帽,使我感动至极。
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加深,方知黎羌教授也和我一样曾经在我国西部、天山脚下就职,我不禁惊叫到:“我们都是新疆人!”还告诉他,我来自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西大沟,童年、青少年时期都在新疆度过;1997年从新疆乌苏市第一中学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后就留校任教至今。虽然我已离开那块热土,在西安生活了20年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一谈起新疆,内心就抑制不住涌起激动之情。尤其是知道黎羌教授也是新疆人,又是我敬仰的新疆有才之人时,那种自豪感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随后,我总是用“你是我们新疆人的骄傲”来赞誉他。
二、宝剑锋从磨砺出
我们今天赏读从表面上看朴素、严肃的《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似乎不如黎羌教授过去出版发行的十几部专著华丽、厚重,但是这部出自商务印书馆的40多万字精品著作,包含了他多少个日日夜夜艰辛的劳动和付出,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黎羌教授告诉过我,为了完成此书,他曾经克服各种困难并排除各种杂事纷扰,目的是为了聚精会神;当别人陶醉在QQ、wechat、MicroBlog等现代时髦娱乐世界时,他在钻研自己钟爱的学问,并且锲而不舍、乐此不疲。回首他所走过的艰辛、漫长的学术道路,不难看出,《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骄人成绩的取得与黎羌教授早期深厚的学术积淀息息相关。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陕西,他撰写的文章还是大块头的著作,有很多其实早已涉及长安和长安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2015年,黎羌书写的关于长安和丝绸之路文化的学术文章有46篇,其中代表性作品包括:《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新疆的陕西清真大寺》(《民族艺林》1988年第1期);《西域飞天丝路游》(《民族艺术》1990年第1期);《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中的歌舞艺术》(《舞蹈论丛》1990年第2期);《阳关三叠与玉门出塞》(《沈阳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1990年第3期);《丝绸之路文化中的音乐歌舞》(《新疆艺术》1990年第6期);《斯文赫定与丝路人文》(《新疆艺术》1992年第3期);《佛教乐舞的华化》(《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1994年第1、2期连载);《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转载《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花儿曲令溯源— 兼论元曲与花儿的传承关系》(《沈阳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1996年第3期);《波斯宗教文化与东方戏剧》(《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1997年第3期);《南戏中的佛教文化》(《山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转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9期);《中国古典杂剧中的外族文化》(《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论华夏民族戏剧的发生与传播》(《文艺研究》2002年3期);《华夏民族戏剧及〈赵氏孤儿〉西渐叙论》(《戏曲研究》2004年第65辑);《宋金元诸宫调及胡汉乐舞戏的熔铸》(《中华戏曲》2008年36辑);《中国禅宗戏剧的缘起与佛教图文的东渐》(《戏剧》2008年第2期);《明代海上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及汤显祖〈牡丹亭〉中描述澳门的研究》(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2008年第68期);《唐五代词与丝绸之路民族诗词交流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论波斯古代诸乐舞杂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台湾《戏曲学报》2009年第2期);《论大明宫与长安文化》(《丝绸之路》2010年第24期);《长安佛教文化与鸠摩罗什的佛教文学译介研究》(收录《首届长安佛教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年版);《长安文化与长安学》(《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唐五代边塞诗词与敦煌曲子词研究》(《长安学术》2011年第2辑);《巴蜀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藏彝走廊民族戏剧乐舞研究》(《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四川巴蜀书社2012年版);《西北丝绸之路文化与跨国民族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关陇文人薪火传承论》(《长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丝路结奇葩合力筑巨厦—丝绸之路文化文学艺术研究回顾与展望》(《丝绸之路》2012年第18期);《丝绸之路文化文学艺术探微》(《西安艺术》2013年第1、2期);《丝绸之路研究中“文学艺术”不该缺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4日版);《古丝绸之路与新丝绸之路》(《人民政协报》2013年9月23、30日版);《论西路豫剧与东路秦腔的历史文化交汇》(收录《中原戏剧的回望与前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丝绸之路上古兰经文学与阿拉伯艺术论衡》(《世界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中华民族古代图腾扮饰与傩文化研究》(收录《声腔表演与戏剧版图—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2014年版);《论陕西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新起点》(《丝绸之路》2014年第22期);《我的丝绸之路文艺梦》(《人民政协报》2014年3月13日版);《中国与琉球群岛及日本戏剧文化交流》(收录《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3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东南亚诸国华人的文学交往与华文戏剧文学的传播》(《长安学术》2014年第6辑);《建构宏大的丝绸之路学学科理论体系》(《新疆艺术》2015年第1期);《丝绸之路诗钞》(《西安艺术》2015年第4期);《中国民族戏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中国古代行旅者与丝路乐舞戏文化传播》(《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唐代演艺文化在东北亚诸国的传播》(《东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丝路文化研究者黎羌说丝路谈文化》(《三秦都市报》2015年8月23日版)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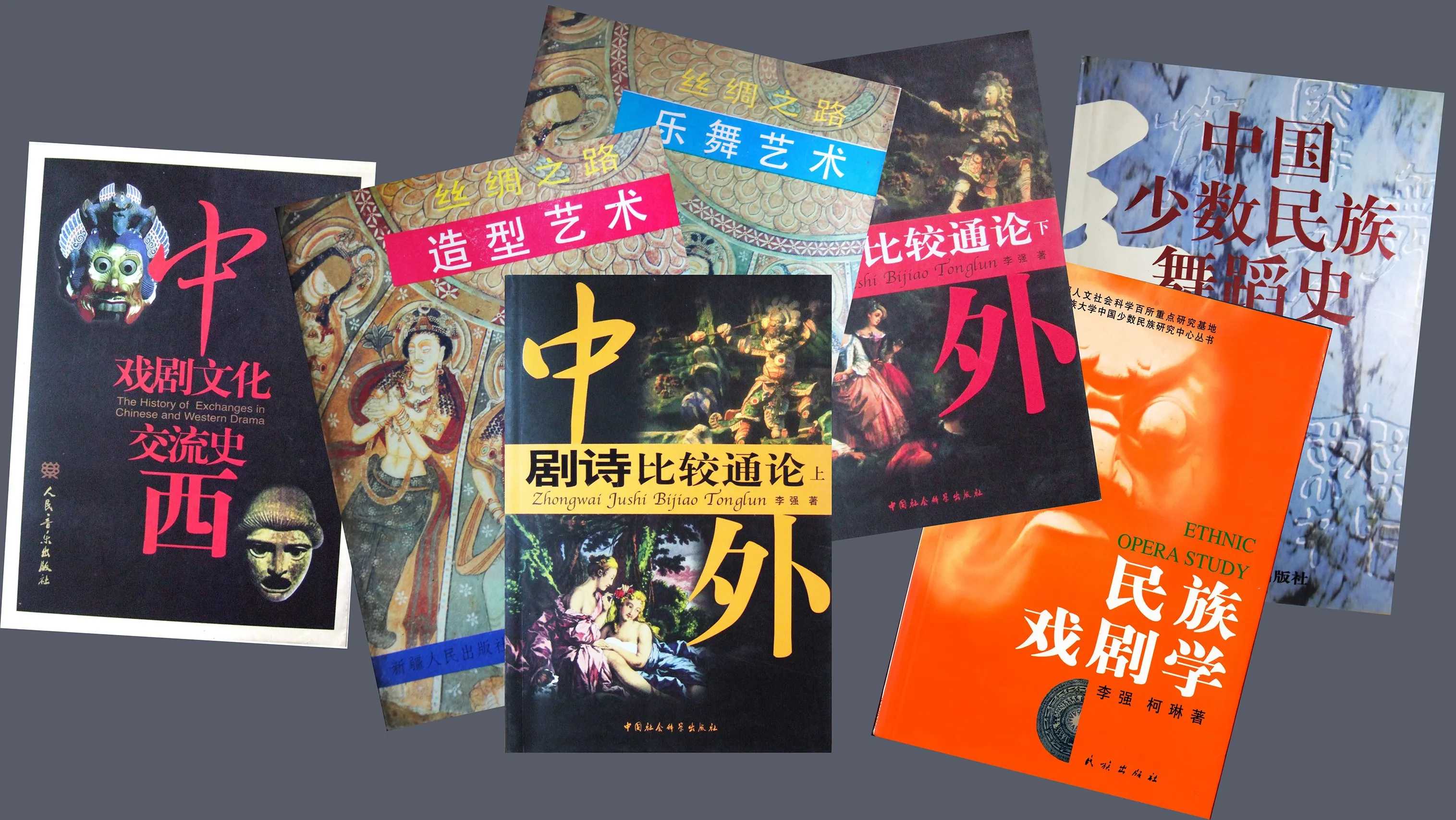
黎羌部分著作
除了大量的学术文章见诸于各类高层次期刊,他撰写、参与编著关于长安和丝绸之路文化论著还有8部之多,其中包括:《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中外剧诗比较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神州大考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修订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丝绸之路音乐研究(修订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民族戏剧文化大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等等。
由此可见,有了先前各种丰硕的学术积淀,才造就了黎羌教授今天在长安学、长安文化、长安文学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或者说,《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是黎羌教授集多重学术背景及成就于一身,将长安文化与中国各民族文学打通研究,对长安文化和长安文学精耕细作、深入浅出的一次学术展示,更是他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学术结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黎羌先生已经著作等身,在后学眼中已经“功成名就”,但是他本人并不认同这一点,仍然谦虚地说:“还要加油著书立说,因为我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变成文字。”黎羌教授就是这样一个笔耕不辍的研究型高校老师。
三、融会贯通中华民族文学
从《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总序”中得知,此书是“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倚靠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平台,衍生出来的一个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此部学术专著不仅对“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且对推动长安文化、长安文学以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民族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为什么《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会聚焦古代长安呢?正如黎羌本人所说:“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诞生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其中,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他在“导论”中认为,研究长安学,研究长安文化和长安民族文学,旨在“铸造长安文化学科的巨舰”,让国人甚至海外学者再次领略光辉灿烂的华夏优秀传统文化。
通读全书,我认为其学术价值和意义非同小可,这从其具体内容及细节可以看出。除了导论和后记,该书共分八章。黎羌教授在第一章讨论了“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炎黄子孙远古文化的繁衍地”、“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策源地”以及“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集散地”;第二章讨论“中华民族与多民族文学”,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与中华民族”、“狄、戎、羌、蛮四夷古族文化”、“中华多民族文化背景与文学艺术”以及“西北边疆地区跨国民族及其文学”;第三章讨论“殷实厚重的长安文学”,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储藏地”、“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示范地”、“中国传统文体分类与文学的发生”以及“《诗经》与中华多民族文学”;第四章讨论“汉唐各民族文学的衍延”,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汉魏南北朝乐府诗的演绎”、“隋唐边塞诗的形成与发展”、“唐五代文人边塞词令的起源”以及“敦煌曲子词与胡人诗词传播”;第五章讨论“中华民族传统文艺理论的演化”,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魏晋南北朝传统文学与诗学”、“隋唐诗学理论及文学的变异”、“宋元时期词学与音乐的关系”以及“明清时期曲学与剧学的演绎”;第六章讨论“长安文学在海内外的传播”,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中印佛教文学融汇与图文结合”、“敦煌禅宗文学经典《坛经》解读”、“禅宗南北宗诗歌词曲的滥觞”以及“中原乐舞戏曲在东南亚的流传”;第七章讨论“长安佛教文化与佛经文学译介”,分五小节展开论述,包括“印度佛教的输入与古代长安佛学”、“长安佛教文化与佛经文学的翻译”、“西域佛教东渐与鸠摩罗什的东行”、“鸠摩罗什佛经译介的学术贡献”以及“中国佛教禅宗文学艺术的东传”;第八章讨论“长安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分四小节展开论述,包括“古代长安文艺诗学薪火的传递”、“长安文学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国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从宏观上看,《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一书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风格自成一家。其基本创作思路遵循先书写历史,再关照地理,然后纵览文化,最后聚焦文学及文学现象的模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微观上来看,此书对长安文化概念,定义明确,篇章设计严谨合理,细节论证方面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写作感情饱满、文笔生动,读后掩卷思索,不觉情趣盎然。
四、守护长安文化精神家园
黎羌教授在《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里通过详实生动的话语试图说明一个质朴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要“投身于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与丝绸之路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洪流”“复兴古代长安文化”。黎羌率先提出“铸造长安文化学科的巨舰”和“守护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家园”的命题,可谓殚精竭虑、语重心长。而且,他本人正在用他的行动和努力为长安学和长安文化的复兴做出积极而全新的贡献。
黎羌教授在书中一直在强调:长安是一座拥有一千多年历史、承载光辉灿烂文化的名城,它聚集着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从本质上讲,长安历久弥新,其蕴含的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等待人们去挖掘整理,更需要后人潜心研究和持续关注。他同时告诉我们:长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也为构建真正的长安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不妨借用陕西省著名文艺理论家肖云儒在《长安文化与长安学》里的话说,长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长安学’不但是‘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此,我们应该有何作为呢?当然必须要认清形势,有所作为。一方面,我们要把长安学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和探讨,认真探寻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存;另一方面,我们要扎根历史传统,从“长安礼学”出发,建构原生态的符合长安风土人情的长安文化,梳理和重塑符合长安历史发展规律的长安文学,既对周、秦、汉、唐文学和文化进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整合和阐释,又高瞻远瞩扩充长安学、长安文化的理据和适用范围,不仅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内在和外在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养成和规范化做出新的卓越贡献。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中国西北地区的神奇、广袤的土地,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养育了黎羌这位不同寻常的学者、教授、戏剧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我们要了解他、认识他,主要通过他的著作、论文、文学作品与学术思想。在你认真阅读了他的新著《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后,你才会发现,只有走近他、走近他的著作,你才能深刻地体会到长安文化、中国西部文化的博大精深,令人敬畏与神往。
(本文图片由黎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