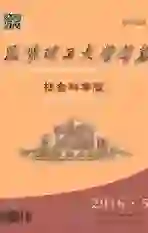工程生活实践智慧的道德哲学阐释
2016-11-21何菁
何菁
摘 要:对具体的工程行为者来说,工程生活是工程实践与个人社会角色、生活习染、文化传统、教育经历、情感欲望相统一的生活;对作为“类”的人来说,工程生活是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人之为人”的生活。因此,工程生活的实践智慧必须努力超越工程伦理规范体系及“我”与“你”“它”关系的紧张,并在现实的工程实践场景中,展现为“我”从“遵行规范”向“正确行动”超越和“正确行动”向“好的生活”升华的目的性进程。亦即,“我”既要按照规范标准遵循职责义务,根据当下的工程实际反思、认识、实践规范提出的道德要求,变通、调整“我”向“你”“它”负责的行为方式,不断探索和总结“正确行动”的手段、途径;又要坚持以德性涵育自身品格与行为方式,思考、践履道德卓越对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下人的生活的真实意义,不断扬弃践行责任与卓越和“好的生活”关系中的感性、片面性,寻求自身的全面发展、自由和幸福。
关键词:工程生活;实践智慧;遵行规范;正确行动;好的生活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5-0011-08
Abstract:To a specific agent of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should be identical with the individual's social role, life influence, cultural tradition, education experience, emotion and desires. To a human being, engineering life should be a kind of life what it is to be human in the whole existence of engineering with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Therefore, the practical wisdom in engineering life must be intended to exceed traditional normative system of engineering ethics and overcome tension between “I-Thou” and “I-It”. In addition, the practical wisdom should be displayed with the goal-directed process in which “I” make effort to do “right actions” rather than merely “obey codes.” What is mor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should be dynamic and activated because “I” devote continuously to striving for “good life” by doing “right action.” That is, on one hand, “I” not only comply with obligations from codes, but also increase flexibility to adjust my behaviors which “I” ough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ou” and “It” according to the moral requirements coming from reflecting,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ing codes in the present engineering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 should continually think about the real meaning of human practices moral excellence in the whole existence of engineering with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Furthermore, “I” should keep self-cultivation in engineering life and persist in seeking human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blessedness in an all-around way; meanwhile “I” should try to sublate sensibility and one-sided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ing moral and pursuing “good life.”
Keywords:engineering life; practicing wisdom; obeying codes; right actions; good life
现代工程实践中主动嵌入道德思考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各工程社团的职业伦理章程,其“工程师应当……”的话语系统较多地呈现形式的意义。但是,“规范往往缺乏理论表述所具有的明晰性”[1]227,工程伦理规范体系作用的对象——工程行为者及其行动——总是展开于具体的工程实践场景中,而具体情境对规范、原则的制约,又往往表现为行为者在实践过程中经由反思、认识后的调整和变通。
“我”如何在工程实践中“正确行动”?工程伦理规范之“应当”的意义明晰化过程是以“我”工程生活实践、对规范的认识和思考为背景,以美德涵蕴自身为途径,以追求卓越为目标,在具体的工程实践场景中转化为“我”通过“正确行动”践履对“你”“它”的责任承诺。责任包含着“应当如何做”和“应当做什么”的行为要求,在当前职业伦理章程中,履行责任的特定主体、所指向的具体对象却都被简略化为“工程师”。然而,工程伦理的实践(包括遵行责任承诺)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形式化的过程,作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行为者应然的存在形态,“我”与“你”“它”布伯(Martin Buber)在其著作《我和你》中用我—它(I-It)关系和我—你(I-Thou)关系描述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具有两重性,一是我—它(I-It)表征经验的世界,“我”经常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开展职业行为,从事职业活动;二是我—你(I-Thou)表征“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met),它通过联系而产生对自然、社会和他人关怀与责任的可能性。这种双重性既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又贯穿于每一个人之中,贯穿于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活动之中。的伦理关系、善之追求与“好的生活”“好的生活”意味着人通过工程活动使得自身潜能充分展开,达致人自身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增进人类的幸福,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实现、个人美德的主动显现更多地体现为工程伦理实践的实质方面,体现在工程实践与个人生活的统一之中。如何扬弃规范形式与伦理实践之间的紧张?这是人类工程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现实地构成了行为者实践智慧的具体内容。
一、“正确行动”该如何做
在现代道德哲学语境里,“正确行动”(right action)特指道德上正当或正确的行动。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动的道德正确性标准取决于它是否能导向幸福,或者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义务论则认为行动的正确性在于是否遵照了规则去行动。因此,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理论奠基的现代工程伦理便对“正确行动”赋予了双重内涵:其一,“正确行动”是工程行为者“致力于保护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福利”[2]337的行动,是追求并努力实现“好的生活”的行动;其二,“正确行动”要求行为者“诚实、公平,忠实地为公众、雇主和客户服务”[2]345,履行职业责任。诚然,在工程伦理的应用实践中,规范、原则通过行为者的接受、认识、实践、反思、再认识、再实践而具体化为多样的“正确行动”,这不仅是对“工程师应当……”规范要求的自主执行,自觉履行职业责任,也是行为者为实现“好的生活”所付出的道德努力,更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下直接体现出行为者的道德实践品格——“我”面向“你”“它”主动承担责任,在遵行规范、践行责任中实践并实现卓越;“我”亦因践诺责任而自愿摆脱“经济人”对物质利益无限渴求的贪婪,自觉抵御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对一切卓越追求的驾驭。
在当前以职业伦理章程为表现样态的工程伦理规范体系中,“正确行动”通常被定义为工程师必须在职业活动中遵循自己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承诺——努力增进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同时又要前瞻性地避免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现实侵害。因章程制订的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理论背景,“正确行动”又可被进一步细化理解为增进最多福利的行动、遵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规则的行动、尊重人的权利的行动等。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3]59,思考作为工程行为者的“我”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究竟该如何“正确行动”。“我”是一位固体废物处理的专业工程师。在“我”所工作的麦迪森县,固体废物规划委员会(SWPC)计划在该县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建立公共废物填埋场。然而,该县少数富人想买下紧挨着这个拟议中的填埋场的一大片土地,因为他们打算建一座有豪华住宅环绕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富人们认为那里是麦迪森县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在拟议地点建立垃圾填埋场会损害他们安居休闲的权利,因此建议将垃圾填埋场改建到县内贫民集中居住的地区,这样方便废物运输、清理和及时填埋;或者将垃圾填埋场迁址到临近麦迪森县最贫瘠地区的土地上,因为只有8000人(麦迪森县有10万居民)住在那里。
先以“风险(成本)—收益”的方法来考虑富人们提议的第一个方案。第一,虽然建垃圾填埋场会占用部分贫民的土地,填埋垃圾时散发出的有害气体会给生活于周围的贫民的健康带来轻度伤害,但在短时期内不致使人生病,而且,由于废物处理效率的高效便捷,会节省很多比如垃圾长途运输、屏蔽气味等费用。第二,富人们向政府支付一定的“垃圾填埋污染税”,用于政府支付招标环境清洁公司消除局部污染,或者对那些被占地的贫民和受到轻微伤害的贫民做出补偿;更重要的是,“污染税”的税收远大于治理污染和补偿的支出。第三,富人们在原址建造的高尔夫球场每年都会吸引附近乃至全国的富豪们前来休闲度假,这为当地政府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若只从成本—收益分析来判定这样做能带来最多的赢利,“我”或者可以认为这是“正确行动”,毕竟它在总体上促进了最好的结果。可是,经济上的获利并不能证明让人口稠密的贫民区承受污染和健康的代价是正当的,即使穷人因其健康损害获得了赔偿,但对整个麦迪森县的10万居民而言,成本和收益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还有,如何对贫民生活的损失或伤害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评估?金钱、货币的价值怎么能够置于人类生活之上?未来的、长远的安全和健康风险又将如何预测?所以,着重于经济利益的、仅凭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决断是否是“正确行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将垃圾填埋场建在人口稠密的贫民集中居住的地区将会使少数富人受益,而代价却是更多贫民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从促进或至少保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出发点来拒绝富人们的第一个提议、接受第二个提议“应该可以”被看作是“正确行动”,因为这貌似为一种对大多数人产生最大好处的行动,而且这颇为符合“在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 [2]344的现代工程职业伦理精神。但是,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生活在临近麦迪森县最贫瘠地区的土地上的8000人的安居和健康的权利如何保障?“正确行动”难道一定要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如果“我”是这8000人中的一员,“我”能否轻易摒弃一般人对安居与健康的基本情感和欲求,只怀有圣人般的牺牲和奉献?
工程伦理规范“责任”要求之下的“正确行动”必须正视并尊重“你”“它”的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将“我”置于“你”“它”的位置上并设想“你”“它”存在的价值,就会发现以上“正确行动”的选项都存在问题。我们不能仅凭某条规范的指示将目光单独地集中于富人、贫民或郊区的少数居民希望怎么做或愿意接受什么,而是“应当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眼光来考虑问题,努力按照人们可以共享的标准来对待他人”[3]70。这种可以共享的标准是建立在尊重“你”“它”存在的基础上的——“我”将自己潜在地视作既是行为的主体又是接受者。在上述案例中,“正确行动”是否就应该建立在最大可能尊重所有人权利的基础上——尊重郊区少数居民安居与健康的权利、尊重城内贫民的健康生活的权利、尊重富人们娱乐休闲的权利、尊重政府休闲经营获利的权利?可是,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而且还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权利问题。“我”该如何做出权衡?
视“你”“它”的存在并尽可能尊重所有人的正当权利的“正确行动”在现实的工程实践中更多地只是理想情形,无论“我”做出何种选择,都必然会侵犯某些人的正当权益。对“我”来说,除了工程职业伦理章程以规范的制约形式明确载明的诸多职业责任以外,作为一个生活于此、有着正常人生活情感和欲望的工程师,“我”还须具有与职业角色相关的胜任、忠诚、谦虚、勇敢等美德,以及作为普通人的仁爱、公德心、善良、同情、正义等品德特征。这些集聚的人格和美德形成了“我”的道德卓越——不仅注重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更应在维持个人完整性的前提下遵循良知的指引,反思规范对“我”提出的责任要求,在可供选择的建议中反复比较和权衡;若给出的可选择建议都不能满足工程实践的卓越标准时,“我”应积极寻求其他方法来充分保障各方的权益——比如,“我”会同意富人们提议的第二个方案,但是富人们必须对居住于此的8000人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政府也要在城内或城郊其他地方给予他们不差于此前生活标准和居住条件的妥善安置;同时,在填埋场附近建造污染监测站,招标生物清洁公司及时处理已发生的或潜藏的污染风险,维持该地方的生态平衡。这种追求卓越的行动,才是既满足于规范的职业责任要求又不囿于规范限制的“正确行动”,它以“我”的生活实践、对规范的认识和思考为背景,以美德涵蕴自身为途径,以追求卓越为目标,“从而实现内在善尤其是公共善或共同体的善,而不允许外在善(如金钱和权力)干扰他们的公共义务”[2]75。
二、“好的生活”是何理想
当代工程伦理的道德哲学实践,使得追求“好的生活”成为一个实践理性的论题;而“好的生活”这一理想引入人类的工程生活,也使伦理学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层面。在行为者的工程实践与个人生活的统一中,“好的生活”不但为“我”践行道德卓越指明努力方向并制约“我”物欲的目标,而且,也为“我”设定了实现的手段和条件——“我”不是仅仅为了对工程活动卓越履责而“正确行动”,“正确行动”不过是“我”追求“好的生活”实现的手段;“好的生活”作为“我”期待并选择的价值目标,又规定了“我”在现实的工程实践中必须“正确行动”。“好的生活”是行为者对工程实践结果的美好期望,尽管不同的工程行为者对“好的生活”有着稍许差异的理解,但都不否认它是以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为主要内容。相较于工程伦理研究视域中的其他对象(比如行为者、行为者的行为、规范等),“好的生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终极的目的;也因为其对卓越的昭示,可以视之为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的完美、完善与幸福。
首先,“好的生活”为人类工程实践指明通达幸福的实然之径。“好的生活”作为人在工程生活中追求的广义的“幸福”,无疑呈现为一种价值形态,即通过“正确行动”得以使“我”自身潜能充分展开以及自身多方面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又关注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好的生活”这种价值形态中,“我”既是需要的主体,也是需要的对象——“我”自身潜能的充分展开,同时也意味着满足“我”自身多方面发展与完善的需要;“我”多方面的发展,并非仅是以技术和工程为工具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而是以“我”“正确行动”、卓越履责而致自身完善为目的。
其次,“好的生活”昭显工程行为者实现卓越的应然之阶。以“好的生活”为目标,“我”自身潜能的充分展开过程同时表现为道德卓越力量的确证过程;正是这种确证过程,赋予“我”追求“好的生活”实现以积极的品格。道德卓越内在于“我”追求“好的生活”的整个过程,展开于“我”工程生活和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在“我”面向“好的生活”将自身潜能充分展开的过程中,“我”遵行规范对“我”多种多样的责任要求,展示了道德赋予“我”认识、反思工程现实的理性能力,显现了美德涵育“我”实现自身价值、创造卓越的实践智慧,“我”亦同时逐渐获得了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好的生活”可以看作是这种肯定在行为者工程实践与个人生活统一的人生领域的展开和具体化。
一方面,“我”自身潜能的充分展开、确证道德卓越力量的“好的生活”实现过程,固然与行为者个体的道德努力相关,但它具体地展开为“我”与自身、“我—你”“我—它”关系。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共生共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人类通过工程实践达致“好的生活”过程不是个体行为者的孤立行为,而总是在人与工程、自然、社会的交流和“我”与“你”“它”的互动中实现的,即使某个个体行为者在工程生活中践行道德卓越、实现自身价值,也离不开前后相承的经验积累及具体的工程社会背景,从而在纵向与横向上都涉及“我”与自身[BF]、“[BFQ]我—你”“我—它”关系。例如,20世纪中期生活于伦敦的市民即使拥有较为丰裕的物质财富也不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好的生活”,雾都劫难1952年12月4日,伦敦城发生了一次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烟尘和气体在低空大量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期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以鲜活的事实显现了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紧密联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工程活动注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同时,“好的生活”作为在一定范围内(工程共同体、社会)的发展过程,“我”自身潜能的展开不仅与行为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为条件,而且卓越也涉及行为者主体间的相互评价:当“我”遵循美德反思、调整、变通规范的指示要求去“正确行动”,当“我”向“你”“它”忠诚履行责任承诺得到其他行为者、共同体或社会公众的承认与肯定时,“我”会因道德实践的成功而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另一方面,“我”与自身、“我—你”“我—它”关系又以时间为其向度,同样制约着“好的生活”的内容及实现形式。具体来说,“好的生活”的时间意义表现在“我”承担对“你”“它”责任的过程性上。“好的生活”并不仅仅是“我”在工程实践中发挥潜能、践行卓越、择善履责并正当获取物质利益的某一时刻的状态;以行为者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的和谐与完善为视域,“好的生活”本质上展开于工程共同体和个体行为者确证道德卓越、主动担负起对“你”“它”责任的过程,在践履不同层次责任的历时性进程中充分展开自身潜能,积极促进自身多方面的发展与完善。作为“好的生活”的本体论前提,行为者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确证、实践道德卓越,实现“我”与自身、“我—你”“我—它”关系的平衡,并在实现的过程中践履不同层次的责任,都是以历时性为特征,无论是在工程共同体(中观)层面,还是从个体行为者(微观)的维度上看,在行为者主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向“你”“它”卓越履责都具有不同的内容,这可看作是“好的生活”这一价值目标对行为者践行道德卓越的不同确证;并且,它亦通过赋予“好的生活”以具体的历史内涵而显示了其时间性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人类工程活动的目标是通过改造自然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改善自身生存和生活条件,那时“好的生活”就被具体化为向自然界攫取更多物质利益、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概言之,就是通过广泛的工业化达到国富民强。但是,进入到20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在战场中的运用使得千万民众无辜丧生,对环境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害性后果,人们开始醒悟到,对技术、工程的功利化利用反而会偏离美好初衷;而接踵而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特内里费空难等重大工程事故造成的“人祸”惨剧又使得人们不断校正对“好的生活”的价值期许,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后代子孙的生存利益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及至进入到21世纪,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广泛关系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人们对“好的生活”的考量也因此扩大到工程—人—自然—社会的整个存在领域。。在个体行为者潜能、人格完善、美德涵育、践行卓越的时间性展开中,“好的生活”也因“我”工程活动的现实境遇和对现状能动认识、反思、实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内涵。简言之,“我”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的时间性,我向“你”“它”卓越履责的历时性,规定了“好的生活”内容及实现的时间性。
再次,“好的生活”是“我”在工程生活中进行伦理实践的必然追求。前已述及,“好的生活”以工程—人—自然—社会完整和谐存在为本体论背景,而“我”在这一存在中的不完满性和有限性既隐含了“好的生活”的过程性和历时性,也确认了“我”存在的伦理实践向度——“我”存在的向善、择善、行善植根于“我”伦理实践的目标、程度、范围,并同时赋予“好的生活”以践履责任承诺、践行道德卓越的伦理实践内涵;更因为人类工程活动中风险和运气的存在,导致“我”在现实的工程实践场景中对“你”“它”负责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卓越对“好的生活”的范导成为必要。道德卓越力量的确证,其意义首先在于通过对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证——“我”要通过“正确行动”,遵行对“你”“它”担负责任的承诺,为“好的生活”的实现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道德对“好的生活”的制约,并不仅仅表现为通过制定工程职业伦理规范来单方面要求“工程师应当……”;卓越对“好的生活”的范导,也不仅仅只是提供一种认识、反思、变通、调整规范对行为者行动要求的思维方式,而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乃是以工程—人—自然—社会完整、和谐、可持续存在为思虑视角,通过对存在的人之为人的规定来影响“好的生活”的发展趋向康德认为,人之所以自由,在于人的理性能够驾驭感性,控制人的欲望;追求幸福虽然合法,但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和方式必须要合乎道德。当康德以“配享幸福”为幸福的前提时,他所关注的是要赋予主体以道德的规定,并以人自身存在的道德性来担保幸福追求的正当性。本文此处类比运用了康德“以德配福”的观点及论证,即以工程行为者存在的道德性来担保追求“好的生活”的正当性。。这里所谓存在的人之为人的规定,是指将公共的道德原则、观念和具体的职业伦理规范化为行为者主体的内在要求和意向,从而使自我潜能的充分发展与完善成为“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从现实形态来看,“好的生活”所涉及的感性内容和感性向度如果缺乏必要的范导,极有可能引发伦理实践与“好的生活”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20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多次重大工程事故从经验方面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为“我”践行对“你”“它”的责任承诺并在履责的“正确行动”中发展自己、完善自身、确证道德卓越的形式及结果,“好的生活”不仅有其物质的、感性的规定,而且也涉及包括精神和理性在内的多重向度。就个体行为者感受“好的生活”而言,“我”对自己与工程实践紧密联系的个人生活的满意,不仅有物质欲望和利益要求,也包括理性需要和欲求的满足;就“好的生活”的结果形式而言,“好的生活”同时体现为行为者以“正确行动”的方式向“你”“它”负责、实现卓越的过程,后者构成了“我”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好的生活”固然离不开行为者“遵行规范”开展工程活动,但其最终的真正实现还是依赖于人类是否能在整个工程生活中始终“正确行动”、践履各层次责任并始终彰显卓越的力量。所以,当代工程伦理实践的终极目标就是过上“好的生活”。“好的生活”带给人类的自由与幸福,总是以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个体行为者自身潜能的充分发展、涵育德性、践履责任、践行卓越为题中之义。
三、工程生活实践智慧的道德哲学意涵
传统的工程伦理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来指导行为者“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体现出人类以实践理性的努力去“正确行动”、实现向公众和社会负责的决心和信心。可是,“正确行动”在具体工程实践场景中的落实,若只以遵行规范为条件,则往往难免走入实践困境。在工程实践与个人生活的统一中,“正确行动”的核心是建诸于认识、实践、反思、变通规范基础上的践履各层次的责任,亦即对行为者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的价值认肯,它参照已有规范设定的正当标准却又不完全依赖于规范对实践场景的抽象判定,而是面向未来以美德涵育自身,不断发展行为者主体潜能,并以追求“好的生活”实现为目标。而“好的生活”的实现,又取决于工程行为者是否自觉自愿地“正确行动”。在这里,自觉自愿反映出行为者潜行知善、笃力向善、积极行善的道德实践意向,凸显出在现实工程生活中的行为者创造并践行道德卓越的意志和决断。工程生活的实践智慧,便表现为“我”在实际的工程实践场景中,“遵行规范”向“正确行动”的超越和“正确行动”向“好的生活”的升华。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而言,“遵行规范”向“正确行动”超越所蕴含的是如下观念:工程伦理规范体系是以“正确行动”理念为根据,以“工程师应当……”的话语系统表达出“正确行动”的道德行为意向;“正确行动”建立在普遍化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在具体的工程实践情境中融入美德对行为者存在价值的进一步思考——“我”如何去真实获得“好的生活”?一方面,仅仅依循职业伦理章程的要求去“遵行规范”并不能让“我”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在章程条款的规约之下,“我”只能是个无条件履行职业责任的“无生”“无脑”“无情”之“无脸”的“工程师”。虽然“正确行动”建诸于规范、原则设定的正当性标准之上,却在工程实践与个人生活的统一中,时刻以理想的人格境地的存在状态为观照,要求“我”将温暖的心理动机凝结为关怀“你”“它”的实践理性,将道德敏感性沉淀为自我行为的道德卓越,清醒地认识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我”与“你”“它”的关系,主动践行“我”对自身、“我—你”和“我—它”的责任。“正确行动”对行为者存在价值的确认,并不仅仅依据行为者是否完成了章程条款所规定的“工作”或“任务”,更多地在于是否真正实现了“我”对“你”“它”的责任承诺,是否在工程生活中发挥自我潜能、获得了自我的多方面发展,是否以彰显卓越价值观的积极姿态去努力追求“好的生活”。可见,在个体的维度上,它所指向的是自我的完善与完满;在群体的层面上,它则以社会的发展与实现“好的生活”为目标。另一方面,对行为者存在价值的肯定,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上往往需要通过职业伦理章程的形式来加以担保,因为“在普遍的形式下,具体的存在才能扬弃个体差异而形成共同的行为导向,在任何条件下都既肯定自我的内在价值,又彼此承认和尊重各自的存在价值”[1]264。与此同时,个体行为者德性、人格、生活与工程实践的统一,促使行为者在当下的工程生活中通过自我反思达到对规范的更新认识,进一步化作行为者要“正确行动”的现实意志冲动。在工程实践场景中“我”每一次对规范的反思、认识、实践都是“我”确认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都是“我”创造、实践卓越的过程,也都是“我”为实现“好的生活”所付出的尝试与努力。
继续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工程伦理实践的走向可以发现,“遵行规范”和“正确行动”的关系类比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经与权的关系。“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春秋繁露·玉英》),工程伦理的规范体系是“经”,正如各工程社团的职业伦理章程确立并强调了规范在工程活动中“必须应当如此”的绝对性和权威性;而在具体的工程实践情境中,“正确行动”又要求对规范因时因境作出变通和调整,这就是“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在生动现实的工程生活中,若“我”拘守职业章程只知依令行事,则常常会遭遇伦理抉择的两难。所以,“我”如欲在工程实践中“正确行动”,就必须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特殊情形对相关的特定条件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对规范进行认识和反思,对规范的作用方式和遵行规范的途径作相应的变通和调整。在此,具体的实践情境梳理和分析,构成了对规范作变通、调整的现实根据;而“我”生活的历史与传统,所受到的伦理教育和美德浸染,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点,都集体地影响了“我”对现实实践场景的情境分析和对规范的反思与再认识,构成了对规范作变通、调整的心理根据。
作为人类工程活动的理想结果,“好的生活”以超验的形式规定了行为者在工程生活中“应当如何”。一方面,“我”要转变在工程实践和个人生活中对规范系统的依赖,实现“我”“我—你”和“我—它”关系平衡并在寻求平衡中践履不同层次的责任;另一方面,“我”要在工程生活中融会贯通人的主体意识、能动信念、实践要求和对人、社会、自然的责任,彰显人在工程实践中的自由意志,创造并践行道德卓越,使得自身潜能充分展开,达致自身多方面的发展。“好的生活”既在形下层面包含人类对物质丰裕的生活理想的期求,也以幸福为价值指向,在形上层面体现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对人的尊严和道德卓越力量的确证。“好的生活”作为人类工程实践的远大志向,具体展现为“我”将规范之“应当如何”在工程活动情境中的需要、欲望、心理提升为主动“正确行动”的情感、意向和意志,并由此在工程实践场景中践行美德要求,创造并践履卓越。“我”“正确行动”的动力因与工程生活的现实联系起来,“正确行动”向“好的生活”的迈进,在某种意义上触及了道德动力系统中形式的方面与实质的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从更深层的视角来看,“好的生活”是“我”实现自身潜能、获得全面发展的内在根源,是鼓励“我”在工程生活中将向“你”“它”践履责任承诺的道德意识和实现卓越的道德境界现实地转变为“正确行动”的源动力。一方面,当“我”在工程生活中认识到“我”“你”“它”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并寻求“我”“我—你”和“我—它”关系的平衡时,“我”会根据规范的行为标准做出某种“应当”的行为选择,在反思、变通、调整后通过所选择的“正确行动”来确证“我”道德卓越的力量和尊严。另一方面,存在于工程—人—自然—社会中的“我”并不是理性的抽象化身,生活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也规定了“我”存在的具体性。除了对工程伦理之“应当如何”的理性自觉之外,“我”在工程实践场景中对“好的生活”的追求每每通过具体的欲望、意向、情感等外化为“正确行动”的心理激励,这种情感、意向等并不是负面的规定,它们同样可以通过升华获得道德的内涵,并在实质的层面构成“我”从“遵行规范”到“正确行动”进而实现“好的生活”的动力因。就“正确行动”本身而言,它可看作是“我”主体人格和德性的外在展现,它时常以“我”潜能的展开和卓越的显现为其本体和根据,因而它总是朝向“好的生活”,规约、引导、鞭策“我”在工程实践中的行为必须符合“应当如何”之伦理信条。
随着人类的工程实践从“遵行规范”到“正确行动”、进而实现“好的生活”的发展和演进,“我”行为方式上从被动到自主的过程主要从形式的方面表现出工程生活的实践智慧特点,亦随着“我”从知善、向善的意向和心理向择善、行善的情感和意志提升,表达出工程实践主体从自觉向自由的成长。真实的德性和人格,总是融入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的“我”的生命结构和生活历程中,作为“我”向善、择善等的精神定势,构成“我”存在的一个现实维度;自我潜能的发挥、自我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我”行善的情感冲动和实践意志,又与美德、人格交织在一起,具体地展开于“我”“在”(existence)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的过程之中,工程生活的实践智慧亦在“我”的道德实践中得到不断地形塑和确证。在这一意义上,“我”的德性、人格不仅与“我”“遵行规范”“正确行动”及追求“好的生活”具有统一性,而且呈现为“我”自身之“在”的内在根据;而二者的协调,同时又意味着工程生活实践智慧的终极价值指向,是“我”的存在方式(从“遵行规范”到“正确行动”进而实现“好的生活”)与存在根据(实现卓越)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迈克·W·马丁,罗兰·辛津格.工程伦理学[M].李世新,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查尔斯·E·哈里斯,迈克尔·S·普里查德,迈克尔·J·雷宾斯.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M]. 丛杭青,沈琪,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