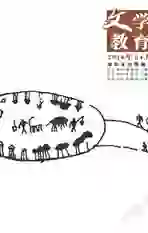试论《秦俑》的叙事技巧
2016-11-19张丽华
内容摘要:《秦俑》的叙事策略较为简单,通过时空的轮回与静止,让人物身份在现实与历史交替发展,借助话语所具有的设置悬念与揭示真相的功能,很好地展示了爱情的千古魅力。
关键词:李碧华 秦俑 时空 身份 话语
一.李碧华的《秦俑》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走红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被文学界称为“奇情才女”,在整个华文界,她独树一帜,独辟一径,成为小说界独特的存在者。她善于将爱恋的悲剧推向极致,造成生死冲突,以此来验明爱情的极致境界,或以此来证明爱情的毁灭性。她将历史的,人生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意蕴灌注其中,使小说丰满而独到,在故事的情节塑造上,可谓奇情妙思夹杂其中,荡人心魄,雅俗共赏中,读者随之惊心动魄。
在李碧华众多的言情小说中,《秦俑》不是她最得意的作品,相比较于《霸王别姬》、《川岛芳子》、《青蛇》等作品,《秦俑》并不显得更有特色,但是在以写爱情悲剧的深刻性著称的李碧华的作品里,我们却在《秦俑》里看到了爱情更为温和的一面。虽然它在秦朝里,猎心地碎裂;虽然它在朱莉莉的世界里,再次不圆满;可是它终于再一次有了轮回,隔着一个又一个的俑像,他还是看见了她,此生,她成了日本女孩,可那羞涩,单纯的笑容里,使这个故事不再冰冷,它穿越重重现实的枷锁,温暖了我们对爱情的心。死一次不可怕,死两次不可怕,只要还能重生,就还能再爱。人生在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爱情考验里,难道不正是因为始终抱持着对爱情的美好想象而能不断地接受爱,哪怕被爱抛弃,伤害,都不甘愿放手。《秦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鼓励读者去爱,因为,无论你前面吃了多少苦,最后会得偿所愿的,而这,对我们这一生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可以说,只有《秦俑》,她写出了最美的爱情,描绘出了最好的男女关系。
二.时空:轮回与静止
《秦俑》不仅仅是秦朝的故事,它描写了自从秦始皇时代起,中间生命静止了三千年的蒙天放,突然之间苏醒过来之后,又续前缘的情定三生的爱情传说。三千年前,作为最受宠信的郎中令,蒙天放却与被列入寻仙药的童女冬儿相恋,仅仅只是几面之缘,他们就情心暗许。在要离开秦朝而去虚无缥缈的蓬莱时,冬儿终于无法抛下这份私情,甘愿一死以求以死相伴。在冬儿以身殉情的那一刻,她把仙丹逼入蒙天放的口中,从而使蒙天放得以存活了三千年而不死,蒙天放当时为了不负此心,请死,不允,自请泥封为俑像,生生世世守护皇陵;接着,三千年飞逝,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一次偶然事件使蒙天放的生命重新复活,他遇到了冬儿的现实版朱莉莉,经历了一系列的患难与共,他们再续前缘,可他们再一次错过;又过了50年,蒙天放成为一名考古人员,当他看到她时,女孩的笑容仿佛是冥冥中冬儿影子的美丽重生。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但读者意犹未止,仿佛又看到一段情缘的再生。《秦俑》里的故事,时空都宏大,互相承接叠加。蒙天放不仅活在秦始皇时代,还活到现代,他的生命贯通历史,不消弭于时间面前,但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在李碧华笔下,就是矢志不渝地爱着冬儿,或者说长得如冬儿那样的女人,而这正是时间的静止表现,万千事物都已经“物非”,但依然“人是”。这种不死的爱恋对李碧华所要传达的爱情意念造成了传奇效应。
时空概念不仅是属于物理的,也是属于哲学的,更是属于人生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使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自由无忌状态,但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里,爱情可以做任何的联想,可以架上翅膀,往它向往的天地飞翔,正是在这样的大空间中,爱情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它的尺度——而这些尺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时间和空间不再是纯粹的、空洞的形式,而是一种统治万物的神秘力量。”[1]李碧华在《秦俑》中通过蒙天放的长生不老来跨越时空的限制,又通过历史故事作为衔接的桥梁,架构起她小说的骨干,从而将言情小说的魅力推向极致。如果此生生死无缘,那就用来生来弥补,如果今生足够相爱,那就让时光停止在这里;如果在这里不能相爱,那就换一个朝代,活在另一个空间里,相爱,爱到彻底。在一次又一次的爱恋里,我们重复地感受到生命里挥之不去的宿命,在前生的爱,今生不会被遗忘,它借助另一个生命复生。爱在这里静止,也在这里完美,悲壮,不复新鲜,却总能一次又一次激起我们心中的怀旧波澜。《秦俑》实际上也渲染了这样一种怀旧情绪,通过时空的轮回,蒙天放和冬儿的爱恋益发显得可贵和刻骨铭心。而朱莉莉在临死之前说的“我会再来的,等我!”一句话仿佛是上天注定,在作品的最后,貌似冬儿的女孩悄然来到蒙天放工作的地方,单纯羞涩,至此,宿命,轮回的主题得到了完全的映证。李碧华用想象穿越了时空的障碍,实现了人的前生和今世的有效对接,从而更加突出了她所渴望表达的爱情的深度。伊瑟尔认为:“想象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认知话语能力,它似乎是在询问事物应该是什么。”[2]其实,李碧华的想象能够达到如此惊人心魂的程度,就与她使用这种叙述策略非常相关。这种想象正是利用和发挥了形象和意义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在完全不违背生活逻辑和人物真实性与统一性的情况下,巧妙地将象征意义融于具体的描写之中,但事实上,所有的实现路径都来源于她采用时空轮回与静止的叙述策略。
三.身份:历史与现实杂糅
《秦俑》中,蒙天放服长生不老药,被泥封三千年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直接由秦朝来到了民国,穿着秦朝郎中令的胄甲,横行于世,格格不入。进入医院,误为黑店;坐入汽车,飞驰而出,在大街上飞跃奔进,阻塞交通;就餐时,不知文明礼仪……他的身份在民国再也得不到认可,他无所适从,一切都不复从前了。一切都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爱情。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感,以至于不断地要求还回墓陵。但他能始终如一认同他的爱情身份,保护、爱护朱莉莉,这个酷似冬儿的女人。李碧华在对秦朝历史做了一番展现中,通过还原那个时代的礼仪、习俗、言语、服饰、建筑,以及当时的人际关系,重构了一段带有浓厚民间情意色彩的“小叙事”。这样,小说通过蒙天放的复活,将历史与现实同时铺开,以冬儿留下的信物,绣花鞋为证物,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绣花鞋不再是绣花鞋本身,而是具有了象征意义,它联系着个人的回忆,回忆也许苍老,但是它却是回忆里仅能抓住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过去。“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历史都是国家民族的历史,即所谓‘大叙事;而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一个集体、家庭、回忆、用这种方法来对抗国家,民族的大叙事。”[3]所以绣花鞋作为蒙天放与冬儿生死不渝的爱情的见证上,在现实中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指证作用。而一双绣花鞋也将历史中的爱情(即秦朝的蒙天放和冬儿)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爱情勾连起来,爱情的幻象变更了,爱恋有了现实的血肉,现代的朱莉莉从一开始就砸碎了蒙天放的痴恋,可前世的爱恋还支配着他的今世。正是这种诡异的爱恋,荒诞不羁的强制性关系,促使李碧华笔下的爱情光芒四射。通过身份的异质性存在,即身份既存在于现实中,又存在于历史中,它具有共生共存性,如此,爱情中的各种依附性关系被瓦解,连爱情的对象也被形似而非神似的人所替换,但爱情依然借尸还魂,攀附其上,接续前生的戏演下去。借助这种叙事手段,李碧华的小说叙事与此得到了充分无羁的施展。
四.话语:悬念与真相
李碧华的语言表达,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画面感,而且能够很好地打通读者各种感官之间的联系,使读者在阅读时,将不同的感受一并体验,让读者置身于身之所触,目之所见,心之所念的世界中。这一点,毋庸置疑,她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就是她语言表达非同寻常的有力证明,但其实她在运用语言时,还另有技巧,她很巧妙地处处设置悬念,在悬念被逐渐析出时,她悄无声息地带领我们走近了一个更具真相的世界。
《秦俑》中的冬儿面对离别,也是永别时,无法忍受此生与所爱从此天涯永隔,毅然出逃,飞蛾扑火地跑进必死的命运里;蒙天放在她以死表白爱情的动容里,也不负卿心,愿意以一死换一生,最后在秦始皇特殊的爱护里,千秋万年为他护陵。在两个人的爱情中,李碧华充分发挥了她的笔力,冬儿的每一次牺牲都是度量过的,她害怕得不到同样的回馈,可是她还是选择了豪赌——赌她一夜情下的爱情,这未尝不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可是在她的每一次惊心胆战中,她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回报,蒙天放没有辜负她,他以同样的牺牲拯救了他们几乎是萍水相逢的爱情,虽然最后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穿越重重悬念,我们看到,每个人活着对爱情的渴望还是彼此不辜负。正是因为现实里有着太多的爱情的“叛变”,所以冬儿和蒙天放被植入生死考验的爱情,才更动人心魄。也许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经历这种考验,可是在小说里,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们内心的真相,这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拍戏的掩饰下,其实白云飞(当时红极一时的男主角)是一个盗墓领头人,在前面种种看似无厘头的故事里,李碧华很好地埋下了伏笔,暗中设置了悬念,后来一个大转弯,将白云飞的真面目揭开,读者读至此,不禁豁然开朗,对朱莉莉先前的厌恶感一扫而空,正是她的无知无畏无聊无趣,她才可能有机会被选中并参与其中,她的作用不再无关轻重,不再只是一个仅仅是添加笑料的对象,她是一个合理的不幸儿。而正是这样极其世俗的女人,追求最为现实的欲望的女人,李碧华给了她一个痴心的爱恋者,那就是三千年后醒来的蒙天放,在一个最不应该得到爱情的女人身上,她却得到了。这难道不像我们的人生吗?人生的真相不在理所当然的逻辑里,而在不可理喻的际遇里。
秦始皇复苏之后,再次掷币,只是这次不是决定蒙天放的生死,而是选择他自己的方向。在秦朝赫赫宣威的皇帝,到了今天,他的存在也变得无可奈何,让秦始皇活过来,给我们设置了悬念,该如何处置他的存在?就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社会上有一个位置,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所依附。现在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而这就是人生真相的一面。
五.结语
李碧华曾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角痴情,我和现代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向往天长地久的感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这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外,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女子。”[4]虽然这里说的是《胭脂扣》里的如花,但其实李碧华很多作品里都有如花这样的女子。《秦俑》里的冬儿就是如花。正如李碧华自己所言,生活是平淡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常常是处于疏离状态,人们对天长地久是怀疑的,但很多人都期望拥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即使是暂时的天长地久,所以李碧华写了天长地久,不过是通过剧烈冲突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冲突是非常态的,一个生,一个死,通过这种生死相依,永不离弃来实现爱情的天长地久,将爱情置之死地而后生。无论是《胭脂扣》、《秦俑》还是其他小说,我们看到李碧华都使用了叙事技巧,里面的故事都穿越了时空的格局,身份在现实与历史中自由转换,通过设置悬念的方式,呈现爱情的真相,而在轮回的因缘中,充满了宿命的意味。在李碧华几部长篇小说中,《秦俑》中的爱情是属于最理想的,这份爱情不再压人心魄,因为这里的爱情悲剧是一种让人安慰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56
[2]王卓慈,张卫凤.潜隐还是显在——李碧华影调小说的“文本互涉”现象[J].成都学刊.2010年第3期:109
[3]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J]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154
[4]张西娜.个体户李碧华[N].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11—12.
(作者介绍:张丽华,广州工商学院基础部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大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