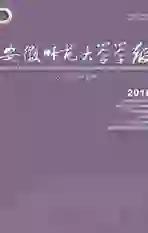人与自然的疏离
2016-11-19张彭松
张彭松
关键词: 疏离;“现代性”道德;道德心理;生态伦理
摘要: 结合道德心理分析,从人疏离自然的历史观念出发,考察传统伦理文化内蕴人与自然同一性的精神资源。通过普遍理性主义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价值颠覆的“现代性”道德,在彰显人的主体性及伦理价值的同时,却由于人与自然伦理价值观盲点,使现代人陷入孤独、空虚等道德心理困境。以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诉诸人的情感,借鉴生态心理学观点,使自身的理论从表层走向深层,为治疗人疏离自然的道德心理困境,提供研究思路,探寻保护自然的主体根据。
中图分类号: B8205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4045307
Key words: alienation; “modern” morality; moral psychology; ecological ethics
Abstract: From the human's historical concept of alienation from nature and the analysis of moral psychology, in traditional ethics culture, there are some inner spiritual resources of the identity of man and natur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volving in modern moral, universal rationalism, what overturns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culture and underlines the value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ethic values, has ignored the new changes in man and nature ethical values. Thus, modern people are vulnerable to moral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neliness and emptiness. Ecological ethics, what loo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its core, resorts to people's emotions and learn the views of eco-psychology so as to make their own theory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deep, provide initial research ideas for the treatment of people alienated from the natural moral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and explore the subject foundation of nature protection.
人应该亲近还是疏离自然?这不单纯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话题,也是牵涉到伦理、价值、情感、信念等多重因素的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当下,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亟需加强生态伦理研究,进一步挖掘、深化和丰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理解和体悟。现代人的生存方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人越处于商品、金钱、股票、科技等受人类主体的主观主义原则支配下,就越难以从情感上主动而切实地亲近和感受自然;反过来,人越疏离自然,就会越固守着主观主义思维方式,陷于人为环境的包围中。这种恶性循环带来难以预料的“现代性的后果”:在人与自然主客截然相分的世界图景中人不再和自然做获益匪浅的“对话”,只和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在人类生存的这种处境下,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主题的生态伦理研究举步维艰,难以找到解决难题的路径。以往生态伦理学从伦理道德层面探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少深入到情感心理层面关注人对自然关联、依存与渗透链条中的道德心理因素探讨,致使生态伦理学解释依然出于人类利益的外在限制而非内在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危险处境似乎有所感觉。由于丧失了与世界与未来的联系,我们的精神似乎焦躁不宁。但我们瘫软无力,过于纠缠在旧有的设想旧有的思路里,看不到怎样摆脱自己的困境。”[1]14因此,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理解和体悟需要进一步挖掘、深化和丰富。本文试图从道德心理视角,揭示人疏离自然的道德心理困境,探寻生态伦理的哲学治疗作用。
一、人疏离自然的道德解析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诞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只能以自我意识打破人与自然的原生态的和谐,进而发展人的社会性,把人性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活。但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发展人的理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疏离”。“疏离”一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出现,有着细微的差异,英文使用是“Alienation”(疏远、转让、异化、精神错乱),德文使用的是“Entfremdung”(疏远、异化)。从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疏离”一词“一般的用法是源自于卢梭,意指人被视为与他们原来的本性产生疏离,甚至完全被切断”[2]5。尽管这层意思又有两种不同的变异用法,但“一种意指人与他们原始的自然产生疏离”更贴近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在哲学伦理学研究中,“疏离”一词一般翻译成“物化”、“异化”等,指主体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分离出对立面的客体,这个客体逐渐跟主体关系疏远,从而成为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相对于“物化”、“异化”等非常专业的哲学词汇相比,“疏离”一词更能体现出道德、情感、心理、宗教和精神等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人疏离自然”的问题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生存状态,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伦理行为及其道德价值观。在拥有精确严密的知识了解外在世界时,人却对于人类的处境与自身的存在问题茫然不知所措,这正源于“现代人的疏离感”。陈鼓应指出认同关系的破灭表现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其中人与自然的疏离是最根本的,“现代人却整日生活在人工装饰的世界,想想看,在都市里的人,一生中有几回见到日出,又有几回欣赏过日落的夕阳之美。都市人的生活完全和自然脱节”[3]133。德国学者孙志文认为“现代人的三重疏离”,首先指出了“和自然的疏离”及其“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人只能够从理性的构思和实用性的观点来看自然……即使是面对自然的美景、各种的文化成就,人仍然是停留在疏离、无聊、挫折、恐惧之中。”[4]68-69在“人疏离自然”的前提下,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甚至于人和他自己也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
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疏离自然的生存状态并不贯穿于历史发展的主线,而是发生在近现代社会的伦理文化演进中。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中自然内涵的演变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古希腊有机论自然观把自然看成是生成着的活的充满理智的秩序,而人不是外在地征服自然,而是从内部直观和服从理性而神圣的自然。即便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承认人类有权利利用和享有自然物,但对上帝的信仰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心在于精神生活,抑制了人类社会对自然存在物利用、占有和支配的冲动。
与西方传统文化相比,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中都能寻找到人与自然同一性的精神资源。从儒家传统伦理中“天人合一”到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无一不提示着一个朴素而明晰的生态伦理原理: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命题;物我一体的价值生存命题;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人自伦理命题。”[5]243佛教追求人生苦恼的彻底解脱,是从探求人生和宇宙的“真实”开始的,以此打破人自身的优越感和人在自然中的优越性。日本著名学者阿部正雄认为生态危机“这个问题与人类同自然的疏离紧密连结”,因为“作为佛教涅槃之基础的宇宙主义观点并不把自然视为人的附属物,而是把人视为自然的附属,更准确地说,是从‘宇宙的立场将人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因此,宇宙主义的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又不失其个性”[6]247。鉴于此,我们不难发现前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在一定限度内保持一定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的疏离。从历史观念出发,传统伦理文化内蕴着人与自然同一性的精神资源。
诚然,传统伦理观念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总体上并不疏离自然,保持着“世界观”对人生观和人性论的前提优先性,使人作为类遵从“本性”、“自然”而行事,进而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来确定自己身份并被他人所确认。如麦金太尔所说,这些社会特性并不是偶然属于人们的特性,不是为了发现“真实自我”而需剥除的东西。“每个个体都在相互联接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了某个独特的位置;没有这种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是一个陌生人或被放逐者。”[7]38当然,麦金太尔并没有直接说明社会伦理的客观性与自然本性的内在关联,但从他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传统的理论阐释,窥见出传统伦理中人与自然本性的同一性观念对社会伦理的客观性提供强有力的担保,使人们自觉恪守或践履道德。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作为伦理根据,社会伦理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形式合理性,但在“资本的逻辑”驱动下,无法抑制住现代人永不餍足的物质欲求——这种欲求会造成对自然、对人自身的“隐蔽的暴力”。
从西方传统伦理向“现代性”道德的转型,凭借西方现代化扩张行为,使几乎大多数民族国家都以现代性为建设纲领和追求目标。现代社会在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但是,影响和推动现代社会生活发展背后的“现代性”道德是通过对诸种传统伦理“价值的颠覆”(舍勒语)所形成的现代道德价值体系,使传统社会伦理的主流价值被边缘化,而一些非主流价值成为根本的、优先的价值,因而,现代人类道德意识愈来愈陷于孤立、萎缩和倒错。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生活在现代文明或“现代文化场”的个人无法看清“现代性”道德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盲点,无法理解和体悟人——自本体论存在意义对“人生观”和人性论的前提优先性,也就难以形成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的“类意识”。
二、人疏离自然的道德心理困境
道德不只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具体事物的知识, 并且经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语)。道德实践是通过人们的认识、思维、行为、判断等过程进行的,必然伴随着许多与心理科学有关的问题。对道德理想和原则的阐释及道德实践活动要受人的心灵的基本结构、人的主导情绪、心理发展模式、社会心理学和人的理性阐释能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判断某种道德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就必须很好地理解它所预设的心理学结构,因为任何道德体系和理想都需要有心理学的理论支持。”[8]然而,为了确保讨论的题材和前提为真,在研究道德问题时常常忽略甚至摒除与之相伴随的情感、信念、意志等心理因素,以致背离了道德理论的实践智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可能会把道德理解为外在的约束或强制,却无法把道德心理视为异己的东西。因为道德心理触及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存在价值。因而,对道德观念及其行为的理论探究,不能只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同样需要重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等道德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关乎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信仰层面的世界观问题上,人对自然的利用、控制、支配,抑或保存、保护、敬畏,不同道德态度及道德心理样式会深层而长远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人疏离自然”的“现代性”道德框架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基本上是以理性的选择为前提,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取利益满足自身需要,内含诸如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现代伦理品质,暗示了一种合作的而不是根据单方面意志来处理涉及他人权益问题的行为模式。这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核心是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reciprocity),尽义务是拥有权利的前提,权利来源于以相互性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应对环境问题或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学试图将现代社会伦理范围拓展到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共同体的生态延伸,意味着一场“伦理学革命”。然而,在“现代性”道德框架下,生态伦理虽然开阔了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却无法从现代社会伦理观念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根据,必然陷入“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9]。道德关注视野的拓展意味着道德立论的依据发生变化,如果以原来的立论依据反驳道德视野拓展的合理性,将是乏力而无效的,因为伦理拓展本身就超越了原来的立论根据。但是,新的伦理拓展须提出新的理论依据并证明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因此,要想找到生态伦理的道德合理性根据,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社会伦理关系,而是首先需要从道德心理角度契入对“现代性”道德的前提性性反思,揭示“人疏离自然”的道德心理困境。
在历史上,“现代性”道德打破前现代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依靠科学技术利用、认识和改造自然,推动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形式上来看,“现代性”道德只关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尊重了历史所记载的有关为争取自由而奋战的史实,具有现代人伦规范的道德合理性。鉴于对“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这一事实的深入思考,只关注人类利益(普遍关注短期的物质利益)的伦理已经疏离了自然,使社会沦为满足个人私利追逐的“竞技场”,“实际上却是延续着一种人本主义的幻觉”[10]208。在形式上,现代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而实际社会生活中人却往往被实现生活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所支配,内在的尊严、人格的完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付之缺如。现代人自由的两面性表明:人类幻觉中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枢,实际上却有一种强烈的孤独、彷徨和存在的空虚。遂使人与人之间趋于疏淡,只有彼此互相利用的价值了。“‘现代性道德乃是一种工具性道德,一种手段合理性技术,或者干脆说,一种现代化的行为技术伦理。”[5]314在这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境遇下人主观上是为自身生命的目的,而客观上却沦为外在目的如金钱、财富等手段,使“人是目的”的现代性设计成了漂浮着的名称,陷入“空虚的形式主义”(黑格尔语)。
“人疏离自然”的“现代性”道德认同只有人本身才有“内在价值”,一切非人的自然仅在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意义上显示其工具价值,即自然只是可为人类所利用的自然都只是“资源”(resource),而不是根源(source)。然而,作为工具性道德而言,认同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的“现代性”道德具有形式合理性或抽象的普遍性,提高了行为及结果的可计算性,却忽略或漠视实践或行为的实质性证实。“人疏离自然”不仅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敌对和疏远,也无法体验到真正的自我,疏离了自己。弗洛姆对“人疏离自我”给予精辟的理论分析,认为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中,人变得越来越自我疏离,这种孤立感导致人们潜意识下渴望与他人结合、联系,“逃离了自由却投入新的偶像崇拜的罗网。”弗洛姆认为人的诞生就意味着脱离自然的襁褓,挣脱自然的束缚,在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成为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人。在前现代社会,通过理性建构的社会伦理没有剪断与自然界连接的“脐带”,直到颠覆传统的“现代性”道德价值观中,人不仅挣脱大自然的桎梏,割断了原始的脐带,随着社会伦理关系的功利化,人也越来越自我疏离。“疏离,就意味着被切断了所有跟外界的联系,这样人也就不能发挥任何人类的力量。因此,疏离也就意味着无助,意味着不能主动地把握这个世界——事物跟人。也就意味这个世界可以毁灭我,而我实际上毫无还手之力。这样,疏离就成为嫉妒焦躁的根源。”[11]12在疏离了自然又缺乏社会归属感的现代社会道德秩序中,人的根本性孤独使人产生遗弃感,被剥夺感、孤立无援,有着因疏离自然而产生的不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的感受。
孤独感与空虚感总是形影不离。除了现代人的根本性孤独之外,充斥人心灵的空虚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只要一个人生存于世都会不同程度地体验到空虚,但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才有极为普遍的空虚感,甚至有学者称这个时代为“空虚时代”(吉尔·利波维茨基语)。当前境况下,解决空虚的办法往往是通过“现代性”生活方式中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消遣方式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殊不知,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会带来更深的空虚。因为这种消遣“不是去发现别人和接触地球。旨在逃避空虚的现代性‘消遣,实际上助长了这种空虚。”[12]86其实,早在现代性的思想发展历程的源头,叔本华就开始了对于现代性的研究与反思,揭示了现代性给人们带来难以负荷的重担。“人生是一种迷误。因为人是欲望的复合物,是很不容易满足的,即使得到满足,那也仅能给予没有痛苦的状态,但却带来更多的烦恼。这个烦恼的感觉是人生空虚的成因,也直接证明生存的无价值。”[13]94叔本华对“空虚”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从意志哲学意义探讨的,也触及到一些道德心理学问题。
叔本华之后,尼采的“虚无主义”、艾略特的“空心人”、弗兰克的“存在的空虚”、罗洛·梅的“空洞的人”等都是思想家们对现代人的“空虚”问题所作出的深刻的分析和概念界定。比较而言,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从道德心理学方面更为明显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现代社会中人对自然的兴趣越来越变成了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兴趣,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主宰、控制和操纵自然,虽然在追求经验的、机械的、可测量的方面蒸蒸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使自然已在极大程度上变成了非人格的(例如科学中),变成了为了聚敛金钱而加以盘算的对象。这种“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现时代的人成为“空洞的人”即内心空虚的人。这种空虚感不仅是指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也指他们对于自己所感受的东西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空虚感反过来会更加疏离自然、他人和自身,无法跳出主观主义思维的逻辑“魔圈”。“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空虚时(正像许多现代人的情形一样),他对周围的自然的体验也是空虚、干瘪、死气沉沉的。这两种空虚的体验乃是同一种生命荒芜贫瘠状态的两个侧面。”[14]50罗洛·梅认为解决现代人普遍的空虚问题,需要人重新建立与自然的内在关联。作为人类存在,在自然中有我们的根,当我们把自己关联于自然,我们不过是把我们的根重新置于其故乡的土壤中。
三、生态伦理的道德心理治疗
实际上,生态危机既是人对自然渐趋疏离的道德观念危机,也是深层的道德心理危机。以往,人们更多关注自然价值观的道德变革,却很少提及关于人对自然的道德心理分析与探讨,以致把生态伦理理解为过分追求言说的自由和境界的高远,而“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通过分析“人疏离自然”的现代性及其道德心理困境,反衬出生态伦理使社会伦理向自然伦理拓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及其道德心理根据。生态伦理只有突破“现代性”道德视域,将伦理观念扩展到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实践伦理观念的变革,促使行为者采取正确行动的心理基础和心理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具有道德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最终会对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触及人的利益”[15]2人的利益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带来的显性利益,更需要超越现代社会利弊性的偏爱秩序而生成的生命价值的整体,如梭罗的“扩展的共同体”、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和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等等。这种生命价值的整体不局限于人类本身,也包括支撑人类生命价值的自然界,给人类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担保,使人类不再执迷于追逐物质利益的心理,开始关注人的心灵健康,探寻宁静的与自然和谐共存幸福生活。
支配现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道德以普遍理性概念为知识论依托的逻辑证明和经验证实方法,寻求个人美德、人际伦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普遍伦理正义,却很难深入到以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生态伦理。目前被公认为“后人本心理学”最重要的心理学家肯·威尔伯认为,完全通过理性认识世界形成“理性私我”,拥有一个控制、分析思考甚至制伏自然界的欲望。在“理性私我”的道德价值观中,“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孤立的、贫乏的、低级的、短暂的——不管怎么说,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无从分辨是非的——所以可以理解,他们感到理性私我的职责便是将自身从这张野蛮的、不道德的网里解脱出来。私我的使命是脱离自然之网。因此这一理性私我经常自称为解脱后的自我、无牵无挂的自我、独立自主的自我等等”[16]254。尽管在普世伦理的视域中“现代性”道德是一种较为先进和普泛的道德资源,但由于疏离自然,存在人与自然伦理价值观盲点,把人和人类视为特殊而高贵的生命存在,将一切非人类的生物和生命看作是实现人和人类目的的纯粹手段或工具。如果这种纯知识论的描述意义上的现代伦理不加限制地转化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人类自我欲望和自我行为的评价标准或价值辩护,那么它就极有可能成为现代人类贪欲行为的托词、甚至是掩盖人类恶行的自辩词。
诚然,理性是人类在推理、演绎、归纳、计算方面显示出来的能力。在理性主义的解释中,理性是人的最高认识官能,利用各种价值工具把自然科学体系中的理性运用到一切人文学科中来,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知识。但受科学技术等理性化知识对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伦理样态越来越理性化,压抑了人的正当的自然情感表达与疏通,带来现代人所特有的道德心理问题,如孤独感、同一性危机、权威性和意义性等等。[17]5377殊不知,这些心理问题的产生都不同程度地与“人疏离自然”的“现代性”道德密切相关,亟需突破人与自然伦理价值观盲点的生态伦理的“哲学治疗”“哲学的治疗”也叫“治疗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其基本意向性指向对各种生存之病的诊断与治疗,以抗衡存在境遇深处的病症威胁,削减人身上的文化附加物,追求人的真正幸福生活。在西方哲学中晚期希腊哲学、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尼采、法兰克福学派、晚期维特根施坦等的相关理论都能够归为“治疗型”哲学。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包含了浓郁的“人生治疗”之基本意向性。。
鉴于此,要想消除“现代性”道德在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上的价值观盲点以及所带来的道德心理困境,生态伦理就不能完全沿用理性方式认识自然,更需要情感的方式理解和体悟自然,才能全面认识人类与自然内在联结的整体,这种生命价值的整体促使人与人之间走出“物的依赖性”,走向自足的幸福生活。相对于理性的认知方式,情感是人们对自己与周围世界(情感对象)所结成的价值关系的感受和评价,包括人对人的情感和人对自然的情感。因此,生态伦理理论并不仅仅是通过理性应对生态危机所确立的人类对待周围自然环境的一系列道德原则、规范,更需要从情感中理解、体悟和感受自然的生命和灵性,治疗人疏离自然的诸如孤独、空虚等道德心理困境,触及到人的内在利益,体现出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和实践意义。生态道德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如果没有自然伦理观念进入人的情感生活及健康心理建构使人的心灵丰富、充盈和活力,那么它们依然外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停留在社会伦理生活的表层。生态伦理的道德规范在人与自然潜在的情感联结的激发下,得到主体的道德认同,形成具有持久的稳定的生态学的道德心。生态学的道德心不是外在强加于人的,而是人内心生活丰富而充实的自觉生成。在这种境况下,如果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具有生态道德心的人犹如自身受到伤害,使保护自然变成对自身利益和权益的维护。生态道德心就是美德伦理的一种体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伦理学反对把所有的道德话语归结为关于‘应当的律法,反对把所有道德心理都整饬为‘出于义务或责任的心态,而是承认情感、渴求等非理性因素的实际存在及其正面作用,这本身就是对于道德心理之日常性和真实性的一种探求。”[18]这充分地解释了保护自然的道德心理意义,表达了我们经常听到的既简单又深刻的道理“爱自然就是爱自己”。
在过度追求理性和效率的“现代性”社会中,人对自然的情感本身就具有道德存在的前瞻意义、导向功能和治疗作用。如果说理性作为人本身的先天形式在因果关系中奠定了道德的社会基础,那么,情感作为人本身的自然属性在同情心中奠定了道德的自然基础。情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也是人对自然联结的情感纽带和精神空间。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灵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强烈情感联结的生态潜意识(ecological unconscious)。生态潜意识是人对自然的内隐态度,人类固有的天性,在“现代性”社会形成过程中一直被追求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道德所掩盖和抑制。“生态心理学的目标是,恢复受抑制的生态潜意识的疗法,唤醒固有的、在生态潜意识之内的环境交互性意识,寻找治愈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更多更根本的疏离。”[19]161相对于生态伦理的显性规范,生态心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深入到人类心理的深层,有利于新道德观念的生成。
结合生态心理学的观点,生态伦理确立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保护自然不仅关注人类的显性利益,更应重视通过人对自然的情感联结,开掘人自身的精神潜能,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使人从孤独、空虚、焦虑走向内心的充实。生态伦理的自然价值观强调人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动植物乃至于宇宙万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如果我们能这样理解主体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便不会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我们会认为动物植物以及一切自然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内在价值和权利。”[20]120人不具有绝对主体性,而是置身于“一群主体”之中,因而人类不能只从自己的主体性出发去确立目标,而必须在与不同主体的交往之中去确立自己的文化目标。在与不同主体的交往中,“重新发现我们与周围实在的关系……我们不再孤独了!我们拥有了所有这些以前不知道的亲戚!”[21]234如梭罗所经历和体会到的:“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到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最忧悒的人也一样。”[22]115116生态伦理的认知观念,只有结合人对自然情感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才能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治疗人疏离自然的道德心理问题,客观表明人类对自然伦理的内在需要与真实渴求。
参考文献:
[1]阿尔·戈尔.频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M].陈嘉映,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2]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3]陈鼓应.失落的自我[M].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3.
[4]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M].陈永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
[5]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M].王雷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7]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8]杨韶刚.道德心理学的哲学思考——论心理学与伦理学的会通与融合[J].心理学探新,2004(3):1925.
[9]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1997(3):4553.
[10]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1]弗洛姆.爱的艺术[M].赵正国,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
[12]莫林,凯恩.地球·祖国[M].马胜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3]叔本华.生存空虚说[M].陈晓南,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14]罗洛·梅.人寻找自己[M].冯川,陈刚,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5]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肯·威尔伯.万物简史[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17]夏洛特·布勒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导论[M].陈宝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8]李义天.道德心理:美德伦理学的反思与诉求[J].道德与文明,2011(2):4045.
[19]吴建平.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0]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1]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2]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