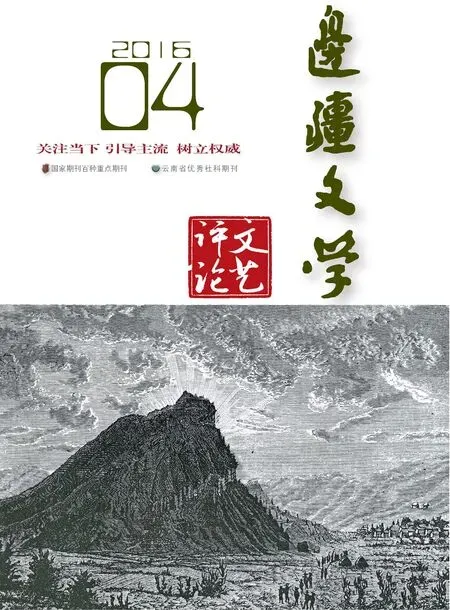消失的祖父,找不回的历史
——胡性能中篇小说《消失的祖父》读后
2016-11-14◎李英
◎李 英
昭通文学研究
消失的祖父,找不回的历史——胡性能中篇小说《消失的祖父》读后
◎李 英
主持人语:昭通籍作家胡性能是云南比较有实力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消失的祖父》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四期头条推出后,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期选编两篇有关《消失的祖父》的评论文章,以期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青年学者李英的文章以王小波的《寻找无双》为参照旁证,追寻隐藏在《消失的祖父》中的文本深处的关于历史、社会、人生的内涵。结论就是:“祖父注定要消失,历史注定找不回。”青年研究生程红丽则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层面解读,认为:“整篇小说的审美基调就是人的孤独与无奈,其创作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雄壮的主题,但是有作者对生命深处刻骨铭心的体悟,对个体心灵细致入微的关怀,而这一切归结于人的一生都在守护孤独。”两篇文章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论述的过程中去殊途同归,都是在探究文本之中的哲学旨意。
一
没有读到《人民文学》2016年第四期之前,我先上了一下《人民文学》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胡性能中篇小说《消失的祖父》节选,还有胡性能的创作谈,标题叫《胡性能:小说是生活的某种可能或延伸》。创作谈很有意思。讲的是一段错误的记忆,或者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不可靠的故事。2014年冬天,作者胡性能先生跟一群人组团去台湾,一个叫“老李”的人在台北街头乱扔烟头,被胡性能嘲讽了一番,又将扔掉的烟头重新拾起来。一年多以后,这些人再次相遇,胡性能再次提起老李乱扔烟头的事,被老李否认。后来,胡性能通过种种办法,想要证明这件事发生过。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老李没有在台北街头乱扔烟头,不仅如此,老李根本就没跟他们一起到过台湾。一个人的记忆出问题了,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所有人的记忆都出了问题,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文章的最后,胡性能说:“也许多年以后,与老李在台北所经历的那个黄昏,会成为我小说中的一个片段”。如果胡性能先生的记忆没有再次出错的话,那么,“一个片段”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件事所产生的“某种可能或延伸”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就是《消失的祖父》。
多年前读王小波的《寻找无双》,不知所云。王仙客到长安城里寻找未婚妻表妹无双,长安城里所有人都说没有这个人。他通过各种逻辑推理,力图证明无双是存在的,而且就住在宣阳坊里,都流于失败。最后不得不抛开逻辑,通过非常手段,才找到了有关无双的线索。这个故事十分怪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往往会选择遗忘掉那些于自己不利的事情,从而造成集体失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历史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胡性能的《消失的祖父》,跟《寻找无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唯一不同的是,王仙客在找到了无双的侍女彩萍后,成功治愈了宣阳坊诸君子的失忆症,得到了有关无双的准确信息,而《消失的祖父》中的我,既没有找到祖父,也没有准确地知道他早年的真实身份,一切的一切,依然是个谜团。无论是宁国强,还是聂保修,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所指。
福柯认为历史从来都不是延续的,不过是话语的堆砌。福柯的意思应该是指强权话语对历史真相的掩埋。历史,永远只属于过去时,既不能从话语中还原,也不能从行动中还原。“我”找到了安青,听完了她的讲述,读到了祖父生前写下的申诉材料,还找到了他的上线黄敏文,但一切都是徒劳。历史,是不可能被找回、被理清的。很大程度上,祖父跟他那张穿着国军上校服的照片一样,不过是一个符号。从一个符号出发,展开的一系列找寻活动,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另一堆符号。
二
如果《人民文学》2016年第四期不把《消失的祖父》刊发在“中篇小说”栏目的头条,或者说《人民文学》不将这个文本定性为小说,那么,我很有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篇长散文来读。整个文本中,除了“丹城”这个地名有虚构的嫌疑之外,其它任何一个名词都显得那么真实。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虚构的文本。从这个意义来说,《消失的祖父》无疑是先锋的。但它除了对形式的探索与摆弄之外,对文本的内容也近乎苛刻。
1983年,“我”的祖父,一个七旬老人离家出走,并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可他的一生却难以盖棺定论,他给家庭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比如“我”的父亲受尽屈辱、晋升无望),却又很有可能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正是因为有宁国强同志传递出来的准确信息,我党领导的云南地下武装‘边纵’,才将从昆明南逃的国民党部队狙击在了元江北岸”)。然而,作为孙辈的“我”,这一切都难以考证。
祖父消失了,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每个人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整个文本的重点不在于“消失”,而在于“祖父”,在“祖父”这个符号背后,隐藏着的是千千万万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人。关于祖父的一生,是通过“我”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我在寻找他消失前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寻找祖父的动机,除了对“我”对他的生平充满了好奇,以及弥补我以前“太年轻,贪玩,渴望自由,梦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与祖父包括父母的交流都很少”的遗憾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还原历史的冲动。尽管大多数人都有还原历史的冲动,但历史是不可能通过话语的方式被还原的,所以“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无用功。
整个文本都在讲述着“我”如何寻找消失的祖父,以及在这过程中获得的线索。从小标题看,整个故事通过“二O一五年:照片”开始回溯,除“一九五O年:逃离”和“一九六六年:回国”是更靠前的回溯外,其它都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来写的,最后以“二O一五年:补记”的形式收尾,看上去脉络十分清晰。但事实上,整个文本在时间概念上都是十分混乱的,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混乱。
在“二O一五年:照片”中,“我”通过从安青那儿得到的祖父的唯一一张照片开始,不仅回忆到了祖父离家出走后“我”父母的情形,还追溯了“我”小时候大姑妈和父亲对祖父的态度,以及祖父从缅甸战场负伤回国疗养的一些事情。所有的记忆都是些碎片,难以粘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这让本文有了一些意识流的感觉。
事实上,在每一个小标题下面,其内容都是零碎的。标题中的时间,不过是“我”的意识流开始的时间,整个文本都在现实与虚拟、过去与现在之间穿梭着。
三
我的意识流是不可靠的。相比之下,安青的讲述要可靠得多。然而,安青的讲述也属于过去时,因为在我开始讲述“消失的祖父”之前,她“已经作古”。“我”在转引安青的讲述时,添加了大量自己的想象。
“一九五O年初,跟随部队进入缅甸的那个夜晚,祖父住在临江的一个傣族村寨里。竹楼上面四处漏光,竹篾的隔板色泽暗淡,弥漫着经年累月的烟火气息,大地退烧,气温变得有些凉,好在没有什么风。屋子正中的火塘已经熄灭,剩下白色的灰。”
“中缅勘界几年前就完成了,229号界碑在对岸一棵合抱粗的榕树旁,隔着界河远远就能看到。祖父从一道数十米高的山崖上滑下来。界河的两岸,有河水经年冲刷留下的沙渚,上面种植着密集的甘蔗。春天的打洛,气温像夏天一样炎热,祖父藏在甘蔗地里,看那些叶片垂落下来,一只蚂蚁爬到了头顶的叶片上,走走停停,充满诱惑。”
这些看上去准确无误的描写与叙述,无不在说明它们的不可靠性。1950年,祖父跟随国民党残部逃入缅甸,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生命危险,生死未定,前途未卜,而且又是晚上,怎么可能对傣族竹楼有那么细致入微的观察?就连竹篾隔板的色泽,火塘里灰烬的颜色都观察得那么仔细。1966年,归国途中的祖父,对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心中充满牵挂,充满了新奇,也充满恐惧,如同丧家之犬找寻昔日的主人,试问,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比量界碑旁榕树的大小,哪有心思观察甘蔗叶上蚂蚁是否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是藏在甘蔗地里的祖父。这就是说,这些话从“我”口里说出来时,已经被加工过了的。这些话,最初是祖父说给安青听的,安青又再讲给“我”听,“我”再转述出来。祖父的原话是什么样的,根本就无从考证。也就是说,安青和“我”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与想象,进行了加工,不仅添加了许多细节,还有可能删除了许多我们自以为无用的内容。一切就变得更加不可靠了。就像《胡性能:小说是生活的某种可能或延伸》中,在老李随地扔烟头之前,也有许多准确、生动的细节描写,远远近近的灯光、高楼、斑马线、等红灯的摩托车以及摩托车启动时的声响,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这些细节所要指向的事物是不可靠的,这些细节也就在根本上被否定了。如果胡性能先生在创作谈的最后,不用最有力的证据——其他同行的人也否认老李一起到过台湾、在台湾拍摄的所有照片上都没有老李,等等——道出这是一个错误的记忆,那么,这就不再是一篇创作谈,而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用最准确、最生动、最细致的语言来讲述一个最经不起推敲的故事,非高手不能为之。
四
不得不承认,胡性能先生具有很强的写实能力。正是这种超强的写实能力,才会让我差点误将《消失的祖父》当成散文。
一直有个观点:小说中所呈现的故事可不可能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可信。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一样,谁都知道不可能发生,但我们都愿意相信。要让虚构的事物令人信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写实的能力。
昆明弥勒寺、弥勒寺附近的云南党史研究室、大观河、水塘里盘旋的海鸥、五一巷、师范学校的教工宿舍、吹箫巷以及昆明西山南麓的金宝山公墓,这些昆明人耳熟能详的地名与事物,不仅符合文本内部的真实,还符合生活的真实。真实到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它们极大地掩盖了“我”寻找祖父这件事的虚构性。这种真实,与祖父的故事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关于祖父的过去,安青的讲述与回忆也不是全都经过了加工。比如文革期间的标语,每一句话都很符合当时的语境。这是因为这些标语都贴在昆明,而安青是目击者。这些都是写实的部分。然而,这些实的部分,最终都是为了“虚”而存在的。谁能够证明祖父回到昆明后留意过那些标语,而且记忆深刻?作者的写实,其目的是为了务虚。在实与虚的交替、杂糅中,祖父消失得更彻底。
五
相比起父亲来,“我”对祖父的态度看起来要客观得多。父亲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希望祖父真的是潜伏在国军里的地下党特工,这样“他背了一辈子家庭出身不好的负担不但可以从此卸下,而且还可以让他扬眉吐气”,同时他又不希望祖父是地下党特工,因为这是那样的话,他“得为祖父回来之后他的冷漠和不孝负责”。但事实上,“我”的客观也是一种假象。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在寻找祖父之前,心里就有了一种预设:祖父是潜伏在国军里的地下党特工。更何况,“我”还坦陈过,“之所以重新想起找寻祖父,完全是因为中风的父亲……我知道祖父如果真是潜伏在敌人阵营的地下党,对父亲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我才会去云南党史研究员查阅档案,才会在跟安青谈话时有意往这个方向引导,其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设想。
“没有谁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清晰而准确的还原”,更没有人能对历史进行清晰而准确的还原。人生不能还原,那是因为记忆会出错;历史不能还原,那是因为历史是由话语组成,这些话语,会左右所有人的记忆,会让真实存在的事物消失,会让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无中生有。
云南省党史研究研究室的大姐不能帮助“我”,是因为她管理的是一堆话语,这些话语中没有关于祖父的记载,而黄敏文写的那份证明材料不足以证明祖父的地下党身份,“还需要其他人的证明”。其他人的证明,说白了,也不过是一堆话语。记录历史的话语,总是根据某种需要进行过删减、增补和改装了的。安青也不能帮“我”,在她那里,要将历史变成话语,与祖父的身份无关,记录得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而这不是“我”所需要的。祖父亲手写下了申诉材料也不能帮我,如果这些材料有用的话,祖父也就不会消失了。并不是任何话语都能够成为历史,还要经过筛选。
当祖父回国后,在大坪农场见到了他当年的上线黄敏文时,他却不肯为祖父证明其身份。这完全是出于一种对权力的畏惧,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右派,而祖父又跟随国军在境外生活了十多年。这样的证明一出,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黄敏文后来肯写证明,是因为他恢复了职务。然而,时过境迁,这份证明已经不能被纳入历史的话语体系当中。
最有意思的是,当祖父消失多年以后,有关单位给他送来了一笔不菲的钱,由“我”父亲继承。这部分内容,在文本中着墨不多,一句话就带过了,却是点睛之笔。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这笔钱为什么不出现在祖父彻底消失之前,而是在之后?历史之所以不能够用话语还原,是因为权力在利用话语掩盖历史的真相。中国自古就有修史的传统,但这传统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前朝历史由后朝来修。后朝史官在修史的过程中,一切都为了当朝服务,对当朝有利的,大书特书,不利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进行美化。比如刘季见蛟龙而生刘邦,比如刘邦斩蛇起义,又比如“我”和父亲力图证明祖父是国民党特工。不同的是,“我”和父亲的权力不够大,不能任意杜撰或篡改历史。
祖父注定要消失,历史注定找不回。离家出走,不过是将抽象的“消失”具体化而已。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