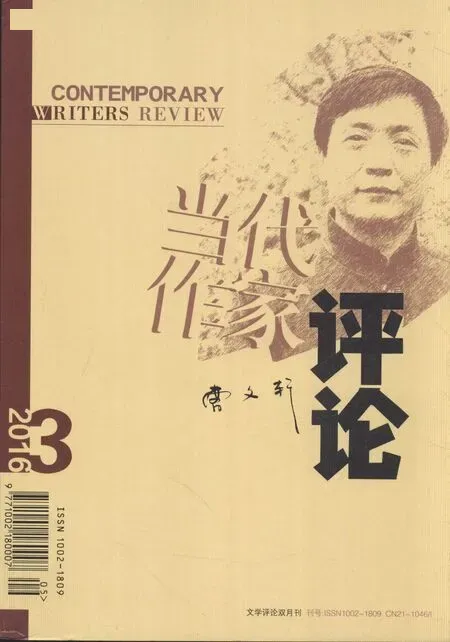晋东南:赵树理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一个中介
——并质疑赵树理系“农业问题专家”说
2016-10-27郭帅
郭 帅
文学史研究
晋东南:赵树理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一个中介
——并质疑赵树理系“农业问题专家”说
郭帅
建国后的赵树理,与柳青、周立波等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将农业合作化当做“农业问题”来考察。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学界对此研究得较为充分。对赵树理如何形成这种独特的认识,目前的研究却并不充分。许多因素,共同影响了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其中,晋东南地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未引起广泛注意。
晋东南*晋东南所辖主要为今长治、晋城二地级市。作为建置,主要指1958年所设“晋东南专区”,辖1市6县,即长治市、武乡县、沁县、壶关县、晋城县、阳城县、黎城。建国前后亦称太行山区、长治专区。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是赵树理的故乡。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入京之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活动在晋东南。一九四九年到文革前夕,赵树理平均每年有三个月时间用以下乡,总共下乡二十次,其中,十八次在晋东南。*据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我们考察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假如不重视“晋东南”对他的具体影响,则难以称得上全面客观,甚至会出现谬误。
一、晋东南地理的特殊性
赵树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所有言论,几乎都离不开晋东南。可以说,晋东南是他观察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重要窗口。与其他省市相比,甚至与同纬度地区相比,晋东南地理具有高度特殊性。
1. 晋东南是抗日期间最大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也是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八路军总部约一半时间设在晋东南武乡沁县一带,*据李志宽、王照骞编《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转战华北期间》整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华北局也长时间驻扎此地。建国后,国家军政高层高度关注晋东南(太行山区)地区,时时予以政策上的支持。
2. 晋东南自一九四二年后便无中等规模以上战事,共产党所进行的“建党、建军、建政”等根据地建设成效显著。*据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四章《根据地的建设(一)——建军、建党、建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在农村建设中,突出表现在两点:
(1)互助组制度相当发达,建国前已经发挥出巨大优越性。晋东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互助组,闻名全国的李顺章互助组建立于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七年,“贫农有80%以上上升为中农”。*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土地志》,第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一九五一年召开“长治专区互助组代表会议”时,长治地区要求“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因为晋东南大部分互助组已经有十年以上历史,有的村,互助组甚至党支部宣布解散。*转引自马社香:《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第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也就是说,在全国多数地市没有建立互助组以脱贫的时候,晋东南的互助组已经到了非革新便成为“富农俱乐部”的地步。
(2)土地改革进行的极为细致彻底,“消灭”了地主阶层。
3. 基层干部优势。作为老根据地,在战争与土改期间,以牺盟会、自卫队、村选运动等,锻炼起了大量基层干部。晋东南地区的土改,尤其锻炼了一大批乡村一级干部。由于长期处于大根据地,这批干部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较高。*如西沟村人口1949年为1148人,可查姓名的先进干部、党员、劳模、烈士等逾40人。据张松斌周建红主编《西沟村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农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对党政任务上心。
(1)群众组织发达,组织性纪律性极高。党与军队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措施,充分发动群众,甚至出现半军事化村落,“每个干部、党员、教师、农村知识分子、地主和农民,都在努力适应混乱的社会和他们所处政治环境的快速变化”。*〔澳〕大卫·古德曼:《晋东南的革命》,《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第261页,田酉如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妇女普遍参与劳动生产,妇女工作开展早,积极性相当高,著名劳模申纪兰即为突出代表。全国范围内的“男女同工同酬”,是首先从晋东南开始的。
5、农耕条件优越,种植业相当发达。一直以来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太行山区=太行山山区,认为太行腹地土壤贫瘠,适合打游击战,不利于发展种植业。这是臆测,“太行山区”与“太行山山区”分明是两种概念。晋东南发展粮食种植业的条件,恰恰比同纬度与山西境内很多地区优越:
(1)晋东南主要地形为盆地、河滩地、山地,山地改造较为成功。一般人对“山地”存在误解,认为山地耕种面积小、土壤贫瘠——这是庸俗地理学的认识。“山地”是地形概念,与耕种面积、土壤质量是平行关系而没有决定关系。具体到晋东南,由于山间梯田的营造,有的山地实际耕种面积大于相同面积的平原地形,其土壤条件也十分优越。
(2)该地区土壤绝大部分为褐土,晋东南边缘部分为草甸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中国土壤图》,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褐土“可耕性好,持水能力较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农业志》,第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是山西主要的地带性土壤,也是农业利用上最好的土壤”*⑧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地理志》,第243、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相比之下,晋东南土壤种植力高于同纬度大部分地区。这种土壤非常利于农作物密植——晋东南植物之茂盛浓密,非亲见者所不能想象。山西是中国“煤都”,亦可见其从古至今植物之繁茂。
(3)位于迎风坡,降水量充沛,水文条件相当优越。据《山西通志》,晋东南年降水量为六百-七百毫米,高于绝大部分同纬度地区。⑧同时,地表水地下水丰富。晋东南是山西全境水浇田比例最小的地区。*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农业志》,第38页“山西省耕地类型构成统计表”,北京,中华书局,1994。
另外,据《山西通志·地理志》,晋东南光照、热量等条件也较良好,在同纬度地区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6. 农耕传统久远深厚,农业相当发达。
(1)晋东南地区轻重工业均不发达,但农耕极为发达,是传统的农业大区。相传炎帝文明发源于此,晋东南中心长治市的老顶山今立有世界最高炎帝铜像,其双手所托举的,便是三株麦子。当地历届政府对农业发展极为重视,常常组织生产丰产竞赛,表彰劳动模范、先进互助组,李顺章、郭玉恩等人,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得到先进劳模等称号。*②③④马社香:《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第71、111-112、114-11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2)作为传统农业地区,晋东南人多地少,这决定了他们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精耕细作,使晋东南农业理念先进,常开风气之先,成为“出经验、出典型”的地方。建立中国第一个互助组,是村民李顺章的主动要求。建立中国第一个合作社,也是晋东南地区互助组的自发要求。西沟农业社在五十年代初“提出了四种方法开展封山育林的建议”,“创全国之先”。②川底村合作社则以“不煮大锅饭”的劳动管理创全国之先。③羊井底合作社则开创“多种经营”的先河。④赵树理概括为“虽然不能说事事走在前边,至少也可以说事事不甘落后”。*《新食堂里忆故人》,《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1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3)农业能人多、模范多。这些“农业明星”技术先进,善于发明革新农具,既吃苦,又钻研。不仅常常得到晋东南地区的表彰,在全国范围内皆有影响,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届“爱国丰产金星奖章”一共颁给四人,其中两人出自晋东南,而且两人是同乡邻村。
(4)农业生产效率高,单产量高而稳定。晋东南人多地少,总产量不乐观,但单产量走在全国前列。据《长治市志》,一九四九年该区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为九十四点五公斤,一九五二年为九十四点八公斤,一九五七年为九十五点五公斤,一九六二年为一百一十三公斤。*长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长治市志》,第152页,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据《安阳市志》,同纬度的河南安阳市,一九四九年为四十五公斤,一九五二年为六十三公斤,一九五七年为六十四公斤,一九六二年为五十九公斤。*河南省安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阳市志》(三),第112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据《聊城地区志》,同一纬度华北平原上有“五百里沃野”美誉的聊城,一九四九年为七十七公斤,一九五二年为九十五公斤,一九五七年为一百零一点五公斤,一九六二年为五十九公斤。*山东省聊城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聊城地区志》,第13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据《平顺县志》,郭玉恩的玉茭亩产在一九五一年就达一千五百八十斤,*山西平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顺县志》,第419页,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至今仍是非常高的数字。同时,晋东南地区粮食单产稳定,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依然保持较高的亩产。

二、晋东南地理对赵树理认识合作化的影响
以上是晋东南较为突出的地理特殊性。当然,以中国之大,找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完全代表中国。但是,有些地方的特殊性较小,而普遍性较大,以之为典型代表,也并非不可。然而说到晋东南,大概中国再难找到这样“五行具备”的地方了。其特殊性过于突出,致使该地区的农业合作化也具备较大的特殊性。赵树理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下乡于斯的晋东南人,这些特殊性,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
1.晋东南建立合作社的优先性和必要性,影响了赵树理对初级社的热烈鼓吹和对高级社的热情呼唤。
晋东南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首先影响了赵树理在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的表现。一九五一年,赵树理直接接触到晋东南地区建立合作社的三个特殊性:晋东南长期无战事,社会稳定生产有序,大部分农民已脱贫,部分农民富农化;互助组已经发展烂熟,升级势在必行;李顺章等劳模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呼吁建社争先。
掌握了这些情况的赵树理,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特别活跃。据当事者回忆,他以“有血有肉的农业社故事,鼓动了参会者的热情”,以致于主持会议的陈伯达“觉得赵树理的话讲的太多”,甚至赵树理与陈伯达抢话,“你说你的,我讲我的,有点小尴尬”。*③马社香:《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第61、15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这次会议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合作社,赵树理如此亢奋,说明他极其赞成全国建社。然而对晋东南发展合作社胸有成竹的赵树理并不知道,此时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仅没有见识过他鼓吹的合作社,连互助组的优越性都没有品尝过。
2.晋东南的全国第一批初级合作社的成功,直接影响了赵树理对《三里湾》的构思,使他将合作社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并热情描绘了“高级社”的蓝图。
著名记者范长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亲往赵树理《三里湾》原型川底村考察其第一年合作社的成果。他写道:“单位面积产量是大大提高了……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产量是四百五十斤……比一九五零年每亩多产一百一十二斤”,比同村强单干户亩产超过44%。在亩产最高产量方面,“每亩产金皇后玉茭一千零五十斤”,比单干强户多一倍。在副业方面,副业收入增加了388%。在扩大生产投资方面,增添了大量牲畜和工具。因此范长江总结道:“农业生产合作社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满足了农民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要求。”*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政协》1952年3月11日。这是川底村的情况,而西沟等村更加乐观。正是基于这些实情,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处处领先于当时的政策,进行了诸多超前性和预见性的描写。欣喜于晋东南发展合作社的优越性,赵树理笔下的《三里湾》溢出了田园牧歌气氛和浪漫主义色彩。
可以说,晋东南合作化具有超前性,《三里湾》的描写则更超前一步。事实上,此时晋东南的第一批合作社,已经不与全国的合作化进程同轨,甚至发生了脱轨。因为晋东南合作社发展太快,远远地将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甩在了后面,成为一个模范遍地和经验丛生的圣地。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并不是特别理想。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关于合作社发展的速度有数次反复。当《三里湾》正在《人民文学》连载的时候,各地合作社出现了种种问题,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以《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的形式提出限制合作社发展过猛的问题,毛泽东又在一九五五年三月提出著名的“停、缩、发”三字方针,对于华北老解放区主要坚持“缩”字诀。当“收缩风”刮到晋东南,西沟等村拒不收缩,而是“继续兴旺发达”。③赵树理着眼于晋东南,认为“《三里湾》可以写到高级社,也可以写到公社”。*《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59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3.晋东南高级社的“超速”,影响了赵树理对全国高级社浪潮的态度。
一九五六年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风行全国,提倡办高级社和大社。一九五六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建国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八),第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一般我们认为高级社大潮是从《高潮》和“四十条”之后开始的。然而,在这两个文件之前,河北省和山西省,早已基本上完成了全省合作社的高级化。
山西省委决定从一九五五年秋开始试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在全省广大的农村中,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社员的觉悟程度的提高,已具备了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而另一方面按土地和劳动付酬分配制度,已经日益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罗汉平:《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第28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从这里看,山西省委对“高级化”的决定,是出乎他们本省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一九五六年三月底,全省百分之九十七点八九的农户加入高级社,继河北省之后第二个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第154-1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具体到晋东南,则更早。
赵树理在此时写了《进了高级社日子怎么过》《给长治地委××的信》与《“春”在农村的变化》等,表达了对目前高级社出现的问题的看法以及喜悦心情。与赵树理一九五九年后的言论相比,此时赵树理的看法,其根本出发点在于顺从山西省委决定,维护高级社的发展。
4.晋东南开展大跃进运动的便利,直接促使赵树理在一九五八年前后迎合大跃进。
(1)赵树理支持水利大跃进,是因为他看到了长治地区兴修水利的状况。“越乡越县互相支援兴修水利在全国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事,而在这个地区(注:长治地区)则是从一九五六年就开始的。”*《下乡杂忆》,《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3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赵树理回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在沁水、高平两地看到高级社发挥出来的优越性,就包括“兴修了一些小型(高平近中性)水利”。赵树理说:“我对这次飞跃的发展是很兴奋的。”*⑦《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80、38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由此可知,赵树理对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兴水利的支持,是来自于他对晋东南一九五八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兴修水利的观察。
(2)赵树理部分地支持大炼钢铁,更是因为他看到了晋东南因为大炼钢铁而拉动的财政收入。一九五九年,赵树理根据自己所在的阳城向邵荃麟汇报:“在工业方面,除了大搞钢铁时间,因技术赶不上出了一些废品已由国家照顾补贴外,其他方面也都丰产……铁在去年虽然有点亏本,可是总产量仍超过以前若干倍,而煤因炼铁的需要也大大增了产;硫磺也因国家的订购而增产一倍。”*⑧《给邵荃麟的信》,《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0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因为晋东南有一条庞大的“煤铁硫矿产组合区”,所以别的省市苦不堪言的炼钢运动,在晋东南则能大大拉动经济发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赵树理在朝鲜看到《朝鲜日报》登载的阳城炼钢放卫星的消息,他激动不已,一边向朝鲜作家现身宣传,一边“用文字交织起来歌颂了一通”。⑦他回国后,又亲自到阳城,亲眼所见,终于写在了给邵荃麟的信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别的省市因为大量抽调劳动力炼钢而耽误秋收导致一九五九年歉收时,晋东南因为妇女早已“同工同酬”,“秋粮大部分是解放了的妇女收的”,⑧所以一九五九年晋东南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反而是一个丰收年。
(3)赵树理对粮食丰产跃进乃至浮夸的欢迎,更是受到了来自他亲眼所见的事实的影响。其实赵树理很早之前就对农业“丰产”很感兴趣,比如他看到一九五四年平顺县在尚不科学的情况下,“玉蜀黍从三百斤增至一千五百八十斤、棉花从百余斤增至千余斤”。*《谈六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杂感》,《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3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在赵树理的意识中,农作物成十几倍的增产,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当面对产量浮夸时,他一开始并没有怀疑。晋东南土壤条件优越,植物自古茂密,当地农民又喜欢密植,赵树理描述在大跃进时看到一个玉米种得很好的社,感到“好像进了竹子园,有些玉米密到每亩万株”*《在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39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赵树理对每亩万株的玉米密植感到欣喜,也是基于对晋东南农业条件的熟悉,作出了先入为主的误判,他甚至为粮食丰产向社写建议信。*《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8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5、一九五九年后,赵树理对合作社和公社进行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大都受到了晋东南合作化问题的影响。晋东南发展农业合作化具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假如拥有如此优越条件的合作社都出现了危机,那么,那些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晋东南的农业社又当如何?——这可能就是赵树理一九五九年后对失望于合作化的认知逻辑。
(1)晋东南合作社的基层干部出现了严重问题,触发了赵树理对干部体制的重新认识和建议。比如“瞒报”“瞒产”,对上级不说实话:“谁也知道不像话……可是年年这样报,也过得去……”*⑤《给邵荃麟的信》,《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10、31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比如公社干部与生产队干部的隔膜。⑤比如乡干部与公社干部隔膜:“乡干部(社的直接上级)则不在生产机构之内,不负盈亏之责,对这问题感觉就不那样敏锐。”*⑧《高级农业合作社遗留给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19、32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我每碰上这些事,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说服区、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实际效率,另一个办法就是默许社干们阳奉阴违。”*《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两封信》,《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2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比如一线的生产队长无法左右生产:“这一切情况,在一个年年负责经营的生产单位内部的成员,总要比管着几十个单位的乡级了解得清楚”,⑧但这些生产能手们最多只能“阳奉阴违”。
最重要的问题是干部领导能力退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热心。《“锻炼锻炼”》中,社主任王聚海经常去县里开会,却解决不了出勤率的问题,而基本不去开会的杨小四、民兵队长等趁社长去开会之际,机智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小说是赵树理配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写的,但也反映出了干部的分化和能力退化。赵树理后来在大连会议上痛陈:“有的想出风头,就放什么卫星”,“有的党员甚至退到落后农民那里去了”,“过去党员轰轰烈烈,现在正经话都不说了”,“一个队真正有一个人去搞社会主义,就很了不起了”……
本来,晋东南搞合作化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干部和人才优势,在革命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们,比如王金生,用“高、大、好、拆、剥”几个字就概括了合作社的所有问题,一个人带一片。而到了后期,王金生不见了,“老定额”到处皆是。赵树理呼唤的好干部潘永福,在那里倡导“实干”——“实干”本就是基层干部的本色,如今却需要倡导。晋东南干部一直是典型,如今这副模样,赵树理借以推测全国其他地区的干部情况,并对干部体制提出建议,是可以理解的。
(2)晋东南群众在合作化后期的涣散表现,影响了赵树理对当前农村农民问题的看法。首先是淳朴民风的淡化。晋东南老区人民,质朴浑厚,然而赵树理看到,一进入高级社,“见到别人能在社里支借,自己就以为谁不支借谁吃亏,因此也不再精打细算来节约了”,“现在入了社,在日常生活上想和别人看齐,因而就非支借不可了”,*见杜国景《相信文本,还是相信作家?——从一篇新发现的赵树理佚文谈起》一文的附,《博览群书》2009年第2期。生产积极性再也不像初级社那样高涨。其次妇女的退化。曾经在全国首倡男女同工同酬的晋东南,《“锻炼锻炼”》中小腿疼、吃不饱竟然占多数,刁蛮任性,已经再没有灵芝、玉梅般的热心和泼辣。尤其是农村固有的“媳妇不亲”和“姑娘白养”等成见,重新抬头。再次,对革命缺乏热情和信仰。赵树理直言:“牛鬼蛇神为什么出来?农民为什么那么不相信集体?”*《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5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赵树理面对他最熟悉的故乡人,当看到他们这样的面貌时,不知会作何感想。他在一九六○年写了一篇《套不住的手》,刻画了一个正面人物陈秉正,他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因为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但干劲儿还是那么大,然而,小说拒绝交代为何他的干劲儿这样大,实在颇有意味。
三、农业问题专家,还是共和国作家?
晋东南地理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晋东南农业合作化。晋东南农业合作化的特殊性,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赵树理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广度、深度与限度。在根本上而言,他对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脱胎于他对晋东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两者一致时,赵树理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两者不一致时,赵树理的认识往往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特殊性。
所以说,经由晋东南合作化来观察中国农业合作化,是赵树理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主要思路。晋东南是赵树理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重要中介。赵树理基于下乡的见闻,获得了对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认识。赵树理的超前鼓吹合作社、拥护高级社、迎合大跃进,以及一九五九年后反思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大都是出乎晋东南经验的选择。可以说,没有对晋东南的认识,赵树理无法建立起他对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认识。他在对合作化发表看法时,之所以语气如此坚决,也正是出于他对晋东南的熟稔和自信。
在认识论上,这种认知方式属于“抽样论证”。邓子恢矫正高级社问题时,一直在避免这种思维,他一方面对包括家乡福建龙岩在内的十几个省市进行考察,一方面派出工作人员去全国各地调研汇总情况。*见邓子恢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十四章之第七节《尽心尽力指导合作化的初衷不变》、第八节《正确处理农业社内部矛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邓子恢据此撰写的《目前合作化运动情况的分析与今后的方针政策》、《国家与合作社的矛盾及解决矛盾的办法》等,与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高级农业合作社遗留给公社的几个主要问题》相比,其高度与口吻基本一致。但是,邓的两篇文章,在具体性、针对性、可行性、专业性、全面性甚至尖锐性上,皆非赵文所能及。相比之下,赵文多显其片面、义愤、外行与粗疏。邓子恢的批评与建设,为了得到对全国合作化整体的认识,对各个地区各种情况展开信息收集。赵树理即使对晋东南如手掌般熟悉,也只有这一隅而已。
进一步而言,晋东南作为赵树理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中介,其特殊性,影响了赵树理对中国农业合作化做出客观与整体的认识。因此,晋东南既是中介,又是障碍。赵树理与一般的批评者不同,他常常“通天彻地”地提出全国性的合作化建议,但他的认识常常体现出特殊与反复的一面——这正是由于他过度地认识了晋东南的合作化,忽视了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关注和思考,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具有理论性、系统性、根本性的认识,因而也就更谈不上某些研究者所说的“超越性”认识。
赵树理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计划写完《三里湾》后到长江流域农村下乡半年。*《一九五三年文学工作计划》,《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2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更为明显的是《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赵树理检查了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己“小天小地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赵树理评价道:这是“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84、3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这说明,赵树理对他认识合作化的方法,已经有所警醒和反思。
然而,近几年来,有学者不断呼吁“重新认识赵树理”,美化赵树理,甚至由于他对合作化的批判和建议,而赠送给他一个“农业问题专家”的身份。赵树理的二公子赵二湖说“我父亲在初级社的时候,就有想法,他认为是搞早了”,“刘少奇当时的思想就是不能超越阶段论。现在看来,他与刘少奇的思想有接近之处”,*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8、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事实是这样的吗?以《三里湾》实际的文本动机来看,当时的赵树理从不认为合作社搞得“太早”“太快”了,而恰恰是搞得“太晚”“太慢”了!但这样的论调,信之者与持之者,大有人在。
赵树理的人格力量固然伟大,文学精神固然崇高,但很多认识终究要具体到某些层面来讨论,不可一概而论。学者钱理群概括道:“赵树理是一位探索中国农民问题,以此出发,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并且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见解,且能坚持的思想者,用为农民写作、从事农村实际工作两种方式参与农村变革的实践者。”*钱理群:《建国后的赵树理——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下)》,《黄河》2015年第2期。不错,对“中国问题”的解答,是赵树理的旨归。但是,绝不能因为目的而忽视过程,以出发点来代替结果,凭借其追求而夸大其事功。所以,即使指认赵树理为农业问题专家,那么他首先是晋东南地区农业问题专家。若指认他为中国农业问题专家,那么,由于方法论的失误所产生的迷误,是这个身份的不可或缺的修饰。
根本而言,赵树理还是作为一个作家,以传统文人士大夫进谏的方式,试图对政治主流所决定的经济主流进行修正,这种修正表面上是修正政治主流,本质上则是以修正政治主流作为巩固政治主流的方式,并与此同时,希望这种修正被历史所证明。因而,这不是一个共和国农业专家的失误,而是一个共和国文人的不幸。他的不幸就在于:即使赵树理得偿所愿,其文学价值仍然必须作为另一个问题被讨论。假如赵树理并未得偿所愿,则又必然会以其文学价值作为牺牲。这其实是一代作家的不幸,只不过赵树理的不幸更加深沉。究其原因,存乎其时,更存乎其人。
马尔库塞说:“那些作为艺术家而与无产阶级取得同一身份的作家,依然是局外人——无论他们为了表达和沟通(无产阶级的内容)怎样摒弃审美的形式。他们之所以是局外人,并非出于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背景,也不是出于他们与物质生产过程的疏远,或出于他们的‘高贵气息’等等,而是由于艺术本身的根本超越性。”*〔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215页,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假如真能对建国后的赵树理作一概括,笔者将更推崇这段话。
(责任编辑韩春燕)
郭帅,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