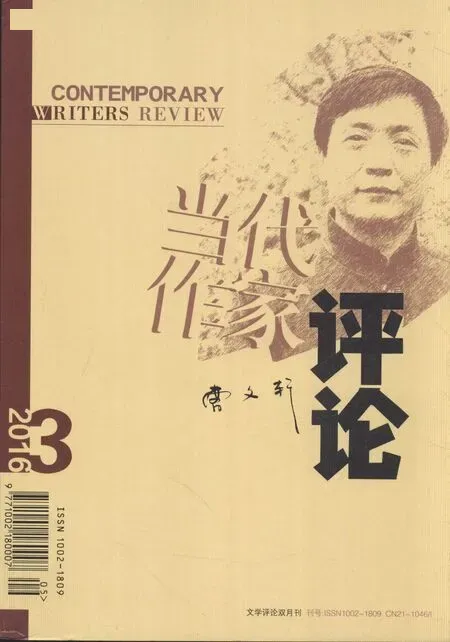道德伦理叙事的审美价值
——李骏虎《母系氏家》论
2016-11-25阎秋霞
阎秋霞
作家作品评论
道德伦理叙事的审美价值
——李骏虎《母系氏家》论
阎秋霞
李骏虎是一个出身乡村的“七○后”作家,很多评论家都认为他的创作生涯有一个从都市情感到乡村回望的“转型”,包括作家本人也这样概括自己的创作。仅就题材而言,他在不同时期的确有不同的选择。但事实上,如果从精神气质、文学的价值观、审美观而言,骏虎又是没有变化的,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谈理想主义以及理想人格的塑造,并赋予道德的审视与批判的力量。
一
作为山西作家,李骏虎的创作视域比较宽广,尽管二十年的写作生涯相比较老作家而言,他是年轻的,但对都市、乡村、历史、现实等题材的驾驭,由诗歌、小说、散文而至评论的扩张均显示了其良好的文学素养,但在所有的作品中,作者最看重的却是《奋斗期的爱情》和《母系氏家》,并认为它们的价值是被低估了的。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这两部作品的精神旨归同出一脉,即对于理想主义的坚守。《奋斗期的爱情》中主人公李乐“像火一样燃烧的理想,像风一样呼啸的勇气,以及像疯子一样与现实的搏斗”*李骏虎:《〈奋斗期的爱情〉修订本附记》,《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的堂吉诃德式的追求与抗争,充满了青春的热情、激情甚至反叛,作者珍视的是自己进入城市之初饱满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而《母系氏家》则镌刻着作者深刻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文化标记,在回望的乡土叙述中,他完成了对乡土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回归,是最能体现作者所追求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的成熟作品。
《母系氏家》在李骏虎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不是因为它给作者带来了很多有分量的文坛奖项(如首届陕西图书奖、赵树理文学奖以及小说的蓝本《前面就是麦季》获得鲁迅文学奖等),而是因为这部描写乡村风俗画卷的小说的表现视角、情感立场都比较独特:与其他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都不同,比如短篇《漏网之鱼》表现转型期在金钱伦理、欲望伦理支配下矿难对人生命的掠夺,中篇《大雪之前》描述乡村政治伦理生态沦丧,中篇《庆有》表现传统乡村社会礼义廉耻失却的焦虑和悲愤;也不同于契诃夫经典味道的短篇《用镰刀割草的男孩》里弥漫的淡淡的伤感,甚至也不同于短篇《还乡》《焰火》,长篇《浮云》等把乡土作为救赎被城市伦理价值体系侵蚀的心灵的良药。这些作品中的乡土,很显然是启蒙立场的乡怨或文化视角的乡愁,城与乡相互对立,彼此作为对方的参照物而存在,作者是以城市边缘人、乡村羁旅者的身份、以回望的姿态试图解决现实的乡村和想象的乡村出现的错位问题,以缓释自己内心的分裂情绪。而《母系氏家》显然秉承了赵树理“亲历”乡村、身在其中、水乳交融的情感,没有鲁迅对乡村的隔膜,也没有那些城市“寓居者”对故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尽管从叙事风格上有沈从文的诗意性,但又没有沈从文对“恶”的疼痛和对美渐行渐远的挽歌意绪,体现出平和、慈悲、宁静、和谐、温馨的乡村生活、乡村政治以及乡村伦理,它不需要在城市的参照下自卑,也无须在文化的审视下忧伤,它只是纯粹的、自足的乡土文化体系。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读者的心灵呢?
《母系氏家》其实并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传奇性,也没有过分戏剧化的情节冲突,语言更是土的掉渣的乡间口语,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令读者掩卷难忘,即使不经意的细节也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例如,写到婆婆们在编排闺女和媳妇子的是非时,小说这样说:“婆婆子敞着怀,干瘪的奶袋像漏完气的猪尿脬贴在胸前,手里握着拐棍在地下划拉,说起闺女的好,说一项轻轻画一个小圆圈,排列整齐,像算盘珠子——心里有数;说起媳妇的歹,拿拐棍狠狠地在地上戳,戳出一片小坑来,满地白麻子。闺女和媳妇在妈或婆那里变得可圈可点,泾渭分明地图解在大地上。”*李骏虎:《母系氏家》,第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小说中可谓俯拾即来,简直就如神来之笔令人惊叹,作者的叙述工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笔者看来,李骏虎身为男性,却能超越自身的性别立场,通过再现三个女人数十年的生存境遇,并以“道德伦理”的叙事立场对“欲望伦理”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反省,才是小说之所以能走进读者内心并产生共鸣的真正魅力。
把作品的叙述核心聚焦于三个女性,虽然视角相当独特,但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其实也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因为受到传统男权意识的影响,一不小心就会把他所喜爱的女性放置于“被看”的位置,即如张贤亮“性神话”对男性肉体的拯救,贾平凹“女性美神话”对男性精神的安抚,莫言“恋母神话”对女性作为生殖工具的认可等等不一而足,都无法规避男权意识对叙事的干涉和侵染,使得很多作品“崇拜女人”的外衣依然难以遮掩作家对女人“自由想象”的“男权期待”,从而受到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讨伐和批判。而一般女性主义者习惯于先验性地设置女人为“弱势群体”,因此,更加关注男权意识强加给女人的种种肉体压制和精神之苦以及自身的生育之痛,女性作为受害者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发起了从生理歧视到社会不平等待遇的各种控诉,为了证明女性之于历史的不可或缺与主体建构性,往往在伸展和张扬女人“自我意识”的时候失之节制,为了追求个性尊严和独立发展,容易陷于感性的愤激、决绝的抗争、本能的仇恨及其偏颇的情绪之中,于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就几乎成了女人百变不离其中的悲剧隐喻。
因此,如何超越自己的性别立场,既没有男性的“霸权”意识,又没有女性的“偏激”愤怒,能够自觉消除两性对立,从基于两性生理差异的文化建设,跨越到关注社会性别差异,并以强化两性和谐为旨归,这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并非易事。那么,以怎样的叙事立场塑造三个女人的形象,就成了作者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变革中的“七十年代”生人,作者沭浴着“山药蛋派”的光辉长大,又受到山西特有文化氛围的影响,其写作精神资源注定了他不会像同龄人如卫慧、棉棉一样热衷于“下半身写作”,把“身体欲望”作为美学革命的基本出发点,也没有其他“七○后”作家作品中常见的嬉皮士精神和逼近世纪末的幻灭感。《母系氏家》中三个女人的曲折命运尽管都与“性”有关,但在整体的叙事中,作者并没有把性作为小说的兴奋点,更没有因此而放纵欲望,而是通过“性”在三个女人生命中的不同功能体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在道德伦理与生命伦理遭遇冲突中,试图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从总体上来说,尽管三个女性都各自有不同的不公平命运,有着无法逃避的宿命,然而,她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和命运进行着不懈地抗争,要么在精神上有自己独立的追求,要么在经济上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可以说,作者既抓住了女性独立中最本质的要素,又对此追求独立与平等的方式保持了清醒理性的思考,既对女性的生命欲望倾注了足够的同情理解,又对这种生命欲望的释放进行了道德伦理的反思。
二
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那个俊俏泼辣,然而姻缘倒错、与命运斗气,几番偷情借种,惹出几十年风流闲话的婆婆兰英。她和赵树理笔下“三仙姑”的境遇非常相似,一个俊俏的姑娘嫁给了一个老实疙瘩,打瞌睡的月下老人也“把个方圆多少村子挑不出第二个好模样儿的兰英,偏偏嫁给了比土疙瘩多口气儿的矮子七星。”但是,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女性观照的态度却决然不同。赵树理对三仙姑四十五岁了还喜欢涂脂抹粉,穿绣花鞋,带各种头饰明显讽刺多于同情,对她装神弄鬼招揽男人的行为不能理解其内心需求的精神抚慰,因此批判也明显多于理解,最终的结局更是让三仙姑受到思想教育,感到了羞愧之心,也就是说作为女人的自觉的精神情感追求被理性的政治叙事所淹没。而“做闺女多少年来对如意郎君的憧憬瞬间成了泡影”并因此人事不省的兰英则获得了李骏虎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她虽然嫁了一个不如意郎君,但是她并没有像三仙姑一样破罐子破摔,寄希望于虚妄之中,而是哭了几天之后,就“心底透亮,竟然想开了”,为让自己的后半辈子风光而奢侈,为了避免生下和七星一样的一窝崽子受人嘲笑,为了能和别人一样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活着,兰英也许唯一能选择和寄托希望的就是把握后代的品种优良,这就是找人才出众的男人来“借种”,于是,一个红杏出墙的暧昧故事在作者这里便有些悲情起来。
与兰英发生关系的一共有三个男人:唯唯诺诺的矮子七星、唇红齿白的公社秘书以及威风凛凛的土匪长盛,而无论是和哪个男人的关系,兰英始终都是主动者,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如为了不怀上矮子的种子,她规定没有她的同意,七星不能碰她;黄毛小伙公社秘书在她的挑逗激将之下懵懵懂懂就犯了错误;土匪长盛更是她苦苦寻觅并周密计划之下的一条上钩的鱼儿。在整个过程中,兰英都是理性和克制的,与秘书云雨之后达到了自己借种的目的,便从此“两两相绝”;即便是勇猛有力的长盛让她有了性的真正觉醒,才知道“做女人原来这么快活”,但也并没有在“性”和“欲望”的力比多推动之下放纵情欲,她毕竟还是对矮子“心里有愧的”,为了自己心里安然,对矮子还不错,而且,为了儿女将来的脸面,她也曾努力和长盛斩断瓜葛。也就是说,兰英的偷情叙事始终有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伦理叙事的制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本叙事中,理性的道德良知往往被感觉的道德良知所替代,而群体的道德伦理也转换为个人的自由伦理,因此,在肯定个体欲望的自然权利时,也无形夸大了个体欲望的自由,关于这一点在近三十年多年的文本叙事中可谓比比皆是,作者这里对于欲望、性爱的反叙事证明了欲望自由并非伦理自由的前景,应该有自律道德的约束,否则,社会的发展中便不再有伦理关怀给予人的温情和抚慰。正是因为在欲望伦理和道德伦理之间选择的艰难,使得兰英欲罢不能,而又不得不承担自己偷情的恶果,受到命运的捉弄:六岁的秀娟无意中看到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疯狂的云雨场面,从此受到了惊吓,心里的阴影伴随了她整个一生,并以终生不嫁作为对母亲犯错的最大惩罚,正如小说所写,“秀娟是妈妈兰英的心头肉,也是兰英心上的一块疮,脸上的一条疤”,“心头肉”、“疮”和“疤”就成了折磨兰英一辈子的三件利器,也是她永远难以消磨的耻辱见证;福元更是以没有生育能力对兰英改换“良种”造成无情打击,当初是为了孕育优良后代,而今却面临了绝后的威胁。更有甚者,兰英在和荷花大战中,长盛不知踪影,只有矮子七星奋力的保护;“文革”中,长盛揭发兰英是破鞋几乎导致了她的毁灭,而在紧要关头,依然是七星舍命的护卫让她免于被批斗的命运。每到生死关头,她眼中“真正的男人”不仅逃避责任还会背叛情感,而那个“不算男人”的七星却恰恰显示了男人的本色,她反抗宿命的动力在于为自己挣得做人的尊严,然而,个人权利的获取并不能保证她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对兰英而言,是讥讽更是惩罚;对作者而言,是对那种只有情爱、没有责任的个体“欲望伦理”的深刻怀疑,是对传统“道德伦理”中责任、义务的呼唤和倾心回归,文本之中源自传统亲情的柔情关怀随处可见。到小说的结束,长盛、七星和兰英居然能够冰释前嫌,坐在一起聊天喝茶,生命中曾经发生过复杂关系的三个人就这样在没了性欲也没了性力之后,获得了一种宽容与和解,作者也许要告诉读者的就是,性、欲望虽然是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人与人的亲情,包括七星对一双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女的疼爱,也包括七星和兰英对抱养来的孙子的万般欣喜。因此说,作者借助于道德伦理叙事,借助于对兰英一生的描写,对近些年困扰读者的“欲望伦理”与“道德伦理”做了深刻的反省,所以“花甲之后,兰英对跛子好得不得了,四十年后,她终于良心发现了。”这也就是他对兰英可以施以足够的同情理解,但并非完全认同她的选择的原因所在。
三
小说中第二个叙事的中心是朴实简单、嫉恶如仇、勤劳快乐的儿媳妇红芳。相对于兰英和秀娟来说,这个形象的塑造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她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直肠子,性格比较单一。她明知道婆婆经常在福元和外人面前编派自己,但也“只是当下听了生气,一路走回去就想开了,觉得没有必要计较,看到婆婆也恨不起来”,即使后来因为背负着不能生育的冤屈,被婆婆明里暗里地指桑骂槐,屡屡遭受福元的痛打,然而不会和人记仇的红芳也从来没有真正怨恨过他们。这样的性格生动鲜活,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源自简单的美。在小说的人物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心事重重,兰英处在偷情的焦虑中,七星处在绿帽子的尴尬中,老金菊处在拉皮条的恶名中,长盛处在背叛感情的怨恨中,秀娟处在无处逃遁的阴影中,福元处在不能生育的痛苦中,而唯有红芳是个通体透明不会勾心斗角的人,也许正因了别人的复杂和满腹的心事,才凸显了红芳单纯的可爱与可贵。
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红芳长年累月地喝那种味道很怪有许多爬虫的中药,以至后来熬药都成了矮子七星的一种生活寄托和仪式。作者这样的处理在笔者看来是为突出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悲剧性而有意为之。女人在一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地位显然和生育有关。当不能生育时,她要背负所有的埋怨和谴责,而一旦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之后也就奠定了她在整个家庭的地位。小说中描写在红芳治病的半年中,兰英把她“当亲闺女待,吃好的喝好的,重活脏活都分派给秀娟干,一心要媳妇子赶紧消了炎怀娃娃”;在福元查出问题后,兰英叮嘱福元“千万不敢告诉红芳,要不你一辈子都栽到她手里了,咱们一家都在她手里活不出来”,而且自此她就“替儿子在媳妇跟前矮了一截”。由此可见,在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悲剧在于她仅仅是一个被利用的“物”,一个符号而已,所以红芳每次挨打的缘由都因不能生育而起,每看到福元在母亲的唆使下把红芳打的死去活来时,都令人心痛不已。尽管当今女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作为“生育工具”的历史使命远没有结束。
好在红芳并不是一个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女性,她“只要理不亏,就和他对打,抓他、咬他”,而且为了不在家里受气,她和别人一起去城里贩卖苹果,小说中写她第一次挣了钱之后,“口袋里的几十块钱让她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点矜持。她憋着一口气,没有像往常一样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她是个心无芥蒂的人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还用说吗,是口袋里的几十块钱给了她充足的底气,甚至觉得福元挺可怜,委屈中生出些怜爱来,而福元听说红芳挣得比自己跑车也不少,压抑不住地兴奋,也顾不得兰英的目光,追到厨房巴结红芳,甚至在晚上行云雨之事时,也更加卖力和温柔。这个细节的捕捉真是非常的厉害,说明作者抓住了女性解放的实质就是赢得经济的独立,否则,无法获取男人的尊重,无法取得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也就不能有自己的人格独立和精神独立。
四
秀娟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女性,虽然在艺术上的塑造不如兰英“丰满”、有张力,但却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所在。她几乎综合了人性所有的优点,虽然表面看来孤僻乖戾,但其实内心善良,对人宽容豁达,是个“不用给别人找原因就能原谅别人的人”,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精神还是经济上都有非常明确的独立意识,这些都构成了这个人物形象的主要元素。她一辈子不嫁人,也许真的是为了惩罚兰英,成为当妈的心里永远的痛;也许真的是为了回报那个知青程和平对她“爱的启蒙”,无论如何,在外人看来,终归是不合常规的不幸女子。
从道德角度看,秀娟无疑是完美道德的理想化身,她是一个为别人而活着的人。她不仅主动出让了自己居住的老磨坊让连喜给村里建纸箱厂,而且提出要求“工人要用村里的人”,还要照顾莲、艳(死了丈夫的两个婆娘,以参加荷花的“土教会”来打发苦闷困顿的日子),还有彩霞(在县里以卖淫为营生的一个媳妇)们先就业;酒后被两个赖小子偷了钱之后,她宁肯背着“被糟蹋”的丑名,也不做任何解释,任由别人给她造谣中伤,直到两个小子被抓了回来,也并无意要送他们进派出所;主动借钱给那个在亲戚处四处碰壁的莲,帮莲渡过难关;每逢村里红白喜事,她都是那个绝不偷奸耍滑的“干活的”;还有她给程和平每年织的毛衣,给侄儿提前做好的两箱子小孩衣物,凡此种种都说明秀娟虽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与《创业史》中梁生宝、《新星》里的李向南、《抉择》当中的李高成等等的抱负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其“仁爱之心”、“修身之德”、“齐家之力”却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道德魅力,放置于“躲避崇高”、“消解意义”、“以丑为美”、“自由自在”等等以追求“审美快感”为目的审美向度背景下,秀娟这一形象的“德性之美”给了读者更多的反省。
一九八○年代以来盛行的文学理论,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还是英美新批评提倡的“张力、反讽和悖论”,抑或尼采的“酒神精神”,弗洛伊德的“性本能”,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代的审美内涵,提供了“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所缺乏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体验,从而把主体引入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空间,使人得以体验和享受“自由的、个性化和本真的生存状态”。*周宪:《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但是,这种以“感性”为特征的审美理想在颠覆“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同时,忽略了审美向善的功能,拒绝道德评判的姿态和立场使得审美判断显得势单力薄,肤浅而脆弱。这些年审美价值观中最缺少对正面精神价值的肯定和弘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文艺审美把人引向至高自由境界的时候,忽略了对人自身道德性的建构,也就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和性能。
因此,秀娟在小说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她本身作为女人自立的意义,而变幻为作者心中圣洁之神的化身,她虽然没有太阳的光辉,没有傲人的事业,甚至都没有出过远门,然而在她的身上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她和红芳的为人做派大不相同,但是她的无私之美和红芳的简单之美却带给读者很多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思考。
五
“尊重生命”、“张扬欲望”似乎是这些年来颇为时髦的口号,也似乎是对“以人为本”思想的有力穿透,但是过度的渲染与关注也使我们忘却了道德审视的痛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母系氏家》显示了它的不平常,作者依托着三个女人在南无村搭起的戏台完成了自己灵魂对故乡的回归,依靠“道德伦理叙事”和“生命伦理叙事”之间的矛盾张力实现了文学要有所承担、有所启迪的追求。相对于他前期的《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作品而言,《母系氏家》少了很多青春的凌厉和浮躁,显示出了人到中年之后对人生理解的宽容大度、沉稳成熟,于是“慈祥”不仅成了小说里长盛、七星们挂在脸上的笑容,更是一种内化在心底的人生姿态。是啊,当所有的历史都成为谈资,男人和女人还有什么恩怨情仇是不能化解、不能两相遗忘的呢?
作者在曾在一篇散文中说:“长久以来,有一个隐秘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最感到事业上得意和生活安逸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与我对视。每一次的对视,都会令我自省一番,失神许久……使我产生一种愧疚和感叹。”*李骏虎:《我是农民中的“逃兵”》,《受伤的文明——李骏虎文化散文》,第20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母系氏家》就是李骏虎骏虎对逃离乡土而不安的一种慰藉,他想要努力忘记城市人的身份,回到大地之子的原初状态,正如《还乡》的结尾:“只觉得一片寂静,仿佛世界已经告别了我,但我分明很充实……我望着流光溢彩的田野,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自己就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李骏虎:《还乡》,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e945ad0100gjy0.html。而《母系氏家》营造了一个关于乡土文明的纯净、纯美的乌托邦图景,让作者获得了凤凰涅槃的精神洗礼,也让读者获得了温柔温馨的心灵抚慰。
如同论者所言“当代作品中表现了太多乡村的破败、荒芜、原始、愚昧、罪恶,也该有人书写乡村的温润与美好了”,*王莹、张艳梅:《李骏虎小说创作论》,《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二十世纪末以来,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对作家们也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一部分作家经不住市场经济的召唤下海为商,标榜自己只为“码字挣钱”的作家不在少数,更有市场、传媒合谋之下名利双收的韩寒、郭敬明们。躲避崇高的痞子文学大行其道,宣扬享乐的形而下文学甚嚣尘上,文学做了利益忠实的奴仆,良知、忧患、责任、批判、高尚、激情等等曾经是文学要义的核心词汇被性欲、物欲、消费、叛逆、平庸、审丑等等所替代,文学在走向边缘的过程中也逐渐失去了其高洁的精神追求。在这种文学生态环境之下,《母系氏家》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作者成长在传统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的浸染下,成年后又历经坎坷艰难奋斗,悲天悯人似乎就成了他的精神标签,在别人宣扬放弃文学的精神启蒙的时候,他在努力用自己的文学发声;在别人热衷于各种眼花缭乱的叙事概念时,他却回归到了笨拙朴素的现实主义;在以书斋写作、闭门造车盛行的年代,他却在体验生活并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在别人以营造丑恶人性为深度的时候,他却在彰显人性的纯美与善良,把社会的承担意识、责任伦理作为创作的前提,不放弃对于传统伦理道德坚守的努力,努力地让他的作品充当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阵地,尽管有些苍凉的意味,却不免让人心生敬意。
(责任编辑王宁)
阎秋霞,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