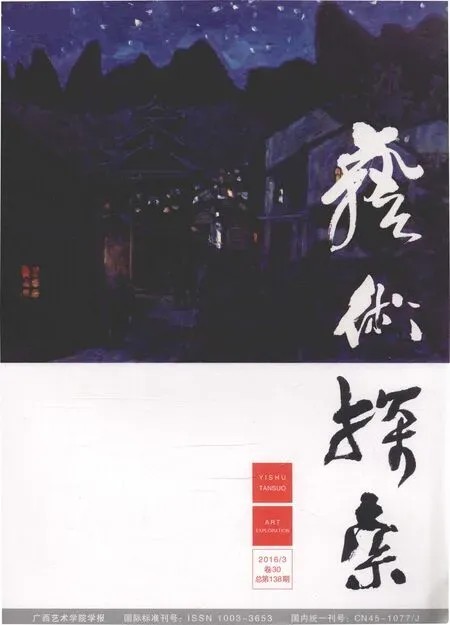创造共享的精神空间
——当代公共艺术的策略与品质
2016-10-19赵志红王珏
赵志红 王珏
(1.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成都610065;2.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创造共享的精神空间
——当代公共艺术的策略与品质
赵志红1王珏2
(1.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成都610065;2.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在公民文化权利受重视的当下,所有艺术门类似乎都在尝试着消解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打破艺术作品与观赏者之间的界限,让观众介入艺术,让艺术融入观众。而公共艺术家在表现的视角、内容以及形式方面,普遍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艺术策略和方式,对突破传统艺术的私密性与博物馆的空间阻隔,构建互动共享的精神空间作出了有益探索。
公共艺术;共存互动;精神场域
在重视公民文化权利的当代,在生活审美化已成为一种潮流的背景下,公共艺术在具有公共意识的艺术家们的营造下,试图以一种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态,成为艺术阵营里一种具有特别属性的门类,改变或改善艺术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感和尴尬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共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中,通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以及在造型艺术所包含的空间、材质、尺度乃至时间意义等方面的种种实验,让艺术介入公共空间,走近公众,让观众融入艺术之中,从而创造出观赏者与艺术创作者、观众与观众、观众与周围景观交流互动的精神场域。
一
传统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一般是被观看与观看的关系。艺术作品往往被放置于特殊的环境中或设置一些特殊的条件,使其与观众保持必要的距离,让观赏者以静观的方式被动地去解读或欣赏这些作品。就是说,艺术家独自创造了一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的大门并非向所有的公众敞开。作为观赏者,要进入这个世界,你必须要具备跨入这个门槛的知识、经验、素养和能力。德国艺术史学家潘若夫斯基(Erwin Panlfsky)在其《图像学研究》中认为,要真正解读艺术作品,必须把握艺术作品内在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是隐藏在艺术作品的视觉形式、题材和主题背后的。作为观赏者,必须要由表及里,跨越多重门槛,才能获得那个深藏其中的秘密——艺术作品的意义。怎样才能解读出艺术作品的意义呢?潘若夫斯基认为必须完成三个步骤。首先是对艺术作品所呈现的实际意义,即对其根本的或自然的题材的(primary or naturalsubjectmatter)的感知。获得了第一层浅表的意义后才能进入第二个步骤,即以特有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去解读从属的或约定俗成的题材(secondary or conventional subject matter),分析作品所传达的特定的文化信息以及意义,从而与艺术的图式相结合,获得某种意象。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第三个步骤,即在调动视觉经验、人文知识与素养的基础上,感悟出那个隐藏在深处的内在的意义或内容(intrinsic meaning or content)——作品所蕴含的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阶层、一种宗教或哲学派系的基本态度的根本原则,亦即新康德主义哲学健将卡西勒(ErnstCassirer)所说的“象征(Symbolical)的价值”。以潘若夫斯基的观点
来看,要成为艺术作品的真正解读者,必须具备三方面的能力:第一要有观察物体的实际经验;第二要有理解文化素材、体裁及观念方面的人文知识;第三要有直觉的综合能力,就是体悟、把握作品蕴含的人生真谛、人类精神实质的能力。否则,你难以走进这个世界,艺术之于你,永远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彼岸天地。
即便你具备了解读这个世界的经验、知识、素养与能力,当艺术作品被置于特定的空间或以一种特定的呈现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时,艺术与公众之间仍然是有空间和心理距离的。当作品被私人收藏,公众并不与作品产生关系,艺术家、作品和公众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感受艺术、享受艺术的人只能是收藏者自己。如果收藏者有感知和欣赏能力的话,他可能成为艺术精神的独享者,如果他不具备这些能力,他最多是一个财富的占有者。当艺术被置于博物馆,艺术作品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无疑是一个公共场所、公共空间,但是在这个空间中展示的艺术作品并不就具有了公共艺术的性质。博物馆作为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并非是人人都能光顾和随意活动的空间。人们要进入这个空间是需要特意准备和选择的。只有进入这个空间的人,才能与艺术作品发生关系。而博物馆本身所特有的功能和属性,也昭示着这是一个不同于广场、商场、草坪、车站或街区这些向所有公众自然开放或所有公众都自然拥有的空间。它是珍贵的艺术和其他人类文化创造物聚集的场所,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在特定的文化场中对过去或现代经典的或独特的文化产品进行仰观、膜拜。在虔诚的凝视中去解读艺术家和文化创造者以及时光所设定的密码,从中获得知识和一种心理的满足。博物馆的环境和功能,更是强化了艺术作品的特殊地位。流动的观众与静态的艺术品之间,发挥主导作用的无疑是艺术作品和它们的创造者。而进入博物馆的人们始终是被动的接受者或观赏者。艺术家是艺术世界的主宰,艺术作品是观众“仰望”的对象。
传统的室外艺术如雕塑、壁画和其他的景观艺术,虽然呈现在公共空间中,但未必是公众审美意趣的表达。其形式和语言可能具有公共性,但其在整体上依然是艺术家和艺术家所依附的赞助者依照自我的方式在言说,观众大都是视觉形式密码的被动解读者和接受者。正如罗沙林·克劳斯所说:“雕塑在传统逻辑上被看作是纪念碑。作为某个祭奠场地的标志,它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它的形式是具象的(不是人就是动物),或抽象的、象征的。就其功能的逻辑而言,一般要求它能独立于环境,要有垂直和大块的底座,易于辨识。作为一种实在,许多雕塑作品能被人们毫不费劲地认出来,道出名字并举出意义所在。”①(美)罗沙林·克劳斯《后现代雕塑——新体验、新语言》,范迪安译,《世界美术》1999年第2期,第3页。观众可以毫不费劲地认出被垂直和大块的底座托起的雕塑的名字,也可能可以举出作品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已是被艺术家规定好的,公众即便有解读的能力,也是被动接受与解读的权利。雕塑的座基,把艺术作品与公众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作了明确的划分。就如传统戏剧舞台,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演出者与观赏者清晰地划分开来一样。
20世纪以来,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现代文明与传统规范、公众权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人的异化现象日趋严重。囿于精英艺术壁垒之中的艺术无济于缓解人们日渐压抑的精神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二战以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医治战争创伤的时代吁求和城市再生运动,促使民主政治、公民权利成为一个被关注的话题。在这种情形下,公众的文化权利,包括享受文化艺术和接受文化艺术教育的权利,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有宗教或信仰,思想和言论自由;有个人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文化方面的各种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等等②《世界人权宣言》第18、19、22、26、27条均涉及文化权利问题。。此外,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活动都反映了人们对文化权利的需求。
普遍的公民文化权利的吁求,把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的公共性问题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艺术在城市重建,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在人的情感传达与沟通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功能被重新讨论和强调。在这种背景下,公共艺术逐渐由处于一种含混的、边缘的、亚艺术的状态和地位,成为一种清晰的、被高度关注的重要的艺术形态。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就是要求艺术家首先要建立公共意识,要站在公众的立场,关注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用艺术作品表达公众的审美意志,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
二
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种现象,当代所有形式的艺
术似乎都在试图消解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打破艺术作品与观赏者之间的界限,热衷于尽量使观赏者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艺术活动,让观众介入艺术,让艺术融入观众。而公共艺术家们在突破艺术的私密性、突破博物馆的空间阻隔等方面,普遍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艺术策略和方式。

图1 乔治·伦丁《本杰明·富兰克林》青铜塑像,1987年

图2 安尼特·卡普尔《云门雕塑》,2006年
一是基座的消解,尺寸的平实化。雕塑作为普遍置于室外空间的艺术,其传统形式是在主体形象下加底座,使其与周围环境相分离,而且从外部将它划定为独立存在的实体。高耸于座基上的塑像,以突出的位置与体量,迫使观赏者背离正常的视线而以仰望的方式来观赏。加底座与仰视的方式,不仅仅是一道空间的界限,也拉开了观赏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而现代许多室外雕塑,降低或取消了底座,使作品融入人群之中,使观众不仅可以用平视的视角观看作品,还能与之平等地处于同一空间里。
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里有一座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铜塑像(图1),其以具象的雕塑手法,塑造了坐在长椅上休闲看报的富兰克林。人物、椅子的尺寸与实际一致,富兰克林侧身坐于椅子的一侧,坐姿随意,神态悠闲。椅子向所有的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与富兰克林同坐一椅,与之“对视”“交谈”。这件作品的空间位置、物像尺寸以及人物神态与公众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伟人似乎就是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一个休闲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与之一同成为艺术中也是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这件作品无疑给众多的观赏者和同坐一椅的休闲者带来亲切感和幽默感。
还有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几组民俗雕塑和深圳市区《深圳人的一天》等街区雕塑,都以无座基和等同于真实的人和物的尺寸来塑造形象,并被安置在公共空间中,与观众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人物雕塑也以开放的姿态自然地接纳所有人的触摸。艺术不仅介入了公共领域,而且赋予了公共空间以新的意义,观众与作品在同一空间中共存互动,使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起来。
二是把公众作为艺术的构成元素,纳入作品的创作之中。传统的艺术,包括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其形式语言、结构以及其他元素,都是由艺术家调配和控制的,艺术家根据自我的理念和审美趣味,把各种形式因素有机组合成一件完整的作品。观众只有在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和素养的前提下,才能理解、接受艺术家提供的作品信息,观众永远是在此岸世界观望艺术的彼岸世界的观望者。而现代公共艺术出于对“公共性”的追求,把艺术的边界向公众开放,甚至让公众直接进入艺术作品之中,使公众成为艺术作品的构成元素。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中央的椭圆形云门雕塑(Cloud Gate,图2),由印裔英国艺术家安尼特·卡普尔(Anish Kapoor)设计,外形极为可爱,犹如银色的豆子,因此人们叫它“大银豆”(Big Silver Bean)。雕塑重110t,因为使用了不锈钢弧面而显得不是那么笨重。极度抛光的不锈钢镜面丰满圆润,宽达66英尺,如立体椭圆的镜子一般,映射出周围的建筑与蓝天白云,似乎把整个芝加哥都搬到了云端上。“大银豆”像一个大磁石一样,吸引了无数游人。人们可以随意触摸它,如果穿过它底部近4m高的拱形“门”,还能在不同的曲面上看到形象各异的自己,有一种照哈哈镜的感觉。人们站在“大银豆”前,仿佛正以一种亲切而又具有未来感的方式,体验着自己与整个城市的关系。
公共艺术不仅可以长存于芝加哥,还因为与人们有了亲密互动而让人们感受到公共艺术可以如此地贴近生活。在此,公共艺术为人们提供了人与环境相遇的机会,也因此重新诠释了公共艺术的美学功能。
公众进入艺术,成为艺术的构成元素,使现代公
共艺术作品不仅消解了传统的公共艺术作品那种恒定不变的视觉形式,能随着与之相遇的人的变换而呈现完全不同的视觉样式,内容与意蕴也不断地变换。同一空间中的同一件作品,在时间的流动和观众的变化中,其形式和意蕴都在不断地变化着。
三是让公众成为艺术家的同盟者。当代公共艺术不仅让观众进入艺术,使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联,打破了艺术与观众之间的隔膜状态,还可能让观众成为艺术创作的参与者,同艺术家一道完成艺术计划。不少公共艺术计划的实施过程和最终结果,并非由艺术家全部预设和规定好,而是在实施过程中随着观众的认同与参与程度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观众与艺术家在空间的创造中实现真正的同盟。
“给卡塞尔的7 000棵橡树”是一个典型的让公众参与到艺术体验中的公共艺术行动计划。1982年,在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举办期间,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依斯出于“对于所有摧残生活和自然力量发出警告”的理念,在弗里德利卡农美术馆前,置放了7 000块花岗石砖,并在其中一块砖旁种下了第一棵经常被用来代表日尔曼人灵魂的橡树。艺术家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只是个开始,他把后续的展开留给了时间和愿意参与此项活动的人。之后,相继有不同身份、性别和职业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重复这一动作。当最后一棵橡树种下时,整个艺术计划才最终完成,而此项艺术方案的设计者却已离开人世。这个向所有愿意参与此项活动的公众开放的艺术计划,让所有的参与者以及与此景象相遇的人,都对这项象征性实践有了一种真切的体验:个人的参与以及人与人的连接,才构成城市这个群体。人的行为在同一个目标的导向下连续性展开,可以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创造出新的生活景象。艺术家设计了方案,并在启动之后隐匿,后续的参与者甚至可能不知道这个艺术家存在,但是他们自愿地成为这个艺术方案的实施者。艺术家把参与实施的权利彻底地提供给公众,公众成为新的空间的创造者。让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得以发挥,创造的权利与欲望得以实现和满足,这是约瑟夫·波依斯信奉的艺术理念,也是“给卡塞尔的7 000棵橡树”艺术方案设计的初衷和实施所追求的意义。实际上这个艺术行动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它从一个角度介入了对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连接、依存关系这样的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并在实践的层面上产生了远远超越艺术家预想的持续效应。
三
改变传统的艺术家话语霸权地位,让欣赏者成为积极的合作者和参与者,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各国出现的一股新的潮流。这种潮流的兴起,与文化艺术领域大众化思潮的勃兴,精英主导地位动摇的趋势相一致。大众文化虽然具有非理性、过分追求感官愉悦和彰显世俗欲望的特征,是一种时效性、娱乐性、表层性的文化形态,难以担负起表达人类深刻的精神体验和情感的使命,但是那种重视公众接受能力和审美趣味,强调公众参与,以求与民同乐的特点,毕竟在形式上或者说表层上显示出对公众的尊重,对公众文化权利的尊重。在这种文化观念之下,艺术家对观众而言不再是艺术这杯“美羹”的施舍者,观众不再是在艺术彼岸接受艺术精神惠泽的守望者,而是和艺术家相互配合,彼此兼顾,共同完成一场盛宴。尽管,这场盛宴中的“菜肴”并不一定精致名贵,但是,参与的过程与“品尝”的现场感,足以让所有的参与者获得快乐。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并非仅仅是艺术家具有公共意识,关注公共话题,创作出能体现公众审美意志的作品,还应该包含在艺术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对公众的角色与位置的思考。从根本上说,艺术价值和效应,只有在艺术家、艺术作品、观众三者的关联与互动中才能最大化地实现。没有观众的艺术,不能与观众产生互动效应的艺术,不能说一定是无价值的艺术,但肯定不是最好的艺术。没有公共意识,对公众不屑一顾的艺术家不能说不是好的艺术家,但可能是一个精神的孤独者或精神的撒娇者。
观众与艺术的互动有不同的方式,除了让观众成为艺术的直接参与者与创造者,在艺术的创造中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创造的潜能,获得创造与表达的快乐外,还有就是通过艺术作品所叙述的故事情节、传达的情感或“有意味的形式”,使观众在静观中生发出主动解读的愿望,在解读中获得与艺术家一样的表达和创造的快感,通过作品这个中介,与艺术家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鸣。再就是艺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与所使用的题材,贴近公众生活和视觉经验,让观众有一种主动接收和解读的愿望,能在虚拟的形式中产生一种观照到自身的快乐,使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彼此的对应中变得模糊起来。这第三种方式,可以看作题材上的生活化、内涵上的平实化、情感上的大众化与形式上的通俗化的体现。
所谓题材上的生活化,就是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
艺术那种纪念碑式的逻辑,不再把帝王、英雄、伟人或那些天才人物作为唯一的、必然的艺术表现对象,而把公众的日常生活情态纳入艺术的表现范畴,缩短艺术与公众间的距离,让公众获得一种亲切感。
所谓内涵上的平实化和情感上的大众化,就是并不追求主题上的庄严感和神圣性,而是关注和传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甚至是塑造一种与生活零距离的形象。观众在与艺术品接触的瞬间,或许不会像观赏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那样,为塑造出来的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或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事件所震撼,并以一种崇拜或敬仰的心情去解读这些人物或事件所负载的不同于寻常的崇高、庄严、神圣的精神品质,或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当代的公共艺术通过公众熟悉的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甚至把观众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常态也物态化、视觉化,叙述历史和道义、表达意识形态的理念为强调分享大众的当下记忆和生活经验的理念所取代,使观众在或熟悉或陌生的空间中,在偶然的不经意的审视中,获得一种亲切感,甚至观照到自身。正如黄海鸣在谈到当代公共艺术时所说,艺术介入都市景观的创作,已逐渐被视为一种将各种印象结合在一起的行为,中心性消失,并且让艺术介入方式多少变得不那么突兀,“作品并不针对纪念一件事件、一个人物,不悼念也不庆祝任何事物,不再现任何的权力中心,只是促成‘公共空间’的‘出现’以及‘交流’,不做无谓的添加,根据现场状况,找出场所中所缺的东西,以最少的介入去促成。”①黄海鸣《介入日常生活的艺术》,转引自(法)卡特琳·格鲁《艺术介入空间》,姚孟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艺术之于观众不再是彼岸世界的精神盛宴,不再是难以企及的精英的理想表征,更不是充满劝导、道义或震慑力量的视觉形式,而是公众可及的此岸天地,是公众身在其中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
所谓形式上的通俗化,就是艺术不再如谜语一般,构筑着一道让观众难以跨越的门槛,甚至是故意以一种对观众不屑一顾的姿态,傲立于公共空间,从而使观众不能也无法去解读其语言的密码,成为艺术面前的旁观者,或匆匆过客,而是在语言、形式和尺度上,贴近观众的视觉经验和视觉习惯,以一种平实的公共的视觉语言和形式,向观众开放,甚至把艺术自身融入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的视觉心理场域之中,让公众获得一种解读的快感,使艺术表现的题材、旨趣、语言与形式,都最大程度地、整体性地向公众开放。
强调艺术的公共性与互动性,并非弱化艺术创作的主体地位。事实上,在互动中,艺术家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充当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任何一项艺术方案的构想与设计,都首先由艺术家来完成。艺术在空间中的形态呈现,材料的选择与运用,各种因素的组合与搭配,最后可能出现的视觉效果等问题,都是由艺术家来思考、把握或预设的。就是观众是否进入以及怎样进入艺术的创作过程,都不是取决于观众自身,而是出自艺术家的设计理念。但是,把公众的审美兴趣和需求纳入自己的艺术计划之中,让艺术融入公众,让公众介入艺术,消解艺术与公众之间的隔膜,让公众进入创作的空间与过程,甚至把决定艺术作品的最终呈现状态的权利让给公众,使艺术与公众始终处于共存互动之中,这毕竟是当代公共艺术不同于传统公共空间艺术以及精英艺术的重要特征和品质之一。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Building Shared Spiritual Space—on Strategies and Qualities of Public Arts
Zhao Zhihong1Wang Jue2
Nowadays,cultural rights of citizens are being more effectively guaranteed.As artists in all genres are striving to b 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ir pieces and the audience,in order to create the synthesis of artistic pieces and the audience through public art.Public artists generally have specific art strategies realized in view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and have made some beneficial exploration,breaking through the space barriers between the privacy of traditional art and museums. while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nd share interactive spiritual space.
Pub lic Art,Interact,Spiritual Space
J0
A
1003-3653(2016)03-0054-05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3.010
2016-04-17
赵志红(1970~),女,博士,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艺术。
2014年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四川藏羌彝走廊生态景观的视觉文化构建研究”子课题(SC14A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