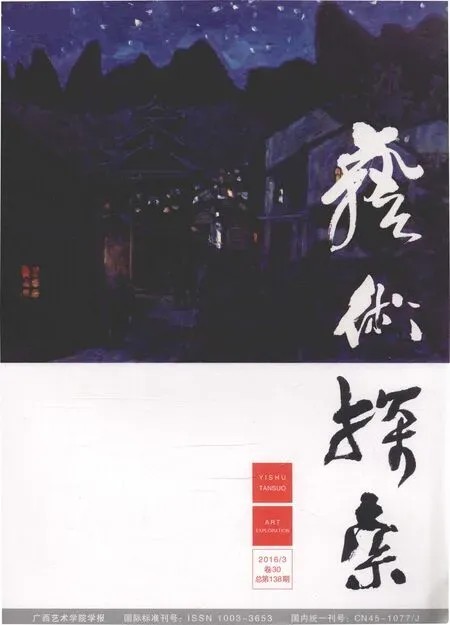公共艺术的概念拓展与功能转换
2016-10-19李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北京100029
李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北京100029)
公共艺术的概念拓展与功能转换
李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北京100029)
公共艺术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其概念内涵、作品形态、运作机制与价值功能等处于持续的变化和拓展之中。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公共艺术已由一项文化福利政策衍生为一种带有普泛性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精神。其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型取向,旨在培养公众借助艺术路径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最终指向具有开放性、公共性、民主性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实现。
公共艺术;“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公共性;城市化;社区文化营造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引介至中国以来,公共艺术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凭借着其与生俱来的公共性及丰富多元的艺术形态逐渐占据了中国大大小小的社会公共空间。其在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艺术理念也逐渐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但不容否认的是,公众对于公共艺术的认知普遍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是在学术界,关于公共艺术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共艺术的明确概念界定相当随意和混乱,甚至存在着不少的理解偏差和认知错误。显然,这些偏差与错误是影响公众认知、接受和参与公共艺术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公共艺术大多徒有其表而缺乏真正公共性的主要因素。为了促进公共艺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让艺术真正深入民众生活,发挥公共艺术的诸种社会功能,必须对公共艺术概念及其功能尽快加以矫正和澄清。
一、公共艺术不是单一的艺术形态
目前学界普遍以20世纪50年代美国“百分比艺术计划”(Percent for Art Program)的实施,作为公共艺术诞生的标志。事实上,“百分比艺术”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其主要是以政府赞助的形式来让艺术家对公共建筑物进行装饰,要求作品体现区域特色,反映社区文化及公众生活状况,以激励民众和彰显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新政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于1934年设立了文化资产部绘画与雕刻处(Treasury Department’s Section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该处通过总统以行政权力划拨新联邦大楼建设经费的1%用于委托艺术家进行公共建筑物的美化。在其存在的9年时间里,先后划拨了1 400多个委托项目。[1]这一将建筑总费用的1%用于艺术装饰的政府行为,便可视为公共艺术政策的雏形。二战之后,城市重建与扩张的现实需要为公共艺术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契机,美国政府更是于1965年设立了国家艺术基金对公共艺术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助和推广。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30多个州为公共艺术立法,明确要求将公共工程建设经费的若干百分比用于艺术建设,由此推动了公共艺术在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城市的大规模出现。公共艺术的形式也不再仅限于壁画、雕塑等传统样式而趋于多元化。公共艺术的功能也并非简单的建筑点
缀,而日益发展成为城市形象塑造、社区文化营造和公众文化福利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新生的艺术概念、一种当代艺术形式,公共艺术并不意味着一种艺术新形态的诞生,而是指向一种新型的艺术观念。该艺术观念赋予传统的艺术形态以新颖的生产机制、呈现方式和价值意义,更多的是对过往艺术形态的改造与新生。所以,公共艺术与绘画艺术、音乐艺术、影视艺术等传统的艺术门类不同,其并非特指某一种艺术类型或艺术形态,也不主动生成新的艺术形式,而是向所有的艺术形态敞开,传统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及当代的装置艺术、景观艺术、大地艺术,乃至行为艺术等皆有可能成为公共艺术。
进一步讲,公共艺术亦不是当代某个具体的艺术流派、艺术运动,其并没有明确的艺术宣言或口号,也没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其诞生之初更多地指向由西方福利国家根据现实需要通过国家行政机构及立法机制而推行的带有某种强制意味的文化政策,旨在强化艺术的社会属性及公益性,建立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民众的深度关联,推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这种文化政策的最初指向仅局限于公共建筑物的装饰与美化,战后的城市美化运动以及公众对于文化艺术的新需求,则促进了这一文化政策的范围和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公共艺术也逐渐由一项单纯的文化政策演变为一种带有普泛性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精神,而逐渐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正如美国费城现代艺术协会主席卡登(Janet Kardon)所指出的那样:“‘公共艺术’不是一种风格或运动,而是以联结社会服务为基础,借由公共空间中艺术作品的存在,使得公众福利被强化。”[2]在这种精神的统摄之下,任何一种艺术风格,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只要能够顺利实现空间的转换和形态的呈现,皆有可能被艺术家拿来诉诸公共艺术表达。
所以,与其说公共艺术是一种新型艺术形态,不如说其是一种当代艺术观念。其更多的是象征一种公共精神,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一种人文艺术理想。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公共艺术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取向。其主要是通过艺术来介入社会、城市、公众的日常生活,最大程度地发挥艺术的功能,最终指向具有开放性、公共性、民主性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实现。基于这种宏观性诉求,公共艺术概念便可以辐射至整个艺术领域,凡是处于公共空间之中,以公共性为理想,以公众的意志和旨趣为诉求,能够彰显公共精神,反映公众的生存体验和生活感受的艺术形态,皆可以称为公共艺术。

图1 皇冠喷泉
在这个意义上,将公共艺术简单等同于建筑装饰,城市街头或公园中的雕塑、公共艺术设施等的认知就略显狭隘与不妥了。早在1985年,美国洛杉矶所拟定的“艺术在公共场所”政策,较之以前的百分比艺术基金政策有了很大的突破,其扩大了公共艺术的范围,将艺术计划、艺术设施和文化信托基金等囊括其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共艺术现已超越了以往的视觉造型艺术范畴,而拓展至融合了各种感觉元素在内的诸多艺术领域。随着材料与技术的不断革新,现在的公共艺术创作亦注意吸纳数字化技术或移动互联网技术,尝试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合作,通过加入声音、灯光、图像等元素,加强艺术物化形态本身的可触摸性和可参与性,使得公众可以获取立体化的感官体验,并与艺术作品产生真正的交互对话。坐落于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内的《皇冠喷泉》(图1)即是这样一个突破了传统公共艺术形式而带给公众多重惊喜的新型公共艺术。而且,当下的公共艺术亦不再局限于以往偏静态性、永久性的艺术形式,临时即兴的表演艺术、行为艺术,包括暂时性的社区公益文艺展演、节日庆典、礼仪活动,因其内在的公共性愈加明显而皆可以被纳入公共艺术范畴之中。此外,传播于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公
共空间之中,被公众广泛关注,并引发公共讨论的艺术形式亦被部分学者称为公共艺术。由此可见,公共艺术是一个随着公民社会发展和公众艺术诉求变迁而不断变化拓展的动态性概念,对其进行讨论与研究必须采用一种历时性的方法和开放性的视野,才能准确把握其内核与宗旨。
二、公共艺术不等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
当下有许多人,甚至包括部分公共艺术创作者在内,皆误以为公共艺术就是“公共空间”和“艺术”的简单叠加,进而想当然地认为公共艺术(Public Art)便是“公共空间中的艺术”(Art in Public Space)。但事实上,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宽泛地讲,所有的公共艺术皆属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二者具有共同的空间属性和艺术属性。但严格来讲,公共艺术又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因为除了公共空间属性外,公共艺术还有区别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的许多要素。一般而言,艺术进入公共空间,便可以被称为“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但其远不能因此而被视为公共艺术。因为部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与传统的室内艺术或美术馆、博物馆艺术相比,除却生成或存放空间的差异外,并无本质的不同,仍是艺术家进行观念探索与艺术实验的个人化作品,更多的是艺术家个体经验与艺术风格的彰显,其并没有考虑太多公共要素,潜存着裹挟公众主观意志与艺术旨趣的可能性。而且,有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虽然被置放于公共空间之中,但并未与周遭的环境形成有机融合,遑论与当地公众建立有效对话和良性互动,甚至与其所在场域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所以,“公共空间中的艺术”绝不等同于公共艺术,尽管此类艺术存在于开放性的公共空间之中,并可能获得了某种资金的支持,亦得到了政府权力机构的认可,但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公共艺术本体规定性——公共性的缺乏。
尽管“公”与“私”的概念区分和事实对立自古便已存在,但相较于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政治与有限的公共自由(仅针对特定的阶级或阶层),普遍意义上的民主与公共性应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性是公众在公共领域中自由交流和开放性对话的过程,是一种就公共事务平等表达个体意见的公共权力机制。其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对每一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等权利的肯定和尊重,也体现了公众对公共领域自觉的权利要求和主动的参与意愿。即是说,公共性存在于当代社会任何一个因普遍性利益而集合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公共领域之中,彰显的是一种平等对话与自由协商的公共精神。具体到艺术的公共性,则可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加以简单理解。
从艺术创作层面讲,区别于以往从政治性功能需要或“为艺术而艺术”纯粹审美诉求出发的艺术创作,艺术的公共性,强调公众艺术意愿的平等表达。公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艺术接受者,而可以参与到从策划到立案再到实施的整个艺术创作过程,其艺术理想和审美旨趣将得到充分的尊重。不仅如此,一旦该艺术方案与绝大多数公众的意愿相违背,公众有权对其进行否决。由此而生的艺术品,便有可能超越国家权力象征或艺术家个人“作品”的层面,而成为综合各方需要、体现公众意志、彰显公共精神与多元价值的公共艺术。
从艺术接受层面讲,与局限于皇宫府邸、私人宅院或艺术沙龙等多少带有私密性的接受空间不同,艺术的公共性,拒绝权力阶层或贵族精英对于艺术接受和审美鉴赏的垄断,而诉诸艺术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力求接续被审美自律性逻辑割断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本然关联,旨在重建公众与艺术间的多重对话关系。这种公共性最直接的表征便是艺术“下架”,走出美术馆、博物馆,进入开放性公共空间,以各种艺术语言与形式表现公众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同时,与公众产生紧密的互动关系,而且艺术的所有权归属公众,为公众所共享和共有。[3]
所以说,公共艺术绝不是简单的艺术置放空间由室内到室外的位移转换,被放置于公共空间之中,仅是艺术成为公共艺术的前提条件,决定其是否是公共艺术的关键质素在于公共性,在于公民权力的彰显与表达。恰如国内公共艺术研究学者孙振华所言:“公共艺术的出现,反映了市民阶层对于公共空间的权力要求和参与的意象,它与社会公共事项的民主化进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公共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力的体现。”[4]简言之,只有具备了
公共性的公共空间艺术才是真正的公共艺术,否则便只是徒有其表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
三、公共艺术不限于城市公共空间
众所周知,公共艺术主要的生成场域与空间载体是现代都市,关于公共艺术的现有讨论或理论研究也基本上以城市为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艺术仅限于城市公共空间,而无法作用于城市之外的其他广阔公共空间;也不等同于其仅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或市民阶层服务,而无法惠及普通的村民百姓。因为尽管公共艺术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但随着公共艺术的发展演变,其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愈发重要,其早已超越了单一的艺术形态而成为一种理想艺术精神的象征,一种当代民主化、福利化社会的重要标杆。
基于此,如果将公共艺术的服务对象仅仅圈定于市民阶层,显然有悖于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价值内核和互惠共享的文化精神,公共艺术服务的对象包括整个社会的全体公民,所有人皆可以参与其中并从中享受艺术审美快感和文化福利。同样的,如果把公共艺术仅仅圈定在城市公共空间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则无疑是对公共艺术所能覆盖地域空间的严重低估,公共艺术适用于所有的公共空间。更何况,公共空间也并不局限于城市公共空间,至少还包括自然景观空间和乡村公共空间。所以公共艺术完全可以跳出城市空间,而介入到城镇与乡村,深入到普通村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具体到中国,公共艺术的作用场域似乎更不应该仅局限于城市空间。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催生了公共艺术的诞生,同时也导致了中国乡村的快速衰落。随着千百万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城市不断扩容和壮大,城乡生活水平差距愈拉愈大,农民对乡村家园的依赖感与认同感愈加弱化,进而导致当下农村人口锐减,老龄化问题尤其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在现代物质文明和城市化生活的冲击之下,乡村原有的乡土文化秩序、历史遗存或建筑古迹丧失殆尽,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民俗生态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大部分乡村也经历着类似于城市化进程过快而导致的信仰缺失、历史断裂等文化病痛。所以说,与当代城市一样,中国的农村同样亟需采取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诸种措施来补救濒临断绝的历史文化脉络和乡村传统记忆。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土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公共艺术能够也应该在中国的农村发挥更大的文化补救功能。

图2 欧宁的“碧山计划”手稿
唯其如此,中国的乡村再次进入了众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视野,当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公共艺术的触角由城市公共空间拓展至乡村公共空间。在他们看来,偏远村落的祠堂、旧戏台、田地,甚至是村道皆是进行公共艺术创作的理想场所。艺术家欧宁在安徽实施的旨在“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的“碧山计划”(图2),某种程度上便是公共艺术介入乡村,作用于乡村改造与建设的典型案例。该艺术计划邀请艺术家、建筑师、导演、音乐人、乡建专家、民间手工艺人、民间戏曲艺人等驻地进行艺术创作与交流,并通过影像放映、舞蹈祭祀、诗歌讨论等多元艺术形式来主导碧山的乡村改造。而且该计划尽力以当地村民作为主体,组织村民开展麻将比赛,引导村民进行艺术创作,并建立青年农场,进行集体化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从而让村民切身体会到由艺术所带来的活力与改变。尽管该计划带有某种程度的知识分子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强烈的启蒙与改造心态、不当的乡土迷恋与田园梦想支配下的现代知识分子,难以与当地村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沟通与观念共鸣,因而使得计划从实施之日起便存有争议,但其作为一个集社会性、公共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公共艺术事件,无疑开启并证明了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与生产的可能性与可行
性,公共艺术走出城市、深入乡村正在成为一种现实,一种公共艺术的新型存在方式。

图3 《深圳人的一天》局部
四、公共艺术不止于公共空间美化
不可否认,公共艺术诞生于城市建筑的美化与都市空间的改造,其最初的功能更多集中于城市建筑空间的点缀与装饰。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僵化地认定公共艺术的功能仅限于公共空间的美化,因为随着后来公共艺术的广泛传播与日趋成熟,其功能不断拓展,其功能愈加丰富,除了自身的艺术审美价值之外,还衍生出诸多社会文化价值、商业价值,甚至具有关乎城市文化形象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的战略性价值。具体表现在:
其一,公共艺术由于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性,使其区别于公共空间中的自然景观或公共设施,而多少带有艺术的质感与美感。尤其是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不仅能够与所在的空间形成完美的融合,而且可以妆点和美化其周围的环境,与其外在空间形成良好的“场效应”,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美感与格调、形象与气质,无形之中还可以起到社会美育的作用,在丰富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提升公众的艺术审美水平与生活品位。
其二,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文化最直观、最鲜明的载体。优秀的公共艺术甚至可以连接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方面是对城市文化脉络的接续和对城市文化记忆的重现,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趋势。这些带有鲜明城市烙印的公共艺术作品,不仅可以唤醒公众记忆深处的城市印象和记忆,而且可以增加他们对所在城市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可以激发公众反思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化他们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自觉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城市公共艺术在一座城市的大范围出现,能够培育当地的文化创新能力,营构一种文化自我“生长”氛围,久而久之,有助于城市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打造新型城市名片。
其三,作为一种深度介入社会的当代艺术力量,公共艺术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尝试着把原本属于市民公众的文化和艺术权利及相关的社会共同资源归还于民,让公众在参与公共艺术实践、与公共艺术互动的过程中,共享社会文化福利,并由此培养市民大众的公民意识以及参与协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动精神,从而使民众成为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体。尤其是社区作为社会的全息缩影与城市的细胞,是现代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某种程度上,城市社区的发展状况标志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公共艺术介入社区文化建设,作用于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无疑会有效解决当代中国居民社区普遍存在的社区文化环境一般,居民自治空间不足,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高、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淡薄等突出的问题,通过积极发挥公共艺术的价值功能,能够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善、社区文脉的传承、社区民心的凝聚和社区活力的提升,进而增强社会的和谐度,激发城市的活力与热度,提升公众的幸福生活指数。
此外,公共艺术虽属于艺术品范畴,却潜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其商业价值并非是指公共艺术作为商品的价格,而是指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外化物质形态,本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符号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其不仅仅是城市的旅游文化资源,更象征了城市整体的文化活力与艺术格调,甚至是整个城市的形象代表,而这一切皆可以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商业活力或是直接的商业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演变成了当地知名的旅游景点,甚至成为所在城市的新型地标。例如,无论是早期的《拓荒牛》还是后来的《深圳人的一天》(图3),都与深圳这座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移民城市形成了完美契合,以艺术的形式完成了对于
城市历史的记述。作为公共艺术的典型案例,二者皆成为了深圳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景观,无形之中也为深圳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结语
不难看出,随着现代社会开放与民主程度的不断扩大,公共艺术的概念内涵、作品形态、运作机制与价值功能等处于持续的变化和拓展之中。尤其是被引入中国之后,公共艺术不可避免地历经被中国化和在地化的过程,故而呈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面貌特质与价值形态。这也使得对于这样一个动态复杂的艺术概念加以准确而清晰的内涵界定变得异常困难。但或许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随着公共艺术实践的不断拓展和公共艺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公共艺术作为一种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当代艺术形态,如今已基本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公共艺术已成为广大市民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彰显社会主体地位的重要路径。公共艺术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定会释放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1]哈莉叶·西奈,莎莉·韦伯斯特,主编.美国公共艺术评论[M].慕心,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9:203.
[2]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
[3]李雷.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构建——21世纪中国公共艺术生态考察[J].文化研究,2014(3):114.
[4]孙振华.公共艺术时代[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37.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Conceptual Extension and Functional Shift of Public Arts
Li Lei
The connotation,representation,mechanism,and function of public arts as a dynamic concept have been expanding. Through constant development,public arts have evolved into cultural ideas and artistic beliefs other than the original welfare policy.Public arts put premium on the social value of arts,which lends testimony to the new orient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s,city,the public and social relations.By artistic cultivation,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s aims at realization of a modern civil society characteristic of openness,publicity,and democracy.
Public Arts,"Arts in Public Space",Publicity,Urbanization,Community Culture Cultivation
J0
A
1003-3653(2016)03-0042-06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3.008
2016-04-18
李雷(1982~),男,山东泰安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公共艺术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美学、当代审美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般研究项目“公共艺术介入北京社区文化建设研究”(ICS-2016-B-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