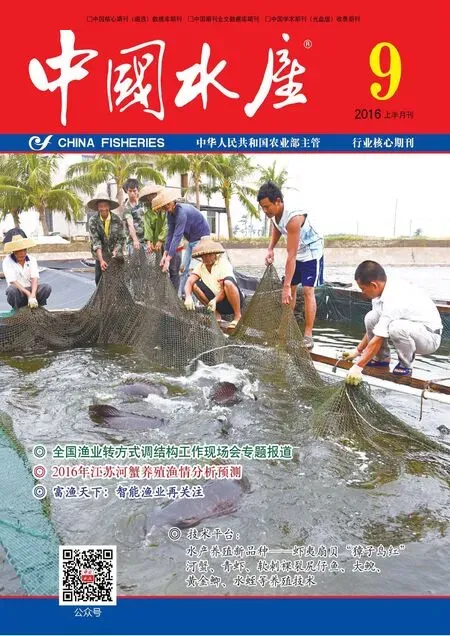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物种和区域选择需要注意的问题
2016-10-14罗刚
文/罗刚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物种和区域选择需要注意的问题
文/罗刚
增殖放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合理规划放流水域和物种是增殖放流工作取得实效的前提和关键。为促进增殖放流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本文就增殖放流区域布局和物种选择进行深入分析,根据增殖放流工作相关制度规范和指导意见,系统提出增殖放流区域和物种选择需要注意的原则性问题,为各地增殖放流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对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渔业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各界资源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随着增殖放流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一些地区也存在布局不合理、针对性不强、生态效益不突出、整体效果不明显等问题,甚至可能产生潜在的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安全问题。
增殖放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规划是增殖放流事业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各地应根据境内水域和水生生物资源分布状况、特点以及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习性,结合当地渔业发展现状和增殖放流实践,科学规划适宜增殖放流的重点水域和物种。为确保放流取得实效,保障原有水域生态安全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充分发挥,推进增殖放流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增殖放流区域布局和物种选择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放流水域
(一)放流水域的公益性
增殖放流水域主要是能够为全社会共同利用的开放型公共水域,不包括由特定单位和个体经营利用的非公共水域。为体现增殖放流的公益性,宜选择跨行政区域的开放性江河湖泊、城市的水源地以及边界水域等重要水域开展增殖放流。目前我国部分沿海滩涂和内陆小型水库(小于50平方公里)多被私人承包,如在以上区域开展在增殖放流,需要注意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问题。部分内陆中型及以上水库(大于50平方公里)如属于私人承包经营,也不宜作为增殖放流水域。
在人工鱼礁及海洋牧场区域开展增殖放流,若技术措施和管理方式得当,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财政资金一般不宜支持在功能为增殖型或休闲开发型的私人企业性质的人工鱼礁或海洋牧场区域开展增殖放流,可以支持功能为资源保护型以及生态环境恢复型的,且由政府相关部门严格管理的公益性质的人工鱼礁或海洋牧场区域。
(二)放流水域生态环境适宜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电开发、围湖造田、交通航运和海洋海岸工程等人类活动的增多,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重要江河均遭受不同程度污染,部分湖泊呈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河口、海湾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多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在环境污染区域开展增殖放流,需充分考虑放流苗种成活率和放流实际成效,增殖放流功能定位宜选择净化水质和改善生态环境,放流地点宜选择污染程度较轻的水域,避开污染源和重度污染区域。
此外,近年来部分地区大规模开发水电资源,流域生态环境和水文特征发生重大改变。在此区域开展增殖放流,要充分考虑水电工程可能对增殖放流鱼类造成不良的生态影响,科学选择放流地点。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水体气体过饱和。在高水头大坝泄洪过程中,水体中的溶解气体往往处于过饱和状态,而溶解气体过饱和容易导致鱼类患气泡病死亡。热电厂等单位排放的温度较高的废水,使一定区域内的水体水温升高,也会引起气体过饱和。据有关调查,在葛洲坝建成初期,曾发生泄洪导致坝下鱼苗死亡的现象,2003年三峡大坝初期蓄水泄洪后,下游捕捞鱼类暂养相比过去存活时间明显缩短,初步分析这些鱼苗及暂养鱼死亡与水中溶解气体含量有关。二是调水调沙。水库进行水力排沙时水库下游河流水体的物理理化性质的变化可能对鱼类等水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主要是微颗粒泥沙淤堵鱼鳃影响其摄入氧气功能和水体溶解氧下降,严重时出现死鱼。例如,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在进入汛期时进行开闸放水排沙,随着下游河流含沙量的提高和排沙时间的持续,就会使很多鱼类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在水面漂流,被称为黄河“流鱼”现象。三是低温水下泄。高坝形成的水库存在温度分层现象,如果下泄水流位于“跃温层”以下,则夏秋季节下泄水温低于天然水温,冬春季节下泄水温高于天然水温。很多鱼类对水温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水温对鱼类的生长、发育、繁殖、疾病、死亡、分布、产量、免疫等均具有重要的影响。三峡大坝蓄水后,由于温度较高的上层水先行下泄,坝下河道秋冬季水温高于高于自然状态,导致近年来中华鲟产卵时间从以往10月中旬延迟到11月中旬。四是其他水文特征改变。鱼类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和演变,会选择适合生存的地方作为自己的产卵、索饵、越冬等栖息场所,栖息地包括水深、流速、水温、底质、弯曲度、泥沙等条件。鱼类的这种习性是一种长期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大坝的修建会改变天然条件下鱼类栖息地的上述条件,鱼类往往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原有的溪流性鱼类可能在流速缓慢的水库静水区域难以生存。例如,三峡大坝蓄水后,秭归至万州段水体转为静水水体,原有喜流性鱼类白甲鱼、中华倒刺鲃、岩原鲤等在渔获物中比例已经很少,铜鱼资源也明显下降,而黄颡鱼、鲤、南方鲇、鲢等缓流性或静水性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例上升。
(三)放流水域的保护措施
放流水域是否具备有效的保护措施是增殖放流取得实效的关键。放流水域缺乏有效保护也是目前增殖放流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开展增殖放流,上游刚刚放流结束,下游就有渔民非法捕捞,放流效果可想而知。为确保放流取得实效,切实提高放流成活率,就要强化增殖放流水域监管,通过采取划定禁渔区和禁渔期等保护措施,强化增殖前后放流区域内有害渔具清理和水上执法检查,以确保放流效果和质量。从提高增殖放流成效的角度,增殖放流实施水域宜选择具备执法监管条件或有效管理机制,违法捕捞可以得到严格控制的天然水域。其中部分鱼类、两栖、爬行类、贝类等活动范围较小的珍稀濒危物种建议仅支持在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特定的渔业资源增殖区内放流。
(四)放流水域的工作积累和整合
增殖放流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实际成效的取得可能需要历年不断的工作积累。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省通过持续在近海开展中国对虾增殖放流,严重衰退的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补充,中国对虾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秋季渔汛,全省秋汛中国对虾回捕产量2005年为1089吨,2010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000吨左右,5年增加了近两倍,参与回捕的渔船单船日产中国对虾最高达2000公斤,近海中国对虾资源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为有效发挥增殖放流规模和累积效应,放流选择水域宜相对固定,具备条件的地方应积极探索建立固定的渔业资源增殖区及配套的增殖站,专业化从事增殖放流。
从国内外资源增殖实践来看,孤立地进行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往往成效较低,应积极提倡“资源增殖体系”的观念,把各种孤立的措施按照时空特点组合为一个体系,形成近似于生产农艺或工艺的程序化的制度或习惯,以获取渔业经济的最佳的、持续的效益。为此日本先后提出并开展了“栽培渔业”和“海洋牧场”建设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在濑户内海建立第一个栽培渔业中心后,把多种技术的应用与海洋牧场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增殖放流经验和成熟的技术,鲑鱼、扇贝、牙鲆等的增殖已十分成功。因此,各地增殖放流区域选择根据增殖放流功能定位,可以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人工鱼巢、人工鱼礁及海洋牧场建设等工作相结合,辅以相关禁渔养护措施,有效整合相关工作,形成资源养护合力,发挥更大成效。
放流物种
(一)放流物种的种质来源
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按照以上规定要求,增殖放流的物种应当是原产地原生物种(土著种),改良种(包括选育种、杂交种和其它技术手段获得的品种)、外来种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物种均不适宜进行增殖放流。
一是要避免放流种质混杂的物种。特别是鲤鲫鱼类要慎重开展放流。主要原因:一是天然资源中的鲤鲫鱼种质难以控制。我国现有的鲤鱼种群、品种之间,由于不加节制的杂交,杂交后代混入天然水域,造成了我国鲤鱼种质的混杂,在长江、珠江和黄河流域已很难找到不受遗传污染的鲤鱼原种。因此,增殖放流的鲤鲫鱼种质纯正的亲本难以从天然资源获得。二是国内目前养殖的鲤鲫鱼种质也难以控制。目前国内鲤鲫鱼养殖品种繁多,种质混杂,放流苗种来源不易控制,如随意放流可能造成基因污染。目前已发现有部分区域增殖放流的鲤鲫鱼为选育种和杂交种。三是放流鲤鲫鱼类苗种种质鉴定不易。鲤鲫鱼类种质通过简单的外观鉴别、可数性状测量等方式很难鉴定区分,需要到实验室进行复杂的检验检测。导致增殖放流苗种种质鉴定十分困难。四是鲤鲫鱼类开展增殖放流作用有限。鲤鲫鱼类本身繁殖条件要求不高,在静水中即能完成整个生活史,因此保护好其栖息地也可逐渐恢复其资源量。鉴于以上因素,《农业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划放流物种中删除了鲤鲫鱼类,即中央财政资金原则上不支持鲤鲫鱼类放流,各省如要开展放流,需通过专家论证,并报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备案。使用其他资金开展放流,也须确保放流苗种种质纯正,来源清晰。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的鲤鲫鱼类特指分类等级种的水平以下的亚种、地理种、变种及各种品种(黑龙江野鲤、黄河鲤、元江鲤、彭泽鲫、淇河鲫、瓯江彩鲤、西吉彩鲫等),不包括鲤鲫鱼类分类等级种的水平以上的其他不同种,比如大头鲤、杞麓鲤、抚仙鲤、尖鳍鲤等。
二是不宜跨水系跨流域放流物种。我国内陆水域的鱼类、两栖类及爬行类都存在地理种群(即地理上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形成不同的地理亚种)。放流物种的亲本应来源于放流水域原产地,即“哪里来哪里放”原则,放流物种的地理种群不宜混杂,否则可能形成潜在的生态风险,后果难以预测。例如河蟹在我国不同水系已形成长江、辽河、瓯江、闽江等不同种群,有不同的形态表型和特征,这是长期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但是,近20年来,河蟹增养殖在我国发展很快,由于苗种北运南调和盲目移植,已引起河蟹不同水系间种质混杂和性状衰退。按照这一原则,为提高增殖放流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指导意见》将全国内陆水域和近海海域按照生物区系和地理水文特征进一步划分为35个流域和16个海区,强化了流域和水系划分。比如,在我国珠江流域增殖放流中华鲟,只能放流从珠江水系捕捞的中华鲟以及其子一代,而不能放流长江水系的中华鲟及其子一代。考虑到闽江、珠江水域中华鲟野生资源已基本消失,增殖放流中华鲟苗种来源受限,《指导意见》在闽江、珠江流域放流物种规划中删除了中华鲟。此外,还有一些物种经过长期进化,在不同流域或者水系形成了新的物种,更不能跨水系跨流域放流。据最新研究表明,鲈鲤属鱼类就存在着这种特殊的地理格局, 即在青藏高原南部的每个主要水系中只分布一种,即金沙鲈鲤(长江上游,包括金沙江等)、花鲈鲤(抚仙湖)、珠江鲈鲤(珠江上游、贵州的南北盘江等)、后背鲈鲤(澜沧江)、萨尔温鲈鲤(怒江)、张氏鲈鲤(元江)。
三是避免放流区域性外来物种。外来物种是指在某地区或生态系统原来不存在、由于人类活动引入的物种,其中来自国际间的称为国外外来物种,来自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称为区域外来物种。区域外来物种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亚种,另一类是不同物种,即本区域原来没有的物种。通常大家提到的区域外来物种指的是第二类。区域外来物种对生态环境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我国东部江河平原区系鱼类,如“四大家鱼”(青草鲢鳙)被引进到西北和西南部高海拔水域,这些物种以及随这些物种的引进而带入的小型杂鱼(鰕虎鱼、麦穗鱼等)所引起的灾难并不亚于国外的物种所引起的灾难。为避免放流区域外来物种对原有水域生态安全造成影响,《指导意见》在部分区域删除了区域外来物种,并在附表中阐明了淡水广布种、区域性物种的分布区域。也就是说广布种也不是全国各流域水系均可开展增殖放流,一般来说不宜在青藏高原、西北内流河水系、西南跨国河流水系等非原分布区域的水体放流。此外,淡水区域性物种不宜在原分布区域外的开放性水体放流,目前这种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团头鲂原产于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属栖息于静水中的物种,现已被引入全国多个省市开展养殖,甚至在江河中开展增殖放流。
(二)放流物种的优先选择
为有效发挥增殖放流规模和累积效应,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避免出现放流水域、物种重点不突出不匹配以及放流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水域增殖放流宜突出重要或特有增殖物种,种类不宜多,防止面面俱到或千篇一律。此外,根据增殖放流历史实践来看,增殖放流要想取得明显成效,需要在适宜水域长期重点开展一种或几种水生生物的放流。美国向海洋放流鲑鱼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联邦政府及西海岸各州建立了众多鲑鱼孵化场,在西太平洋沿岸主要开展太平洋银鲑、大鳞大麻哈鱼、大麻哈鱼三种鲑鱼的增殖放流,使海洋中的鲑鱼资源得到大幅度增殖,目前三者的产量的46%、40%、4%均系从孵化场培育出来后放流入海的。
重要物种是指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通常是该水域历史上数量或产量比较高的物种。特有物种是部分地方特有的,具有较高经济、生态等价值的物种。对于部分小型野生鱼类,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繁殖条件要求不高的,一般不宜作为主要增殖放流物种,例如洛氏鱥、红鳍鮊、马口鱼等。
(三)放流物种的针对性
针对水域存在的渔业资源衰退、濒危程度加剧、蓝藻赤潮等生物灾害爆发以及水域生态荒漠化等问题,各地应结合渔业发展现状和增殖放流实践,合理确定不同水域增殖放流功能定位及主要适宜放流物种,以形成区域规划布局与重点水域放流功能定位相协调,适宜放流物种与重点解决的水域生态问题相一致,推动增殖放流科学、规范、有序进行,实现生态系统水平的增殖放流。定位于渔业种群资源恢复,放流物种宜选择目前资源严重衰退的重要经济物种或地方特有物种;定位于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放流物种宜选择杂食性、滤食性水生生物物种;定位于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放流物种则选择珍稀濒危物种和区域特有物种;定位于渔业增收和增加渔民收入,放流物种宜选择资源量容易恢复的重要经济物种。
目前《指导意见》规划的主要经济物种是指具有公有属性和重要经济价值的鱼虾蟹等游泳生物,不包括贝类、藻类等定居性物种。但实际上贝类、藻类等净化水质,吸收有害有毒物质能力很强。近年来,相关部门在长江口水域开展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增殖放流巨牡蛎,在河口形成106.5万吨的生物量,每年去除营养盐和重金属所产生的环境效益等同于净化河流污水731万吨,相当于一个日处理能力约为2万吨的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因此建议在一些河口及港湾等污染严重水域,且不属于特定单位和私人经营利用区域,可以由财政支持开展贝藻类等定居性种类试验性增殖放流,已达到水域生态修复的目的。此外在人工鱼礁、海洋牧场以及内陆人工藻场等具备监管条件的公共水域也可以开展贝藻类等定居性种类的增殖放流,以利于有效修复水域生态,促进生态平衡。
(四)凶猛性鱼类的放流策略
凶猛性鱼类对于维持水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以将经济价值较低的野杂鱼转化为附加值较高的经济鱼类,有利于渔业增收。但凶猛性鱼类增殖放流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江苏省于2002~2004年在太湖放流翘嘴红鲌鱼苗,总数达257.7万尾,达到平均0.09公顷分布1尾,大规模的放流对太湖大银鱼和太湖新银鱼等鱼类资源产生较大影响,使2004~2005年太湖银鱼产量进入历史纪录以来的最低点,几乎没有产量。因此,凶猛性鱼类增殖放流需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进行生态安全风险评估,充分考虑其不利影响和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根据其不同物种的生物习性、资源状况、水域特点及增殖放流功能定位,科学确定是否开展放流以及具体放流策略,以确保原有水域生态安全。具备条件的可先行开展试验性的增殖放流。考虑到可能存在潜在生态风险,各种凶猛性鱼类基本放流策略建议如下:鳡、鯮类凶猛性鱼类自然资源严重衰退,虽已部分突破人工繁育,但由于其异常凶猛,对鱼类资源危害极大,一般不作为放流对象;乌鳢、斑鳢类凶猛性鱼类目前增殖放流苗种供应没有问题,但其野外生存极强,并且能够自行扩散其他水域,同时目前还存在相当的资源量,一般不应作为放流对象;鲈鲤、哲罗鲑、单纹似鳡、巨魾等珍稀濒危凶猛性鱼类,目前资源已严重衰竭,宜尽快开展增殖放流;怀头鲇、南方鲇、白斑狗鱼、黑斑狗鱼等地方特有的凶猛性鱼类,目前资源已不断衰竭,宜在特定区域慎重放流。翘嘴鲌、鲇、鳜等广布性凶猛鱼类,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慎重开展放流,一般不宜单独作为放流对象,可作为放流其他物种的搭配对象,数量、规格和结构也要严格控制。

此外,从凶猛性鱼类放流功能定位来看,如果单纯从渔业增收的目的考虑直接开展凶猛性鱼类的增殖放流,可能对营养级较低的种类带来不利影响,可能改变水域的生物结构,破坏原有水域生态平衡,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如果原有水域凶猛性鱼类仍存在少量资源量,也可以考虑通过放流营养级较低的种类,修复食物链网络等间接手段恢复其种群资源。例如鲈鱼在山东省很少开展放流,但通过放流中国对虾、日本对虾等,鲈鱼的捕获量明显提高。
(五)放流种类的公益性
为充分发挥增殖放流多功能作用,体现增殖放流公益性,增殖放流物种选择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增殖放流活动不能过于注重本地渔民增收,增殖放流物种选择不能以定居性或游动性不强的水生生物为主,要积极增殖放流大范围洄游性的水生生物物种。目前部分沿海地区热衷于放流贝类、棘皮类、多毛类等定居性物种,增殖放流鱼类以恋礁性、底栖性鱼类为主,游泳性、漂流性以及洄游性鱼类放流较少,其结果是部分地区受益,甚至少部分人受益,难以体现增殖放流普遍受益的活动宗旨。二是增殖放流活动不能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要统筹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增殖放流活动社会参与面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对于企业或个人等社会行为可以完成的放流品种,财政资金不应予以支持。比如部分高档水产品,海参、鲍鱼、扇贝等。财政资金应重点支持企业与个人不愿进行放流的公益性品种。例如部分区域性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兰州鲇、哲罗鲑、大头鲤、抗浪白鱼、滇池金线鲃等,目前人工育苗难度大成本高,但因价格、消费习惯等因素导致市场需求量很低,其生产的苗种只能主要用来增殖放流。如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其苗种生产单位开展增殖放流,可能其苗种繁育生产工作将难以为继,相应的其物种资源恢复和保护工作也将难以开展。因此财政资金应积极支持这些种类的增殖放流,引导其苗种生产单位逐步扩大苗种繁育规模,以满足物种资源恢复的实际需要。此外,斑鰶、鲻、鮻等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有比较重要的生态位,但是由于其经济效益低下,人工繁育研究和实际生产少有开展,所以基本没有供苗量。这种有必要放流,而实际无法实现放流的品种,财政资金也应该重点支持。三是按照现代渔业发展全面贯彻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在放流物种和区域布局上,要以生态效益为先,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增殖放流功能定位上更加注重生态要求,物种选择突出水质净化、水域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作用,不断加大生态性放流的比重。例如传统名贵鱼类鳗鲡,珠江水系四大名贵河鲜中的斑鳠、卷口鱼,长江上游重要经济鱼类圆口铜鱼、铜鱼,澜沧江水系中国结鱼等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经济物种,本身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历史上曾是水域的重要经济鱼类。然而目前资源已严重衰竭,部分鱼类已多年不见其踪迹,亟需开展增殖放流以恢复其自然资源,但由于人工繁育技术不成熟等瓶颈限制不能开展规模放流,财政资金应积极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支持开展人工繁育技术研究和实验性的增殖放流活动。
作者单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