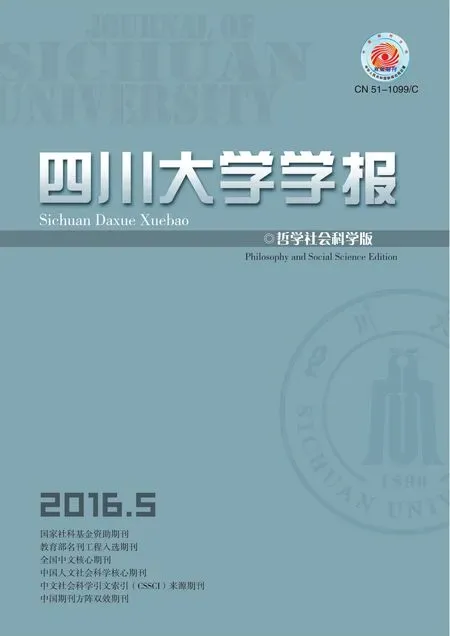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2016-10-13郭庆财
郭庆财
§古代文学研究§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郭庆财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朱熹;南岳酬唱;诗禁;“中和说”
南宋乾道三年丁亥七月,朱熹携弟子林用中访著名学者张栻于潭州,相与论学两月之久,其间曾与张栻、林用中相偕共为衡岳之游,且一路穷绝幽胜,往来酬唱,共得诗一百四十余篇,其中即景抒情、情气兼备之作往往而见,可谓理学家们少有的忘情之娱。这在朱熹的诗歌创作中也标示出了一个小高峰,并逐渐引起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参见王利民:《流水高山万古心:南岳倡酬集论析》,《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叶文举:《南宋理学家集会的文学因素及其思想内涵》,《国学研究》第二十八卷,第237-261页。对于研究者来说,除了南岳酬唱中的诗歌文本需认真研讨之外,三人在南岳唱酬后有一个禁诗之约,也颇值得玩味。
《南岳倡酬集》前朱熹、张栻各为序一篇,皆谈到禁诗问题。大意是,鉴于游山期间唱和诗太多,有“荒于诗”之慨,三人约定“异日当止”。但朱序又指出,禁诗七天之后的丙戌日,朱熹、林用中即将东归崇安,张栻远送至槠州,离别在即,朱熹又提出“解禁”,不过仍有怵惕警惧之情:
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然则前日一时矫枉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悠游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荧惑耳目、感移心志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朱熹:《南岳倡酬集原序》,《南岳倡酬集》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本文所引南岳酬唱诗均出此集。
在朱、张、林三人中,朱熹对作诗的态度最为复杂,大体经历了禁诗—解禁—自警的心理冲突。如何看待朱熹这种前后矛盾呢?莫砺锋先生在论及此问题时曾经指出,朱熹“表面上似乎还是对诗歌声色俱厉,实际上却已为之大开方便之门”。*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页。但是莫先生对朱熹的矛盾心态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论析。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此前也有数量繁夥的唱和之作,但对作诗感到愧悔与纠结这是第一次。其早年的次韵诗《次秀野韵五首》中有“惆怅春余几日光,从今风雨莫颠狂。急呼我辈穿花去,未觉诗情与道妨”之句,*《朱熹集》卷三,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就明言作诗与“道”并不相妨。除此诗之外,他坦陈诗酒情怀、觅句摛藻的酬唱诗甚多,与南岳酬唱“诗禁”中的自省戒惧之状大不相同。朱熹为何在南岳酬唱后突然对作诗的合理性问题敏感起来,这与其学术思想有何关系?本文以为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南岳酬唱诗风与朱熹的思想矛盾
我们不妨先从《南岳倡酬集》的文本出发,从体式、情思、风格等方面来考察一下其中的诗作,并从中略窥朱熹矛盾心理的原因。
首先,朱熹三人的南岳倡酬属于典型的师友唱和,采用唱和中难度最大的步韵,依原诗韵步步押韵且别创新词。这种“文本互涉”的形式决定了唱和之作(尤其是和作)难免有“依韵造语”的色彩,即为了应和诗韵而套用现有的模式化表达。三人唱和的部分诗语,可通过下表做一比较:

诗题朱熹张栻林用中《马迹桥》不用移文远见招。不为山僧远见招。《后洞雪压竹枝横道》山中景物总清奇。山中景物自新奇。《方广奉怀定叟》忽忆画船斋里人。城市山林虽一致,……每逢佳趣忆吾人。山林城市休关念,……独对西风忆羽人。……《莲花峰次敬夫韵》月皎风清堕白莲,……撩得新诗续旧篇。十丈花开自白莲,……强作新诗续古篇。《林间残雪时落锵然有声》青鞋布袜踏琼瑶,……恍疑鸣璬落丛霄。林中光洁尽琼瑶,……锵然玉佩响层霄。天花乱落类琼瑶,……数声佩玉遍青霄。《过高台获信老诗集》萧然僧榻碧云端,坐看君诗兴不阑。今朝移步野云端,幸得新诗读夜阑。《霜月次择之韵》莲花峰顶雪晴天。月华明洁好霜天。雪霁云收月满天。
从表中可以看出,和诗存在大量词汇重复、移用现象。因为在酬唱行程中,众人即兴唱和,吟咏对象相同且现场次韵,命意、结构、造语的雷同就是难免的了。其中,林用中所作以和诗为主,无力避复出奇且有窘迫之态,常常沦为续貂之作。相较之下,朱熹、张栻的唱诗尚能写出自己的一点面目,但个别诗作仍显造语粗疏,如朱熹《赋罗汉果》:“目劳足倦登乔岳,吻燥肠枯到上方。从遣山僧煮罗汉,未妨分我一杯汤。”即思致平平,亦无甚趣味。
其次,三人唱和诗以流连山水为主,偶有说理论道的成分也所涉不深。唱酬诗带有游戏性,其乐趣乃在于数人同为一题、往来步韵的难中见巧,以及各逞才学带来的自我满足感。不过,人的心思毕竟有限,由于唱和诗必专意于步韵、章法、用典、藻彩等诗歌体式,三人很难潜心于学理的思考和论辩,天理性命之思在诗中或被搁置,或偶尔有所流露却又因采用写景加说理的模式来表达,所传达的思想往往较浅直。如朱熹《崖边积雪取食清甚次敬夫韵》:“落叶踈林射日光,谁分残雪与同尝。平生愿学程夫子,恍忆当年洗俗肠。”由同尝山间残雪联想到修习二程之道亦有澡雪精神的功效,表达显得直白而少味。该集中的说理之作大抵如此,即思想模糊而肤廓,更说不上三人“思想的碰撞”。*如叶文举《南宋理学家集会的文学因素及其思想内涵》认为,南岳酬唱的诗作中,朱熹所谓的“天心”之上尚有“理”这一本体,而张栻诗中的“白云流水此时心”则以“心”为本体,因而与朱熹不同。细观之,叶文并没有对朱熹中和思想做过切实考察,而是以记录朱熹晚年思想的《朱子语类》作为分析朱熹南岳时思想的依据,因此得出了当时朱、张思想存在诸多分歧的结论,对二人思想差异的分析难免过当。
唱酬诗一向名声不佳,往往被认为缺乏思想和艺术价值,*参见周裕锴:《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马东瑶:《苏门酬唱与宋调的发展》,《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如上所析,南岳酬唱在思想与艺术方面亦不能无憾。但从朱熹的集序来看,其愧悔反省并非针对于此,他所着眼的反倒是酬唱诗“可以群”的交际性功能,认为这有助于沟通学者间的情感,可增进友谊,有“群居辅仁之益”,是酬唱诗所独具的优长。因此酬唱诗对声韵辞藻的讲求及学理的淡化,并不足以构成朱熹愧悔警惧的主要原因。
反观朱熹《倡酬集序》,其中说到作酬唱诗时,数次言及“流而生患”“流乃几至于丧志”等顾虑,这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儒者多以悠游中平为心性修养的追求,以“志”的流荡失中为警戒。从朱熹的倡酬诗来看,很多诗皆情思发露,神情气势都颇为流动。就写作视角而言,如果说前人的“万物静观皆自得”乃静心照物时的情感体验,而朱熹则采用了“动观”的方式仰观俯察,如《登定王台》以“千峰顶”为立足点,俯瞰的视角造成一种廖远高旷之感,《石廪峰》则仰观“七十二峰都插天”,将情思引入浑茫。另如其游山途中所作《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随兴所至,移步换景,诗思畅达活泼。与这种变换的视角相关,朱诗的情感亦颇为浓郁和流动,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霜月皓然、云气腾涌的衡山奇景激发了理学家们的山水之兴,三人豪情自然涌动,其中朱熹诗作尤为突出。远望莲花峰,朱熹作《莲花峰次敬夫韵》曰:“月皎风清堕白莲,世间无物敢争妍。如何今夜峰头雪,撩得新诗续旧篇。”一个“撩”字显示了衡山雪景对其诗情的触引和感发,而随着登临南岳绝顶,诗人情思愈壮,更有生机勃发、气格宏大之作。如《自上封登祝融峰顶次敬夫韵》:“衡岳千仞起,祝融一峰高。群出畏突兀,奔走如曹逃。我来雪月中,历览快所遭。扪天滑青壁,俯壑崩银涛。所恨无十犗,一掣了六鳌。遄归青莲宫,坐对白玉毫。重阁一徙倚,霜风利如刀。”此诗颇有风烟苍茫、通贯天地的磅礴之气,清人洪力行评曰:“登绝顶名山,须得有惊人之语,然非胸襟素具,不能矫也。‘扪天’、‘俯壑’四句,豪迈极矣。……想先生未落笔时,已早有荡地摇天、胸吞山岳气魄。”*洪力行:《朱子可闻诗集》卷二,见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卷五上,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460页。再如《醉下祝融峰》:“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更是文气流动,风情耿耿,绝无拘谨之态。
变动周流,情气发溢,乃是南岳酬唱时朱熹诗作的主要特点。钱穆先生在论及朱熹的诗风时称:“惟朱熹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之文学》,第五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此论是就朱诗的总体倾向而言,并非全面,至少朱熹南岳酬唱的很多诗就难以称得上“雅澹”。朱熹对作诗的陷溺和流荡之警觉正缘于此。作诗和“禁诗”之间的心理纠结,其核心乃在于作诗“言志”和“丧志”之间的尺度不好把握。自邵雍以来的理学诗派亦宣扬“诗言志”之旧义,而本着对性理精神的信守,他们的诗言志其实即是“诗言性”,亦即诗歌是对于人生哲理和道德境界的呈现;*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二册,第279页)论及邵雍的性情思想时说:“这样‘性’就代替了‘情’;而‘明心见性’就代替了言志与抒情。”但是诗歌写作往往伴有无定向的情思萌动,形成不吐不快的情感流,难免会造成对清明理性的瓦解和伤害,即“言志”而难免于“丧志”。一味作诗而缺少“戒惧警省”的工夫,则会造成情思之放逸,朱熹序文中称之为“流”;尤其是离群索居时的德性修习对自我操存功夫要求更高,若热衷于作诗更容易“流而生患”。
二、中和旧说与志、气关系
朱熹对于作诗既热情又警戒的矛盾态度,实际带有乾道三年其思想转变的独特印记。朱熹在入湖湘访张栻的前一年(即乾道二年丙戌)刚刚确立了“中和旧说”,*关于朱熹发表中和旧说的时间,学界一向颇有争议。钱穆、刘述先等人以为中和旧说完成于乾道四年戊子,牟宗三、束景南、陈来等人认为是在乾道二年丙戌,本文采用后说。此问题可以参见陈来先生的相关考辨(《朱子哲学研究》第七章《已发未发》所附“中和旧说年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另外,朱熹《答许顺之》第十一书中曾专门提及自己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绝句,该诗与中和旧说第一书“消息相通”(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论未发与已发》,第二册,第234页),故《答许顺之》第十一书写作时间应与中和旧说的形成时间相去不远;由书中所言 “刘帅遣到人时已热,遂辍行”,所谓“刘帅”,是指刘珙时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而乾道三年十一月刘珙已转任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参见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可知第十一书当作于乾道三年,据此中和旧说至少不应晚于乾道三年朱熹赴衡湘。其在《酬唱集序》中所表示的愧悔和警戒,实际反映了他对于中和旧说的犹疑,而这正是朱熹复杂诗观的思想背景。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情欲的适当节制是一个久远的话题。如何以道德约束情感且约束至何种程度才能合乎人性,更是奢谈道德心性的理学家关注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礼记·中庸》的“中和”说成为他们重要的思想资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5页。所论的正是德性修养中对情感变化的控驭问题。宋人对《中庸》文本极为关注,而何为“未发”“已发”以及两者的主体究竟分别是什么,二程、杨时、胡宏等人所论皆有分歧。*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第二章《程伊川分解的表示》第六节《中和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第十三章《未发已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对此问题,朱熹历经长期的思考、切磋和自我更正,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和旧说”和后来的“中和新说”,而张栻则一直是朱熹中和学说的主要讨论对象。该问题涉及朱熹理学之心性动静问题,与作诗之心理机制亦有相通之处,故我们不妨先对其中和旧说略窥一二。
(一)凡言心皆为已发。朱熹在给张栻论“中和”的第四封信中说得很明确:“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朱熹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第1373页。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两者为内外体用的关系,此即朱熹“中和旧说”之核心观念。所谓“天机活物”,朱熹又称为“天命流行之体”,乃为浑然无分际、无间断的心,虚灵不昧而应物无穷,其作用从未停止;性(即是理)作为心之本体,超乎形气动静之外,“未发”实即“不能发”,不能显现,因而被搁置起来,中和旧说所关注的其实是心的“已发”。既然此心莫非已发,因此无需刻意把捉,只要勿忘勿助,自然可以触处朗然,通于大本达道。从“於穆不已”“纯亦不已”的心体中见出活泼泼的气象,是朱熹中和旧说所强调的精神,他以著名的绝句诗《观书有感》记述了这一体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用了隐喻的手法,极富于理趣。若结合中和旧说来看,半亩方塘即是心的隐喻,源头活水即是心体念念相续、冲融无间断的流行状态。
既然凡言心皆为已发,也就肯定了此心念念相续的意识流动过程,许多心灵活动也被视为必然和不可避免,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了情感的发溢,打消了作文害道的顾虑和矜持。这是一种活泼无碍、万涂竞萌的心理状态,与诗家津津乐道的精鹜八极、神思遒举颇有相通之处,在此心境之下所作诗歌也呈现出一种流动婉转的活泼之美。而就三人所面对的南岳山水而言,既可以从中观天地之生气和生理,亦可由此体验心体之“发”。北宋理学家早已确立了“观物理以察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3页。的格物传统,即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于物上观察其理,亦能体悟自我之心性。朱熹的中和旧说即认为:良心萌蘖的因事发见与天命流行之体的显发乃是二而一的关系。*参见《朱熹集》卷三十二《与张钦夫》,第1290页。因此,人心即是天地之心,作山水诗是体认自然造化之妙,亦是写心、领悟生命的意义。这样,南岳的霞光山色、霜月云根,在理学家那里便有了一种生生不已的天命流行色彩;而在朱熹文心的观照下,更显得气象混茫,满盈着冲和阔大之气。因此,从朱熹酬唱诗作本身来看,我们很难看到“性其情”的节宣其情的理学工夫,而更多的是“诗情缘境发”*皎然:《昼上人集》卷一《五言秋日遥和卢使君》,四部丛刊本。及“情与气偕”*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4页。的诗学精神。
(二)对“气以动志”的反省与对“敬”的关注。如果细绎朱熹的中和旧说,其实更接近于自孟子以来至于大程子的一脉。孟子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有本者若是。”*《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泉源混混,乃是本心之知觉虚灵不昧、流行不息的一种比喻。程颢注重仁者自由安乐的心理体验,尤其重视活泼泼之心体,他说:“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程集》,第76页。而朱熹中和旧说也讲“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浑无间断,似乎是对孟子、程颢“心体”之说的发扬。不过,孟子、大程子至善而无迹的良心之“发见”,在朱熹那里则往往具化为形气之“发动”,如其所言:“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只是来得无穷,便常有个未发底耳。若无此物,则天命有已时,生物有尽处,气化断绝,有古无今,久矣!”*《朱熹集》卷三十二《与张钦夫》,第1290页。朱熹在“气”的层面上讨论超越的心体,所说为“气化之迹”,牟宗三先生认为“仅为一气机鼓荡之直线流,其心之发动往往降格于气息流行上说,其论心乃是平看的实然的心”。*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第二章《程伊川分解的表示》第六节《中和篇》,第79页。也就是说,气才是心体流行的实然的动力。但是孟子早有谨防“气以动志”之训,朱熹认为凡言心则为已发,放任了“气”的一味流行,难免会“动志”,造成对性理的损害和修养的妄躁。
中和旧说中隐含的“志”与“气”矛盾,亦即纯净至善的性理和念念不已的情气之间的矛盾,从乾道二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朱熹,对此他曾从行为日用中自省:“盖其所见一向如是,以故应事接物处但觉粗厉勇果增倍于前,而宽裕雍容之气略无毫发。”*《朱熹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第1372页。这一矛盾直到乾道三年入湖湘访张栻也未得到满意的解释。既然凡言心皆为已发,那如何使心中情思之发能中律合道?心有没有一个静定的“安宅”?即使在南岳游山后朱熹仍旧表达了这种困惑:“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所谓“几微之间、毫忽之际”,亦即“寂感真几”的心体的微妙活动,如何恰当把控使其获得未发之中、已发之和?这其实既是心性修养的问题,也是作诗的合理性问题。
对中和问题的探索与困惑,使朱熹对“涵养用敬”逐渐有所关注和强调。因为“敬”作为心灵自律功夫,不但是存心养心之要法,也是“致中和”、涵养宽裕雍容之气的保证。朱熹对“敬”的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乾道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早在乾道二年,朱熹给张栻论中和的书信中开始提及“致知格物、居敬精义之功”,其同年所作《答何叔京》第三书云:“若果见得分明,则天性人心、未发已发,浑然一致,更无分别,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终其业。”但这仅是一笔带过,未有深论,直到乾道三年初赴湖湘前所作的《答何叔京》第六书他才大畅厥旨,专论“居敬集义”之意:
尝窃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气有以动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临事接物之际,真心现前,卓然而不可乱,则又安有此患哉?或谓:子程子曰:心术最难执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尝曰:操约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内,故其义有以方外,义集而气得所养,则夫喜怒哀乐之发,其不中节者寡矣。*以上引文分见《朱熹集》卷三十二、卷四十,第1373、1843、1849页。《答何叔京》第六书书作于朱熹湖湘之行约半年之前,可参见陈来先生《朱熹书信编年考证》(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3页)中的相关考证。
虽然朱熹此时对“敬”的体认尚浅,但毕竟提供了解决“志”“气”矛盾的一种方法。孟子即已倡明“夫志,气之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的宗旨;*《孟子·公孙丑上》,《十三经注疏》,第2685页。理学家亦承认“志”对于“气”具有优先性,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摆脱“情思”之“气”的搅扰而主“敬”,以“志”率“气”,维护纯一的性理,防止情感的放逸无归,“言志”而不“丧志”,这体现了朱熹对作诗的自觉和反省。
南岳酬唱时朱熹的思想状况,一方面是“心为已发”的念念未已,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气的不免流荡;另一方面是对“敬”的关注和强调,形成对情、气的约束。这两方面对作诗所起的作用是正相反对的,也是朱熹在游山时难免忘情作诗,冷静下来后又警惕作诗的矛盾之根本症结所在。作为有志于优入圣域的理学家,朱熹的天平必然会向“敬”的一方倾斜,致使其对诗文创作的检束也愈发严格。这一倾向从其南岳之行结束后的《东归乱稿序》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朱熹与张栻告别后,偕范德念、林用中返闽。途中除了讲论问之外,凡感事触物亦形于诗作,这即是《东归乱稿》。其序曰:
盖自槠州历宜春泛清江,泊豫章,涉饶信之境,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后至于崇安,始尽胠其橐,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取而读之虽不能当义理,中音节,然视其间则交规自警之词愈为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见而不忘者,以故不复毁弃,姑序而存之以见吾党直谅多闻之益,不以游谈燕乐而废。
此序态度明确,不再是《南岳倡酬集序》中游移于体道与抒情之间的无所适从,而是以“交规自警”为创作的主导精神。在《东归乱稿》中,他也以诗表达此种思想:“不是讥诃语太轻,题诗只要警流情。烦君属和增危惕,虎尾春冰寄此生。”*以上所引诗文分见《朱熹集》卷七十五《东归乱稿序》、卷五《东归乱稿》,第3941、214页。申明了其反对诗人情感放逸及怵惕警醒之意;同时,他还以“题二阕后自是不复作矣”为一首次韵诗的诗题,显露出更为斩截的愧悔之情。
当然,朱熹的“诗禁”并未真正见诸实行,从其后来的创作看反倒有些“变本加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淳熙二年三月吕祖谦赴建阳寒泉精舍访朱熹,两人曾同游芦峰、百丈山,并有分韵诗作,《晦庵集》卷六就存有《游芦峰分韵得尽字》《游百丈山以徙倚弄云泉分韵赋诗得云字》等作品。罗大经《鹤林玉露》中也记述了朱子禁诗而不止的事例:“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朱文公论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页。这说明如何吟诗而不妨道,确实是朱熹面对的一大难题。
三、南岳之后:中和新说与诗风转变
乾道三年南岳酬唱之后,朱熹一方面进行着中和问题的再思考,同时也在寻求诗风的突破,以解决吟诗而又不妨碍性理的难题。在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作诗亦是心性修养的实践,是诗人当下证入和体验的过程,与中和问题一样,其核心在于对情感的合理控驭。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朱熹在乾道五年己丑形成了中和新说(即己丑之悟),新说的基本思想见于当年其答张栻的书信: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朱熹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第1403-1404页。
朱熹认为心有“未发”“已发”的不同时段——“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未发,“事物交至、思虑萌焉”为已发,并且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统贯性、情。关于此书,有二点值得注意:
第一,中和旧说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新说则转变为“心统性情”、“性”“情”对说。虽然新说亦认为“性为未发”,但“性”不是“不能发”,而只是“未尝发”,从可能性上来说,性完全可以发而为情。这样性、情两者并非体用关系,而是处在了或动或静的同一层面,构成一种动态转化关系,使得通过调节性、情的微妙关系以控驭情感成为可能。大体上说,朱熹中和新说的性、情之别更接近小程子,程颐在早年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便将性情对说:“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二程集》,第577页。和程颐一样,朱熹中和新说从浑沦的“心”中析出了“情”,基于正心养性的立场,其修养的关注点在于把握好“情”的动向,不使之过度。这一转变可以用下图表示:*关于朱熹中和新说与旧说之间的区别,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第七章《已发未发》中有较为详明的论述,本文在吸纳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旧说中“性之未发”为“不能发”,新说中的“性之未发”为“未尝发”,因而朱熹由旧说的性情浑然不分转化为新说的性情之动态变化关系,由此前对心之“已发”的无可如何,转向调节性情、控驭“已发”的“可能性”。因为性、情之间有动态转变的可能,故本文在图中用虚线表示。
第二,“持敬”思想的完善。从修养工夫来说,如何“致中和”,即达到性情的无所偏倚呢?朱熹在中和新说中强调“敬”的调节作用。此前他亦关注到“敬”,但由于视心为已发,其所谓“敬”强调的是“已发处省察”的工夫。*如朱熹中和旧说第一书:“其良心之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于夜气不足以存而陷于禽兽,则谁之罪哉?”(《朱熹集》卷三十《与张钦夫》,第1290页)而中和新说认识到心有“未发”和“已发”的动静之别,“敬”即是将未发时的“涵养”和已发时的“察识”工夫结合起来,时时用“敬”,则此心无所偏倚,情感自然中节。此即贯通动静的“敬”的工夫,也成为朱熹成德之教的不二法门。
对“涵养用敬”的强调,避免了性情的流荡,当然也限制了情思的发溢。一般说来,作诗与学道对情感的态度相反,作诗需要才性和情气发动,学道则需适当遏抑情感之流,以敬静之心会合于万象之“理”。如牟宗三先生所揭出的:“顺气言性”,开出才性一路;“逆气显理”,开出超越领域和成德之学。*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二章第六节,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前者乃是文学家的思路,后者正是理学家的追求。朱熹对苏轼等文人的批评也是基于这一点,他指出:“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2页。苏轼诗文词情洋溢,且喜欢以“气”评诗论艺,*如《王维吴道子画》“笔所未到气已吞”;《与顿起孙勉泛舟探韵得未字》“要将百篇诗,一吐千丈气”;《送参寥师》“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次韵张畹》“知君不向穷愁老,尚有清诗气吐虹”等。分见《东坡集》卷一、十、十四,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3、837、863、1233页。而其所谓“气”往往与作者的先天禀赋、性情相关,乃是充塞于主体、显发于诗文的生命力,并没有道德的内涵;“气”作为才性的载体,也没有合“度”的问题和节制的必要。这即是“顺气言(才)性”的路子,正与朱熹愈发成熟的“用敬”思想针锋相对。除了对苏轼的严格排斥,中和新说确立之后,朱熹对自我作诗亦加强了约束和防检:乾道五年七月间,他在给林用中的信中提到自己与林氏的唱和诗说:“数诗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语,勿示人也。”*《朱熹集》别集卷六《答林择之书》,第5469页。对诗文的这种反思和批评,应该说与其己丑之悟后对“敬”的明确体认不无关系。但朱熹毕竟不是程颐,程颐的性情论隐含着“性善情恶”的预设,故严判性情之别;而朱熹虽然在中和新说中将“性”“情”并提,却并未使两者对立,而是解释为一种圆融相通的关系。他认识到,诗从根本上说乃是情与欲发动的结果,诗尽可以作,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这种情思使之平和醇正,同时又富有生机,有“鸢飞鱼跃”的活泼境界。在朱熹南岳酬唱时这两种向度是矛盾的,而乾道五年的中和新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受此影响,朱熹后期的诗学精神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追求:
1.静中涵动,富于生意。朱熹的中和新说主“敬”,是一种贯通已发未发、动静相须的工夫。它一方面是内心之存养工夫,虽未发而知觉不昧,生机不泯,乃“静中之动”;另一方面它又保证了此心接物时,虽思虑萌动,情感已发而仍能中节,为“动中之静”。因此,感而常寂,寂而常感,周流贯彻,乃是朱熹所追求的一种圆融境界。体现于诗作,即朱熹的许多写景作品中既渗透着一种“静观”的态度,又充满生生之“仁”的生机与活力。如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之四:“静观灵台妙,万化从此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厚味纷朵颐,妍姿坐倾国。”*《朱熹集》卷四,第178页。他在乾道末、淳熙初所作的武夷山诸绝句,亦是对武夷山各类景物的静中观照,如《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武夷棹歌十首》等等,写暮雨朝晴、鱼鸟相亲的武夷佳胜,从中透出的是一种安闲从容的心态,其情感、意趣与南岳酬唱诸作的流动发溢显然有别。
2.从容不迫,沉潜温婉。朱熹的中和新说思想形成后,曾与湖南诸儒多次书信交流,但赞同者极少,“惟钦夫(张栻)复书深以为然”。*《朱熹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第3950页。张栻大体上接受了朱熹的中和新说,但并未完全放弃“察识”相较于“涵养”的优先地位,他亦主“敬”,但他所谓“敬”更偏重“已发省察”一边,即应事接物时对念念不已的心体之省察。其弊病在于精神难免发露,情感发动未必能中节合度。朱熹正是认为张栻之诗有发露之病且是内在修养偏差所致,因而以平和蕴藉相启诱。如他乾道六年的《答张敬夫书》曰:“抑又有所献:熹幸从游之久,窃目间所存,大抵庄重沉密气象有所未足,以故所发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养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虑事,吾恐视听之不能审,而思虑之不能详也。”*《朱熹集》卷二十五,第1051页。朱熹还在这封书信的附注中说:“近年见所为文,多无节奏条理,又多语学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无大小,小者如此,则大者可知矣。”他认为,张栻的文章芜杂而无节奏条理,其实是思虑不详审、内心浮躁的外现。张栻少了涵养用敬的工夫,所以沉潜不足,诗文也粗率不耐读。
朱熹反复强调诗思平和,但并不等于其后期诗作便也温润和平而不失性情之正。一般说来,诗人的创作心理都是丰富而复杂的,诗学理想和实践存在一些差异也是文学史中的常态。其实,张栻也曾反过来批评朱熹的诗作不够温厚蕴藉,其淳熙二年《答朱晦叔》云:“山中诸诗纡余淡泊,讽之不能已,但觉其间犹时有未和平之语,此非是语病,正恐发处气禀所偏,尚微有存也,更幸深察之。”*《张栻全集》卷二十三,杨世文、王蓉贵校点,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868页。所谓“山中诸诗”,应是指当年七月朱熹的云谷居落成,乃有《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等诗作,且曾寄张栻共赏。这两组诗均为五言之作,前者以摹景为主,后者则杂记云谷生活百态,如谢客、劳农、玩月、登山、宴坐等,风格偏于纡徐温婉,蕴藉醇厚,颇有陶诗的娴雅风味。但是张栻所谓“时有未和平之语”,也并非虚说,如朱熹《讲道》篇:“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亹亹玄运驶,林林群动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朱熹集》卷六,第286页。天道杳冥,万象迁流,人生亦然。此诗流露出一种欲静而不得的流驶心态,与朱熹中和旧说时“心为已发”的思想反倒颇为相似。张栻予以委婉的批评和警劝,乃是受朱熹中和思想影响后对朱熹的“反影响”。二人为论学讲贯之益友,在修养目标和方法上达成一致,而在诗学方面也以温厚平和的精神相互砥砺。
综合以上所论:在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作诗亦是心性修养的实践,是诗人当下证入和体验的过程。对理学家来说,如何引导情感中正以达成诗风醇正和平,与生命的实践其实是一回事。中和旧说的未发已发论,从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具体到作诗的实践,心体的发动(气)和性理的纯一(志)之间难免会有冲突,这也是朱熹作诗与禁诗矛盾心理的根源。朱熹经历了一番困心衡虑之后,将“凡言心皆为已发”的中和旧说调整为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敬贯未发已发的中和新说,其对性情关系的阐释愈发趋于圆通。受此影响,朱熹的诗学精神也从任情发溢逐渐变为温厚平和、涵泳悠游;而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乃是我们考察其思想变化和诗风变化的重要节点。“诗禁”体现了朱熹、张栻等人对自己心灵和情感世界的反观,隐含着对道德家作诗之合法性问题的思考,也是对诗的本体性追问,显示出了诗学与理学思想之间巨大的理论张力。
(责任编辑:庞礴)
On the “Poem Ban” after Composing Verse in Response to One Another on Mount Heng and Zhu Xi's Change of “Zhonghe”(中和) Idea
Guo Qingcai
In the 3rd year of Qiandao period,after composing verses in response to one another on Mount Heng, Zhu Xi, Zhang Shi and Lin Yongzhong concluded an agreement of forbidding poems, but the ban was lift several days later, which demonstrates Zhu Xi's paradoxical attitude toward writing poems and cultivating himself according to Confucian doctrine, and shows the signs of Zhu Xi's shift in thinking of “Zhonghe”. “The Old Theory of Zhonghe” regards “humanity” as hidden and “mind” as manifest, viewing the flowing of mind from the level of vigor, which will easily cause the restlessness of emotion and vigor. After proposing “the Old Theory of Zhonghe”, Zhu Xi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espect”, which is the introspectiveness of mind and the control of emotion and vigor. These two aspects were contradictory in the effect of writing poems, which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Zhu Xi's writing poems enthusiastically on the one hand and scrupulously on the other.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heory of Zhonghe”, which regards “humanity” as hidden and “feeling” as manifest, Zhu Xi reached a new level in the emotional control of cultivating himself according to Confucian doctrine and writing poems. How to write poems with dynamic and vigor but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hidden and quiet feeling became Zhu Xi's higher poetic pursuit.
Zhu Xi,composing verse in response to one another on Mount Heng, poem ban, “the Theory of Zhonghe”
郭庆财,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临汾041004)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南宋的学派之争与文学嬗变”(13CZW036)
I206.2;B244
A
1006-0766(2016)05-009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