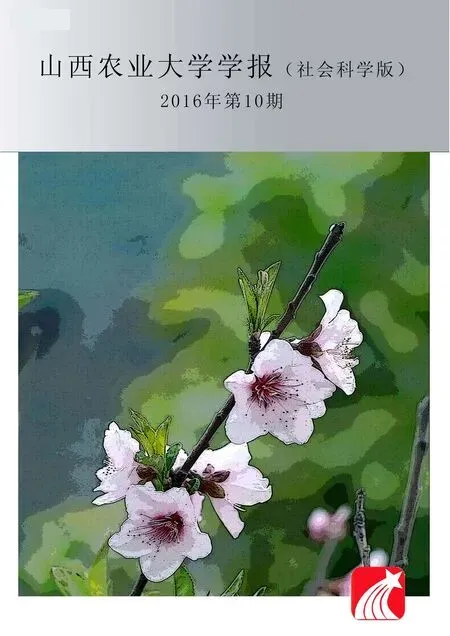广东历代方志研究
——以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为视角
2016-09-26何崚陈伟明
何崚,陈伟明
(1.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6032;2.广东药科大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广东历代方志研究
——以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为视角
何崚1,2,陈伟明1
(1.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6032;2.广东药科大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在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中,方志是主要的文献之一,其中主要的方志包括地方志、山川志、寺观志、名胜志、游记等。本文以研究茶史文化为视角,对广东历代方志的编修撰的特点做一个初步的归纳与探讨,亦对初期从事茶史和农业史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查找文献的指引。
广东;方志;茶史与茶文化
在国内的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中,方志是主要的利用文献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近代茶叶奠基人吴觉农先生在开展茶叶研究工作之初,首先是着手搜集国内各省地方志的茶叶历史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有关茶叶著作,写成了《湖南茶叶史话》《四川茶叶史话》等专著,并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再有著名农史专家朱自振先生,由于其主攻方向为茶史,早年与陈祖槼先生等共同搜集资料,于1981年编撰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后于1991年编撰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续编·方志茶叶资料汇编》,在此资料的基础上,于1996年写成了茶叶专著《茶史初探》。从以上两个例子可知方志资料对于研究茶史和茶文化的重要性。不论是研究茶叶,还是研究其他作物的农业史,方志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对此,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亦指出:“有良方,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隆污,于兹系焉。”此言已较全面地说明了方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在历代方志中,作为茶史与茶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除了保存最多的地方志外,还有山川志、寺观志、名胜志、游记等,现将广东历代各种方志的记载情况做一初步的归纳与探讨。
一、地方志
广东历代地方志是研究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的最重要文献资料之一,亦是每位研究者必备的资料。《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是当前搜集最多、最完整的广东地方志书的一套书籍。它收集广东各地方志共计433种,分为省部、广州府部、韶州府部、南雄府部、惠州府部、潮州府部、肇庆府部、高州府部、雷州府部、琼州府部、廉州府部和附录共11部、277册。该套书籍为每一位历史及相关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惟其不足是大部分为明清地方志,而且部分明代地方志编修较简略(例如崇祯恩平县志、崇祯揭阳县志、万历普宁县志、万历阳春县志、正德兴宁县志等),且明代地方志亦相当部分佚失不齐(据统计,明朝广东修志共224种,其中省志3种,府志47种,州志12种,县志162种,然而现存的明代地方志仅55部[1]),无法更好地对明代和明代之前的广东茶史文化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从现存的明清地方志来看,其编写的体例大体相似,而有关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志中的地理志、食货志和艺文志中,另外风俗志、外志、杂志和人物志亦有部分记载,而其他的教化志、建置志、赋役志、秩官志、政事志和寺观志等则稍有记载。

在历代方志中,艺文志部分是研究广东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官宦士人、文人墨客、僧侣道士等喜爱幽胜之地,借助幽雅的景色和饮茶的意境,以诗文等抒发情感,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碑刻、建筑、游记、诗词歌赋等众多作品,许多优秀的作品被地方志所收录,成为研究茶文化的一个重要文献,因此以诗文等为证亦成为研究茶文化的重要途径。此类作品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小结:从明清地方志的编修情况来看,已保留了许多广东茶文化的文献,为后世的研究者理清广东茶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但地方志中关于茶条的记载,地理志、食货志和艺文志仍然过于简略和模糊,其他风俗志部分则更少,并不有助于后世研究者对广东茶文化的深入分析研究,阻碍了广东茶业的发展步伐。
二、山川志、寺观志
随着明清广东茶叶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茶叶生长的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由于僧侣日常修行对茶的大量需求等,出现一批山川志、寺观志等专论著作,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方志记载的不足,其中著名的有《西樵白云洞志》(清·黄亨撰辑)、《西樵山志》(清·马符録撰)、《鼎湖山志》(清·释成鹫撰)、《罗浮山志汇编》(清·宋广业撰)、《罗浮山志》(明·陈璉撰)、《禺峡山志》(清·孙绳祖撰)、《重修曹溪通志》(清·马元,释真樸重修)等。这类山川志、寺观志专论著作的撰写体例类似,均有历史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形胜、殿阁堂寮、艺文碑碣、山事杂志、人物传等内容。由于是专论著作,所记载内容较为详细和丰富,在茶叶方面的记载亦是如此。《鼎湖山志》不仅记录了鼎湖山的自然环境,亦对鼎湖茶有详细的记载:“考邑志所传,谓山多佳茗,以龙口为最胜。汲龙泉烹之,香色殊常。窃谓茶性清洁,如幽人之高尚,宜于烟霞,不宜尘坌,均草木耳。产于名山,瀹以清泉,则气味深远。移植人间,火焦水浊,则味薄而气索然,所谓迁乎其地,不能为良。物性宜然,亦阴阳之气,有以致之也。向使山中,老衲舍其真乐,失其故我,去泉石而入城市,其不为,味薄而气索然者,几希矣。”[5]这段对于鼎湖茶的记载在后世的地方志和其他作品多有引用。
据《西樵白云洞志》对西樵山茶的记载:“白云茶产于白云洞前,亦名寺前茶,以洞口有白云寺也,出茶之地不多,皆生晒,山顶所产者,远不逮。”[6]这段是对西樵山名茶白云茶的记载,详细地说明了茶产地、制茶、产量、品质以及命名等各方面的内容。另有明·霍益芳《西樵山志》记载:“蝇木:南海西樵村人种茶,植之以为阴。木高数丈,叶细如豆叶,落畦上,则茶不生螆。山人多植于畦中,早则蝇树降水以滋茶,潦则蝇树升水以燥茶,故茶恒无旱潦之患。又夏秋时,蝇皆集于蝇树不集茶,故茶无螆而芳,味好盖蝇树,茶之所赖以为洁者也。己受蝇污而以洁与茶,为德于茶者也,山下茶畦多种之,山上则否。以山上云雾多而不生蝇也。”[7]从详细记载可知,西樵人将蝇树与茶树混植,蝇树高于茶树,可以给茶树遮阴,还可以防止茶树生涝和生螆。
小结:对于研究广东茶史与茶文化,山川志和寺观志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且由于高山环境对于茶叶品质至关重要,且名茶往往出自僧人手制,且佛堂也往往设有茶寮或茶堂以接待来宾,山川志和寺观志对于茶叶的记载往往较为详细和丰富。但这类专著的缺陷亦非常明显,从茶叶方面的记载来看,除了地理、物产和艺文志方面多有介绍,经济、社会、政治、风俗等方面却甚少涉及,亦不能更多地了解茶叶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风俗方面的影响。
三、名胜志、游记
名胜志和游记均属于地理类山水之属,其共同特点是对祖国名山大川作志,这方面的作品亦属于专著类,记载内容亦详细和丰富。由于高山云雾环境出产的茶叶品质佳且珍贵,且往往名山大川亦出名茶,在明清广东茶文化与茶叶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这类专著亦不失遗漏的将其写入著作中。著名的名胜志、游记专著有《岭海名胜记》(明·郭棐撰)、《增补岭海名胜记》(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补)、《西樵游览记》(清·刘子秀撰)、《纪游西樵山记:西樵名胜古迹考》(清·梁念祖等撰)、《粤东名胜记》(清·徐琪撰)、《粵游紀行》(清·李定业撰)、《粤游小识》(清·张心泰撰)等。
这类方志的撰写体例以名山、大川和寺庙等为记,如名胜志代表作《岭海名胜记》所记载名胜较多,其目录有粤会记、粤秀山记、五仙观记、白云山记、南海廟記、飛來寺記、羅浮山記、西樵山記等,内容以文诗词赋等艺文为主。而游记代表作如《西樵游览记》目录包括名胜、峰峦、岩洞、溪泉、台石、院馆、山村、古迹、物产、艺文、杂事等,从目录可知其游记的地点单一,但记载较为详细全面。
在名胜记方面的专著,除了诗赋类有较多茶文化内容外,记、序、文等文体记载的更为详实。如《岭海名胜记》中的一篇明·湛若水的文章《都宪韩襄毅公祠记》:“此韩公也。(永乐)、成化而上,吾樵茶租之征重矣,金花之银,锡蛇之酷极。吾樵之民,逃窜四散,几不免水火矣。赖都宪姑苏韩公雍奏革之,乃安居乐业,此与生我养我免於水火者等也。岁食茶业与植桑,衣我艺谷食我者等也。吾与尔等,宜思所以报之无穷焉。”[8]该文记载自明永乐以来,西樵茶租甚重,以致樵民四散,后韩雍请奏革樵茶税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说明了从事植茶业的樵民众多,而且侧面说明了西樵山茶的名气和产量大,朝廷重视征敛西樵山茶租。
在游记方面的专著,以《西樵游览记》为代表,对西樵山茶的记载最为详细,对西樵山茶的发展历史、植茶环境与技术、茶区分布、采制加工、樵民以茶为业等均有介绍,不仅全面地收集了旧志中关于樵茶的资料,还对樵茶的栽培采制技术进行古今对比分析,如引用旧志,“按周氏樵志,以植茶之地,崖必阳,苑必阴,产于石面者,必资阳和以发之,以石之性寒也,产于土上者,必资阴,阴以节之,以土之性敷也,阴阳相济,滋长得其宜,而茶之芳味好,又以山顶所产向东南者为上,山顶常在云气之中,土皆附石,茶生期间,得阳气之先,品最居上。”[9]然后与当时樵茶对比分析到,“今樵茶亦无分上下阴阳,其佳品全在人为,大概采必应时,焙必应候而又择之精,濯之洁,火之良,则茶未有不甘芬者,但不能致远,一出山味,反劣,乃囿于地土也”。[9]
小结:对于研究广东茶史与茶文化,这类地理类的方志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且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亦是可以弥补地方志、山川志和寺观志的不足。但该类方志不足之处在于,现存的游记有相当部分介绍简略,例如《二樵樵者壮游图记》(清·黄璟撰绘)、《罗浮外史》(清·钱以塏撰)、《游罗浮记》《广州游览小志》(清·王士禎撰) 等。
总结:方志的类型很多,本文仅以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为方向,对所涉及的方志进行大致的归纳和分析,一方面对地方志的撰写体例和内容的详略进行分析,分析地方志不足之处,另外,对相关的山川志、寺观志、名胜志和游记等的体例和特点进行归纳分析,与地方志进行对比,以利于后世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涉猎不同文献,作更深入的研究。
[1]马建和.广东旧方志研究[J].中国地方志,2000(2):60-72.
[2][明]戴璟修,[明]張岳纂.广东通志初稿(卷31)《土产》[M].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3][明]郭棐撰.(万历)广东通志(卷14)《广州府之山川》[M].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4][明]郭棐撰.(万历)广东通志(卷18)《广州府之土产》[M].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5][清]丁易修,[清]释成鹫纂.鼎湖山志(卷一)《土产》[M].清康熙间刻本.//广州大典,第三十四辑,史部地理类第二十冊.
[6][清]黄亨纂辑.西樵白云洞志,《艺文》.//沈雲龙主编.中国名山胜蹟志丛刊[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113.
[7][清]潘尚楫等修;[清]鄧士憲等纂.(道光)南海縣志(卷8)《舆地略四》[M].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
[8][清]郭棐著,王元林等校注.(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岭海名胜记(卷十三)《西樵山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85.
[9][清]刘子秀著,[清]黄亨,谭药晨刊补.(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西樵游览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19.
(编辑:程俐萍)
The study of Guangdong Chronicles in the past dynasties——in the perspective of Guangdong tea history and tea culture research
He Ling1,2,Chen Weiming1
(1.CollegeofLiterature,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2.SchoolofBiosciencesandBiopharmaceutics,GuangdongPharmaceut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In the research of Guangdong tea history and tea culture, chronicles has always been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and the main portion includs local chronicles, mountain and river, temple records,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 sites, travel notes etc. The paper made a preliminary induc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Guangdong chronicles editing in the past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 history and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d a literature guidance for researchers just entering the study of tea history 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Guangdong; Chronicles; Tea history and tea culture
2016-04-30
何崚(1980-),男(汉),广东高明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茶史与茶文化方面的研究。
陈伟明(1957-),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540718565@qq.com
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之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13WYXM0065); 广州市委《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课题资助项目(2015GZY21)
K291
A
1671-816X(2016)10-07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