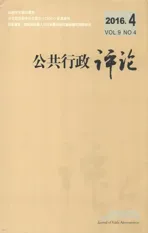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
2016-09-07刘涛
刘 涛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
刘涛*
论文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源起和制度设计及其诞生以来经历的诸项改革,并分析了该制度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主要发展趋势。根据西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论文分析性地探索了福利五角中的国家、市场、家庭、社会网络和非营利取向的社会福利组织在德国如何相互混合并协同完成长期照护这一福利目标。论文进一步指出了具有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性质的长期照护制度不同于其他社会保险险种而具有自身的制度独特性,这使得单一的福利国家视角已无法解释和涵盖照护保险领域里的实际发展,而混合型态的福利多元主义则有助于理论解释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设计。此外,论文还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长期照护制度的启示。
照护保险福利多元主义混合福利国家福利社会
一、引言
1995年1月1日德国长期照护(Long Term Care)*Long Term Care的国内译法有过争执。学者认为,Long Term Care 提供的服务兼顾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所以翻译成长期照护、长期照料或长期护理都有失偏颇。经综合考虑,我们在此采用长期照护。保险法律正式生效,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历经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最终将社会保险的第五支柱纳入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中。德国也是全球第一个明确将长期照护纳入法定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Klie,2005)。本文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历史缘起和制度性设计,并介绍了自长期照护保险诞生以来二十多年延续不断的改革和所衍生的新社会问题。论文不仅在于介绍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政策内容和制度设计,更着重于建立一个抽象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德国长期照护制度的实践。通过理论层面的分析,该论文得出的结论为单一的福利国家角色和福利国家理论已经无法“捕捉”照护政策的实际发展,而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供给者的混合协同机制则有助于把握住长期照护保险的实践。
相较于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其他险种,德国的照护保险制度不仅仅是建立在货币的补偿制度上,而是更多建筑于广义的社会工作、社会义工和社会服务基础上。与现代福利国家特别强调的匿名性、情感中立性和客观性等特征相比,长期照护具有情感性、具名性、重视主观感受性等特征,传统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福利国家未必完全胜任提供长期照护的任务。长期照护的这些“制度特异性”为福利角色的多元介入和多元供给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如何解决社会中长期照护的难题,福利国家的单一角色已然无法胜任,多元的福利角色供给才能够提供更优化的制度路径选择。
二、理论分析框架
福利多元主义在哲学基础上与北美大陆复兴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具有一定的“亲近性”,而社群主义于1980年代在英美文化中的复苏和兴起又与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具有一定联系。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认为福利国家产生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进程中,传统社会角色如家庭、家族、行会、职业协会及教会功能性衰退使得社会出现了“福利真空”(Achinger,1953)。在传统角色式微的过程中,国家的福利供给地位日益重要,福利国家逐步取代了家族、部落和行会的角色来主导福利产品的供给(Kaufmann,1997;Ullrich, 2005)。社群主义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异化,使得国家管制的范围日益扩大,其对家庭和社会领域的全面介入容易导致膨胀的国家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扩张损害了社会自治的传统,削弱了家庭内部和社会提供福利产品的动机,削弱了公民社会以自治为基础的相互援助和情感纽带,同时也削弱了家庭内部有机联系的纽带,总之福利国家损害了公民社会的自治和自助精神,削弱了社会团结(Rodger,2000;Gilman,2005),而公民社会的自治才能真正体现由社会而来的社会之“善”,这里“社群主义”的哲学可以和古典时期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礼俗社群”(Gemeinschaft)的观点相呼应(Tönnies,1887)。
社群主义在思想理念层面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将社会置于一种“原子化”的局面,削弱了社会的整合;同时社群主义也以福利国家为论战目标,反对国家包办一切,尤其反对以一元主义视角(Monolithic Perspective)为基础的福利产品的供给,认为福利国家从另外一个层面损害了社会的自治基础,他们提出了“重振社会”和“重塑社会责任和义务价值观”的观点(Chandhoke,2001)。以社群主义为基础,社会角色如非营利组织、教会和社会中间型组织被鼓励起来承担更多福利产品供给的社会责任。研究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学者也观察到,美国社会和欧洲大陆如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具有明显区别。在德国社会中很多由福利国家承担的任务如公共保障房、医疗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在美国则由教会和慈善的社会福利组织来完成(Kaufmann,2013)。
福利多元主义承接了社群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一元主义倾向的批评,但在诸多层面也区别于社群主义。福利多元主义并不否定国家在供给福利产品中的作用,但更多受到现代社会功能分化思想(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 der Gesellschaft)的影响,仅仅将国家视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并将政治系统视作社会诸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而已(Luhmann, 1997)。福利国家并非高高在上、居于穹顶来干预一切的一个“利维坦”的角色(Hobbes,1794),相反,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分化使得现代社会更像一个“群龙无首”的去中心化的社会。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在社会功能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政治系统仅仅是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如家庭、教育、科学、经济等相并列的一个平横存在的社会系统(Luhmann,2000),而非一个主导社会其他子系统并以垂直关系为基础的中心系统。而福利国家不断扩张其对社会次系统管理的边界,终将导致福利国家达到自己的“能力边界”,从社会组织上和财政上不堪负荷而无法完成日益扩张、却难以完成的社会福利目标,其结果往往为:福利国家想要完成的目标无法完成,而其意想不到的社会副作用却不断产生(Luhmann,1981)。
与社群主义相较,福利多元主义的思想并不追求解构国家在福利产品供给中的角色,福利多元主义解构的毋宁说是将“福利”与“国家”同置于一个语义结构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一元主义”的思维。福利多元主义所强调的是社会语意上的“多”,也即“多元结构”取代了“一元结构”,“社会多中心主义”逐步取代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而“福利混合”取代“福利国家”成为福利制度中的中心内涵。在“福利多元”和“福利混合”的理论流派中,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为:社会中不同的角色如国家公法权力体制、市场、社区、家庭、邻里、社会慈善福利组织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分别提供不同的社会福利产品,众多福利组织者发挥着协同作用来共同完成社会福利目标。例如,研究社会福利学者德诺贝格(Chris de Neubourg)提出的福利五边形的观点(Welfare Pentagon)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家庭或一位居民在一个社会中可以获取社会福利的渠道都不只一个,而是存在着一种多元的渠道,公权(国家)、市场、家庭、社会网络(如亲戚圈层和熟人朋友圈层)以及会员组织(如教会成员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提供了福利产品的来源。一个家庭和一位居民可以从工作市场获得收入以增进个人福利,也可能从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那里获得养老金或是国家社会救济,当然也存在着从家庭、亲友和社会网络那里获得社会福利甚至财政转移支付的可能性,进而,作为协会和社会团体的成员,会员组织也可以为居民和家庭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de Neubourg,2002)。

图1 福利五边形的观点
资料来源:de Neubourg,2002。
相较于英美学界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德国学者阿德尔伯特·艾维斯(Adalbert Evers)、伊凡·斯维特里克(Ivan Svetlik)和托马斯·沃尔克(Thomas Olk)等针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更是将该项讨论推向了理论的纵深层面(Evers & Wintersberger,1988;Evers & Svetlik,1993;Evers & Olk,1996)。与一般强调福利多元角色与这些角色和社福组织的“协同作用”相较,德国学者的讨论更加强调各个福利部门重合、交叠和相互交叉的局面,其核心思想基础在于:超越近现代以来西方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所产生的对“国家”和“社会”的界限性区分,以及后来对“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元区分。艾维斯和沃尔克认为,无论是福利国家的理论,还是后来对福利多元的讨论,都没能超越过去时代的局限:即将各个福利组织者的角色视为界限分明、组织清晰和相对独立的界阈。这或许符合现代社会的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后现代社会,这样的观点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艾维斯和沃尔克区分了市场、国家、社群和公民社会四种福利机制,分别相对应的是市场、国家、非正式和非营利领域,其核心福利供给角色分别为企业、等级化的行政制度、家庭及社会网络和社会中间性协调组织(见表1),四个领域的核心伦理价值基础分别为自由、平等、互惠和团结,其辅助的价值理念分别为福祉、安全、个人参与和社会政治的积极进取,通过这些机制获取福利的条件分别为:货币支付能力、作为合法公民的资格受益权利、预先赋予的角色和福利需求(表1)。

表1 福利产品领域里的特征
资料来源:翻译整理自(Evers & Olk,1996: 23)。
艾维斯和沃尔克的福利多元主义认为每一种福利供给机制皆具长处和短处,例如,运用货币可以立即购买福利产品,但无可避免地带来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后果和社会排除效应;国家公法机构的科层化官僚体制固然可以通过垂直的上下模式迅速为社会提供福利产品,但无法满足对社会多样化服务的需求,而且限制了人们支配自由,削弱了公民自我救助的动机;家庭固然可以提供以亲情为基础的照护服务,但归根结底家庭福利是以部落主义和互惠为基础的福利,无法复制到整个社会,而协会组织提供的福利也难以完全保证服务质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性。福利多元主义恰恰观察到了多种机制相互交叠交叉、相互重合和相互取长补短的局面,各种机制的优势互补恰恰可以创造一种相互嵌入的新福利模式来提供社会服务。人们选择社会服务的模式不再是一种唯一机制,也不仅仅是多种选项的并列,而更多选择的是多种机制的“组合”和“交叉”(Evers & Olk,1996)。
传统的福利多元主义视角所强调的提供、递送福利产品组织角色的“多样性”,与此相较,德国的社会照护保险制度更显示出“多样性”的创新含义,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一样,德国社会照护保险制度中的受众——具有照护需求的失能人士可以从家庭照护、上门流动照护、住院式照护中选择不同的照护递送模式,甚至可以在照护递送的方式上根据主观愿望和需求进行组合式搭配选择,例如同时选定家庭照护和上门流动式照护或是同时选择半住院式照护、半居家式照护等。照护递送方式的多元选择和多元组合不仅为传统的福利多元主义带来了崭新视角,也可以为未来福利多元主义研究提供新理论路径和更宽阔的理论思维。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的发展
(一)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设计及改革
199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了有关长期照护保险的法律,社会法典十一卷为长期照护保险提供了法律规范(Sozialgesetzbuch XI),德国因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全社会的照护需求纳入社会保险政策领域里的国家。长期照护保险由雇员和雇主共同支付保险费率。就组织架构而言,长期照护保险隶属于法定医疗保险。由于长期照护保险具有其独特性,需要不同于医疗保险这一险种的单独组织架构,由此,在医疗保险所内部一个单独的照护保险基金得以成立(Pflegekasse)(Klie,2005)。长期照护保险额覆盖范围和医疗保险体系是相当的,即占德国总人口近85%的居民被法定长期照护保险所覆盖,这意味着,所有承担法定义务必须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同时也必须参与法定照护保险,包括雇员、职员、失业金领取者、社会救济领取者、退休人员、学生等都被纳入法定长期照护保险,家庭成员如孩子可以跟随家庭内主要参保人免费参加照护保险,夫妻双方入一方收入较低,也可以免费跟随主要参保人参加法定长期照护保险(Bäcker et al.,2000),其他未被包含在法定照护保险里的居民也须参加私人照护保险。
而长期照护保险的费率在1995年至1996年6月30日为毛收入的1.0%,1996年7月1日,其增加到了1.70%,直到2008年,照护保险费率都维持在这个水平。自2008年7月1日起,保险费率从1.70%上升到1.95%,保险费率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担,这意味着雇主雇员各缴纳0.975%的费率,长期照护保险和法定医疗保险有着同样的缴费上限(Bäcker et al.,2010)。自2015年1月1日开始,长期照护保险的费率上升为2.35%*2015年开始雇主和雇员各自分担缴纳长期照护保险费用占毛工资的1.175%,总计费率为2.35%,而没有孩子的居民需额外支付照护保险保费0.25个百分点。参见(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2015)。。
长期照护保险与法定医疗保险的目标不尽相同*法定医疗保险和法定长照保险在照护项目上有所重合,但又有所区别。在法定医疗保险内部,由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后需要康复及照护,诸如此种由单一疾病或手术而产生的康复性照护一般属于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之部分,其往往具有“一次性”和“可再康复性”特征。而法定长照保险所涵盖的照护需求则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及“不可再逆转性”特征,一般这样的照护需求由身体功能性失能或长期疾病引发,需要较长时段甚至是终生之照护。,德国的医疗保险在理论上应满足所有保险人的医疗需求,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并没有试图覆盖所有参保人员的照护需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那些有照护需求的人员提供以家庭和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照护,而通过专业照护中心和照护所提供的住院照护仅被视为最后一种手段(Rothgang,2009)。
针对照护保险的讨论其实自1970年代后期就出现于德国的学界和政界,因人均寿命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老化(Birg,2001;Kaufmann,2005),对老年人照护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加,社会救助制度被迫承担了“照护”这一日益沉重的社会负担。另外,越来越多的居民需要家庭以外的照护,最终他们不得不选择申请社会救助项目的援助。除了社会救助制度以外,医疗保险也部分覆盖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由于德国当时尚未建立独立的照护保险制度,社会的照护需求完全依靠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来补助,而社会救助则主要由基层的社会福利局来支付,这导致了基层的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救助项目被迫用来大量支付照护需求导致了社会救助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因为社会救助原本的政策目标是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支柱为处于生活困境中的居民提供现金援助(Cash Transfer)的。这意味着从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而来的许多资源都被投入到了老年人照护当中。
法律制定者希望通过独立的照护保险来缓解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的照护负担,避免这些社会保障项目为长期照护这一他们本身制度之外的目标过度担责(Popp,2011)。例如,自从建立长期照护保险以来,社会救助制度针对住院照护的专项补助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th & Rothgang,2001);从1994年到1997年,联邦德国范围内社会救助制度对于上门照护服务和住院照护的总支出由91亿欧元下降到35亿欧元,从中可以看到,新建立的照护保险制度成效明显,社会救助制度被大大降压,逐步回到了其制度本源的目的上(Roth & Rothgang,2001)。*在长期照护保险建立之前,需要长期照护人士在无法负担高额的照护费用时,可向社会救济制度的专项救助制度申请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中的这项分类救助制度即为所谓的“照护救助”(Hilfe zur Pflege),其由国家财政支付,申请对象必须接受资格审查,也就是需接受家庭收入及不动产收入等调查,只有符合申请标准且有实质需求的人员可以获得该专项救助制度。即使到今日,“照护救助”制度依然没有消失,在法定长照保险覆盖范围之外,如果照护人员需自付费用的部分过高并入不敷出时,依然可以向社会救助制度中的“照护救助”制度申请救助。只是通过建立长照保险制度,整个社会救助制度的负担被显著减轻,社会救助制度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为贫困者、低收入者、失业者等提供现金救助。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已被东亚国家如日韩等国关注并效仿,日本甚至模仿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于2000年建立了自身的法定照护保险制度。但德国照护保险和日本照护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为,日本的照护保险制度主要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及40至60岁群体的照护需求,而德国则针对全体国民的照护需求,即使是工作年龄阶段的残障人士具有照护需求,也同样被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所覆盖。当然,各个年龄阶段的照护需求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照护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见表2),例如15至60岁之间有照护需求的居民仅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0.5%,而60至65岁的比例仅微升为1.8%,65至70岁为2.8%,而70至75岁则上升为4.8%,75至80岁为9.8%,高龄群体如80至85岁的有照护需求的群体则飙升为20.5%,85至90岁为38.0%,90以上则为57.8%,这意味着在联邦德国,9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平均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有照护需求。其中,女性由于平均寿命较高,65.2%的90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具有照护需求。

表2 2011年德国分年龄、分性别的照护需求(占该年龄段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Pflegestatistik 2011,Wiesbaden。
需要照护的人群被分为三类:一级照护服务于有显著照护需求的人群,二级照护为非常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三级照护则是针对最需要照护的人群而设置的。*一级照护每日需要至少90分钟的照护及45分钟的基本照护;二级照护每日需要180分钟的照护及120分钟的基本照护;三级照护则升高至每日需要300分钟的照护及240分钟的基本照护。基本照护主要涉及起居方面的照护,其照护所需时间大约与一个家庭成员所投入的照护时间相当,不等同于专业照护人员所需照护时间。基本照护包括例如洗漱、梳头、洗澡、协助准备餐饮、空间移动及步行、就寝、起床、换衣、访问和离开专业照护机构等。而家政方面的照护则不在基本照护范围之内,例如买菜、烧菜做饭、打扫房间及洗衣等。照护可以分为家庭照护或是住院照护。在家庭照护中,家庭成员如果参与照护,可以得到照护津贴的补助。这意味着,如果家庭成员因承担照护的任务或是因为照护而放弃工作,将得到一部分现金补贴作为补偿。而家庭照护人员也享有社会保险的权益,当其每周照护超过14小时就必须参加法定养老保险,长期照护保险所支付家庭照护人员的养老保险保费,但养老保险待遇和一般工作相比较低。此外,长期照护保险所还将家庭照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除家庭成员外,需要照护的人士也可以自行选择亲属、邻居和友人来进行照护服务,他们均可获得现金形式的照护津贴,照护津贴的高低根据照护级别而定,照护级别越高,则给付的照护津贴也越高。如果专业福利机构上门服务进行照护,那么照护保险基金也可以部分支付这样的专业上门照护所提供的服务。
在这三个照护层次上,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申请货币型的照护津贴还是单纯的照护服务。在家庭式的照护服务中*流动式照护服务是以专业照护人员进行上门服务这一形式来提供照护咨询和照护协助服务的。,为了家庭成员考虑,多数受益人倾向货币性的转移支付,例如,需要一级照护的居民能够得到每月244欧元的照护津贴或是得到每月468欧元的照护服务。但是,需要住院照护的重度失能人士通常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申请住院照护服务而不是现金式的照护津贴。选择住院照护的居民,既可以选择完全住院照护,也可以选择部分住院照护(见表3)。特殊情况下,那些处于三级照护这一层面的最需要照护的群体,能够通过法定长期照护保险体系获得最高每月为1 995欧元标准的照护服务。在德国模式下的照护保险体系里,社会照护保险没有也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照护需求,在照护保险的补贴之外,受益人还需要自付相当比例的照护费用。
值得指出的是,有照护需求的居民还可以选择一种组合形式的照护递送方式,即可以申请部分的照护津贴以及部分照护服务,也就是说可以同时选择家庭成员进行部分照护,而提供长照的机构如福利协会也通过上门照护服务来满足失能人士的另一部分照护需求。在这样一种“照护递送方式组合”中,参与照护的家庭成员可以兼顾自身就业需求和照顾失能亲人的需要,例如其可以在每日工作结束后承担部分照护任务,而社会福利机构则在家属工作的时间段内提供上门的流动照护服务。在这样一种组合模式中,照护保险所可以在提供给家庭成员以现金补偿(Cash Transfer)的同时也负责支付上门照护服务(Care Service)。这样的照护递送模式的选择是“组合式”的,失能人士也可以选择半住院式照护服务,也就是部分时间在专业照护机构接受住院式照护,而在另一部分时间内则选择上门流动式照护服务或家属照护。照护递送模式上呈现出多种组合的可能性。

图2 德国照护递送模式的组合性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德国照护保险领域里并非单单出现组织供给角色“多样化”的特征,更呈现出了递送方式选项“多元混合”的特征,而递送方式的组合也体现出了德国社会福利体制特殊的宗教伦理和文化价值观。在探讨德国的宗教及文化对于德国福利制度的影响时出现了“悖论”现象:一般而言,根据传统福利国家分类研究,德国被划分到“保守主义”和“法团主义”福利国家的范围(Esping-Andersen,1990;Siaroff,1994;Kaufmann,2003a,2003b),而“保守主义”体现出德国新教教派路德宗的基本价值观,即路德教派强调的“爱邻人意识”“慈善意识”和“社会团结”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庭、邻舍和教区的慈善意识得到宗教伦理价值观的支撑,“保守式”的福利体制更强调的是家庭福利和社区福利,性别上更加将女性的社会角色固定为“家庭教育和照护员”的角色,这样的“福利家庭”和“福利社会”不利于男女两性平权,更不利于现代福利国家的介入。这样的理论路径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视了德国走向现代以来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浓厚的“国家主义”(Etatismus)倾向。普鲁士强国之路是以其高抬国家理性地位和国家精神为基础的,国家成为超越社会各个分散团体、从更高层面来理性凝聚社会的一种超越性力量,国家精英应当具有非凡之见识和远见,来为国家未来发展之路进行长远谋划,而普鲁士国家精神后来也演化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这里,“国家”的地位又得到强化。这部分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立法介入的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于德国,“福利国家”之雏形也产生于德国。而德国的照护保险制度恰恰体现了德国福利国家文化的两个层面,即一方面重视家庭和社会自治的传统,同时也重视国家介入和规划福利产品供给的作用,“家庭”“社会”和“国家”三边交汇点即产生了现代的社会照护保险制度。

表3 2015年德国长期照护保险补助待遇(欧元/月)
注:这里的“家庭照护”“部分式住院照护”和“全住院照护”可以类比我国的三种照护模式——“居家照护”“社区照护”和“机构照护”。
资料来源:AOK-Bundesverband,2015。
一般来说,提供照护的服务机构分为三类,包括公立福利协会、私人照护公司和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机构,其中,社会福利机构在德国归属于所谓的既非国家也非市场的“第三领域”,例如德国平等福利协会(Deutsche Paritätischer Wohlfahrtsverband)、德国慈爱会(Deutscher Caritasverband)、劳工福利(Arbeitswohlfahrt)、德国红十字协会(Deutsches Rotes Kreuz)、基督教慈善机构(Diakonisches Werk)、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局(Zentralwohlfahrtsstell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均为最重要的社会福利团体(Schmidt,2007)。这些非营利的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在早期的历史中大都具有宗教色彩,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宗教色彩逐渐淡化,突出了其社会福利、劳工保护的职能。除了历史上这些久负盛名的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外,其他一些小型的社会福利机构也在长期照护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也是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私人照护所和照护公司可以根据市场平均价格和购买力来提供长期照护的服务(Hämel,2012)。长期照护保险所与各地区的主要提供照护的服务机构进行关于服务价格及照护员工工资的谈判,根据谈判结果以决定照护服务的价格。
法定长期照护保险体系在德国的福利国家历史中可说是一个突破。基本上,该体系与大力强调平等、包容性、再分配和团结性的医疗保险有类似之处。因为大部分的人群是被法律规定义务性地参加到该体系中来,并需要支付强制性长期照护保险的保费。在这些需要照护的人群和那些无此需求的人群之间有一个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另外,国家在照护服务上推行多元主义的路径,鼓励多元化的角色参与到为需求人群提供照护服务中来,其中的途径就包括促进家庭、社区、福利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照护服务。截至2013年12月31日,在法定照护保险覆盖范围内,德国总计有247.9万人需要照护服务,他们中的70%(173.9万)在家里接受照护服务,而剩下的需要照护的居民(74万)则在各类照护机构得到照护。在选择家庭照护的群体里,125万的人已经接受了货币形式的照护津贴(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2014)。
尽管德国为法定社会保险体系贡献了一种极有创新意义的照护模式,且该体系也被日本等东亚国家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依然是实验性的,需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完善。德国的法定长期照护保险体系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只是部分地得到满足,例如,居民如果选择住院照护,只有照护本身的费用可以报销,但住院费用和餐饮费用则必须由参保人自付。考虑到专业化的照护所产生的费用极其昂贵,法定照护保险的唯一保险支柱根本无法全额补贴不断攀升的专业照护服务的费用。所以,未来的主要改革方向为从国外引进专业照护人员以及风险分担的多元化,有学者甚至提出照护保险的多支柱模式。有以下几项最新的改革动向值得引起关注。
1.照护市场对于低收入的东欧国家及中国等国家的开放
2013年,德国联邦政府决定由邻近的低收入国家引入专业照护人员。在欧盟的框架下,经济政策对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市场有着直接影响。在市场开放后,越来越多来自东欧国家的照护人员将会涌入富有的西欧国家,在德国,这股移民潮可能会降低长期照护保险体系非常高昂的费用。从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等国到来的廉价照护人员将会重塑长期照护保险市场。德国联邦政府还考虑从中国引进照护人员。但是,这一改革方向已经引起了关于“社会倾销”的讨论:当地专业照护人员的收入将受到一定冲击,移民的低收入将会拉低国内照护人员的收入水平。
2.对于痴呆症患者照护需求的供给
在原来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中,痴呆症患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得到照护保险的补贴并通过法定长期照护保险获得照顾。在新的改革里,明确规定如果一个老人患有痴呆症或精神障碍明显制约日常生活能力,即使身体健康,也可以申请每月123欧元的照护津贴(照护级别为0),或者申请每月为231欧元标准的医疗服务。一级、二级和三级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分别能申请每月为316、545和728欧元的津贴,或是每月为689、1 298和1 612欧元标准的照护服务(AOK-Bundesverband,2015)。
3.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新支柱
由于长期照护问题不能只由单一的财政资源来解决,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等主要的国际组织也在推行一种新照护模式,就是通过向老年退休金计划等社会保险领域学习而获得经验。改革由德国自民党所推荐,主要建议为建立额外的基金积累的私人保险体系。在这种基金积累模式中,每个保险人将其长期照护保险费的一定份额存入其个人账户,这样资本存量就能得到累加。在有照护需求的情况下,照护需求将由两个支柱共同支付:第一支柱为法定照护保险,第二支柱为私人照护保险账户,国家针对第二照护支柱则负责采取法律来监督、规范投资。另外一个讨论则是鼓励个人储蓄,即个人自愿为未来的长期照护保险储蓄照护基金。通过采取多支柱保险制度,政策设计者尝试通过不同来源的资金组合来减轻照护的负担,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和资本投机的问题(Popp,2011);另一种担心是在那些有经济能力来支付个人账户和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的人群之间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还会不断增强。事实上,这种长期照护部分私有化虽然一直被一些政治家所讨论,但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这一改革议程的主要推动力是自于自民党的前联邦卫生部部长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和他的跟随者丹尼尔·巴哈尔(Daniel Bahr)(Die Zeit,2012)。
(二)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
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展现了一幅福利多元主义文化的图景:从提供照护服务的组织者和供给者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角色相互合作并协同性地发挥了提供社会福利产品的作用,国家、市场、家庭、邻里、社会网络、社区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及社会福利组织等共同提供福利的产品。一位具有照护需求的居民获得的不仅仅是从单一福利组织而来的照护服务,而是从一个不同角色和机构的系列组合中获得社会福利产品。同样,一位具有照护需求的居民也具有一定的支配自由权从这一系列“组合产品”中实施个人选择,决定通过何种方式满足自己的照护需求。这意味着,有照护需求的居民既可以选择家庭式照护服务,也可以选择住院式照护服务,而在家庭式照护服务中,可以选择家庭成员、亲属或邻居提供的照护服务(所谓的现金福利津贴选项),也可以选择来自于私人照护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福利协会提供的专业化上门照护服务(所谓的流动照护服务选项),或是选择现金福利津贴和上门照护服务的一个双边组合(Combi-allowances)。在住院照护服务中,既可以选择完全住院照护服务,也可以选择部分住院照护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照护需求的居民选择的是现金福利津贴选项,即完全接受家庭成员、亲属或是邻居的照护服务,这里的家庭也不再是传统社会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家庭”和“家庭照护”,因为照护需求如同养老一样,一旦被定义为“社会贡献”,那么家庭对病人或老人的照护贡献就转化为“社会贡献”的一部分,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于是,家庭成员通过照护将获得一笔“照护津贴”,如果家庭成员被迫放弃工作而参与家庭照护,那么其贡献将得到国家法定照护保险制度的承认,不仅获得货币化的现金补贴,而且,因其提供了家庭照护,还具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权益,获得的照护津贴也不作为一般的工作收入看待,即这笔收入将免除税收义务。如果提供家庭照护的人士本人还要领取失业金和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那么这笔收入也不计算为实质收入。只有在家庭照护者和被照护人签署一个就业合同的情况下,这笔收入才被算作提供照护的家庭人员的正式工作收入。实施家庭照护服务工作的居民不仅仅限于家庭成员和直系亲属,还包括亲戚、邻里和朋友等。在这里,国家的制度性力量与家庭、社区和邻里进行了相互对接,实现了相互交叠、交叉和重合。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和社区照护转化成为国家制度运用货币支付的社会服务,家庭照护实现了社会化和货币化的过程。
社区、社会组织和私人照护公司提供的照护服务,也将得到社会照护保险法律的规范,其提供的福利待遇也处于社会法律的管理和监督之下。在这里,国家、市场和社会公益性及非营利组织也共同实现了长期照护保险经办机构的多元化。不同机制和组织架构将长期共存,协同提供长期照护的服务。

表4 2005年德国提供上门照护和住院照护服务经办机构的种类和数量
资料来源:Bäcker et al.,2010。
从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角度来看,市场角色和社会角色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相较于私营机构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公立机构在提供照护服务方处于一种较为弱势的状态。在流动上门服务领域,提供该项服务的私营机构占所有经办机构的57.6%,而在照护所方面,则社会公益组织略微占有优势,社会公益机构占提供该项服务的经办者的总数量的55.1%(见表4)。
(三)德国长期照护制度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自从诞生以来就面临结构性的问题和困境,虽然照护保险制度有助于减缓和降低因照护需求而产生的社会风险,但该制度无法担负照护保险的全责,“部分担责”是和照护需求本身的“持续性”和昂贵的费用相联系的。在这里,可以捕捉到医疗保险制度和照护保险制度初始设计的差异: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致力于覆盖由医疗而产生的需求,“需求覆盖”原则隐含的是将医疗、药品和康复的费用完全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承担下来,虽然医疗保险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也要求病人自付费用或部分自付费用,例如安装假牙或购买药品等,但就整体而言,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追求的是“承担全责”,也就是只要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需求存在,医保制度就致力于全面涵盖疾病风险。而照护保险的初始制度设计则和医疗保险有显著不同,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担负的只是“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目标设定为“预算控制”,而非“需求覆盖”。例如住院式照护的住院和伙食费用都需要由被照护人自付,这必然导致不同群体因为收入状况的差别而出现不同的经济负担能力,从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实质照护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根据德国“老年人之家”的统计,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在2011年度根据平均住院照护费用(市场价格)和照护保险补贴费用之差计算出来的一级、二级和三级照护中自理费用为每月1 538、1 719和1 988欧元(Portal für Senioren,2011),这显示出照护保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漏洞。
其他对于照护保险制度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的不同批判性意见,由于德国照护制度组织者如社会福利协会征召大量临时照护人员和钟点工照护人员来提供照护服务,以求显著节省照护费用,这样的照护服务提供方式不仅引起了对照护服务质量的质疑,更加引发了对低收入群体过度剥削的批评(Hämel,2012),因为接受临时照护工作者大多为学生和女性临时照护员,而临时照护人员的薪酬较为低下,依靠按钟点来计算的薪酬往往无法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基本需求。许多参与提供照护的人员本身就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是由于专业照护人员存在巨大缺口所导致的。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也有学者对专业化的照护提出了批评,认为过度的“专业化”缺乏情感性和人文关怀,容易导致将照护的对象“客体化”和“物化”,而对于被照护对象不尊重甚至虐待的报道也不时见诸媒体(Weibler & Canzler,2006;Klement,2006)。
四、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2011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约有3 300万老年居民需要照护,其中1 100万需要家庭以外的额外照护。相较于养老保险和医疗等热门话题,老年人照护的议题长期处于相对边缘化的状态(Liu & Sun,2014),除了一些私人养老院和一些富裕省市在社区范围内实施的老年人照护服务试点外,大多数照护任务还是由家庭成员来完成。当家庭成员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胜任照护任务时,许多老年人的照护状况就实质上处于空白状态。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在农村尤为严重,因为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青年人口外流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一些地区普遍存在失能老年人无人照护的状况(Liu & Flöthmann,2013),而且,我国还缺乏全国层面的专项针对老年人照护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需要照护的老年人将达到8 000万,在人口迅速老化、家庭核心化和少子化的趋势持续下,老年人的照护将成为极为严峻和棘手的社会问题,我国急需要在该项领域建立老年人照护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我国有价值的启示(试比较:Liu,2014)。
参考德国建立社会保险类型的长期照护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建立类似的照护保险制度是可行的,也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确立国家制度化类型的照护制度,不外乎采取以下形式:1.国家财政给付模式;2.社会保险模式。而国家财政给付模式又可以细分为(1)普惠式的照护保障和(2)根据严格需求调查而来的照护救助。任何国家,即使是富裕的西方国家也无法采取普惠式的照护保障,而根据需求调查而来的照护救助又可能因为严苛的“审核措施”和“入口障碍”导致大多数的照护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在社会保险领域,照护保险当然可以划归到医疗保险之下,然而在一个医疗保险制度负担日益沉重、费用居高不下的时代,医疗保险制度资源过度投入到长期照护容易导致医疗保险制度的整体“异化”*例如日本建立照护保险之后的经验也证明了照护保险的建立缓和了医疗保险制度的财政赤字和沉重负担(仝利民,2008),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照护保险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险内部不同险种的资源合理分配和发展。;而照护风险的独特性和长期性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符合照护风险规律的、高度专业分化的保险制度来满足社会巨大的照护需求。
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用过高在我国政界和学界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和重视,似乎额外再建立一个新社会保险险种——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较为困难。但仔细对比我国社会保险和德国的社会保险领域里的差别,我们就可以发现进一步改革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我国和德国的社会保险均包含五个领域,我国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德国则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长期照护保险,通过对比,可见两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非常类似,主要的差别在于我国有一个生育保险制度,德国有一个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而西方主要国家鲜有国家单独建立生育保险制度的,例如德国的生育保险自动包含在劳资协定之中,包括生育之后的工资续付政策,而国家财政也单独支付儿童养育津贴和父母津贴等,似没有特别的需求建立一个单独的生育保险制度。在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是由雇主一方支付保费的(与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劳资双方分摊保险费用有显著差别),这样的保险制度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雇主因为需支付额外的生育保险待遇而不愿雇佣女性劳工和职员。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社会保险领域里的“合理化战略重构”的需求,我国应该逐步取消生育保险这个险种,将其归于劳动保护政策中去,或是采取国家财政支付的“生育保障”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新的照护保险险种来应对社会实质的巨大需求和社会风险——老年照护。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就反映出了作者提出的社会保险制度内部各险种重构的基本格局。
在照护保险制度覆盖群体上,德国采取的是近乎覆盖整体国民(不分年龄阶段)的需求,而日本采取的是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及40至60岁的群体的照护需求的照护保险制度,在这一点上我国似宜借鉴日本模式,因为根据分年龄阶段的照护需求来看,60岁以下的群体照护需求是非常低的,对于这样的需求可采取家庭照护或是国家财政补助的模式来覆盖,而照护保险制度锁定的主要照护对象还应是60岁、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民众。因为随着在老龄阶段年龄的提高,特别是进入高龄阶段后,照护需求则显著上升。因此我国的照护制度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老年照护制度,而并非针对不分年龄群体的照护保险制度,根据我国的平均寿命,老年阶段的照护保障可考虑定在60岁,而针对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可以设计更为宽松的老年照护保险制度,照护保险的补贴和补助可以适当增加。
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并非一个“全额保障”的制度,承担的仅仅是“部分责任”,但至少可以部分、甚至是显著减缓了由照护需求而带来的社会风险。我国的老年照护保险模式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制度构建,也就是建立的国家照护保险制度并非要承担全责,而是担任一个“部分减压阀“的角色。同时,国家整体制度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但在具体经办实施照护服务和照护递送上充分考虑到照护制度的“福利多元主义”特征,鼓励多元的角色参与照护,专业照护的服务费用应得到社会保险制度的补贴和报销。在我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环境下,我国是否能借鉴德国照护保险模式对家庭成员和邻里居家照护给予单独的“照护津贴”之专项给付,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和商榷的。预计会出现的批评观点为,对家庭成员内部的照护进行货币补贴会导致家庭内部关系的“货币化”,会导致我国传统家庭关系和家庭有机团结的“弱化”和“异化”,但家庭人员部分放弃工作而居家照护家人其实也等于放弃了部分“货币收入”,如果其隐形净收入损失无法得到补偿,那么其家庭生活势必陷入困境,也势必向我国的低保制度求助。从这个角度来说,给予提供照护的家庭成员照护保险金的补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家庭成员选择工作而不是留守家中照护,那么需要照护的老人仍然要向社会保障制度求助的。
考虑到我国照护需求日增,而照护领域的保障缺口日益扩大,国家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行地方试点,并根据国家统一规划来推动加速建立我国老年人照护保障制度的进程,最终建立我国社会保险的新险种——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展开“长期护理保险”(人社厅,2016)的试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广泛借鉴长期照护保险首创国——德国的经验,充分学习和吸收德国完备的长期照护保险法典中的立法条款和德国丰富的长期照护实践,根据德国长期照护领域的庞大数据库分析其基本发展趋势,以期充分借鉴德国这一福利超级大国的难得经验来为我国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而服务。为了完成这一战略性目标,需要我国和德国社会政策界及实业界的紧密联系与长期合作研究,国际知识的转移和本土内化必将大大促进我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向纵深方向发展。
人社厅(201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8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1607/t20160705_242951.html.2016年8月1日访问.
仝利民(2008).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及其对上海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Achinger, H. (1953).SozialeSicherheit:EineHistorisch-soziologischeUntersuchungneuerHilfsmethoden. Stuttgart: Vorwerk.
AOK-Bundesverband.(2015).PflegegeldunddasVerhinderungspflegegeld.Available at(March 15,2015):http://www.aok-bv.de/zahlen/gesundheitswesen/index_00539.html.
Bäcker, G., Bispinck, R., Hofemann, K. & Naegele, G. (2000).SozialpolitikundSozialeLageinDeutschland.BandII. Wiesbaden: Wesdeutscher Verlag.
Bäcker, G., Bispinck, R., Hofemann, K. & Naegele, G. (2010).SozialpolitikundSozialeLageinDeutschland.BandII.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Birg, H. (2001).DieDemographischeZeitenwende.DerBevölkerungsrückganginDeutschlandundEuropa.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2015).Sozialversicherung2015. Available at(March 15,2015):http://www.sozialversicherung-aktuell24.de/.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2014).ZahlenundFaktenzurPflegeversicherung. Available at(March 15,2015):http://bmg.bund.de/fileadmin/dateien/Downloads/Statistiken/Pflegeversicherung/Zahlen_und_Fakten/Zahlen_Fakten_05-2014.pdf.Chandhoke, N. (2001). The “Civil” and the “Political” in 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8(2): 1-24.
de Neubourg, C. (2002). The Welfare Pentag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of Risks. In Sigg, R. & Behrendt, R. Eds.SocialSecurityintheGlobalVillag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Die Zeit(2012).ZahlenundFaktenzumPflege-Bahr. Available at(March 15,2015):http://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2-06/Pflege-Bahr.
Esping-Andresen, G. (1990).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vers, A. & Wintersberger, H. (1988).ShiftsintheWelfareMix.TheirImpactonWork,SocialServicesandWelfarePolicies. Vienna: Europäisches Zentrum für Ausbildung und Forschung auf dem Gebiet der sozialen Wohlfahrt.
Evers, A. & Svetlik, I. (1993).BalancingPluralism.NewWelfareMixesinCarefortheElderly. Aldershot, Brookfield etc.: Avebury.Evers, A. & Olk, T. (1996).Wohlfahrtspluralismus.VomWohlfahrtsstaatzurWohlfahrtsgesellscha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Gliman, M. E. (2005). Poverty and Communitarianism: Toward a Community-based Welfare System.UniversityofPittsburghLawReview, 66: 721-820.
Hämel, K. (2012). ÖffnungundEngagement.AltenpflegeheimeZwischenStaatlicherRegulierung,WettbewerbundZivilgesellschaftlicherEinbettung.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Hobbes, T. (1794).Leviathan,OderderKirchlicheundBürgerlicheStaat. Halle: Hendel.
Kaufmann, F. X. (1997).HerausforderungendesSozialstaat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Kaufmann, F. X. (2003a).VariationsoftheWelfareState:GreatBritain,Sweden,France,GermanybetweenCapitalismandSocialism. Berlin: Springer.
Kaufmann, F. X. (2003b).ThinkingaboutSocialPolicy:TheGermanTradition. Berlin: Springer.
Kaufmann, F. X. (2005).SchrumpfendeGesellschaft:VomBevölkerungsrückgangundSeinen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Kaufmann, F. X.(2013).VariationsoftheWelfareStates:GreatBritain,Sweden,FranceandGermanybetweenCapitalismandSocialism. Berlin: Springer.
Klement, C. (2006).VonderLaienarbeitzurProfession?ZumHandelnundSelbstverständnisberuflicherAkteureinderambulantenAltenpflege. Opladen: Budrich.
Klie, T.( 2005).Pflegeversicherung. 7.Auflage. Hannover: Vincentz.
Liu, T. & Flöthmann, E. J. (2013). Die neue Alternde Gesellschaft. Demographische Transformation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Altersversorgung und Altenpflege in China.ZeitschriftfürGerontologieundGeriatrie, 46(5): 465-475.
Liu, T. (2014). Nursing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in Germany and China: A Bilateral Comparison and Exploration of Policy Transfer.JournalofNursing&Care, 3 (6): 1-4.
Liu, T. & Sun, L.(2014). An Apocalyptic Vision of Ageing in China: Old Age Care for the Largest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World.ZeitschriftfürGerontologieundGeriatrie, 48(4): 354-364.
Luhmann, N. (1981).PolitischeTheorieimWohlfahrtsstaat. München: Günter Olzog Verlag.
Luhmann, N. (1997).DieGesellschaftder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Luhmann, N. (2000).DiePolitikder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Portal für Senioren.(2011).VersorgungslückenbeiPflegebedürftigkeit. Available at(July 20, 2015):http://www.portal-fuer-senioren.com/finanzen-und-vorsorge/ versorgungsluecken-bei-pflegebeduerftigkeit/.
Rodger, J. J. (2000).FromaWelfareStatetoaWelfareSociet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etc.: The Palgrave Macmillan.
Roth, G. & Rothgang, H. (2001). Sozialhilfe und Pflegebedürftigkeit: Analyse der Zielerreichung und Zielverfehlung der Gesetzlichen Pflegeversicherung nach fünf Jahren.ZeitschriftfürGerontologieundGeriatrie, 34: 292-305.
Rothgang, H. (2009):TheorieundEmpiriederPflegeversicherung. Berlin: LIT Verlag.
Siaroff, A. (1994). Work, Welfare and Gender Equality: A New Typology. In Sainsbury, D. Ed.GenderingWelfareStat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Schmidt, M. (2007).PflegeversicherunginFrageundAntwort. 4.Auflage.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Tönnies, F. (1887).GemeinschagftundGesellschaft. Leipzig: Fues’s Verlag.
Ullrich, C. G. (2005).SoziologiedesWohlfahrtsstaate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Verlag.
Weibler, U. & Canzler, M. (2006).QualitätinderAltenpflege:Bestandsaufnahme,Informationen, Ratgeber. Nierstein: Iatros-Verlag.
D669
A
1674-2486(2016)04-0068-20
*刘涛,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青年教授;德国华人教授协会成员;北京大学“触摸思想,倾听智慧”系列讲座,荣誉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