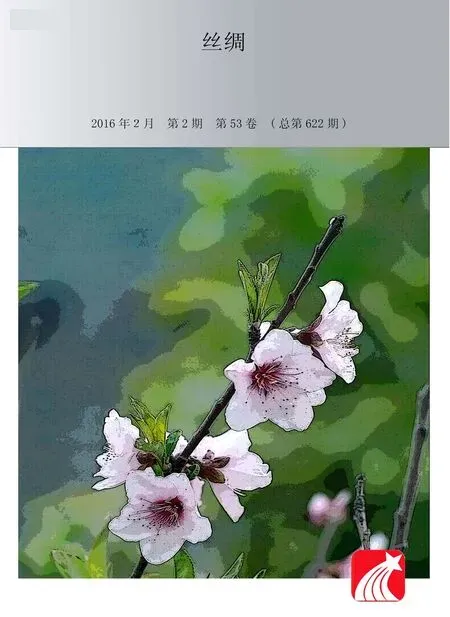宋代绞经丝织物研究
2016-08-13蔡欣
蔡 欣
(东华大学 服装·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51)
历史与文化
宋代绞经丝织物研究
蔡欣
(东华大学 服装·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51)
摘要:绞经织物是一种古老的织物类型,在宋代丝绸中发展定型并广泛流行。采用文献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观察法、实证研究法、数量研究法,对历史文献和出土实物中的宋代绞经织物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研究表明:考古发现的宋代绞经织物中数量最多的依次为四经绞素织物、二经绞素织物和三经绞提花织物;根据对织物纹样规格的分析,三经绞织物应是由加装绞综的束综提花机织制的;考古发现的大部分绞经织物来自长江以南地区,这与文献中关于土产的记载吻合;对照文献记载可推测,宋代民间根据织物肌理效果更倾向于将二经绞织物称为纱,将三经绞织物和四经绞织物称为罗;宋代纺织界则根据织机和织造工艺将二经绞和三经绞织物称为纱,将四经绞织物称为罗。
关键词:宋代;纱;罗;绞经;丝织物;丝绸;考古发现
纬线相缠称为纠,经线相缠称为绞。相邻的经线(纬线)不相平行的纠绞织物最初以手工编织物的形式出现。根据对1987年河南省郑州市仰韶文化时期青台遗址出土的织物残片进行研究,人们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将编织和原始腰机挑花技术相结合织出了绞经织物[1],实现了这类织物从编织物到梭织物的过渡。绞经织物在宋代发展定型,并且开始广泛流行。
《淮南子·汜论训》中曾提到“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制罗始于上古时代的生产活动,罗是猎渔和捕鸟的网具。早期即将绞经织物称为“罗”可能与上述网罗具有很大的关系[2]。典型的绞经织物,如四经绞罗类织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3]60,终于元末明初,延续了1 500年以上的时间[4]。现代织物组织学认为,织物中仅纬线相互平行排列,经线分为绞经和地经,绞、地经相互扭绞地与纬线交织的情况可称为纱罗组织[5]135,由纱罗组织构成的纱罗织物等同于绞经织物。
有学者认为,由于在汉、唐期间产生了“方孔曰纱,椒孔曰罗”的定名,于是可推断“纱”是平纹织物,“罗”才是绞经织物,到了明、清,因出现了纺织名称的相互借用,纱罗才被作为绞纱织物的统称[6]。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周全。在很多史料中,都有宋代花纱或者暗花纱的记载,这类纱就是绞纱。从染织史学科的角度来看,关于纱(绞纱)和罗的区别与联系,须按照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将遗存的文献记载与实际物品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
1 考古发现的宋代绞经织物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出土的丝织品并不算丰富,建立政权以来,已知有丝织品出土的宋代墓葬和遗址总数也只有十余个。其中主要的考古发现的地址、名称和发掘时间如下:浙江兰溪南宋潘慈明夫妻合葬墓(1966年)[7]、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1966—1967)[8]、湖南衡阳何家皂山北宋墓(1973年)[9]、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1975年)[10]、福建福州南宋黄昇墓(1975年)[11]、江苏苏州瑞光塔北宋遗址(1978年)[4]、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1986年)[12]、福建福州茶园村南宋墓(1986年,有关具体丝织品考古报告尚未公开发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1988年)[13]、江苏高淳花山宋墓(2003年)[14]、江苏南京长干寺北宋地宫(2008年)[15]、浙江余姚史嵩之南宋墓(2012年,有关具体丝织品考古报告尚未公开发表)、浙江武义徐谓礼南宋墓(2012年,有关具体丝织品考古报告尚未公开发表)。每个墓葬遗址所出土的丝织品中都有绞经织物。遗憾的是,在发现宋代丝织品实物的时候,几乎没有同时发现能直接佐证丝织品名称和类别的文字资料。
1.1二经绞织物出土情况
考古中发现的宋代二经绞织物整理汇总如表1所示。

表1 考古发现的宋代二经绞织物情况汇总
1.2三经绞织物出土情况
考古中发现的宋代三经绞织物整理汇总如表2所示。

表2 考古发现的宋代三经绞织物情况汇总
1.3四经绞织物出土情况
考古中发现的宋代四经绞织物整理汇总如表3所示。

表3 考古发现的宋代四经绞织物情况汇总
1.4绞经织物的组织结构类型
在对文物实物进行分析和整理汇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目前已确定的宋代绞经织物进行了组织结构复原和分类工作,结果如图1—图10所示。其中图3、图4分别为一顺绞二经绞地浮纬花织物、对称绞二经绞地浮纬花织物。实际上,根据织造原理推断有对称绞二经绞素织物和对称绞二经绞平纹花织物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只是笔者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及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两种类型。

图1 二经绞素织物Fig.1 Two-Ends-Twisted plain fabrics

图2 一顺绞二经绞地平纹花织物Fig.2 One cross warp twisted with one ground warp jacquard leno with tabby weave pattern and Two-Ends-Twisted ground

图3 一顺绞二经绞地浮纬花织物Fig.3 One cross warp twisted with one ground warp jacquard leno with floats pattern and Two-Ends-Twisted ground

图4 对称绞二经绞地浮纬花织物Fig.4 Symmetric warp twisted jacquard leno fabric with weft floats pattern and Two-Ends-Twisted ground

图5 三经绞素织物Fig.5 Three-Ends-Twisted plain gauze

图6 三经绞地平纹花织物Fig.6 Fancy gauze with tabby weave pattern and Three-Ends-Twisted ground

图7 三经绞地斜纹花织物Fig.7 Fancy gauze with twill weave pattern and Three-Ends-Twisted ground

图8 三经绞地隐纹花织物Fig.8 Fancy gauze with hidden warp floats pattern and Three-Ends-Twisted ground

图9 四经绞罗Fig.9 Four-Ends-Twisted leno

图10 四经绞地二经绞花(二经绞地四经绞花)织物Fig.10 Leno fabric with Four-Ends-Twisted pattern and Two-Ends-Twisted ground (Two-Ends-Twisted pattern and Four-Ends-Twisted ground)
2 宋代绞经织物的技术信息
绞经织物的结构和性能比较特别,在生产中最关键的两点是对经线进行特殊处理和使用起绞机具。
2.1经线处理
经线扭绞的结构需要经线具备更大强度,宋人广泛采用过糊工艺对绞经织物的经线进行预处理。过糊工艺现代称为上浆,原理是通过给经线刷浆液来增加强度,防止和减少在织造过程中产生的擦毛和断头。通常在通经时进行,即在印架和经轴之间用筘过糊,同时浆丝者用剪刀修理。黑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吴注本《蚕织图》上画出了过糊的工具和操作(图11左部分“作织”)[3]277。

图11 吴注本《蚕织图》局部Fig.11 Part of Silkworm and Weaving, Wu’s version with annotations

图12 《耕织图》中装有绞综的提花机Fig.12 Jacquard loom with doup harness in Sericulture and Weaving
2.2织机机构
目前历史文献中最清晰的织机形象来自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宋《耕织图》,可见机前位于普通综片和织工之间侧面用连杆相连的对偶式绞综(图12)[3]279。整个绞综由两个综框构成,综框间有一活动连杆将其连接,两综框可以各自在连杆控制的范围内上下运动,每一综框各有一片基综和一片半综组成,完全对称的两综框才组成一个完整的绞综[18]。绞综(半综)的综圈两两勾连,横穿基综下口,地经位于两基综之间的绞综勾连线圈之上,绞经穿在前片综的综圈内。因为存在连杆,相互勾连的绞综线圈处于半紧张状态,经线与综圈不会互相缠绕。织造时,对偶式绞综所形成的三种梭口形式如图13所示。

图13 对偶式绞综在织造绞经织物时所形成的三种梭口Fig.13 Three sheds formed by coupled doup harness
薛景石的木制机具专著《梓人遗制》成书于宋元之交,书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小扇椿子”(绞综)(《梓人遗制图说》一书作者认为“大泛扇椿子”为绞综,笔者认为“大泛扇椿子”为起综)的“罗机子”(织罗机)和带有“白踏椿子”(绞综)的“华机子”(一种提花机),两者的区别在于织机上有无筬框(筘)及是否用斫刀打纬(图14、图15)[19]61-72,85-88。有筘的织机用于织造有固定绞组的绞经织物,无筘且用斫刀打纬的织机用于织造无固定绞组的绞经织物。
2.3织物纹样
因为织造技术的进步,大量出现了上文所介绍的多种结构的绞经织物,织物上的纹样也更加丰富多变。
2.3.1纹样题材
通过对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宋代绞经织物上出现过的主要纹样主题如表4所示。

图14 《梓人遗制》中的华机子(郑巨欣博士加注)Fig.14 Draw loom (Hua Ji Zi) in Time-Honoured Institutions of Carpenters(Zi Ren Yi Zhi), with Ph. D ZHENG Juxin’s annotation

图15 《梓人遗制》中的罗机子Fig.15 Complex leno loom (Luo Ji Zi) in Time-Honoured Institutions of Carpenters (Zi Ren Yi Zhi)

织物类型提花纹样主题二经绞地平纹花织物玫瑰、卍字菊花等小朵花、如意、缠枝花二经绞地浮纬花织物方格飞鸾、花卉纹、卍字梅花、几何纹等小朵花、长安竹、折枝花三经绞地平纹花织物缠枝花卉、芍药、兰花等组成团花图案、折枝花、穿枝花、如意纹、杂宝纹、璎珞纹三经绞地斜纹花织物缠枝花卉、折枝花、穿枝花、如意纹、杂宝纹三经绞地隐纹花织物花卉四经绞地二经绞花(二经绞地四经绞花)几何纹、缠枝花卉、朵花、小花
元人戚辅之在其所著《佩楚轩客谈》中记载宋代十样锦,其一便是长安竹。于少先先生推测德安周氏墓中形似竹叶和梅花的纹样为长安竹(图16)[3]44,如此将相同纹样运用到不同织物种类上的情况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常有出现。
当时非常流行小折枝花样式(图17)[3]44,在二经和三经绞织物中都有体现;在器物纹样方面,运用较多的主题是如意(图17)和杂宝(图18)[11]87。矩纹是自汉代就出现的几何纹样,在宋代依然流行(图19)[10]25。
2.3.2纹样形式
从方格飞鸾纹(图20)[15]70的出现,亦可以印证装有绞综装置的束综提花机在宋代的普及。该纹样出自南京长干寺北宋地宫中的二经绞浮纬花织物,纹样在经向和纬向上均得到重复的特征正是得益于束综提花机花本中一根脚子线可控制几根衢线的工艺优势。
三经绞织物的大量出现和流行推动了纹样设计方面的创新。这个时期流行的一种花卉纹样形式为在大型写生折枝或缠枝花卉的主花叶中加入写实风格的小型宾花(图21)[11]97,写实造型和虚构配伍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纹样本身的装饰效果。

图16 长安竹Fig.16 Chang’an bamboo

图17 如意纹和折枝花Fig.17 Wishful pattern and floral sprays

图18 杂宝Fig.18 Treasures pattern

图19 矩纹Fig.19 Geometric pattern

图20 方格飞鸾纹Fig.20 Check and pheasants

图21 叶内织梅花Fig.21 Plum blossom in leaves
黄昇墓中出土的多件用于服饰品面料的三经绞织物,其纹样的花回均在30 cm×20 cm以上。以当时织物的普通幅宽多在50~60 cm推测,这类型的织物很可能只在纬向上重复两次。此种情况亦说明这样的织物应该是在束综提花机上织造的。
3 有关绞经织物的文献与实物对比研究
3.1宋代绞经织物主产区域
宋代丝织业发达的河北地区(包括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四川地区(包括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江南地区(包括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都有各具特色的绞经织物出产。
3.1.1黄河以北及四川地区
宋官府重视绞经织物织造,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罗织物生产,设立了专门的官营织造机构。根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记载,设立在都城的大型手工业作坊文思院,成立之初的“七十四作”中就有“织罗作”(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七二至七三),这也许是对唐代织染署织纫之作中罗作的沿袭。
河北东路定州产质地厚重的定罗,是著名土产。
成都府路有花纱、春罗、大花罗、单丝罗、彭州产彭州罗,《老学庵笔记》中提到遂宁府对越州尼院织罗进行仿制,所生产的罗后来也被叫做越罗,超过了原越州越罗的品质(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3.1.2长江以南
宋官府在江宁府、润州、常州等地设有织罗务(元代脱脱等《宋史》食货上三卷一百七十五、《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八),同时明确规定生产罗织物的劳动时长。如润州织罗务,在景德年间规定工匠在十二日织成一匹罗(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八)。对于产品质量亦有标准,平罗一匹要及一十九两,婺罗一匹二十二两(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志六四之二八至二九)。
值得一提的是,两浙路逐渐成了全国最主要的罗织物产地。北宋某几年中岁租之入的罗织物共860匹,全部产自两浙路;两浙路所产罗织物为65 731匹,占到全国总产罗织物的40%以上(原始数据出自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至九)。《嘉定赤城志》有载,两浙路越州和台州等地所产罗织物,自唐代就有“越罗”的好名声(宋代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浙中部的婺州逐渐成为新的产罗重地,婺州辖区内的义乌“山谷之民,织罗为生”(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四),已出现专业的织罗户,婺罗的名气后来盖过了越罗。南宋时期,临安府所藏的罗织物就是来自于越州和婺州的。所谓浙东有茜绯花纱、越罗和四经绞提花罗、邻近的婺州产含春罗、暗花罗等,这些产品在当时远近闻名,在历史上也传下美誉。
3.1.3对比研究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目前已知有绞经织物出土的13座宋代墓葬遗址中,有5座位于今江苏省境内,4座位于今浙江省境内,1座位于今江西省境内。这10座墓葬均属于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地域范围内,与文献记载中的情况有很大部分吻合。
3.2宋代绞经织物的名贵品种
根据当时的记载,可知绞经织物确实有纱和罗区别。有关宋代纱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专题笔记和地方志中,能留下文字记录的在当时都是名贵品种。宋代罗的记载广泛出现在专题笔记、地方志及给皇帝的奏折中。从文字和介绍看来有素罗,也有花罗。
3.2.1宋代纱
从对这些纱织物的介绍来分析,大多数为平纹纱,有绵州产的巴西纱子(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五),临川上饶人开发的醒骨纱(宋代陶谷《清异录》卷三),抚州莲花寺的莲花纱(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京东一带单州成武县所织纱(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上),唐代就已闻名的亳州轻纱(宋代张詠《乖崖集存》卷一《筵上赠小英》、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这些纱的共同特点为轻薄透孔,适合作为夏季的衣料,织者大多掌握了密不外传的技术要领,因此产品质量不易被超越。轻容纱在唐代也已闻名,关于它的介绍最为清楚:“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无花薄纱也’(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
明确对花纱列举出现在《梦梁录》中。作者记录了当时杭州所产的丝织名品,其中纱包括纱、素纱、天净、三法暗花纱、栗地纱、茸纱(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一八《丝织品》)。这里的纱应是指与上文相同的平纹纱,素纱则指的是二经绞素织物,花纱有天净、三法暗花纱、栗地纱、茸纱。
3.2.2宋代罗
如《鸡肋编》中记载有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有文人评论说因两浙所产蚕丝纤细,织出的罗比北方的定罗轻薄(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上),这也算明显的地域特点。《嘉泰会稽志》中介绍越州尼院中的宝街罗是对唐代越州上贡宝花罗者的继承,后来又发展出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等样式,档次更高(宋代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布帛》)。《梦梁录》记载了当时杭州所产的丝织品有“罗花素、结罗、熟罗”(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一八《丝织品》)。朱熹在向宋孝宗皇帝上奏状,弹劾贪官唐仲友,要求惩治其非法行径的奏折中提到暗花罗、瓜子罗、春罗(宋代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王明清所著《挥麈后录馀话》记载了南宋初年左丞相叶梦得与宋高宗之间关于婺州上贡罗的对话,其中提到贡罗有平罗、婺罗、花罗三等(宋代王明清《挥麈后录馀话》卷一)。《武林旧事》中记录了将生花番罗二百匹、暗花婺罗二百匹作为高档贡品献给皇帝的事件,此外作为礼品送给官员的有紫罗和罗缬(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3.2.3对比研究
虽然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宋代纱罗名品的产地和名称,但由于文物出土时无明确对应的文字记载,所以文献和实物的对比研究很难进一步开展。目前只有赵承泽先生根据二重证据法尝试过对“三法暗花纱”的名物考证。
3.3宋代绞经织物主要用途
绞经织物作为费时费工的贵重丝织品,虽然主要产自民间,但寻常百姓是用不起的,这些丝绸只能通过交租税、土贡和贸易交换等途径来实现其价值。绞经织物在日常生活中用于高档服饰和家居用品。
3.3.1国家所用
《文献通考》曾记载,宋代縠、帛、金、铁物产四类租税中,仅布帛丝绵之品就有十种,以罗为首,第四种为纱(在此文献中没有明确纱的指代,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四考五七)。《宋史》(食货上二卷一百七十四)中关于岁赋之物也有相同的介绍。史料中也多见关于纱、罗作为税、贡的记载,如北宋时期宋仁宗于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降敕减轻东西两川织造上供花纱等高档织物的任务(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二二),南宋时期宋高宗于绍兴三年下诏给婺州人减少岁额上供罗数量(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田赋五考六三)。这些罗织物到了宋官府手中,主要用途有三:一是作为对外买和时的“岁赐”送给辽,如在契丹主生日和契丹主母亲生日时辽向宋要求的贺礼中就明确提到杂色罗和纱;二是按照相关规定为本朝官员发放俸禄,如《宋史·职官志》所记载的朝廷给予官员的实物俸禄有很大一部分是丝绸,其中罗织物占到一定比例,又如官员每年春、冬两季的衣赐中也包括不少罗织物;三是进行国际贸易,如宋朝向高丽输入大量丝绸,多达几十个品种,其中就有花纱和罗[20],再如真里富国(今柬埔寨)人所用绯红罗绢都是由宋朝商舶带去进行贸易交换的(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九),还有宋朝与西夏在保安军所置榷场中用包含罗在内的丝织品交换羊、马、牛、驼、玉、毡毯、甘草等西夏土产(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一考二〇一)。
3.3.2成品形式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骚人墨客异常活跃的时期,宋代文人在其作品中留下了关于丝织品的大量记载。文学作品中有关丝织品的信息涉及色彩、工艺、产地、纹样、感官效果、品种、成品名称(服饰或家居用品为主)等。
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在前版基础上更加广泛精确地收录了宋词作品。通过对全书所计辑的1 330余家两宋词人约20 000首词作进行研读和摘抄,本研究整理并过滤出宋词中所提到的纱罗织物及制品,如表5[21]所示。全书中共出现过14种丝织品的名称,涵盖了中国古代丝织品种中的大多数,各类丝织品被提及的频率不一,其中以罗为最。由于诗词受格律和字数的限制,描述简洁,通常只能表达色彩、工艺、产地、纹样和感官效果中的一到两项,对于纹样的具体描述相对欠缺。但是这些记载仍是将文献资料和实物进行对照研究以推测当时织物定名的重要依据。
3.3.3对比研究
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裂峰山耶律羽之墓、宝山1号和2号墓、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墓等一系列高规格的辽国墓葬中所发现的绞经织物[22],以及阿城金齐国王墓所出土的绞经织物[23]可知,宋朝与同时期存在的辽金政权确实存在纺织品方面的往来。余姚史嵩之墓、金坛周瑀墓等官员墓葬中占所发现丝织品比例较高的绞经织物所制成的大量衣物,也印证了当时官员的实物俸禄中涉及不少罗织物的史实。来自考古发现的绞经织物成品形式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亦有能够对应的部分,具体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表5 《全宋词》中提到的宋代绞经织物
4 绞经织物在宋代的定名探讨
4.1与现代纱、罗织物的关系
无固定绞组的绞经织物,如四经绞素罗和四经绞花罗,因其制造工艺复杂,生产效率低下,元末明初以后就被更简单的新结构所取代。现代织物组织学将纱和罗定义为两种不同的织物。凡每织一根纬线或共口的数根纬线后,绞经与地经相互扭转一次,使织物表面呈现均匀分布纱孔的组织称为绞纱组织(图22)[5]135。绞纱组织与平纹组织沿纵向或横向联合,使织物表面呈现横条或纵条纱孔的组织为罗组织(图23)[5]136。现代纺织术语中的纱与古代的纱还相对接近,但罗与古代的罗已相去甚远,概念中全无“椒孔”的痕迹。

图22 现代纱织物组织结构图例Fig.22 Typical weave structures of modern gauze fabrics

图23 现代罗织物组织结构图例Fig.23 Typical weave structures of modern leno fabrics
4.2宋代民间对纱、罗的区分
总体而言,在古代文献中对纱、罗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这也影响到当代学者对古代纱、罗的定名研究。例如,地经与绞经比例为1︰1,一纬一绞的二经绞素织物,可以叫做二经绞素纱,在唐代也曾被称为单丝罗(唐代李林甫修《唐六典》卷三)。四经绞罗在很长时间内也被称为链式罗。纱与罗在界定上模糊的原因可能是在中国古代,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包括织工织匠)通常文化程度较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能力为后世留下关于纺织技术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资料。目前,所能见到的提及宋代丝织品的文献,大都出自当时的文人之手。他们普遍缺乏工艺实务经验与专业知识,有些记载仅凭日常生活经验和民间口口相传的叫法。
以《全宋词》为例,“罗”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所描绘的罗织物和罗制品色彩丰富、用途广泛。根据前文中有关墓葬遗址的出土丝织品整理汇总,可以进行粗略统计,绞经织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三类为四经绞素织物、二经绞素织物和三经绞提花织物。实物中的四经绞织物大部分与文献记载的“罗”吻合,除了衣裙之外就连襟、袖、袂,绶、带,巾、帕等服装零部件或者小服饰品也能与文献表达对应;三经绞织物用在衣、裙、衣襟、袖口、鞋、袜等处,即与文献中的“纱”相关,又与“罗”相关;二经绞织物用于衣、裙、帽、袖口、巾、帕,与文献中提到的纱衫子、纱裙、纱巾、纱帽、纱帕子等基本对应。《全宋词》中没有提到花纱,只提到了越纱,二经绞织物实物中也是素织物的数量占多数。《元丰九域志》所介绍的越州土贡特产中有绯红花纱和轻容纱(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卷第五两浙路越州),这两种纱一种是二经绞组织的绞经织物,一种是轻薄的平纹织物,很有可能《全宋词》中的越纱是对它们的泛指,由此推测,二经绞织物在当时还是普遍被叫做纱的。赵承泽先生曾经将文献和实物进行对照研究,他推测周瑀墓中出土的二经绞平纹花纱为前文中引用过的《梦梁录》所记载的三法暗花纱,因为这种花纱的图案以三行类似“工”字的纹样为基础,组成了矩纹[24]。三经绞织物是唐宋时期发展出的新种类,质地比二经绞织物厚实,结构比二经绞织物牢固,织造工艺比四经绞织物简单,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晚但生命力旺盛,直到民国时期的传世实物中还能找到唐宋三经绞织物的变异结构。根据实物研究可知,三经绞织物在宋代已得到大量生产,是当时主要的丝织品种之一。可是文献中却鲜有关于三经绞织物的明确记载,记载得最多的还是“罗”。结合文献与实物分析,笔者推测,在宋代,民间更倾向于把三经绞织物称为罗。综上所述,宋代民间区分纱、罗的主要依据在于织物的肌理效果。
4.3宋代纺织界对纱、罗的区分
成书于宋元交接之际的木制机具专著《梓人遗制》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从中可见宋代纺织界界定纱和罗的方法。作者薛景石是出生于设计制造织机的木工世家,他亦是木工匠师和理论家。书中有关于“罗机子”和”华机子”记载。
其中“华机子”条“用材”部分介绍:“或织纱,则用白踏。”“白踏”为“白踏椿子”的简称,就是指用于经线起绞的绞综机构。根据前文所列举的织物组织复原图,二经绞和三经绞织物在织造中需要使用带筘的织机,四经绞罗在织造中只能用打纬刀打纬;以及前文对出土文物纹样规格的分析,可推测三经绞织物应由“华机子”即加装有绞综的束综提花机织造。因此可知,当时匠人包括织工和木匠是按织物有无固定绞组来区分纱(绞纱)和罗的,将二经绞和三经绞织物称为纱,四经绞织物称为罗。
5 结 语
绞经织物轻薄透气,结构稳定,牢固耐用,在古代曾被长期用作夏季服饰和家居用品面料。宋代大量生产纱、罗,主要分布在当时的三大丝织业产地,而且各个地区都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特产,这在历史文献中亦得到了印证。这些结构特殊、工艺复杂的纱、罗,成为国家税收、对外交流、国际贸易所用丝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代织物组织学与古代织物组织学存在较大差异,宋代文献中对于纱和罗的绝大部分记载并不专业,给染织史研究带来一定困难,迫切需要结合文献与实证的综合研究以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已发现的宋代墓葬相对其他朝代较少,但只要有丝绸出土,丝绸中就有绞经织物。经过对有关纱、罗文献的整理汇总和对考古发现第一手资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对比可知,罗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高于纱;目前所知实物中数量最多的前三种绞经织物分别为四经绞素织物、二经绞素织物和三经绞提花织物;根据对织物纹样规格的分析,三经绞织物应是由加装绞综的束综提花机织制的;考古发现中的绞经织物地域来源(长江以南地区)与文献中关于土产的记载有很大部分吻合;宋代对纱罗的定名分为两种情况,民间按照织物的肌理效果来区分,纺织界按照生产所需的织造工具和工艺来界定;二经绞织物和平纹纱同样被称为纱,四经绞织物被称为罗,唐宋时期发展的新品种三经绞织物很有可能在民间被称为罗,在业界被称为纱。
参考文献:
[1]沈莲玉,高汉玉,周启澄.中国古代织花技艺与织机发展的研究[J].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5,21(2):32-39.
SHEN Lianyu, GAO Hanyu, ZHOU Qicheng. A study on developments of techniques and looms for pattern weaving in ancient China[J]. Journal of Donghua University,1995,21(2):32-39.
[2]史文训.中国古代绞纱织制技术及其发展[D].杭州:浙江丝绸工学院,1985:21,49.
SHI Wenxun. The Guaze Weaving Technique and Its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D]. Hangzhou: Zhejiang Institute of Silk Textile Technology,1985:21,49.
[3]赵丰.中国丝绸通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ZHAO Fe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ilk[M].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2005.
[4]吴文寰.从瑞光寺塔发现的丝织品看古代链式罗[J].文物,1979(11):40-42.
WU Wenhuan. A study of ancient complex gauz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ilk relics excavated from the pagoda of Ruiguang Temple, Suzhou[J]. Cultural Relics,1979(11):40-42.
[5]顾平.织物结构与设计学[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GU Ping. Fabric Structure and Design [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Co, Ltd,2004.
[6]夏正兴.中国古代罗织物[J].上海纺织工学院学报,1979(3):86-92.
XIA Zhengxing. Ancient Chinese leno[J]. Shanghai College of Textile Technology,1979(3):86-92.
[7]赵丰.古代纱罗织物及其对现行组织学的启示[J].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86,3(4):50-55.
ZHAO Feng. Ancient leno weaves suggestive of extending the range of modern leno weave[J]. Journal of Zhejiang Institute of Silk Textiles,1986,3(4):50-55.
[8]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J].文物,1973(1):48-53.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lics excavated from Huiguang Pagod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ui’an, Zhejiang[J]. Cultural Relics,1973(1):48-53.
[9]陈国安.浅谈衡阳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J].文物,1984(12):77-81.
CHEN Guo’an. A study of textiles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Hejiazao Moutai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ngyang[J]. Cultural Relics,1984(12):77-81.
[10]镇江博物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7):22-26.
Zhenjiang Museum. A bulletin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Zhouyu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Jintan, Jiangsu[J]. Cultural Relics,1977(7):22-26.
[11]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6-76,87,97.
Fujian Museum. Thirteenth-Century Tomb near Fuzhou[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1982:26-76,87,97.
[12]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J].考古,1986(3):247-268.
CHEN Jing, CHEN Lihua. A summary of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near Wujin of the Southern Song, Jiangsu[J]. Archeology,1986(3):247-268.
[13]周迪人,周旸,杨明.德安南宋周氏墓[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19-25,27-30,33-38,44.
ZHOU Diren, ZHOU Yang, YANG Ming. Thirteenth-Century Tomb at De’an in Jiangxi[M].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9:19-25,27-30,33-38,44.
[14]顾苏宁.高淳花山宋墓出土丝绸服饰的初步认识[G]//学耕文获集:南京市博物馆论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52-68.
GU Suning. A study of the silk costume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Hua Moutain of the Song dynasty, Gaochun County[G]// Study Harvest: the Symposium of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ublishing Ltd,2008:52-68.
[15]南京市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等.南京报恩寺遗址地宫文物保护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2-87.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et al. A Study of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Excavated from the Underground Palace Historic Site of Bao’en Temple, Nanjing[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2014:62-87.
[16]袁宣萍.浙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36-37.
YUAN Xuanping. Gauze from Zhejiang[M].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2011:36-37.
[17]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302-303.
CHEN Weiji.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ese Textiles: Ancient Section[M]. Beijing: Science Press,1984:302-303.
[18]张培高.南宋楼璹《耕织图》上的提花机[G]//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编委会.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12集.北京:纺织科学研究出版社,1983:36.
ZHANG Peigao. Drawloom in Gengzhitu drew by Loushou in Southern Song[G]//The 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Text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Documents of China texti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Volume 12. Beijing: Textile Science Research Press,1983:36.
[19]郑巨欣.梓人遗制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61-72,85-88.
ZHENG Juxin. Time-Honoured Institutions of Carpenters(Ziren Yizhi) with Annotation[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2006:61-72,85-88.
[20]陈慧.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J].东疆学刊,2009,26(7):99-105.
CHEN Hui. Koryo’s tribute trade with the Song dynasty[J]. Dongjiang Journal,2009,26(7):99-105.
[21]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TANG Guizhang. Entire Verses of Song Dynast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22]赵丰.辽代丝绸[M].香港: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17-29.
ZHAO Feng. LIAO Textile & Constumes[M]. Hongkong: Muwen Tang Fine Arts Publication Ltd,2004:17-29.
[23]赵评春,赵鲜姬.金代丝织艺术:古代金锦玉丝织专题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0-87.
ZHAO Pingchun, ZHAO Xianji. The Silk Art in the Jin Dynasty: Special Review of Ancient Golden Brocade and Silk[M].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1:80-87.
[24]赵承泽.谈福州、金坛出土的南宋织品和当时的纺织工艺[J].文物,1977(7):28-32.
ZHAO Chengze. Textile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Fuzhou and Jintan and contemporary weaving technology[J]. Cultural Relics,1977(7):28-32.
DOI:10.3969/j.issn.1001-7003.2016.02.011
收稿日期:2015-04-08; 修回日期: 2015-12-21
作者简介:蔡欣(1982—),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代染织服饰史论。
中图分类号:TS941.12;K87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2016)02-0061-12引用页码: 021301
Study on warp twisted silk fabrics in Song dynasty
CAI Xin
(Fashion·Art Design Institut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51, China)
Abstract:Warp twisted fabric is an ancient fabric type, which developed with finalized design and became widely popular silk fabrics in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Song warp twisted fabrics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s and unearthed objects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 observation method, empirical study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study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Four-Ends-Twisted plain fabrics, Two-Ends-Twisted plain fabrics and Three-Ends-Twisted jacquard fabrics have the largest quantity among Song warp twisted fabrics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analysis on fabric pattern specification, Three-Ends-Twisted fabrics are woven with jacquard loom with doup harness. Most warp twisted fabrics discovered come from region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records about local product in literatures. According to documentary record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t was more inclined to call Two-Ends-Twisted fabrics as gauze and Three-Ends-Twisted and Four-Ends-Twisted fabrics as leno in Song civil society according to texture effect of fabrics; Two-Ends-Twisted fabrics and Three-Ends-Twisted fabrics were called as gauze and Four-Ends-Twisted fabrics were called as leno in Song textile industry according to loom and weaving process.
Key words:Song dynasty; gauze; leno; warp twisted; silk; archaeological fi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