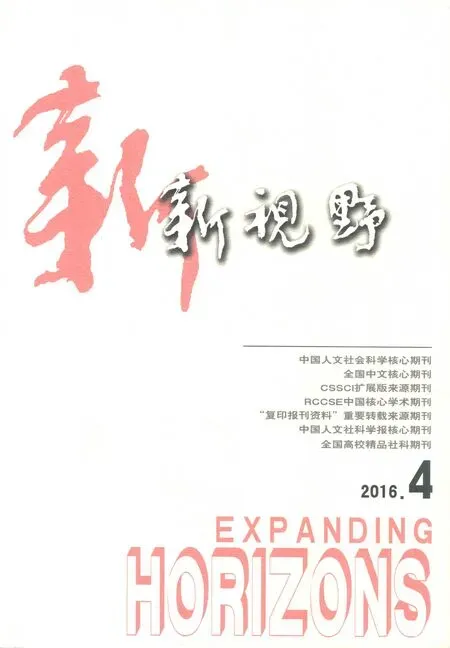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重大判断
2016-08-03杨海秀李志峰
文/杨海秀 李志峰
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重大判断
文/杨海秀 李志峰
摘要:钱学森不仅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有着独特贡献的思想家。他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作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重大判断,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第四次伟大尝试”。并基于此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键词: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不仅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有着独特贡献的思想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作了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在其晚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思想。他的丰富哲学思想既体现在他的各类论著中,也见之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所写的大量书信中。本文主要以其书信为基础,介绍他晚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中提出的三个重大判断,相信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创新不无裨益。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
钱学森在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科学技术的一线工作后,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全方位、综合性的学术工作。他十分注意系统论的发展动态,以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视野,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最终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在钱学森看来,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一个整体,它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这其中,当然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而在这一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最高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技术体系,并运用这个体系去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
钱学森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论著的启发,结合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面掌握,在1993年7月致戴汝为、钱学敏等人的书信中,绘制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到1996年7月又添加了“建筑哲学”,成为11大部门。见图1。
从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一,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看作一个整体,具体分成11个门类,而每一个门类的“科学”又可以分为由低到高的“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等不同的层次。第二,从人类丰富的感性实践上升到具体科学、再进而上升到作为“桥梁”的11个门类“部门哲学”,在最高层次都归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钱学森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就主要体现在这些“部门哲学”当中。第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动态发展的。从前科学逐渐发展到科学技术体系,再上升到所对应的部门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第四,每一个现代科学技术部门都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而不是一门门孤立的分隔的学问。第五,大成智慧教育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结构为其最核心的概念。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次与概括。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因为“近一百多年来,人类知识的发展绝大部分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注意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中吸取营养”,[1]必须综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内容。
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非常鲜明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所有门类的科学技术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另一方面,所有门类的科学技术都通过部门哲学这座“桥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这体现了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抽象、要素与系统的内在统一。

图1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将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当作科学,而将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看成是技术,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这是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重大判断。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钱学森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3]很显然,这一观点不同于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并列的传统观念。在钱学森看来,唯物史观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概括,是以社会系统的运动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是一种部门哲学,它只是社会科学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不能将其放在与辩证唯物主义同等重要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重大判断。
那么钱学森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什么呢?钱学森早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及,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过程中,要把实际和理论灵活地结合起来,而“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4]钱学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等“时髦”的提法,也不屑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坚决反对机械唯物论与唯心主义,也反对二元论。他认为:“机械唯物论及二元论都是哲学名词,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唯物论不承认意识和精神的存在,所以是错误的。二元论承认物质与精神并存,二者有相互作用,但又不知道意识来源于物质的高层次活动,所以精神的本源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不得不求助于上帝!所以二元论也是错误的。当然还有一个唯心主义,当然是错误的了。”[5]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如钱学森所认为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传统观念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呢?很显然,两种不同的讲法,实质上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逻辑形态如何把握的重大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所创立的哲学叫做“现代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而最早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是狄慈根,其次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中都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如何构建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初步构想。
最早以“辩证唯物主义”命名的文章和著作都是前苏联哲学家德波林所撰写的。之后,在前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概念风行一时,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出了多部《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和教科书,并逐渐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架构:物质本体论、能动反映论之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板块”框架通过其中文译本直接影响了30年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如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都基本采用了这个框架。而1938年前苏联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则进一步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板块架构。该教程共12章,其中第四章第二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开篇即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世界观。由于斯大林的政治地位,这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影响巨大。在中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探讨人的主体性、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反思并试图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氛围中,才逐步摆脱了前苏联哲学体系的教条主义束缚。
我们当然不能全盘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但它确实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黄枬森曾在《哲学的科学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研究》中对这一体系的科学性做出如是评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科学体系,但不够完整和严密。”[6]他进而指出,如果是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突出地位,而将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大体上是可以的,但并不缜密。揆诸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程,其早期哲学思想就是围绕历史哲学展开的,表现为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恩格斯也把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视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而问题是能否简单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很显然,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是在理解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质之后,才形成他的现代唯物主义的。没有在历史观领域唯物主义思想的突破,不可能形成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总的统一性概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就产生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前提与基础,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机械运用。
在此背景下,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而非传统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清晰地勾勒出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到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第二,厘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及其逻辑关系。在钱学森的哲学视野中,辩证唯物主义内涵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概括,是11大部门哲学之一,而辩证唯物主义是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等部门哲学的最高概括。第三,对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围绕着人的主体性问题、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对原苏联哲学体系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固化的反思,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设置与建构提出了多种意见,影响最大的有“实践唯物主义”等。钱学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反对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等最终导向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的。这当然也体现出他作为通晓现代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伟大科学家一贯的唯物论基本观点与坚定立场。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第四次伟大尝试”
钱学森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科学真理。同时,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继承坚持又要创新发展。他在1993年10月2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体会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应该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国外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可取之处,再加我们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发展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7]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方面,钱学森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目标和建议。他受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的博士论文《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的启发,提出要进行“第四次伟大尝试”,并向张岱年等提出从中国前代哲学中提取精华用来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题。在1992年致黄枬森的书信中,再一次提出进行“第四次伟大尝试”的宏伟目标:“以下再报告我现在的一个想法:王东同志的书中说,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系统化做第一次伟大尝试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做第二次尝试的是狄慈根;做第三次伟大尝试的是列宁。所以我告诉王东同志,现在该是我们中国人搞第四次伟大尝试了,而且我们要力求成功。我们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在50年前就开始了。”[8]“第四次伟大尝试”,其“实质上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9]这可谓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个重要判断。
据王东的考证,写出《辩证法》书稿是马克思长期一贯的哲学夙愿,是他未能完成的最宏大的理论抱负之一。马克思的这种学术动机和愿望见之于他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也见之于1868年5月9日《资本论》刚刚出版后致狄慈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写到:“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10]
恩格斯深知马克思的哲学夙愿,“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11]为此,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致力于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系统化的工作,写出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从整体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逻辑体系的代表性著作。这相当于是为完成马克思“哲学夙愿”而做出的第一次尝试。当然,从理论形态的完整性、纯粹性、哲学体系的科学性等维度来审视,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实现马克思“写出《辩证法》”的宏大计划,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毕竟是第一次有益的尝试。
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是除了恩格斯之外,最了解马克思的哲学夙愿并自觉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1868年5月马克思给他的信中,就得知了马克思有完成《资本论》后就写《辩证法》的打算,并深受鼓舞。之后,狄慈根在19世纪80年代所写的几部哲学著作就是围绕着要实现马克思的哲学夙愿这个主题展开的。这可谓狄慈根独立地做出的实现马克思哲学夙愿的重要尝试。同恩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相比,狄慈根限于自身学识及其理论水平,其理论探索没有能够达到理想的高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来看,对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体系探索具有重大影响。
王东认为,列宁《哲学笔记》是为实现马克思哲学遗愿所作的第三次伟大尝试,极大地推进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系统化。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即《哲学笔记》中关于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总体设想,其哲学价值在于启迪我们从哲学高度总结现代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和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新成果、新趋势,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系统化,以期为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南。
钱学森所提倡的“第四次伟大尝试”是一个宏伟的哲学工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继承与创新。如果说第一、第二次尝试主要是在西欧完成的,第三次尝试是由列宁做出的,那么第四次伟大尝试应该由中国人来完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实践产生哲学,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哲学。我们能否在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哲学笔记》、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基础上,写出具有时代内涵的“辩证法”,是历史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考验。
总而言之,作为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在其著作和书信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当代人类哲学思想的制高点,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重要论断,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座巍峨大厦奠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石之上,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直接相连的畅通渠道,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列宁晚年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中所提出的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联盟的“哲学遗嘱”。“我的体会是我们要根据人类在马克思之后的一个世纪来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12]这可视作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总结论。
注释:
[1]《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24页。
[2]奚启新:《钱学森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1页。
[3]《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262页。
[4]奚启新:《钱学森传》,第496页。
[5]《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244-245页。
[6]黄枬森:《哲学的科学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7]《钱学森书信选》下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834-835页。
[8]《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636页。
[9]《钱学森书信选》上卷,第5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页。
[12]《钱学森书信选》下卷,第1097页。
责任编辑 顾伟伟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6)04-0067-05
作者简介:杨海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厦门市,361005;李志峰,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南宁市,5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