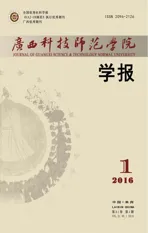刑法学本科教材量化研究
2016-07-24高永明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扬州225127
高永明(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扬州 225127)
刑法学本科教材量化研究
高永明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扬州225127)
摘要:目前在中国刑法学本科教材种类繁多,蔚为大观。但教材质量不可一概而论。文章从出版地、作者、引用、选用等方面对刑法学教材出版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为合理选择刑法学教材,使用刑法学教材提供背景性资料。
关键词:刑法学本科教材;量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学教材呈现出繁荣之势——各出版社、各法学院校乃至各法学教师出于各自的目的都竞相出版法学教材[1]。从刑法学教材来看,也是种类繁多,遍地开花。不可否认,这给了教师或者学生较大的选择余地。但正如法学教材繁荣背后存在的巨大隐忧[2],刑法学教材的现状如何,值得探讨。对于法学本科生而言,初次接触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对其影响非常重要。法学本科教材内容的主导方向影响着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法学本科教材质量的优劣决定着培养人才的质量的高低[3]76。因而刑法学教材的质量及选用标准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对刑法学教材出版使用情况作一分析,呈现其目前的现状,为合理选择刑法学教材,使用刑法学教材提供背景性资料。
从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刑法学教材不胜繁多,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以最新的中国出版集团主管、新华书店总店组编的2015年9月出版、专门适用于2016年春季学期的《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中的刑法学教材(该书收录了全国200多家出版社的教材信息,内容全面权威)作为研究对象①在统计标准上,总论和各论由同一人主编的,按一本教材算。专为研究生适用的教材不计入,也不包括外国刑法学教材和考研辅导用书。不包括专题性研究,如刘宪权《刑法学专题理论研究》,也不包括研究性专著,如曲伶俐《刑法适用与社会稳定》。虽然这些仍然属于《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征订范围内的书。同时编写教材时职称不是教授的也不计入。从统计结果看,共有50部刑法学教材。
一、出版地现状
上述50部刑法学教材的出版社情况按地理分布情况如表1:

表1 刑法学教材出版地分布情况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格致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上海重庆济南郑州厦门上海武汉1 1 1 1 3 1 2
上表共有15家出版社,北京的出版社共有8家,占总数的近54%。出版教材共50本,北京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共40本,数量占全部教材的80%,也处于绝对多数的位置。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因为北京汇集了国内众多名牌高校,基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学校建立了各自的出版社,因而取决于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这些出版社利用所依托高校的较强教学科研力量组织编写刑法学教材就是自然的了。而这些数量较多的出版社自然也使得刑法学教材出版的数量占绝对优势。
从形式上看,我国各家出版社均可以自由决定出版刑法学教材,教材出版的市场竞争化正在形成。但是,上表中无法体现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出版社出版刑法学教材的差异并不完全是市场自由竞争导致的。从上述北京地区出版的教材大多冠以一定的名号,比如“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以及从“六五”到目前的“十二五”规划教材等。这些教材都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另外还有一大批省级教育部门组织的“省级精品教材”[4]。刑法学教材表面上看起来种类繁多,实际上出版仍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并不是太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刑法学教材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组织编写的教材大多集中了较强的力量,主要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较强科研能力的专家组成编写团队,因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这些教材的质量。反之,粗制滥造的刑法学教材最终会被市场淘汰。
政府教育部门主导组织专家编写教材看来在我国还是常态的,基于教育部门在项目、经费等各方面的决定权,因而召集组织专家编写教材较为容易。教材编写者也可以借教材名利双收。问题是,刑法学教材需要充分的市场竞争吗?如果需要充分的市场竞争则就不需要教育部门组织编写而交由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如果需要市场竞争由教材质量决定教材命运,教育部门组织编写的刑法教材能保证教材质量的话,就不需要市场竞争。该问题有两个方面需要解决。
一是刑法学教材质量问题。刑法学教材质量是由教材内容决定的。关于教材内容在国内一般的观点是有关的概念、范畴、原理、体系等基本知识应当尽可能统一,而不能各话各说[5]。甚至国内有人认为教材不能成为宣称、推行个人观点的场所[6]348。如果这样的话,教材内容就不会有多大差别,进而质量差异就不会太明显。区别可能仅在于教材体系、语言风格等技术性问题上。事实上,所谓许多受到赞誉的刑法学教材的观点和其他一般观点并没有什么差别。因而这里的刑法学教材“质量”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不是以内容来确定的,而仅以形式上的编纂体例等技术性问题确定的。因此,要真正提高刑法学教材质量必须改变内容、观点大一统的局面,需要鲜明的论证有力的新鲜理论出现于刑法学教材中。正如葛洪义先生所言,否定这点实际上是维护了个别人的学术霸权及对学术问题的垄断,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公然鼓励抄袭和剽窃[6]38。但现实是具有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的刑法学教材并不多。因此,刑法学教材质量总体来看,基本是具有抄袭、重复性质的东西,质量难言上乘。这种缺乏创新性的教材对人才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3]78。
政府主导编写的刑法学教材还出于一定的教化目的、政治目的等实际上很难突破固有的范式牢笼。市场主导下的教材出版商为了商业利益生存,必然想方设法提高教材质量,而不是短视的、政治性的出版教材。德国、美国的教材市场化程度相当高,出版商而不是政府成为高校教材建设的主导者与推动者[7],因此涌现出历经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经典教材。
二是政府教育部门的教材编写理念问题。是不是必须由教育部门主导才能编写出质量上乘的教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我国的出版市场已经放开,在教材编写出版问题上并不需要国家把握专业知识方向,国家提供宏观层面的制度保障即可。国外教材出版的市场主导化未来必然成为我国教材出版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或许会担心,教材出版的市场化会导致无序竞争。可即便是无序竞争,也必然会通过一定的周期完成市场的优胜劣汰,最终胜出的还是高质量教材。
二、作者现状
在上述50本教材中,其中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法总论》没有在《汇编》中注明作者。其余49本教材共有作者37位,其中有10人出版教材2部以上,最多的一人出版了5部教材。具有鲜明特点的是,一位出版5部教材的编者在同一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2部教材,另外3部教材在不同的出版社同时出版。除该编者外,另外9位分别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了2部以上的教材。从同时出版的教材的名称看,名称大同小异,内容基本一样。换言之,同一作者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并不是新版与旧版的关系。同一作者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名称也基本一样,如《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在另一家出版社换成了《刑法》(总论、各论)。查阅、对比分析一位编者出版的不同教材,内容基本雷同,属于典型的重复建设。
在50部刑法教材中,有4部是个人独著,其余全部是主编制。从我国第一批刑法学教材以来,都是主编制,主编一般是学界权威,该类教材的观点四平八稳,一般采学界“通说”。这种状况持续了近30年,近几年来出现了专著型教材。专著型刑法教材的出版并不是偶然的。
近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变,即作为刑法总论核心内容的犯罪论出现了由传统四要件向大陆法系三阶层转变的趋势,并产生较大争议,由此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和两套不同的学术话语。在刑法学教材上,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四要件格局,引进并改良了三阶层理论,最新的司法考试用书也是这种改进的一种。同时随着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的介绍乃至深入研究,大量的学术论文开始以大陆法系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刊和话语载出来,不对其进行了解很可能根本看不懂这类文章,甚至单纯以传统知识体系撰写的论文也很难发表出来。因此,传统四要件体系的刑法学教材和现在的学术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立。因此教材的知识结构、语言和学术知识结构、语言成为两套不同体系,教材和论文根本就是两回事,教材记的再熟,依然无法看懂学术专著和论文[8]。在这种尴尬现实下,两种知识的通约成为必要,学术性的新话语体系和知识转化为教材内容,使教材出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这类教材以张明楷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为代表,颇受好评。在通说的编著教材和个性的专著教材之间,由于前者“主编不编”、内容陈旧、观点重复、论证不强等问题而备受诟病,后者或许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从教材作者的职称看,以上50部教材的作者或者主编全部是教授,而且基本囊括了国内刑法学方面的权威教授。许多作者著作丰硕,学术影响大。其中也有一些科研能力较强的青年才俊,这些作者或者主编前期也具有较多的科研成果,在某一研究领域小有影响。这些作者或者主编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理论上能够保证教材的质量。本文没有将《汇编》中的另外8部教材作为专门的统计对象,虽然这些教材的主编有的也是教授职称,但从中国知网上检索他们的论文发现,有的作者甚至只有2篇论文就出版了教材,而这8部教材无一例外均属于这种情况。这点可能印证了教材是基于职称评定、学科评估等原因出版的结论[9]。这种教材基本上是属于观点抄袭性质的重复出版,市场占有率低,甚至出版后从没有被任何法学院校采用过。
三、引用现状
正如苏力所言,引证对论文的质量至关重要:“引证本身就表明作者在写作时或修改时考虑到了他/她所引资料中所蕴涵的某些重要信息;无论是作为支持材料还是反驳对象,他/她都必须更多思考这些相关资料、综合更多前人智慧。因此,就同一作者而言、其引证资料多的论文一定要比其引证少的论文花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一些、因此论文会更成熟一些、也会更有分量一些,更少可能自我重复,更可能对一个问题有相对透彻的分析阐释,论文可能比较全面和完整。”[10]同理,如果一篇论文被引率较高,也说明该论文的质量相对而言能够得到保证。一种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多寡,是其学术水平或期刊价值极好的测度[11]。对于学术期刊、论者而言这几乎可以认为是真理,但是对于刑法学教材能否以引用率来确定其质量呢?换言之,能否以某刑法学教材被引率较高来决定选用教材呢?
上述问题与刑法学的目的定位有关。即刑法学我国有学者认为,编写者在教材编写中,必须将读者置于首位,为学生的“利益”定位教材的内容[12]。刑法学本科教材的使用对象是本科生,其意义在于能够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这一结论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细化而言,本科教材为了学生的“利益”,究竟是为了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还是用以培养其科研能力抑或二者兼具呢?本科教材首先应向学生传授基本法律知识,让他们在学习法律的初始阶段对法律有个系统学习,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认知体系。目前对学生的培养同时注重他们的实践能力,力求“学则能用”。毋庸讳言,在此前提下,本科教材能够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则可谓尽善尽美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本科阶段的学习能为未来进行科研工作打下基础,但不能期待本科生在本科阶段就能出很多科研成果,因而对于本科生而言实际上难言真正的科研产出。因此对于使用教材的学生而言,本教材的引用率实际上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也就不能以教材的被引率来判断教材的质量。况且有时引证本身会存在各种问题,因此用不过引证分析作为评价指标必须慎之又慎[13]。如果本教材的被引率较高,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真正适用于本科生并提升他们的法律素养,或许只能说明本教材对搞研究的人意义较大,在培养本科生基本能力方面无法显示出其优势。
四、选用现状
课程建设是高校教学内容的核心,其中的教材建设直接关系到课程设计、课程组织与实施、教学目标的实现以及教学质量和知识的传授。对于一般具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或刑法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的法学院校而言,基于现有教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学术影响力等方面的限制,编写教材的现实意义并不大。在教材编写这种直接建设不可行的情况下,对教材的选择就尤为重要。
本文以所在省份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点的高校为样本进行统计,发现这些学校对刑法教材的使用极不统一,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期会使用不同的教材,而教材的选择基本是由授课老师自己确定。这种现状在全国范围内也基本如此。归纳来看,教材选用的标准或动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教材的影响选择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各种国家级规划教材。这种情况居于多数,这也使得地方性教材处于逐渐边缘化地位。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用,如选用自己尊崇的某位知名学者编写的教材。三是选用自己或自己的导师编写的教材,以提高教材的销售额,或者让其他高校熟悉的老师帮助推销自己或自己导师编写的教材。这种教材多是地方性的。总体来看,在高校刑法学教材使用上已经基本不存在强制性使用某种教材的情况,许多法学院校都是由任课教师自己选用教材。但教师个人选用教材基于上述几种情况使得教材选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甚至只要是教师主编的教材不论学生的情况如何而一律选用。如有学者出了一本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自考教材,在给所在学校的该专业研究生讲课时,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教材,讲的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该教师也显然知道自考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重大区别,并不好采用同一本教材。教材的选用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基本没有问题。问题是要认真看待教材的作用,实际上在目前的教学改革背景下已经不必纠结于教材如何选用的问题。
研究型教学已经成为近年来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其特色在于教师在授课时应重点讲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告诉学生所学知识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教师不应拘泥于教材,教材中的知识只能作为讲授方法、思路的一部分素材[14]。学生在上课前要查阅许多文献,挖掘出可能用以解决问题的信息。因而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下,教材的作用被弱化,特别是教师授课不再依赖于教材,对学生的评价也不再依赖于学期结束时依教材对学生的考试,教材仅仅成为参考资料的一种而已。在传统教学方式中,一部教材可能对学生影响至深,但研究型教学的展开使得教材的选择和使用意义已经大大弱化,有些教师已经不再给学生征订教材,而是上课前布置学生去图书馆或者知网等网络资源上查阅相关文献。或许在未来, 教材不会再成为大学中人手一册的“宝书”。
五、结语
我国刑法学表面的出版繁荣无法掩盖教材质量总体欠佳的事实,因一本教材而名扬天下者几乎不可能出现,而作为一生学术历程总结、凝结一生研究精华的教材在目前似乎更不可能出现。由于观念和理论的差异,即便由著名学者组织的数人撰写的教材也并一定能够保证教材的质量。数人大杂烩式合成撰写教材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在教材应凝结研究精华的共识下,必须认真对待刑法学教材的撰写而不是编写,刑法学教材应该是著作而不是编物。这种教材的引用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教材的质量,因而此时引用率才可以作为选用教材的标准。
[参考文献]
[1]邓肄.探寻法学教材的迷失之处[N].法制日报,2012-08-22(12).
[2]杨军.法学教材编写要重视智慧与能力[N].光明日报,2014-05-13(13).
[3]范云茹.我国法学专业本科教材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2).
[4]王文华.刑法学教科书60年回顾与反思[J].政法论坛,2010(2):126.
[5]王利明.关于中国法学教材建设的几点意见[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18.
[6]葛洪义.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M].青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7]高等教育教材考察团.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促进我国教材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3(2):30.
[8]徐爽.开放的互动:法学教材和学术成果之间[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2):124.
[9]汤强.对高等法学教材出版的认识与思考[J].大学出版,2005(2):47.
[10]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4-85.
[11]崔旺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01(2):30.
[12]胡玉鸿.试论法学教材的编写目的[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5.
[13]张彦.用引证分析作为评价指标须慎之又慎[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6(4):21.
[14]司凤山.研究型教学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2(11):17.
(责任编辑:雷凯)
The Quantization Research of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terial of Criminal Law Textbook
GAO Yongming
(Law School,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225127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riminal law textbook,but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qua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lace of publication and usage from the aspects of publishing site,the author,the quote and the choice,which provides background materials for rational selection and the use of criminal law textbook.
Key words: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terial of criminal law textbook;quantization;research
中图分类号:D9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1-0095-05
[收稿日期]2016-01-10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江苏省法学本科重点专业建设资金的资助。
[作者简介]高永明(1976—),男,江苏邳州人,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