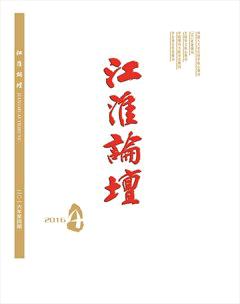桓范《世要论》与“韩学”研究*
2016-07-04宋洪兵
宋洪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872)
桓范《世要论》与“韩学”研究*
宋洪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桓范《世要论》之法家特质,主要体现为“为君难”之君道观、“臣不易”之臣道观以及围绕刑德关系问题呈现的基本治国之道。桓范认为,“君道”的本质在于施惠于万民,君主治国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主张理想之“臣道”应该忠顺体国,以道事君,现实政治领域“臣不易”体现在人臣坚守清白时往往遭遇谗毁与迫害;桓范主张刑德并重,强调慎刑的同时也主张必罚,主张军事实力源自良好内政。桓范虽名列“法家”,但并非先秦时期纯粹意义上的“法家”,其思想中蕴含了不少儒家的政治理念。桓范及汉末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韩学”特质,这既是汉末以来乱世格局的思想回应,亦为魏晋政治实践之理论先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实践均产生了一定思想影响。
关键词:桓范;世要论;法家;韩学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法家及韩非子之学,因应春秋战国之纷争局面,本是对治“大争之世”的良方。汉魏之际,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群雄并起,政局混乱,乃典型的乱世。当此之时,无论内政治理还是政权之间的实力竞争,均彰显了法家思想之重要性。自汉季以至蜀魏,崇尚事功实学的法家确实大行其道。对此,章太炎有非常精到的评论:“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萛之述《政论》也,皆辩章功实,而深疾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自汉季以至蜀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法治为章。”[1]228-229章太炎提及之“五蠹”及“宽缓之政”,均出自《韩非子·五蠹》。在章太炎看来,“韩学”在王符、仲长统及崔萛等人那里有所体现。王符、仲长统、崔萛号称“汉末三杰”,其思想具有鲜明法家特质,已为学界所关注。吕思勉曾详细考察魏晋法术之学,得出如下结论:“汉治自永初而后,纵驰极矣。外戚专权,宦竖窃柄,官方不肃,处士横议,盖自朝宁宫禁学校之中,无一以国事为念者。一时通达治体之士,若王符、仲长统、崔萛等,咸欲以综核名实之治救之,当时莫能行,然三国开创之君臣,实皆用此以致治。”[2]861他又说:“三国承汉季纵恣之后,督责之术,乃时势所需,非魏武、孔明等一二人故为严峻也。故其时薄有才略之君,皆能留意于此。”[2]866然于同时代之桓范及其思想特质,却很少进入学界考察的视野。本文拟在“韩学”脉络中梳理桓范《世要论》的主要观念,以此见出汉魏之际“韩学”之学术影响。
桓范,字符则,沛国人,生于东汉末年,具体年代未知。《三国志》无传,《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桓范“世为冠族”,表明他出生于豪门世族。桓范为官清廉,“号为晓事”,时人尊为“智囊”,他曾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现存《世要论》所阐发的,几乎全为时政论的治国观点。
《隋书·经籍志》“法家类”记载:“《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书·艺文志》亦有相同记载,唯《旧唐书·经籍志》作“《代要论》十卷”。后世各书征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实则皆为《世要论》一书。《群书治要》收录《政要论》十四篇,是目前了解该书思想观点的主要文献文集。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三十七辑录了桓范的奏章、《世要论》及散见典籍的言论。现就桓范《世要论》中的法家特征略作探讨。
一、《世要论》之“君道观”
桓范与刘訥生活在同一时代,稍晚,二人曾同朝为官。刘訥曾生发治国不易、“为君难”的感慨(《政论·疑贤》)。桓范也深有体会,进一步阐述了“为君难”,借此表达了他的“君道观”。
《世要论·为君难》认为,君之地位犹如天。天覆万物,协和施化,无有缺漏。君临天下,如何能够像天一样普惠万民而不遗漏一人,“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当为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所谓“为君难”,即难在如何将君主普惠万民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加以落实。桓范既点出了“君道”的本质在于施惠万民,同时也道出了君主治国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桓范心目中理想的君主不仅是心忧天下、体恤万民的仁者,而且还是思虑周全、洞察幽隐的智者。“是以在上者体人君之大德,怀恤下之小心,阐化立教,必以其道,发言则通四海,行政则动万物,虑之于心,思之于内,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庙堂之上,而化应于千里之外,虽?纩塞耳,隐屏而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动作周旋,无事不虑。”仁智之君在位,一方面体恤民生之艰难而善待百姓,“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这是典型的仁者形象;另一方面又时刻怀有忧患意识,赏功罚罪,任贤使能,深恐赏罚失当,官吏不贤,所谓“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赏毫牦之善,必有所劝,罚纤芥之恶,必有所沮”,这是典型的智者形象。君主仁心待民,且又智慧超群,就能在现实政治领域惩恶扬善、移风易俗,进而拯救衰世,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君主亦因此而受万民的敬畏与爱戴:“使化若春气,泽如时雨,消凋污之人,移薄伪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桓范意识到,即便仁智之君在位,也未必能够实现上述理想,还必须群臣辅佐。然而,群臣的素质恰恰成为横亘在君与民之间难以忽视的一个障碍。他说:
且佐治之臣,历世难遇,庸人众而贤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干,伊吕之辅,犹造父不能皆得骐骥之乘,追风之匹也。御醻啮必烦辔衔,统庸臣必劳智虑,是以人君其所以济辅群下,均养小大,审核真伪,考察变态,在于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纤微之间,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尽于此哉!(《世要论·为君难》)
“庸人众而贤才寡”的现实,使君主很难获得伊尹、吕望这样的佐治良臣,必然依赖一帮“庸臣”,这就需要审核真伪,考察功过,甚至需要具备在幽冥细微的环境下甄别是非的能力。这既对君主治国的智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也呈现出治国过程中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难度极大。桓范提醒君主治国需要关注“御臣之道”,也即他所说的“九虑七恕”。
所谓“九虑”,就是要考虑人臣在现实政治领域应当防范的九种行为,分别是“虑之以诈”、“虑之以虚”、“虑之以嫉”、“虑之以谗”、“虑之以奸”、“虑之以欺”、“虑之以伪”、“虑之以祸”、“虑之以佞”。“九虑”的政治功能在于“防恶。”
所谓“七恕”,即是宽容对待那些动机高尚言语冒犯的正直之臣,要看到他们更为本质的一面,不必对他们太过苛刻:“恕之以直”、“恕之以质”、“恕之以忠”、“恕之以公”、“恕之以贞”、“恕之以难”、“恕之以劲”。治国之所以需要“七恕”,根本原因在于劝善进能:“所以进善接下之理也。”
因此,桓范“为君难”的核心其实在于御臣之难,其思想中的韩非子色彩亦由此得以充分凸显。按理,最早生发“为君难”感慨的人是孔子。《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回答鲁定公 “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问题时就有“为君难,为臣不易”的观点,说明为君应该注重自己的言论,如果以错误的言论治国,就会“一言以丧邦”。桓范在阐述“为君难”的问题时,开篇就以孔子的话为依据:“仲尼称‘为君难’。”表面上看,桓范思想似乎是在沿着孔子思路展开,应该以尊奉儒家思想为理论依归。但是,这并非事实。
或曰:仲尼称“为君难”。夫人君者,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则受其功,治成则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穑,弃也。理讼,皋陶也。尧无事焉,而由之圣治,何为君难耶?
在此,桓范不动声色地将孔子、孟子以及荀子主张的“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政治理念完全推翻。他只是形式上借鉴孔子“为君难”的说法,而非思想内涵的自觉继承。其“为君难”在于御臣之难的观念实质继承了韩非子“索人不劳,使人不佚”的政治思路,“九虑七恕”之说更是具体的御臣之道,而不是儒家式任用贤能便可垂拱无为的政治规划。“庸人众而贤才寡”的说法,佐证了桓范与韩非子之间在思想层面的亲和力。韩非子主张“众人多而圣人寡”(《韩非子·解老》)、“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韩非子·难势》)、“贵仁者寡,能义者难”(《韩非子·五蠹》)。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才有加强对“庸臣”考核和监督的“九虑”。这些都体现了桓范思想中韩非子的影响。
关于御臣之道,韩非子强调君主应该独揽生杀赏罚大权,不可以轻易让人臣行使,《韩非子·主道》提出人主有“五壅”:“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为了有效避免奸臣迎合君主个人好恶而获得宠信进而窃取权柄,韩非子主张君主应该“去好去恶”,同时运用御臣之术:“众端参观。”(《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谓“众端参观”,就是广听博闻,尽可能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对照比较,从而看清事情真相,此即韩非子之“术”。他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
再看《世要论·决雍》对同样问题的阐述。桓范认为人君为人臣所欺骗蒙蔽,乃无国不有的现象,因为“利在于壅也”,“壅则擅宠于身,威权独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祷祝面求也”,指出人臣欺骗君主的手段十分巧妙,往往发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及至人君悔悟,政已败亡。如何防止人臣蒙蔽君主?桓范给出的方法也是韩非子的“众端参观”之“术”。他说:“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若此,则所闻见者广,所闻见者广,则虽欲求壅,弗得也。”桓范顺着韩非子的思路,也提出了“去好去恶”之说:“人主之好恶,不可见于外也。所好恶见于外,则臣妾乘其所好恶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无见其意,将为下饵。……古今亡国多矣。皆由壅蔽于帷幄之内,沉溺于谄谀之言也。”(《世要论·决雍》)人君不能表现个人好恶,必须节欲。“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世要论·节欲》)这与《韩非子·亡征》之“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以及“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等反对君主纵欲的说法,也是一脉相承。
显而易见,桓范对于《韩非子》可谓烂熟于胸。《世要论·尊嫡》谓:
凡光祖祢,安宗庙,传国土,利民人者,在于立嗣继世,继世之道,莫重于尊嫡别庶也。故圣人之制礼贵嫡,异其服数,殊其宠秩,所以一群下之望,塞变争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虑,历观前代后妻贱而侄媵贵,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争乱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带之难,齐有无知之祸,晋有庄伯之患,卫有州吁之篡。故传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桓范身处曹魏政权面临司马氏严重威胁之际,关注“王权焦虑”亦在情理之中。尊嫡的观念,韩非子有过非常深入的讨论,目的在于解决春秋以来的“王权焦虑”问题。韩非子认为,解决“王权焦虑”的重心之一,就是“急置太子”(《韩非子·扬权》),借此消除觊觎王位的非分之想。晚置太子会导致王室手足相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韩非子·难三》)韩非子反复阐述太子与庶子之间的尊卑关系不可破坏,如果破坏,国将衰亡:“轻其适正,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又说:“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其中,“太子卑而庶子尊”一句为桓范原封不动地袭用。
二、《世要论》之“臣道观”
桓范也关注为臣之道。根据孔子观点,桓范亦认为“为臣不易”。按照通常的说法,为人臣不难,只要做到恪尽职守之“忠顺”就可以。然而,桓范发现,现实政治领域,并非那么简单。之所以为臣不易,是因为必须在君臣关系之中去衡量难易。君臣之间,最好状态当然是“以贤事圣,以圣事贤”,但是桓范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清醒意识到这种贤圣相遭的可能性极低:“贤圣相遭既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犹未能得,斯诚不易也。”更多情况则是“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暗为难”。加上君臣之间没有父子关系那样的亲情,即便父子亲情尚且有所抵牾,没有亲情纽带的君臣关系难以处理,亦不言而喻了。(《世要论·臣不易》)
桓范认为,理想的为臣之道,应该公忠体国、肝脑涂地,始终秉持正确的做事原则,不因事情难易或个人安危而有所动摇,更不会因一己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去贪图荣华富贵。他说:
且夫事君者,竭忠义之道,尽忠义之节,服劳辱之事,当危之难,肝脑涂地,膏液润草而不辞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为一代之圣明,己为一世之良辅,辅千乘则念过管晏,佐天下则思丑稷禹,岂为七尺之躯,宠一官之贵,贪充家之禄,荣华嚣之观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于成功立事,便国利民,故不为难易变节,安危革行也。……动依典礼,事念忠笃,乃当匡上之行,谏主之非,献可济否,匪躬之故,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也(《世要论·臣不易》)
“以道事君”,是桓范为臣之道的根本宗旨。桓范甚至主张为人臣应该“使怨咎从己身,而众善自君发”。桓范主张人臣应该通过谏争的形式纳君于道。《世要论·谏争》说:“夫谏争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正言直谏,难免得罪君主而生怨,为人情所难免:“然则稭人之耳,逆人之意,变人之情,抑人之欲,不尔,不为谏也。虽有父子兄弟,犹用生怨隟焉。况臣于君,有天壤之殊,无亲戚之属,以至贱干至贵,以至稀间至亲,何庸易耶?恶死亡而乐生存,耻困辱而乐荣宠,虽甚愚人,犹知之也。况士君子乎?”君主应该体谅直谏之臣的良苦用心,虚心纳谏,而不是心怀怨恨加以惩罚和报复。为臣之难,于此可见。
不惟如此,正直的大臣,往往还会遭遇“邪臣”和“幸臣”的谄毁和迫害,人君不察,贞臣轻则斥逐,重则丧命,所以桓范反复申说“为臣不易”:
然或为邪臣所谮,幸臣所乱,听一疑而不见信,事似然而不可释,忠诡计而为非,善事变而为恶,罪结于天,无所祷请,激直言而无所诉,深者实时伏剑赐死,浅者以渐斥逐放弃,盖比干、龙逢所以见害于飞廉、恶来,孔子、周公所以见毁于管蔡、季孙也。斯则大臣所以不易也(《世要论·臣不易》)。
桓范的上述观点,近承王符“贤难”之说,远绍韩非子“难言”之论,尤其论述君臣未有父子之亲更难以相处的思路,与韩非子的思想可谓叠韵双声,一唱一和。《韩非子·奸劫弑臣》说:“父之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世要论·臣不易》则谓:“且父子以恩亲,君臣以义固,恩有所为亏,况义能无所为缺哉?苟有亏缺,亦何容易。”桓范并不直引韩非子之语,而是用自己的话转述。
桓范认为,为大臣不易,为小臣更难。小臣地位卑贱,他们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思不出位,忠信诚实:“为小臣者,得任则治其职,受事(则)修其业,思不出其位,虑不过其责,竭力致诚,忠信而已。”然而,他们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常常面临险境,稍不注意就会身死为戮,落得悲剧结局:
然以至轻至微,至疏至贱,干万乘之主,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执政之臣,暴其所短,说合则裁,自若不当,则离祸害。或计不欲人知,事不从人豫,而己策谋适合,陈偶同上者,或显戮其身以神其计,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夺其策,盖关思见杀于郑,韩非受诛于秦,庞涓刖孙膑之足,魏齐折应侯之胁,斯又孤宦小臣所以为难也。
在此,桓范不仅以深切的同情心直接将韩非子与关其思、孙膑、应侯等历史悲剧人物加以正面称颂,而且在观念层面套用了《韩非子·说难》的说法。韩非子说:“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关其思的例子就是韩非子在《说难》篇特意提及的一个悲剧人物。韩非子这段话的意思,正是桓范“或计不欲人知,事不从人豫,而己策谋适合,陈偶同上者,或显戮其身以神其计,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夺其策”说法的思想源头。
忠直小臣不仅面临昏庸君主的惩罚,而且还会因不善谄媚而遭受君主身边的近臣及邪臣的嫉妒和排斥,在是非混淆的政治环境中,真正“忠上爱主”之臣往往难逃被陷害的悲剧命运,近臣及邪臣利用他们在君主面前的亲近与宠信优势,谗害忠良:“奉公侠私之吏求害之以见直,怀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世要论·臣不易》)
外臣也不易。外臣主要指手握军权镇守边疆的大臣,他们尽心竭力,忧公无私,兴利除害,安定一方。即使某些地方有违朝廷政策,君主亦应该本着“七恕”原则加以体谅与宽容。然而,外臣不易的根源同样在于君主左右及贵臣,“或逆而毁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谮之,使不得其所。吴起见毁于魏,李牧见杀于赵,乐毅见谗于燕,章邯畏诛于秦,斯又外臣所以为危也”(《世要论·臣不易》)。
在桓范看来,欲解决“臣不易”的问题,必须鼓励忠直之臣坚守原则清白做人,君主必须做到“九虑七恕”,防恶进善,打击奸臣邪臣,任用贤能正直之臣。如此,君主治国需要“辨能”。《世要论·辨能》曰:
夫商鞅、申、韩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则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有可取焉。宁成、郅都辈,放商、韩之治,专以残暴为能,然其抑强抚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趣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辨,但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魾,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而俗犹共言其能执政者,选用不废者,何也?为贵势之所持,人间之士所称,听声用名者众,察实审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
桓范将人臣分为四个等级:伊尹、周公及西汉邵信臣为第一等级。商鞅、申不害与韩非子等具有法家观念的人臣为第二等级。西汉酷吏宁成、郅都为第三等级。最差的就是没有实际才能,依靠权势及虚名获得官位却又以权谋私的人臣。桓范在此显然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对汉末以来官场的腐朽与无能极度不满。桓范对当时“爵以赂至,官以贿成”的官场可谓深恶痛疾。当时奸吏沆瀣一气,互相吹捧,死后还有很多“门生故吏”为其歌功颂德,桓范认为这是君主失去权柄所造成的恶果:“且夫赏生以爵禄,荣死以诔谥,是人主权柄,而汉世不禁,使私称与王命争流,臣子与君上俱用,善恶无章,得失无效,岂不误哉。”(《世要论·铭诔》)他依然强调由君主维护赏罚权柄,在铭诔问题上维护“王名”的权威,打击私称,肃清官场腐败。值得注意的是,桓范对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人物的能力亦颇有认可,这也清晰表明他的政治观念中蕴涵着法家因素;即便对于宁成、郅都等酷吏,亦认为他们有可取之处,而未完全否定。同时,他指出“专以残暴为能”的酷吏乃商鞅、韩非子之罪人,亦是深刻的思想洞见。
总之,桓范“臣道观”秉持“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强调“谏诤”之重要性,分析了“大臣”、“小臣”及“外臣”在非正常政治环境中的种种不易,意在彰显赏贤使能、忠信无私、公正清廉的“臣道观”。桓范在坚持儒家基本政治价值的前提下,借鉴了诸多韩非子的政治智慧。
三、《世要论》之治国方略
在治国方略层面,桓范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政治见解,包括刑德关系、军事主张以及基本的为政之道。桓范主张刑德并重,赏功罚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世要论·治本》(1))桓范将历史分为“五帝”、“三王”、“五霸”、“秦”四个阶段,这既是历史顺序,也是体现治国原则的价值顺序。“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此三者,治乱之本也。”刑德先后与主次之分,是判定先秦儒家与法家根本区别的标准之一。桓范明确反对秦朝的纯用刑罚之治,然在德刑主次与先后方面,他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他并未反对刑多德少的“五霸”之政,刑德相半的情况,他视为“三王”之政,实际已经大大提升了强制性的刑罚在治国过程中的地位。他主张刑德由君主“专持”,实则韩非子“二柄”之说的继承。
桓范重视刑罚的治国功能,提出了“详刑”的思想。“详刑”之说,首见于《尚书·吕刑》:“有邦有土,告尔祥刑。”祥,郑玄注:“审察之也。”《说文解字》注“详”为:“审议也。”因此,所谓“详刑”,实则审刑、议刑。桓范“详刑”思想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慎刑、恤刑。人死不能复生,生命宝贵,治国应该审慎对待刑罚:“夫刑辟之作,所从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详慎之者,以为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夫尧、舜之明,犹惟刑之恤也。是以后圣制法,设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讯,然犹复三判,佥曰可杀,然后杀之,罚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其二,执法公正无私,惩恶扬善。如果做到了慎刑、恤刑以及公正无私,刑罚的惩戒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受罚者亦心甘情愿:“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详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明刑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此之谓矣。”其中,“明刑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与韩非子及商鞅的“以刑去刑”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其三,刑罚必行,维护法令权威,消除侥幸心理。倘若不能“详刑而必行之”,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公信力丧失:“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桓范“必罚”的观念,亦源自韩非子。《韩非子·说林下》就强调“必”的重要性:“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韩非子·内储说上》也主张“必罚明威”。
桓范的《世要论》虽然被后世目录学文献列入“法家类”,但与崔萛、刘訥一样,桓范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法家。在天下一统时代,政治思想已经不可能像先秦百家争鸣时期那样互相对立,而是呈现融合状态。桓范在吸收和继承韩非子政治理念时,并未排斥儒家观念。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臣道观”将伊尹、周公等人视为高于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等人的层面,而且他的慎刑、恤刑观念,也同样具有儒家特色。《世要论·治本》强调“长民治国之本在身”,沿袭了先秦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思路,《世要论·政务》亦吸取孔子的“正身”理论,主张“为政之务,务在正身”。《世要论·兵要》一方面强调军事理论的根本在于内政,“夫兵之要,在于修政”,这与《韩非子·五蠹》有关军事与内政关系的阐述是高度一致的:“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另一方面,内政治理层面,桓范认同韩非子“明赏罚”执政理念的同时,也主张 “得民心”,“仁以爱之,义以理之”,崇尚所谓“王者之兵”。他说:“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此王者之兵也。”显然,这种以德为先、以威为辅、修行仁义的观念,具有典型的儒家特征。
总之,桓范《世要论》在“君道观”与“臣道观”方面都深受韩非子及先秦法家思想的影响,务实冷静地分析政治领域的复杂情势,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尤其他能深切同情韩非子,确实难能可贵。然而,总体而言,他的思想本质上具有儒法交融的特征,他既是一个拥护儒家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深具务实情怀的政治家。
四、结 语
桓范及汉末思想家如王符、仲长统、崔萛等,其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韩学”特质。这既是汉末以来乱世格局的思想回应,亦为魏晋政治实践之理论先声。可以说,魏晋时期,因“王权焦虑”而对韩非子之学的格外关注,或多或少与汉末具有法家情怀的思想家有关。桓范身为曹魏政权之大司农,其对当时政治实践应有一定影响力。
曹丕代汉称帝之后,为了加强皇权,避免后宫、外戚以及宦官干政,即位伊始便下诏:“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目的在于限制宦官权力;黄初三年,又下诏:“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目的在于杜绝外戚干政之弊。总的目标,就是加强皇权。曹丕加强皇权的举措,实则来自法家,尤其是韩非子。韩非子曾专门论及国君应该警惕身边之人篡权,著有《备内》、《八奸》,同时也对君主“左右”、“近习”侵权夺利的行为多有告诫:“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韩非子·孤愤》)韩非子认为:“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韩非子·和氏》)这是韩非子加强君权时一再强调的两点内容。曹丕虽热衷复兴儒学,但在最为关键的加强皇权问题上,他依然采用了韩非子的思路。
曹丕的举措,虽然堵住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漏洞,却忽视了以世家大族为背景的权臣兴起。曹魏王朝,存续时间不过短短四十六年,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安宁和稳定。随着司马氏势力的不断壮大,司马炎最终在魏元帝咸熙二年逼迫曹奂禅位,西晋始立,魏作为一个王朝遂告灭亡。
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主要政绩就是灭掉东吴,实现了中国短暂的统一,但是“皇权焦虑”现象并未消除。他传位于近乎痴呆的司马衷,由此重启外戚专政之门。司马氏诸王觊觎神器,更是皇权衰落的直接表象,“主弱臣强”的格局依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东晋。田余庆在论及两晋政治特征时说:“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3]25其实,无论宗室强王专权也好,士族名士主导的门阀政治也罢,都在彰显皇帝权力的衰微。赵翼在观察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现象时,同样发现“东晋多幼主”。他说:“晋南渡后,惟元帝年四十二即位,简文帝年五十一即位,其余则践阼时多幼弱。明帝二十四岁,成帝五岁,康帝二十一岁,穆帝二岁,哀帝二十三岁,废帝二十一岁,孝武帝十二岁,安帝二十二岁,至恭帝即位年三十二,而国已归刘宋矣。”[4]162-163幼主当国,自然给门阀士族掌控皇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与东汉时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从“王权焦虑”的角度来说,实则异曲同工。在西晋以来的“主弱臣强”格局中,有为之君自然不甘大权旁落。越是想有所作为,“王权焦虑”亦愈甚。于是,偏居江左的晋元帝开始着手加强皇权,而给他相应政治启迪的,实则也是法家的“申韩之学”。直到南朝刘裕实现“主威独运”,依然草蛇灰线,隐隐透露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韩学”的影迹。
注释:
(1)《群书治要》将《臣不易》与《治本》联为一篇,今据严可均《全三国文》改为《治本》。
参考文献:
[1]章太炎.检论·学变[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吕思勉.读史札记·魏晋法术之学(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赵翼.廿二史諸记·东晋多幼主[M]//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吴勇)
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078-007
*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韩(非)学史略”(12YJAZH118)
作者简介:宋洪兵(1975—),四川犍为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法家思想及其当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