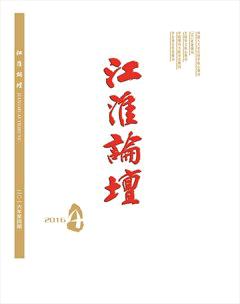《慈善法》之善:对立法目标的法理阐释
2016-07-04蔡琳
蔡 琳
(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 210093)
《慈善法》之善:对立法目标的法理阐释
蔡琳
(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3)
摘要:《慈善法》是一部具有道德色彩的法律。《慈善法》所理解的慈善活动是一种“大慈善”的概念。慈善是为公益的志愿行为,“公益”即为慈善行为或慈善组织所指向或锻造的目标。“公益”的内涵应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进行公益性测试认定。为了实现《慈善法》促进慈善事业的目标,应该放宽慈善的公益目标的理解,对慈善活动的动机、影响因素、税收激励绩效有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慈善;公益;捐赠;志愿服务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慈善法》是一部特殊的法律,之所以特殊,是因其内容不仅包括对慈善组织进行法律规制(例如信息公开),也包括了如何促进慈善组织的形成(慈善组织、促进措施)、关涉慈善活动的开展、慈善服务等道德行为。这是一部兼具多重目的、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法律,因此,有人以“善法”形容之。所谓“善”就是“好的”,对于一部法律来说,这个“善”意味着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法律的“善”。第一种“善”是指法律的目标,通过法律的颁布与施行而试图促进某种“好的”价值或行为,因此,如果说《慈善法》是善法,也就意味着《慈善法》所要促进和规制的“慈善活动”是好的。这里包含两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慈善法》所要促进的“慈善”活动,继而讨论这种慈善活动为什么是好的。第二种“善”则是关涉法律的功能,如果说慈善法所促进和规制的慈善活动是好的,那么,就这个法律的颁布和施行而言,是否可以预见地有助于实现这个良善的目标。
一、“慈善”的界定
有学者总结《慈善法》的亮点之一为“采用‘大慈善’的概念,体现了慈善活动发展的趋势”。[1]那么,何谓“大慈善”?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必须理解慈善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多样性。
大体而言,西方有两类慈善传统:一类传统被称为“救济”或怜悯的传统,通常是针对灾难、贫困,解决眼前的困难和需求。这种传统将慈善建立在私人美德之上,对于受益人来说,“救济”本身是施惠人一种恩惠的赠与,是赠与者表现慈悲心肠的方式。[2]9因此,这种慈善的理解往往与宗教中的怜悯情感或宗教理念密切相关,历史上也往往由宗教组织承担这类救济型的慈善服务。但是,这并不是慈善的全部。除此传统之外,另有一种从古希腊、古罗马公共事业而来、公益指向的传统,这种主张并不强调救济与怜悯,也并不将慈善视为怜悯行为,或视为一种私人美德的体现,而是将慈善作为一种提升公益、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3]164-172
就现代观念看来,怜悯与施舍只是为了缓解痛苦[3]53,而慈善的目标往往并不局限于此。究其原因则是:将慈善理解为救济与怜悯具有一个无法避免的、深层的道德危机。
一个救济贫困的捐赠活动,从捐赠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视为捐赠人美德的呈现;并且很多情况下,捐赠行为也的确是在这种美德指引下的道德行为。但若是换一种角度,所谓的救济贫困事实上就是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这种财富的转移预设了富人和穷人在社会等级上的差异;而且,通过这种济贫的慈善活动,甚至潜在地固化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社会等级和道德等级的差异。对于受益人来说,慈善活动的本意是试图消除苦难,但是在这样的救济行为中,给受益人同时带来了屈辱感和羞耻感[4],这种隐含的等级界限在道德上贬低了受益者。如果说一个真正具有美德的行为本身并不应该表现、更不应该创造这种不平等[2]100-101,那么,救济贫困就不是一种没有道德瑕疵的活动。这一点,在西塞罗的《论义务》一书中早已有所讨论。慈善与正义并不是同样的事情,慈善的责任更多属于具有特殊人身关系的人们之间,例如朋友和亲属之间善行可以补充正义,但是必须以正义为前提,人们之间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伙伴关系。[2]27-28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道德危机,现代社会中救济穷人的活动必须经由一种转化,这种转化使得赠予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施惠与受惠的关系转变为每个社会个体获得救济的权利。也就是说救济行为必须通过政府或国家予以转化,“在政府收税为穷人提供救济时,每个人都有作贡献的义务,为穷人提供的救济就变成了权利而不是恩惠。”[2]100-101就西方历史来看,16世纪中期开始起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从教堂手中获得了救济穷人的控制权,这是把穷人救济从宗教向公民权利转变的重要步骤。[2]70-71到了18世纪末,人们开始认为,国家能够并且应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分配或者重新分配财富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2]77,现代国家主要承担了济贫的责任与义务。
因此,现代社会中的救济贫困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不同的形式:一是私人救助,不作为法律所调整的内容;二是社会保障,主要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救助义务;三是慈善活动,慈善组织或慈善活动可以以济贫为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构成慈善组织法律上的义务。
虽然说济贫助困并不是慈善活动的全部,也不构成慈善组织法律上的义务,但这并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济贫助困的慈善活动不重要。慈善组织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时相比国家来说往往具有更高的效能,又不会像企业那样需要考虑盈利。因此,对于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济贫助困,慈善捐赠依然是比较重要的力量。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将慈善活动的功能仅仅理解为济贫或助困,慈善本身并不仅仅是“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关切与照料那些在第一次分配中不如意而二次分配中又不可能尽如人意的弱势人群”。[5]
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慈善的另一个传统,也即“公益指向”的传统。其实,不仅西方传统中存在将慈善作为一种提升公益、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的理解,我国历史上的慈善活动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济贫的“社仓”或“育婴堂”。
以学者梁其姿对明清时期慈善活动的研究为例,明清时期慈善活动与宋朝的长期济贫机构不同,其往往以小社区为基础,强化儒家价值,维护中下层儒生的利益。小社区通过慈善组织重整社会秩序,例如清代的乡镇善堂就成为极为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教化工具。[6]223其中有两种非常特殊的慈善机构可为例证:一种是儒生本于文昌信仰而形成的“惜字会”组织,他们将募捐来的善款雇人定时收拾废纸或购买废纸,建造烧纸的惜字炉,定期焚化这些纸张,并派员送灰到海。[6]126-148另一个是救济年轻寡妇的清节堂,这种慈善组织主要捐助清贫儒寡,避免其妻子迫于压力而改嫁他人,通过互助的形式给孤儿寡妇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6]148-173就前者而言,其并无传统意义上的济贫救困的形式与对象;就后者而言,虽然从形式上说是一种济贫,但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并无道德等级差异,而是清贫儒士的一种自救方式。究其本质,这两类均是为了维护儒生的道德价值,是为强化某种价值或某种理念的组织,而并非以济贫为目标。
总而言之,就现代社会而言,慈善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慈善组织也呈现为相当多元化的样态。因此,我国《慈善法》第三条亦规定,所谓慈善活动可以包括扶贫、济困,也可以包括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等其他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从这个条款来看,我国的《慈善法》所理解的慈善活动与佩顿主张的慈善概念是一致的:所谓慈善即是为了公益事业的志愿行为。[3]12
二、“慈善”之“善”
如果说所谓慈善是为了公益事业的志愿行为,那么“公益”即为慈善行为或慈善组织所指向或锻造的目标。因此,如果说慈善活动是好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慈善活动所指向的目标即 “公益”是好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慈善”之“善”。
也许立刻会有观点认为,“公益是好的”这样的命题完全不需要讨论,因为在日常用语中,“公益”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获得正面肯定的良善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公益”是一个可争议的概念,如何理解“公益”,不同的群体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当我们主张慈善的目标是为“公益”时,我们所指称的公益,是有着特定的内涵或实质标准,还是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主张多元的公益理解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慈善不仅仅是扶危济贫,若以现代慈善活动理念观之,慈善活动也并不等同于为了他人的个体利益[3]79而为之行为,“公益”亦并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为“他人之利益”,因此,“公益”的范围比救济贫困宽泛许多。有学者根据表达性维度和公益性维度将慈善分为四种模式:同情慈善、公共慈善、个性慈善以及战略慈善。其中“个性慈善”就是体现了捐赠人的价值偏好和个体追求,低公益性的慈善方式。[7]那么,那些有独立价值诉求、通过“个性的”慈善方式形成的非营利组织,是否可以被视为追求公益的慈善组织?基于某个特殊社区的利益而形成的组织,是否可以视为真正公益性的慈善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的思路:一是家长主义的思路,也即立法者为了避免在具体情境中再去考量某种慈善目标是否属于“公益”范畴,而事先界定公益的内涵或实质性的标准。但是,这样的思路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很显然,公益的内涵和实质性的标准是非常难以确定的,不同时期、不同群体都可能对此有不同的认识,限定某种公益的认识本质上也意味着一种价值判断上的专断。其次,如果对于公益的判断很难确定,为了规范慈善活动,法律就很容易将公益与特定的慈善组织相关联,其他慈善活动也就比较难以获得合法的认可或发展的机会。
另一种则是自由主义的思路,也即事先不去限定公益的内涵,而鼓励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开展。对于自由主义的慈善观来说,如果将公益限定于固定的内容或标准,事实上将会限制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发展。如果没有慈善组织的活动,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少数群体的权利、生存状态也就不会进入公共领域,也不会被关注。2014年风靡的“冰桶挑战赛”[8]就是很典型的事例,这个冰桶挑战使得关注罕见病人的生存状态和权益成为公共领域中被讨论和被认知的公益。因此,与其说将公益视为被“寻找”的标准,不如说“公益”是通过慈善组织积极开展社会文化项目在公共领域中所锻造出来的东西。[3]79这也可以理解为慈善活动“先驱开拓功能”的一种体现。[3]49慈善组织作为公益保护的先驱者,通过其积极的锻造与慈善活动,使得一些原先不为人们所关注的公益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并尝试集体解决公共问题[3]17,并最终促进国家保障此种公益的实现。[9]就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而言,慈善活动也越来越呈现出的大众性、草根性与社会性的一面。[10]
因此,如果秉持自由主义的观点,基于“公益”理解的群体性差异,当形成慈善组织时,一般不应限定作为慈善目标之“公益”的具体内涵。只要其目的并非为个人之私利,而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公共利益,例如特殊群体的权利、特殊物种的保护、特殊地区的文化等等,都可以形成慈善组织,都可以为基于公益的志愿行为。
但是,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公益锻造与慈善组织的多样化,也可能会受到这样的批评:这种自由主义多元化的公益理解或慈善活动可能会导致社会的碎片化,或者反而加剧群体之间的差异性。[11]386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多元化的公益理解本身并不一定导致社会的碎片化。因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并不等同于社群内部的共同体团结模式,两者之间也并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而且,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可能存在目标上的交叉与重合,并不一定造成群体对于公益认知上的差异性。因此,自由主义理念下的慈善或公益理解不一定意味着慈善组织最终会走向社群主义、群体化的 “志愿转向”。[4]
其次,自由主义理念有助于慈善组织的发展、丰富以及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本身即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从组织方式来看,这种多样化的慈善机构是公民出于自愿与公益的慈善目标而形成的团体或组织,这种组织存在于家庭、国家、市场之外,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美国的慈善组织发展历史来看,慈善组织作为社会力量,脱离于国家和市场[11]382-383,构成社会自组织的一种基本方式,这种方式蕴含了“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个性”等作为社会认同根基的特质[10],因此,慈善组织的多样化恰恰反应了这些现代社会所珍视的价值。
从其目标与运作方式来看,通过慈善活动以及慈善组织,人们形成一定程度的紧密联系。这是一种共享慈善目标的社区式共同体团结形式。这种共同体式的团结本身亦是慈善组织所主张和推进的公益之一种。例如英国2006年慈善法第2 (2)(e)条就规定 “促进公民意识和社区/共同体(community)的发展”作为其慈善目标。[12]慈善组织的群体团结本身值得珍视,通过慈善组织的活动,可以在慈善组织以及共享相同价值的社群内部形成紧密的共同体联结。这种共同体联结的方式,促进了自我与好生活实质性目标的实现。[13]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国的慈善组织可以视为单位制度解体之后建立社会组织和社会团结的一种替代方案。[4]
第三,虽然说公益的理解具有群体性和多元化,慈善组织也具有多样性,但是必须区分两个问题:慈善组织的形成可以秉持自由主义的原则,慈善组织的公益性以及是否因其公益性享受税收优惠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其之所以可能享受税收减免的待遇是因为其追求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指向,慈善组织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就国外的立法例来看,英国2006年慈善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如何理解这些公益性质的慈善目标,并列举出12条具体的慈善目标以及1条兜底条款。其中第2(3)条又对第2(2)条中相关的概念,例如宗教、体育、何为促进健康等内容作了相当宽泛的界定。[12]这些宽泛界定的内容基本能够涵盖几乎所有的常见慈善目标。美国关于慈善组织免税规定的《国内税收法典》501(c)(3)条款中也列举了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教育,孩子与动物权利等慈善目标作为公益慈善的具体内容,并且对于慈善组织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也有所限定。[14]我国《慈善法》第3条同样也列举了公益活动的种类。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这样限定慈善目标的公益性质,是否意味着公益的内涵具有了实质性的标准,违反了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前述通过慈善组织锻造公益的观点?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这些公益目标的列举并非是完全列举,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判断某个特定慈善组织的目标是否具有公益性。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公益性的判断不应采用肯定式的限定。例如,美国《国内税收法典》规定为慈善事业的法人机构、社区福利基金或基金会,只要其净收益不是为了保证使私人股东或个人受益,其行为的实质不是为了进行宣传倡导活动或企图影响立法,不参与或干涉竞选活动[15],就可以视为其具有减免税收的资格。英国的2006年《慈善法》第3、4条也规定了慈善组织必须经过公益性测试,一是慈善组织主张能够给社会带来切实的客观利益,二是对于受益人的范围并不能封闭性地限定。
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慈善法中慈善活动所指向的“公益”目标,应该能够包容相当宽泛的含义,其理解的多元化本身亦具有正面而积极的意义。
三、慈善“法”之“善”
如果说慈善法所促进和规制的慈善活动是好的,那么,就这个法律的颁布和施行而言,是否可以预见地有助于实现这个良善的目标?我们必须结合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分析或预测,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或可称之为慈善“法”之“善”的探究。
首先,如前所论,作为慈善目标的“公益”本身应采更为广泛的、多样化的理解,而不应限定在固定的内涵与实质性标准之中。不仅如此,如果说《慈善法》第1条规定的“发展慈善事业”意味着促进慈善组织的形成、慈善活动的普遍化,那么一般来说,为了促进慈善活动和组织的多样化与发展,也需要对慈善的观念有相对宽泛的理解,不能对慈善目标限定过窄,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秉持公益的多元化理解。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相关规定?《慈善法》第9条规定了慈善组织应该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一项即为“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而所谓慈善活动则为《慈善法》第3条所列举的内容。那么,如果依据《慈善法》第10条成立慈善组织,是否可能存在对其慈善活动进行实质性判断——例如是否符合第3条的规定?当然一般来说,慈善法第10条规定在设立慈善组织时采用登记制,并不应进行实质性的判断,但是根据第9条、第3条的规定,也完全可能出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据第9条第(一)项“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同时基于其自身对公益的判断而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那么,我们是秉持上述自由主义立场的主张,还是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定慈善目标的家长主义的做法?如果说慈善法秉持的是 “大慈善”的概念,并且在慈善的“公益性”上做开放性的理解,那么,其公益性判断的程序应如何设计?应由谁来判断?是否有讨论抗辩的程序?这些内容尚需仔细的衡量、制定相应的细则。
其次,从目的来说,所谓慈善是为“公益”之事业;但不仅如此,这种事业也是一种“志愿”行为的事业。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捐赠人为何捐赠,志愿者为何志愿提供服务,这样方能促进慈善活动的发展。从慈善捐赠报告来看,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捐赠数额、志愿服务都有着显著的增长[16],其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捐赠和志愿服务?当一个人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给予没有权利得到救济的人以救济,是一种美德。[2]74美德固然是公益事业的源头之一,但即便如此,就理性人的捐赠而言,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慈善活动的动机中利他和自利两方面都可能存在;除此之外,影响捐赠动机的因素还包括外部条件、回馈、个人感知、个人特征四个方面;其中外部条件包括具体的募捐方式、募捐的制度设计、一次性募捐还是多次捐赠机会。[17]除了自愿捐赠之外,志愿服务的心理动机又是如何?是否也存在利他与自利动机共存的状态?不仅如此,一国之慈善文化、慈善意识对于慈善活动的开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居民之间的普遍信任水平、媒体的舆论,以及慈善组织自身的管理和信息披露、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对慈善行为也存在相当深刻的影响,例如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的社会捐款数额大幅度下降就是一例。[18]
如许种种虽然并不需要都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但至少如下四个方面与慈善法密切相关。
第一,当法律在鼓励捐赠和鼓励志愿服务的时候,是否可能会导致利他动机的减少,反而使得在激励之下的捐赠和志愿服务变成一种自利行为?法律应该如何激励捐赠或鼓励志愿服务?
第二,慈善组织应该如何确保其自身公益目的的实现、由谁评估或促进慈善组织的公益目的的实现?慈善组织并非以营利为目标,其所追求的公益往往并不体现为某种物质利益,甚至实现其所追寻的目标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因此其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式与效能评估可能与其他组织有着较大差异,那么《慈善法》第95条第二款规定的慈善组织的评估制度,其评估的合理标准应该如何具体化?
第三,既然信息披露、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与慈善行为密切相关,那么,以信息公开为核心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就是促进慈善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与慈善法第1条规定的目标——“规范慈善行为”在功能层面上是一致的。但是,这里还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例如,如果对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进行监管,其理由是什么?因为慈善组织的形成与政府部门、市场私主体不同,因此对其进行监管所要求的信息公开是否应有所不同?
第四,就世界各国的慈善法中所常见的税收激励而言,美国的大多数研究表明,采取慈善税收减免不会改变一个人是否捐赠,但的确会影响他们捐赠的数额。[3]58《慈善法》的第79条到第83条均原则性地规定了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都可以享有特殊的税收优惠,但是这些原则性的规定需要具体化,明确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免税的范围,修正并推进慈善税收的相关法律政策。
当然,为了实现《慈善法》的目标,法律规制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内容。作为第三部门的慈善组织,构成了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市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慈善组织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与第二次分配一样,纳入一种制度性调整框架,通过与国家、个体利益之间合作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促进了共同的善。作为调整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的《慈善法》,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杨思斌.慈善法草案的亮点解析[J].中国民政,2016,(4).
[2][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M].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9.
[3][美]佩顿,穆迪.慈善的意义与使命[M].郭烁,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4]战洋.作为团结机制的慈善及其困境——一则政治人类学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5]徐剑锋.培育第三种力量 撬动第三种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深远意义[N].中国社会报,2016-4-18.
[6]梁其姿.施善与教化 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陈可鉴,郁建兴.慈善的性质与模式[J].南京社会科学,2015,(5).
[8]张天潘.“轻公益”的来临——“冰桶挑战赛”宣告公益进入2.0时代//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5(慈善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9-245.
[9]AlbertM.Sacks.TheRoleofPhilanthropy:An Institutional View[J].Virginia Law Review[J].Law and Philanthropy,1960,(3):523.
[10]刘威.重新为慈善正名——写在《人民日报》社论“为慈善正名”发表二十周年之际[J].浙江社会科学,2014,(9).
[11]Bruce R.Sievers.Philanthropy’s Role in Liberal Democracy[J].TheJournalofSpeculative Philosophy,2010,(4):386.
[12]参见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6/50/ section/1.
[13][美]弗雷泽.身份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再分配、承认和参与//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的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
[14]Oliver A.Houck.With Charity for All[J].The Yale Law Journal,1984,(8):1421-1437.
[15]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管理及启示//2011年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年《美国蓝皮书》)[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mg/ 201310/t20131026_593321.shtml.
[16]宋宗合.2013—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7-32.
[17]郑筱婷,钱艳萍.理性人为何捐赠?——关于慈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一个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14,(1).
[18]石国亮.我国居民的慈善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J].理论探讨,2014,(2).
(责任编辑焦德武)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026-006
作者简介:蔡琳(1977—),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