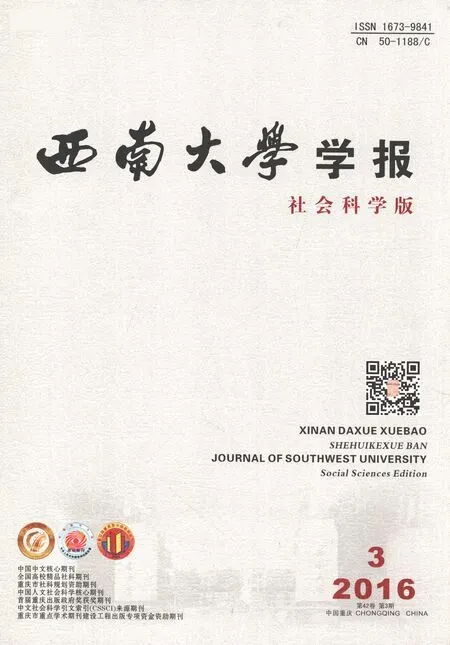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①
——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
2016-06-20兰剑,慈勤英
兰 剑,慈 勤 英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①
——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
兰剑,慈 勤 英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低保受助者重新就业,是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规避救助依赖的重要方式。采用城市低保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以及失业后再就业积极性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具有“双重效用”,既可以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但也可能降低未就业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强化受助者救助依赖心理,导致新的福利依赖问题。由此提出:要适当调整现行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加强对就业困难低保受助者的直接就业援助;由解决“收入贫困”问题转向破解“能力贫困”问题,构建以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适龄劳动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能力培养。
关键词:社会救助;城市低保;福利依赖;反福利依赖;再就业;收入贫困;能力贫困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救助制度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着“福利依赖”与“反福利依赖”的博弈。两者博弈的焦点在于如何平衡救助人口与提升受助者自我发展能力上,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如何通过社会救助提升受助者自我发展能力,如提升再就业主观愿望与再就业竞争力,从而规避受助者陷入长期“福利依赖”的恶性循环中。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高额的福利支出,西方福利国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福利依赖”问题,克服社会福利制度中“奖懒罚勤”的缺陷,纷纷进行福利政策调整,推出系列反福利依赖政策,其普遍做法就是“从被动的福利给付转向增加求职和工作要求,以鼓励就业的吸收和减少福利依赖的目的”[1],要求有劳动能力的福利受助者必须履行一系列和工作有关的义务,主张“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福利政策,以打破“福利循环”,减少福利依赖[2],强调被救助者“为福利而工作”(Work-for-your Welfare),“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必须参加政府提供的工作或者培训,以作为对政府救助的回报”[3]。例如,美国在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中将福利制度从“资格机制”改为“工作优先”模式,对福利给予采取时间限制,提出强制性的工作要求[4]。在同期,包括法国、英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经合组织国家(OECD)也积极采取有效的“反福利依赖”措施,如实行缩短失业津贴领取期限等新对策[5],要求在限期内失业者不能轻易拒绝就业机会。例如,英国在1996年把“失业津贴”改为“求职者津贴”,要求领取者必须签订一份详细规定求职活动的“求职者协议”,若不履行协议中的条款,求职者必须接受一份指定的工作或参加就业培训,否则将会受到惩罚[6]。再如德国,开始实施于2002年的“哈茨法案”,以“创业补贴”代替过去单纯性发放的失业津贴,规定获得补贴的前提是失业者需要接受一个低水平的工作[7],该系列法案突破了以往把失业津贴作为福利的惯性思维,从法律上实现了从“失业福利模式”向“工作福利模式”的颠覆性转变。综上所言,欧美发达国家“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核心准则,就是推行受助权利与履行责任相结合的工作福利制,“强调创造工作机会、弹性劳动市场和加强教育与训练,从而使社会福利和劳动市场的就业服务紧密连结”[8];作为“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有效利器,工作福利制更加强调被救助者的“责任和义务”,旨在提高救助对象自身实现再就业的努力程度,从而有效地降低救助依赖,提高救助对象的就业率[9]。
但是,作为西方福利国家“反福利依赖”改革利器的“工作福利制”,也一直备受争议,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工作福利制的有效性问题。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赞成工作福利能有效地实现反福利依赖。例如,Joel[10]认为,工作福利制不仅能够实现减贫,还为受助者提供了现实的选择,有利于促使遭受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重新回归主流社会,让缺乏就业机会或缺乏就业技能的被排斥对象获得社会的吸纳和认同;Huber等[1]通过对德国工作福利计划的实证研究发现,提升受助者被雇佣率的短期和长期培训计划能够降低参加者的“福利依赖”,“为欧元而工作”的工作福利计划在长期来看也能降低“福利依赖”。另外一类观点却认为,工作福利制带来的并非全是积极作用。例如,工作福利制过度注重强制性的社区体验,以及过分严格的工作要求,使受助者因担心受到制裁而被迫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引发受助者不满;或者因政府安排的工作过于低下,受助者自感受辱,因而宁愿选择就业市场不理想的工作,也不愿接受政府推荐的工作,最终出现“以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为代价的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扩张”,从而出现“工作着的穷人”[11]。另外,民众对工作福利制的抵制,也使其面临着诸多挑战,引发不少争议。
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反福利依赖”改革,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规避救助依赖问题提供了参考。例如,目前我国多数城市要求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需要参加公益性社区服务,这与西方福利国家实施的社区体验政策是相似的。对于我国可能面临的救助依赖风险,国内学者也已经进行了研究。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出现的一些问题,王丽华、孟湘泓[12]认为,我国救助资源受益分配瞄准偏差,就业激励机制和就业援助专项制度缺失漏洞,内在地存在着反贫困功能梗塞。对于我国如何进行反福利依赖,有学者结合西方福利国家工作福利制改革经验,提出应对之策。如建立健全就业激励机制,扩大灵活就业的保障覆盖面[13];以积极的社会政策代替消极的福利给付,把教育和培训作为福利政策的重点,实现福利事业从公益型向人力资本投资型的转变[9]。对于反福利依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问题,关信平[14]认为,采用积极社会救助以化解福利依赖,准确确定受助者致贫原因,以便提供切合其特点的服务;李乐为、王丽华[15]指出,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彭宅文[16]通过对“中国式福利依赖”的研究,提出把工作培训、就业服务等劳动政策的相关内容与救助政策相结合,在救助期间提高救助对象的就业能力,以使其彻底摆脱低保救助。
国内外对反福利依赖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就业激励与工作福利制度等层面展开,这些措施都有助于规避社会救助的“依赖陷阱”。因此,如何平衡救助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反福利依赖政策,解决低保救助的依赖问题,成为破解现行社会救助制度“负激励”效用的重要举措。据此,本研究以城市低保调查为数据来源,从我国城市低保救助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出发,构建回归模型,探究城市低保救助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对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以及未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以进一步掌握现行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效果,为相关政策调整与改革提供依据。
二、研究框架与变量测量
(一)来源数据介绍
本研究所用数据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课题组,于2014年在湖北省和辽宁省等地进行低保调查所采集的数据。调查对象为目前正在接受低保或曾经接受过低保的群体。为确保问卷数据获得的真实性,由调查者一对一地对低保受助者进行问答,调查者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填写问卷,并由课题组成员进行现场督导与陪访。为保证样本的无偏和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分阶段抽样,通过四个阶段,分别在县(区)-街道(乡镇)-村(居)-家户(个人)层面上进行配额随机抽样。抽样总量为1 100个,最后完成的有效样本量为1 015个,有效率为92.3%。本研究只选取城市低保户作为数据分析对象,符合条件的样本量为687个。之所以选择城市低保受助者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根据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村低保救助的反福利依赖政策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地方甚至还是空白;但与此相比,城市低保的反福利依赖政策执行时间更长,相关政策也更加规范和成熟,因此可使研究结论更具价值。
(二)研究框架与主要变量
目前,国家在城市低保救助上对正处于适龄劳动阶段的受助者设置了一系列“反福利依赖政策”,如要求未就业受助者需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实现就业,参加公益劳动与职业培训等。本研究旨在探究该类政策是否发挥了反福利依赖的作用,能否促进受助者就业,是否提升了失业者的再就业积极性等。就问卷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调查地主要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包括:(1)要求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低保受助者限期实现再就业;(2)基层街道办或社区推荐和介绍工作,未就业受助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3)在失业期间需要参加职业培训;(4)在接受低保救助期间,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需要参加公益服务,如社区组织的义务劳动等。因此,本研究将一一探究以上反福利依赖政策是否能够有力地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或者提升未就业受助者的再就业积极性。据此,设置以下主要变量(表1):
1.被解释变量。反福利依赖政策的目标是抑制低保受助者的救助依赖,促进受助者积极就业。因此选取低保群体的就业情况、失业后再就业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三个变量:(1)低保受助者目前的“就业情况”(就业还是失业);(2)“再就业行为”,即低保群体失业者“目前是否正在找工作”;(3)“再就业意愿”,即“如果有一份工作,是否愿意立即去工作”。
2.解释变量。根据被调查地“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执行情况,选取以下五项作为自变量,主要包括:(1)是否要求找工作。该变量视为对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要求,已经失业的受助者需要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就业,这对于约束受助者的救助依赖行为有直接影响。(2)政府部门是否介绍过工作。该变量主要用来表示对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低保群体进行的就业支持,对促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或者失业后再就业具有重要影响。(3)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该变量主要要求未就业的低保受助者接受职业培训,提升受助者就业能力。(4)是否组织公益性劳动。该变量从政府角度出发,要求低保受助者履行一定的义务,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弱化受助者的救助依赖心理。(5)是否参加过公益劳动。该变量从受助者的角度出发,探寻受助者对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执行程度。
3.控制变量。反福利依赖政策是否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受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以及救助给予等方面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包括:(1)与个体就业密切相关的健康状况、年龄条件。一般地,健康条件越好的,就业的可能性也越高,找工作与再就业的意愿也越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找工作或再就业的积极性在降低。(2)与家庭经济条件相关的家庭成员、医疗教育支出情况。老年人通常需要专人照顾,并且老年人往往体弱多病,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医疗支出,这些容易加大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会影响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行为以及再就业意愿。家庭的医疗与教育支出越大,说明家庭有病患,或者有在学子女,这些都需要专人照顾,也会影响低保受助者的就业或者再就业行为。(3)与救助给予相关的低保救助。低保金额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受助者的就业意愿。一般而言,低保金额越高,以及个人社会救助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越高,受助者的就业意愿就越低。

表1 主要变量描述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根据以上要求,分别对各变量进行操作化后,选取“就业情况”、“再就业行为”、“再就业意愿”等三个测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反映“反福利依赖政策”的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首先,在分析之前,将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考察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表2)。从表2的分析结果来看,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各主要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小,可以避免模型的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模型构建。

表2 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关系分析表
注:显著度:***p<0.001,**p<0.01,*p<0.05
(一)“反福利依赖政策”对所有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的影响
以城市低保群体的“就业行为”,即目前是否正在工作,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先后加入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共构建2个模型(表3)。首先,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考察“反福利依赖政策”对低保群体就业行为的影响情况,构建模型A1。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卡方检验值为66.646(df=5),已知给定显著度0.05,自由度为5的卡方临界值是11.070,从而判定模型检验的卡方检验值66.646>11.070,并且相应的Sig.值小于0.001,因此该模型通过检验,表明可以拒绝零假设,认为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解释变量的全体与Logit P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采用该模型是合理的;另外从-2对数似然值527.503大于卡方临界值11.070,Nagelkerke R方=0.171,以及H-L检验卡方检验值5.330小于卡方临界值11.070,其中Sig.(0.377)>0.05的显著度,也充分说明该模型整体性拟合效果良好。从变量影响情况来看,“是否介绍过工作”、“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是否参加过公益劳动”等变量对低保群体的就业呈正面影响,其他变量对低保受助者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如被介绍过工作的低保受助者,其就业几率是未被介绍过工作受助者的3.01倍(e1.102=3.01);参加过公益劳动的低保受助者,其就业几率比未参加过公益劳动的受助者高105%(e0.720-1=1.05)。这说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低保受助者的就业。

表3 “反福利依赖政策”对所有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影响的回归模型
注:N=687,显著度:***p<0.001,**p<0.01,*p<0.05
加入控制变量,构建模型A2,观察新变量与原有变量对低保群体就业行为的影响情况。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卡方检验值为278.425(df=11),给定显著度0.05,自由度为11的卡方临界值是19.675,从而判定模型检验的卡方检验值278.425>11.070,并且相应的Sig.值小于0.001,因此该模型通过检验;另外从-2对数似然值315.724大于卡方临界值19.675,Nagelkerke R方=0.598,以及H-L检验卡方检验值6.959小于卡方临界值15.507(其中df=8,a=0.05),其中Sig.(0.541)>0.05的显著度,也充分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良好,可以采纳该模型;并且从Nagelkerke R方来看,模型A2的解释力度比模型A1明显提升。加入控制变量后,发现“是否要求找工作(B=0.764,p<0.05)”“是否介绍过工作(B=0.913,p<0.05)”对低保受助者的就业呈正面影响,其他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如被要求找工作的低保受助者,其就业几率比未被要求找工作的受助者高115%(e0.764-1=1.15);被介绍过工作的受助者就业几率比未被介绍过工作的受助者高149%(e0.913-1=1.49),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反福利依赖政策能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从加入的控制变量来看,“是否有老年人”“人均低保金额”“个人社会救助占比”等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面的。这说明三个问题:有老年人的家庭,因为需要低保受助者专门照顾,降低了受助者就业的可能性;人均低保金额越高,受助者就业的可能性也越低;个人社会救助收入占个人总收入比重越高,个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性越强,其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这些说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家庭有老年人的低保群体影响无效,对个人社会救助占个人总收入比例超过80%的群体无效,并且,随着人均低保金额的增加,这种促进就业的反福利依赖正常效果也在降低。
以上两个模型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能有力地促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但对于有些群体,反福利依赖政策并不能发挥促进就业的效果。例如,对于家庭有老年人的群体,个人社会救助收入超过个人总收入80%的群体。并且随着低保金额的增加,反福利依赖政策的这种就业促进效用也在降低。
(二)“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失业低保受助者“再就业行为”的影响
以失业低保群体的“再就业行为”为被解释变量,即“目前是否正在寻找工作”,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表4)。首先,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只考察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从模型B1运行结果来看,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卡方值为7.119,给定显著度0.05,自由度为5的卡方临界值是11.070,说明在给定0.05的显著度下,模型检验卡方值小于临界值11.070,说明该模型未通过检验;另外从-2对数似然值207.261>卡方临界值11.070,模型通过检验,但从Nagelkerke R方=0.046来看,模型拟合优度比较低。这些说明自变量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失业低保群体的找工作积极性没有显著影响。从模型的回归系数与P值也可以看出,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已经失业的受助者“再就业行为”影响不显著。从表2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来看,也发现了反福利依赖政策与未就业低保受助者“目前是否正在找工作”仅仅呈现微弱的相关性。这些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没有发挥出提升失业低保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的作用。
加入控制变量,构建模型B2,观察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变化情况。从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P值<0.01),H-L检验Sig.(0.706)>0.05,以及Nagelkerke R方=0.167,说明该模型通过检验,可以拒绝零假设,反福利依赖政策变量与控制变量能显著地预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从模型回归系数来看,发现“是否组织公益性劳动”(B=-1.142,p<0.05)对因变量产生负面影响,即组织过公益劳动的地方,其低保受助者积极找工作的几率却比未组织过公益劳动的受助者低68.1%(e-1.142-1=-0.681),这说明反福利依赖政策不但没有起到促进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的作用,反而降低了受助者寻找新工作的积极性,反福利依赖政策导致了新的救助依赖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就业的低保受助者在某种程度上把参加公益劳动与获得低保救助,视为一种交换行为,并从心理上认为,既然参加了公益劳动,付出了自身的劳动成果,那么就可以以接受低保救助作为对参加公益劳动的补偿或交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助者找工作的积极性。加入的控制变量中,“健康状况”与因变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健康状况越好,其找工作的可能性也更高;变量“年龄”(≥40岁)、“个人社会救助”(占个人总收入比例≥0.8)对因变量呈负面影响,说明年龄大于40岁的群体,其找工作的积极性比年小者低,并且个人收入越依赖于社会救助收入群体,其找工作的积极性也在降低。

表4 “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失业低保受助者“再就业行为”影响的回归模型
注:N=535,显著度:***p<0.001,**p<0.01,*p<0.05
从以上两个模型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反福利依赖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升未就业低保受助者找工作的积极性,但对已经失业的受助者却没有发挥促进其积极寻找工作的作用,甚至出现了负面影响。反福利依赖政策导致了新的救助依赖问题。
(三)“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失业低保受助者“再就业意愿”的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反福利依赖政策的作用,以城市失业低保群体的“再就业意愿”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C1和C2(表5)。首先,不加入控制变量,只观察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构建模型C1。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P值<0.001),Nagelkerke R方=0.174,H-L检验Sig.(0.515)>0.05,说明模型拟合良好,可以拒绝零假设,认为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变量“是否参加职业培训”(B=1.815,p<0.01)对低保群体的“再就业意愿”产生正面影响,即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低保受助者,有再就业意愿的几率比那些未参加过职业培训受助者高514.1%(e1.815-1=5.141);变量“是否组织公益性劳动(B=-1.379,p<0.01)”对因变量产生负面影响,说明组织过公益劳动的地方,其低保受助者有再就业意愿的几率要比未组织过公益劳动的低74.8%(e-1.379-1=-0.748)。这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能提升低保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但有的政策也会降低低保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充分说明了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双重效用,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效应。反福利依赖政策产生了新的福利依赖问题。
加入控制变量,构建模型C2,该模型综合检验P值<0.001,说明模型通过检验;H-L检验Sig.(0.895)>0.05,以及Nagelkerke R方=0.294,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并且相比于模型C1,模型C2的解释力度明显增加。加入控制变量后,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仍然存在。从回归系数来看,“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变量能提升低保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而“是否组织公益性劳动”对因变量仍然呈现负面影响,说明反福利依赖政策的负面效应仍然存在。新加入的控制变量“医疗与教育支出情况”(占总支出比≥0.3),以及“个人社会救助”(占个人总收入比≥0.8),对因变量呈负面影响。教育与医疗支出越大,说明家庭有病患,或者有在学子女,这些都需要低保受助者照顾,因此降低了受助者再就业意愿;个人社会救助所占个人总收入比例越高,说明该受助者越依赖于社会救助,那么其再就业意愿也越低。

表5 “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失业低保受助者“再就业意愿”影响的回归模型
注:N=535,显著度:***p<0.001,**p<0.01,*p<0.05
以上模型的运行结果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能够提升低保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如“参加职业培训”,但一些政策也呈现负面效应,这与模型B2运行的结果一致,如“组织公益劳动”,会降低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这些说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在促进低保受助者再就业积极性的同时,有些政策却反而降低了低保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反福利依赖政策导致了新的福利依赖问题产生。这也充分表明了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双重效用。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反福利依赖政策具有双重效用,既可以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但也可能降低未就业受助者的找工作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形成新的救助依赖“陷阱”:一是反福利依赖政策能有力地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如“要求找工作”“介绍工作”“参加职业培训”“参加公益劳动”等举措能有效地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降低失业风险;二是反福利依赖政策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未就业低保受助者找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再就业的意愿,如“组织公益性劳动”。研究数据表明,相比于未组织公益劳动的地方,组织过公益劳动的地方,其低保受助者找工作的积极性与再就业的意愿都要低。这也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发挥的作用不一定完全是正面效用,也可能产生新的救助依赖问题,即未就业受助者越发依赖低保救助,其再就业愿望和寻找新工作的积极性却不高。反福利依赖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抑制低保受助者的救助依赖,提升受助者的就业可能性,以及增加未就业受助者找工作的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但却事与愿违,反福利依赖政策在发挥反福利依赖效用的同时,出现了新的救助依赖问题,表明了反福利依赖政策存在“双重”效用。
因此,为进一步发挥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正面作用,规避其负面效应,需要对有些反福利依赖政策进行调整,加强就业激励,实施就业收入豁免政策与渐退救助政策,并且反福利依赖政策的着眼点仍在于如何破解受助者的“能力贫困”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合理设置政策,对出现负面效应的反福利依赖政策进行调整,并加强对就业困难受助者的直接工作援助。对于能够激发受助者就业积极性、提升受助者再就业意愿的政策,例如,“要求未就业受助者限期实现再就业”“对就业困难的受助者推荐和介绍工作”“组织和提供职业培训”等,进行完善和进一步规范。而对于可能助长新的福利依赖心理的政策应该进行调整或中止,如“组织公益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就业受助者找工作的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受助者之所以在参加公益劳动之后,其再就业积极性降低,原因就在于误解了该项政策,认为参加公益劳动是对获得低保救助的一种“交换”,认为既然采用参加公益劳动的方式获得低保救助,那么就可以理所应当地享受低保,从而导致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的降低。另外,影响低保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和再就业意愿的因素,还包括个人与家庭条件,如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家庭有未成年子女或重病患者需要照顾等。因此,考虑到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际效用,以及低保受助者自身的实际情况,应该加强对就业困难低保受助者的直接就业援助,如考虑把“公益服务”设置成“公益岗位”,直接提供或推荐给就业困难的低保受助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助者对低保救助的过度依赖,提升了受助者的自立程度,依靠劳动自力更生。
其次,改变收入与救助的简单补差替代,实施就业收入豁免政策与渐退救助政策。目前低保救助推行的是“补差性”救助,即实际救助额等于政府救助标准扣除救助者现有收入后的差额,这实际上相当于对其新增的每单位劳动收入征收了边际税率100%的税收,是劳动所得对救济待遇的简单替代,收入多少就减去多少救助,这使得低收入群体在工作前和工作后的总收入基本一致,因此对于那些工作技能较差、工作后实际收入较低的受助者,其再就业的意愿将被弱化。这种简单的补差替代,非但不能鼓励劳动与就业,反而严重抑制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用劳动增加收入以退出受助行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应该采取一定的就业收入豁免政策,以取代全额抵扣就业收入的方式来确定实际救助标准。在基本生活费扣除中,考虑到就业的通勤成本等因素,以及鼓励就业所获奖励,应确定较低的抵扣率,进而使得就业收入的一部分得以保留,让受助者参加工作后的实际收入显著高于不就业时的收入。另外,实施渐退救助的办法,对重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受助者,不是立即停发低保救助,而应该按时间实行逐步退出的办法,并且剥除与低保资格捆绑在一起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应考虑困难群体的实际情况,按需提供各项救助。
再次,加强对适龄劳动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能力培养,实现由传统的给钱给物的“救济型助人”,向现代注重能力发展的“扶助型助人”转变。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重新进入就业市场,是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规避社会救助“依赖陷阱”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就需要进一步细化标准,分类施救,把受助对象分为无劳动能力和有劳动能力两类,对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加强“能力培训”。推动“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变,关键在于提升有劳动能力受助者的自力更生能力,帮助其获得重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与资本。通过规范化、正规化的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增强受助者文化素养与职业技能,开发受助者劳动潜力,帮助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构建完善的就业激励机制,用优惠政策鼓励失业群体自谋职业,提高受助者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因此,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根本着眼点在于,由解决“收入贫困”问题转向破解“能力贫困”问题,确立以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就业支持体系,对适龄就业的受助群体加强教育与技能培训,并实施包括教育救助在内的“代际贫困阻断”计划,对困难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加强教育扶持,使其家庭提升脱贫致富的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HUBER M, LECHNER M, WUNSCH C, et al. Do german welfare-to-work programmes reduce welfare dependency and increase employment?[J]. Germ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2(2):182-204.
[2]段美枝.社会救助制度变革方向[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5):94-97.
[3]GOUL Andersen, J.rgen. Welfare crisis and Danish welfare polici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London/N.Y.: Roultledge,2000.
[4]YBARRA M.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Why applicants leave the extended welfare application process[J].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2011,38(1).
[5]HANS Hansen. Transition from unemployment benefits to social assistance in seven european OECD countries[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8,23(1/2).
[6]尼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等.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M].王金龙,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53-80.
[7]杨伟国,格哈德·伊林,陈立坤.哈茨改革及其绩效评估[J].欧洲研究,2007(3):26-37.
[8]JESSOP. Bob. The stat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knowledge-diven economy[M].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2000.
[9]张敏杰.工作福利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J].浙江社会科学,2006(4):91-96.
[10]JOEL F. Handler. Social citizenship and work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The paradox of inclus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1]PECK, Jamie and THEODORE. Nikolas. Works first: workfare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ntingent labour markets [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
[12]王丽华,孟湘.反贫困视角(原文为“视觉”)下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安排[J].甘肃社会科学,2012(2):47-49.
[13]邱莉莉.国外救助与就业激励政策及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0(2):20-25.
[14]关信平.朝向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4(7):16-19.
[15]李乐为,王丽华.就业激励和援助:贫困救助制度演进和优化的基本取向[J].甘肃社会科学,2011(3):138-141.
[16]彭宅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救助对象的劳动激励:“中国式福利依赖”及其调整[J].社会保障研究,2009(2):163-173.
责任编辑刘荣军
网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05
收稿日期:①2015-09-04
作者简介:兰剑,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13JZD020),首席专家:慈勤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救助‘依赖陷阱’及其就业激励机制研究”(2014117010201),项目负责人:兰剑。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3-003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