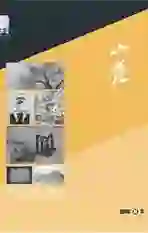京沪双城对照记
2016-06-16张慧瑜
80年代以来有两个城市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北京。这样两个城市在民国时期就有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之别。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上海与香港成为彼此互为镜像的双城记,那么上海与北京则更像彼此相关但又品性不同的亲兄弟。
中国城市文学的特殊性
在50到70年代,关于上海和北京的城市文学不是很多,因为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工业题材、城市题材相对边缘,革命历史和农村、军事题材比较多。那个时代的城市文学经常讲述工厂车间或街道社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故事,以城市工人为主角、揭开生产领域的面纱,但是这些城市文学却并不强调都市文化的地域性,因为在阶级话语的主轴中,北京、上海等地域特色被压抑,只有到80年代以来的城市故事中,地域性才被作为城市的本质属性,甚至为了凸显城市文化形象而建构不同的城市文化记忆。这本身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城市和现代化故事表达的特殊性。
西方现代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的历史。正如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是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消灭农民变成工业劳动者是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因此,对现代性、现代化的反思,也是对城市化的反思。在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地图中,诸如伦敦、巴黎、柏林、纽约等超级大都市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与这些城市相关的文学、电影、理论文本也不一而足。不过,西方现代城市的表述中,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堕落之源、罪恶之城,是19世纪的“恶之花”,也是20世纪的城市“荒原”。如19世纪的侦探小说、20世纪中叶的黑色电影等都是典型的城市故事。与这种负面的、反现代的城市表述相参照,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大量对于城市和现代化的正面描述和赞美,出现了一种“工业城市”、“现代化田园”的意向。工业城市不仅不是污染源,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识。比如毛泽东时代有很多文艺作品歌颂工业城市、现代化城市,赋予工业化、现代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城市的罪恶,黑暗城市是诱惑、欲望、消费的“恶之花”,另一方面阳光下的城市、喧闹的城市、工人的城市又是现代化、现代文明的代表。在毛泽东时代有两种典型的城市形象,一种是作为旧社会、旧中国的象征,是消费性的、腐朽没落的城市,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性、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新城市。在社会主义城市的书写中,城市变成了以工业生产和国营工厂为主体的生活样式,工厂既充当着生产、工作的任务,又是工人家庭生活的背景。这种对工业的正面表述,既与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有关,又与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渴望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述得以出现的前提是把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放置在历史的主体位置上。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工厂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标志,工厂工人也成为城市的主人。这从艾芜的《百炼成钢》和草明的《乘风破浪》等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发生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文学也尝试描述新的城市经验,但是基本上没有走向对现代性、城市文明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当下的城市文学主要充当着双重功能:一种是怀旧性,寻找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如老北京、老上海;二是书写新的都市经验,就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描述外来人在都市这一欲望之城中的“人间喜剧”。这恐怕与中国始终处在渴望现代、追赶现代的历史情境有关。
从老北京到新北京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城市文学主要是改革文学,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反映工厂实行内部改革的故事。80年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北京和上海“突然”拥有了自己的城市记忆。 在新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开始追溯历史和传统。这体现在北京城市文学中出现了老北京、城南北京,上海则开始回到30年代的夜上海和老上海。
北京的城市记忆主要是借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及老舍的现代文学作品(在80年代初期被大量搬上银幕),重新找到一个革命前的民国北京,一个贫民的、底层的北京。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以及改编的同名电影一方面延续了现代文学的传统,表现受苦人的、苦命人的北京,另一方面这种回望的视角又实现对这种底层北京的去革命化、去政治化的文化效果,这也高度吻合于80年代之初的时代需要。小英子眼中消失的驼铃、带有古诗韵味的《送别》在80年代中后期转化为北京古玩、字画、各种八旗子弟的玩意等京味文化,借助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刘绍棠等当代作家的京味小说,使得胡同、四合院、北京民俗成为老北京的文化符号。这种京味文学的出现与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化的潮流有关,不同于8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化反思以及激烈的反传统,这种对传统、民俗、地域文化的重构是为了确立新的文化身份和主体认同。这些老北京文化及其代表这种文化的城南空间在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创意产业中被作为北京的文化象征和北京旅游的文化资源。
80年代中后期对北京城市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作家王朔。王朔笔下的顽主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顽主作为成长于文革后期的红小兵,他们没能赶上父辈“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豪情,就连兄长们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历史也没有自己的份,他们只有在无尽的懊恼和向往中把自己“镶嵌”于想象的革命大戏里,“戏仿”成为顽主们扮演革命者或革命后裔的文化路径。顽主并没有随着80年代的落幕而终结,反而在90年代的影视剧中风生水起。这种对革命行动匮乏而产生的巨大渴求以及革命大厦将倾之计的荒诞之感,使得顽主经常表现为两幅面孔。他们不相信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但又保持一份对革命的理想和纯洁想象;他们在80年代最先下海、积极投身经济改革的洪流,但又不屑于做暴发户或拜金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绝非视金钱为粪土;他们宁愿做光明磊落的真小人,也不愿意假装一脸正气。也就是说,在顽主身上既有旧时代的影子,又有新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居间位置,使得顽主既可以春风得意,又可以嘲讽一切。这就是90年代以来王朔的两位精神传承人姜文和冯小刚所扮演的角色。
顽主中的“主”本身带有京味文化的特色,与北京称呼中的“爷”相似,是对人的一种尊称和尊敬,“顽主”的“顽”本身则很符合无所事事、整日闲逛、走街串巷、喝茶侃山的形象。小说《顽主》讲述了一个典型的80年代“待业青年”的故事。三个80年代的待业青年突发奇想,创办“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合伙公司本身是一种80年代新出现的社会组织形态,一种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运行的新体制。三T公司的“创意”与其说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购买社会服务,不如说用这种新的公司体制来戏仿、替换50-70年代存在的社会主义单位制。不过,悖论在于三T公司恰好在模仿中成为了他们所讽刺的社会主义单位,他们像基层单位一样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顽主看似与旧时代的话语一刀两断,却不经意间采取了他们所批判对象的形式,甚至在嘲讽中他们变成了被嘲讽对象。王朔以畅销书作家、开影视公司等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亲自实践着他作品中所书写的新的人格和人生。
90年代以来,除了老北京故事外,还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国际化的新北京。这种新北京又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以邱华栋为代表描写外地青年在现代化的北京追求梦想以及作为中产阶级的新北京人的都市情感故事(如《环境戏剧人》《时装人》《可供消费的人生》和《来自生活的威胁》等),第二种是以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为代表胡同北京的平民故事,大杂院、胡同不只是审美的空间,也意味着贫穷和底层状态。新世纪以来,以徐则臣、荆永鸣、石一枫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主要书写北漂、蚁族们在一个阶层急剧分化的时代里的内心挣扎和艰难生活,如徐则臣的早期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以及石一枫近一两年发表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都涉及到全球化时代都市青年人的底层化和绝望感。
从老上海到小时代
与这种带有平民色彩的北京城市文学不同的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张爱玲的“重现”以及香港文化人念兹在兹的“双城记”,旧上海又华丽转身为摩登(现代)、风韵、带有小资格调的夜上海,这是一个抹除了50到70年代革命(工业)上海记忆之后回眸与怀旧中的老上海,使得90年代经济高歌猛进中的上海找回了昔日的长恨之歌和风花雪月,如1996年王安忆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1998年女作家陈丹燕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等。如果说30年代的老上海、60、70年代的香港是新上海的“前世”,那么新世纪之交女作家卫慧则把这种“从十里洋场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优越感”转化为“今生”的“上海宝贝”,成为讲述20世纪历史的“新常态”。在这波“声势浩大”的“上海热”中,浮现出来的是晚清歌妓、民国月份牌美女和上海女宝贝,而这些上海往事的书写者则是归来的张爱玲、知青作家王安忆、儿童作家陈丹燕和美女作家卫慧等女性,正如《长恨歌》以“上海小姐”王琦瑶作为贯穿历史的主角和见证人。与这些女性的身影相伴随的是,90年代的上海已经从50-70年代布满工厂的新中国工业之都变成一个石库门、咖啡馆、购物时尚广场的国际化消费之都。与这种后工业的国际大都市同时发生的是中国从八九十年代以来走向对外贸易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种女性的身体既作为一种穿行于新旧上海历史的主体,又作为一处全球化时代文化消费和物恋的对象。
新世纪以来,上海故事又升级为“民国”故事和“小时代”的故事,从而实现了30年代的夜上海(黄浦江西岸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与东方明珠塔下的新上海(黄浦江东岸的陆家嘴)的完美对接。新世纪以来,郭敬明的《小时代》成为新的上海故事。《小时代》发表于2007年,2008年以来已经出版了三部曲,是郭敬明近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非常敏锐地把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一个大历史、大政治终结的时代。从80年代以来那种个人与时代命运相连的“大时代”就已经逐渐成为过去,不管是80年代的人性论、“大写的人”,还是90年代的“特立独行的猪”,都把个人、个人主义放置在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这与市场经济中个人作为理性人、自由人的主体想象是一致的。而《小时代》的意义在于呈现了新世纪以来个人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变成了一种“微茫的存在”。在小说开头段落,郭敬明这样描述“小时代”所处的空间载体——上海,“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人们的心脏被挖出一个又一个洞,然后再被埋进滴答滴答的炸弹。财富迅速地两极分化,活生生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小时代》被描述为一种悖论的状态,几个年轻人(富二代及其朋友)一方面把上海浦东陆家嘴变成他们的“儿童主题公园”,他们在这个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地带如履平地、一马平川,他们无需向历史索要记忆,也无需谄媚于西方的目光(就像《上海宝贝》中性无能的中国男人和超前性能力的德国男人),他们在“黑暗无边”的世界里成为主角和主人,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甚至是“最最渺小微茫的一个部分”。
与这种“小小星辰”相对应的就是《小时代》关于社会的想象。在小说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是青春靓丽的作家周崇光的致辞:“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这段话使用了《小时代》中经常出现的把社会、时代描述为“浩瀚的宇宙”的修辞方式。这种个人之“小”与宇宙、社会之“大”的强烈对比不仅是郭敬明式的“长不大”的少年情结,更是一种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想象。社会中的个人变成了“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也就是说,“我”(个人)被淹没在一望无垠、无边无际的宇宙沙漠里。这种支配性的、如同如来佛手掌心般的空间秩序,恰好就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从90年代以对外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向以房地产为中介的金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定,对于21世纪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再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也没有官方与民间的对抗,地上与地下的界限也失效了。借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中国变成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种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双重体制演变成了单一的社会制度和空间秩序。在这里,社会、时代对于个人来说成了一种笼罩性的、充满了无边黑暗的“铁屋子”。与鲁迅的“铁屋子”不同,鲁迅可以走进、走出铁屋子,他纠结于要不要去唤醒熟睡的人们,因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打碎铁屋子,而郭敬明的“无边黑暗”却是看不到边界、走不到尽头的宇宙,只能“被失望拖进深渊”,这才是真正的“大大的绝望”。
作者简介:
张慧瑜,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