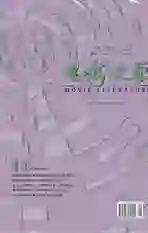多元式大和解:台湾当代电影的身份建构
2016-06-14李洋杨颖达
李洋 杨颖达
[摘要]台湾电影的身份认同建构方式在近些年来呈现出多元式大和解的趋势,其中《海角七号》是颇为典型的例证。影片以在地为立足点,以呈现在地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冲突作为发端,经过多重努力与妥协最终实现多元式大和解,这种由混杂冲突到包容和解的推演过程体现在全球化与在地、多元族群、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传统与现代等多个面向。影片在接收与认可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通过和平共存、彼此包容、多元融合的逻辑建构出大家都是在地人的身份共识。
[关键词]台湾电影;身份认同;《海角七号》
提到台湾当代电影,就不能不提到《海角七号》这部影片,它的“一鸣惊人”给长期处于昏暗中的台湾电影市场带来了希望的光亮。该片于2008年8月22日在台湾上映,于一周之内全台票房突破一千两百万新台币,不到一个月便突破一亿元新台币,至12月12日下片时,《海角七号》在113天的时间内在台湾总共取得了5.3亿新台币的票房。在它的带动下,一批新导演和新作品逐渐受到关注,台湾岛内掀起了观看“国片”的热潮,《囧男孩》《一八九五》等一系列影片突破了千万元的大关,票房超过百万的影片也不在少数,甚至连在《海角七号》之前上映的《九降风》(2008),也因为“海角热”而获得重新上映的机会,并受到比此前更多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海角七号》不仅缔造了票房奇迹,同时也使台湾电影“奇迹般”地重获新生,一时之间“支持国片形成了一种态度,亦可说是一种风潮”[1]。对于这股风潮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其中,台湾影评人郑秉泓认为:“《海角七号》的全民争看热潮,不应该被简化为跟风、追流行的‘蛋挞效应,关键在于影片本身流露出来的正港‘台湾魂,确实征服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2]而这里所提到的“台湾魂”,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共识的身份认同。在充满混杂、差异、矛盾的现实中,《海角七号》到底是通过怎样的叙事策略进行身份认同建构的?又是如何实现对观众的感召进而达成认同共识的?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细致探究。
列维-斯特劳斯对古希腊神话传说进行深入研究时曾指出,“古往今来、人类不同时代的叙事行为,具有共同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千差万别、面目各异的故事,共同呈现某种潜在于其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并尝试予以平衡或提供想象性解决”[3]。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海角七号》的情节推演恰是如此。
一、在地与全球化的和解
“在地”是《海角七号》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同时也是影片进行身份认同建构的立足点,即以在地作为自我的身份定位,并试图据此形成稳定的归属感。影片中有许多细节都在标榜在地,例如,在招募乐队成员的报名现场,工作人员会要求查看报名者的身份证,从而保证乐队成员的在地身份。
在地身份在遭遇全球化强烈冲击的同时,也对其做出执意的抵抗。其中,代表会主席洪国荣(以下简称“代表”)是以在地对抗全球化的关键性人物。他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明显表现出对在地的坚持和对全球化的排斥。外国人来恒春海滩拍摄照片宣传春天呐喊演唱会,他不顾阻拦地径直从镜头前走过,并用不满的眼神盯着那些外来的“闯入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全球化的“侵入”进行抗议。后来,当饭店经理因为举办春呐演唱会需要申请沙滩使用权时,代表再次扮演了倔强的在地守卫者形象,与经理发生激烈争执。他认为所谓资源共享的地球村模式,其实存在着强势力量对弱势力量的不断挤压、收编或吞噬,而在恒春举办的春天呐喊演唱会其实就是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一个突出表现,正如片中人物所言:“每年我们恒春都在春天呐喊,我们在地人呢?有什么享受?有啦!在台下跟着吱吱叫,最大的福利,就是捡垃圾。”
代表会主席执意让本土乐队为春呐演唱会暖场,而不是请外援,其坚定程度近乎偏执,甚至不惜使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镇长最终同意用本地乐队来暖场。他一直以自己所坚持的方式,代表在地与全球化进行对抗。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暖场乐队终于成功组建并完成演出。这样一来,在地人在春天呐喊演唱会上终于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只是一支暖场乐团,但他们的演出却意味着在地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在地领域的成功保卫。换言之,在与全球化的对抗中,在地取得了某种象征性的胜利。
不仅如此,乐团的成功演出还包含着在地与全球化之间实现和解的意涵。乐团临时加唱《野玫瑰》时,日本歌手中孝介突然上台用日语和他们一起合唱,默契的合作赢得观众阵阵欢呼,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在地与全球化之间实现某种想象性和解的隐喻。
由此看来,影片以在地成功保卫自己的方式使得它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获得某种象征性的解决,进而完成两者之间的想象性和解。而这个由威胁到自保、由矛盾到和解的过程,其实也是标榜与建构在地身份的过程。
二、多元族群的和解
除了在地与全球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与和解之外,还有剧中不同人物身份所表现出的族群大和解。当下台湾社会颇为盛行闽南、客家、外省和原住民的“四大族群”论述。根据族群的比例来看,以闽南人最多(约70%),其次为客家人(约15%),再次为外省人(约13%),最后原住民族最少(不到2%)。[4]这四大族群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族群想象,是根据原乡地域和来台时期的不同划分出来的。“这种社会人群分类方式逐渐为台湾社会接受,成为至今十年来思考族群与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议题时的重要参考架构。”[5]
《海角七号》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多元混杂的身份,且具有比较明显的族群印记。以暖场乐队的成员为例,乐队的主唱阿嘉和鼓手水蛙是年轻的恒春在地人,摇铃手茂伯是经历过日本殖民时期的恒春在地人,他们都属于闽南人族群;贝斯手马拉桑是客家人;吉他手劳马属于原住民族群;键盘手大大是有日本血统的混血儿。显然,这是一支身份多元混杂的乐队。
不同的族群身份均具有自身的特色。阿嘉和水蛙以说闽南语为主;劳马演唱原住民歌曲一直佩戴着传统的原住民饰品,且很爱喝酒;茂伯平时都说闽南语,同时也可以自如地使用日语,他佩戴着妈祖挂饰,常常弹奏月琴;客家人马拉桑则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形象。这些具有不同族群身份的乐团成员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冲突。例如,乐队在平日排练时,成员之间常常会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常引发激烈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显然,乐队成员的身份是多元混杂的,他们在语言、形象和性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甚至发生矛盾冲突。但是,他们也拥有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一群拥有失意与梦想的小人物。男主人公阿嘉曾经在台北组乐团,追求音乐梦想,可是过了15年,依然没有成功,壮志未酬的他砸烂心爱的吉他,愤然离开台北回到家乡恒春,音乐和吉他成为他的一块伤疤,也是一个禁忌。原住民劳马遭遇了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他曾经在台北当警察,无暇顾及家庭,妻子的离家出走令他深受打击,一次工作中的意外让他在医院躺了半年,而后被调回家乡,只能强忍着情感和事业的变故,郁郁寡欢地当一名交警。客家青年马拉桑是推销小米酒的业务员,勤勤恳恳地工作,却常常碰壁受挫。水蛙是一家修车行的技师,对已婚的老板娘一往情深,也只能是充满苦涩的单恋。年事已高的茂伯是名邮差,也是被奉为“国宝级”的月琴师,却无人懂得欣赏,只好时常顾影自怜地弹着月琴。
不仅个人经历有相通之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可以代表在地在春天呐喊演唱会上成功演出。也就是说,无论身份如何多元混杂,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身份——“在地人”。
(友子买了原住民特色的项链饰品送给乐团的每一个人)
茂伯戴上项链之后,突然很担心地问道:我这有妈祖,会不会吵架?
原住民劳马立刻回答说:不会啦!大家都是一家人,怎么会吵架?
于是,影片所呈现的多元族群身份间的矛盾与差异,成为在地人家庭内部的小摩擦。经过不断磨合,这支曾经被视为“破铜烂铁”的在地乐团终于上演了一出令观众欢呼不已的暖场表演。可以说,通过展现具有不同族群身份的乐队成员之间的矛盾消解与互相包容,通过呈现不同族群身份为了保卫在地而齐心协力的景象,影片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族群之间的大和解。
三、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和解
与此同时,影片的多重和解还体现在历史层面,即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具体是指曾经的殖民地台湾与殖民主日本之间的历史和解。不难发现,《海角七号》中有许多关于日本的呈现,开场部分首先出现的是一段日语旁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友子,太阳已经完全没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经完全看不见台湾岛了,你还站在那里等我吗?
影片一开始便将时间拉回至日本结束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之时,画面上呈现的是一个日本人站在船上,依依不舍地遥望着渐行渐远的台湾岛。而后随着情节的推演,陆续有日本人物出场,除了战败离台的日本教师之外,还有在台湾读大学并留下来工作的友子和被邀请来台担任春呐演唱会嘉宾的中孝介。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并不负面甚至颇为受欢迎,中孝介抵达台湾时有众多歌迷在机场等候接机,还有歌迷特意跑到海滩周围遥望彩排,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连他的助手都有些惊讶。
并且,影片所呈现的在地日常生活中也存在日本元素,例如,茂伯平时会用月琴伴奏哼唱日语歌曲,还能熟练地说日语。更为重要的是,影片中有两段台日之间的爱情故事:曾经的日本籍男教师与台湾女学生之间被迫分离的悲情故事;如今的阿嘉与友子之间由冤家变恋人的浪漫故事。这两个爱情故事巧妙地互相交叉与呼应,不仅构成了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和重要推动力,也为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和解营造了充满悲情与浪漫的氛围。
一位日本籍男教师孤独地登上离开台湾的船,同时也被迫告别了他的台湾恋人——友子,而友子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她的恋人随着船只渐行渐远。美好的爱情没能敌得过政治的变迁,一对曾经近在咫尺的恋人就这样阔别天涯,留下了无限的惆怅和一辈子的思念。在这段爱情故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日本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被迫离开台湾的不舍与悲痛。对于剧中那位日本教师来说,台湾是其生活与成长的地方,甚至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家乡,离开台湾就意味着远走他乡,正如他在心中写到的那样:“十二月的海总是带着愤怒,我承受着耻辱和悔恨的臭味,陪同不安静地晃荡,不明白我到底是归乡,还是离乡!”并且,台湾不仅是他生活的地方,还是爱情的发生地,离开台湾就意味着割舍爱情。他在众人熟睡的甲板上反复低喃着:“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在看到日本人的悲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台湾人面对分离时的伤感与难舍。在那位与日本教师相恋的台湾学生眼中,日本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摆脱殖民统治的欢欣,而是带来了被迫与恋人永远分别的伤痛。
实际上,贯穿影片的那七封情书,不仅是在传达“最真最美的思念”,也是在透过爱情故事来诉说台湾被日本殖民的那段历史。
友子,请原谅我这个懦弱的男人,从来不敢承认我们两人的相爱,我甚至已经忘记,我是如何迷上那个不照规定理发而惹得我大发雷霆的女孩子了。友子,你固执不讲理,爱玩爱流行,我却如此受不住地迷恋你,只是好不容易你毕业了,我们却战败了。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
不难发现,影片所书写的日本殖民史存在一定程度的“美化”,关于日本的殖民记忆被幻化成一封封感人至深的情书,由日语旁白娓娓道来。在影片的叙述中,观众几乎看不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惯有的对立与排斥、冲突与纠葛,同时可以充分感受到双方面对历史洪流的无能为力与痛苦伤感,以及错综复杂又浓烈绵长的情感关系。对于那一段殖民历史,导演表示不想去解读或批判,也不想用政治来看历史,只希望用轻松的方式对待它。[6]
影片的结尾,阿嘉终于找到了七封情书的收件人,也为过去那段充满遗憾的台日恋找到了一份归属,而阿嘉自己则在当下开启另一段台日恋,终于说出“跟你走”或者“留下来”的深情告白,两段分别发生在过去和现在的台日之间的爱情都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圆满结局。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暖场表演的最后,阿嘉和中孝介分别用中文和日文合唱舒伯特的《野玫瑰》,用当下的合唱勾起过去的记忆,也用当下的合作来弥合曾经的伤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两段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是默契十足的合作演出,都是在以某种轻松的方式,隐喻着殖民者日本与被殖民者台湾在历史与现实中实现双重和解。
四、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除了社会、历史、族群和情感等层面之外,影片中还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影片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音乐是较为突出的一个面向。
影片中传统音乐的代表人物是茂伯,他很爱弹月琴,却无人欣赏,只好生气地抱怨道:“我弹琴要弹给谁听?现在什么时代了,还有人听我们这些老的弹琴?……像我这种国宝,就要出去让人欣赏,不是放在家里当神主牌。”可见传统的月琴在时代的发展潮流中所遭遇的冷落。当茂伯想拥有一个表演机会而要求加入暖场乐队时,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便进一步发生碰撞。这支由在地人组成的暖场乐队以流行音乐为主要表演形式,使用的是吉他、贝斯、架子鼓等现代乐器,茂伯所擅长的传统乐器月琴难以融入其中。于是,茂伯只好被迫改成练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贝斯,结果却因练习效果不佳而被乐队其他成员嫌弃。最后,他只好极不情愿地推荐本来就会弹贝斯的马拉桑,虽然很不服气为什么“会弹贝斯就那么嚣张”,可是为了能够在台上表演,茂伯也只能委曲求全地站在一旁用摇铃打节奏。
实际上,呈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正是为了最终的和解做铺垫。影片最终通过乐队临时加唱一曲的情节设置,使茂伯有机会拿起他的月琴,与其他乐器一起合作演出,以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融合的形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海角七号》到底是通过怎样的叙事策略进行身份认同建构的?又是如何实现对观众的感召进而达成认同共识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探究。
五、结语:多元和解式的身份建构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海角七号》以在地作为身份建构的立足点,将观众的视线引至台湾南部的恒春小镇,带领观众欣赏在地风貌,结识在地人物,感受在地风情。在这个恒春小镇里,虽然社会、族群、历史等诸多面向均存在种种差异、失衡或矛盾,如在地与全球化的对抗、多元族群之间的差异、曾经的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但是,影片在展现这些差异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让双方在影片中厮杀、决斗,而只是让他们碰撞出美丽又没有杀伤力的火花,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将这些看似势不两立的矛盾融合在一起,让它们和平共处、相辅相成。最终,一切伤痛都得到抚慰,一切矛盾冲突都获得和解,形成一片和谐共荣的美好景象。正如导演魏德圣所言:“人们总急着要去清理那个时代,毁掉旧的一切,重新来过。其实,新旧可以完美和解,不一定是对立的,应以更开阔的视野来接受新时代。我追求一种相互包容的新精神。”[7]
于是,在光影构筑的在地世界里,全球化与在地、多元族群、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传统与现代等多个层面实现了由混杂冲突到包容和解的过渡,在为观众提供“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8]的同时,也蕴含着借由战胜来自异己或自身的威胁来激发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在地身份并借此达成认同共识的深层动机,即在“在地”的召唤下凝聚在同是“在地人”的本土社会里,无论历史如何断裂,个体如何混杂,社会如何矛盾重重,最终都会实现想象性的和解。在接受与认可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通过和平共存、彼此包容、多元融合的逻辑建构出大家都是在地人的身份共识。
[参考文献]
[1] 2009年台湾电影年鉴[M].台北: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9:64.
[2] 郑秉泓.台湾电影爱与死[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58.
[3] [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42-69.
[4] 徐富珍,陈信木.蕃薯+芋头=台湾土豆?——台湾当前族群认同状况比较分析[A].台湾人口学会2004年年会暨“人口、家庭与国民健康政策回顾与展望”研讨会[C].2004:1-16.
[5] 萧阿勤.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典范——历史叙事、策略的本质主义与国家暴力[A].重建想象共同体——国家、族群、叙述[C].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4:220-221.
[6] 《海角七号》是如何炼成的[N].时代周报,2008-11-06.
[7] 常丽平.包容中的守望、追寻与迷失——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J].电影文学,2009(10).
[8]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