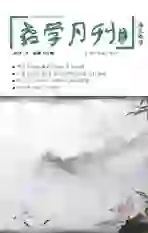老于的课堂
2016-06-12龚志民
龚志民
语文的秘密和魅力不在理念,而在于表现生活;不在理性的推演,而在形象演绎;不在模式,而在性灵飞扬。保持优秀的民族本真精神与培养创新能力一样,是人文的两翼,共同构成民族的张力。
老于在市里举行的公开课终于要进行了,上的是《荆轲刺秦王》。公开课放在深秋进行。秋主收,冬主藏,这是昭昭天道。文人所谓为天地立心,其实天地本来就有“心”,从不假手人立,返道而行就是立。天之心在民,在自然。人敬之、和之,即为立。
语文课堂应该是一幅会动的画,有了淋漓的元气,画面才会一片粲然。语文课独特的“味”得靠长期修炼、熏养。上一次公开课,就像棕熊夏天养成的一身膘,一次冬眠就耗得精瘦。真正的公开课就像严冬一样耗人,一次又一次地抽空语文老师的灵感、激情和体验。
大教室里一派肃穆,细看后面有点零乱,除了隐隐约约的耳语闲聊,还不断有从较远的学校赶来听课的人进进出出,坐在前面几排的学生却静悄悄的,完全没有平时下课那样的热闹气氛。已经习惯了的学生知道今天又要上公开课了,下课后也不闲聊和追逐打闹,一直悄无声息地待在教室,连零食也不吃,静候上课的铃声。冷落的秋日下,地面有点蔫蔫的,除了葵花向日倾,其他的花与叶都偃旗息鼓,默不作声。可以容纳几百人的阶梯教室偶尔有人进进出出,整个教室有点印象派绘画的味道:笔触细碎,意境悠远。
老于顶着一头似有似无的短发、踱着方步上了讲台,如见上宾,如承大祭。他似乎想用发型给观众传递潜台词——黔首浅草,亦能没马蹄;暴秦之恨,更行更远还生。老于觉得自己的发型也是课堂导入语的一部分。
“司马迁为什么为荆轲专门写一篇‘列传?”老于前一天留给学生一道思考题。换句话说,荆轲刺秦王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仅仅为了讲一个杀人未遂的故事或者偏爱荆轲让其青史留名吗?如果是为了留下精神的火种,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老于站上讲台,气聚神凝,先目光流转,再环视低垂。“在一个民族阴盛阳衰、元气衰微的时代,沐冠而猴之徒多,舍身求法、舍身证义者少,司马迁为华夏民族画出的这张原始基因图,让迷失者能够按图索骥,重塑民族脊梁。”老于把自己的思考作为探究课文的开场白。他删繁就简,先声夺人,把荆轲的历史背景和精神气质寥寥几笔画成一幅简笔画——我武维扬。
“1924年黄埔正门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嘉宾戾止,我武维扬。中国古代的镖局,都会在镖旗旁插上一面‘我武维扬旗帜,同学们知道‘我武维扬的意思和来历吗?”
“‘止和‘维是助词,黄埔正门对联的意思是:欢迎贤才俊杰,扬我华夏武威。”
老于轻点鼠标,屏幕上显示周武王《尚书·泰誓》中的句子:“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
老于略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中气十足,音调起伏,似空旷中衡阳孤雁的鸣叫,隐隐还夹杂着刚硬的刀剑碰撞的金属之声。老于渐渐感受到教室升起的腾腾热气,一缕缕一股股汇聚成团,仿佛盛夏原野蒸腾的阳焰,拉扯得眼前的许多人影有点变形。老于说:这是祖先的誓言,也曾是华夏的图腾和原始基因之一。说到这里,老于心底涌起声调变化多端的岭南古音、百越的古名,还有被五祖弘忍称为“獦獠”后终成圣贤的惠能,心中有几分莫名的向往和沧桑。
导语虽简,却不是快餐文化那种简,而是大道至简那种简。全场觉得老于似乎把他们带到了古代。老于没有对《尚书》周武王的誓词作过多解释,简笔画不需如工笔画那么纤毫毕现。工笔画流行的朝代,大多高颜值低武力,看看弱宋就知道。老于更喜欢泼墨大写意,空灵有气势。墨恣意地洒下去,浓淡润枯,再用折钗股屋漏痕的笔法就势落笔,便成了势。天清就点染些山居人家,云黑就添头逆风耕土的老牛,春和日丽时隐约涂一点清淡色彩,意与境就浑然天成了。武力也有境界高低之别,秦舞阳用拳头打败拳头,荆轲用灵魂驱赶灵魂。
老于点击鼠标,更新了屏幕上的画面,一枚国玺呈现在巨大的屏幕上: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大秦一统天下,华夏有了始皇帝和祖龙。从此一家独大,百家湮灭。
历史在幻灯片中飞驰,人物一个个粉墨登场。老于缓缓破题:“荆轲刺秦前,诸侯林立;荆轲刺秦后,天下一统。历经坎坷的和氏璧成了大秦国玺,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后又历尽辗转。王莽篡汉国玺曾破一角,现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突然一学生举手问道:“那荆轲算是悲剧英雄还是喜剧小丑?”这个问题本来打算放在结尾时再谈,学生昨天认真预习了文本,问题被提前了。
老于略一思索,回答说:“阳刚烈血与密室阴谋、纵横捭阖与攻城略地交相缠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秋功过,任人评说。但必须记住:是那些烈士、壮士、智士,甚至某些荒诞不经的思想和行动,共同构筑的九死不悔的华夏进取和奋争精神,共同托起我华夏飞龙在天。战争有胜与负,进取和奋争精神是没有胜与负的。荆轲是大写的人,一个追得秦王在秦宫乱窜的神勇之人。秦王扫六合,打诸侯的脸;他入秦廷,打了秦王的脸。”
老于停顿了一下,恍惚间自己变成了在茶坊中让人听得入神的说书人。讲台上放着老于随身携带的一杯专门用清冽井水泡的浓茶,老于把粉笔当作了醒木,轻轻在台上一拍,粉笔断成了两截。但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在说书,士不应该是说书人,即使落魄,也得是“奉旨填词”的柳永,务使技近乎道,不做媚俗之态。
下一张幻灯片,突然变成与课文内容毫不相干的两株大树,一株在原始森林恣意野性地怒长,另一株在悬崖的石缝间倒挂。倒挂在悬崖的大树,给老于一种刀欲劈、山若倾的感觉,老于浅发欲竖,不由得奋神振作。
课堂渐入佳境,老于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语调渐渐高昂:“这就是春秋那个时代。那时,华夏的青山正葱茏,满地青春,正当年华。仁爱,是圣贤们自用、自利,还没有从心里移到嘴上来卖萌讨巧。商鞅之法,王子与庶民同罪同功同爵;智与勇,是用来为国立功、为民谋生、为己立名的,开放、纳士、激赏军功,人才与财货自由流动。那个时代,对人才随时敞开大门,并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名词——客卿,专门授予非本国人而在本国任高级官员的人。荆轲等许多名垂青史的文臣武将都担任过不同诸侯国的客卿。那个时代,虽然动荡不安,却是讲政治规矩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教化生成忠孝礼义,熏育人心,由人心成就社会风气,言由衷,心役物。儒家还没有演化成董仲舒‘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那样的刻板教条和外在桎梏。”
再往下,老于嫌幻灯片静态而缺乏生命活力,人与电脑不能合一,干脆不再播放。他决定清唱。
“易水畔,太子丹带领一群全身着白衣冠的队列缓步而来,神情像进行某种仪式。高渐离陪在荆轲身旁,一起唱着不太整齐的旋律。远处的地上时见尸体,这些尸体死时好像没有痛苦,也没有激动,张开的嘴似乎在悲戚地吟唱着什么。荆轲好像看到了自己童年经历过的饥饿和流离,看到了无数赤身战士手拿长矛弓箭,义无反顾地冲锋,那些出窍的灵魂升上了天空,藏匿在头顶低沉暗淡的烟云里徘徊。唱声戛然而止,荆轲猜想这些灵魂会不会一路尾随自己去秦宫?所有人都随太子丹起身,纷纷半鞠躬,恭敬地说着什么,荆轲只听到自己的心脏还在随刚才的旋律收缩扩张,别的没心情听。荆轲知道自己是卫国人,血管里流淌的血,与周天子同基因。”
老于顿了一顿,惬意地伸展双臂扩了扩胸,以此来放松课堂也放松自己。听课者见惯了仪表堂堂、言之凿凿的课堂,对老于休闲的生活化肢体语言轻轻地会心一笑,凝重的教室气氛变得轻松了些。老于不屑于细讲接下来的荆轲“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这样的细节,龌龊行贿是历史的常态,却不是历史的主流,尽管这个细节差点害死了秦王。老于准备直接进入课文的高潮:刺秦。
应该“图穷而匕见”了。一种惊天下、主沉浮的意气从心底涌起,老于觉得浑身筋骨盘虬,如倒悬于岩石中生长的那棵曲敧纠结的树。老于情绪昂扬,更加觉得幻灯片太呆板,哪会有活人的精气神?
他站在讲台一侧,沉静地微笑,有点佞,还有点狠,如立身于秦王的几案旁。老于徐徐诵读“右手持匕首揕之”一句,语调尖锐而长,好像要用声音穿透秦王的胸膛。老于睁圆眼睛,退后两步,用厚实的腰背靠了一下投影屏幕旁边的墙壁,如虎蹭痒。教室里鸦雀无声,目光笼罩着老于。刹那间秦王绝袖绕柱而逃,老于轻轻一跃,如同跃过列国,从方方正正的井田一跃至长城之巅,秦王的太阿宝剑虽利,但芒在鞘锋在野,利有何用?虎狼之士,尽在殿下。十步之内,人可敌国。
老于把手中的粉笔头化作匕首,似怒熊奋臂,望空一掷,好像楚兵向阿房宫投火把,好像苍海公向秦王掷铁锥,粉笔头“啪”地击中教室右侧的墙壁,那面墙犹如秦殿的金丝楠木巨柱,发出清脆的回声。老于感觉到教室前前后后的听众,眼中、心中都腾腾地升起火苗。老于确信真正的华夏、炎黄、诸子百家,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墨子的非攻,也是先有利器热血,后言兼爱止战利天下。
“王负剑,王负剑”,从刀丛中一路杀过来的秦王猛然醒悟:在腰的剑是装饰,王者戏子都一样,在手的剑才是武器。他推剑至后背,如背负青天。荆轲立马左腿被斩断。老于一口气讲到这里,也不由得有点喘气。满教室的人也都微微张开了嘴,似乎缺氧造成了气短神浮。
荆轲感觉自己的血正在快速流尽,眼前幻影晃动,黑影重重,阶下那些诸侯卿大夫统统变成了黔首,天下的血流成了河,逆黄河而上,汇入咸阳,秦王被血色环绕,膨胀欲裂。
荆轲突然感到自己全身每一滴血都在跳跃欢唱,他知道自己即将在涅槃中解脱。如果灵光不昧,自己愿来世仍往生于华夏某处,与高渐离一起击筑吹箫舞剑踏雪。他依稀感觉到又不太可能。那幅摊放在秦王几案上的督亢地图,边界线在一点点消失,图中黄河之堤不断长高,督亢一点点放大成整个华夏,而后又快速缩小,飞入秦王的长袖中。荆轲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背靠柱子箕踞而坐,支撑起残躯,靠在金丝楠木巨柱上,大骂一声,如京剧的拖腔,绕梁不绝。他的额头亮晶晶的,回光返照,浑身不停冒着如珠如油的绝汗。但觉得自己已经尽兴,他下意识地飞出了匕首,无憾地完成了人生最后一个自选动作。黑黢黢的匕首在巨柱上停止了颤动,荆轲笑了。他依稀看见前朝的春秋五霸、屠夫白起,后世的腐儒董仲舒、掉光了胡子的司马迁,一个接一个从另一个世界轻飘飘地降临下来,共同凝成了一块无字碑。
黑色、红色一点点沉淀下去,刹那间荆轲眼前清亮如晨曦。黄河九曲,大地百川,变得清晰如掌纹。百川投一海,海不藏一滴而自用。天不藏私,海河晏清。
秦王目眩良久,大殿死一般地寂静,隐匿在秦王背后巨大屏风内的史官书记员,手一抖动,一滴浓墨掉在竹简上,又顺势流淌到地面,他就势写完了“燕”字下面的“火”,地面那滴墨像一点火星,他用脚踩踏了几下,墨迹入地三分,宛然若新。讲台上的老于,突然领悟到梁启超所膜拜的“少年中国”的真正内涵!老于灿烂地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像徐夫人匕首一样闪亮。
那是激情理智、大智大勇的中国!那时中国,墨子制作的鸟儿在天空飞三天不落,姑射山有神人入水火不浸,曲阜孔子奔走列国不倦;那时中国,百家著述于坊间闾巷流布,鬼谷子藏于深山课徒,老子袅袅紫气西出函谷关,预言“秦将大出于天下”。台下的听众被老于半实半虚的课文演绎惊得呆了,青春的眼睛闪动着无限神往。老于缓缓转过身,如出定的高僧,在黑板上写两句话作为结束语:苟中国之少年如斯,则少年之中国无疆。
下课铃响了,铃声是温婉的《大长今》主题曲,老于哼着这首曲子走出了教室。
(责任编辑:巫作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