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慧寺诸天塑像的后续调查与研究
2016-06-01邢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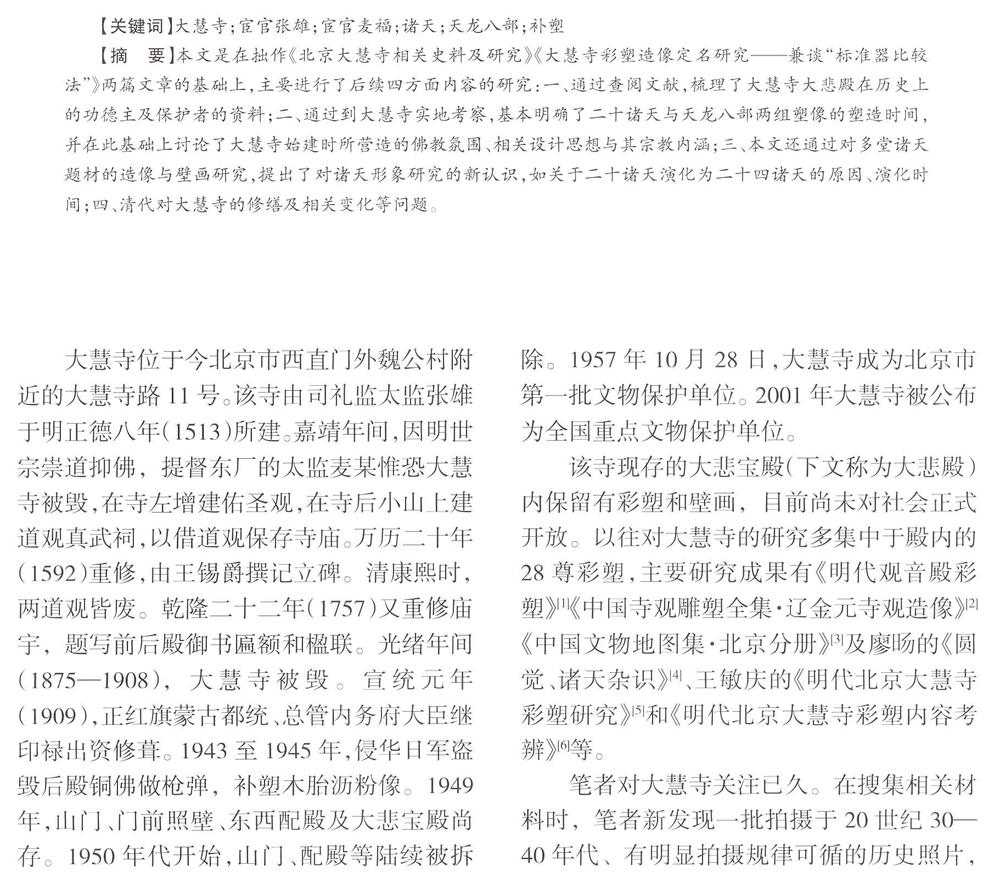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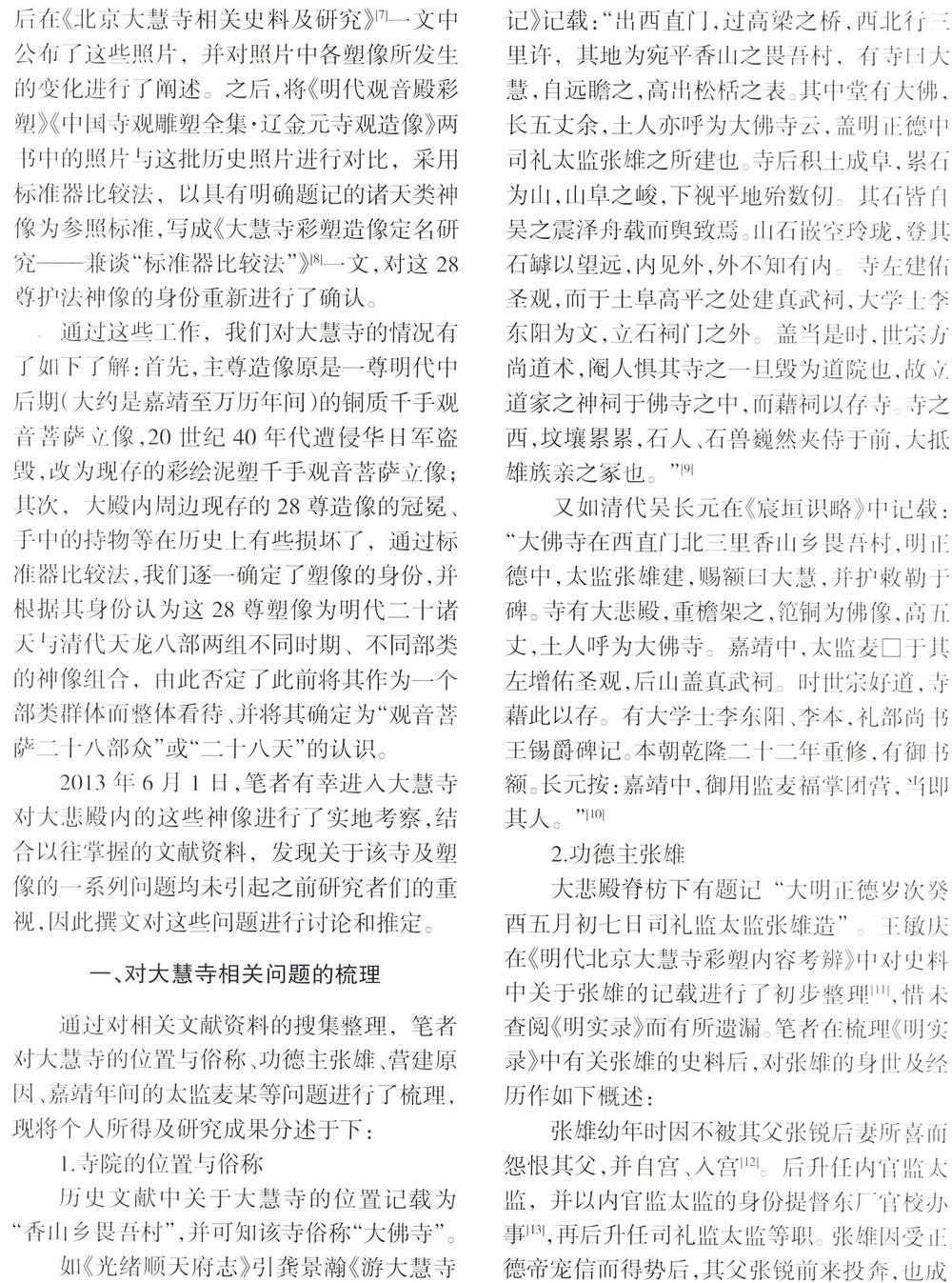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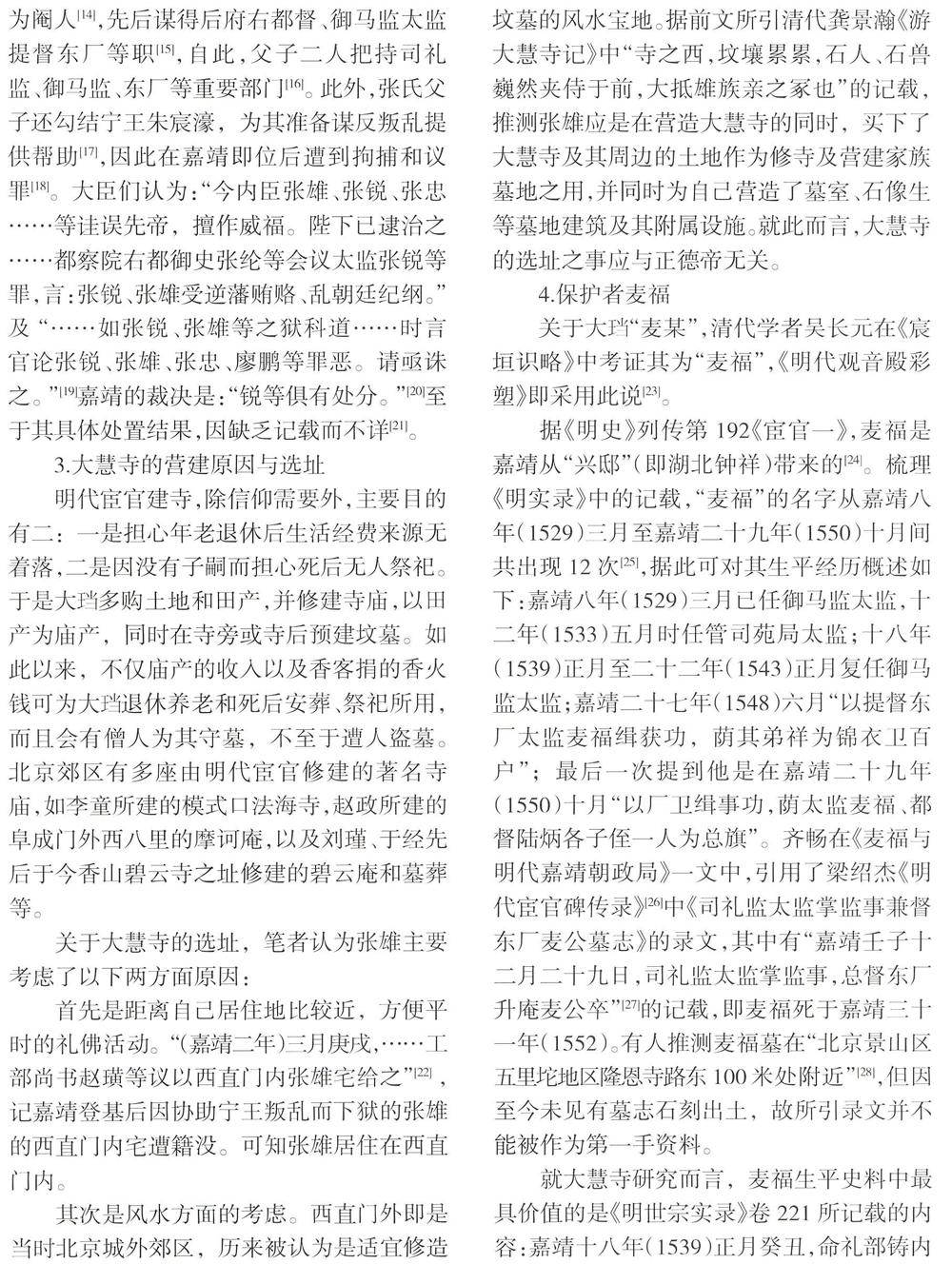
【摘 要】本文是在拙作《北京大慧寺相关史料及研究》《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后续四方面内容的研究:一、通过查阅文献,梳理了大慧寺大悲殿在历史上的功德主及保护者的资料;二、通过到大慧寺实地考察,基本明确了二十诸天与天龙八部两组塑像的塑造时间,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大慧寺始建时所营造的佛教氛围、相关设计思想与其宗教内涵;三、本文还通过对多堂诸天题材的造像与壁画研究,提出了对诸天形象研究的新认识,如关于二十诸天演化为二十四诸天的原因、演化时间;四、清代对大慧寺的修缮及相关变化等问题。
【关键词】大慧寺;宦官张雄;宦官麦福;诸天;天龙八部;补塑
大慧寺位于今北京市西直门外魏公村附近的大慧寺路11号。该寺由司礼监太监张雄于明正德八年(1513)所建。嘉靖年间,因明世宗崇道抑佛,提督东厂的太监麦某惟恐大慧寺被毁,在寺左增建佑圣观,在寺后小山上建道观真武祠,以借道观保存寺庙。万历二十年(1592)重修,由王锡爵撰记立碑。清康熙时,两道观皆废。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重修庙宇,题写前后殿御书匾额和楹联。光绪年间(1875—1908),大慧寺被毁。宣统元年(1909),正红旗蒙古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继印禄出资修葺。1943至1945年,侵华日军盗毁后殿铜佛做枪弹,补塑木胎沥粉像。1949年,山门、门前照壁、东西配殿及大悲宝殿尚存。1950年代开始,山门、配殿等陆续被拆除。1957年10月28日,大慧寺成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大慧寺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寺现存的大悲宝殿(下文称为大悲殿)内保留有彩塑和壁画,目前尚未对社会正式开放。以往对大慧寺的研究多集中于殿内的28尊彩塑,主要研究成果有《明代观音殿彩塑》[1]《中国寺观雕塑全集·辽金元寺观造像》[2]《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3]及廖的《圆觉、诸天杂识》[4]、王敏庆的《明代北京大慧寺彩塑研究》[5]和《明代北京大慧寺彩塑内容考辨》[6]等。
笔者对大慧寺关注已久。在搜集相关材料时,笔者新发现一批拍摄于20世纪30—40年代、有明显拍摄规律可循的历史照片,后在《北京大慧寺相关史料及研究》[7]一文中公布了这些照片,并对照片中各塑像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阐述。之后,将《明代观音殿彩塑》《中国寺观雕塑全集·辽金元寺观造像》两书中的照片与这批历史照片进行对比,采用标准器比较法,以具有明确题记的诸天类神像为参照标准,写成《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8]一文,对这28尊护法神像的身份重新进行了确认。
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对大慧寺的情况有了如下了解:首先,主尊造像原是一尊明代中后期(大约是嘉靖至万历年间)的铜质千手观音菩萨立像,20世纪40年代遭侵华日军盗毁,改为现存的彩绘泥塑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其次,大殿内周边现存的28尊造像的冠冕、手中的持物等在历史上有些损坏了,通过标准器比较法,我们逐一确定了塑像的身份,并根据其身份认为这28尊塑像为明代二十诸天与清代天龙八部两组不同时期、不同部类的神像组合,由此否定了此前将其作为一个部类群体而整体看待、并将其确定为“观音菩萨二十八部众”或“二十八天”的认识。
2013年6月1日,笔者有幸进入大慧寺对大悲殿内的这些神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以往掌握的文献资料,发现关于该寺及塑像的一系列问题均未引起之前研究者们的重视,因此撰文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推定。
一、对大慧寺相关问题的梳理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笔者对大慧寺的位置与俗称、功德主张雄、营建原因、嘉靖年间的太监麦某等问题进行了梳理,现将个人所得及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1.寺院的位置与俗称
历史文献中关于大慧寺的位置记载为“香山乡畏吾村”,并可知该寺俗称“大佛寺”。
如《光绪顺天府志》引龚景瀚《游大慧寺记》记载:“出西直门,过高梁之桥,西北行三里许,其地为宛平香山之畏吾村,有寺曰大慧,自远瞻之,高出松栝之表。其中堂有大佛,长五丈余,土人亦呼为大佛寺云,盖明正德中司礼太监张雄之所建也。寺后积土成阜,累石为山,山阜之峻,下视平地殆数仞。其石皆自吴之震泽舟载而舆致焉。山石嵌空玲珑,登其石罅以望远,内见外,外不知有内。寺左建佑圣观,而于土阜高平之处建真武祠,大学士李东阳为文,立石祠门之外。盖当是时,世宗方尚道术,阉人惧其寺之一旦毁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而藉祠以存寺。寺之西,坟壤累累,石人、石兽巍然夹侍于前,大抵雄族亲之冢也。”[9]
又如清代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记载:“大佛寺在西直门北三里香山乡畏吾村,明正德中,太监张雄建,赐额曰大慧,并护敕勒于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铜为佛像,高五丈,土人呼为大佛寺。嘉靖中,太监麦□于其左增佑圣观,后山盖真武祠。时世宗好道,寺藉此以存。有大学士李东阳、李本,礼部尚书王锡爵碑记。本朝乾隆二十二年重修,有御书额。长元按:嘉靖中,御用监麦福掌团营,当即其人。”[10]
2.功德主张雄
大悲殿脊枋下有题记“大明正德岁次癸酉五月初七日司礼监太监张雄造” 。王敏庆在《明代北京大慧寺彩塑内容考辨》中对史料中关于张雄的记载进行了初步整理[11],惜未查阅《明实录》而有所遗漏。笔者在梳理《明实录》中有关张雄的史料后,对张雄的身世及经历作如下概述:
张雄幼年时因不被其父张锐后妻所喜而怨恨其父,并自宫、入宫[12]。后升任内官监太监,并以内官监太监的身份提督东厂官校办事[13],再后升任司礼监太监等职。张雄因受正德帝宠信而得势后,其父张锐前来投奔,也成为阉人[14],先后谋得后府右都督、御马监太监提督东厂等职[15],自此,父子二人把持司礼监、御马监、东厂等重要部门[16]。此外,张氏父子还勾结宁王朱宸濠,为其准备谋反叛乱提供帮助[17],因此在嘉靖即位后遭到拘捕和议罪[18]。大臣们认为:“今内臣张雄、张锐、张忠……等诖误先帝,擅作威福。陛下已逮治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纶等会议太监张锐等罪,言:张锐、张雄受逆藩贿赂、乱朝廷纪纲。”及 “……如张锐、张雄等之狱科道……时言官论张锐、张雄、张忠、廖鹏等罪恶。请亟诛之。”[19]嘉靖的裁决是:“锐等俱有处分。”[20]至于其具体处置结果,因缺乏记载而不详[21]。
3.大慧寺的营建原因与选址
明代宦官建寺,除信仰需要外,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担心年老退休后生活经费来源无着落,二是因没有子嗣而担心死后无人祭祀。于是大多购土地和田产,并修建寺庙,以田产为庙产,同时在寺旁或寺后预建坟墓。如此以来,不仅庙产的收入以及香客捐的香火钱可为大退休养老和死后安葬、祭祀所用,而且会有僧人为其守墓,不至于遭人盗墓。北京郊区有多座由明代宦官修建的著名寺庙,如李童所建的模式口法海寺,赵政所建的阜成门外西八里的摩诃庵,以及刘瑾、于经先后于今香山碧云寺之址修建的碧云庵和墓葬等。
关于大慧寺的选址,笔者认为张雄主要考虑了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距离自己居住地比较近,方便平时的礼佛活动。“(嘉靖二年)三月庚戌,……工部尚书赵璜等议以西直门内张雄宅给之”[22] ,记嘉靖登基后因协助宁王叛乱而下狱的张雄的西直门内宅遭籍没。可知张雄居住在西直门内。
其次是风水方面的考虑。西直门外即是当时北京城外郊区,历来被认为是适宜修造坟墓的风水宝地。据前文所引清代龚景瀚《游大慧寺记》中“寺之西,坟壤累累,石人、石兽巍然夹侍于前,大抵雄族亲之冢也”的记载,推测张雄应是在营造大慧寺的同时,买下了大慧寺及其周边的土地作为修寺及营建家族墓地之用,并同时为自己营造了墓室、石像生等墓地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就此而言,大慧寺的选址之事应与正德帝无关。
4.保护者麦福
关于大“麦某”,清代学者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考证其为“麦福”,《明代观音殿彩塑》即采用此说[23]。
据《明史》列传第192《宦官一》,麦福是嘉靖从“兴邸”(即湖北钟祥)带来的[24]。梳理《明实录》中的记载,“麦福”的名字从嘉靖八年(1529)三月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月间共出现12次[25],据此可对其生平经历概述如下:嘉靖八年(1529)三月已任御马监太监,十二年(1533)五月时任管司苑局太监;十八年(1539)正月至二十二年(1543)正月复任御马监太监;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以提督东厂太监麦福缉获功,荫其弟祥为锦衣卫百户”;最后一次提到他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月“以厂卫缉事功,荫太监麦福、都督陆炳各子侄一人为总旗”。齐畅在《麦福与明代嘉靖朝政局》一文中,引用了梁绍杰《明代宦官碑传录》[26]中《司礼监太监掌监事兼督东厂麦公墓志》的录文,其中有“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司礼监太监掌监事,总督东厂升庵麦公卒”[27]的记载,即麦福死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有人推测麦福墓在“北京景山区五里坨地区隆恩寺路东100米处附近”[28],但因至今未见有墓志石刻出土,故所引录文并不能被作为第一手资料。
就大慧寺研究而言,麦福生平史料中最具价值的是《明世宗实录》卷221所记载的内容: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癸丑,命礼部铸内提督团营关防给御马监太监麦福[29]。“内提督团营”是嘉靖组建的太监武装,嘉靖十八年正月指派御马监太监麦福为统领,特命礼部铸造相关关防印信交给麦福作为身份的证明。而其中“提督团营”应该就是清代学者吴长元考定麦福营建佑圣观的依据。
此外,当时北京有民谣夸说其富有:“滕太监房,麦太监马,高太监金银似砖瓦。滕名祥,御用监。麦名福,掌团营。……”[30]
大慧寺在明代中后期成为高级宦官们的享堂和纪念堂。如明代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一书中记载:“凡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故后各有牌位,送外经厂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门外大佛寺供安。看厂监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绝也。”[31]这里的“西直门外大佛寺”即大慧寺——“因其中有铜铸‘佛像高五丈(约十五米),故当地人俗称之为大佛寺”[32] 。
二、大悲殿内塑像分析
——天龙八部和二十诸天
在考察过程中,经从事雕塑艺术工作及佛教美术研究的黄文智先生提醒,我们发现 天龙八部的8尊塑像在线条、神态等多方面与二十诸天的塑像有所不同:二十诸天造像比例匀称优美,应是明代作品,其塑造时间应是在正德八年(1513)至万历九年(1581)之间[33],可能更接近于前者;而天龙八部诸像造型臃肿,衣褶处理也不够好,与清代中期的风格更为接近。由此推知这28尊塑像的塑造时间是不同的,天龙八部8尊塑像应是清代中期作品。
另外,笔者注意到大悲殿主尊造像和28尊护法神塑像之下的台座为白石质 ,据笔者分析,时间应为清中期以后。笔者曾在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孔庙对其中的14座明、清御碑亭进行过调查,其台明部分所用材料的变化规律为:明代是用砖砌,清康熙、雍正年间用青石,乾隆之后采用白石制作。因此我们认为,在建筑装修中台座部分大规模使用白石的时间应是清代中期之后。可做佐证的是,北京地区始建于明代的石景山模式口法海寺、西山大觉寺等大殿内两侧的神像台座均为砖砌,而非石质。
同时,白石台座上雕刻的莲瓣、台座束腰部分雕刻的卡子花等浮雕图案都具备典型的清代风格特点[34],尤其是宽大、丰满的莲瓣特点与带乾隆年款的金铜造像上的莲瓣相一致[35],也可证明其是属于清代中期的作品。
白石台座的年代既确定为清代中期,则与大悲殿的题记为明正德年间不符,笔者认为这与清乾隆二十二年大慧寺重修工程[36] 有关。王敏庆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及的28尊塑像之间距离较近、显得空间关系紧张,且有两尊天王像头部所戴天冠装饰因抵触房梁而折断等情况[37],都应与此次修缮有关。
笔者推测,重修工程涉及大悲殿内塑像的内容包括:1.将 二十诸天 塑像的原有砖砌台座改为白石雕刻的台座,并对塑像进行移动;2.在移动塑像时,除帝释天像(西1)、大梵天像(东1)外,其余塑像全部移至大殿东西两侧的台座上,并因此造成诸天间距离较近、空间关系显得紧张;3.在大殿北侧墙壁下新塑天龙八部像。
经过此番调整,一方面大悲殿内的宗教氛围发生了变化:增补前的大悲殿内宗教氛围是通过表现观音菩萨及其护法诸天来表现其修行的道场——普陀落伽,同时宣扬大乘佛教菩萨行思想,以及诸天护国的思想。而增补后,大悲殿的造像群形成了以观音像为主尊,配以二十诸天及天龙八部像的组合。虽然这种组合关系于佛教经典中尚未找到明确记载,亦未见到现存的其他实例,但在许多佛经的开头与结尾处记述参加法会的信众时,经常同时提到诸天和天龙八部,故而推测大修后的大悲殿内泥塑组合表现的是观音菩萨为眷属讲法时的“佛会”道场场景,可在形式上激发前来礼佛信众的读经向善之心。另一方面,由于大悲殿的主尊是千手千眼观音像,其有眷属二十八部众,而在补充了天龙八部像后,因其数量暗合了“28”,且二十诸天与天龙八部诸神之名号有许多与二十八部众相同(含四天王的梵文音译名号),很容易使普通信众、甚或学识不够精深的僧人难以区分,而误认为是二十八部众。《明代观音殿彩塑》一书即出现了这种错误[38],白化文先生也持此观点[39]。
三、明代大慧寺诸天的仪轨道场推测
根据前述对天龙八部像塑造时间的推定,笔者认为,在清代中期之前,大悲殿内的造像组合应是主尊及二十诸天塑像的场景。如何理解这种组合关系呢?
诸天造像的供奉与《金光明经》的菩萨行和护国思想有关。诸天是指六道中的天道,是众多的天众,通称为诸天。《金光明经》中多次提到众多的天众,如功德天、大辩天等。隋代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根据《金光明经》的忏悔思想制定了《金光明忏法》,后代据此简略成《斋天科仪》,成为寺院中供奉诸天为护法神——供天的仪轨。“大致地说,五代至宋代的人,所供天数已经达到十六天以至二十天。……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癸巳,天台宗僧人行霆整理出《重编诸天传》,列位为二十诸天。为‘诸天立传后,慢慢地固定下来,‘诸天逐渐以二十天为准。”[40]
刘鹿鸣在《金光明经》前言中介绍大乘思想时指出,《金光明经》具有菩萨行思想:“其菩萨行的立足点是因地的凡夫菩萨愿行,具有一种重视当下现实行的意味。”[41]大慧寺大悲殿内主尊是观音菩萨像,观音菩萨在信众心目中就是佛教慈悲、救苦的神灵,其所救之苦多为祈祷者“当下”之苦,因此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菩萨行思想的代表。观音菩萨像与二十诸天像的组合应是加强表现菩萨救苦救难思想的。
《金光明经》中的诸天不仅有佛教护法的功能,而且有护国和民功能:“凡流传宣讲本经的国土都将得到诸天的拥护,可使国家饥馑、饥疫、战乱等一切不吉祥事消除,……”[42]这一点更符合功德主张雄作为皇帝近侍大而营建佛寺的思想初衷:塑造菩萨和诸天像,并祈请其帮助皇帝护国,从而达到讨好皇帝的目的。
笔者通过对现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明代诸天塑像的研究发现,诸天造像组合的数量从明初至正德年间都是20尊,如宣德时期北京大觉寺诸天塑像、正统时期北京石景山法海寺壁画。到嘉靖、万历时期吸收了紧那罗王、紫微大帝、东岳大帝和雷神等道教神灵而发展为24尊,如万历时期的北京千佛寺(清代称拈花寺)、山西长治观音堂等。这一数量的变化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明代汉地民间出现佛、道、儒三教合流的现象,例如河北邯郸北响堂山石窟中释迦佛像与老子像、孔子像共雕于同一窟龛中,在山西长治观音堂的彩塑中也有类似现象;另一方面是嘉靖帝崇道抑佛,佛教徒及信众为了保护佛教及寺院,主动吸收外来因素,以求自保。自保的手法有二:一是在佛教寺院中增建道教宫观,如北京大慧寺;二是主动吸收道教的神灵成为佛教护法神。笔者认为,佛教在吸收了最重要的三位道教神灵紫微大帝、东岳大帝与雷神后,诸天这一群体的数量为23位,呈奇数,不便于在殿堂内以对称的形式供奉,又将原天龙八部中的紧那罗增补进诸天行列——由于许多佛经在经文起首的“序分”及“流通分” 部分介绍会众时都提到该神参加法会,因此对于僧众而言可能更熟悉和易于接纳。这4尊神像增补的时间可能在嘉靖年间,所以到了万历朝,普通民众在思想中也就认可了诸天的数量为24尊。
综上,笔者认为大慧寺现存的大悲殿内28尊护法神像的塑造时间并不一致,其中属于二十诸天的20尊像是明代作品,当时的神像组合关系是观音菩萨与诸天;而属于天龙八部的8尊神像应是清代中期(乾隆年间)后增补的,当时还调整了原20尊塑像的安放位置,形成明代二十诸天与清代天龙八部的组合,并保持至今。由此可知,这样一堂历史久远、保存完整的汉传佛教供奉观音菩萨与二十诸天和天龙八部组合塑像的道场是十分珍贵和难得的,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都十分重要,更是我们研究明代佛教寺院、殿堂布局等内容的生动教材。
[1][23][38]王智敏,闪淑华.明代观音殿彩塑[M].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4.
[2]金维诺.中国寺观雕塑全集:辽金元寺观造像[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
[3]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23—224.
[4]金维诺.中国寺观壁画全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1—35.
[5][11][37]王敏庆.明代北京大慧寺彩塑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6][21][32][36]王敏庆.明代北京大慧寺彩塑内容考辨[J].文博:2010(2).
[7]邢鹏.北京大慧寺相关史料及研究[J].北京文博:2011(4).
[8][33]邢鹏.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2).
[9]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548—549.
[10]吴长元.宸垣识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81.
[12]a.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192宦官一:卷304[M].北京:中华书局,1974. b.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宫廷史料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1544.
[13][15]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宫廷史料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1543.
[14]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三)[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119.
[16]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85—86.
[17]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三)[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125.
[18][24]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192宦官一[M].卷304.北京:中华书局,1974:7795.
[19]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4[M/OL].http://wenxian.fanren8.com/06/03/42/5.htm.
[20]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8[M/OL].http://wenxian.fanren8.com/06/03/42/9.htm.
[22]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汇编(三)[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159.
[25]明实录[M/OL].http://wenxian.fanren8.com/06/03/42/.
[26]梁绍杰.明代宦官碑传录[M].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1997.
[27]齐畅.麦福与明代嘉靖朝政局[M]//明史研究:第13辑.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3:3—35.
[28]苗天娥.石景山区五里坨发现明代大太监墓[EB/OL].
http://www.bjww.gov.cn/2012/1-5/1325741800125.html.
[29]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宫廷史料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1548.
[30]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卷51[M]. 北京:中华书局,1958:641—642.
[31]刘若愚.酌中志:卷16[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99.
[34]李鼎霞,白化文.佛教造像手印[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66.
[35]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17.
[39][40]白化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诸天”的变化(上)[N].中国艺术报:2011-2-11(5).
[41][42]赖永海.金光明经[M].刘鹿鸣,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11-12.
〔责任编辑:谷丽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