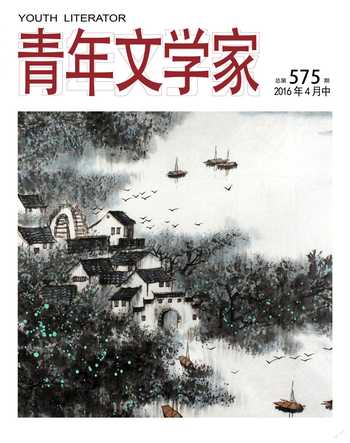《红楼梦新谈》的亚里士多德“诗人特质”摭谭
2016-05-30张贺婷
张贺婷
摘 要:吴宓先生的《红楼梦新谈》中,是吴宓将他对《红楼梦》的看法架构在西方文学理论上,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审视的了《红楼梦》这一不朽名著。其中,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总结出悲剧名著中主人公往往具有“诗人特质”。本文结合吴宓从亚里士多德悲剧观中的这一总结,分析《红楼梦》主人公林黛玉的“诗人特质”,探讨“诗人特质”这一观点的艺术价值,从而更深刻地了解《红楼梦》的悲剧之美。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红楼梦;诗人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一、亚里士多德悲剧观与“诗人特质”
在《红楼梦新谈》中,吴宓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将红楼梦架构于西方文学理论之上,与西方文学作品进行多重对比,并对《红楼梦》作出了高度评价。其中,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他将悲剧主角的特征概括为“诗人特质”。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主张中,将悲剧定义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认为,成功的悲剧主人公,主角往往出生于富贵之家,家资甚巨,且大多才华卓越,德行高尚,但是往往他们遭遇不幸,并非由于自身罪行,而大多处于自己的疏忽,或者本身天性中的不足
在这一讨论中,吴宓将悲剧观的主人公的特点抽象地总结为“诗人特质”,并以贾宝玉为例,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凡诗人率皆(一)富于想象力(imagination),(二)感情深挚,(三)而其察人阅世,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准则。凡具此者,皆宝玉也。”
吴宓指出,“诗人特质”首先的一个特征是富于想象力,“眼前实在之境界,终无满意之时,故常神游象外,造成种种幻境,浮泳其中以自适。”人活在现实世界中,其胸中丘壑往往不能得到满足,这时,主人公往往会依凭其丰富的想象力,在梦境中得到满足。贾宝玉出身,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极得宠爱,“栩栩于群芳之中,而终不快乐。在现实中看似生活悠游自在的他,在心灵上始终饱受着各种禁锢,难得自由,最终转而追寻梦境,以求心灵追求的满足。宝玉所游历太虚幻境,即是其想象力之佐证之一。
同时,具备“诗人特质”的人,往往具有丰富的感情。在脂砚斋的批语中,贾宝玉不仅位列情榜之首,更以“情不情”所称,不仅对有情人有情,对无情人也有情。宝玉自身的感情常常不自主流露,他的感情不仅体现在对林黛玉的“两心相照”,更体现在对周遭红楼女儿的呵护和尊重,甚至大观园的一草一木,他也要倾注自己的感情。
再次,“诗人特质”之人常以“艺术”为处世原则。“盖哲学家每斤斤于真伪之辨,道德家则力别善恶,至美术家,惟以妍媸美丑为上下去取之权衡。众所周知的贾宝玉“女儿观”中,他厌恶男子,认为男子乃“须眉浊物”,认为女儿才是“极清净”的富于灵气的所在。他对美有着很高的鉴赏水平,他的处世也往往以“美”为准则。在宁府中,他见《燃藜图》,“心中便有些不快。”别人提起“仕途经济”,便要发火。这些都是他颇具诗人特征的体现。
二、黛玉“诗人特质”的表征
《新谈》第二讲的第一句,就提到了”宝黛深情。黛玉亦一诗人。”吴宓认为黛玉“与宝玉性情根本契合,应为匹配,而黛玉卒不得为宝玉妇。可见林黛玉也同样具备了“诗人特质”。而黛玉“诗人特质”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清贵之家,名门之女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观点,大部分悲剧的主人公角“必生贵家,席丰履厚”。林黛玉父亲林如海,为姑苏探花巡盐的御史,不仅是前科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更是钦点的巡盐御史,集文职与实权于一身。而且,黛玉的家族并不是新兴的贵族,而是有着世袭传承的真正的名门世家。林家祖上袭列侯,至黛玉父亲已经五代。母亲贾敏是史老太君的独生女。她“通身的气派”首先就符合了亚里士多德悲剧主角的潜在条件,为她的“诗人特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姿容绝世,标致人物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对林黛玉形貌的这一段表述,广为人知,传诵不衰。贾宝玉初見黛玉,称之为“一个神仙似的妹妹。”贾宝玉杜撰的“香玉”的故事,称黛玉“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凤姐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也不是一味的奉承客气之语。二十五回薛蟠“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可见林黛玉的美貌,不仅“雅俗共赏”,更是贾府上下之所共见。第二十六回,作者侧面描写了黛玉的美貌,称之为“秉绝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一哭之下,连花花草草,宿鸟栖鸦也心惊难过。文中末了还附诗称黛玉“颦儿才貌世应希。”可见在作者笔下,黛玉绝对可以算作“绝美”。
3.扫眉之才,富于想象
想象力上,作者毫不吝惜地在全书的开头部分就点明了黛玉有“咏絮之才”,潇湘妃子的才华和想象力、创造力,元妃省亲,宝玉写诗乏术,黛玉在一旁替宝玉着急,“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应变神速,所写的《杏帘在望》让宝玉觉得“高过自己十倍。
她博览群书,从《四书》到诗词典故,作诗作词,联句谜语,无一不通,无一不会。第三十七回中,众人写菊花诗,众人皆悄然思索,“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等到众人都写完,黛玉 “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凹晶馆中黛湘联诗,她和湘云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虽凄清冷寂,但却是千古传唱的名联。
4.感情丰富,细腻深挚
吴宓评价黛玉“与宝玉性情根本契合,”黛玉本身是一个心思细腻,情感世界非常丰富的少女形象。她对宝玉,至情至性。”《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中,宝玉来看望黛玉,离开时外边下雨,宝玉不愿拿灯,黛玉道:“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黛玉对宝玉的关心,并不是一味地使小性子,拌嘴吵架,更多的时候,却是发自肺腑的温暖的感情流露,连宝玉摔跤这样的潜在危险,她也要念及。
宝玉挨打,众人皆哭。但各有不同。王夫人哭儿子不肖,袭人哭主子“不争气”,众人都散去了,唯独黛玉哭成泪人,只说了一句“你从今后都改了吧!”可见她的情感往往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表现方式上也往往热情而直接。
5.察人阅世,艺术为纲
薛宝钗为人端庄持重,对于女子的才华往往抱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自己觉得无才是德,一方面,她轻易不会展露才华。但黛玉纵横才气,将文学视为精神伴侣。第四十八回,指导香菱学写诗,指出写诗应当“不以词害意”,在奉行“女子无才”的社会,她却追求生活的艺术,创造的艺术,主动教香菱写诗。对待传统封建女德的束缚,她却有着自己的个性追求。
亚里士多德看来,拥有“诗人特质”的主人公,“即便是物,也会被悲剧诗人感觉为造成苦难的合谋者。她的以艺术为追求行事,从她对待自然中的一景一物,也有所体现。《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里,她惦记燕子不能顺利归巢,让紫鹃等燕子回来再放帘子,“看到桃花败落,她也拿起花锄,将花埋葬。”
三、悲剧主角“诗人特质”的多重意义
“诗人特质”是吴宓对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一种高度概括,是在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理念上的进行的一种升华。把握了悲剧主人公的“诗人特质”,对理解悲剧作品和作家创作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引发独特的精神感受
悲剧主角的“诗人特质”是悲剧精神之最集中体现,主角往往凝聚了人类的负面情感。根据《诗学》的观点“悲剧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这一点在中西方名著中有普遍体现。《茶花女》中的主人公玛格丽特,美貌惊人,纯洁善良,她虽沦落风尘,但却文雅端庄,保持着心灵的高贵纯洁和人格的独立完整,对自由的生活和平等纯真的爱情有着不懈的追求和真挚的向往。然而,最终她却不断遭到打击和屈辱,对生活的美好理想全部被打碎,香消玉殒,走向毁灭。《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德伯家中的苔丝》里的苔丝,也都是這一类具有“诗人特质” 的悲剧主人公。她们美好高尚的品质和他们痛苦流离的遭遇,集中引发了读者的对主人公的怜悯和丢对人生无常的恐惧,悲剧的力量激发阅读受众主体宣泄自身的负面情感,引发强烈共鸣,对全书的悲剧精神有了深刻理解。
从期待视野上来看,人们在阅读悲剧的时候,一般会抱着品味“失去和否定”的情绪,而不是期待从中获取愉悦和满足,“诗人特质”主人公悲剧的经历,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缺憾性”的快感。因为生命的无常之感并不是每个人一生中经常能遭遇的体验,而得不到的东西或者珍贵事物的遗失,能使人对它产生更深更长久的眷念。
同时,悲剧主人公“诗人特质”加强了阅读主体对主人公的喜爱和期待,因此当悲剧的重要情节发生时,悲剧便具有了喜剧通常不具备的启示作用。相当美好的事物,出其不意地遭遇不幸,坎坷悲痛,这种强烈的反差非常具有表现力地阐释了现实生活存在的不可避免也不可预料的不幸。比如人生的困顿、对命运的疑惑、失败的无奈感,偶然事件的不可抗性,人生种种,会直接引发接受主体悲从中来,思绪万千。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受众群体有了丰富的阅读体验,产生了深刻思想感悟。
2.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品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史性。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诗人特质”的主人公在读者的阅读接受过程中,所具有的美学价值也是多重而独特的。
正如利普斯曾说,“我已丧失者,我不仅目前依然能享受,并似乎更热烈地在享受。它业已丧失,它的价值尤其令我感动;这一点能加强悲痛,不过也能加强喜悦。假设失物仍然为我所有,也许我就很少甚或不会看重它。被打碎和毁灭的美丽,在绝望和缺憾中更能引发读者欣赏和对其美学价值的长久思索。《红楼梦》中,贾宝玉一生都无法与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结合,不断被命运和家族支配,黛玉泪尽而逝,宝玉“弱水三千,再无一瓢可饮。永远的失去所爱与他看上去拥有一切的“富贵豪奢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哀伤的美感给读者带来的震撼可以说是巨大的。《源氏物语》中的“光华公子”光源氏,拈花惹草无数,但他的至爱紫姬死去后,灵魂与肉欲在挣扎中激烈冲突,最终弃家出走,面壁向佛。美好与繁华最终归于冷寂,在审美上给了读者“鲜花着锦”与“青灯古佛”的两种境界穿插之感。人生的青春之美、爱情之美、肉体之美,与思维的空寂之美,人生的凋零之美,死亡之美,最终都融合在“诗人特质”中,散发出不朽的魅力。
因此,“诗人特质”不仅是吴宓对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一种高度概括,更是对世界文学中悲剧主人公的特质进行的一种总结。研究悲剧主人公的“诗人特质”,对鉴赏悲剧名作、感受悲剧内在的精神力量,汲取悲剧的美学精华,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振,关于《诗学》悲剧定义的理解问题——兼评吕新雨对《诗学》悲剧定义的分析[J].外国文学研究,1997(03).
[2]张平,亚里士多德 《诗学》 中的悲剧定义新探——以诗艺的标准为分析点[J]. 美与时代(下),2014(01).
[3]郭灵巧,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4]段启明,重读吴宓《红楼梦新谈》[J].红楼梦学刊,2008(05).
[5]沈治钧,吴宓红学讲座述略[J].红楼梦学刊,2008(05).
[6]饶芃子,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其它[J]. 文艺研究. 1996(01).